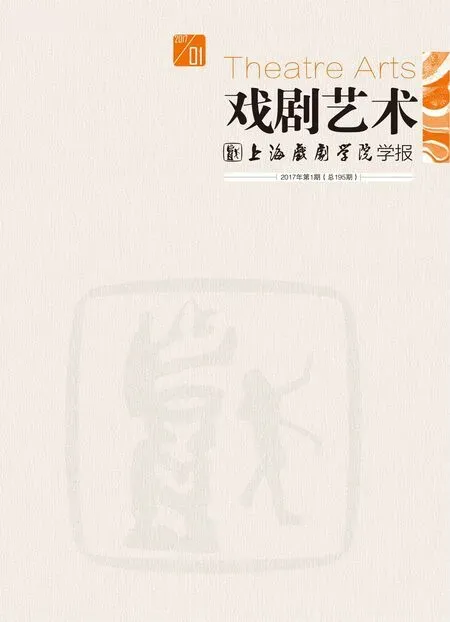误读与祛弊:胡适《易卜生主义》新解
■穆 杨
误读与祛弊:胡适《易卜生主义》新解
■穆 杨
胡适《易卜生主义》的本意不在于宣扬写实主义戏剧,而在于启蒙中国戏剧工作者的自由意志。虽然把《易卜生主义》纳入戏剧学的研究范畴有一点勉强,但胡适的启蒙思想仍然对中国戏剧的发展有着指导性的意义:只有当戏剧工作者首先是一个现代人时,我们才有可能确保戏剧作品的现代性,确保中国戏剧真正走进现代社会。《易卜生主义》一文在文化层面指引了中国戏剧的价值追求,即现代戏剧的自由意志和独立品格。
胡适 易卜生主义 启蒙 自由意志 现代戏剧
胡适是现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被誉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之父”。这样一位文化巨人,虽不是戏剧研究的专家,却以极严谨的态度,写出了对中国戏剧影响深远的《易卜生主义》。有关这篇文章的讨论在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被学界视为一个旧话题。但话题的新旧并不取决于讨论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话题本身的意义。虽然关于《易卜生主义》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其重要性和深刻性却未被充分地估量。在“五四”时期,它被视为戏剧界的精神旗帜;在“前三十年”,它又被当作思想界的“毒瘤”。进入21世纪后,胡适的启蒙戏剧观不但没有被重新正视,反而遭到了多方势力的合力“解构”。普遍的蒙昧主义、傲慢的文化民族主义,或冷眼或欢呼它的即将消亡。
回望百年中国戏剧的发展,《易卜生主义》所要呼唤的戏剧品格——戏剧的自由——仍然是当下戏剧界乃至思想界未能实现的目标。若不严肃对待,而任由其消亡,那结果只能是戏剧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破坏殆尽。因此,回到胡适的启蒙戏剧观,不但必要,而且迫切。这就决定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很值得重新加以解读。
要准确地把握和评价胡适的戏剧思想,就应对《易卜生主义》进行细致的分析。十分危险的是,启蒙的意义正在逐渐被淡忘,对胡适偏爱写实风格戏剧的指责取代了我们对其文主旨的辩证分析。我们似乎不能明白:其本质不在于宣扬一种写实主义的戏剧,而在于启蒙中国戏剧工作者的自由意志。
一、是胡适误读了易卜生,还是我们误读了胡适
学界对胡适戏剧思想的批评是从他误读易卜生开始的,理由是写实主义概括不了易卜生的全部戏剧。且不说易卜生早期有多年从事佳构剧的经验,单看他后期大量使用象征来拓宽剧情与剧意的那些作品,也远远超出了写实主义的范畴。故而,《易卜生主义》一文就需要为中国戏剧的“畸形”发展负一定的责任。易卜生是胡适为中国话剧精心挑选的大旗,但这面大旗却树立在胡适对写实主义的狭隘理解和极端偏好之上,虽然说倡导“社会问题剧”可能更符合“五四”时代精神,但也掩盖不了现代戏剧的丰富性在中国被压抑的客观事实。
然而,在批判《易卜生主义》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追问一个前提:我们解读《易卜生主义》的视角,是最合理的吗?除了读出胡适对易卜生的误读,我们还能读出什么?如果胡适撰写此文的目的主要不是指导大家如何写戏,那我们对胡适进行的戏剧学批评还有多大的意义?换句话说,是胡适误读了易卜生,还是我们误读了胡适?
虽然我们可以挑剔胡适的戏剧学知识,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要谈的重点,不是易卜生做戏的技法,而是易卜生做人的态度。胡适全文都没有从戏剧思潮、流派乃至发展史的角度介绍易卜生,而是展现易卜生做人做戏的精神力量,以及这种精神力量对社会的影响。胡适的醉翁之意是对国人进行思想的“启蒙”。
从“倡导启蒙运动”而非“普及写实戏剧”的角度解读《易卜生主义》,是否符合事实?我们先看胡适自己的解释。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3期上刊登了一封署名T.F.C的读者来信,他询问胡适为何要译介当时中国尚无能力扮演的易卜生的戏剧,胡适的回答是:
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1](P.199)。
如果担心这只是胡适事后的“自圆其说”,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文本出发,检验这番话的真伪。胡适把《易卜生主义》一文分为六个部分,其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清晰地表明了胡适的目的:他试图把抽象的“启蒙”概念,通过一个个“易卜生式”的实例,形象化地普及给读者。
胡适开宗名义地告诉我们,有一种人生态度,叫“说老实话”,它是中国社会最缺乏的人生态度。而“说老实话”,就是胡适启蒙工作的第一个关键词:批判精神。在文章第一部分,胡适用这种批判精神,从整体上检视了国人的“病根”,希望民众能有易卜生这样发现问题的理性。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脏官污官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点病都没有!……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2](P.111)。
如果中国社会能有易卜生的批判精神,那又会怎样呢?接下来,胡适便带领着读者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性检视。这一检视,便发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包括:家庭的罪恶(第二部分)、法律的缺陷、宗教的虚伪、道德的腐朽(第三部分)乃至社会对个人的奴役压迫(第四部分)。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觉察到,易卜生的戏剧作品并不是文章的主角,它们只是用来证明批判精神力量之强大的例证。用这样的批评精神,可以发现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未曾敢于正视的问题。
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社会里有许多陈腐的习惯,老朽的思想,极不堪的迷信,个人生在社会中,不能不受这些势力的影响……社会对于那班服从社会命令、维持陈旧迷信、传播腐败思想的人,一个一个的都有重赏……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处处和社会的风俗习惯反对,是该受重罚的。执行这种重罚的机关,便是“舆论”。便是大多数的“公论”。世间有一种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2](P.116-118)。
对社会进行一番批判性的检视之后,胡适笔锋一转,将全文的结尾(第六部分)落脚在与批判精神互为表里的第二个关键词——自由意志——之上。自由意志和批评精神的内在联系在于:个人只有拥有了自由意志,才可能真正拥有批判性的精神力量,也才可能在对自己负责任的同时,对社会担干系。
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世间只有奴隶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是不用担干系的。 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2](P.123)。
批判精神和自由意志在胡适的启蒙思想中,最终都指向一种现代人不同于过往的精神追求,这也是胡适启蒙的最终目标。因此,普及批判精神,呼唤自由意志,才是胡适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
从启蒙的角度解读《易卜生主义》不但符合事实,而且便于我们准确回应学界对胡适误读易卜生的批评。回应这个批评需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客观上,胡适介绍的易卜生戏剧是不完整的;二、误读者没能把握住胡适的启蒙思想。
我们当然可以单方面地挑剔胡适对于易卜生的“选择性”译介,但这种挑剔不但没有道理,而且没有意义。戏剧知识的丰富系统和去伪存真本就是学术研究的常态,以不完备为由去苛责前人是没有道理的。更何况胡适清晰地表明了他译介易卜生的意义不在其戏剧,而在其思想。如果我们对胡适的批评建立在我们自身对胡适的不理解上,那这种批评就是没有意义的。
反过来说,反思我们自身对胡适文章的误读,才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由于过多局限于“指实”意义的理解,我们把一个基本的逻辑关系颠倒了。《易卜生主义》一文所揭示的是:先有启蒙思想孕育了剧作家的批判精神,才有社会问题剧的产生和发达,社会问题剧是手段,而非目的——倘若我们理顺了这个逻辑,就不难想通——批判精神和自由意志,不是妨碍,而是有助于我们学习其他的戏剧流派,写出同样饱含人性深度的作品。
很多学者洞悉了这个道理,却在评价这个问题时,陷入了两难。他们一方面深知胡适的启蒙思想在今天仍有坚持的必要,但另一方面又碍于戏剧界对胡适文章的误读,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故不得不在坚持胡适的启蒙思想和考虑误读者接受心理的现实之间,无奈地做出一个折中的评价:一方面不否认胡适的误读,一方面又坚持着启蒙。
但在对胡适的评价上我们无须退让,因为只能在社会问题剧的意义上理解胡适的人,不但误解了胡适的本意,而且没有真正被启蒙。如果我们具备了启蒙所要求的理性,就不会分不清楚启蒙和戏剧在胡适文章中的辩证关系,更不会将胡适的思想概括为罔顾学理的“戏剧霸权”。恰恰相反,胡适在为个人自由意志立法的同时,也将中国戏剧的未来提升到了和世界戏剧潮流相一致的自由的高度。阐明这一点,我们就能体会到为什么《易卜生主义》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要严肃面对的“新”问题。
二、是胡适的启蒙错了,还是我们理解的启蒙错了
认识到《易卜生主义》一文的本质是在宣扬启蒙,或许并不困难,但对启蒙戏剧思想的接受,却不会因为误读的澄清就变得顺理成章。胡适将启蒙思想发挥到戏剧上,之所以会遭到抵抗,更大的原因还在于抵抗者对“启蒙”这一概念的陌生。这导致了“启蒙戏剧”总是和作为工具论的“政治戏剧”一起出现。比如傅谨先生在《陈独秀〈论戏曲〉与二十世纪中国戏曲之命运》一文中就持有这样的观念:
从梁启超、陈独秀一直到稍后的胡适、钱玄同等人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在视戏曲为社会改造工具这一点上,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深刻表现出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理论倾向,并且对戏曲界产生了长达百年之久的理论影响。在整个二十世纪的戏曲发展过程中,它的功过是非常复杂的[3](P.58-59)。
傅谨先生对这种“长达百年之久的理论影响”给予的评价并不高,恰恰相反,他呼吁的是一种回归艺术本体的“去政治化”戏曲。这里不得不说,傅谨先生对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戏剧理论的批判是相当深刻的,但他把胡适和梁启超、陈独秀的戏剧思想混为一谈,则表明了启蒙戏剧思想仍然没有被学界正确理解。
因此我们需要回顾“启蒙运动”的历史,借此辨析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陈独秀的《论戏曲》的本质不同,找到“启蒙”的真义。
从人类“启蒙运动”的历史进程看,它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才到达最后的终点①。
第一阶段是伏尔泰式的启蒙。这一阶段启蒙的特点是,启蒙者更多希望通过直接传输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开启民智,消除封建思想和宗教思想对人的约束。《百科全书》的编写就是一个例证。但实际的情形却是:当这些启蒙者在对民众进行教育时,不可避免地把民众视为乌合之众,而把自己视为绝对真理的化身。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悖论:启蒙者的本意是启迪民众的自由思想,但结果却让民众变成了自己思想的奴仆。启蒙变成了一种灌输。同样的道理,正如同傅谨先生所理解的那样,梁启超、陈独秀所教给戏剧界的是“戏剧服务社会”的理论方针以及“戏剧创作准则”的实践方法。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4](P.77)。
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一、宜多新编有益风化之戏。二、采用西法。三、不可演神仙鬼怪之戏。四、不可演淫戏。五、除富贵功名之俗套[5](P.52-55)。
这样一来,当启蒙者尝试破除落后的成见时,一种新的成见实际上取代了旧的成见。而自由之名也被工具之实置换,成为戏剧创作的宗旨。这也就无怪乎傅谨先生会认为,梁启超、陈独秀说到底是要把戏剧变成实践他们社会理想的工具,而非尊重戏剧艺术的独立性。倘若我们只在这个层面理解启蒙,那这样的戏剧思想,自然与后来“政治挂帅”的理论存在逻辑一致性。这一点,傅谨先生并没有说错。
然而,第一阶段只是启蒙的未完成状态,而不是启蒙的终点。它的终点在第二阶段康德式的启蒙。康德对启蒙的理解,正是针对第一阶段启蒙的悖论发难的。他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说了一段非常拗口的话: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口号[6](P.1)。
质言之,在康德式的启蒙阶段,启蒙者不以一种绝对真理的姿态出现,而是以一种鼓舞被启蒙者和启蒙者一起追求真理的姿态出现。而追求真理的内核,并不是灌输一种固定的学说、一种确定的规范、一种既定的世界观,而是获得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一种哲学生活。它的向度,就是启发民众敢于自己思维、自己判断、自己立法。以怀疑的眼光反思一切人的观念,这里的一切人包括自我本身;以批判的态度审视一切社会的现实,这里的一切社会包括优越于过往的当下。康德式启蒙的精神实质和胡适在《易卜生主义》里向我们揭示的主旨,如出一辙。
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哪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十年前用补药,十年后或者须用泻药了;十年前用凉药,十年后或者须用热药了。……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渚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2](P.124)。
胡适借易卜生之口说出的“白血轮精神”,就是康德所谓的“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也就是对自由的追求。辩明了启蒙的真义,我们便能清晰地区分胡适和梁启超、陈独秀的不同。梁、陈戏剧思想其实质是“文以载道”的近代翻版,只不过梁启超、陈独秀所要宣扬的“道”是相对于封建旧道德的一种新道德。他们的建议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摆脱封建愚昧,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相比之下,胡适所希望的新剧,却超越了宣传新道德这个有局限性的功利层面,他的价值也绝不会因时代的变迁,就显示出历史的局限性。胡适通过普及批判精神,把未来新剧的品格,提升到了一种独立的自由意志之上。启蒙戏剧和政治戏剧的根本不同也就在这里:政治戏剧总是服膺于具体的政治主张,即使这些政治主张有可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但启蒙戏剧却跳出了这种历史局限性,因为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自由。
因此,胡适的启蒙思想和“去政治化”在宗旨上不但不矛盾,相反,启蒙戏剧更有一种毫不妥协的抗争性。这种抗争性在政治奴役戏剧的社会中,并不是“去政治化”戏剧的盟友,而是它们存在的前提。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没有抗争力量的社会中,纯艺术的构想能成为现实。
胡适所希望戏剧承担的社会功能,就是唤起民众睁眼看社会、大胆讲实话的勇气和能力。这对于承担了不少封建愚民思想的晚清戏曲而言,这样的启蒙戏剧思想所起到的作用是振聋发聩的。它的社会功能,又怎么是梁启超、陈独秀狭隘的功利目的支配下的戏曲观所能比拟的呢?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今天的戏曲界、乃至整个戏剧界,仍然不能用自己的脑子创作,非要在“听话”的状态下才敢动笔,那胡适希望戏剧所能承担的社会功能,仍然需要被我们这个时代重新提及。
三、是胡适政治化了戏剧,还是我们政治化了胡适
辨析了启蒙戏剧和政治戏剧的区别,自然也就能澄清戏剧界一个长达百年的理论谬误:不是胡适政治化了戏剧,而是我们政治化了胡适。但我们仍要继续追问: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政治化地理解胡适、理解戏剧、理解启蒙?这个问题,是我们重读《易卜生主义》要回答的根本问题。它立足原文,指向当下。
要理解胡适并没有政治化戏剧,还是要回到《易卜生主义》。在文章的第五部分,胡适插入了一段易卜生政治主张的介绍。这部分初读起来感觉突兀,可一旦我们理解了胡适启蒙的真义,便可意识到,这部分不但必要,而且对我们理解启蒙和政治的关系有着持续的启示意义。
胡适借易卜生的思想,阐明了现代人对于政治的基本态度。他认为以批判精神和自由意志为宗旨的启蒙精神,最终并不会把主体导向消极的无政府主义,而是以一种并不狭隘的国家主义,生活在现实政治中。换言之,如果说封建社会中,个人是政治的奴仆,一切生活都要匍匐在政治的“指挥棒”下,那么现代人则调转了这一关系,现代人是政治的主人。
易卜生的纯粹无政府主义,后来渐渐的改变了。他亲自看见巴黎“市民政府”(Commune)的完全失败(1871),便把他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热心减了许多……但是他终究不曾加入政党……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一八八八年,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道:知识思想略为发达的人,对于旧式的国家观念,总不满意。我们不能以为有了我们所属的政治团体便足够了[2](P.120-121)。
这便是现代人需要政治,同时也需要批判政治的生活状态。明白这一点,自然也就更加可以确信,胡适撰文的目的,不在于普及写实主义戏剧,而在于启蒙包括戏剧工作者在内的所有人。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思想上还是未能全然摆脱专制主义教育的影响,因此政治化地解读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仍然是我们思想中难以摆脱的枷锁。这套枷锁,无疑也把持着我们的戏剧观。“泛政治化”像一个幽灵,让我们的理智长久地处于沉睡之中。
学界并非没有学者严正地指出这个问题,董健先生曾多次撰文论述启蒙和政治的区别,他在《现代启蒙精神与中国话剧百年》一文中说:
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些主张戏剧“去政治化”的人,总是在否定和“解构”启蒙,因为他们只看到启蒙和政治的联系,而完全看不到两者的区别。“启蒙精神”和“战斗性”的关系,就像“启蒙”和“政治”的关系一样,二者即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不处在一个文化层面上。启蒙运动有可能变成政治运动,政治运动也会借助于启蒙的张力以成其事。但是开明、进步、代表民意的民主政治与启蒙是友,黑暗、反动、违背民意的专制政治与启蒙是敌,后者最怕启蒙,故反启蒙是其统治术中的重要一环。所以,笼统地讲“战斗性”,就分不清这两种政治,也就分不清真启蒙与假启蒙[7](P.112)。
董健先生回答这个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将良善政治的戏剧称为真启蒙戏剧,恶劣政治的戏剧称为假启蒙戏剧,并且他一再强调,即使是良善政治的戏剧,戏剧和政治也只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而非尊卑的雇佣关系。他的论述把握住了启蒙戏剧和政治戏剧的本质区别。
但这种论述却在现实中遭遇了接受的困境:对于已然理解启蒙意义的人而言,它一针见血;但对于反对启蒙的人而言,它可被反驳。在反对者看来,启蒙无所谓真假,只有好坏,而判断启蒙好坏的标准由政治权威把持。在不接受启蒙自有其独立价值的前提下,启蒙只是政治的一套话语策略。需要的时候,启蒙就是进步的;不需要的时候,则是反动的。这套逻辑,对于长期接受专制主义教育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对于无力辨别政治好坏的人来说,是不加反思的;对于甘愿选择相信政治一定正确的人来说,是最好不过的;对于明哲保身远离政治的人来说,是任其鼓吹的。当这些或反对、或愚昧、或功利、或麻木的力量纠结在一起时,启蒙的价值便被扼杀。这就是胡适的启蒙戏剧思想一直被误解为政治工具论的根本原因。
因此,我认为不必将启蒙和政治相联系。虽然从启蒙运动发展的历史看,启发一套良善的政治主张和启发彻底的批判精神,都曾共享过启蒙之“名”,这是尊重历史的事实判断,也是董健先生将良善政治的戏剧和启蒙戏剧相联系的理论依据。但从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启发新的政治主张并不是启蒙的终点,只是启蒙的一种未完成状态。启蒙的终点在于拥有批判的精神和自由的灵魂,而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前者是否一定会走向后者,仍值得怀疑。因此,如果要给启蒙戏剧下一个价值判断,那么结论是:良善政治下的戏剧,还不能称为启蒙戏剧,因为它还不具备启蒙之“实”。
如果有足够彻底的批判精神,我们甚至可以怀疑康德所谓的“人类从不成熟的状态走出”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一旦我们对这个启蒙设定的终点始终表现出现实的担忧,那启蒙之于政治的区别将更加明确:启蒙和政治之间只存在检视和被检视的关系。启蒙是现代人经历了发现理性、坚持理性和反思理性三个阶段后,内化而成的一种精神气质。政治在这种精神气质面前,无论进步还是反动,都是自由意志批判的对象。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易卜生主义》一文的当代意义:胡适的启蒙思想对于当代人的生活仍然有着指导性的意义,它是我们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必经阶段。并且,胡适启蒙思想还是戏剧现代品格得以获得的前提,它是现代戏剧的价值支柱。启蒙思想和艺术价值之间并不是“互损”关系,正相反,在通往现代的道路上,启蒙决定了戏剧工作者是否现代,审美决定了戏剧艺术是否现代。而只有当戏剧工作者首先是一个现代人时,我们才有可能走出中国戏剧的现代化之路。
结 语
严格意义上讲,把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纳入戏剧学研究的范畴有一点勉强,因为这篇文章本身不是一篇严谨探讨戏剧艺术的论文。它虽然对易卜生的写实戏剧有所涉及,可其本质还在于宣扬启蒙思想。但20世纪的中国戏剧,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却都无法回避它的影响。这不仅在于它催生了中国现代戏剧,更在于它的思想光辉照亮了中国戏剧工作者的灵魂。如果我们能放下偏见,肯定其在确立批判精神和自由意志上的贡献,那中国戏剧亦可以从这里找到它现代品质的根基。这一根基便是我们今天仍在不断追求的艺术自由。
注 释:
① 启蒙的两个阶段说:参见李秋零教授的论文《康德与启蒙运动》,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第65-70页。
[1]胡适.答 T.F.C.[A].耿云志.胡适书信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胡适.易卜生主义[A].洪治纲.胡适经典文存[C].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3]傅谨.陈独秀《论戏曲》与二十世纪中国戏曲之命运[J].文艺研究,1997(5).
[4]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洪治纲.梁启超经典文存[C].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5]陈独秀.论戏曲[A].阿英.晚清文学丛钞戏剧小说卷[C].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6]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A].江怡.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7]董健.现代启蒙精神与中国话剧百年[A].启蒙、文学与戏剧[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Title:Misreading and Disenchantment:A New Analysis of Hu Shi's Ibsenism
Author:Mu Yang
The essence of Hu Shi’s Ibsenism is not advocating the Realistic Drama,but evoking the free will of Chinese dramatists.Although it is a little unreasonable to classify Hu Shi’s Ibsenism into the research category of Drama Studies,his enlightenment for Chinese drama is still having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s.Only the dramatist as a modern person with free will,possesses the possibility of modernizing Chinese drama.Hu Shi’s Ibsenism establishes the modernity of Chinese drama in the cultural level.
Hu Shi; Ibsenism; enlightenment; free will; modern drama
J80
A
0257-943X(2017)01-0055-09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王忠祥教授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