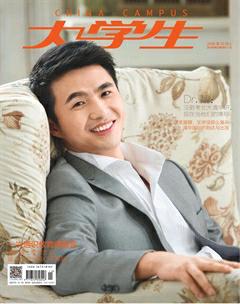李敬泽、麦家对谈:诺奖提醒,文学没那么复杂
孙云帆 王新娟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花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官方授奖词中写道,鲍勃·迪伦在伟大的美国民谣传统中创造出新的诗歌意境。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有人认为这是诺奖颁发的一次突破,也有人气愤地表示把诺奖颁发给歌手是一件任性的事儿。
10月25日,著名文学家麦家邀请好友李敬泽在清华大学建馆报告厅进行了一场“悦读咖 | 谈文学,不止理想——国人心中的诺奖”为主题的文学对谈。
回到文学本源
李敬泽:
说起鲍勃·迪伦,我马上就回忆起我年轻的时候,买了盒磁带,曾经反复地听鲍勃·迪伦的歌。所以诺贝尔奖比较符合我们老文艺青年、老文学人的口味。我不知道所说的“哗然”是指的什么,但是我想,如果我是瑞典文学院的那些老先生,我需要隔一段时间就要调配一下,我隔一段时间就要恢复一下,或者是打破你们的预期,恢复一下我的活力,不让你们说我是有规则的。
因为说到底,文学,在我们现代社会中,有一种倾向,就是越来越专门化,越来越变得高大上或者是高精尖。某种程度上讲,也意味着他越来越失去活力,失去它作为一个野孩子那样奔放的精神。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怕跟一帮搞文学的人谈文学,为什么呢?大家都博览群书,一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规矩那么多,段子那么多,套路那么深,你就觉得永远自己读书太少。但是话又讲回来了,难道文学仅仅是这样吗?时间长了,我们需要回到文学的本源。
麦家:
诺贝尔文学奖,一说到它,我首先想到三个人:第一个人,是莫言。他代表中国第一次拿到了瞩目的文学奖,所以一谈到文学奖,我就想到了莫言。莫言不但是给自己,也给我们中国文学,甚至给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拿了我们一直期望得到的那个奖。
第二个人是谁呢?我想到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文学当中的巨匠,站在最高峰的人,他没有得。我觉得他应该是得诺奖的,但是他没有得。还有一个人在我看来也是应该得,但是他没有得,是谁呢?卡夫卡。这里我想起的第三个人我刚才说了,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文学最高的那个人,而卡夫卡是现代主义文学最初的那个人。我觉得不论是诗歌、文学,还是艺术,它的源头在哪里,或者说集中的高峰在哪里,就是集中在卡夫卡身上。这么一个象征着、暗示着现代主义文学朝气蓬勃的人也没有得奖,这也是让我感到很遗憾的地方。
我并不是说诺奖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诺奖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有问题,那是人的问题。只要是人颁这个奖,或者说这个奖是颁给人的,总是不公平,没有公平。这个世界要说是公平的,我觉得首先是不公平的。有的人含着金钥匙来到这个世界,有的人是身无分文来到世界。但是世界又是公平的,含着金钥匙的人照样生病,照样经历失恋,最后也是这么老去。他一天是24小时,我的一天也是24小时,从这个意义来说,世界是公平。所以不要追求完全的公平。诺奖也是这样,公平公正。我觉得他大体是公平的,大体也是公正的,没有绝对,没有完美,只要是人做的事总是有遗憾,总是有缺陷,有缺陷、不完美才是我们人做的事。
即使有这么多的缺陷与遗憾,没有哪个世界哪个组织可以替换诺奖。它呼唤的东西,它召唤的东西,它激发了很多作家的创造力,也激发了很多大众对文学的向往,对文学的喜爱。我觉得这也是诺奖存在至今的价值,包括以后的价值。
本源是简单、直接的
麦家:
我觉得文学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想接触它和不想接触它,它都存在于我们身边,陪伴着我们一路往前。现在很多人觉得文学是作家或者是中文系的事,那真的不是这样。文学是大家的事情,文学就是生活,我们从出生开始,文学一直在陪伴着我们。我一直觉得文学就像月光,它好像是没用的,其实他用处很大。我们可以想象,一生当中抽掉这些故事:你曾经看过的文学书籍,写过的情书……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抽掉了,我们的人生会非常寡淡无趣。
好像看起来月光是没用的,太阳光才有用,没有太阳,万物就无法存在。好像没有月光没关系,但是如果没有月光,我们人类会少掉多少的情思,多少的思念。这个世界有趣、审美的层面会削弱很多很多。我们的生活完全是为了硬邦邦的要一些利益吗?我想肯定不是这样的。
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故事,他都要虚实相兼,有虚的一面,有实的一面。文学就是让我们太坚硬、太硬邦邦的生活虚化了。有了这个虚化,生活就变得更加有弹性,你的内心也会变得更加温暖。我想,内心的温暖、丰富、生动,比身外的身份重要的多得多。
李敬泽:
文学的本源是什么呢?实际上刚才老麦谈到月光,非常单纯的东西。文学曾经在本源上是非常简单、非常直接的东西,不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东西。所以现在,2016年,瑞典文学院的老爷子们忽然要调皮一下,说我们给鲍勃·迪伦!给鲍勃·迪伦凭什么呢?瑞典文学院特别谈到说,鲍勃·迪伦让我们想起了荷马和古代游吟诗人。荷马也好,游吟诗人也好,他们都是站在文学的本源上。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理论,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没有那么多套路。他们就是从远方走来,站在你们面前,上边有天,下边有地,对着你们,对着我们所有的人来歌唱,这是文学的本源。
这不光西方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世界上都是这样来的。这某种意义上称得上是文学的力量,其实这种力量也是文学至今还有力量的根子所在。
所以我特别特别觉得在这个意义上,瑞典文学院是做得好的,提醒我们一下说文学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高大上,就是那样不衫不履的摇滚歌手站在这里,对着这个世界的怒吼和歌唱,他就是文学。
诺奖寻找的理想
李敬泽:
“理想”二字,肯定是两个好字。但是何谓理想?可能都需要我们自己在生命中慢慢去找,去慢慢地确认。诺贝尔对于诺贝尔奖写了五条遗嘱,第一条是要对全人类有意义,最后一条专门说要奖给什么呢?要奖给有理想倾向的作品。
“理想”二字就出来了。“理想”二字可把瑞典文学院的老先生给难住了,关于文学作品中到底什么算是有理想?这个100多年来反复争论。诺贝尔文学奖早期的时候,你要想到当时是一帮19世纪初的老先生,他们对理想的认识是近乎于什么呢?理想是什么?理想是符合我的习惯,符合我的通行规则。早期的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认识,解释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在早期来说,托尔斯泰肯定是不理想的,包括就在瑞典旁边,当时有一个人,现在看也是伟大的大师——易卜生,也不理想。
后来渐渐的,到了1930年代、1940年代,特别是二战之后,人们对理想的理解有了新的认识,这个理想包含着对于人类生活,对于自己的一种可能性的追求。或者说我更愿意找一个词,与其我们说是“可能性”,倒不如说是“不可能性”,就是说有一些事情你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来试一试。要用上那句俗话,要是万一就行了呢?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是现代主义,特别是二战之后,我们对于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关于理想的新象征。其实人生也是同样如此,我想人生中所谓的理想,大概也是这么一个意思。
麦家:
分享文学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分享理想。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文学是理想一半的代名词。这个时代大家都在挣钱,羞于谈什么理想,也很少谈论文学。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对的想法。至少是对人生态度、处世态度,都是有一点偏颇的。所以我想利用我个人的一点点地位也好,影响力也好,竭尽所能,想传播我对文学的一些看法,我也希望和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分享文学的成果,文学还是安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