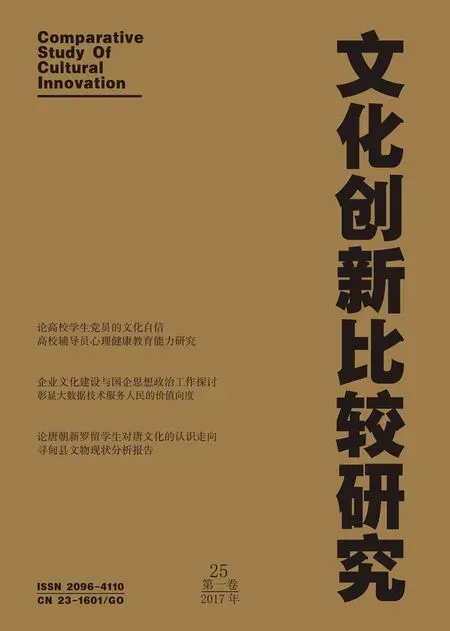罪恶的移情:领袖与替罪羊
俞媛媛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91)
贝克尔的《拒斥死亡》中告诉我们:我们身处的世界,是令人恐惧的。而我们人类行为的基本需要就是控制基本焦虑的需要,是拒斥死亡的需要。我们若要去坦然地面对死亡,就必须得坦然地面对内心深处如影如形的恐惧、害怕、焦虑……于是,人们试图把自己塑造成英雄。如果不能成为英雄,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领袖。
1 领袖和群众的共生性
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各种类型的“领袖”。贝克尔指出,在我们人类的全部历史里,大量的民众总地跟随着“领袖”。虽然当“领袖”的魔咒消失的时候,我们会震惊于我们竟然曾经臣服于他的魔力之下。可是,我们毕竟曾经受过符咒的蛊惑。
用贝克尔的话说,这是一种“迷惑力”,在领袖的身上,往往都拥有这种象征权力的迷惑力:“这样的人身上似乎有某种东西放射出来,把我们融进他的灵光之中。”奥登称此为“自恋人格”的迷惑效果,荣格则倾向于称其为“MANA”(魔力)人格。
然而,我们将这种具有魔力的灵光剥除了之后,所谓的“迷惑力”“魔力”,究竟它的本原是什么呢?
根据雷德尔的说法,“群体利用领袖来获得各种开脱,缓和冲突,获取爱情,甚至把领袖作为对立面——即各种攻击和憎恨的目标”。拜昂认为,“领袖是群体的被造物,恰如群体是领袖的被造物。”我们可以用卡内蒂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种“利用”:人们把自己想象成领袖的暂时的牺牲品。他们越是屈服于领袖的魔力,他们就越是感到那些过失并不属于他们所有。这样,民众就把领袖当成了他们的“替罪羊”。
如果要追溯替罪羊的历史渊源,弗雷泽的人类学巨著《金枝》是再好不过的了。《金枝》的命名,来自一个十分古老而神秘的传说。在古罗马附近的狄安娜神庙里,有一位祭司长年地守护。有趣的是,这位祭司向来是由逃亡的奴隶所担任的。他的罪行可以一笔勾销,还能拥有“森林之王”的称号。可是,这个称号,并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事。他永远地拿着武器,徘徊在月光下的狄安娜圣林里,像野兽一样警觉地留意着身边最细微的每一丝动静。因为,任何一个能够杀死他的人,就是下一任祭司。
贝克尔也注意到了《金枝》。替罪羊原型在长久的历史中,不断地进行移位,根据世界各地和各个民族的风俗,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变体。
要知道,神也是会死亡的。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塑造了神,人的肉体会消亡,而神也会死亡。例如埃及的大神奥西里斯,他就被他的兄弟害死了,埃及人发明了制作木乃伊的技术,希望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获得重生。原始部落的人,认为当他们的神(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他们的部落首领)衰弱死亡,就会给他们的部落带来灾祸,所以必须在人(或者神)的能力露出衰退的迹象的时候,将他杀死。与此类似的还有所谓的“替身神王”,他们会在担任替身王结束的时候被处死。这样的做法,用弗雷泽的话说,是为了“使神灵的精力永远保持年轻活力,使它不受年老身体衰弱的影响。”
2 从弗洛伊德的集体心理学到荣格的集体无意识
从遥远的古代和异国归来,回到心理学的国度,面对的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巨人: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在《自我本我与集体心理学》里面,着重评论了勒邦的观点。勒邦认为,领袖人物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大约等同于荣格的MANA),而他把这种力量称之为“威望”。他把威望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为的威望,这种威望能够依靠财富、名誉、声望而获得,所以也称为“获得的”威望。但还有另一种更高等级的威望,那就是人格的威望。具有这种“人格的威望”,才可能成为“领袖人物”。“这种威望能使所有的人对他俯首贴耳,使他们仿佛受了某种有吸引力的魔力的影响似的。”他还提出,“无论哪种威望都有赖于成功,如果遭到失败,这些威望就会丧失”。
我们可以解释《金枝》开头的传说了。当祭司被另一个人杀死的时候,他作为祭司的社会作用就消失了,或者,当一个部落的首领变得衰弱的时候,他的威望也就丧失了。祭司会被杀死,部落首领会被取代,而领袖,则会失去他的灵光,他的追随者也将会从符咒的魔力中清醒。
弗洛伊德认为,人是被部落首领领导的一种游牧动物。群体并未创造什么新的东西,只不过群体满足了人们深植心底的爱欲情感。这就像一种精神的粘合剂,把人们封闭在了一种几乎没有理智的相互依赖的状态之中。在弗洛伊德看来,勒邦所提到的无意识,“特别包括隐藏得最深的种族心灵的特征”,是“自我的核心”,弗洛伊德还从中区别出了“被压抑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便是从这种“祖先遗产”的一部分中产生出来的。
走到这里,不得不再次重复一遍荣格 “集体无意识”的基本概念: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基本上是由“原型”构成。原型概念是集体无意识概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联物,它表示似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种种确定形式在精神中的存在。
让我们再次回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因为衰弱而被杀死的神王,作为一种原型,不断进行移位,在对社会习俗的各种调整和适应中,终于走到了现代社会。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仅以求得丰饶为第一目的,对神祗的献祭就是古代人应付天灾人祸的方式。
可是,随着社会发展,人类对世界和宇宙的了解越来越多,原型也开始进行移位,领袖也将成为与当前社会相适应的更新型的“领袖”。
3 曼森家族——恶性自恋人格
贝克尔说:领袖的力量依赖于他能为群众做些什么,而不是他自身所拥有的魔力。人们把自己的难题投射给领袖,从而确定了他的角色和地位。有一点必须指出:不仅是领袖塑造群体,也是群体在塑造领袖。也许在生产关系较单一的原始社会,这一点也显得单一而不突出,但在现代社会,这一点从未如此多样化和复杂。
看一看臭名昭著的曼森家族。过早的流浪街头,造成了曼森的人格扭曲。他成立了他的“曼森家族”,“家族”里都是他的追随者。他以音乐和药物控制这些追随者,还制定了一个“终极计划”——发动末日种族和阶级战争。他声称自己是耶稣转世,将带领他的信徒进入一个“无底洞”中躲过一场大劫。在他的“计划”中,受害者们以极端血腥的方式被害。
曼森不仅是一个偏执型的精神分裂患者,而且有相当突出的“恶性自恋”人格障碍。自恋,原本是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神话中的那喀索斯迷恋自己水中的美丽倒影而伸手拥抱。弗罗姆也指出:自恋令人过高估计自身生命的重要性,贬低他人生命的价值。恶性自恋者与普通自恋者的差别在于,这类患者常常会表现出反社会的人格,偏执,缺乏道德伦理的判断力,甚至可能具有强烈的施虐狂式的攻击性。
曼森完全具有以上这些特征。在他的追随者眼里,他是一个类似弗洛伊德口中“原父”般的存在。曼森的狂想就有如英雄使命,而他的追随者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有资格来参与这个使命,哪怕是谋杀,也是“光荣的英雄”。
从弗雷泽《金枝》里面,我们已经了解到,所谓的“替罪羊”就是对于神祇、命运、自然的祭品。曼森的追随者,用被他们杀害的人的生命换取了他们“更丰富的生活”,在他们眼里,被害者是以“最高级的方式优先对世界作出了贡献”。所以曼森的追随者们并不感到罪恶感,一切都已经由他们的领袖所承担了。
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中,领袖的追随者的罪恶感,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抹煞的。贝克尔特别提到,“犯罪集团和匪徒也总是利用同样的心理学,即通过犯罪活动彼此本身更紧地绑在一起”。极端如纳粹的血盟,平常如身边犯罪案子里面的“从犯”,常常是受主犯要胁而犯罪的,大家都犯了罪让他们更紧密而不可分。
于是,最终,我们的英雄主义失败了。“作为某个希特勒或某个曼森之英雄使命而发端的东西,却由欺侮和威胁——外加恐惧和罪过感——来加以支持”。
贝克尔如是说。
所以曼森家族逃往沙漠等待世界末日,纳粹战斗到柏林毁灭的那一天。因为作为追随者,他们已经无从选择,英雄主义已经幻灭,他们不得不继续按领袖的意志与群体共同生存下去——不得不如此做,因为这已经是他们唯一的生存方式。
4 结语
遥望彼岸——非破坏性英雄主义我们总是需要一个移情的对象的。那个被我们移情的偶像越强大,我们就越轻松。我们会觉得我们也是不朽的,因为我们也参与了创造不朽。根据贝克尔的说法,移情更恰当的一个称谓是“移情英雄诗”,是安全的英雄主义,降格的英雄主义。很显然,曼森家族式的移情,是绝不可取的,因为它充满了破坏性和毁灭性。
于是,贝克尔天才地勾画了非破坏性英雄主义。
第一,我们不再需要“替罪羊”这种形式来释放我们的恨意,我们可以把恨的对象转移到诸如“贫穷、疾病、压迫或自然灾害上面”,把破坏性能量导向创造性的用途。
第二,让我们“练习”死亡。或者说,让我们正视死亡,并正确地面对死亡。人们不能把自己局限于黑暗的、血腥的、宗族的、陕隘的乌托邦之中,而应该让这些有勇气有道德的人们建立一个新的惺惺相惜的社群。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个体”所聚集的群体,他们所谓“怀着死亡的自觉意识而活在世上,有能力选择绝望”的真正的人。
贝克尔的构想是天才的,但也是遥远的、缥渺的。所以,我们只能留在我们的此岸,远望并渴求着他的——彼岸。
[1](美)厄内斯特·贝克尔.拒斥死亡[M].林和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2](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3](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本我与集体心理学[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
[4](瑞士)荣格.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徐德林,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
[5](美)巴特尔.犯罪心理学[M].杨波,李林,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