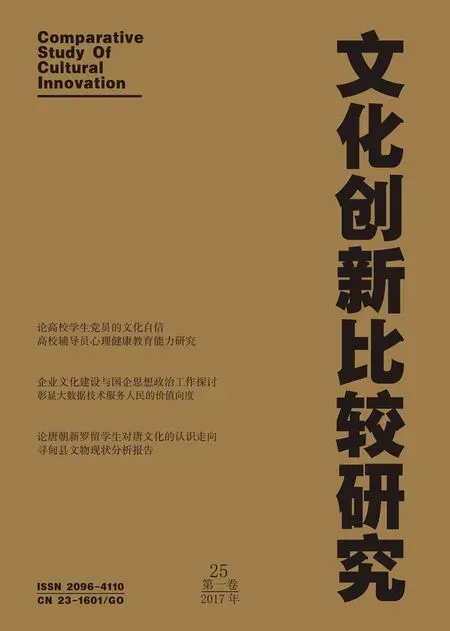浅析写意精神在中国画线条中的发展
李宗奎
(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与体育教育学院,贵州铜仁 554300)
1 “线”的写意精神
“作为重要的艺术形式语言之一,笔法对中国画笔墨独立审美价值的彰显和意境的表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画笔法的认识是一个“笔笔是笔,笔笔非笔”(清·邹一桂“八法”)的过程。”
2 写意精神在“线”中的发展
现存最早的画作在战国时期的帛画《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中的线条虽然不甚流畅但均匀连贯的描绘出了龙凤的形象,是以线条描绘形象作为祈祷升天等宗教性质的实用性和宗教性美术作品,此时的绘画表现依然是以刻画形象、故事为存在因素,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要素,在作品绘制中多采用严谨、细致的线条,此时的线条只是作品形象的造型手段,还不具备审美的要素。在此之前河姆渡文化时期的《朱纹钵》中,野猪的形象特点鲜明、惟妙惟肖,以线条刻画,作为部落图腾,或祈祷、狩猎、养殖、繁衍的崇拜、记录等因素。此时的绘画形象是描绘形象、传递信息的公用。具有相同意义的还有仰韶文化的《彩陶人面鱼纹盆》,新石器时代《鹳鱼石斧图》等。
及至西汉时期,这一时期的漆棺彩绘《双鹿图》中的双鹿,以及河南洛阳卜千秋墓中的彩绘朱雀最具有代表性。在观察《朱雀》时我们可以发现,在墓壁与棺椁上绘制相对于在帛上差异较大,所以在这两幅作品中绘制不及帛画精致。但依然可以观察到虽然也是先用线勾勒朱雀的形象再敷以朱色,但在朱雀尾羽与雀足的勾勒上出现了明显的线条粗细变化,尾羽用线条的一端纤细入笔,中间顺着笔势渐粗而有力,末端顺势撇出,整条线条飘逸流畅且短促含有力度,排列的线条恰如其分的表现出了羽毛的状态。而朱雀的双足用一条较粗的线条一笔绘成,两足用线条的粗细完成了外粗内细的透视规律。在绘制朱雀脚趾,也利用线条的特性很好的描绘出了各个细节的变化,包括脚趾都生动自然,这与当今笔墨语言的运用并无二致,可见早在千百年前的墓室壁画中,画家已经有意或无意的领会到了对线条的运用,线条开始成为一种表现手段,开始作为一种艺术语言而存在。
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线条的运用已经逐渐超越了早期的“自觉”意识,而确定为一种艺术语言,而且是画面的重要构成。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以用线为代表的绘画样式,以线条的优劣品评画作是否成功。这一时期代表的绘画样式有因线纹“连绵不断”而被称为“一笔画”的陆探微,还有以细劲的线条表现紧贴在身躯衣纹,“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被称为“曹衣出水”的曹仲达,而最负盛名的顾恺之更是用线如“春蚕吐丝”,其代表作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洛神赋图》中用线“紧劲连绵,循环超忽”,恰如其分的描绘出了洛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飘忽往来,也描绘出了曹植与洛神之间动人悱恻的爱情故事。此时的线已是画家笔下传情达意的重要表现手段,而且根据画家不同的性格、审美赋予了各异的生命灵魂与审美气质。但却没有脱离造物象形的功效,始终是画面众多要素的组成部分之一。及至唐代吴道子、阎立本、李公麟等人将线的造型手段发挥到了极致,并形成了只以线为表现方式的画面形式—“白描”。但此时的线并没有较多的感情色彩。而另一方面,随着谢赫“六法论”的提出,“骨法用笔”被推到了相当的高度,顾名思义,其强调笔法在绘画当中起到支撑作用,决定了一幅画是否健康,进而品评画格的高下与雅俗。然而,对线的骨法用笔,李嵩、崔白、李唐等人已经有自觉意识的变化,赋予个人风格与审美能力。例如李唐《采薇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马麟《静听松风图》中的树石,以书法用笔,具有较强的主观意识,此时的画面当中两种不同的用线方式同时存在,共同形成画面的对比,构成了丰富的美感。
北宋苏轼的《枯木怪石图》以书法用笔,纵横恣肆,用笔、用墨浑天成以难分彼此。绘画已具有写的意味,画面更多的追求“意境”、“趣味”,笔墨语言无疑成为最能够表现画面风格的绘画语言,从宋迪,晁补之等人最早被冠以“士夫画”以来,士大夫所推崇的文人画已悄然兴起,他们在绘画中更看中文人情怀的抒发,学识的彰显以及品格的高下,往往以书入画,追求笔墨的韵味,而除却苏轼,同时期的王庭筠更是将笔墨在画面中的应用,在塑造画面形象当中更是妙趣横生又不失法度,他的《幽竹枯槎图》墨色淋漓,枯树树干枝桠笔锋形散而意不散,用笔苍劲、顿挫恰如其分的表现出了枯槎的沧桑质感,枝桠上的藤蔓以笔尖锋画出,使毛笔的特性达到了充分的利用,是对毛笔使用方法的一次重大的突破,而一旁的墨竹弯而不曲,细小的竹枝充满了坚韧,竹叶则显得酣畅潇洒,簇簇的竹叶似随风摇曳,对不同事物笔法的转化、墨色的应用,展现出了画者雄姿英发,气宇铮铮的傲人才气,画面当中隐而不发,文人书卷气溢与卷外,作者“天纵其能,情高格逸”,而其作品“发乎天然,非繇述作。”这幅作品堪称“逸品”,正如画卷上所云“黄华山真隐,一行涉世,便觉俗状可憎,时拈秃笔作枯木竹石、幽竹枯槎,以自料理耳。”然而真正把线从“线”中完全解放出来的当属梁楷,如他的《泼墨仙人图》、《六祖斫竹图》。正是“梁疯子”的出人意表、不拘一格才打破了固守的藩篱。他的笔下纵横捭阖,已难分笔墨,造型与表现交错,墨色与笔墨酣畅淋漓。
到赵孟頫时期,确立了书画一体的主张。“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秀石疏林图》中的用笔很好地诠释了书画同源的主张,赵孟頫特殊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全面的艺术才能使他在处于画坛的领导位地位,他的艺术主张无疑在元代整个画坛中具有导向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人士大夫以及大众的审美情趣及艺术走向。倪瓒《竹枝图卷》,倪瓒题曰“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倪瓒在画中更是抛弃了对造型的苛求与深究更侧重于个人情绪的抒发与逸气的表达。倪瓒“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艺术主张使这幅作品中线(笔墨)真正的摆脱了为塑造形体而存在,而是与其他绘画语言融为一体,每一笔线的存在都是画面,每处画面都是一条线。
明陈淳、徐渭在发挥前人笔墨的基础上又大胆突破,徐渭的《墨葡萄》、《芭蕉图》更是汪洋恣肆,难见笔迹,将写意精神推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一笔一墨无不彰显艺术节桀骜的性格和才华横溢的才气。
3 “线”中写意精神的形成
“写意精神,无疑是中国画最重要的文化审美品格。中国画观照世界的方式,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或再现,而是借助于审美对象并通过毛笔的书写性以表现艺术主体的思想意趣与精神品位。”线是最具有中国文人精神的符号,而写意精神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文化内涵,写意精神在中国画线条中的发展体现了中国画的哲学思想。
[1]尚辉.笔法维度中国画写意精神的坐标基点[J].展览档案,2012(6):66-69.
[2]王国栋.笔笔是笔,笔笔非笔——写意人物画笔法分析[D].中央美术学院,2008.
[3]邓小刚.解读中国雕塑的写意精神[D].湖南师范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