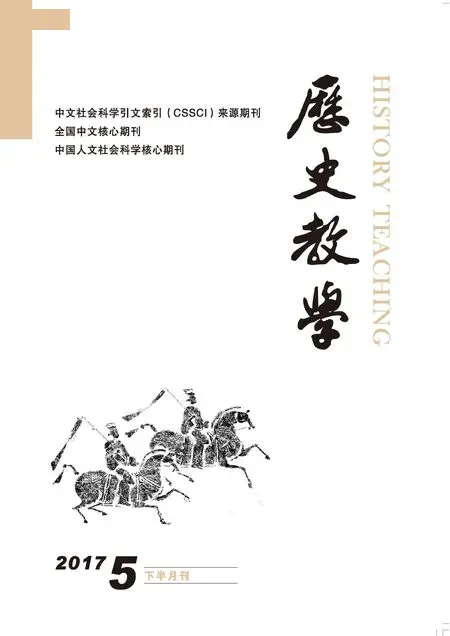“一战”期间在中国的奥匈战俘
〔匈〕马加什 江 沛
(1.2.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350)
“一战”期间在中国的奥匈战俘
〔匈〕马加什1江 沛2
(1.2.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350)
“一战”期间共有数百万奥匈帝国官兵沦为俘虏。不少关押于俄国境内的奥匈战俘流亡中国东北,受到尚处中立的中国当局及他国民间组织的救助。1917年民国北京政府对同盟国宣战,奥匈帝国使馆卫队及天津奥匈租界驻军就地解除武装,成为新的战俘,先后被收容于北京。在华的奥匈战俘,有的因对本国政府不满而成为暴乱的制造者,有的则奋进为著名人士,如上海建筑业先锋邬达克。这一特殊群体无疑是审视战争、反映当时中国政治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窗口。
奥匈战俘,第一次世界大战,天津德国助赈会,奥匈租界,邬达克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四年有余,给参战的同盟国与协约国人民均带来深重苦难。战俘是战争产生的特殊群体,亦为审视战时国家内政外交的窗口之一。本文以在中国的奥匈战俘为研究对象,通过论述其来源、安置、救济等问题,考察战俘个体的迥异命运,旨在从一个侧面展现战争影响下的政治社会变迁和历史复杂面相。
一、俄国政府对于奥匈战俘的处置
一战爆发后不久,沙俄军队就在加利西亚(Galicia,当时属奥匈帝国,今位于乌克兰)俘虏了超过10万的奥匈战俘。随着东线战事愈演愈烈,俄军俘获的奥匈战俘日益增多,至1916年“勃鲁西洛夫攻势”(BrusilovOffensive)结束后已逾40万人。①其中绝大多数奥匈战俘,一部分1914年被俘于加利西亚(Galicia,今位于乌克兰),一部分1915年被俘于普热梅希尔(Przemysl,今波兰南方),还有一部分1916年被俘于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今位于乌克兰、斯洛伐克)。参见Reinhard Nachtigal and Lena Radauer,“Prisoners of War(Russian Empire)”,October 10,2014,DOI:http://dx.doi.org/10.15463/ie1418.10386,2015年12月4日。据统计,整个一战期间,共有277万奥匈帝国官兵沦为沙俄的俘虏。②Alon Rachamimov,POWs and the Great War:Captivity on the Eastern Front,New York:Berg,2002,pp.4、31.如何处置这一庞大群体,成为沙俄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按照当时的通行方式,这些战俘必须从前线步行三四个月到俄国境内的火车站,由火车送往位于基辅或莫斯科的中心收容所(central assemblycamp),再被遣送至各地战俘营关押。前往车站的路上,战俘们只能以微薄给养和沿途居民的救济为生。奥匈帝国军队中民族成分复杂,斯拉夫和犹太裔战俘往往因获沙俄境内居民的民族认同而得到较好的救济;相比之下,德意志、奥地利和匈牙利裔战俘则处境悲惨。③Alon Rachamimov,POWs and the Great War:Captivity on the Eastern Front,p.49.经过数月跋涉,抵达车站的战俘大都意志消沉、饥饿不堪。乘火车前往中心收容所的旅途也不轻松,三四十人挤在一节被称为“暖厢”(warm wagon,俄文теплушка)的狭小车厢,里面只有一个火炉、两三排床铺和一个马桶,战俘们还须忍受斑疹伤寒和跳蚤的折磨。④尽管车厢被称为“暖厢”,但据战俘们回忆,实际是冬冷夏热。参见Alon Rachamimov,POWs and the Great War:Captivity on the Eastern Front,p.52;Gerald H.Davis,“The Life of Prisoners of War in Russia.1914~1921”,pp.165~166.in Samuel R.Williamson, Peter Pastor,ed.,Essays on World War I:Origins and Prisoners of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pp.163~197.
抵达中心收容所后,战俘首先要进行注册。他们根据不同民族被分为几类。其中,斯拉夫人(约占奥匈战俘的一半)、阿尔萨斯人(被认为是德国境内的法裔)和意大利人(主要来自奥匈帝国的南蒂罗尔、伊佐拉和达尔马提亚)、比德意志人、奥地利人(约占奥匈战俘的1/4)和匈牙利人(约占奥匈战俘的1/4)要享有稍好的待遇,①Peter Pastor,“Hungarian POWs in Russia During the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in Samuel R.Williamson,Peter Pastor,eds.,pp. 149~150,转引自Reinhard Nachtigal and Lena Radauer,“Prisoners of War(Russian Empire)”,2014此处与前文不一致;Alon Rachamimov,POWs and the Great War:Captivity on the Eastern Front,pp.57,59;Reinhard Nachtigal,“Privilegiensystem und Zwangsrekrutierung.Russische Nationalitätenpolitik gegenüber Kriegsgefangenen aus österreich~Ungarn”,in Jochen Oltmer,ed., Kriegsgefangene im Europa des Ersten Weltkriegs,Paderborn:Schoening Ferdinand Gmbh,2006,pp.181~187.但也仅是相对而言。例如,捷克战俘的境遇就令其十分失望,并未感受到太多俄国人所宣扬的“斯拉夫兄弟情谊”。②Alon Rachamimov,POWs and the Great War:Captivity on the Eastern Front,p.96.注册后,战俘名字被汇成表单提交国际红十字会,由红十字会来告知其亲属,这项工作实际开展得也不顺利。③Alon Rachamimov,POWs and the Great War:Captivity on the Eastern Front,p.54.
在中心收容所完成上述工作后,沙俄政府开始将战俘送往境内各地的战俘营。④到1917年,俄境内共有400多座战俘收容设施(interment facility)。其中128座在莫斯科地区,另有30座在伊尔库斯克周围,28座在鄂木斯克周围。参见Grekov N.V.,Germanskie i avstriiskie plennye v Sibiri(1914~1917)[German and Austrian prisoners in Siberia(1914~1917)],in Vibe P.P.,ed.,Nemtsy Rossiia Sibir’[Germans,Russia,Siberia],Omsk 1997,p.159,转引自Reinhard Nachtigal,Lena Radauer,Prisonersof War(Russian Empire),2014。《海牙公约》⑤参见1907年海牙公约《陆战法规和惯例》,http://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misc/hagueconvention4-18101907.htm, 2016年2月12日。对于沙俄政府1914年10月在彼得堡的战俘政策制定影响甚微。⑥Alon Rachamimov,POWs and the Great War:Captivity on the Eastern Front,p.120;Gerald H.Davis,“The Life of Prisoners of War in Russia.1914~1921”,p.174,转引自Reinhard Nachtigal,Lena Radauer,Prisonersof War(Russian Empire),2014。俄国对战俘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境内欧洲部分的战俘营条件最好,中亚次之,而远东—西伯利亚的条件最差,当地自然环境尤其恶劣。不过,实际情况更加多样。⑦尽管俄政府制定了统一的战俘政策,但各战俘营的实际落实程度差异很大。参见Elsa Brändström,Unter Kriegsgefangenen in Ruβland und Sibirien 1914~1920,Berlin: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M.B.H.,1922,p.7.战俘们并不都生活在由铁丝网包围的集中营,其住宿地点多种多样,包括工厂、学校、戏院、民房、军营和酒厂等等。在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和滨海边疆区(Primorskaya district),民用设施有限,战俘绝大多数住在条件恶劣的砖砌军营。⑧Alon Rachamimov,POWs and the Great War:Captivity on the Eastern Front,pp.90~91、97、112.在那里,被俘军官待遇较好,无需劳动,而士兵却缺乏相关法律保障,⑨Alon Rachamimov,POWs and the Great War:Captivity on the Eastern Front,pp.90~91、97、112.被作为劳动力大量使用于当地的工农业生产,如摩尔曼斯克(Murmansk)和彼得堡(Petrograd,今圣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间的极地铁路即由其建设。⑩Alon Rachamimov,POWs and the Great War:Captivity on the Eastern Front,pp.90~91、97、112.尽管1916至1917年战俘的生活条件略有提高,但整个一战期间,在俄关押的战俘死亡率高达17.6%,仅次于塞尔维亚的25%和罗马尼亚的23%。⑪⑪Alon Rachamimov,POWs and the Great War:Captivity on the Eastern Front,p.106.此外,总计死亡人数在40万左右。参见Reinhard Nachtigal,Lena Radauer,Prisonersof War(Russian Empire),2014。
1917年初俄国爆发二月革命,以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废除了区别对待奥匈战俘之政策,却同时提高了他们的劳动强度,加强对战俘营的纪律管控。新战俘政策收效微小,反而使各战俘营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十月革命之后,奥匈战俘的境遇发生转机。苏俄政府为了尽快跳出一战泥潭,决意彻底解决战俘问题,宣布境内战俘重获自由。⑫⑫Peter Pastor,“Hungarian POWs in Russia During the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pp.151,154.转引自Reinhard Nachtigal,Lena Radauer,Prisonersof War(Russian Empire),2014。
出于对结束战争和返回家乡的渴望,绝大多数奥匈战俘欢欣鼓舞。还有少数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和红军国际师。⑬⑬Striegnitz,Sonja,“Vorwort”,in Pardon Inge,Shurawljow Waleri W.eds.,Lager,Front,Heimat:Deutsche Kriegsgefangene in Sowjetruβland 1917 bis 1920,Munich:K.G.Saur,1994,vol.i,pp.7,9,转引自Reinhard Nachtigal,Lena Radauer,Prisonersof War(Russian Empire),2014.当时的中国报纸称这批人为“过激派”。⑭⑭参见李学通、古为明:《中国德奥战俘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0页。可是,奥匈战俘的苦难并未就此结束,苏俄内战和协约国的干涉,使其大批滞留俄境。更严重的是,由捷克裔和斯洛伐克裔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兵团于1918年5月发动叛乱,迅速成为反对苏俄势力的急先锋。他们四处破坏铁路交通,阻止奥匈战俘回国,并强迫其中的捷克裔和斯洛伐克裔战俘加入兵团,因而声名狼藉。
二、吉林和黑龙江的德奥战俘收容所
随着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①虽然“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两个地理概念所指区域有一定重叠,但外文文献中,仍将其并列表述,其所指“西伯利亚”实际并不包括“远东地区”。本文遵循所参考外文史料的表述习惯,同样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并列,下同。等处战俘增多,战俘营内生存条件愈益恶劣,加之俄方的战俘管理比较粗放,常有俘虏借机脱逃,与俄接壤的中国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成为很多奥匈战俘的逃亡之地。逃至中国的战俘在当时有一个专有名词——“东北逃俘”。②李学通、古为明:《中国德奥战俘营》,第130页。民国初年的吉林省与当今吉林省的区划有很大不同,包括松花江以东至与俄罗斯,朝鲜接壤的广阔地区,政治中心是吉林而非长春。其选择来华,一方面由于俄罗斯领土广袤、气候寒冷以及敌国政府的控制均使自西伯利亚和远东启程的西行归乡之路艰险漫长。另一方面,大多数战俘知道他们临近中国边境,且民国北京政府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不仅如此,远东地区有的战俘已经同中俄边境的华人有了一段时间的交往。③在俄国滨海区乌苏里斯克/双城子(Nikolsk Ussuriysky,今Ussuriysk)关押的战俘从赤塔(Chita)坐火车经由哈尔滨前往战俘营。乘车途中,有的战俘在哈尔滨火车站下车之后就不上车了,从而成为中国的俘虏。住在乌苏里斯克的奥匈官兵跟本地唐人街的华人常常有交流,有的战俘甚至学了中文。参见József Gazda,Emlékek魣zsiája.Budapest:Terebess Kiadó,2003,pp.7~8、32~33。中国境内的非政府慈善组织也不断接济逃亡战俘。这更促使战俘逃向中国。有的人先到中国,后转道日本、美国,最终重返欧洲故乡,其流亡经历类似冒险的“奥德赛故事”。④Bokor,Ervin Dr.,Menekülés a szibériai fogságból Japánon és Anglián keresztül.Két magyar tiszt viszontagságai,Budapest:Franklin, 1919,pp.341~364.
1915年初,从沙俄战俘营脱逃的德国和奥匈帝国战俘已出现于中国东北边境。这年1月,吉林省当局接到东宁县报告,一些冻伤严重的德国战俘从绥芬河对岸入境。东宁县一面给予伙食,一面请示应如何回应俄方已提出的关于遣返逃俘之要求。吉林巡按使孟恩远指示:“德俘即入我界,应照中立惯例由县看护,不能交给俄方,并且命令东宁县将该德俘等冻疮速为治疗,加以相当待遇,同时缜密看守,勿令逃亡。”同时将此情况呈报北京政府外交部。接到孟恩远报告后不久,外交部也收到俄国驻华公使关于逃俘问题的照会。经过交涉,外交部指示吉林方面:“1907海牙保和会陆战中立条约中有关中立国收容逃亡俘虏的相关规定,是中方处置德人之事确之根据,极为紧要,务祈遵守缜办,万勿夫之轻忽。”⑤⑥⑦⑧李学通、古为明:《中国德奥战俘营》,第130~131、150~151、168、105页。随着逃俘不断增多,吉林方面不得不在吉林市西门外设立一座俘虏收容所来安置他们。
一战爆发后,黑龙江地区的外国人也骤然增多,其中就有不少“逃俘”。黑龙江当局为安置他们,在海伦和龙江(今齐齐哈尔市)分别开设了战俘收容所。其中,海伦收容所设立于1917年3月9日,刚一建立就收容了德奥两国战俘300余名,还接纳了一些来自奥斯曼土耳其的逃俘。⑥李学通、古为明:《中国德奥战俘营》,第130~131、150~151、168、105页。龙江战俘收容所成立于1918年9月15日,共收容战俘456名。在所有一战时期中国设立的德奥俘虏收容所中,此处收容的奥匈战俘数量最多。⑦李学通、古为明:《中国德奥战俘营》,第130~131、150~151、168、105页。
三、天津德国助赈会与战俘救济
1915年秋,奥匈帝国当局着手解决他国战俘收容所里衣物、食品和药品短缺等战俘救济问题。⑧李学通、古为明:《中国德奥战俘营》,第130~131、150~151、168、105页。基督教男青年会(YMCA)和丹麦、瑞典的红十字会等非政府组织也参与其中。在天津,一个名为天津德国助赈会(Tientsin Hilfsaktion)⑨全名“救济西伯利亚德奥俘虏行动”,德文写作“Hilfsaktion für deutsche und österreich-ungarische Gefangene in Sibirien”,英文写作“Tientsin Relief Organization”。因为汉纳根夫人与这一行动组织的密切关系,故当时这一救济行动通常被称为“汉纳根救济行动”,英文写作“Hilfsaktion von Hanneken”(参见Wurzer,Georg,Die Kriegsgefangenen der Mittelm覿chte in Russland im Ersten Weltkrieg,PhD Dissertation,Eberhard KarlsUniversität Tübingen,2000)。的组织也在积极救助德奥战俘。该会创始人艾尔莎·冯·汉纳根夫人(Frau Elsa von Hanneken)是曾任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之女、德国商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之妻。⑩Insitute für Genealogie und Heraldik,2015-11-18,http://www.schlossarchiv.de/TNG//familygroup.php?familyID=F895311H&tr ee=tree1,2016年3月28日。1914年她听说有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逃亡的德军战俘经中国东北逃至天津。为了救助这些同胞,她前往北京请求德、俄、美三国公使馆为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返津后,她又建立了一个救济委员会,即天津德国助赈会,专门募款来救助中国境内的德奥逃俘。
助赈会很快募集到约八万金马克的善款,并委托两名美国人将三分之一的资金送往俄国西伯利亚的赤塔和滨海区的战俘营,同时让他们记录战俘名字,制成名单反馈给委员会。①Frau Elsa von Hanneken,“Die Tientsiner Hilfsaktion:Eine Hilfskaktion für Kriegs-und Zivilgefangene in Tientsin”,in Hans Weiland,Leopold Kern,eds.,In Feindeshand:Die Gefangenschaft im Weltkriege in Einzeldarstellungen,vol.2,1931,pp.266~267.据汉纳根夫人所述,1917年天津德国助赈会所施救助最多,总计向俄罗斯境内110个战俘营邮寄六万笔汇款,还为约十八万名德奥战俘送去了军装、棉衣、长靴和书本等物品。②Frau Elsa von Hanneken,“Die Tientsiner Hilfsaktion:Eine Hilfskaktion für Kriegs-und Zivilgefangene in Tientsin”,in Hans Weiland,Leopold Kern,eds.,In Feindeshand:Die Gefangenschaft im Weltkriege in Einzeldarstellungen,vol.2,1931,p.267.
助赈会的成员全是德奥公民,汉纳根夫人亲自担任委员长和秘书,其他职位也都由天津德奥租界里的德国和奥匈帝国公民担任。③Frau Elsa von Hanneken,“Die Tientsiner Hilfsaktion:Eine Hilfskaktion für Kriegs-und Zivilgefangene in Tientsin”,in Hans Weiland,Leopold Kern,eds.,In Feindeshand:Die Gefangenschaft im Weltkriege in Einzeldarstellungen,vol.2,1931,p.267.1915年,助赈会的员工已达60人,并且有了专门的办公地点,其工作得到广泛支持。天津德奥租界里的女士和孩子为战俘们缝制衣物,亚洲多地的德国和奥匈帝国公民积极为助赈会捐款,各同盟国也积极支持在天津的救济活动。此外,1917年美国对德宣战前,美红十字会一直是天津德国助赈会的有力助手,而瑞典和丹麦两国的红十字会也帮助赈会援助德奥战俘。④一战期间,瑞典红十字会一直为在俄境内关押的同盟国战俘提供救助。瑞典护士Elsa Brändstörm因其善举,受到奥匈帝国和德国战俘的感激,有“西伯利亚天使”之美誉(参见Alon Rachamimov,p.168)。
天津德国助赈会因有浓厚的同盟国背景而成为协约国的仇视对象。先是有人纵火焚烧助赈会办公室,后来该会又被赶出位于英租界的办公地。⑤Frau Elsa von Hanneken,“Die Tientsiner Hilfsaktion:Eine Hilfskaktion für Kriegs-und Zivilgefangene in Tientsin”,in Hans Weiland,Leopold Kern,eds.,In Feindeshand:Die Gefangenschaft im Weltkriege in Einzeldarstellungen,vol.2,1931,p.267.据其成员Olga Fischer-Togo夫人(奥地利人)记述,中国参加一战前,当局对同盟国公民尤其是德国公民比较尊重,并为他们提供必要帮助。⑥Frau Olga Fischer-Togo,“Erinnerungen an Tientsin”,in HansWeiland,Leopold Kern,eds.,p.268.但是1918年3月,迫于协约国的压力,中国政府的警察部门还是勒令天津德国助赈会关闭办公地点,并将文件全部没收。协约国当局还视汉纳根夫人为同盟国间谍,但是她并未放弃自己的救助事业。⑦Frau Elsa von Hanneken,“Die Tientsiner Hilfsaktion:Eine Hilfskaktion für Kriegs-und Zivilgefangene in Tientsin”,in Hans Weiland,Leopold Kern,eds.,In Feindeshand:Die Gefangenschaft im Weltkriege in Einzeldarstellungen,vol.2,1931,p.267.
四、在北京的缴械奥匈战俘
在北京收容的奥匈战俘与“东北逃俘”不同,实则为中国参加一战后就地缴械的北京奥匈使馆和天津奥匈租界之驻军。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同盟国宣战,与德奥两国骤然成为敌对关系。民国北京政府专门出台处置中国境内奥匈帝国军事人员的办法:“在北京奥使馆之卫兵或租界之奥国商团及其余有武装之奥国军人,均应自动解除武装,由中国陆军部或各省区军事长官派员点验收容,送往指定收容地点。”⑧李学通、古为明:《中国德奥战俘营》,第52页。对此,奥匈帝国驻华使馆最初采取拖延战术,通过荷兰驻华使馆与北京政府外交部交涉,并利用荷兰的中立国地位来庇护奥匈驻华军事人员。⑨“Dutch Legation Cares For Austrian Interests”,Peking Gazette,August 15,1917;“THE AUSTRIAN GUARDS:Their Internment Soon Question Over Their Arms”,Peking Daily News,August 25,1917.荷兰方面提出:中国宣战后,奥国军人自愿归荷馆保护,已由荷兰使馆令其解除武装暂行收容。荷兰理由是:按照海牙和平会议公约规定,交战国的军队可以往中立国境地内寻求其保护……但考虑到中国的地域主权,荷兰认为必须要给中国以实行参与的权利。⑩李学通、古为明:《中国德奥战俘营》,第53页。
但是经过谈判,荷兰方面最终妥协。9月13日,奥匈使馆卫队在30名荷兰人、一营中国警察和两个骑兵连的押送下,徒步前往中国政府指定的西苑收容所。1918年1月,又被迁往万寿寺。⑪转迁时间一说是1918年4月。万寿寺位于今北京海淀区高梁河(长河)广源闸西侧,原名聚瑟寺,始建于唐朝。士兵战俘被安排在三个大殿和四周房屋内居住,军官战俘则住到该寺过去为慈禧准备的房间里。寺院前面是负责看守的中国军人宿舍,“最后一个院里住着主持和尚及他的弟子们。再后面有一块600平米的平地,成了俘虏们踢足球、打网球的场所”。荷兰公使对万寿寺非常满意。一位当年被收容于此的战俘后来表示“乐意回顾”这段时光。奥匈帝国驻华公使罗斯托恩(Arthur von Rosthorn)也承认:“我从没遇到一个(在华的)奥地利人叫苦,他们受到了良好的待遇。”①李学通、古为明:《中国德奥战俘营》,第54~55页。
奥匈使馆卫队被迁至万寿寺之后,西苑收容所成为天津奥匈战俘的住地。1901年,奥匈驻华公使根据《辛丑条约》,提出在华划定租界的要求。1902年中奥两国签订协定,奥匈帝国在天津获得了一块一千余亩的租界,②《奥租界设立合同》,天津档案馆、南开大学分校档案系编:《天津租界档案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36页。并在河东二马路设兵营(位于今民主道上),驻军40余人,由一上尉军官统领。③“A MI KIS KHIN魣NK.A tientsini osztrák-magyar telepítvény”,Vasárnapi újság,Május1,1904,p.294;来新夏、杨大辛:《天津的九国租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3页。1917年,中国参战消息哄传,天津奥匈租界情形不稳,甚至出现凶杀命案(即后文所谈密谋进攻租界一事)。驻北京奥匈帝国使馆卫队派32名水兵,赴天津奥匈租界弹压。中国对奥匈帝国宣战当日,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派中国军警进驻租界,接管行政权。临时来津的奥匈使馆卫队水兵就地缴械后,于17日被送往北京西苑收容所。天津奥租界原驻军后来也集中到北京管理。④李学通、古为明:《中国德奥战俘营》,第80~81页;“The Austrian Concession in Tientsin”,Peking Gazette,August 15,1917;“Tientsin Concession Taken Over”,The North China Herald&Supreme Court Gazette,August 25,1917.
五、谋划进攻租界——逃俘对奥匈当局的反抗
1917年7月31日下午两点,一名奥匈海员在天津英租界维多利亚路乘坐洋车,打算前往德租界的天津德国助赈会。行至麦加利银行(Chartered Bank)时突遭一人阻拦,随后又出现三人,共同持枪将海员挟持。在前往德租界的路上,海员趁机逃跑。绑架者在追逐过程中开枪,错杀一名中国警察。最终海员顺利逃入德租界,四名绑匪被英租界警察逮捕。⑤Tagesblatt für Nord~China.1917-8-1,转引自Balázs Pálvölgyi,Zwischenfall in Tientsin ein Stück der Doppelmonarchie in China im Jahre 1917,in:Radovan David,Jan Necka,Martin Orgonik,David Sehnalek,Jaromir Tauchen,Ji i Valdhans,eds.,COFOLA(Conference for Young Lawyers),May 13~14,2008,organized by:Masarykova Univerzita,Brno,Czech Republic,pp. 1100~1118,p.7;Balázs Pálvölgyi,Kaland a kaland végén:összeesküvés az Osztrák~Magyar Monarchia távol keleti érdekeltségei ellen,in:Máthé Gábor,Mezey Barna,eds.,ünnepi tanulmányok Révész T.Mihály 65.születésnapja tiszteletére, Budapest:Gondolat,2010,pp.358~370,p.360.经过审问,绑匪的目标正是奥匈帝国在天津租界内的领事馆,其中三人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奥匈逃俘。
一战期间,不少奥匈战俘逃至中国东北后,因身体虚弱、不堪严寒而向奥匈领事馆求助,希望能在天津租界居住。⑥Settlement Tientsin(Gönnert und Genossen)Augustus30,1917,AS 032,033 NS 0083,ZI 1729/17,OEStA-HHStA.而奥匈当局怀疑这些人中混有俄国间谍,对他们保持怀疑警惕。⑦1914年波兰族Bozich的案件,参见Herr Bozich Dezember 5,1916,AS 007 NS 0043,Res.No.155.1043,OEStA-HHStA.不仅如此,一些逃俘还被奥匈在华驻军强行征召,不少人心怀不满,暗地组织反抗活动。
英租界绑架案的绑匪头目Josef.Gönnert是一名已在中国生活12年的奥匈冒险家,因未能获得在奥租界的居住权而一直怨恨租界当局。据讯问笔录,在其贸易生意被取缔后,他曾用手枪威胁过领事馆人员,因此被驱逐出天津。⑧“Austrian Brutality in China.How the Authorities Treat Prisoners”,Shanghai Times,October 11,1917;“Warrant”,参见Settlement Tientsin(Gönnert und Genossen)Augustus30,1917,AS 032,033 NS 0083,ZI 1637/18,OEStA HHStA.1913年,Gönnert从日本辗转俄罗斯远东地区后回到中国,一战爆发时在陕西龙山法比铁路公司(Société Franco-Belgie)任职。⑨“Austrian Brutality in China.How the AuthoritiesTreat Prisoners”,Shanghai Times,October 11,1917.据其后来在上海会审公廨(Mixed Court)的证词,⑩Gönnert 1917年9月因相关事件上海法庭诉讼Shanghai Times报道了这一事件。他反对奥匈租界当局的缘由是因反感其对帝国臣民的恶劣态度。据他讲,北京奥匈使馆关押着不少政治犯,“东北逃俘”的求援也往往被领事馆人员拒绝。⑪“AUSTRIAN OPPRESSION DROVE HIM TO ORGANIZE REVOLUTION”,Peking Daily News,Sep.24,1917.
出于类似不满,反抗者们集合在一起,密谋武装占领奥匈租界和领事馆,解散驻军,宣布奥匈租界共和,并拥立一名意大利裔奥匈海军军官为“共和国总统”,与协约国结盟。①海军官HugoAccurti在奥匈领事馆提出的证据。参见Settlement Tientsin(G觟nnert und Genossen)1917 Augustus 30 AS 032,033 NS 0083,ZI 1593/17,OEStA-HHStA,转引自Mathieu Gotteland,The Austro~Hungarian Concession in Tianjin and World War One,Conference Paper,in Austrian StudiesAssociation’sConference,Austin,Texas,USA,February 7,2014.
此项密谋的参与者包括“东北逃俘”、驻京奥匈使馆卫队逃兵、②Balázs Pálvölgyi,Zwischenfall in Tientsin-ein Stück der Doppelmonarchie in China im Jahre 1917,pp.3~5;Balázs Pálvölgyi, Kaland a kaland végén:összeesküvésaz Osztrák-Magyar Monarchia távol keleti érdekeltségei ellen,pp.362~363.奥匈船运公司(Austrian Lloyd)海员和英、法、日三国的情报部门。③BalázsPálvölgyi,Zwischenfall in Tientsin ein Stück der Doppelmonarchie in China im Jahre 1917,p.5.BalázsPálvölgyi,Kaland a kaland végén:összeesküvésaz Osztrák-Magyar Monarchia távol keleti érdekeltségei ellen,p.363.按照密谋计划,一旦中国介入此事,日本会立即出兵干涉。④海军军官HugoAccurti在奥匈领事馆提出的证据。
但是,由于上述那位“总统”和部分参与者向奥匈租界当局告密,奥驻京使馆及时派兵镇压,使攻占租界的计划破产。⑤BalázsPálvölgyi,Zwischenfall in Tientsin ein Stück der Doppelmonarchie in China im Jahre 1917,p.6.BalázsPálvölgyi,Kaland a kaland végén:összeesküvésaz Osztrák-Magyar Monarchia távol keleti érdekeltségei ellen,p.364;李学通、古为明:《中国德奥战俘营》,第80页。不过,反抗者们继续谋划在协约国的帮助下对上海奥匈领事馆发起攻击,同时夺取上海港口隶属于奥匈船运公司的三艘商船转交给英国。⑥Balázs Pálvölgyi,Kaland a kaland végén:összeesküvés az Osztrák~Magyar Monarchia távol keleti érdekeltségei ellen,p. 358.这个计划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一名密谋者在追捕行动中被枪杀。⑦“Murder at Austrian Consulate:One Man Shot Dead”,The North China Herald&Supreme Court Gazette,August 18,1917.
六、邬达克——从逃亡者到上海建筑业先锋
邬达克(1893~1958,László/Ladislav·Hugyecz/ Hudec)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拜斯特尔采巴尼亚(Besztercebánya,今斯洛伐克的班斯卡-比斯特里察Banská Bystrica),父亲是建筑工程营造商(master builder),母亲是路德教会牧师之女。他曾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皇家约瑟夫技术大学(Hungarian Royal Joseph Technical University)建筑系攻读学位。1914年应征入伍,1916年在前线被俄军俘虏。⑧华霞虹:《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21、43页。最初,邬达克与3000名同伴一起被送往哈巴罗夫斯克军官战俘营。1917年,又转至红列奇卡(Krasnaya Rechka)战俘营。在此期间,他学习了波兰语、俄语、法语和英语。⑨Ladislav Kabos,The man who changed Shanghai,2013~04~24,www.ladislavhudec.eu,2015年12月8日。由于他是斯洛伐克族,在战俘营中被认为是“斯拉夫人”,故受到比其他同盟国战俘更好的对待。⑩Luca Poncellini,Júlia Csejdy,Hudec László,Budapest:Holnap Kiadó,2010,pp.11、12.
1918年4月,在丹麦红十字会的保证下,邬达克被允许搭乘火车回国。由于俄国内战,境内铁路交通陷入混乱,其所乘火车被迫停于贝加尔湖附近。当时正逢捷克斯洛伐克兵团叛乱,叛军在俄国各地强迫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战俘参加,不从者就地枪决,邬达克既不愿参加叛军又不愿坐以待毙,最终选择逃往中国东北。几经周折抵达哈尔滨后,他在当地丹麦外交官的帮助下,于1918年10月来到上海。⑪Luca Poncellini,Júlia Csejdy,Hudec László,Budapest:Holnap Kiadó,2010,pp.11、12.
借助自己的建筑专业背景,邬达克很快在上海找到了工作,担任克利洋行(Rowland A.Curry)助理建筑师。1922年,他与德国富商的女儿结婚,婚后设计和修建了自己的第一幢住宅。⑫华霞虹:《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21、43页。1925年,他在横滨正金银行(Yokohama Bank)大厦成立事务所,开始独立创业,其业务不仅面向西方客户。中国政府就曾委托他设计和建造西门妇孺医院。⑬Hudec Cultural Foundation Hudec Heritage Project,Biography,2015~11~3,www.hudecproject.com,2015年12月8日。
1929年,邬达克前往美国,在纽约和旧金山等地考察摩天楼的发展近况,着手设计上海国际饭店(Park Hotel)。国际饭店是他建筑师生涯中的经典之作,曾享有“远东第一高楼”之美誉。⑭华霞虹:《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21、43页。从这时起到1937年,是邬达克的多产时代。其间他设计了上海一系列赫赫有名的建筑,例如大光明大戏院(Grand Theatre)、斜桥弄巨厦(P.C.Woo's Residence)和达华公寓(Hubertus Court)。
1942年,邬达克被任命为匈牙利领事馆驻上海的荣誉领事。他虽没有实权,但却不顾个人安危,直率抨击法西斯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①上海匈牙利人5%左右是犹太出身,参见Hudec Cultural Foundation Hudec Heritage Project,Biography,www.hudecproject.com, 2015年12月8日。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1947年初,看到国民党政府已经出现衰亡征兆,邬达克带着家人离开了自己生活和工作近30年的中国。之后他定居美国,告别了自己倾注半生心血的建筑事业,进入加州大学潜心研究宗教和考古。1958年,在伯克利的家中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65岁,依照其遗愿,遗体最终归葬故土。②华霞虹:《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第25页。
综上所述,一战期间奥匈战俘出现在中国,与战争的进行及中国战时国际身份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一群体虽处历史之边缘,却依然能够折射出那一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变迁。身在中国、来源不同的两类奥匈战俘,尽管遭遇大不相同,战俘个体的境况也存在天壤之别,但作为战争的产物,战俘整体的命运无疑是不幸的、悲惨的。在战乱频仍的岁月里,他们不仅寄居异乡甚至流离失所,还要遭受交战国政府的利用与怀疑,多数人生存在国家间政治博弈和军事对抗的夹缝之中。不过,中国多处战俘收容所的人道帮扶,天津德国助赈会等组织和个人的善举,以及邬达克之辈身处逆境仍奋进不已的事迹,还是令人透过战争阴云看到一丝光亮,感受人性的纯美。而以上种种所引发的,更是今人反思战争、品味历史的心灵拷问。
Austro-Hungarian Prisoners of War in China during World War One
During the Great War millions of Austro-Hungarian soldiers fell into their enemy countries’captivity.Many of those detained by the Russian authorities managed to flee towards Manchuria, receiving aid from neutral China and from their countries’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In 1917, Beijing declared war on the Central Powers,subsequently resulting in the Austro-Hungarian Legation Guard as well as the Tianjin Marine detachment beingdisarmed and interned in Beijing. Some ofthe dissatisfied Siberian refugee POWs had conspired against their country’s consulates, while others later found fame and fortune,like Shanghai’s modern architecture’s vanguard Ladislav Hudec.By examining this special group of POWs,it sheds light o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social and historical changes.
Austro-Hungarian Prisoners of War,World War One,Tianjin German Relief Fund(Hilfsaktion),Austro-Hungarian Concession,LadislavHudec
K2
A
0457-6241(2017)10-0042-07
马加什(M atyas.M ervay),匈牙利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在华外侨生活、中奥匈关系史、天津奥匈租界史的研究。
【责任编辑:杨莲霞】
2017-03-27
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