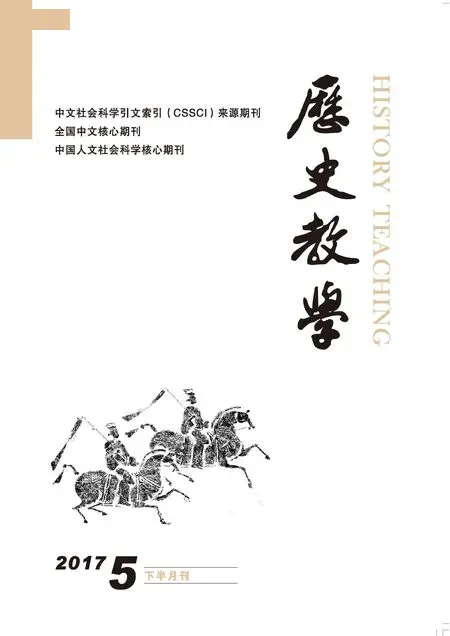20世纪70年代以来加拿大印第安人土地权利建构
——以尼斯加族为例
杨令侠 徐 天
(1.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1;2.美国天主教大学,华盛顿特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加拿大印第安人土地权利建构
——以尼斯加族为例
杨令侠1徐 天2
(1.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1;2.美国天主教大学,华盛顿特区)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尼斯加族,是从未与任何政府签订过任何条约的印第安人族群。1973年他们再一次启动争取原生土地权利的程序。经过20多年与联邦政府和省政府的谈判、协商后,三方终于在1998年签订了《尼斯加最终协议》。这个协议改变了加拿大其他印第安族群争取土地权利的进程。然而,尼斯加族在谈判过程中不得不以适应主流文化为代价,做出让步。因此,他们得到的土地权利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加拿大,印第安人土地权利,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尼斯加族
加拿大1982年新增宪法《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规定,加拿大的土著民族,①据2015年10月加拿大官方统计,加拿大总人口为3598万,土著人口117万。http://www.statcan.gc.ca/pub/89-645-x/20100 01/,2015年12月20日。包括北美印第安人、②North American Indians,是加拿大最早的居民之一。他们更愿意用“First Peoples”(原住民)称呼自己,以示是第一批来到现在称为北美洲这个地方的人。加拿大官方亦称印第安人为“First NationsPeople”。梅蒂人和因纽特人。自古以来居住在今天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纳斯河流域的尼斯加族群(Nisga’a Nation)是北美印第安族群之一,现今约有6000人。③http://www.statcan.gc.ca/pub/89-645-x/2010001/,2015年12月20日。无论在英属殖民地时期还是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成立之后,他们对原生居住土地的诉求一直得不到实现。这个为自己土地权利与各种政府抗争了一个世纪的民族,在20世纪70年代再次开启争取土地权利的努力,终于在1998年与省政府和联邦政府签订了一个历史性的条约——《尼斯加最终协议》(The Nisga’a Final Agreement)。可能连尼斯加人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个协议不仅改变了尼斯加人自己,也改变了解决加拿大印第安事务的路径。
对加拿大印第安人权利问题,国内学者做过一些有益的研究,④姜德顺:《加拿大土著民艰辛的维权之路——解读“土著权利”和“条约权利”》,《世界民族》2007年第10期;丁见民:《二战后加拿大土著民族政策的演变》,《历史教学》2010年第4期;陈巴特尔、高霞:《民族文化自觉与国家权利介入——加拿大土著族群语言的保护》,《暨南学报》2011年第3期;郭跃:《加拿大土著民族土地权利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第8期;徐利英:《从契约与法案看加拿大土著民族的权利演变》,《科学经济社会》2013年第3期;王助:《加拿大土著人身份法律确认的演变及现状》,《世界民族》2007年第5期,等。但是对印第安人土地权利的研究,却不多见,而国外却有针对尼斯加族土地权利问题的细致研究,⑤Alex Rose,Bringing our Ancestors Home:The Repatriation of Nisga’a Artifacts,Gitlaxt’aamiks(formerly New Aiyansh),BC:Nisga’a Tribal Council,2000;Alex Rose,Nisga’a:People of the Nass,Madeira Park,BC:Douglas-Mcintyre Press,1993.有代表性的论著也不少。汤姆·莫洛伊撰写的专著《世界是我们的证人:尼斯加人在加拿大的历史》⑥Tom Molloy,The World is Our Witness:The Historic Journey of the Nisga’a into Canada,Markham,ON:Fifth House Publishers, 2006.更像是一部尼斯加人和政府的谈判史,因为他本人曾是政府方的主要谈判者。除了追溯尼斯加人的历史外,该书主要细致地表述和分析了《尼斯加最终协议》签订的细节,以及不同政治集团的不同政治目标。特蕾西·利·斯科特的《殖民地时期后的主权国家?——尼斯加人的最终协议》①Tracie Lea Scott,Postcolonial Sovereignty?—The Nisga’a Final Agreement,Vancouver:Purich Publishing Limited,2012.从主权这个概念出发,认为通过最终协议,尼斯加这个“nation”部分地实现了他们还原祖先土地的夙愿。亚历克斯·罗斯的专著《马佳町口湖的魂之舞:格斯纳尔首领和尼斯加条约》②Alex Rose,Spirit Dance at Meziadin:Chief Gosnell and the Nisga’a Treaty,Madeira Park,BC:Harbour Publishing,2000.的价值不仅在于使用了一手资料,探究了尼斯加族从未与白人接触前到当代的历史细节,而且作者与“尼斯加部落议事会”一起为条约的制定工作了11年,熟识原住民领导人。该书在附录中列举了相关书目和大事年表,对理解尼斯加文化和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的历史都有很大帮助。作者认为,尼斯加协议虽然没有彻底解决印第安权利问题,但的确为尼斯加族群创造出一种其他非尼斯加人尚未进入的自治的途径。瑞克·庞廷撰写的《尼斯加条约:在比较语境中探寻动态和政治传播学》③Rick Ponting,The Nisga’a Treaty:Polling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Comparative Context,Peterborough:Broadview Press,2006.一书,提供了大量不列颠哥伦比亚政府公开的观点和支持尼斯加条约的宣传,但几乎没有涉及政府政策的决策过程以及条约的细节。作者采用问卷形式对几个印第安族群的群体动态做了调查和分析。
本文以尼斯加族争取土地权利的斗争为例,探讨现代加拿大印第安人土地权要求的依据、发轫、特点和复杂性。
一
欧洲大陆的白人到达并统治加拿大这个地方后,曾与一部分印第安人签订条约、划定保留地,并提供补助;尼斯加人则从来没有机会与白人签订任何条约。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成立后,尼斯加族的土地权利并没有得到解决,其许多原生居住地被宣布为王室的领地。他们多次向联邦政府请愿,要求政府承认尼斯加人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和监管权,但始终没能和政府签订过任何协定。
加拿大印第安人权利包括很多内容,比如语言文化权利、资源开采权利和选举权利④加拿大土著民族选举权获得的时间相比美国要早,分联邦和省两级。鉴于土著民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联邦政府1917年颁布《军人投票条例》,其中确认在加拿大或英国军队中现役的土著军人享有选举的权利;1950年和1960年分别承认因纽特人和具有条约身份的土著人的选举权。省一级的土著民族选举权获得情况则差别很大,比如1949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第一次赋予没有条约身份的印第安人省内选举权,1969年魁北克省赋予没有条约身份的印第安人和有条约身份的印第安妇女省内选举权。等,其中土地权利的获得过程最长、也最艰难。位于加拿大最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全国最早孕育现代印第安人土地权利体系的省份,但是在历史上,却以亏待印第安人而闻名。实际上,50、60年代之前,在整个加拿大,印第安事务都处于不被重视的状态。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约有40多个印第安族群。早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⑤即新法兰西时期(1608~1763年)。就有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历史。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拥有对加拿大在内的北美洲大部分地区的直接控制权,直到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建立。英属殖民地的加拿大继续根据条约划定印第安人保留地。这两段殖民地历史,使加拿大的土著民族在成分上更加多样,⑥比如梅蒂(Meiti’s)这个民族,即印第安人与法国人(后通指白人)的混血后裔,世界上只有加拿大独有。并且较早地与殖民地政府确立了权利关系。
对印第安人土地权利的界定,概括起来大致为三种,即“原生居住权利”“条约中权利”和“非条约权利”。
“原生居住权利”是指印第安人事实上的对原生居住地的权利。而历史上,他们曾经拥有构成现在加拿大的绝大部分疆土。况且1763年《皇室公告》(Royal Proclamation)⑦七年战争后,为了稳定北美这块新殖民地,英国殖民政府以承认加拿大印第安人对土地拥有部分权力为代价,换取土地与和平。《皇室公告》中涉及北美印第安人的内容有,划定印第安人的狩猎和捕鱼范围、规定只有殖民政府才能就土地事务与印第安人进行谈判、土著族群附属于英国皇室。该公告的意义在于,它是第一个涉及加拿大土著族群和欧洲殖民者之间土地关系的协议。也曾这样肯定过,即,在白人与印第安人未签订条约之前,印第安人具有原生的土地权利。⑧《皇室公告》是第一个涉及北美印第安人土地的协议,其重要意义在于首次确定土著民族和欧洲殖民者的关系。但是,主流社会一直不肯认可这个理念,并要求土著——这些没有文字的族群,拿出他们曾经拥有大片土地的证据来。
“条约中权利”是指印第安人同法国殖民政府、尤其是英国殖民政府、①1857年英国殖民政府还曾颁布《渐次开化法》,用财产和金钱鼓动加拿大印第安人脱离部族社会,进入“文明”的生活方式,以寻求“解放”;1859年又通过《开化与解放法》,但只有少数印第安人为换取解放而放弃自己的身份和权利。甚至后来的联邦政府签订的许许多多条约中规定的权利。凡签约“注册”的印第安人被叫做“条约印第安人”,其可享受有限的权利,并受到当时的殖民政府和后来的联邦政府的保护,因此加拿大印第安人对英帝国怀有明显的归属意识。这种传统构成了加拿大土著民族历史的独特性和法律权利的基础。加拿大大部分印第安人较早就与英国殖民政府或联邦政府建立了包括土地归属在内的条约关系。
“非条约权利”是指那些没有同各种政府签订过任何条约的印第安人的权利。这部分权利最脆弱,也最难取得和保护。不幸的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中大都是“非条约印第安人”,因而遭受了因未签订条约而被夺走土地的待遇。况且,在英帝国与温哥华岛上的印第安人签订14份条约(1850至1854年)之后,该省的条约缔结进程就停滞了。②“Our HomesAre Bleeding”,in“Background on Indian Reservesin British Columbia”,http://www.ubcic.bc.ca/Resources/ourhome sare/,2012年2月17日。此后省政府挤占原住民生存空间的情况愈演愈烈。
作为新生国家的宪法,1867年的《不列颠北美法》不仅沿用了英国的许多政体形式,而且承袭、肯定了英属殖民地时期的关于印第安人的契约和协定,其中的《印第安人法》是联邦政府颁布的第一个针对加拿大土著民族的法。③徐利英:《从契约与法案看加拿大土著民族的权利演变》,《科学经济社会》2013年第1期。它从宪法层面上肯定了印第安人的权利。自治领建立后,加拿大为避免发生美国内战那样的状况,着意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印第安事务自然划归联邦一级的政府管理。《印第安人法》赋予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力以控制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至于那些在殖民地时期注册过的印第安人,在联邦法律上也被认同是印第安人或条约印第安人,继续享有特定的权利和利益。
1871至1921年间,联邦政府与落基山西部多地印第安人进行了大量的和平谈判,将缔约范围推进到加拿大西北部,不仅成功地缔结了《条约1-11》(Treaties 1-11),协调土地和资源等问题,而且奠定了政府与印第安人交涉的方式。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1876年签订的《条约6》和《条约7》允诺,如遇饥荒,联邦政府将提供条约中印第安人健康服务和食品等。加拿大历史上也存在迫害、杀害印第安人和强占其土地的情况,但没有大规模杀戮印第安人的记载。
联邦政府在建国初期只对土著民族中的印第安人颁布法令或与签订条约,是因为其他两个民族,即梅蒂人和因纽特人的地位更低,其受歧视和被边缘化的程度更深。历史上,居住在加拿大西部红河地区的梅蒂人的土地权利更得不到保障与索取条件,19世纪后半期两次梅蒂人起义即缘于此故。④加拿大自治领成立后,在向西拓展土地、修建太平洋铁路和移民的过程中,梅蒂人的生存空间被侵占,不得不放弃游猎生活。19世纪末,加拿大大部分印第安人已经移入保留地,开始农耕生活,但梅蒂人不被划入印第安人之列,所以得不到政府的保留地补贴,而且连土地权利也丧失了。其土地被政府卖给新移民,他们成了非法占地者。与联邦政府多次协商不成,梅蒂人分别于1869年和1884年在路易·里埃尔领导下发动了两次武装起义,并得到一部分印第安人的支持。两次起义都很快被镇压下去。里埃尔被判叛国罪,处以绞刑。及后,1968年联邦政府成立的“印第安人及因纽特人事务局”(Indian and Inuit Affairs),名称上竟没有显示梅蒂人。因纽特人则长期与世隔绝,生活在北极极地和次极地。
自治领成立后颁布的《印第安人法》和缔结的《条约1-11》,并没有惠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印第安人。1887年1月,尼斯加等土著民族的首领们乘着小船到达维多利亚内港,向省政府寻求他们认为没有补偿、没有条约就被“偷”走的土地。当他们进入省立法机关大门时,省总理威廉姆·史密斯拦住了他们。他告诉这些印第安首领,“先让白人进。你们比牧场上的牲畜强不了哪去”。⑤Alex Rose,Spirit Dance at Meziadin,p.2.加拿大全社会对印第安人的歧视直到20世纪初也未见改善。
为了更有力地争取权利,印第安人组织起来,分别于1921年成立了“加拿大印第安人联盟”(The League of Indians of Canada)、1930年成立了“艾伯塔印第安人协会”(The Indians Association of Alberta)、1944年成立了“萨斯喀彻温印第安人联盟”(The Federation ofSaskatchewan Indians)。
1951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出台了新的《印第安人法》;23年后的1969年,又颁布了《加拿大政府关于印第安人政策的声明》。前者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强制同化的传统方针,后者则以权利平等和赔偿为原则试图改善印第安人的政治法律地位。这两套文件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如战后政治和民权运动)下改造了僵化的印第安权利体系,但仍然没有改变白人主流社会单方操作的实质。1969年的《加拿大政府关于印第安人政策的声明》因印第安人表示不能接受政府的安排,并提出强烈的抗议,最终被束之高阁。①丁见民:《二战后加拿大土著民族政策的演变》,《历史教学》2010年第4期。
实际上20世纪上半叶,加拿大政府还不太重视印第安人权利及其相关事务,1936年到1950年间,联邦政府的“印第安事务监管”(Superintendent-General of Indian Affairs)竟然被划归“矿务资源部长办公室”(the Office of Minister of Mines and Resources)管理。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加拿大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好转,印第安人事务受到更多重视。1966年联邦政府组建“印第安事务和北方开发部”(Department of Indian Affairs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1968年重组为三个部门,即“印第安人及因纽特人事务局”“北方事务局”(Northern Affairs)和“加拿大国家公园事务局”(ParksCanada)。②1974年联邦政府又增设“土著人索赔办公室”(Office of Native Claims),负责协调政府与土著人之间土地资源纠纷;到了90年代末,关于印第安索赔的事务由“索赔科”(ClaimsSector)负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索赔事务由设立在温哥华的“联邦条约谈判办公室”(Federal Treaty NegotiationsOffice)负责。到60年代末,加拿大印第安人已经获得了较完整的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但遗留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没有解决那些未曾与各种政府签订过条约的印第安人的土地权利问题。
有的加拿大学者将美国与加拿大进行类比,认为两国对印第安事务的处理方式大同小异。③T.R.L.MacInnes,“History of Indian Administration in Canada”,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Vol. 12,No.3,1946,pp.387,388,390,392.这种看法是偏颇的,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忽略了两国印第安人权利的历史差异,由此忽视了加拿大印第安事务的特殊性。加拿大和美国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受欧洲文明的影响。美国在独立之前,其印第安事务与母国英国的关系,是与建国前的加拿大基本一致的。可是待美国彻底与英国脱离关系后,美国和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权利体系便进入了不同的轨道,并产生了各具特色的结果。加拿大印第安人一直保持与英帝国的传统政治纽带,接受英国殖民政府和加拿大联邦政府较为宽松的管理,因为尽管加拿大在1867年建国了,但仍旧是英帝国的一个自治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上与母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独立后的美国,印第安人则成为受到美国宪法严格管束的境内居民,经历了被同化、驱赶和部落制终止等政策的残酷洗礼。美国的印第安人更经常提及与美国政府的历史纠纷及其决议。美国印第安权利体系在联邦政府的塑造和泛印第安人运动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国家化。相应地,当代加拿大印第安人的权利建构,是在英帝国传统政治和法律纽带的重新解读中确立起来的,并逐步地方化,即省化。这也是加拿大土著民族事务的一大特点。
20世纪上半叶,加拿大印第安事务主要由联邦政府管理,其土地权利问题的解决模式,一是承认英属殖民地时期的有关印第安法规、条例的法律效力,继续以此为据;二是遵从国内现有法律。④加拿大的《印第安条约》(Indian Treaties)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条约,而是个包括年代很久远、囊括内容很复杂的集合名词,通指印第安人与法、英殖民政府和加拿大联邦政府,签订在1676年之后的、1754~1814年签约高峰期的、联邦前的、联邦后的和现代的20多类种的条约。这两者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第安人土地权利建构三个依据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二
随着宪法的解释,20世纪中期以后,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权力被一步步削弱。这竟令得尼斯加族对土地权利的追求经历更为曲折、复杂。20世纪70年代初,尼斯加族群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状告到联邦最高法院;调解无效后,到90年代初,不得不直接与省政府交涉谈判。这个转变也重新建构了印第安人追求土地权利的模式。
虽然20世纪50年代后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事务没有完全放权,但其一些权力已被逐渐转移到各省去了。加拿大印第安人土地权利体系的建构,便在各省政府权责的膨胀过程中被逐渐地方化了。以省为单位的印第安人维权运动,使得省政府成为建构印第安土地权利的第二个重要部分。与此同时,印第安人自觉意识加强,主动通过诉讼和谈判,使主流社会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印第安族群的独特诉求。印第安人土地权利诉求的谈判就形成了联邦政府—省政府—印第安族群三足鼎立的局面,尼斯加族的维权过程就是典型的事例。
就土地权利与联邦政府和省政府进行多次交涉未果后,在1973年,尼斯加族部落理事会的首领弗兰克·考尔德作为原告,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告到联邦最高法院,再次要求裁定有关土地所有权纠纷问题。尼斯加人上诉省政府,不是偶然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虽说是发轫现代加拿大印第安人土地权利体系之地,但在历史上,与其他省份相比,却对印第安人相对不公。“没有条约”是印第安人争取土地权利的软肋,没有自己的文字更增加了诉求的困难,所以到20世纪70年代,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印第安人仍旧没有寻回对传统土地的拥有权。这种极端现象在整个北美也是鲜见的,被学者称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特异性”(The British Columbia Anomaly)。①Christopher F.Roth,“Without Treaty,Without Occupation:Indigenous Sovereignty in Post-Delgamuukw British Columbia”, Wicazo Sa Review,Autumn,2002,p.144.德格姆卡案系1997年前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部印第安人打赢的与省政府的官司,获得了对印第安德格姆卡保留地的所有权。——作者注尼斯加人就是这些因未签订条约而丧失土地的印第安族群之一。
联邦最高法院的七位法官中有六位达成共识,认为1763年英国政府颁布的《皇室公告》确实可以证明,印第安人的原生土地权利是存在的。于是,最高法院对尼斯加人土地诉求案做出了重要判决:根据1763年《皇室公告》,在白人与印第安人未签订条约之前,印第安人具有原生的土地权利。这个判决的重要意义在于,联邦政府终于改变了之前对印第安人土地权利的看法,接受了“没有条约身份的印第安居民可以拥有土地权力”的观念。这个著名的判例被称为“考尔德案”或“考尔德诉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司法部长”。可能当初连尼斯加人自己也没有料到,此次状告省政府会影响日后全国印第安人土地权利建构的进程与方式。
1973年的判决确认了印第安人的“原生土地权利”,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为它广泛承认了“非条约”族群的土地权,将这类族群曾经的最大劣势转变为其维权优势。
同年,当政的皮埃尔·特鲁多政府(1968~1979年;1980~1984年)对此事明确地表明其基本立场,即非条约印第安人的索赔要求必须解决,而解决的最佳途径是谈判。联邦政府的鲜明立场是与1971年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国家政策②20世纪60年代初,加拿大创造出“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这个概念,并于1971年使之成为“国家政策”,使用至今。的颁布有关,更与加拿大是一个谈判机制非常发达的国家有关。③甚至这个国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与英国母国谈判谈出来的。参见杨令侠:《加拿大国民性刍议》,《历史教学》2007年第10期。自1973年这次著名的“考尔德案”判决后,“谈判”开始被认定为解决印第安权利最有效的形式。同一时期,美国也开启了印第安人土地谈判和自治进程,北美的印第安人权利进入了一个新的建构阶段。
土著民族的权利要求和主动参与,成为建构当代加拿大土著民族权利的重要元素。1968年“加拿大全国印第安人兄弟会”成立。1971年因纽特人成立了“加拿大因纽特人联盟”(Inuit Tapirisat of Canada),1976年提出建立自治政府的要求。1975年魁北克的印第安人与联邦政府签订《詹姆斯湾与北部魁北克协定》。1986年因纽特人召开了第一届首领大会;1992年与联邦政府谈判终于成功,达成协定七年后从加拿大原西北地区为因纽特人划分出一个自治行政区。1999年4月1日,因纽特人的努纳武特自治区正式建立。加拿大土著民族的这些维权活动都坚定了尼斯加人的维权意志。
1976年,联邦政府与尼斯加族的谈判开始启动,然而漫长的维权过程才刚刚开始。土地归属不清是谈判的最大障碍。虽然联邦最高法院承认了印第安人的原生土地权力,但是《皇室公告》所承认的土地权利范围非常不明确,因为“七年战争”后,北美全部属于英国统治,当时加拿大西部的边境还未确定。此外,印第安人如何证明哪些土地是他们自己的,是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印第安人没有文字,在上诉时,法院是否承认并接受他们作为证据的口述史的有效性,是他们能否拥有土地权力的关键。
1990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加入联邦政府与尼斯加族的谈判,三方格局确立,尼斯加人诉求的最终实现才有了可能。如果说,加拿大联邦政府多少能为印第安人维权提供大多数依据,那么省政府则给印第安人带来的是实际限制,而省政府在印第安人土地权利建构中扮演的角色,有时比联邦政府更为直接和重要。联邦政府与印第安族群的对话,由于省政府的介入变得更为复杂,并且需要省政府的支持才能产生效果。这种现象在加拿大中西部各省体现得尤为明显。
20世纪90年代后,为了表明坚决捍卫土地权利的态度,包括尼斯加人在内的印第安人经常在土地归属不明的地区设置路障,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开发自然资源的行为加以干涉。他们在土地所有权存在争议的公路、私人伐木路和铁道上当道而立,封路的时间短则一小时,长则四五日。在1990年,该省路障事件的数量呈井喷状态,20余个族群先后发动了30余次设置路障的活动,路障一时遍布全省。①NicholasBlomley,“Shut the Province Down:First Nation Blockadesin British Columbia”,BC Studies,No.3,1996,p.10.
受到1990年三方谈判的推动以及路障运动的刺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于1991年启动了面向全省印第安人的“不列颠哥伦比亚条约进程”(British Columbia Treaty Process,简称“条约进程”),并设立“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条约委员会”对实施过程进行监督。1996年,尼斯加人与省政府、联邦政府的谈判进入全面诉求阶段,包括土地诉求在内的一系列特定的政治和经济自治权等内容被纳入谈判范围;同年,谈判三方向全社会公布了《尼斯加协议草案》;1998年,《尼斯加最终协议》(亦称《尼斯加条约》)正式签订。
《尼斯加最终协议》具有非凡的意义。这是尼斯加人与政府签订的首个条约。它不仅填补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近百年来没有土著条约的空白,并且重新定义了联邦—省—原住民之间的关系。尼斯加族群争取土地权利的模式首先普及到全省,之后,影响到全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土地权利的建构。1998年6月28日,加拿大联邦、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两级政府与“原住民峰会”的代表们共同在一份名为《不列颠哥伦比亚诉求专案组报告》(The Report of the British Columbia Claims Task Force)的文件上签字。该文件表示:“原住民、加拿大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三方应在相互信任、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通过政治谈判建立全新的关系。”②“Mission Statement:Monitoring Adherence to the BC Claims Task Force Report”,http://www.bctreaty.net/files/about us.php,2012年2月6日。这次三方合作的框架,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尼斯加案例的经验。
《尼斯加最终协议》于2000年5月11日生效。通过这项协定,尼斯加人获得了可观的土地所有权和空前广泛的自治权,但同时也损失重大。“该协议的签订并不意味两级政府做得很好,相反,可以看出政府还没有准备好去完全地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去承认少数族裔的平等性;协议从各个方面限制了尼斯加人的土地权利。”③Paul Rynard,“‘Welcome In,But Check Your Rights at the Door’:The James Bay and Nisga’a Agreements in Canada”,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3,No.2(Jun.,2000),p.212.
《尼斯加最终协议》规定,尼斯加人收回纳斯河谷下游1992平方公里土地的所有权;拥有其地上和地下的所有矿产和森林资源;获得1亿9千万加元的财政补偿;通过一段过渡期后,必须上缴所得税和营业税;放弃未来向联邦政府提出土地诉求的权利。④J.Rick Ponding,The Nisga’a Treaty:Polling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Comparative Context,Peterborough:Broadview Press,2006,pp.137~138.也就是说,尼斯加人在获得土地的同时,丧失了过去享有的保留地免税的权利,以及日后再就土地问题继续上诉的权利。
该协议确立的原则,构成了当代加拿大印第安人争取土地权利的一个新范式。这个范式的积极意义是,它以白人与印第安人在殖民地时期的关系为依据,以国内法为指导,实现印第安人参与族群政治进程、重构自身权利体系的目标。它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也是加拿大联邦政府与原住民关系史上的重大突破,是现代史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签署的第一份印第安土地诉求协定。它的意义在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印第安人改写了长期由白人掌握的游戏规则。
从上述条款中亦可看出,在印第安人土地权利得到维护的同时,加拿大的国家权威也得到了严格的再确认,即印第安人的部分特权被清晰地终止或修改了。这样的谈判结果,只反映特定族群的特定需求和妥协限度。但随着尼斯加范式被借鉴到全省乃至全国的“条约进程”,即特定的谈判结果被逐渐制度化后,引发了政策制度化与单个族群特殊性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当主流制度的框架在印第安族群中确立起来的时候,当代政治整合、经济模式和主流文化也随之进入了印第安人的日常生活。
三
在“条约进程”中,由于主流社会在政治和社会资源上的绝对优势,当西方法律概念与印第安人的诉求发生矛盾时,往往是印第安人一方削足适履,调整自己原有的诉求以适应主流社会的“制度装置”。①关凯:《族群政治》,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6页。尼斯加族在获得土地权利后,同样难脱其“臼”。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至今已有尼斯加人、查瓦森(Tsawwassen)人建立了完全意义上的自治政府,其自治模式和权力限定大体相同。虽然自治政府的权利构成看似合理,但是很多观察家和印第安族群成员都怀疑,这种自治方式并没有承袭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和管理习惯。②Graham White,“Treaty Federalism in Northern Canada:Aboriginal-Government Land ClaimsBoards”,Publics,Vol.32,No.3,2002, p.111.为获得自治,印第安人不得不在主流社会的政治框架内寻求政治自主,关键问题是,印第安人与主流社会对“土地”和“权利”等概念的理解是相当不同的。
从印第安人的角度来看,自治权意味着本族群的任何事务不受族群之外的任何人管辖。根据这个理念,“土地”意味着土地上下的一切,包括自治、资源、文化、生产生活方式,甚至语言;“土地”不是政府让与的,而是各个印第安族群自始就享有的。但对于主流社会来说,自治的前提和方式,都只能由主流社会控制并规定。③Graham White,“Treaty Federalism in Northern Canada”,p.98.主流社会还担心自治会使加拿大土地上出现以民族为单位的政府,④John Dawson,“Treaty not Perfect,but Let'sDo It”,Times Colonist,A3,12/7/1998.实际情况却是,自治政府在形制上与省内其他自治实体是一样的,唯一的特异性是族群构成单一。和其他地方政府一样,印第安人的自治实体也要经省府授权、对省府负责,参与全省乃至全国的税收活动,运用国家法律而不是印第安人习惯法来判决族群内部的纠纷。除此之外,自治政府建立起的警察系统、招商系统⑤具体事例可参见尼斯加自治政府官方网站中有关招商引资的介绍,http://www.nisgaalisims.ca/files/nlg/u3/Nass%20Region, 2012年4月20日。正在对族群社会加以重新整合。印第安人独特的部落协商制度和土地文化被政府分工和商业精神所浸染。印第安人自治政府与主流社会的兼容度越来越高。
根据《尼斯加最终协议》,印第安人拥有合法开发利用土地的权利,但同时又对土地持有恒久的、不可推卸的维护责任。这便是西方法律文化中的“所有权”和“财产”的概念不能概括印第安人土地观的一个例子。在印第安人观念中,土地归属他们是天经地义的;如果说自己的土地荒疏着就会犯法,那是不可思议的。⑥Paul Nadasdy,“‘Property’and Aboriginal Land Claimsin the Canadian Subarctic: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104,No.1,2002,p.248.但省政府认为,“所有权”的界定已经为经济发展提供“确定性”,⑦“确定性”是指,原住民与政府通过条约的方式,明确区分彼此的土地边界和权责界限,直到双方不再有任何悬而未决的争议为止。参见Carole Blackburn,“Searching Guarantee in the Midst of Uncertainty:Negotiating Aboriginal Rightsand Title in British Columbia”,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107,No.4,2005,pp.586~596.以后的事就是要土地为省的经济繁荣做贡献。尼斯加人与不列颠哥伦比亚政府在土地经营观念上的冲突,反映了原住民逻辑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张力。
鉴于印第安人对土地在法律方面的认知淡漠,省府“条约委员会”特编印宣传手册《为什么是条约?——从法律视角解释》。该手册开宗明义地讲:“(与土著人)签订条约是我省未竟的事业。这一未完成的事业,导致大面积土地所有权的‘不确定’,使我省经济每年遭受巨大损失。”⑧“Why Treaties?—A Legal Perspective”,http://www.bctreaty.net/files/pdf_documents/why_treaties_update_Aug08.pdf,2012年2月6日。签订条约是省政府为了减少非原住民人口的经济损失的一个途径,其手段是“用法律从技术上保证条约不遗漏任何一种权利和义务,并确保没有任何未被定义的权利流失到条约之外”。⑨Mark L.Stevenson,“Visions of Certainty:Challenging Assumptions”,in Andrew Woolford,“Negotiating Affirmative Repair:Symbolic Violence in the British Columbia Treaty Process”,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29,No.1,2004,p.115.由此看来,这些土地在按照西方法律程序移交到印第安人手中之时,也是印第安人开始承担一系列条约责任和义务之日。印第安人对土地传统的松散的管理、甚至不管理,在条约之后已经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了。加之《尼斯加最终协议》中具有“该族群可以出让由条约所得的任何一部分土地的使用权”①“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Nisga’a Tribal Council-Government of Canada:Nisga'a Final Agreement”,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Vol.37,No.6,Nov.1998.这一条款,为了生计,有的印第安人也只有出让、转卖刚到手的土地。印第安人对土地应承担的维护义务,使得刚刚获得的土地又脱手而出。白人社会的法律把印第安人瞬间引入了土地交易的时代。印第安人与土地之间的天然纽带,在条约进程中被永远地资本化了。
尼斯加族以条约的形式为本族群落实了土地权利,但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因为它提出了一个过去很少提及的问题,即印第安人的土地所有权是仍旧属于集体,还是像其他加拿大人一样,属于个人。因为在欧洲人来到北美大陆之前,包括尼斯加人在内的印第安人的土地所有权是集体所有,而非个人所有。这个概念(collective or individual ownership)也将引起加拿大其他印第安人族群关于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新思考。
《尼斯加最终协议》的另一个表现文化强权的方面,在于它的“不可修正性”。在谈判中,联邦政府和省政府都坚持“签订条约的原住民,在未来将不能向法庭寻求其权利的扩大”。②Mark L.Stevenson,"Visionsof Certainty:Challenging Assumptions”,in Andrew Woolford,“Negotiating Affirmative Repair:Symbolic Violence in the British Columbia Treaty Process”,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29,No.1,2004,p.126.
印第安人在不得不接受“条约不可修正性”这一原则的同时,“条约进程”还加剧了印第安人生活、生产方式的主流化。他们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谈判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尼斯加最终协议》中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有关经济权利和政府赔偿,譬如政府承诺尼斯加人获得了矿产和森林的开采权,以及原来被省政府夺去的纳斯河谷捕鱼权;政府将分阶段向尼斯加自治政府支付财政补偿等。生活条件的提高,需仰赖原住民经济的发展。原住民经济要想在生产社会化的时代获得发展,就需要改变原有的以渔猎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民族传统和现代生活之间,印第安人的心理天平不得不有所倾斜。当印第安人收回日思夜想的矿产和森林开采权时,马上面临资金短缺的窘况。他们只能与主流社会“合作”,通过贩卖原材料和土特产维持生计。主流社会的产业结构就会反客为主,把印第安人的自然资源和经济生活卷入其中。
尽管尼斯加人居住在风景秀美、森林茂密的纳斯河谷,但并不富有。旅游、捕鱼和蘑菇采摘业工资很低,且有季节限制,而大型的资源加工工业则需要尼斯加人支付不起的资本和专业技术。那些外来的持有营业执照的大公司,高薪聘请非印第安的专业人员,而印第安人只能做些短工粗活。因此,《尼斯加最终协议》签订之后,三分之二的尼斯加人住在领地之外,失业率达60%。③Richard Wright,“The Nisga’a Experiment”,Property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 Report,Vol.32,No.2,(Autumn/Winter) 2013,http://www.perc.org/articles/nisgaa-experiment.
从保持原住民独特性的角度来看,生产方式的改变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流失。原住民既希望自己的生活可以提升到与主流社会一致的水准,又想同时保持自身文化与主流文化不一致的状态。他们不愿放弃更好的生活,而更好的生活却经常以“融入主流”为代价。
《尼斯加最终协议》试图纠正不平等的经济框架,减少社会差异,而原住民更注重长期被忽视的文化身份、树立群体文化的独特性。《尼斯加最终协议》的最终效果引起了更多人参与的大讨论。
四
《尼斯加最终协议》震动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乃至整个加拿大社会,许多加拿大人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都卷入这个热议的话题。这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没有停止过的、针对印第安人权利再建构的争论,增加了加拿大族群政治新局面的不确定性,也把公民权利、国家政治架构和土著权利独特性的争论,与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国家秩序稳定和族群政治优化等问题纠结在一起。
在1867年建国时,加拿大的国父们就把“和平、秩序和良好的管理”作为宪法追求的目标,而加拿大社会也一直崇尚稳定、有序和宪法的尊严。现代印第安人争取的权利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加拿大学界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支持合法性的学者认为,既然“条约进程”把印第安权利建构问题制度化了,那么条约的约束力就是至高无上的;大家都应该崇尚政治结构的稳定性,把印第安人基于土地的自治权看作“条约式的联邦主义”,①Graham White,“Treaty Federalism in Northern Canada”,p.101;Kirsty Gover,“Comparative Tribal Constitutionalism:Membership Governance in Australia,Canada,New Zealand,and the United States”,Law&Social Inquiry,Vol.35,No.3,2010,pp.689~762.因此将印第安人的土地、自治等权利纳入现有政治架构是完全合法的。但也有不少学者质疑这种合法性,认为印第安人所争取的权利已经超出了加拿大现行制度的界限,会对国家的稳定性和联邦的完整性产生冲击。②W.Thomas Molloy,“A Testament to Good Faith:The Process and Structure of the Nisga'a Negotiations--A Federal Negotiator's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inority and Group Rights,No.11,2004,pp.251~258;Kathleen M.Sullivan,“Landscaping Sovereignty in British Columbia,Canada”,Polar: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Vol.29,No.1,2006,pp.44~65.不少学者在媒体上发表言论,以国家认同和政治架构受到威胁为由,抨击印第安人的维权行动。
在权利合法性这一问题上,相关研究以具体案例为常见,而其中又以针对尼斯加族群和德加穆库(Delgamuukw)族群的研究为最深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卡罗尔·布莱克本把考察集中在尼斯加族群上。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她发现,这一族群在维权过程中虽然强调自主权利和文化独特性,却没表现出分离主义的倾向,恰恰相反,族人对加拿大政府及其制度非常尊重,一直努力寻求用现有的制度语言表达自身文化的传统诉求。③Carole Blackburn,“Producing Legitimacy:Reconciliation and the Negotiation of Aboriginal Rightsin Canada”,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No.13,2007,pp.621~638.克里斯托弗·罗斯认为,德加穆库族群、尼斯加族群与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民族问题缓和的重要保障,条约使印第安人与土地的关系、口述资料在谈判中的价值等问题得到了澄清,是加拿大内政方面的进步。④Christopher F.Roth,“Without Treaty,Without Occupation”,p.160.哈马尔·福斯特的文章⑤Hamar Foster,“Honouring the Queen’sFlag:A Leg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Nisga’a Treaty”,BC Studies,120(1998/ 1999),p.30.认为,《最终协议》既不违反宪法,也不是以某个种族为目标,只是解决历史问题而已。
在实际谈判过程中,除了经费匮乏,证据不足一直困扰着印第安人。法院和谈判机构对印第安人口述史的法律效力的否定,是证据不足的主要原因。尼斯加人的土地观念决定了他们的政治观念,即他们与土地的自然纽带、对土地的传统占有是确立族群身份和自治权的基础。虽然尼斯加协议最终在加拿大的国内法体系中争取到一席之地,但却与西方法理中的自然权利(基于个人)有所不同,因此这类领土纠纷解决起来就遇到国内和国际多重困难。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学者担心尼斯加协议影响的扩展会动摇加拿大的主权基础和宪法基础,怀疑以联邦为约束、以省甚至族群为单位的主权解释。在加拿大的政治框架下,尼斯加协议似乎建构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混沌地带。这也是协议引发大讨论的政治原因。
一些加拿大学者还考察了原住民维权运动的文化含义。保罗·纳达斯蒂研究了主流社会的话语语境,专门论述印第安人与主流社会在土地观念上的差异,认为:“强迫原住民使用所有权的语言去思考和辩论这件事,已经破坏了土地权利协定本应保护的印第安人的信仰和行为。”⑥Paul Nadasdy,“‘Property’and Aboriginal Land Claimsin the Canadian Subarctic”,pp.247~261.安德鲁·伍尔福德的研究则更进一步。这位学者指出,主流社会在面对印第安人维权运动的时候,谈判的预设就是不平等的,因为“修补历史伤痛的愿景,往往囿于当今实用主义的考虑”;实用主义的考量,使主流社会在与印第安人对话时无法真正从尊重异己文化的角度出发,甚而南辕北辙,用程序正义、制度设置等理由钳制印第安人的诉求;“程序”“联邦”“普适性”这些主流社会标榜的文化符号,对印第安人形成了一种“软暴力”。⑦Andrew Woolford,“Negotiating Affirmative Repair”,p.111.
印第安人本身也认识到了当代权利体系中潜藏的某种“文化霸权”。一部分印第安族群从一开始就拒绝“条约进程”的安排,认为“条约进程”是对印第安主权的出卖。1995年,不少没有参与到“条约进程”的族群再次设置路障,抵制“条约进程”的扩展。
上述言论在最初印第安人普遍接受“条约进程”的潮流中显得极不合群,但在“条约进程”实行约十年以后,许多当年接受“条约进程”的印第安族群也开始对这一制度表示出相似的不满情绪。1999年4月22日,不列颠哥伦比亚“原住民大会”副会长萨特桑,在抱怨加拿大最高法院在条约谈判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时说:“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各级政府对我们说,我们已经替你们准备了最好的方案,你们只要遵循它就准没错;如果你们想提起诉讼,诉讼过程要花很长时间和很多钱;况且你们是搜集不到赢得诉讼的证据的。他们就这样直接把这些话说给我们听。”①
为了摆脱被主流社会同化的命运,当代印第安人在维权过程中强调本民族的独特性,并尽力使主流社会接受之;同时又试图用印第安文化观念重构西方话语中的“权利”,严格界定印第安人权利的界限,将特定权利的形式和内容印第安化。这些努力在建构多元的权利观念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比如,尼斯加人在维权过程中提供了一种新的“公民权”定义,即权利与领土之间的重要联系。他们借鉴了自由主义理论中关于公民权利和现代民族国家的论述,希望以此说服主流社会,承认原住民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是处于独立和自治状态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乃至全国的印第安族群的土地权利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场变化的基础便是印第安族群传统土地文化观念在法律上得到重新解读。但土著土地权利的制度化,并不意味着加拿大印第安族群政治的终结,而是提出了关于民族国家构建、政府结构整合和少数族裔独特性等方面的新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当代加拿大原住民的政治生活,确实通过土地权利重建的启动打开了崭新的局面。印第安人不但有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诉求,还有政治上的诉求,即旗帜鲜明地强化印第安人权利的独特性。尼斯加人争取土地权利的案例表明,印第安人在权利建构中的有效参与,是当代加拿大土著民族事务中的最显著特点。不管尼斯加人出发点如何,他们最终获得的成果勾画出以族群为单位的主权草图,至少在法律上表现出与省政府、甚至联邦政府分庭抗礼的态势。
尼斯加人维权史的特殊意义,抑或讲加拿大的谈判传统、政府结构演变历程以及省与原住民族群关系的特殊性,都让尼斯加协议的签订成为一项创举。
作为族群关系较为缓和的多民族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加拿大印第安人土地权利的进程既是一种重要历史经验,也是一种值得持续关注的政治实验。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anadian Indian’s Land Right since 1970’s Case Studies of Nisga’a People
The Nisga’a people,live in British Columbia,Canada,was one of the groups that never signed any treaty with any government in its history.In 1973,the Nisga’a Tribal petitioned government to recognize their connection with land again.Through more than 20 years of negotiations with B. C.government and federal government,the Nisga’a Final Agreement was signed on May 27th, 1998.The agreement has changed the process of land claim between other aboriginal tribes and Canadian government.After Nisga’a people enjoyed their victory after the agreement,confusion, frustration and uncertainty overshadows the land right obtained after long struggle and caused wide spread concerns.
Canada,Canadian Indian’s Land Right,British Columbia,Nisga’a People
K1
A
0457-6241(2017)10-0017-10
杨令侠,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加拿大社会史、加美关系史。
徐天,美国天主教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美国移民史。
【责任编辑:杨莲霞】
2017-03-18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加拿大少数族裔移民的移入、融入与文化调试研究”(项目编号:15JJD7700 16)阶段性成果。
①Richard J.F.Day and Tonio Sadik,“The BC Land Question,Liberal Multiculturalism,and the Specter of Aboriginal Nationhood”, BC Studies,No.134,2002,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