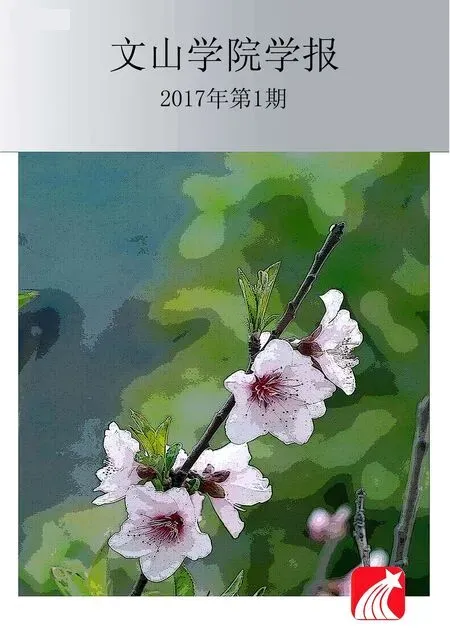清朝的法治及在南方土司地区的法治建设
方悦萌
(云南民族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
清朝的法治及在南方土司地区的法治建设
方悦萌
(云南民族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
清朝是中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制度建设达到新的高峰。清朝将法治提到巩固统治、改造社会、收揽人心的高度,强调法治应符合实际,“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法治建设应具有连续性,因此进入古代法治建设的成熟期。在南方土司地区的法治建设方面,上述特点得到充分的体现。
清朝;法治建设;南方土司地区
关于清朝的法治尤其是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法治,以及清朝在南方土司地区的法治建设问题,过去学人研究不多,因试为探讨,以求教于前辈。
一、清朝的历史地位与统治特点
清朝立国276年,是古代统治时间较长的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又是中国古代向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因此具有不同于其他朝代的一些特点。从相异的视角,可对清朝的历史阶段进行不同的划分。
从中国古代向近现代转变的视角来看,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界,清朝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若考虑到清朝统治发展的阶段性,可将清代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清史专家戴逸先生认为,1644年明朝覆亡清军入关,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是清朝统一全国并清除叛乱、稳定全国局势的时期。其中发生长达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康熙二十年(1681)清朝平定“三藩之乱”,消除了威胁全国统一的严重隐患。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清朝出现“康雍乾盛世”,这是清朝统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道光二十年(1840),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但全国的经济仍在持续发展,各地的反抗虽屡有发生,但清朝的统治尚可维持。道光二十年(1840)至宣统三年(1911),是清朝衰败和走向灭亡的时期。[2]这一时期由于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中国与西方列强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同时诱发了清朝深层的社会问题,封建王朝后期的衰败也明显表现出来,以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统治。笔者赞同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界,将清朝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意见。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3]清朝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清朝制定并实施了较为符合实际的民族政策,成功地处理了与汉、蒙及其他民族的关系。自顺治始至清晚期,清朝始终坚持“满汉一体”的政策。满、蒙、汉三个民族的相互关系,构成清朝立国的基石。其次,清朝的吏治较为清明,清朝坚持严惩贪官污吏,伴之以思想教化;同时大力表彰清官廉吏,由此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繁荣与稳定。其三,历代清帝大都文武兼备,勤于政事,事必躬亲,严于治理,这在古代并不多见。尤其是康雍乾盛世的形成,奠定了清朝相对稳定、持续繁荣的基础。其四,清朝统治者有较强的国家观念,坚持国家的大一统,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做出宝贵的贡献。其五,清朝重视统治制度的建设,积极推动法治,在统治制度和法治建设方面取得成绩,不少制度可说是集历代之大成,有效保证了清朝统治的高效与稳定,对后世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六,清朝积极经营和开发边疆地区,尤其是对南方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的有效经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有利于全国政治、经济一体格局的形成。
另一方面,清朝的统治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面对内外的巨大压力,清朝统治消极的一面渐趋明显,引发的后果也很严重,由此反映了清朝统治的局限性。
清朝统治者已形成较为明确及完整的国土观,统治者认识到对保卫国土负有责任。清建国之初,北部疆域遇到严重动乱与外敌入侵的挑战。在西南边疆地区,乾隆三十二年(1767),清廷令将军明瑞率大军征缅甸,征缅战争进一步扩大。清军大举征缅是由于缅军多次侵扰云南边境,严重威胁西南边疆的安全。因此,清朝统治者对边疆的安全十分重视,经常进行认真研究并细致设计,并希望通过法治的途径,在边疆民族地区实现长治久安。
鸦片战争以前的历代清朝皇帝,接受“守在四夷”的传统思想。雍正皇帝就前代贬低“夷狄”不以为然,认为清朝统一天下,“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4]清朝的版图广阔稳定,统治者有明确的国土守护意识,因此十分重视治边与边疆治理制度的建设。清朝治边企望实现长治久安,充分注意到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革,施行规范化、持续化的管理。所制定的边疆治理制度,在历代王朝中堪称最为系统、完整和成熟,在实践中也取得良好成效,由此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清朝治边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彻底解决了受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的问题。清代有过长达300年近600人次具有多重意义的满蒙联姻,其意义和影响超过以往任何朝代。[5]后金与漠南蒙古上层的联姻很早便开始,为统一全国后通过大规模联姻,与漠南蒙古建立密切合作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兼有在北方草原有效传播佛教等因素的配合,清朝最终解决了北方游牧势力经常南下、严重威胁统一王朝安全的问题。严复说:“若除此(汉唐)两朝,则中原之被北狄蹂躏,真更仆难数。盖北狄之勇战,固天性也。今满蒙皆逸居无事也,此乃喇嘛佛法毒之,且亦阅二百余年,而始有然。”[6]严复将北方游牧势力不再南下,归于清廷以“喇嘛佛法毒之”的看法虽可商榷,但清代“满蒙皆逸居无事”则为确凿的事实。
清朝统治者形成较高层次的全局观。统治者将边疆视为安置内地人口与获取资源不可或缺的地区。雍正前期的西南民族地区,存在部分土司纵恣不法、危害社会等问题,为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及早处理“目前虽无大害,日久将为隐忧”的边疆土司,雍正朝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为了以较小的代价完成“改流”,雍正朝臣注意调查研究,制定主要策略,并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形采取对策。“改流”的实质是对西南边疆的弊端做必要改革,并非彻底废除土司制度,“改流”基本上达到预期的效果。
清中期全国的人口数量激增。清代中期承受内地人口严重膨胀的压力,于是朝廷把云南等边疆地区视为人口分流的空间;并在云南等地大量开采铜、银等矿藏,供京城和南方诸省铸币之用。由于清廷的积极开发,云南的采铜业获得迅速发展。元朝在南方民族地区推行土官制度,在北部草原继续其他统治制度,清朝进一步发展这一做法,形成因地制宜施行统治的趋势。除在西南民族地区施行土司制度,并通过“改土归流”进行改革外,在其他边疆地区,中原王朝推行有别于土司制度的统治制度。清朝在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实行的各种制度,其共有的特点是注重法治,将这些制度纳入规范化管理的轨道,希望藉此在施治地区实现长期的稳定。
二、清朝法治的特点及其演变过程
清朝出现过长达百余年的康雍乾盛世,统治者十分重视统治制度的建设,并取得很大的成就,堪称是中国古代统治制度建设的高峰和鼎盛时期,法治建设也不例外。清朝不仅制定了完整、严密的国家法律,在实施方面也取得很大的成就,清朝的法治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清朝的法治在中国法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清朝的法治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统治者注意保持法律制度的连续性。[7]204入关以前,满洲尚无成文法典,施行的主要是习惯法,但后金时已接触并初步熟悉明朝的法治,并对之称赞有加。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进一步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认为必须延续中原王朝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康熙称赞明太祖“治隆唐宋”,认为其主要功绩是强化了君主专制制度。因此,清朝努力学习和继承明朝的法律制度,使清朝的法治建设及其制度化具有连续性的特点。
其次,清朝统治者认为法治的根本目的是“正人心、厚风俗”,即将法治提高到巩固国家统治以及改造社会和收揽人心的高度。为达此目的,清朝将《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列为士人必读,并积极提倡程朱理学,宣传“明刑弼教”“正人心、厚风俗”的理学思想。为消除异端思想,清朝大搞“文字狱”,在思想文化方面施行专制统治。清朝的法治与此相适应,国家法律不仅包含思想文化方面专制的内容,朝廷还重视通过发展教育,在边疆民族地区传播儒家思想,用儒家思想、封建专制思想影响和改造边疆各民族。
其三,统治者强调“人治”,以及“人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原则。清代诸帝普遍勤政,尤其康雍乾三代帝王之勤政,以及执政之清醒和高效,在历代帝王中都十分突出。清朝皇帝亲自掌握刑罚大权,同时高度重视立法和司法实务。清朝皇帝曾三次亲自撰写法典的序文,对重要案件必亲自过问,甚至亲自裁决。记载“改土归流”的史籍,记录了雍正皇帝参与“改土归流”的详细经过,从整体设计、挑选人选、确定谋略、具体实施到善后处理,雍正皇帝都认真听取汇报并提出具体指示,保证了“改土归流”获得成功。类似的记载在清代史籍中随处可见。清朝统治者重视“人治”,强调司法官员对皇帝必须忠实。皇帝认为司法官员的素质,一定程度上决定法治的质量和成败。由于地方大吏兼管司法之权,清朝皇帝对派往边疆和民族地区的地方大吏的选择十分慎重,认真考察其忠诚的程度,以及各方面具有的素质。派往云南等地的官吏,甚至还过问其健康的情况,防止难以适应“瘴气”的环境。同时,清朝统治者认为“人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重视对法律的制订和健全,做到执法有法典可依,让“人治”在具备完备法律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作用。统治者还认为施法应“宽猛相济”,以“宽严之用、因乎其时”为法治的指导思想,根据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灵活应用法律,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而高素质的执法官吏,又是法治取得成功的基本前提。
其四,清朝的法治强调符合实际,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如此。[8]清朝在中央设立专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机构理藩院。理藩院原是专理蒙古事务的衙门。以后蒙古诸部归附渐多,乃更名为“理藩院”,并提高级别,将其置于与六部同等的地位。清朝统一全国后,理藩院辖旗籍、王会、柔远、典属、理刑、徕远等六清吏司,职能扩充到掌管内外藩蒙古、回部及诸番杂部。理藩院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理,由蒙古地区扩展到新疆、西藏、青海等地,重点是北部、西北部和西南边疆。在上述边疆地区,清朝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制定和实行不同的统治制度,并相应制定一些法规和必须遵循的原则。
对内外蒙古诸部,清朝实行吸收八旗制度因素的盟旗制度,在维吾尔族地区则实行伯克制度。在西藏地区清朝实行政教合一的管理制度,派遣驻藏大臣代表朝廷处理西藏事务,并借重驻前藏的达赖喇嘛、驻后藏的班禅额尔德尼两个宗教领袖,规定其地位和职权与驻藏大臣平等,共同协商处理政务。同时加强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创立遴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承人的金瓶掣签转世制度。对西南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清朝进行了改革。雍正前期的西南民族地区,存在部分土司或夷霸纵恣不法、危害社会,与朝廷争夺土地、矿藏等资源,阻挠驿路通行与外来人口进入等严重问题,为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及早处理“目前虽无大害,日久将为隐忧”的边疆土司,雍正朝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针对土司制度的弊端进行必要的改革。
清朝制定统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参汉酌金”,[9]即参考明朝的统治制度,从中汲取营养和可用的部分,同时斟酌吸收满族原有的习惯法,再根据本朝的实际情况制定各项制度,法治建设也不例外。皇太极认真总结开国肇基的实践经验,提出“宣布法纪,修明典常,为保邦致治之计”的统治思想,[10]并进一步明确“参汉酌金”的立法原则,为以后诸帝所遵循。天聪七年(1633),文馆大臣宁完我就立法问题提出“参汉酌金”的建议。他说:“《大明会典》虽是好书,我国今日全照它行不得,……况且《会典》一书,自洪武至今,不知增减改易了几番,何我今日不敢把《会典》打动它一字?他们必说律令之事非圣人不可定,我等何人,擅敢更议?此大不通变之言,独不思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制作。”因此建议“参汉酌金,用心筹思,就今日规模,立个《金典》出来。”[11]宁完我的建议得到皇太极赞同。清军入关以前制定的法律,已体现了“参汉酌金”的思想。如采“十恶”入法律,不依服制而定罪,不搞族株连坐等内容,都来自明朝的法律。
清军入关后,将制定严密法律的问题提上日程。顺治元年(1644),先行进驻北京的摄政王多尔衮颁令“自后问刑,准依明律”,[12]并要求司法官员与廷臣着力研究明律,参酌时宜,集议成文,以备裁定成书,将国家法律颁行天下。顺治三年(1646),经过司法官员与廷臣的认真准备,制定了《大清律集解附例》,于次年颁行全国。这是清朝首部以刑法为主要内容的成文法典。康熙继位以后,针对王朝疆域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问题,提出对旧有新例“应去应存”的要求,命令朝臣会同商议酌定。次年,刑部将修改并经核准的《刑部现行则例》上报。《刑部现行则例》的主要内容,是就超出现有法律的各类犯罪,做出轻重不等的处罚规定。康熙令交九卿议准,将《刑部现行则例》补充入大清律。[13]康熙四十六年(1707),最终完成将现行则例分门别类,其内容并入大清律的繁重工作。但康熙一朝并未颁布执行。
雍正皇帝即位后,以大学士朱轼等为总裁,令以“删繁就约、轻重有权、宽严得体”为原则,进一步修改已完成的内容。雍正三年(1725)完成呈报,雍正五年(1727)以《大清律集解》的名称颁布。乾隆皇帝即位后以三泰为总裁,对原有的律例逐条考正,并详拟定例,增减损益,最后经乾隆皇帝亲自审定,于乾隆五年(1740)“刊布中外,永远遵行”,此即著名的《大清律例》。《大清律例》共有律文436条,附例1 049条,是清朝制定的第三部法典,堪称是封建王朝最后厘定的法典。《大清律例》集明、清两代国家法律之大成,内容十分丰富,格式严密周详,朝廷规定以后必按时修改,不断完善。乾隆十一年(1746)颁布定制:条例规定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
除《大清律例》等法典以外,清朝还编撰了五部会典。[7]206首部《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始编撰,历时六年完成,主要汇集清朝开国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各种法规和制度。雍正十年(1733)编定的《钦定大清会典》,内容主要是各部院的规章制度。乾隆十二年(1747),清朝开始编撰新的《钦定大清会典》,主要是将则例另行择出,分别编成《钦定大清会典》100卷与《大清会典则例》180卷。嘉庆十七年(1812)编成的《钦定大清会典》,增加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嘉庆十七年(1812)之各衙门制度的事例,并按年份编录。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朝编成第五部《大清会典》,计100卷,同时完成的还有《大清会典事例》1 220卷。至此,清朝建立了一整套“以《会典》为纲,则例为目”的行政管理制度。
此外,清朝还重视编撰条例、则例、事例、成例,统称“例”。“例”是清朝重要的法律形式。有人说:“清以例治天下”,[14]此言略有夸张,但足见“例”在清朝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清代法律体系以“例”为核心,绝大多数法律规定都以此方式固定下来。其中,“条例”专指刑事方面的法规,大部分编入《大清律例》。“则例”是单一行政部门的法规汇编。“事例”是皇帝发布的“上谕”或经皇帝批准的政府公文。“成例”指经过整理的事例,包括条例及单行的法规。“例”也有不少边疆地区、民族地区法治的内容。
历数清代的法律典籍与文件,以《大清律例》最具有代表性,可说是清代法律体系中的根本大法。它确定了以皇权为象征的统治权力中心和保障其效力的行政制度设计,同时赋予地方相应的自主管理权利,这种自主权权限被严格界定,实施方式、要求、界限均有明确规定,严格保证了中央集权的无上权威。《大清律例》通行全国,其内容对各地区、各民族均称适用。同时,根据《大清律例》的基本内容,结合各地区、各民族的具体情形,清朝又先后制定一些补充律令。[15]补充律令共有的特点,是照顾到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酌情吸收传统习惯法的内容,让《大清律例》被各地方严格执行的同时,兼顾地方社情,因此有一定的灵活性。
清朝又参考苗、瑶等南方民族的习惯法,制定并实施《苗律》。参考蒙古族的习惯法制定的《蒙古律例》,规定刑罚以罚交牲畜为主,虽犯死罪亦可用牲畜冲顶,体现出草原游牧社会的特点。清朝先后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制定的法规,主要有《蒙古律》《回律》《番律》《苗律》《番例条款》《钦定西藏章程》《钦定理藩部则例》等。《钦定理藩部则例》的内容十分丰富,根据法规施行的情形,朝廷先后组织认真修改,修改后的《钦定理藩部则例》共有713条,其中增加的部分有526条,[16]还不算先后修改保留的部分,由此可见办事之认真,以及对边疆地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之重视。
清朝的整套法律体系,反映了中央和地方立法的高度统一。一方面,《大清律例》肯定了清朝中央集权的控制,同时确立地方行政机构构成和职权范围。还为地方立法提供了指导原则和立法方向。另一方面,其他地方性、民族性的具体条规,和《大清律例》基本精神为一脉相承,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及具体化。如双方均有处理的权力,形成法律上的竞合,《大清律例》的效力层次更高于地方立法:如遇到重大的案件,类似于发生谋叛重罪,必须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执行。史载称:“有大狱讼者,皆决于流官。”[17]若发生程度轻微的案件,则根据具体的条规,甚至参考习惯法或约定俗成的规则处理。这些反映了清朝立法体系的完整性和平衡性,同时也反映了相关立法在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实施,允许有较大的灵活性与可变通性。
三、清朝对南方土司地区的统治
清代的南方土司地区,大致包括今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清朝对南方土司地区的统治,经历了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在雍正实行“改土归流”以前,南方土司地区的管理十分混乱,土司违法的情形很多。但清朝无暇顾及,事实上当时也不存在严格治理的条件。雍正施行“改土归流”期间,对违法的土司及夷霸进行惩治,一些法治规定先后确立。但此时存在执法过严的情形,兼之“改流”以后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外来移民侵占少数民族权益的情形较普遍,雍正后期及乾隆前期,南方土司地区爆发反抗清朝统治的起义,朝廷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落实善后及缓和社会矛盾。道光以后土司地区各地逐渐稳定,但深层的矛盾仍然存在。清朝的做法是加紧法治建设,贵州巡抚等官员议定的《苗疆善后章程》,完成对法治规定的系统化,并在土司地区广泛推行保甲制度,这一时期对少数民族的管理也日趋严格。
雍正年间,清朝对南方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进行重大的改革即“改土归流”。本次改革的规模大,涉及范围广泛,改革彻底深入。但“改土归流”并非取消土司制度,而是在部分地区以流官代替原先的土司,对统治的方式做必要的调整。从司法的角度来看,“改土归流”不是必然导致“改流”地区在法律适用方面进入汉法的体系。因为即便通过“改流”,在国家行政体制方面完成了新的制度设置,基层亦可将其逐渐消化。“改流”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对府县级的土司进行“改流”,但其下社会组织的变化并不大。二是“改流”贯彻到府县以下的级别,则意味着当地的百姓有了新的司法救助途径,基层的管理相应将发生变化。在乡土社会,基层社会的组织体制对上层行政制度的实施有决定性的影响。若下层社会组织未发生改变,上层行政制度可能被消融或减弱。因此,“改流”后南方民族地区的某些部分,其社会结构可能发生决定性的改变,但不是绝对的,重要的是朝廷强化了对基层的管理和控制。清朝对此十分重视,甚至将其作为“改流”后的主要措施来执行。
“改流”以后,清朝加强对南方民族地区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保甲制度。清朝治理地方主要是靠保甲制度,保甲制度因此成为清代的基层社会组织,对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保甲制度不仅体现国家对地方的控制,而且也是地方自治的一种方式,同时保甲制度还具有一定的司法功能。因此,清代很多地方官吏都重视保甲制度的完善和推行。“改流”完成以后,清朝采取的一个主要措施,是将保甲制度移植到南方民族地区。清代中期徐栋所撰《保甲书辑要》,共四卷,收集了清代保甲制度方面的法规,以及清人和前人的相关论述。从该书中可看出“改流”以后,清朝在南方民族地区推行保甲制度的情形。
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提出在“改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的设想。他说:“保甲之法,旧以十户为率。云贵土苗杂处,户多畸零,保甲之不行,多主此议。不知除生苗外,无论民夷,凡自三户起,皆可编为一甲,其不及三户者,令迁附近地方,毋许独住,则逐村清理,逐户稽查,责在乡保、甲长,一遇有事,罚先及之,一家被盗,一村干连。乡保、甲长不能觉察,左邻右舍不能救护,各皆酌拟,无所逃罪。”[18]鄂尔泰认为在“改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不必拘泥于户数多寡与保甲制度职能是否健全,关键是发挥保甲制度责任连坐,以及乡保、甲长施行监管的作用,为“改流”以后在南方民族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定下基调。“改流”完成以后,保甲制度在“改流”地区得到推行,其间也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调整与改革。
清朝统治南方土司地区,还把兴办学校、传播儒学教育作为必不可少的手段。清朝在边疆地区兴办学校,其目的与明朝有一定的差异。明朝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农业区域办学,主要是让卫所军士的子弟受到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虽也设置学校,则是希望提高土司子弟的文化水平,实现改善各级土司素质的设想。清朝在南方民族地区兴办儒学教育,在规模、范围和成效方面都远超明代。清朝规定土司应袭职位的子弟,必须入学学习。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朝重申《学政全书》关于“土司应袭子弟,令该学立课教训,俾知礼义,俟父兄卸事之日,回籍袭职”的规定。[19]清朝兴办儒学教育,官学经费由财政开支,允许社会力量兴办私学,所设学校有府学、县学、书院、义学、私塾等多种。对各地少数民族考生,朝廷在名额、录取、待遇等方面予以照顾。清末既废科举,官府在各地设新学堂,一些地方新学与私塾并存。对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清朝统治者有较长远的考虑,包括有效增强边民的文化素质,培养边疆各族的国家意识与爱国观念等内容。对少数民族接受儒学教育所发生的变化,清人吴大勋说:“国家承平百数十年,王化渐摩已久,有力之夷,居然衣冠文物,读书稽古,为子衿者,盖已无算,科目出身,亦往往而有。至于土司子弟,尤慕斯文,既赋采芹,又袭土职,居然正途士宦,夷民敬服,别种推重,此皆圣泽旁敷,无远弗届,过化存神之大验也,猗欤盛哉!”[20]
四、清朝在南方土司地区的法治建设
清朝在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法治管理,表现出灵活多样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以及系列化和文典化等特点,反映出清朝统治者具有针对不同民族立法的意识。在调查研究、撰写修改与付诸实践等方面,清朝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可说是达到中国古代民族立法的最高峰。[21]
清朝统治者重视民族法治的原因,在于认识到“所谓因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者,盖怀柔驾驭之道,即于是寓焉矣”,企望藉此实现“屏藩万里,中外一家”。[22]清代南方土司地区涵盖的范围甚广,大致包括今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清朝专门为南方民族制定法律,较为系统、完整者首推《苗律》。在清代的《大清律例》《钦定大清会典》等重要法律典籍中,也有较多的关于“新辟苗疆”及当地苗族、瑶族的法治律令与其他文献材料。究其原因,当与“改土归流”后所称之“新辟苗疆”地区,在清代前期因土司割据专横长期得不到解决有关,也有“新辟苗疆”是雍正“改土归流”的重点地区,清朝的诸多方略、应对之策由此地而起方面的原因。另外,还与“改土归流”后当地民族的反抗迭起,统治者为善后安排与稳定局势不无关系。进一步来说,鉴于“新辟苗疆”情况复杂,相关情形牵动全局,朝廷以之为样板制订法治对策,进而推广到其他土司地区,亦可能是朝廷制订《苗律》的初衷之一。清代记载中的“苗疆”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苗疆指今云南、贵州、川西南、广西等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狭义的苗疆指贵州东南部以古州为中心的苗族地区,又称“新辟苗疆”。因此,主要针对“新辟苗疆”的情况而制定的《苗律》,大体上也适用于广义的苗疆。
针对苗疆的具体情况,清朝的一些普遍性规定在苗疆可适当变通。清朝所制订《苗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承认南方少数民族社会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认可其习惯法。统治者对此有明确的认识。乾隆元年(1736),乾隆帝针对贵州“改流”地区的情形说:“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不同,以后苗众的自相争讼之事,都根据苗例完结。至有与兵民、熟苗关涉案件,隶文官者,仍听文官办理;隶武官者,仍听武弁办理。”[23]但对威胁到封建统治的犯罪,清朝则严格处置,决不姑息。
清朝统治者注意到“生苗”与“熟苗”的区别,对犯法的“生苗”或“熟苗”有不同的处置办法。关于两者的区分,据《苗疆风俗考》:“边情以外者为生苗,边情以内者,间与民村相错居住或佃耕民地,供赋当差与内地人民无异者,则熟苗也。”康熙四十年(1701),复准熟苗、生苗若有害人者,熟苗照民例治罪,生苗仍苗人例治罪。”[24]乾隆三十一年(1766)定例称:“云南贵州苗人,犯该徒流军遣,仍照旧例枷责完结……至苗人中有剃发衣冠与民人无别者,犯罪到官,悉照民例治罪。”[25]另据记载对“生苗”内部的争斗,通常依据习惯法处理:“又以苗地风俗与内地百姓迥别,谕令苗众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治以官法。”[26]
在南方土司地区,还存在清朝以习惯法为基础,吸收内地法治的因素,先后形成本地法规的情形,以顺利完成中央立法在本土移植的过程,以云南傣族地区较为典型。现今可见的清代傣族法规,主要有《西双版纳傣族的封建法规和礼仪规程》《孟连宣抚司法规》《西双版纳傣族封建社会的民刑法规》《西双版纳傣族法规》等。上述法规由以下部分构成:处理诉讼的原则、态度及方法,地方之间违反公约接受罚款的规定,关于罚金与赎罪的规定,处理民事、刑事的法律原则等。在其他民族地区,还普遍存在一些各种形式的本地法规,如瑶族刻于石碑上的石牌律,贵州彝族的《夜郎君法规》,侗族的侗款与苗族的议榔等。
总体来看,清朝较为重视南方土司地区的法治建设,并具有因地制宜、不断改进和完善的特点。清朝在南方土司地区的法治取得较好效果,对稳定南方土司地区、维护改土归流的成果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夏家骏.清朝史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1.
[2] 李学勤,等.中国古代史导读[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1:499.
[3] 李治亭.清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8.
[4] 雍正.大义觉迷录[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5.
[5] 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34.
[6] 严复.论支那之不可分[M]//郑振铎.编.晚清文选.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2.
[7] 苗延波.中国法制史[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8] 焦利.经略边疆:清代治边之法的得失[M]//汪世荣,等.主编.中国边疆法律治理的历史经验.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357.
[9] 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52.
[10]《清太宗实录》卷36[Z]. 崇德二年六月甲寅,日本东京大藏株式会社影印本.
[11]《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Z].
[12]《清太宗实录》卷5[Z]. 顺治元年五月甲戌.
[13]清史稿·卷142·刑法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14]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5[M].北京:中华书局,1958:581.
[15]沈大明.《大清律例》与清代的社会控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6.
[16]钦定理藩部则例·卷1·原奏之三[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点校本:31.
[17](清)《黔南职方纪略》卷7[Z]. 道光刊本.
[18]《云贵总督鄂尔泰为分别流土考成、以专职守、以靖边方事奏》(雍正四年八月六日),载《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二[Z]. 故宫文物馆编, 1930年印,云南大学图书馆藏.
[19]大清会典事例·卷145吏部·土官承袭·土官请封·土官大计[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0](清)吴大勋.滇南闻见录·夷种[M].云南大学图书馆藏.
[21]李鸣.中国民族法制史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366.
[22]《大清一统志》卷534[Z].
[23]《清高宗实录》卷22[Z]. 乾隆元年七月辛丑.
[24]《皇朝政典类纂》卷374[Z].
[25]《大清律例》卷19[Z]. 乾隆刻本.
[26]《清高宗实录》卷55[Z]. 乾隆二年九月丁卯.
(责任编辑 杨永福)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Legal Construction in Southern Tusi Regions in the Qing Dynasty
FANG Yuemeng
(School of Law, 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Kunming 650504, China)
The Qing dynasty is the last feudal dynasty in China and its system construction reach a new summit. It shifts the rule of law to the degree of consolidating control, reforming society and winning over people, focuses on practical rule and balance between the rule of man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continuity, so its legal construction enters maturity. The above features are embodied in the legal construction in southern Tusi regions.
the Qing dynasty; legal construction; southern Tusi regions
D691.4
A
1674 - 9200(2017)01 - 0032 - 07
2016 - 10 - 0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边疆治理传统战略研究”(14XZS002)研究成果。
方悦萌,女,云南昆明人,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边疆史与法制史研究。
——李良品《中国土司学导论》读书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