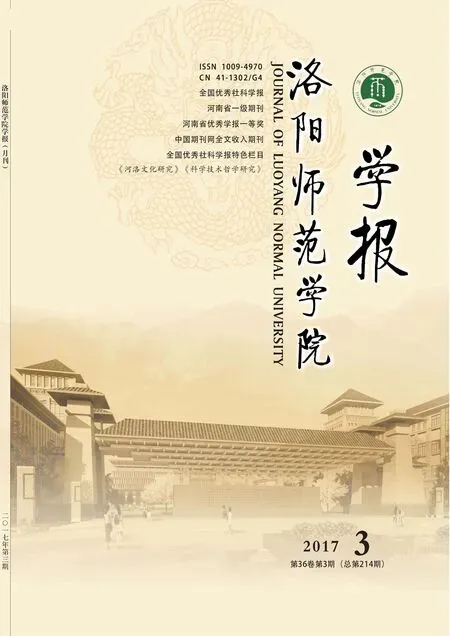女性生命意识的封闭与放纵
——原型视角下的《永远有多远》
蒲伊琳
(河南大学 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0)
女性生命意识的封闭与放纵
——原型视角下的《永远有多远》
蒲伊琳
(河南大学 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0)
“原型”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 因而作家在创作时总是会有意或无意地引入原型。 在《永远有多远》中, 铁凝将母亲原型和“狐狸精”原型运用到作品中, 塑造出性格上截然对立的两类女性, 并将她们放在同一环境下进行比较, 从而使白大省的善、 西单小六的媚以及小玢的蛮都更加鲜明。 铁凝从时代角度出发, 对男权社会下女性生存境遇的深切观照, 展现女性对当下自身生存状态和更深层次的生命体验的思考与追问。 关键词: 原型批评;母亲原型;“狐狸精”原型;女性生命意识
《永远有多远》是当代著名女作家铁凝所创作的中篇小说, 小说荣获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第一届老舍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 在这部作品中, 铁凝“以一种隐忍的悲悯、 一种温婉的原宥去环绕、 去触摸、 去记述某一时刻、 某一情境, 某个荒唐而痛苦、 不断浮现在追索与希望之中、 又不断沉沦于挫败与绝望之下的心之旅”[1]5。 小说的丰富内涵给研究者带来了无限阐释的空间和说不尽的话题, 因而从它诞生之日起, 各类评论文章就纷至沓来。 有的侧重展现主人公白大省的“仁义”品质, 呼吁和召唤这种现代社会所缺失的美德;有的从性格角度出发, 寻找造成白大省人生悲剧性的决定因素;也有的从文化差异入手, 真实呈现女性在当下对自身生存境遇的思考。 通过细读文本, 笔者发现似乎还可以借助原型理论来进行一番解读。
一、原型理论阐释
何谓“原型”?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认为, “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所谓的‘原型’”[2]40。 他从心理层面来定义原型, 强调了原型作为一种人类心理长期积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的潜在作用。 之后的加拿大文艺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莱在荣格的基础上, 引入结构主义、 叙事学、 人类学等理论资源, 从而使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更加系统化、 完整化。 作为神话原型批评的集大成者, 弗莱的一大贡献就是将原型的概念范畴推及文学领域, 建立起以“文学原型”为核心的原型批评理论。 弗莱的原型理论为中西方文艺批评界提供了重要的批评介入方式和理论支撑。
弗莱在《文学即整体关系:析弥尔顿诗〈黎西达斯〉》中提到:“我运用原型这个术语, 是指一个或一组文学象征, 它们在文学中为作家们反复地运用因而形成为约定俗成的东西。”[3]341可以说, 文学领域中的原型就是一种“原始意象”, 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认知原点, 承袭着民族文化的精神内蕴, 从古至今的文学艺术, 无不显现着这代代相传的文化符号。 在历史的浪潮中, 历代文人通过反复的艺术再加工, 使得这些展现“集体无意识”的艺术原型在时代外衣的装点下寓意更加丰富。 因而, 运用原型批评的方法进入文本, 有利于扩展研究的思维路径, 弥补以往研究中被遮蔽的内容, 通过捕捉文中的原型, 进而全面理解作品中表现出的对现代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 对男性社会文化下女性探寻自我主体意识的矛盾与困惑。
二、《永远有多远》中的原型分析
(一)个性湮灭的仁母原型的变换书写——女性生命意识的封闭
神话原型批评奠基者之一的荣格认为, 在人类的普遍意识形态中, 母亲原型是较为常见的一类原型意象。 “传统性别文化规定给女性的性别角色就是顺从与隐忍、 奉献与牺牲”, 母亲作为女性性别角色的典型代表, 善良、 仁慈、 奉献自是其性质的核心显现。[4]35小说中的主人公白大省就是母亲原型的一种变换书写, 是藏在“现代女性洁白的衣领下”的“原始女人”。[5]350这个从小就因“仁义”而广受赞誉的平凡女性, 在渴求自由与自觉自愿遵循大众标准的矛盾挣扎中, 终于没能冲破道德视阈的规诫, 完成她内心自我形象的召唤:成为像西单小六那样魔鬼般的女人, 直至成为扼住自我欲求的咽喉, 丧失主体个性的“好女人”。
在性格上, 白大省身上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始终如一的仁义善良、 无私奉献, 无疑, 她就是所谓严格恪守传统伦理规范的道德标兵。 她自小就被邻居赵奶奶夸“仁义”, 小学二年级, 她就担负起每日给姥姥倒便盆的责任, 却常常被姥姥数落“笨”“神不守舍”, 但她却毫无怨言, 尽心侍候姥姥。 小小年纪就处处懂得礼让和承担责任, 仿佛善良和任劳任怨就是她骨子里自带的。 面对姥姥对弟弟白大鸣的过分溺爱, 她觉得理所应当。 对弟弟, 她是真心疼爱, 有求必应, 面对弟弟索要她房子的无理要求, 她甚至还为自己一时性急说出的几句气话而感到愧疚, 随后便心甘情愿许诺让出房屋。 白大省不仅在家是吃亏让人的好孩子, 在学校是乐于助人的好学生, 工作后也是业绩拔尖、 人缘颇好的好员工。 从传统观念来看, 白大省确是个人人称赞的“楷模”, 甚至是善良到有些傻里傻气的女人。 然而, 她现在成为的这种“好人”从来就不是她想成为的那种人。 她也想过改变, 甚至试图改变, 但根深蒂固的道德准则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她内心萌生的一丝“叛逆”念头彻底浇熄, 仁义与正派终究替代自由完成了其道德上的规训, 成为白大省的性格标签。 白大省的自我个性被彻底封闭, 成为一个完全丧失现代意识的“现代人”。
在爱情上, 白大省“永远空怀着一腔过时的热情, 迷恋她喜欢的男性”。 她时时保持一种母性的关怀去对待男友, 可以说是处处周到, 无限包容, 在潜意识中, 白大省早已经用母性意识取代了女性意识。 然而正是如此这般的善良体贴难以令男友心生爱怜, 难以将其置于女友的位置。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种心态致使她作为女性显现出一种深刻的内在匮乏。 在处理自己的恋爱婚姻问题时, 她从一开始就确定了“我爱他比他爱我更深”的无私得让人心酸的择偶标准。 对于她交往的几任男友, 她几乎无一例外献出全部真心, 但这样的真心付出很多时候更像是超越了恋人的母性关怀。 她主动要求给男友过生日, 以这样的方式企图深化她和男友的关系, 这种充溢着宠爱意味的恋爱方式宛然映射着一种母爱般的怜爱心态。 她“把伺候郭宏当成最大的乐事, 她给他买烟, 给他洗袜子, 给他做饭”, “为了给郭宏的小侄子买一只‘沙皮狗’”, 她甚至“背着姨父和姨妈卖了家里一台旧电扇”, 她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讨好郭宏。 她对关朋羽说“要是咱们俩过日子, 我什么都不让你干”, 这完全是一个悉心照料孩子、 任劳任怨的母亲形象。 她任凭夏欣在她家里白吃白喝外加穷“白活”, 整个一副母亲溺爱孩子的心态, 而没有未婚男女相处应有的平等。 最终她选择和曾经抛弃过她的郭宏结婚, 竟是因为孩子的一块脏手绢。 这块散发着馊奶味儿的脏手绢深深唤起了她的母性柔情, 唤醒了她作为女性所具有的母性原欲, 终于她决定宁可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也要与郭宏结婚。 在男性中心文化的规训下, 白大省最终选择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话语权”。 这样的结局正暗含着铁凝对于女性原初生命欲求在无数次生命轮回中所造成的悲剧命运的反思与质询。
白大省的身上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界定的“好人”的种种品质, 然而“好人”却没能得到“好报”, 在这只有一个太阳的“男性的天空”[5]352下,白大省最终只能发出“她可能永远也变不成她一生都想变成的那种人”的无望叹息, 这正展现着铁凝对于女性生存境遇的揭示和对女性生命意识的呼唤。 对于具有母性般的宽容与无私, 内心永远充满着温情的白大省, 铁凝是怀着同情与惋惜之情来诉说她那想变却又无法改变的痛苦与无奈。
(二)妖媚的“狐狸精”原型——女性生命意识的放纵
“狐”的形象, 中西方文献资料中都有记载。 在西方, 狐主要出现在寓言和童话故事中; 但是在中国, 狐有它自己独特的象征, 并且已融入人们的文化观念中。 “狐”的形象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多次出现, 其中, 狐幻化成女性的形象尤为突出, 并且这类形象还有一个独特的称谓——“狐狸精”[6]38。 “狐狸精”的形象是对“狐”的形象的变形处理, “狐狸精”往往外表美艳, 妩媚动人, 借着这美貌, 她们得以蛊惑男性从而达到某种目的。 褒姒、 妲己、 赵飞燕等就是古代文学史上经典的“狐狸精”形象。 纵观这些“狐狸精”形象, 不难发现, 在这类形象身上, “狐”之前的一些象征意义, 如“狡猾多疑”等已经被淡化, 因其幻化为美女, 因而魅人的特性得到强化。 “狐”一旦幻化为美女, 也就达到了魅惑人心的效果, 于是在人们的观念里专会魅惑男人的“狐狸精”就出现了。 “狐狸精”的这一语义在当今文化语境中得以延续, 具有相当的普适性。
在《永远有多远》这部小说中, 较之相貌平平又不善打扮的仁义代言人白大省来说, 潇洒妖娆的西单小六, 娇蛮可爱的小玢身上具备太多让男性痴迷的因素。 她们是与白大省截然不同的形象, 她们身上展现的是极具时代色彩、 极富时代神韵的潇洒之美。 可以说, 西单小六和小玢就是“狐狸精”原型的变化演绎。
西单小六在小说中是一个鲜活饱满的形象, 铁凝对她的描写虽然不是很多, 但却相当到位地勾画出一个美丽、 风骚、 洒脱的女性形象。 在传统道德视阈下, 西单小六绝对可以归为“坏女人”的阵营。 她“天生一副媚入骨髓的形态, 天生一股招引男人的风情”, 凭着这美貌和张扬不羁的行为, 她成为“西单纵队”里唯一的女成员。 她的身边没有什么女性朋友, 但她不在乎, 因为她的周边有数不清的男性朋友。 她喜欢和男人在一起, 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和这纵队里的所有男人睡觉”。 她很享受被男人喜欢的感觉, 甚至喜欢男人为她打架。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历史上记载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古有褒姒戏诸侯, 今有“西单”闹“纵队”。 如此诸多的荒唐行径, 本该令她孤立无援, 可她偏偏有能力让兄弟姐妹争相在父亲面前为她求情, 甚至私下向“西单纵队”通风报信, 从而发生了使整条胡同都为之震撼的深夜抢人事件, 这样的传奇故事为西单小六又平添了几分神秘和奇诡, 这种种因素集中于一人身上, 也难怪邻居会用“狐狸精”来形容她。 可以说, 西单小六将自己的美丽和妖娆发挥到了极致, 不仅是男性, 这种魅惑力甚至令女性都心神向往。 “这个染着恶俗的杏黄色脚趾甲的女人”非但不令“我”厌恶, 她还“开垦了我心中那无边无际的黑暗的自由主义情愫, 张扬起我渴望变成她那样的女人的充满罪恶感的梦想”。 没有人会想到, 西单小六这个如同“狐狸精”一般的存在却是好人白大省心目中最崇拜的偶像。 她那敢于挣脱传统伦理道德枷锁的勇气, “受八面来风而双肩一耸”的潇洒以及张扬自我生命意识的奔放都是白大省可望而不可即的。 “她巴望自己能变成西单小六那样的女人, 骄傲, 貌美, 让男人围着, 想跟谁好就跟谁好。”她还“常常站在梳妆镜前, 学着西单小六的样子松散地编小辫, 并三扯两扯扯出鬓边的几撮头发”。她白大省喜欢到能为之昏过去的男人, 西单小六却几乎连正眼都不看一下就能让他神魂颠倒, 这是白大省羡慕不已却永远都不可能具有的魅力。 西单小六的人生似乎注定要与众多男人纠缠, 她的美丽, 她的放荡不羁, 她的洒脱自在, 她的一切一切都足以让男人为之倾倒。 四十几岁的她嫁了一个小她十几岁的丈夫, 如果不是因为美艳自信的外表, 性感妖娆的身躯, 又能如何解释呢?西单小六的美貌、 性格以及她身上所发生的传奇事件, 无疑为她的“狐狸精”色彩更添例证。
小玢的“媚”虽不及西单小六, 但她却有让人难以拒绝的可爱。 她的存在能够唤醒男人潜意识中的骑士精神, 激荡起男人内心中的高大伟岸之感, 不自觉地想去照顾和保护她。 小玢是白大省生活在外省的表妹, 在经历了几次高考失败之后, 她决定来北京读服装学校, 闯出属于她自己的一番天地。 她性格属于天生的自来熟, 与人交往毫不忸怩。 她寄宿在白大省家, 本该保持谦卑懂礼的态度, 但是她却反客为主, 全然将这里变成了她的家。 她把自己的衣服挂进衣橱, 将桌面的小镜框都替换为自己的玉照, 又在迎门处悬挂上自己的巨幅写真, 这整个就是在装扮自己的家。 就连睡觉的床, 她也理直气壮地抢占。 她处处占尽白大省的便宜:抢去白大省大半午餐, 迫使白大省下午下班要在办公室吃饼干充饥;利用白大省的关系进入其单位的圈子, 开拓自己的人际关系网, 进而免费享受到客房部干洗衣物的服务, 有车的同事也乐于无偿送她上学。 小玢没有西单小六妖娆美丽, 她能在白大省的同事圈混得如鱼得水自是要归功于她的娇蛮可爱。 在她这里, 动不动拍男人大腿这样看似没教养的动作却像一阵春风拂过, 让男人整颗心都兴奋颤动。 她那娇小可爱的外表“给人一种介乎于女人和孩子之间的感觉”, 让人无论如何都无法迁怒于她。 如果这些不足以将她和“狐狸精”联系起来, 那么没见过几次面就把和白大省交往一年多的男友关朋羽夺走绝对是不能被忽略的证明。 小玢能如此迅速地将表姐白大省的男友变成自己的丈夫, 一方面是靠她那明显更具诱惑力的娇媚可爱的脸庞, 另一方面则是那小鸟依人般的灵动柔弱能充分激起男性的保护欲。 和白大省在一起的关朋羽被许以什么都不用干的承诺, 而小玢的出现使关朋羽尘封已久的高大形象得以苏醒, 这种感觉让他骄傲和兴奋。 至此, 小玢可以永久留在北京, 她要在北京闯荡的梦想也有了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 凭借自己的优势夺走表姐的男友, 单是这一点, 小玢也难以摆脱自己同“狐狸精”的关系了。
西单小六和小玢被置于“狐狸精”的原型之中, 但铁凝却将自己展现女性关怀的希望之火由此点燃。 铁凝没有让这类“坏女人”掉入“善恶因果”的理想法则的轮回之中, 而是让她们得到了完满的幸福结局。 这正体现了铁凝从女性视角出发, 探寻女性生存命运, 坚持“寻找女性自我”的女性生命意识的时代主题的创作之路。
女性评论家戴锦华曾言:“铁凝之于女性体验的书写, 更多的是一种自省, 是对女性的历史与现实境遇的深刻的、 近于冷峻的质询, 一种对文明社会中女性位置的设问。”[5]348诚然, 当女性价值在当代都市生活中发生转变时, 固守传统的女性是否还能在社会中为自己求得一席之地?这样的探寻与质疑伴随着铁凝对于女性性别和女性生命意识内在匮乏的思索与感悟。 白大省这样将自我意识封闭于道德的象牙塔无疑只会导致自我本真的彻底沦陷, “文明社会的到来, 意味着一种女性的解放、 一种‘挪动’, 同时意味着一种放逐”[5]351。 在这层意义上, 西单小六和小玢的自我张扬与自我言说所展现出的女性生命动力发掘后的自我放纵, 铁凝是予以肯定的。 通过对两类迥然不同的女性形象的对比书写, 铁凝所展现出的正是其作为一个兼具时代感和现实感的女性作家对男权社会下女性开掘自我生命意识的茫然与困惑的深刻揭示, 以及对女性理想人格建构的希冀和思索。
[1] 戴锦华. 真淳者的质询:重读铁凝[J].文学评论, 1994(5).
[2] 荣格.荣格文集[M].冯川, 译.北京:改革出版社, 1997.
[3] 弗莱.文学即整体关系:析弥尔顿诗《黎西达斯》[M]∥吴持哲.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4] 任一鸣.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5]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6] 陈宏.狐狸精原型的文化阐释[J].北方论丛, 1995(2).
[责任编辑 尹 番 杨 倩]
The Closedness and the Indulgence of Feminine Life Consciousness— “HowFarIsForever”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Archetypal Criticism
PU Yi-lin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HenanUniversity,Kaifeng475000 ,China)
“Archetype” carries the common cultural psychology of a nation. Thus, writers bring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archetypes into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InHowFarisForever, Tie Ning applies mother archetype and “fox spirit” archetype in portraying two types of females of distinct personalities and comparing them in the same setting, where the good nature of Bai Daxing, the bewitching charm of Xidan Xiao Liu and the peremptory character of Xiao Fen are more distinctively brought to life. Tie Ning shows deep concern for the living circumstances of females 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form perspective of times, which reveals how females think about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nd life experiences on a deeper level.
archetypal criticism; mother archetype; “fox spirit” prototype; females’ life consciousness
2016-10-17
蒲伊琳(1991—), 女, 河南焦作人, 硕士研究生。
I207
A
1009-4970(2017)03-006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