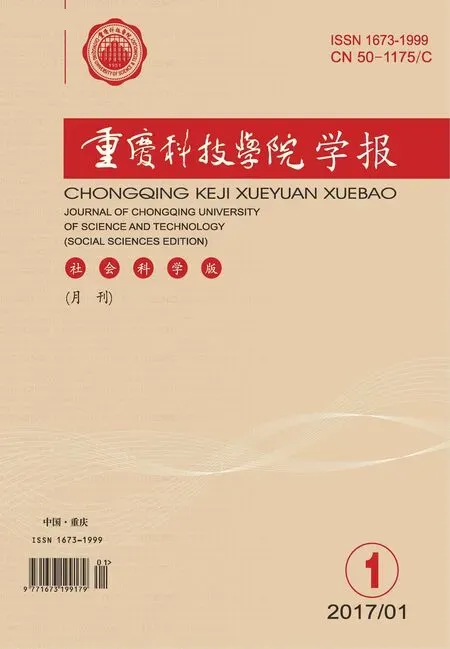论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
殷艳梅
论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
殷艳梅
司法实践中对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举证时限制度的运用存在一些问题。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法官对举证时限制度的使用态度较为消极且释明不够。应进一步强化法官的释明义务。复杂案件进行庭前证据交换。对已在庭前进行证据交换的案件和未在庭前进行证据交换的案件,应分别确定不同的举证期限。
举证期限;证据失权;证据交换;释明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简称《民诉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不同情形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此条规定确立的举证时限制度明确要求当事人应当及时举证,同时将逾期举证的后果细化为训诫、罚款及证据失权3种情形。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简称《证据若干规定》)相比,《民诉法》第65条在举证期限的确定、逾期举证的处理上更为科学合理。但是,对于具体适用的情形,第65条的规定并不明确,需要进一步做出符合法理和实际需要的解释,以增强可操作性。
一、对逾期举证法律后果的理解
从时间上看,提供的证据超过了举证期限均应视为逾期证据。这里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通常意义上的“新的证据”。例如,一审中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因客观原因未及时提供的新发现证据,经法院准许后的延长期限内仍未提供的证据,二审中提交的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另一种情况是当事人未及时提交的证据。无论当事人是否故意,均构成逾期举证,证据必须说明理由才能提交法庭。第65条既为有正当理由的逾期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提供了通道,也赋予了当事人说明理由的义务。第65条也指出,当事人不能作合理说明时才承担不利后果;如果有正当理由,则可以直接接受证据[1]。因此,何为正当、何为不正当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充分保障当事人举证权利的前提下确定举证期限后,采用客观标准评判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有无正当理由。这不但对于当事人有约束力,对于法官也有制约作用,可以避免法官将逾期提供的证据直接纳入诉讼体系,保证程序和结果的公正性。因此,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首先应考虑是否存在其不能控制的客观原因,如遭遇不可抗力或对方当事人提出了新的证据。确实存在客观原因的,法官应在听取当事人理由后,组织对证据进行质证,无需考虑是否应给予相应惩戒。其次,从程序上应尊重当事人双方的平等权利。当事人一方的正当理由应当让对方知晓,至于是否需要双方当事人与法官共同在场进行说明,或者赋予对方当事人对于将逾期证据纳入诉讼的异议权,法律未作明确规定的,不宜作硬性要求。若对方觉得不当,可以将其作为一个上诉的理由。
二、《民诉法》第65条适用现状
(一)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
实践中,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低下不仅体现在收集证据的能力方面,更主要的是当事人理解哪些证据对证明事实有利的能力不足[2]。前者尚可通过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来弥补,而后者却不能。调查中,当事人称“不知道这个证据有没有用,想想还是拿来了”。这一理由严格来说不能称之为正当理由,但又具有合理性。不仅如此,当事人庭后主动提交的证据对事实认定大多没有影响,从当事人仍积极提交的情况来看,其事先明知的概率极小。更何况,举证责任分配本身就是较为复杂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变动性,当事人难以理解也很正常。
(二)法官对举证时限制度的适用态度较为消极且释明不足
在举证时限制度的接受方面,法官普遍认为,要求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完成举证是很难实现的,第65条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取得立法所预期的适用效果。因此,对于逾期提交的证据,法庭一般都会组织质证,并未真正采取训诫、罚款和不予采纳证据的制裁措施。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客观要求下,法官之所以能接受逾期举证,是因为逾期举证在当事人举证能力低、不了解程序法等因素下具有合理性。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逾期举证为多数法官所接受。《民诉法》第65条所规定的法律后果虽较《证据若干规定》有所缓和[3],但法官基本不认可对逾期举证的证据直接认定失权,对于训诫和罚款也十分慎重。
在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法官有没有做到相应的释明义务呢?从诉讼流程来看,在证据交换或庭审之前,除给予当事人书面举证通知书外,法官一般不对当事人进行举证指导,除非当事人主动询问。而证据交换仅是“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才能适用,基层法院一般不会在庭审前组织证据交换。同时,受《证据若干规定》的适用影响,证据交换一般不超过两次,这对于涉及医患、知识产权、房地产、建筑工程等方面的复杂案件而言,根本不能完全满足充分举证、质证、补充举证、再质证的司法程序的需求。因此,庭审便成为当事人了解法官心证和揣测其举证是否充分的主要阶段,庭后补充提交证据成为唯一的补救方式。
《民诉法》第65条规定,法官需根据案件审理情况及当事人主张确定举证期限,但实践中,很少有法官针对案件本身差别化地确定举证期限。法官受理案件后,通常以举证通知书的形式指定举证期限,期限一般在开庭日期前[4]。此时,案件未进行实际审理,证据也没有进行交换,法官只是凭借原告的诉状和初步证据来指定举证期限。随着证据交换或庭审的进行,法官会允许当事人不断补充举证,甚至不会限制当事人补充证据的时间。因此,当事人也难以认识到所谓举证期限及逾期举证法律后果的严肃性。关于举证期限的主观认知的调查显示,部分法官受《证据若干规定》的影响,认为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为收到应诉材料后的15天,普通程序的举证期限为收到应诉材料后的30天。多数法官认为举证期限是在收到应诉材料后至开庭前,只有个别法官认为举证期限是在言辞辩论终结前。因此,举证期限制度的适用问题,首先是如何合理确定举证期限的问题,然后才是如何适用逾期举证法律后果的问题。
三、对完善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建议
(一)强化对当事人举证权利的保障
1.强化法官的释明义务
法官的充分释明是当事人及时举证的重要保障。诉讼实务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由当事人本人参加诉讼。他们通常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不熟悉诉讼程序,因此,法官必须履行释明义务,主动向当事人发问或提出建议。结合诉讼流程,为保证当事人充分举证,应强化法官的释明义务。首先,庭前明确告知当事人举证内容。在受理案件后,法官应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明确告知当事人举证范围、权利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弥补目前举证通知书内容的不足。因庭前法官不可能完全了解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及案件具体情况,庭前释明应以该类案件一般举证内容为主。如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的特点,法院总结受害人主张法定损失项一般应提交的证据,在立案阶段或庭前交给当事人。根据类型化审理的要求,对其他类型案件也应进行总结,这将大大减少庭前口头释明的工作量。其次,庭审阶段就当事人是否已充分举证进行释明。实践中,法官往往以庭审的形式组织当事人双方对证据进行质证,对双方无争议或争议点较少的案件组织辩论[5]。在庭审阶段,法官应对当事人举证是否充分进行释明,特别是对影响法官裁量而当事人还未意识到的重要事实,法官应向当事人释明,给予其充分举证的机会。
2.复杂案件进行庭前证据交换
国外有关法律通常规定,在庭前应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使当事人明确需搜集和提供哪些证据,保证当事人充分举证。在我国,对于一般案件来说,庭前交换证据制度在实践中无效率上的优势。我们也不宜实行美国式的发现程序,因为没有发达的律师制度作保障。因此,将庭前交换证据与庭审中交换证据严格区分开来并无实际意义。但对于复杂案件而言,在庭前组织证据交换却是必要的。关于证据交换问题,《证据若干规定》第37条至第40条的规定不尽合理。笔者认为,基于案件的复杂性,法官在受理案件之初,不应直接确定举证期限,而应指定第一次证据交换的时间或第一次审前会议的时间,尽早启动证据交换程序。为了充分保障当事人举证的程序权利,证据交换不应统一限制次数[6]。
(二)不同情形下举证期限的确定
《民诉法》第65条否定了法官直接指定举证期限的做法,举证期限的确定就不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而应是动态过程的结果[7]。举证时限届满是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补证、再质证的反复过程后,围绕原告的诉讼请求,结合审理的实际情况,有时甚至需要经过释明程序后,由法官酌情做出的决定。根据有无庭前证据交换程序,举证期限的确定应有所区别。
第一,对于已在庭前进行证据交换的案件,法官在根据案件情况确定第一次证据交换的时间后,应根据当事人的举证情况,与当事人双方共同确定举证期限。在该期限内,当事人应能完成举证,且举证是充分的。因此,最后一次证据交换即证据交换程序终结的时间应是举证期限届满的时间。举证期限届满的效力表现为:当事人在之后的言辞辩论中,原则上将不得提交任何新的证据材料,除非如第65条所规定的存在客观原因。
第二,对于未在庭前进行证据交换的案件,当事人充分举证的前提是法官的充分释明,即法官应基于对法律关系的判断,结合实体法规定及案件具体情况,对当事人举证责任承担及理由、所要达到的证明要求充分释明[8]。在此基础上,认定举证期限届满才具有合理性。根据诉讼流程,法庭言辞辩论终结应是法官判断当事人举证完毕,案件事实及法律关系明晰的节点,该时间应同时是举证期限届满之时。
四、结语
《民诉法》第65条的实施促进了举证时限制度的适用。司法实践对第65条的适用现状为我们完善及推进举证时限制度的适用提供了思考方向,需在充分保障当事人举证权利的基础上,正确理解举证期限及逾期举证法律后果的规定。这既需要从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相关内容,也需要积极的司法实践。
[1]张洪铭.新民诉法中举证时限制度的思考[N].北京:人民法院报,2012-11-20.
[2]彭万林.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161.
[3]奚晓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142.
[4]李浩.举证时限制度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法学,2005(3).
[5]熊跃敏.民事诉讼中法院释明的实证分析[J].中国法学,2010(4).
[6]关保权,吴行政.庭前证据交换规则在我国的确立及证据失权问题研究[J].人民司法,2001(9).
[7]丁巧仁.民事诉讼证据制度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480.
[8]张卫平.民事诉讼中举证迟延的对策分析[J].法学家,2012(5).
(编辑:王苑岭)
D925.113
A
1673-1999(2017)01-0023-03
殷艳梅(1978—),女,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2016-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