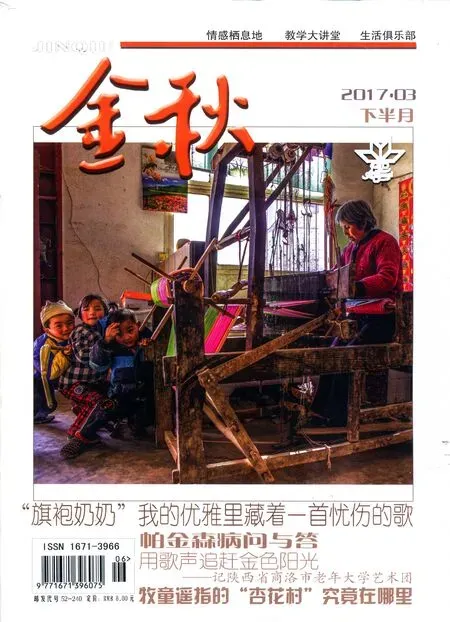我有一位牛“哥哥”
文/傅建海
我有一位牛“哥哥”
文/傅建海
我的这位“哥哥”和我都生于1949年,不同的是他生在5月份,是解放前,我生在11月,属解放后。我的这位“哥哥”不是人,是头牛,是我们家的大犍牛。
我家在1926年前曾有过一头牛。那时北洋军阀刘镇华的部队有一个班在我们家住了半年,临撤退时,他们不但没给房租钱,连我们家的牛也给拉走了。对一个农家来说,一头牛就是半个家当,人们要靠它拉犁耕地,拉碌碡碾场,拉磨子磨面,所以我们对刘镇华部队的痛恨是很深的。没牛的日子父亲过了20多年,快解放的时候,他下决心要买一头牛。大牛买不起,听说七八里外的村子有一家的老牛刚下了个牛娃,就跑去买,人家说刚下了两天,买回去也养不活。父亲说:“放心吧,过两年你来看,一定是一头大犍牛”。
牛犊到家后,全家人像抱养了个男娃一样高兴。我奶每天烧一锅小米粥,把牛抱在怀里,一勺子一勺子地喂,我父亲则陪牛睡了好几个月。半年过去,牛娃长大了,我也出生了。那一年农历是牛年,我属牛,它是牛,全家人都说一年添了两头牛,我小应该把牛叫哥。
在全家人的精心呵护下,小牛两年后就和成年大牛没有什么区别。按当时的习惯,牛两岁时人就开始教它干活,但爱牛如子的父亲却说:“牛和人一样,太小了干活挣着了就长不大了,我都二十几年没使过牲口了,也不在乎这一年半载”。所以到3岁时父亲才教牛上套。那时我也3岁了,经常和牛一起玩。牛很听话,真像我的大哥哥,懂得大让小,攥耳朵拉尾巴打屁股,怎么惹它它也不恼,还经常舔我的头和胳膊。我常拉着它转圈子,转累了就骑在它的背上无休无止地和它说着话。我奶说:“这俩真是亲兄弟”。
那时我的牛“哥哥”是我们村数一数二的大犍牛,一对拳头般的大眼睛透着灵气,两个高高翘起的半尺长的犄角向世界宣示着它的存在和威严,深红色的毛发整整齐齐,在太阳下熠熠生辉。它的屁股就像个大磨盘,脊背平得可以当床睡。和别的牛一起耕地,它跑的快,耕的深,并且第一个到达地头。拉磨磨面,同样多的粮食,别的牛两小时磨完,它一个小时就行了。村里没牛的人家总爱借我这位“哥哥”干活,送回来时都夸它力气大,听使唤。我父亲特别惜牛,耕地时总是自己扛犁,牵着牛走到地里才上套。我四五岁后,凡是到地里干活,都是我牵牛。牛耕地时,我就在地头拔草,一个来回回来,我就手捧着新鲜的野草给牛吃。收工时,父亲扛着犁唱着咣咣乱弹走在前面,我牵着牛也学着父亲的样唱着自己也不知啥意思的戏走在后面。有时父亲还让我坐在牛背上,夕阳匀匀地洒在人和牛的身上,真是一首绝妙的田园诗。
后来,农业合作化开始了,不但土地要入社,牲口也要入社,我父亲是副社长,自然要带头。我们都舍不得牛走,特别是我奶奶,真像谁把她亲孙子抢走一样,嚎啕大哭,弄得我父亲没办法,答应先拉去做个样子,然后再拉回来住一个礼拜。给别人解释说家里草料没吃完,吃完了就过来。一个礼拜后真要走的时候,全家人都流泪了,我奶哭得不敢出屋子。牛也知道这一走再也回不来了,一步三回头,哞哞地叫着到了农业社的饲养室。
牛虽然归了公,但我们始终认为它还是我们家里的一个重要成员,过几天便要去看看膘掉了没有、毛乱了没有。我奶是小脚,过一段时间还要我们扶着她颤颤巍巍地去看牛。牛见了我奶哞的一声长叫,惊得正在专心吃草的其它牛抬起头都往这边瞧。我奶抓一把麸皮放在牛的嘴边,牛迟迟不动,一眼不眨地看着我奶,用嘴舔着我奶的手,那个亲密样谁看了都要流眼泪。奶奶给饲养员大伯说:“娃呀,你要把大犍牛喂好啊,这牛乖,不要叫别的牛欺负啊!”饲养员连声答应:“姨,你放心,我一定把你的心肝宝贝喂好”。
人想牛,牛也想人。我们队的地就在我家门前,牛要干活必须从我家经过,它拉着犁走到我家门口时总要叫几声,好像给我们打招呼:“我干活去了”。收工回来时,只要我们家门开着,牛都拉着犁往里跑,人是拽不住的,只能跟着到我家。我们不管谁在家,都会给牛和上一盆麸子水,没有麸子了,有啥和啥,甚至麦面都给和过。牛喝过麸子水后,还不忘和我们亲热一番,拱得我们全身都是麸皮。虽然弄脏了衣服,但我们宁愿洗衣服也没扫过它的兴。有一次,牛很长时间没见我家的人,拉套回来又见门关着,就长时间站着不动,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家的门,好像在思考着什么,打都打不走,还流下了眼泪。好几个扶犁的社员很感动,只好等牛自己愿意走时才跟着回到饲养室。我们听说此事后心里都很难受,分别到饲养室把牛看了一回。
到了1959年的上半年,“三年自然灾害”的兆头已经出现:粮食不够吃了,食堂也解散了,牲口料也少了,牛开始掉膘了;到了下半年一些老弱病残的牲口开始死亡。1960年一开春,青壮年牛就连续死了好几头。我奶不放心大犍牛,叫我去看了几回,还好,牛虽然掉了膘,气势还在,到底还是身体素质好。我们都默默地为它祈福,希望它和我们一起渡过难关。然而,到了下半年,40多头牲口只剩下了20多头,能干活的也就七八头了。牛越少,活越重,又吃不上料,大犍牛终于支持不住了,瘦得皮包骨头,走路摇摇晃晃,就这还坚持出工。我奶叫给队长说一下,别给牛派活了。可谁去说呢?说了顶事吗?
有一天放学,我看见一群人在剥牛皮,到跟前一看是大犍牛,赶快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早已知道了,她让我小声点,别让我奶听见。我放下书包就去看杀牛,等着分肉。大家都知道我们全家人对大犍牛的感情,一致同意给我们家多分一斤肉,并把牛头和四个蹄子送给我们作纪念。有人还说,老婆(指我奶)见了非哭不可。果然,一见牛头我奶就大声哭了起来,引得我们都掉了眼泪。按理说我们不能吃大犍牛的肉,我们也真的不忍心吃,但在那个年代,吃了上顿没下顿,不吃怎么办?头和蹄子上还有肉,我们不忍心再剥,埋到了后院的椿树根下。我先堆了个坟墓样,父亲叫铲平了,说看了难受。我当兵后每年探亲回来,都要在椿树底下待一会。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忘怀那位英年早逝的牛“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