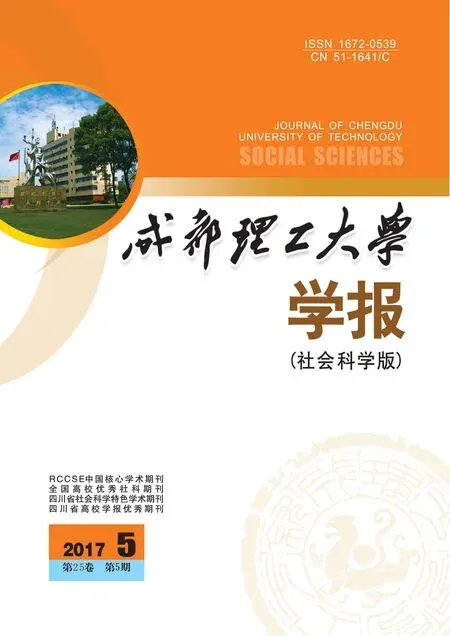论作为爱敬之德的孝道如何使“移孝作忠”成为可能
陈志雄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论作为爱敬之德的孝道如何使“移孝作忠”成为可能
陈志雄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孝”是儒家所倡导的一个德目,爱敬构成了孝之为孝的内在性支撑,是其所包含的内在德性。爱敬之德根植于人之天性,故可成为政教之基始。从内在德性培养以及德性的生发功能上来讲,“移孝作忠”是成其为可能的,因为当人心由事亲之极而内在生发出事君治事之敬时,这是一种内在德性的自我发用,内在德性给自己立下了法则,要求自己去做合理、正确的事情,因而保持了“孝”与“忠”在内涵和实践上的不断裂。
爱;敬;内在德性;孝道;移孝作忠
一、爱敬源于人之天性
“孝”是儒家倡导的一个德目,其所内含的具体德性就是“爱”与“敬”。《孝经》中就有并言“爱敬”来讲明孝道的,如“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孝经·天子章》)爱敬构成了孝之为孝的内在性支撑,当我们去追问一些关于孝的根本性问题时,就必须对“爱敬”的来源问题做一推敲。孟子言:“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尚未免于父母之怀的孩提,葆有爱亲敬长的本然之善,即所谓良知良能也。这种爱敬之心可以由尽心以臻于仁义之德,并且人之“仁”首先在于爱亲,人之“义”首先在于敬长。此乃人性分中之事也,故可达之于天下而无不同。所以人之为孝,更无他求,在于不断去发越此爱敬之心。
本于天性的爱敬之“孝”在教化天下上具有独特的意义。陈壁生在分析《孝经·三才章》“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一句时谈到:“言先王在立法之时已经看到,天地人皆有自然之道,在天为春夏秋冬的四时循环,生长收藏的更替,在地为五土高下的区别,在人为不教而知的孝悌恭敬,天地自然有常道,而人要法则这种常道,视天之四时而行事,因地之高下而耕作,这就是‘孝’的至顺之道。”[1]在这里,是从天道层面指出了“孝悌恭敬”是人之自然,而不能说是把“孝悌恭敬”刻意标榜为天经地义之理后,外在强加于人身上,成为与人本不相干的一种负担,从而只会和人之心、人之情扞格不入。因此曾子喟然叹曰:“甚哉,孝之大也”,其成其为“大”,在于作为爱敬之德的孝乃是根于人之本性,可与天地人相贯通,也就使得因孝以教化天下成为可能,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可“达之天下也”。
“孝”首先要处理的是父子关系这一问题,故郑玄在注解《孝经·开宗明义章》时,卓有锐见地将“先王”定位到禹,皮锡瑞对此申言:“陆氏推郑之意,以为五帝官天下,禹始传子,传子者尤重孝,故为孝教之始。”[2]也就是说,家庭与家天下之政治秩序的维持都亟需提出孝作为至德要道来纲纪。进一步说,家天下的社会治理会更加重视将本自人心的爱敬加以引导和发越,不然这种爱敬之心只会滞留在质朴层面,而只是一种基本的情感与趋向。一个人儿时会对父母有依恋之情,之后对已逝父母更有思慕之情,于是孟子慨叹曰:“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万章上》)从儿时的依恋到成年时的思慕,这是爱敬之心不断得到发扬的表现。即便是禹之前的舜,不是以传子重孝来治理天下,却依然身为世范,能够真正做到了爱敬之“孝”。故有斯人,即有此爱敬之心。
然而,无论是在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还是边沁及穆勒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中,他们都只是抛出一个抽象的、完全普泛化的道德原则来约束个体,而儒家的孝道则是专门地指涉于一个特定情景、特定角色下的个体来思考其所应当做出的行为。这个问题就不得不与孝德所包含的“爱”相联系起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儒家讲的“爱”首先不是一种私己收敛的“情爱”,而是可以不断推扩开来的仁爱之情,它有着亲爱、仁慈、悲悯等广泛的、不同层次的内涵。因此在施予这番“爱”的时候要讲求差序分化。之所以造成差序的局面乃是导源于主体所面对的人物的改变以及相应地自己要做出角色转化。
儒家的这种理解思维正是将人与人看成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从而再来谈社会秩序的建构。凭依个体当下的角色及与他人的关系来讲求修养道德的具体问题,激发人们通过人的呵护相系而不断生成道德力,并由此可以直达到人的内心本性。这也就是安乐哲所勾勒出的儒家角色伦理学,“这种整体视角性哲学建立的基础,是事物相系的重要性;它挑战原教旨性的‘自由个人主义’。‘自由个人主义’将人视为各不相关、一己自为、算计、不受管束、经常以一己利益驱使的个体。”[3]因此,儒家会认为,在德性的生发功能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与人、事物与事物之间没有天然的沟壑,他们之间随时可以互相转变与接合,因此人在道德施予上又具有了相通的可能性。个体的特殊性只在于他不断扩展这种相通性,不断将道德行为落实到不同情境下的不同对象,进而反身性地来映照和修养自己。
人们会发现,发轫于人之天性的孝德,将其践行之是一个充满活泼与生机的过程,而不是对一个抽象诫命的死守。在这种活泼与生机中又始终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统一到主体心灵上来,即不管情景与角色如何变化,任何情况下你都要秉“义”而行所当行之事——即“敬”以持之而不逾矩,使得“孝”之“爱”与“敬”在这里得到了汇合。
二、爱与敬之别
爱之情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强调人与人的相亲合同。如前所述,这种爱不是指具有排他性的情爱,而是可以推扩开来的,故朱熹常把“仁”释为“爱之理,心之德也。”[4]“仁”主于爱,仁者爱人,而爱人莫大于爱亲,不教爱即忘亲,则亲人与路人何殊?故孝为行仁之本。但父子关系中如果一味以“爱”来维持,而不加以庄严,则父子之道流于简易而狎昵,不复有父慈子孝之理。此时,一旦引入“敬”的道理,则将父子关系庄严化,强调父子长幼尊卑之别。《礼记》开篇即点明要旨曰:“毋不敬”(《礼记·曲礼》),《孝经·广要道章》云:“礼者,敬而已矣。”敬之情则会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其养成与礼制相关而更多是强调一个别异、秩序规范与遵守。当然,“敬”也有指做事认真负责的态度,如言“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总之,爱敬都是基于人情的具体变化,而来加以理顺,增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古人言“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5]前者是爱深而敬薄,后者是严多而爱杀,此番言语正是对爱敬之合理状态的一个关注。爱与敬之多少的合理搭配成为人情向外表达的一个通常途径。
所以“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孝经·士章》)明皇御注:“言爱父与母同,敬父与君同。”[6]很明显,明皇这是在故意取消事君与事父的区别,而强调要忠君爱国。在这里的“同”不是指等同、平移,而应该有“通”之义,即情意之通、德性之通。郑玄注曰:“事父与母,爱同,敬不同也。事父与君,敬同,爱不同。”[2]这种“不同”是指程度多少上的不同,而不是指没有。子亲其母,与母亲亲近相处,亲爱之情自然增多,则必然导致的就是敬意减少,这是自然之理。好比《论语》中所言:“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与人交往长久而亲密则敬意往往就会在无意中衰减,虽久而能敬爱如新,所以为难能可贵。故子于其母,爱多而敬少,子于其父,敬多而爱少,这与人日常所言“严父慈母”的人情现象相一致。另一方面,这段经文也表明:子于其母是爱之深,于其父是敬之极,人之爱首先在爱母,人之敬首先是在敬父,此亦是人之自然之理,能亲亲才能去仁民爱物。因此,这句经文前后蕴含着两个自然之理。
同样是作为“孝”所包涵的两大德性,“爱”与“敬”在样态上存在着区分,从而构成了人情的丰富形态,进而决定了人在施予孝德时不是一味地抱守一个僵化的道德规范,而是要因人因时加以合情合理地表达。
“敬”显然是带有严肃和敬畏的意思,如果要把这种效果的达成放到政教层面上来,我们可以看到,先王并不是通过下命令来教之以“敬”,而是通过尊敬自己家中的长者来为百姓做出表率,引导百姓主动参与到自我规范的社会秩序中来。而通常依靠强制手段使百姓顺服所形成的自上而下的强权秩序,是变“敬”为“战栗”,并完全抹杀了“爱”之温情——君臣无有情义,君民也只是牧羊人与羊群的关系了。
三、爱敬之德是政教之基始
《孝经》明确指出:“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孝经·圣治章》)明皇注曰:“亲犹爱也。‘膝下’谓孩幼之时也。言亲爱之心生于孩幼,比及年长,渐识义方,则日加尊严,能致敬于父母也。”[6]每个人对父母的亲爱之心早已萌发于孩提之时对父母的依恋之情,随着逐渐能够认知道德规范,并由社会规范对己之行为加以严正化,从而能够培养起敬奉父母的能力与意识。相比“爱”,“敬”中带有更多的理性成分,其发生所需要的外在条件更多。因此“敬”的感情与道德意识更需要外在规范的约束与引导,在应对洒扫中逐步培育起来。
郑注说得更条畅明白:“因人尊严其父,教之为敬。因亲近于其母,教之为爱。顺人情之事。圣人因人情而教之,人皆乐之,故不肃而成……孝道流行,故乃不严而治。”[7]经文在这里就进入到关于政教的问题,但它并不直接就去谈孝,而是先谈爱敬。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德目的孝对于“政教应当基于人的何种质地来建构”之问题,它是抽象暧昧的,必由前始之爱敬而得以明朗。这也就说明爱敬是孝之培养的基始,爱敬之教即是教以孝也,以此来推行政教,则可以不待严肃而自然成治。盖人在蒙幼之年受外界扰攘较少,最容易葆有人伦之正性,君王若能加以合理地引导与发展,则孝教之流沛然矣!
如前所述,正是因为爱敬是人之不容已之心,故作为爱敬之德的“孝”可以成为一种普遍道德而被君王所倡导,以化成天下。在这里指出,君王教化活动的展开必须根植于人心之自然,因顺人情,才能够达到实质性效果。所以,作为爱敬之德的孝道在社会治理与秩序建构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孝所化成的社会秩序是一种自然而合理的政治秩序;这种秩序首先是从每个个体内心开出来的,而不是外力所绑扎在人身上的;因为维持这种秩序的道德力量有一个源泉混混的来源,社会就成为一个绝对的道德共同体。人心的协同必然会带来社会的和合,社会的和合必然会带来秩序的井然,如此才称得上众之本教曰孝。
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征之于《论语》我们可以看到,行孝不能是装模作样,以膏粱糊口便能了事,尽管这种孝让我们看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和谐。真正的孝需要更多的付出,它不仅表现为行为上的“我愿意”,更要以“我渴望”或“我想要”的态度来履行之。所以,出于道德责任的压力而勉强行之,或者出于一时兴致的爱好都将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爱敬之孝,它们在道德价值问题上也会是无从谈起的。因为,既然孝包含了“敬”的成分,而“敬”就是要求有一种深思熟虑的审慎与无怨无悔的自我付出意识,并能让自己在践行孝的过程中得到无穷的心安与乐趣。所以,经过“敬”洗礼后的孝行就会笼罩着一股义无反顾的从容之感,这才是古典儒家所想要达到的效果。
进一步地,如果只根据西方“权利人”(rights-bearers)的概念来讨论,而不是放在儒家政教所开辟的家庭视阈下来思考,当代社会政治所纠缠的许多难题——诸如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女性能否自由选择堕胎、同性恋婚姻应该被允许么——是永远也得不到解决的。因为脱离了家庭的环境,原本的自然人再次被打散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也就谈不上有所谓的爱敬之德,因为他首先完全可以按着自己的一时癖好来做出自由选择。因为他们所谓的自由就是独立自己,并不存在一种互系相连的角色伦理。他们所在的家庭只是被理解为:根据成人双方自愿结合而形成的非原生性机构,当其不再能够体现双方自我利益时可以随时加以撤除。这种意义上的“家庭”当然就不能孕育出“爱”之温情与“敬”之庄重。如此,人的生存境遇与大自然中四处游荡的野兽并没有什么两样,永远也找不到一个能够与他人安心共处的归宿。社会公德(如“作忠”)对他们来说只会是逢场作戏式的暂时配合,并没有激发出一个内在道德心来促成他去这样做,更谈不上会拓展出关于国家责任的观念。
四、移孝作忠:爱敬之德贯乎家国
爱敬之德既明矣,则“孝”之内涵亦明矣。然者何谓之“忠”,“忠”者,最先的意思应该如朱熹所言的“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4]即要求人专注于内心的诚意恳切,所以它在《论语》中经常会与“信”字连言。也就是说,它首先是在要求人的一种内在德性的孕育与保持,而不是如后人所理解的将其内涵死死地限定在绝对效忠于君之事功层面。
首先,一个不爱敬其父母的人,而能够在公共生活领域中善待他人,这是难以想像的事情。即使表面上他能够做到,也只会是出于一己之私的考虑而阿意奉承,是虚妄无实的。因为他的行动完全缺乏一个内在来源,而纯粹由外在功利性目的来驱动。而一个对父母毕恭毕敬之人,如何能够使其必然在公共生活领域做到真诚与善良,这会是儒家孝道之原理所要解决的难题。以君臣关系为例,君臣与父子虽同为五伦之一,但具有较大的差异,父子是无所逃之天伦,君臣则以义合,那么“移孝作忠”所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将根植于天伦的道德顺利地培育到以道义相合的君臣关系之环境中,其间因境况与条件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如何来弥合?
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曰:“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周易·彖传·家人》)即一家人有严正的君长,指的是父母。此言难免有将君长与父母相比附之嫌,力图合同二者。孔颖达疏曰:“上明义均天地,此又言道齐邦国。父母一家之主,家人尊事,同于国有严君焉,故曰‘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8]孔氏认为尊父同于严君,但此“同”是何种性质上的“同”,是何种程度上的“同”,这是孔颖达所没有告诉我们的。其又曰:“正家之功,可以定于天下,申成道齐邦国。既家有严君,即父不失父道,乃至妇不失妇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后为家道之正。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8]通过尊严其父母来生成尊卑上下之序,严正治家之道,这是对纲常之道的正常维护。但这种维护与张扬并不能泯灭正家何以能正国治天下的问题。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三纲中,前一纲涉及国家政治生活,后两纲则完全在家庭生活范围之内,历来学者都试图去证明:后两纲是前一纲得以实现的基础,只有先正一家之事,方有可能治国平天下。如董仲舒言:“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则民如麋鹿,各从其欲,家自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虽有城郭,名曰虚邑。”相应地,苏舆注云:“民生而有欲,圣人范之以礼,为之立父子兄弟之等以致其严……家无良子弟,君亦安得有良民臣哉?故政教之本,必在家庭;庠序之义,首申孝悌。”[9]显然,他们都认识到了:无孝悌则家自为俗,民风败坏,家与国休戚相关,唇亡则齿寒矣,两者互为渗透,相为表里。然究竟上“唇”不是“齿”,“齿”不是“唇”。家与国可以在价值设计上实现一致,意义追求上实现勾连,但是并不能否认其内在的实质性差异。否则,当治国出现问题时,只会去向治家之法讨要经验,这种暧昧不清,只会给国家治理带来混乱与麻烦。
人之内在德性的生发性为解决这个困境开辟了可能。“移孝作忠”不能成为一种道德灌输与情势渲染,而应该强调治理社会要善于诱发人之内在德性,这可以成为一种以简御烦、标本兼治的治理途径。也就是说,人内在之德性可以促成此“移”。此“移”不仅仅是道德经验的复制或平移——即学会了一套事亲的规范后,将其刻意搬弄到事君之事上,然后重复进行着经验的展开,这就流于外在教条式的约束了。应当是人心由事亲之极而内在生发出事君治事之敬,这更是一种内在德性的自我发用,内在德性给自己立下了法则,要求自己去做合理、正确的事情。这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是对道德之价值的绝对肯定,也是对道德主体性的一次挺立。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赵岐注云:“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10]在这句注解中,首先是要反对一个人的邪曲不正,强调为孝要正己,这一环节虽没有比“无后”来得重大,但它是最基础性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到为孝与出仕的问题。这恰恰说明了内在德性的培育对其他事为及道德之树立的重要意义。孝子之事亲,其中的应有之义就是不允许他在外做犯上作乱之事而遗父母之忧,陷亲于不义。而事君则可以显亲以养父母,乃至于仕功大成时可以博施济众,佑护黎民,使天下老有所养,无鳏寡之患,皆得其所,这即是“大写的”敬养父母。如此看来,事亲与事君存在着莫大的关联性。“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在事亲——事君——立身这一链条上,事亲较事君具有发生上的优先性,也就是说:人在事亲之事上培养起孝之德,从而可以为正确地事君准备必要条件。同样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8]422这是从另一个侧面强调:夫妇、父子亲情关系的确立,也就是家庭秩序的条理化后,可以为君臣秩序的维护奠定基础。
如此而后有“忠臣必出孝子之门”的观念,这种观念本是一种经验的总结,但它指明了:“忠”与“孝”之间确实存在着德性上的逻辑一致性。当然这种内在德性的正确性还在于:必须要意识到君臣是以义合的,如若君不守其分,则臣有谏诤以匡正之的义务,情况严重的话就应该义正辞严地做出“待放三年”或“接淅而行”的行动。这就是前面所谈到的,为孝要“敬”以持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秉义而行。
《为政篇》有言曰: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就是说,把自己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德行推广并影响到政治上去,这也是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又何必居位得权才是为政呢!显然,孔子是不把为政与谋取官位操作权力等同起来。换句话讲,当孝友之道得以昌明,人伦关系与政治秩序自然就会得到理顺,为政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此,所以行孝友、尊德性即是为政。这种通达的理解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1]陈壁生.孝经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32-133.
[2][清]皮锡瑞.孝经郑注疏[M].师伏堂丛书,光绪乙未刊本.
[3]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挑战个人主义意识形态[J].孔子研究,2014,(1):7-9.
[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50.
[5][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264.
[6][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9.
[7]陈铁凡.孝经郑注校证[M].台北:“国立”编译馆,1987:136-138.
[8][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212.
[9][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168.
[10][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10.
编辑:黄航
Theory as the Virtue of Love and Filial Pietyto Make It Possible to Move “Filial Piety as Loyalty”
CHEN Zhixiong
(School of Philosoph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Filial piety” is the Confucian advocated by a German, love worship constitutes the internality of filial piety as filial piety, is inherent in its virtue. Love the worship degen rooted in human nature, it can be the base of the beginning of church and state. Cultivate virtue, and virtue of germinal function from within, “move the filial piety as loyalty”is a possible, because when the heart by the close of the number of things while germinal accident within the worship, this is a kind of inner moral self use, inner virtue to set the rules, requests itself reasonable, the right thing to do. Thus keeping the“filial piety”and “loyal”on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practice without fracture.
love;worship;the inner virtue; filial piety; move the filial piety as loyalty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5.008
2017-01-15
2014年度西南政法大学科研训练创新活动专门项目(14XZ-BZX-044)
陈志雄(1992-),男,福建泉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儒学、中国政治哲学。
B222
A
1672-0539(2017)05-0041-05
——以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讨论中心
——从明代朱鸿《孝经》类编著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