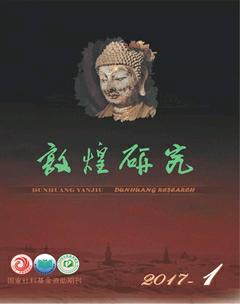论敦煌变文骈句的个性与功能
许松+程兴丽
内容摘要:敦煌变文中频繁地使用了骈句,与传统骈文相比较,它的特点体现在驰骋才气的长句对仗;匠心密运的错综对;语言平易流畅,基本不用典故,文字浅显易懂;对仗不精切;对仗触犯了禁忌。变文骈句在文中的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摹状人物,渲染场景;直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提升变文的文学韵味;有助于记诵。变文没有排斥骈文的必要,相反,还可以吸收骈文的长处为我所用。
关键词:敦煌;变文;骈文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1-0111-09
杨雄先生在《敦煌文学中的骈体文》一文中说:“骈体文在敦煌文学中并非偶发、个别的现象,而是敦煌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1]敦煌遗书中,许多文体都使用过骈句,有的是零散地出现,有的则是大段的骈文,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中的骈句篇幅超过了散文,散文俨然是骈句的点缀而已。敦煌骈文集中出现于以下文献中:碑铭文、书仪、邈真赞、愿文、变文、各类文范等。
作为敦煌文学大宗的变文,涉及骈文之处甚为繁多,不特《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为骈文奇观,即使如《伍子胥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五)》亦有精彩奕奕的骈文,读之仿佛于彩舟云淡之际忽见星河鹭起,振人神智。因此,有必要对它的骈文使用情况做出一番探索。传统骈文的特点不外乎:辞藻华美、对仗精工、用典富雅、句式灵动、音韵协调,变文骈句里完全可以按照五个方面逐一寻找材料以证成其符合标准骈文的规范,但清代袁枚所说“意义俱被说过,作者往往有叠床架屋之病,最难出色”[2],为了避免叠床架屋之弊,今拈出敦煌变文骈句中具有独特个性、不同于传统骈文之处,以彰显变文骈句之文学价值。
一 变文骈句的个性
(一)驰骋才气的长句对仗
柳宗元《乞巧文》说骈文的特征是:“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四言句、六言句成了骈句里面最常用的句式,当然,与四六言一起常用的还有五言句、七言句。骈文作家笔下络绎奔赴的奇采俪句往往不会超过七言,但是,在变文中,我们看到变文作者对七言以上长句的积极尝试。《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遥瞻日月而□归龙楼,远降丝纶而撫安鬼郡”[3],上下句均为九言句。《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碎肉迸溅于四门之外,凝血滂沛于狱墙之畔”也是九言长对。
还有一种情况是同一种对仗方式,连续对仗达四句之长,如《双恩记》“使织妇不劳于机杼,耕夫罢役于犁牛,渔翁断钓于江河,猎士解网于林野”[3]931,这四句都是“主语谓语补语”的结构,变文中虽然也有连续四个七言句对仗的情况,如《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一)“日日满空呈瑞彩,时时四远有祯祥。天龙数数垂加护,贤圣频频又赞扬”,但是往往一二句相互对仗,三四句相互对仗,句子结构也不一样,像《双恩记》这般有意用一种结构进行排比对仗的例子极为少见。
变文文献里最长最复杂的骈句要算《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中描写如来盛大威仪的这八句:
隐隐逸逸,天上天下无如匹。左边沉右边没,如山岌岌云中出;崔崔嵬嵬,天堂地狱一时开。行如雨动如雷,似月团团海上来。[3]1035
这里的“隐隐”跟“崔崔嵬嵬”一样,都是高大雄峻之义,而非隐隐约约之义[4]。“隐隐逸逸”对“崔崔嵬嵬”、“岌岌”对“团团”六个重音联绵词构成严谨的对仗”,属于《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中的“联绵对”[5]。上联四句、下联四句分别对仗,并且每一联都是四七六七的句式。两联对仗的字数长达四十八字,真是使人叹为奇观!
我们再投以鉴赏的目光,发现这一联长对不仅上下联互对,而且句中还有自对,渗透着作者苦心孤诣的深深匠心,今以下划线表示当句自对,以着重符号表示上下句或者隔句远对,可以一目了然:
隐隐逸逸,天上天下无如匹。左边沉右边没,如山岌岌云中出;崔崔嵬嵬,天堂地狱一时开。行如雨动如雷,似月团团海上来。
变文此处的两联长句对仗,不仅参与对仗的句子长、字数多,“隐隐逸逸”、“崔崔嵬嵬”、“岌岌”、“团团”等联绵词对仗多,而且还深藏着上下句互对与句中自对这般复杂的对仗情况,真是体现了变文作者沕密的文心。
(二)匠心密运的错综对
“错综”是将本来可以整齐对称的语言形式故意变为参差错落,适当地使用这种修辞手法可以避免平直单调,使句子富于变化新鲜之感。如《淮南子·主术训》:“夫疾风而波兴,木茂而鸟集”,波兴、木茂、鸟集都是名词加动词的主谓短语,而唯有“疾风”是形容词加名词的偏正短语,显得与其他三个词语格格不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读解,若可以改为“风疾而波兴”则显得多此一举了,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云“上言疾风,下言木茂,亦错综其词。《意林》引此,作‘风疾而波兴,由不知古人文法之变而以意改之”[6]。“错综对”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把本来可以对仗的句子中的某个字词变换位置造成不对仗的效果。变文中的错综对可以找出丰足的例子:
降魔杵上火光生,智慧刀边起霜雪。
——《降魔变文》
本为:“降魔杵上火光生,智慧刀边霜雪起”或“降魔杵上生火光,智慧刀边起霜雪”。
或白如玉,或似黄金。——《茶酒论》
本可为:“或白如玉,或黄似金”或者“或如白玉,或似黄金”。
衙官坐泣刀剺面,九姓行哀截耳珰。
——《王昭君变文》
本为:衙官坐泣刀剺面,九姓行哀耳截珰。
秋冬石窟隐,春夏在人间。
——《燕子赋》(二)
本为:秋冬隐石窟,春夏在人间。
山南朱桂,不变四时;岭北寒梅,一枝独秀。
——《破魔变》
本为:“山南朱桂,不变四时;岭北寒梅,独秀一枝”,或者“山南朱桂,四时不变;岭北寒梅,一枝独秀”。
石壁侵天万丈,入地藤竹纵横。
——《伍子胥变文》
本为:“石壁侵天万丈,藤竹入地纵横”,或者“侵天石壁万丈,入地藤竹纵横”。
变文作者通过对传统模式的变形营造了陌生化的效果,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逆向受挫的审美效果,因而在人民大众间广受欢迎,取得了恒久的艺术影响。“那些真正富于创新意义与艺术魅力的作品,在阅读过程中,常常会伴随着期待指向的遇挫……实际上,真正赢得大多数读者喜爱的作品,往往既有顺向相应又有逆向遇挫。一方面,文本不时唤起读者期待视野中的预定积累,同时又在不断设法打破读者的期待惯性,以出其不意的人物、情节或意境牵动读者的想象。在这样的阅读过程中,读者既会因旧有经验的重温而快适,又会因期待视野得以丰富补充而欣慰。一部作品藝术成就的高低,显然与这样一种对读者期待视野丰富补充的程度,也就是超越读者期待视野的程度有关。”[7]
(三)语言平易流畅,基本不用典故
传统的骈文除了对仗精工之外,还有两个典型的风格,一是频繁用典,并且所用之典从精妙切合以至于追求生僻尖新,借以彰显博学,炫耀才华,《文心雕龙》所云“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8]。南朝陈伏知道《为王宽与妇义安主书》:
昔鱼岭逢车,芝田息驾,虽见妖媱,终成挥忽。遂使家胜阳台,为欢非梦,人惭萧史,相偶成仙。[9]
这是伏知道替王宽执笔,写给王宽妻子的书信,表达离别后无穷无尽的思念和对美满幸福生活的憧憬祈盼。本来写给自己夫人的篇章应该是话家常、传真情,用语当如建安时曹丕《与吴质书》那样平易流畅而真情饱满,反观伏知道的这篇文章,则雕缋满眼,用典繁深。“鱼岭逢车”用《搜神记》弦超于济北鱼山邂逅神女的典故,“芝田息驾”用曹植《洛神赋》“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的典故,“家胜阳台”用宋玉《高唐赋》巫山神女的故事,“人惭萧史”用《列仙传》萧史与弄玉吹箫引凤之事。短短的八个分句中用了四个典故,如瀑布飞泻,目不暇接。
传统骈文不仅用典繁盛富丽,而且用语雅深。“雅”指用字的高雅,“深”指文意的含蓄。聊举一例以彰显其风姿,北魏孝文帝《举贤诏》:
炎阳爽节,秋零卷澍。在予之责,实深悚栗。故辍膳三晨,以命上诉。灵鉴诚款,曲流云液。虽休弗休,宁敢愆怠。将有贤人湛德,高士凝栖,虽加铨采,未能招致。其精访幽谷,举兹贤彦,直言极谏,匡予不及。[9]64
“秋零”、“澍”、“云液”都是指“雨水”,但作者为了避熟求新,使用了“秋零”、“澍”、“云液”来替代,这三个词语比起“雨水”来显得更为高雅含蓄。《颜氏家训·勉学》云“博士买驴,书劵三纸,未有驴字”[10],这里甚有“书词三次,未有雨字”的趣味。
敦煌变文在用典遣字上的风格与传统的骈文比起来,它既没有繁复的典故,几乎不用古人之事入于文章,亦不以费解的辞藻镶嵌文句,显得清新活泼,平易流畅。论说道理的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帝王以四海为家,万民作子,出一嘉言,士女以悦;布一善政,人神以和。因当刑不夭命,役无劳力。则风雨顺时,寒暄应节,百谷滋繁,桑麻郁茂。如此持斋亦大矣,如此不煞亦众矣。宁在阙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后方为弘济耶”;颂扬帝德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我皇帝国奢示人以俭,国俭示人以礼。所以兢兢在位,惕惕忧民,操持契合于天心,淡素恭修于王道。意欲永空囹圄,长息烽烟,兴解网之仁慈,开结绳之教化。圣明两备,畏爱双彰,实为五运之尊,真是兆民之主”;写路途之风景则如《秋胡变文》“崖悬万仞,藤挂千寻。涧谷迂回,深溪交结。鸟道不通,人踪寂绝。秋胡行至此山,遂登磎入谷,绕涧巡林,道路崎岖,泉源滴浍。”
南朝沈约曾提出过著名“三易说”:
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征亦尝谓吾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用事邪?”[10]272
易见事,即在需要用典的时候使用浅显明白的典故,而不是搜索枯肠、探奇志怪,使用读者不知何意的典故。例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兴解网之仁慈,开结绳之教化”一句,“解网”用的是商汤德及禽兽的典故,在最通行的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即有记载,不须搜肠刮肚即能知其要表达的意义。“开结绳之教化”则出自《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上两处所引用典故均取材于世间常见典籍。
综前所述,我们可以说敦煌变文的行文风格正体现着沈约“易见事”、“易识字”的理论。至于“易读诵”即声调和谐,这在笔者《〈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性质、作者与用韵研究》(刊于《敦煌研究》2015年第3期)一文中有详细论述。
(四)对仗不精切
诗歌的对仗对于动词、副词、代词等没有详细的分类,对名词分类的细密却达到了针脚般细密的地步,如《诗腋》将名词分为人伦部、人事部、天文部、时令部等36种,门径森严。画疆立圻之烦琐正如律令之深文罗织,左右有雷池之忌,行于诗山者往往有捉襟见肘之叹!所以,诗歌的创作加入了变通手段,衍生成三种对仗。一是工对,即同一门类的名词相对仗,天文对天文,地理对地理。如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11],“日”与“烟”即是天文类的工整对仗。二是邻对,这也有一定的讲究,例如天文与时令对、天文与地理对、器物与衣服对,方位与数字对,等等。张籍《寄和州刘使君》“晓来江气连城白,雨后山光满郭青”[12]中“晓”“雨”是时令与天文相邻对。方干《叙钱塘异胜》“夜雪未知东岸绿,春风犹放半江晴”[12]7531中“东”“半”是方位与数字的邻对。三是宽对,即不论名词是否属于同一门类,只要是名词对仗名词、动词对仗动词、副词对副词、助词对助词就可以。如张籍《书怀寄王秘书》“下药远求新熟酒,看山多上最高楼”[12]4343,“药”与“山”是饮食门与地理门的宽对,“酒”与“楼”是饮食门与宫室门的宽对。
敦煌变文骈句作为长篇讲唱文学的构成部分,篇幅远远长于诗歌,如果讲求严整的工对的话便如同背负胖人而攀登悬崖,自然是力难为继、心难为巧的事情,是以,变文的对仗基本遵从宽对的法则,如《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一)“香烟霭霭旋为盖,宫树蒙蒙自变春”,“烟”与“树”是天文门与草木花果门的宽对,“盖”与“春”是器物门与时令门的宽对。同篇“风吹丛竹兮韵合宫商,鹤笑孤松兮声和角徵。队队野猿,潺潺流水。有心永住林泉,无意暂游帝里。忽闻空中人言,又见庵前云起”的对仗也是宽对。从目前所辑录的骈句来看,宽对是敦煌变文骈句中典型的对仗类型。
有趣的是,敦煌变文的许多骈句连宽对的要求都不能达到,很频繁地出现对仗不工整的情况,显得拙朴粗犷,今分而论述之。
1. 参与对仗的句子只有部分词语对仗(以下将符合对仗的部分用着重号“﹒”标出)
A、上对下不对
凤管长休息,龙城永绝闻。
——《王昭君变文》
离迦毗之罗城,赴雪山而苦行。
——《八相变》(一)
钟鼓轰轰声动天,瑞气明明而皎洁。
——《降魔变文》
第一例中“休息”是两个意义相同的动词组合在一起,而“绝闻”是动词加名词的动宾短语。第二例“罗城”是定中短语,“苦行”是形容词加动词的状中短语。第三例“动天”是动词加名词的动宾短语,“皎洁”则是形容词,与“动天”不相为对。
B、上不对下对
所好成毛羽,恶者成疮癣。
——《王昭君变文》
独乐一身,苦他万姓。——《王昭君变文》
娇容何处去?丑陋此时来。
——《破魔变》
第三例“娇容”是形容词加名词的偏正短语,而“丑陋”是由两个形容词组成的复合词,结构完全不同。
C、中间对两头不对
衙官坐泣刀剺面,九姓行哀截耳珰。
——《王昭君变文》
“衙”是名词,“九”为数词,对仗不工。“刀剺面”是名词动词名词,“截耳珰”是动词名词名词,也不对仗。
D、中间不对两头对
草青青而吐绿,花照灼而开红。
——《降魔变文》
“青青”是叠音词,而且“青”是形容词。而“照灼”是两个动词构成的双声词,双声对叠音,动词对形容词,如方凿圆枘不能相融合。
千般锦绣铺床座,万道珠幡空里悬。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上下句唯独中间“铺床”、“空里”不对仗。“铺床”是动词加名词的动宾短语,“空里”是名词加方位词的方位短语。
E、隔句对中一三句不对,二四句对仗
宋王有衣,妾亦不着;王若有食,妾亦不尝。——《韩朋赋》
鱼鳖在水,不乐高堂。燕雀群飞,不乐凤凰。——《韩朋赋》
第二例中“鱼鳖在水”与“燕雀群飞”表面上对仗,实则对仗并不完全。“鱼鳖”与“燕雀”的对仗没有瑕疵,但是“在水”是动词加名词,“群飞”是副词加动词,词性不同,不符合对仗原则。
F、隔句对中一三句对仗,二四句不对仗
学生好博,忘读书诗;小儿好博,笞挞及之。——《孔子项讬相问书》
仙娥从后,持宝盖以后随;织女引前,扇香风而塞路。——《破魔变》
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蜀山、蒙顶,骑山蓦岭。——《茶酒论》
剑树千寻以芳发,针刺相揩;刀山万仞而横连,巉岩乱倒。——《救母变文》
第二例“后随”是方位詞加动词,“塞路”是动词加名词,不相对。第四例“针刺”是两个名词构成的并列短语,“巉岩”则是形容词加名词的偏正短语。
2. 意对而字不对
这种情况下每两句之间的意思都是对应的,但是几乎找不到完全对仗的词语,是属于散文化气息很重的意对。
与旧时之美质,转胜于前;复婉丽之容仪,过于往日。——《破魔变》
“旧时”是形容词加名词的偏正短语,“婉丽”是两个形容词组成的并列短语,不相对。“美质”乃形容词加名词的偏正短语,“容仪”又是两个名词构成的并列短语,他们也不能构成对仗。“转胜于前”与“过于往日”意思能够相对,但字面上几乎完全不对仗,如果改为“转胜前色”对“竟逾昔姿”方可工整。
大众里不觉闹,独自坐不恓恓。
——《降魔变文》
屋无强梁,必当颓毁;墙无好土,不久即崩;国无忠臣,如何不坏?——《伍子胥变文》
眉郁翠如青山之两重,犹江海之广阔。——《降魔变文》
第四例乃叠音词,“郁翠”是两个形容词并列,不相对。“青山”为形容词加名词的偏正短语,“江海”则又是并列短语,难为对仗。“广阔”是形容词并列短语,“两重”则是数量词,“广阔”与“两重”亦天渊不合。
3. 上下句字数不等
意对而字不对,已经是对仗中很严重的问题,而参与对仗的上下句居然字数也不相等,这应当算是最严重的问题了。且看下文的例证。(字数不相称的地方用下划线“ ”标出)
一马不被二鞍,单牛岂有双车并驾。
——《秋胡变文》
睹佛玉毫之相,何福不臻;现金人最胜之形,何灾不殄!——《破魔变》
天地既不辨东西,昏暗岂知南北。
——《破魔变》
面皱如皮里髑髅,项长一似筋头子。
——《破魔变》
变江海而成苏酪,化大地而为琉璃水精。
——《降魔变文》
今年本种五升,来岁利收于十斛。
——《双恩记》
败军之将,不可语勇;亡躯大丈夫,不可图存。——《李陵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