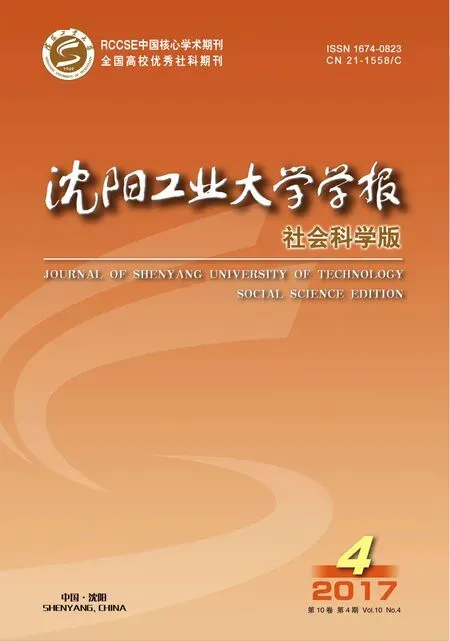死刑的制度变迁及历史命运*
——兼及《刑法修正案(九)》的刑罚理念
张学永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体战训学院,北京100038)
【专题论坛:社会变迁的法制回应】
死刑的制度变迁及历史命运*
——兼及《刑法修正案(九)》的刑罚理念
张学永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体战训学院,北京100038)
死刑的发展历程是人类刑罚文明进化史的缩影。古今中外,死刑的变迁经历了从野蛮到文明、从恣意到规范的发展变化过程。无论是欧美、亚洲国家,还是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死刑的正当性都受到过强烈而有力的质疑。但死刑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及不断消逝的发展趋势表明,死刑的正当性得到了较为广泛的确认,同时因为死刑的残酷性其也正不断受到抑制和消解。我国历次刑法修正案不断缩减死刑罪名,《刑法修正案(九)》明确确立的终身监禁制度进一步压缩了死刑的适用空间。死刑的命运,将会经历一个不断缩减直至消亡的历史过程。
死刑;制度变迁;终身监禁;刑法修正案
死刑作为一种刑罚已经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时至今日,死刑问题仍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受到法律学者甚至其他领域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对于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来说,对死刑问题的研究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世界上第一部明确规定了死刑的法律是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1]。在世界各国法律发展的漫长历史中,死刑在刑罚体系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死刑仍然是很多国家刑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持续进步,也有很多国家已经完全废除了死刑,使得死刑成为历史的记忆与尘埃。对死刑的历史予以鸟瞰式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死刑,并为理性地探讨和预测死刑的未来走向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在进入刑罚理念日趋宽容、刑罚执行方式也越来越人道化的时代之后死刑的发展及其走势,以及死刑的未来命运。为了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死刑理论及实践,笔者在此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区域和国家,对其死刑问题加以简要的介绍和粗浅的评论,并关注我国的死刑立法和司法实践及死刑的历史命运。
一、欧美国家死刑问题的历史回眸
1.欧美刑事法律史上的死刑问题概览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死刑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发挥着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不管这种作用是否真实的存在或者是否能够得以充分的发挥,至少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死刑的作用和正当性并没有受到普遍的质疑。
而且,在欧美刑罚的发展史上,死刑的执行方式也曾经一样是血腥、残忍和非人道的,人的身体曾经被作为威慑与警戒的工具,被残酷地予以对待并加以展示。法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福柯在其不朽名著《规训与惩罚》中,对早期刑罚的残酷性有过细致的描述:在1757年的巴黎,一个罪犯被公开处死,该罪犯所犯下的罪行是谋杀君主。处死该罪犯的过程是公开的,并极尽残酷之能事。该罪犯在被处死的过程中,先是经历了被千刀万剐的凌迟,并被用油烧灼,死亡之后被分尸,并被焚烧,最后骨灰也被抛弃。而在80年后的巴黎某监狱,某囚犯的日程表被严格管理和规定。福柯通过对上述两种图景的对比指出,在1750—1820年间的欧洲以及美国,刑罚的理念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刑罚的目的从报应开始转向矫正和教育,而刑罚客体的重心也相应地从人的肉体转向人的精神和灵魂[2]。这种转变具有极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对于整个世界法律历史来说,显然也具有极为深远的划时代的意义,它对法律理论与法律实践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这种历史的转向不仅仅发生在法国和美国,也发生在世界七大洲上的其他各个国家,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些转折有早有晚、有长有短而已。详细探究蛮荒时代的死刑种类及其执行方式,是法律史学家的任务,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2.欧盟国家死刑的历史
众所周知,1764年贝卡利亚在其经典巨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对死刑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提出了有力的质疑,并明确提出应当废除死刑,自此死刑存废问题方才成为人们广为争议的问题。而在此之前,不仅是在欧洲,即使是在全世界,死刑存在的正当性也没有受到有力的质疑,一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现实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在贝卡利亚发出对死刑的质疑之后,人们开始对死刑存废问题倾注了更多的关注,但是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质疑的声音并未从根本上撼动死刑。直至1865年,欧洲才有两个国家全面废除了死刑,这两个国家一个是圣马力诺,一个是罗马尼亚。但是罗马尼亚又于1939年恢复了死刑。因此,在欧洲,第一个废除了所有犯罪死刑的国家是小小的山地共和国圣马力诺。并且,圣马力诺不仅在死刑废止问题上领欧洲之先,而且于1848年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这在世界上也是第一个。在二战前,荷兰于1870年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随后挪威、葡萄牙、瑞典、意大利、瑞士等国家也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冰岛于1928年开始全面废除死刑,但是二战前全面废除死刑的国家还是极少数,欧洲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全面废除死刑,而是仍然对部分特殊犯罪保留了死刑[1,3]。
在二战之前,死刑问题还只是各国国内法的问题,并未有国际公约或区域性公约对死刑问题作出统一性的规范或要求。二战之后,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和人权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死刑问题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国际法上的问题。二战结束后成立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纳粹头目,对罪恶累累的战争罪犯判处极刑,并在之后不久绞死了11名纳粹头目。在当时,对这些纳粹战犯处以极刑并没有任何争议。数十年后联合国安理会为处理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暴行,又建立了两个国际刑事法庭,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不同的是,这两个国际刑事法庭已经不允许判处死刑,而只能对相关责任人判处自由刑。这无疑和《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通过密切相关[4]。国际社会在限制死刑的适用方面,逐步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
二战之后,联合国在推动改进世界人权状况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在欧洲范围内,欧洲各国也为改进区域的人权状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在欧洲理事会的主持之下得以签署,并在1953年9月3日生效。该公约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区域性的国际人权公约,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公约明确保护人的生命权,但是并未表明其反对死刑的立场,而是认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死刑判决。而至1985年生效的《欧洲人权公约有关废除死刑的第六号议定书》明确表明了废除死刑的态度和立场,但是该议定书仍认可在战时或非常时期(紧急状态下)的某些特殊犯罪可以判处死刑。时间推进至2002年,《欧洲人权公约有关废除死刑的第十三号议定书》终于确立了全面废除死刑的立场,即无论在和平时期或者是战争时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判处和执行死刑。至今,欧盟国家不仅在欧盟区域内废除了死刑,而且将废除死刑作为其他国家加入欧盟的必要条件,除此之外,欧盟及其成员国家还为在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作出了积极的努力[3]。
3.美国的死刑状况
美国曾经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其文化与法律传统和英国非常接近,可以说受到了英国的深远影响。时至今日,英美法系仍然以其独特的判例法传统而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及司法体系具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和1998年完全废除了死刑的英国相比[3],美国对死刑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到目前为止,在限制和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的大背景下,美国仍然是保留了死刑并有死刑执行的国家之一。
美国(包括殖民时期)最早的关于死刑的史料记载,是1608年弗吉尼亚州的一位军官被发现是西班牙的间谍从而被执行了死刑。在美国的殖民地时期,各州都规定了名目繁多的死刑罪名[4]。自独立战争以后,美国各州于1787年建立起统一的联邦宪法,死刑仍然得以延续,并一直持续至今。虽然美国上下也曾经因为死刑问题产生了很多的争论,但美国最高法院仍然通过判例确认了死刑的合法性。关于美国死刑问题的演进和争论,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不得不提。一个是Furman v.Georgia,另一个是Gregg v.Georgia,即福尔曼诉佐治亚州案和格雷格诉佐治亚州案。美国的政治体制为联邦制,其法律体系也分为州法律和联邦法律,各州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和司法系统。而各州审理的案件中,只有极少数能够上诉到最高法院并经最高法院审理,因为最高法院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就涉及宪法解释问题的案件进行裁决[5]。而福尔曼案和格雷格案都是关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的重要案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福尔曼和格雷格都是幸运儿,其命运能够受到全美公众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关注。
在1972年的福尔曼诉佐治亚州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共合并了三个独立的死刑案件,其中两个被告来自佐治亚州,一个因为谋杀罪被判处死刑,一个因为强奸罪被判处死刑;另一个被告来自德克萨斯州,因为强奸罪被判处死刑。三个被告都是黑人,三人均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其上诉理由是死刑判决方式违反了美国联邦宪法。因为三个案件都关系到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三个案件合并审理[4]。
福尔曼诉佐治亚州案争议的焦点是死刑判决是否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八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①美国联邦宪法第八条修正案:“不得要求过多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重的罚金,不得施加残酷和非常的惩罚。”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中则规定了“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的内容。参见任东来等:《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572、574页。。美国最高联邦法院经审查后形成的法庭意见认为,福尔曼等三人的死刑判决违反了美国联邦宪法第八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该案适用死刑的法律违反了美国联邦宪法第八条修正案,死刑判决构成残酷的、异常的刑罚;死刑判决方式也违反了美国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违反了法律的正当程序,因此裁决撤销死刑判决,发回重审。该法庭意见是经联邦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根据多数原则由5∶4的比例作出的,即赞同法庭意见的大法官占多数,共5人,而持异议的大法官为少数,占4人[6-7]。
4位持异议的法官中,都是支持死刑并认为福尔曼等人的死刑判决没有违反法律和正当程序的。而在5位支持法庭意见的法官中,也并非都认为死刑本身存在正当性和适度性的疑问,其中只有布伦南(Brennan)大法官和马歇尔(Marshall)大法官否认死刑存在的正当性,认为死刑本身即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八条修正案②参见郑延谱:《美国死刑制度的新发展与对中国的启示》,载赵秉志、(加)威廉·夏巴斯主编:《死刑立法改革专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186-188页和邱兴隆主编:《比较刑法(第一卷):死刑专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447-454页。在该书中,邱兴隆将Brennan大法官的汉语名字翻译为“布里兰”,这只是由于对英文名字汉语译法选字的不同,基于类似的原因,邱教授将Furman翻译为“华曼”。。布伦南大法官在支持法庭意见的附议意见中,明确表达了其反对死刑的立场,认为:死刑是一种异常严厉的刑罚,它的适用有辱人类的尊严;当代社会对死刑的反对是绝对的,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并且,死刑还存在被滥用的极大的风险;另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死刑比监禁刑更能实现刑罚的目的。因此,死刑是违反美国宪法第八条修正案的残酷的、异常的刑罚。另外3位支持法庭意见的大法官则并不是因为反对死刑本身,而是认为福尔曼案的几名被告没有得到法律及正当程序的公平对待,或者认为死刑判决缺少明确的、可供严格适用的具有操作性的统一的标准,因而对该个案的判决结果表示反对。也就是说,如果被告得到了公平合理的对待,并经明确的严格统一的正当法律程序,死刑判决并非是不可接受的[8-9]。基于这样的原因,几年之后的格雷格案出现另一种结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时间推进到1976年,在福尔曼案发生短短4年之后,又一则关于死刑判决是否合宪的案例摆在了联邦最高法院的面前,它就是格雷格诉佐治亚州案。格雷格同样是由于犯谋杀罪而被佐治亚州最高法院判处死刑的,这和4年前的福尔曼案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是,格雷格却没有福尔曼等人的幸运,其死刑判决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以7∶2的比例维持了。也就是说,在9名大法官中,认为格雷格的死刑判决合宪的法官共有7名,而只有2名大法官认为格雷格的死刑判决违宪。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因为福尔曼之后美国各州都修订了自己的法律,将死刑罪名予以缩减,只对特别严重的罪行规定了死刑,死刑罪名得到了大幅度的减少;另一方面,各州还进一步严格规定了死刑案件的审理程序,使得死刑案件能够得到更为严格的公平对待,保障死刑适用的公平性与严谨性。因此,除了反对死刑本身正当性的布伦南大法官和马歇尔大法官,其他7名大法官都支持佐治亚州最高法院对格雷格的死刑判决[6]。通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述判例不难看出,虽然死刑问题在美国也曾经面临合宪性的争议,但是受到美国法律文化传统及社会公众民意的影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是毅然确立了死刑的合宪性。直到目前,面对全球限制和废除死刑的潮流,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存在死刑并有死刑执行的国家之一。只是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各州的死刑判决和死刑执行人数都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民意对死刑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支持死刑的人数比例减少,而反对死刑的人数比例有所上升,支持以不可假释的终身监禁代替死刑的人数有所增加[9]。
上述美国死刑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充分显示了死刑问题的复杂性,经济、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民意的影响都对死刑的发展和走势具有重要影响。虽然欧盟等废除了死刑的国家也尽力推动在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但是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仍然坚持保留死刑,一方面体现了大国的自信,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本国文化及民意的尊重。
二、亚洲部分国家的死刑状况
欧美发达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和文化传统,亚洲作为世界第一大洲拥有众多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地位,其各个国家的死刑状况也值得重视和研究。笔者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对其死刑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简要的介绍。
1.日韩死刑的发展近况
日本作为目前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以其很小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很高的经济效益,毫无疑问是一个经济强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很高的关注度。由于地理、历史的原因,日本文化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保留死刑的观念在其国民的思想深处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作为目前仍然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日本国内民众对死刑的存在保持了较高的支持率。二战之后的数次民意调查均显示,日本民众对死刑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1956、1967、1989年的3次民意调查均显示民众对死刑的支持率维持在大约70%的水平,而2005年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死刑的支持率上升到了81%的水平[10]!
基于民意对死刑的高支持率,日本官方对死刑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死刑在现阶段还不能废除而应当保留。日本刑法中共规定了12种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在1995年的刑法典修订中这些死刑得以保留。虽然二战后日本宪法有不得施加酷刑的明确规定,但是日本最高裁判所审查后认为,死刑判决并不违反宪法中关于禁止酷刑的规定。日本的立法机关认为,虽然限制和废除死刑是一种世界性的发展趋势,但是在日本,因为民众对死刑的支持,废除死刑还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2006年,日本的法务大臣也明确表态:没有废除死刑的计划[4]。
在最近,日本关于死刑问题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特征,其一是死刑执行数量比较少,其二是在死刑裁判中引入陪审员制度。尤其是后一个特征值得关注。可以说,日本裁判所将死刑判决权力的很大一部分交给民众去行使,无疑是将死刑的命运交给公众去裁判,既增加了判决的权威性和可接受性,也使得死刑判决能够更好地体现民意的要求。
韩国作为亚洲的一员,以其较强的经济实力也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相当广泛的关注度。韩国法律也保留了死刑,其中最严重的刑罚就是绞刑。和日本类似,影响韩国死刑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民意对死刑的支持。因为民意可以对立法者施加政治影响,所以韩国法律中一直保留了死刑。其立法机关认为,违背民意废除死刑将会削弱法律的权威,也会降低国民对法律的信任,同时还和民主制度的精神不相符。韩国司法机关的态度和立法机关的态度是相似的。韩国大法院认为,死刑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具有积极的价值,民众对死刑的支持显示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韩国宪法法院也认为,基于国民的法情感死刑是妥当的刑罚。韩国法务部的态度也比较明确,认为死刑存在是维护社会秩序和遏制犯罪的需要,同时还必须考虑国民的法情感与道德因素,综合来看死刑是合宪的和必要的[10]。
自1945年摆脱日本统治之后,韩国执行死刑的人数共为1 634人,其最后一次执行死刑是1997年12月执行了23名罪犯。从1997年12月最后一次执行死刑之后,韩国虽然在法律上仍然保留了死刑,但是至今没有再执行死刑。由于近15年没有执行过死刑,国际特赦组织将韩国分类为废除死刑的国家。在学术界,韩国目前也被认为是事实上已经废除了死刑的国家[1]。
日本和韩国都是中国的近邻,其文化传统都和中华文化渊源甚深,其法律文化及死刑制度的发展与走势,无疑对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具有良好的启迪意义。
2.我国死刑的历史沿革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死刑一直是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也最为重要的刑罚种类之一。尤其是在奴隶社会和漫长的封建时代,死刑成为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重要工具。
死刑和原始社会的血亲复仇和私人复仇具有很深的渊源。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以血缘关系维系在一起,部落成员被杀害或者伤害,就是整个部落被伤害和侮辱,因此,和被害人血缘关系比较亲近的人就会为部落内的被害人复仇,将施害者杀死或杀伤。随着社会的发展,氏族部落制度逐渐没落,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没有之前氏族部落时期那么紧密,随后血亲复仇也逐渐演变为私人复仇,由此造成了私刑的泛滥。国家产生以后,惩罚加害人的权力就从私人手中转移为国家的刑罚权。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曾说死刑是人类社会以血还血、同态复仇的习惯的延续和表现。恩格斯也说,法律上的死刑不过是原先人类社会野蛮复仇的文明形式[11]。
据《尚书·大禹谟》记载,在我国夏朝建立之前的大禹时代,曾经有“与其杀无辜,宁失不经”的理念,就是疑罪从轻、以免错杀无辜的思想。在当时,这样的思想无疑包含了非常先进的慎刑理念,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这样的理念在夏朝初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死刑可以赎免。但是在政权稳固之后,夏朝统治者开始重用死刑。商朝进一步扩大了死刑的范围。而周朝的统治者则厉行“德教”,信奉“明德慎刑”,并创设了死刑执行的等级制度,不同的死刑等级其严酷性也有所不同。后世各朝代的死刑也都各有特点,但都基本保持了死刑种类的多样性,也保留了死刑执行方式的严厉性和残酷性特征[12]。
在我国的文化和法律传统中,死刑不但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倚重和青睐,而且其执行方式也多种多样,曾经极尽残酷恐怖之能事。比如,西周时期的吕刑,仅仅有关死刑的条文就多达二百余条。秦律在我国法律史上也以严酷著称,其死刑包括戮、弃市、定杀、族、夷三族、腰斩、枭首、车裂、肢解、镬烹、凿颠、抽肋、具五刑等残酷的种类[11],不但及于犯罪者本人,而且祸及其亲属,甚至是很远的血亲也受株连。另外,古代死刑中还有焚杀、锯引、凌迟等惨无人道的执行方式[13],可谓残酷至极。
虽然隋唐时期由于封建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进步刑罚曾经趋于宽缓化,执行方式的严酷性也大大降低,但是这样的状况并没有在之后的朝代中得以延续,尤其是封建社会末期,由于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和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封建统治者也用残酷的刑罚加以镇压,死刑的种类和残酷性都有所反弹。直至鸦片战争以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清王朝迫于外国列强的压力,开始对法律体系及刑罚制度进行一定的改革,死刑罪名有所减少,死刑的执行方式也渐趋人道化。这一趋势延续到了之后的民国时期[12]。
虽然西方社会在18世纪就由于贝卡利亚对死刑的批判而开始了对死刑的反思与争论,但是在遥远的东方古国中国,当时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仍然非常倚重死刑的威慑力对统治者政权的保护作用,死刑也基本没有受到合理性的质疑。对死刑的反思和死刑存废的讨论,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不断快速发展才逐渐进入了刑法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在我国当前的刑法理论界,保留死刑和废除死刑的观点都有学者坚持,但整体而言还是保留死刑的意见占据了优势地位,这也是和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相适应的客观现实。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治化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文革时期法治状况有所倒退,但是总体而言,我国的法治化程度是越来越高的,体现在刑罚方面就是刑罚的严厉性不断降低,刑罚执行也更加人道化。具体到死刑方面,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司法机关基本坚持了少杀、慎杀的原则,对死刑案件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标准和要求。尤其是新刑法、新的刑事诉讼法颁布以后,关于死刑案件的实体、程序要求和控制都极为严格,只有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才考虑判处死刑,并且对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死刑罪犯适用了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为死刑犯继续存续生命保留了机会和希望。
2007年,最高法院统一收回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使得死刑案件的法律适用更加公平公正和统一,对下级法院死刑案件的判决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死刑案件的实体公正及程序公正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在此之前,由于省级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核准死刑,使得我国司法实践中判决死刑的案件总量较多,同时由于我国地域广袤、地区发展不均衡,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有很大的差异,导致全国各地适用死刑的标准也难以得到有效的统一。因此,死刑判决的公平公正性难以得到合理的保障,死刑案件的公信力常常受到公众的质疑,影响到司法机关判决的权威性,其负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这也导致刑事法律理论界一致呼吁,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除了从程序上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我国立法机关也在减少死刑的适用方面作出了很多积极的努力。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种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并且规定了一般不对已满75周岁的老人适用死刑(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总体而言,在目前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减少和限制死刑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在目前我国刑法学界主张废除死刑的观点也并不鲜见,有的甚至主张立即或者在不久的将来废除死刑。比如,著名刑法学者邱兴隆就是一名坚定的死刑废止论者,一直在为死刑的废止而四处呼吁[14]。不过总体而言,我国刑法学界对死刑问题的主流观点是在现阶段还不能废除死刑,现实而可行的选择是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经过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逐步过渡到废除死刑的阶段。
三、余论:我国死刑立法的最新发展及趋势
近些年来,我国刑法理论界呼吁废除死刑的声音不绝于耳,诸多专家为死刑的废除撰文发声,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最近两次的刑法修正也大幅度地缩减死刑罪名,并对死刑的适用标准作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这无疑体现了我国进一步宽缓化的刑罚改革趋势,顺应了世界范围内刑罚文明、刑罚人道主义的发展潮流。应当注意的是,我国《刑法修正案(九)》确立的终身监禁制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上述刑罚宽缓化的大背景下,这一制度的确立无疑严密了我国的刑罚体系,有利于更进一步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
对于终身监禁制度,有学者认为其实际上并非新的刑种,也非新的刑罚制度,而是适用于特定犯罪(贪污受贿犯罪)的刑罚裁量和执行措施。并且就刑罚的严厉性而言,终身监禁实质上要轻于死刑立即执行而重于死刑缓期执行[14]。但是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值得商榷。我国现有的刑罚体系中死刑无疑是最为严厉的刑罚,而死刑之外的刑罚中最为严厉的刑罚即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实际上是无期徒刑的一种执行方式,在没有减刑、假释的情况下,对无期徒刑的受刑人实施终身监禁应是其题中应有之意,因此,很难说终身监禁的刑罚重于死刑缓期执行。当然,由于刑罚执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受刑人有重大立功表现等原因,可能存在死刑缓期执行和终身监禁减为有期徒刑的情况,但是不能因此认为终身监禁的刑罚重于死刑缓期执行。不过,终身监禁制度无疑进一步压缩了死刑的适用空间。
最近两次刑法修正案除了大幅度地减少死刑罪名以外,刑罚的执行方式也进一步人道化和宽缓化。《刑法修正案(九)》对于死刑缓期执行制度进行了相应的修改,无疑使得我国刑罚的严厉性进一步降低。根据《刑法修正案(九)》,死刑缓期执行考验期间内,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才会启动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的程序,对于死刑缓期执行考验期内未达到情节恶劣程度的故意犯罪,只是重新计算死刑缓期执行的考验期限,并不导致执行死刑的后果。同时,也有学者呼吁,我国死刑立法应进一步缩减死刑罪名、完善死刑适用标准,并给予老年人、哺乳期妇女、精神病人和聋哑人等特殊主体以人性关怀,改进和建立上述特殊群体的免死制度[16]。
总体来看,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个维度上,我国死刑制度的改革一直在路上。虽然充满争议,但是由于刑罚人道化是世界刑事法治史上的一个发展趋势,我国也顺应了刑罚宽缓化的潮流,刑罚及其执行制度变得更为严密、合理、轻缓、人道。我国死刑的命运也必将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在不断缩减的道路上走向逐渐消亡。
[1]王水明,邵文文.国际刑法中的死刑限制与废止问题研究[M]//赵秉志,威廉·夏巴斯.死刑立法改革专题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31.
[2]朱苏力.福柯的刑罚史研究及对法学的贡献[J].比较法研究,1993(2):23-27.
[3]何荣功.欧盟代表性国家死刑废止道路研究[M]//赵秉志,威廉·夏巴斯.死刑立法改革专题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69-70.
[4]威廉·夏巴斯.联合国与死刑废止[M]//赵秉志,威廉·夏巴斯.死刑立法改革专题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3-9.
[5]郑延谱.美国死刑制度的新发展与对中国的启示[M]//赵秉志,威廉·夏巴斯.死刑立法改革专题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179.
[6]任东来.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6.
[7]邱兴隆.比较刑法:第1卷(死刑专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444-463.
[8]虞平.死刑适用的统一性与量刑个别化的冲突[M]//杰罗姆·柯恩,赵秉志.死刑司法控制论及其替代措施.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389-390.
[9]Richard C.美国对死刑问题的观念转变[M]//杰罗姆·柯恩,赵秉志.死刑司法控制论及其替代措施.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367-387.
[10]周国良.死刑存废中的民意与国家决策之关系[M]//赵秉志,威廉·夏巴斯.死刑立法改革专题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153-154.
[11]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下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27-128.
[12]马松建.死刑司法控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0.
[13]王觐.中华刑法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467.
[14]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24.
[15]黄京平.终身监禁的法律定位与司法适用[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66-69.
[16]赵秉志.中国死刑改革立法新思考: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主要视角[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1):5-20.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historical destiny of death penalty:and on concept of penalty of Crim inal Law Amendment(Nine)
ZHANG Xue-yong
(School of Polic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38,China)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death penalty is the m iniature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penalty civilization.At all times and in all countries,the evolution of death penalty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and arbitrariness to normal.Whether in European countries,in American countries,in other Asian countries,or in China as an ancient civilization,the legitimacy of death penalty has been challenged strongly and powerfully.But the evolving trend of the w ide existence and incremental diminishing of death penalty all over the world shows that the legitimacy of death penalty has been w idely accepted,and is being refrained and eliminated because of the cruel nature of death penalty.The charge of death penalty is continuously reduced by previous criminal law amendments in China.The application space is further compress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system of life imprisonment in Criminal Law Amendment(Nine).The fate of death penalty w ill go through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shrinking and disappearing.
death penalty;institutional evolution;life imprisonment;criminal law amendment
D 914
:A
:1674-0823(2017)04-0289-07
10.7688/j.issn.1674-0823.2017.04.01
(责任编辑:吉海涛)
2016-11-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820049);中央基本科研经费项目(2016JKF02202)。
张学永(1981-),男,河南开封人,讲师,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刑法学、公安执法、法律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
*本文已于2017-03-30 14∶31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 20170330.1431.018.htm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