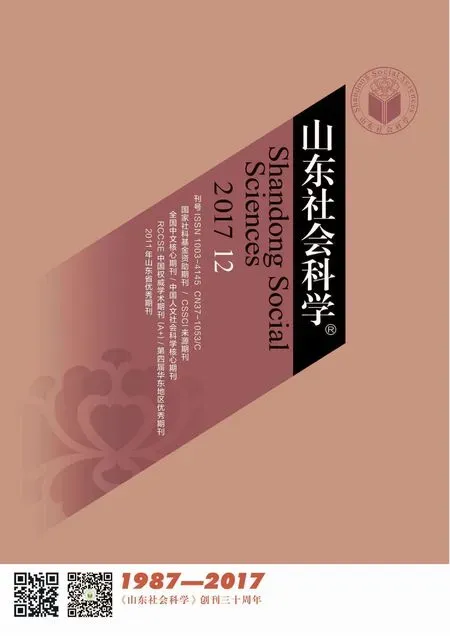唯美、尚情、娱玩
——论齐梁文艺三位一体诉求美学属性
纪 燕
唯美、尚情、娱玩
——论齐梁文艺三位一体诉求美学属性
纪 燕
(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山东济南 250101)
对于向来颇受靡丽、藻饰等指责的齐梁文艺,如果我们从齐之萧子显、梁之萧统、萧纲三兄弟倡导的以变求新的重声律对偶、尚娱耳玩目和吟咏情性的文艺观念入手,结合当时对新变体诗赋作品的创作,就能发现这种集唯美、尚情、娱玩三位一体的审美诉求,实际上是一种吸取先哲、前贤思想中的声、色、味美学思想资源而内化而成的人性化审美欲望观念,在诗赋艺术创作上成为自魏、晋、宋以来一个重要的殿后阶段,应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齐梁文艺;唯美、尚情、娱玩;声律对偶;吟咏情性
在文学史和艺术史上,关于南朝齐梁①齐梁时期是指南朝齐朝、梁朝,都是由萧姓创立的,两个朝代存留的时间都很短,加起来统共78年,但却形成诗歌发展的新诗风,即“齐梁体”,其对隋唐及随后的中国传统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时期文艺成就的评判可谓是有喜有忧。在那个动荡凌乱、门阀士族观念异常浓重的年代,有着“布衣素族”之称的萧氏一族却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文艺王朝,形成了不同于别时的文学样式和艺术风貌。与此同时,由于皇帝酷喜文学,大力施行振兴儒学、繁荣文学、促进史学等举措,大批皇室成员涌入文艺领域,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学集团,“江左三百年的文物之盛达到顶峰”②龚斌:《论齐梁萧氏文艺的美学品格》,《琼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此时的诗歌创作以风华流丽的语言、工稳精巧的对仗、信手拈来的用典隶事引领着后世隋唐文化的繁荣。但不可否认的是,齐梁时期的诗歌多为争胜、斗艳等目的而创作的作品,由于生活方式和人生格局的限制,创作者多视野局限,诗歌题材单调狭窄、内容空洞,过分强调藻饰而湮没诗人个性③袁行霈、罗宗强主编:《中国文学史》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页。,被认为“是市井浮华风气同宫廷奢侈享乐的生活汇合的产物,是市井流行歌曲在宫廷中恶性发展的结果”④商伟:《论宫体诗》,《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待齐梁文艺的态度和看法,存在巨大差异和鸿沟,那么,究竟该如何去看待齐梁时期的文艺呢?怎样给予齐梁文艺客观公正的评价?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一书中曾这样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的最后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⑤[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9页。对于齐梁文艺的认识和评判也应遵循这一思路。
一、齐梁审美风尚转变:唯美、尚情、娱玩的美学新追求
魏晋六朝是文学艺术自觉的时代。这种自觉首先是人性的自觉和追求个性价值,究其原因,玄学的兴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宗白华先生引用了《世说新语》中的《雅量》《识鉴》《品藻》《容止》等多篇故事记载,得出这样一个认识——这些篇章都是鉴赏和形容“人格个性之美”⑥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载《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的,认为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⑦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载《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0页。之美学,而这种鉴赏“人格个性之美”的风尚“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⑧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载《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3页。。它“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①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载《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卷第十·缪称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3页。。闻一多先生说,魏晋之间庄子变得声势浩大起来,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成为“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②闻一多:《古典新义·庄子》,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79页。 杨天宇:《礼记译注·乐记第十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页。,“三日不读《老》《庄》,则舌本间强”③闻一多:《古典新义·庄子》,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80页。 [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而作为中国传统文艺主流的山水诗、山水画,亦如徐复观先生所说,“乃是玄学中的庄学的产物”④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141页。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序》,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页。,它们崇尚和追求的是与天地合一的快乐。
然而,进入齐梁时期,审美风尚突然发生变化和转向,开始了对唯美、尚情、娱玩的文艺美追求。这种新追求集中体现在几乎是同时期的齐萧子显(485—537)所撰的《南齐书·文学传论》、梁萧统(501—531)所著的《文选序》及其弟萧纲(503—551)所写的《与湘东王书》等能够充分代表和体现时代文艺纲领的名篇里。齐萧是史学世家,梁萧是诗、文、书法世家,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爱好文艺,加之都是王室成员,正如上文所提及的,萧氏王族引领着齐梁时期文人、学士的文艺追求与创作倾向,他们的著作和文章则具有引导和标帜性。
萧子显由齐入梁,受到梁武帝萧衍和简文帝萧纲的信赖和倚重,担任过国子祭酒等职。《南齐书》是他在梁时撰写的,其中《文学传论》一文代表他的基本文艺观。他给“文章”即广义的文学所下定义是:“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⑤[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7页。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序》,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页。,认为“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⑥[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7页。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序》,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页。,“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⑦[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7页。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页。。他在例举出各个名家的不同体制之作后,特别指出“五言之制,独秀众品”,还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⑧[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8页。这种主张变革的文学史观,不仅显现出他的史学家眼光,更是时代的心声。定情性为风标,律吕是神明,这是在谈论诗赋的艺术本性;主新变则是强调文学要随时代而变。萧子显十分好学,文采非凡,他的《鸿序赋》曾得到过沈约“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⑨[唐]姚思廉:《梁书·卷三十五·列传第二十九·萧子恪》,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11页。的极高评价,后者是四声论的发明人。而齐梁时期的诗中新变——讲求韵律的永明体,就是谢眺、任昉、沈约、萧衍等“竟陵八友”的诗作,因此会反映在萧子显的文学定义之中。至于“情性”则是个古老的话题。屈骚云“发愤以抒情”⑩[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九章第四·惜诵》,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6页。,《淮南子》说“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外者也”①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载《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卷第十·缪称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3页。,《乐记》则称“情动于中,故形于声”②闻一多:《古典新义·庄子》,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79页。 杨天宇:《礼记译注·乐记第十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页。,《毛诗序》则说“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变风发乎情”③闻一多:《古典新义·庄子》,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80页。 [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等,西晋时期的陆机在其《文赋》中区分出十种文体,唯“诗缘情而绮靡”,专门突出和强调“情”才是诗之质。萧子显讲“情性之风标”,将“情性”视作诗赋艺术的外在标识,并且与律吕、声韵相配,是心灵的自然流露。这样一来,不仅突出了文学的要义,而且强调其是与音韵不可分离的,显示出萧子显对文学的新认识和新高度,也是对新体诗与赋的新总结和新要求。
萧统在《文选序》中第一次阐明和区分诗赋的艺术性质与经、史、子、集诸种文体的不同,在这部由他召集和组织文人编选而成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中,所选、所辑的皆为这种性质的诗赋文章,故而他提出著名的命题:“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④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141页。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序》,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页。方算是艺术诗文。他从源头上考察诗文的本源及其演变,诗骚传统久远:“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⑤[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7页。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序》,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页。;骚之吟咏而演而赋,“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⑥[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7页。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序》,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页。(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则称:“赋者古诗之流也”⑦[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7页。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页。),此皆“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诗赋亦“随时变改”①[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序》,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页。。这种增华、变改缘自历史,因此新的诗赋必然出于“沉思”即艺术构思,必然表现为丰富的“翰藻”即辞采之美。这些观点与萧子显不谋而合,都是齐梁之音。但他在讲述诗、骚演变为不同文体和四言、五言或三言、九言多种形式时,强调指出它们就如陶匏类乐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之织物“俱为悦目之玩”②[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序》,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页。。这里谈到的耳娱、目玩相当于今天的审美感性愉悦,与增华、变厉和翰藻等概念是一致的,是齐梁时期的文人特别突出的一种诗赋艺术审美功能观,与萧子显的文学观相比又多了一层含义,即“娱玩”也就是诗赋文学的娱乐功能。
简文帝萧纲的《与湘东王书》是写给其弟湘东王(后为梁元帝)萧绎的,主要是讨论当时京师文体的优劣得失,着重批评的是裴子野(467—528)在其《雕虫论并序》中表现出来的好古宗经而诋毁藻绘文学为雕虫之作的言论,实际上也是在维护乃兄萧统的踵事增华观。在信中,萧纲针对某些“儒钝”之作“既殊比兴、正背风骚”的情况,不无讽刺地说“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礼记》篇名——笔者注)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尚书·周书》篇名——笔者注)之作”③[唐]姚思廉:《梁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四十三·文学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0页。,由此可见,《与湘东王书》与《文选序》持同一论调。所以,萧纲认为裴子野虽然是“良史之才”,但他的文章却“了无篇什之美”,“质不宜慕”,同时还认为德才兼具之辈不应“瞻郑邦而知退”,“望闽乡而叹息”。④[唐]姚思廉:《梁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四十三·文学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1页。书中还讲到“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听”,阳春高妙之作尤应“精讨锱铢”⑤[唐]姚思廉:《梁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四十三·文学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1页。,讲究声律和辞藻,推崇“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乃“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⑥[唐]姚思廉:《梁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四十三·文学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1页。,一褒一贬,审美倾向极为明确。因此,《与湘东王书》可以说是与《文选序》相配合的又一文艺宣言书。而萧纲在其《答张缵谢示集书》一文中,甚至斥责扬雄视赋为“雕虫篆刻”而壮夫不为的言论其实就是“小言破道”(小言即不合大道的言论);而“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⑦[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十八·杂文部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67年版,第1042页。。他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一文中诫示儿子:“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⑧[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二十五·人部九·嘲戏》,上海古籍出版社1967年版,第455页。。在萧纲看来,文章立身之道的根本就在“放荡”二字,进一步阐释说就是不拘于礼义、典诰而能自由地想象与驱遣文辞。这一论点很有庄子逍遥游的意味,尽管萧纲着重的是藻绘诗文,而非庄骚式的浪漫文学。
二、齐梁新变体诗应和唯美、尚情、娱玩三位一体的审美新诉求
齐梁新变体诗是在传统诗文对偶和发明四声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萧子显、萧纲以及稍晚的萧绎(508—554)在《金楼子·立言篇》中辨析文、笔之别这些文艺思想与主张,不仅仅是对时文的总结和肯定,也是与实际创作者的对话、交流和互动,如果要考核其准确与否以及是非得失,应当结合新变体诗的实际来观察和衡量。
新变体诗是从“竟陵八友”所创的“永明体”开始的,以后还有“吴均体”⑨吴均体指的是南朝梁文学家吴均的诗歌特点,古称“清拔有古气”,即诗歌清峻挺拔有风骨,用典恰当且语言清新隽逸、美感十足。和“宫体”,进而演变成一股潮流和风尚。“竟陵八友”中文学成就最高的当属小谢——谢眺(464—499),沈约(441—513)次之,而任昉(460—508)等人则稍逊。“小谢”(谢眺)可谓是“大谢”(谢灵运)山水诗创制后之殿军,小谢对山水诗与新变体诗都极为擅长,尤其是后者,现存大约有40首,已初具五言律诗的雏形。小谢的五绝诗也具有发蒙性的特点。现分别各举一例以明之。
其五言律诗如《离夜》:“玉绳隐高树,斜汉耿层台。离堂华烛尽,别幌清琴哀。翻潮尚知恨,客思眇难裁。山川不可尽,况朶故人杯。”这四联中除“高”“知”二字应仄而平外,其余每联都是合律的。对偶情况也是除了末联未工之外,其余每联都有字对、声对、意对之妙。
其五绝诗如《同王主簿有所思》:“佳期期未归,望望下鸣机,徘徊东陌上,月出行人稀。”虽然联句未粘,但是语精意约,已经十分接近后来唐代诗歌的意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他对沈约、周颙等人在永明年间萧子良于京城考文、审音时发明并提出的“四声”“八病”之说尚未深知有关。
沈约作《伤谢眺》称赞他“吏部信才杰,文峰振奇响。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但转又悲悼“岂言陵霜质,忽随人事往。尺璧示何冤,一旦同丘壤”①袁世硕主编:《古代文学作品选》(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这首伤悼诗写于499年,谢眺遭他人诬告而冤死狱中,时年仅三十六。谢眺生前曾与沈约同朝为官,二人感情甚笃,沈约亦是非常推崇谢眺的文才,称赞谢眺的五言诗为“二百年来无此诗也”②[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26页。。沈约自己作《早发定山》《别范安成》等五言诗,也是韵律极为协调、对偶自然多样。其五言诗《别范安成》中的“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被称为唐代王维名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之蓝本,足见其影响力和历史意义了。到梁陈时期,庾信所作的《拟咏怀》《哀江南赋》等五言诗和《寄王琳》《和侃法师》等五言绝句,其声律、对仗更趋工整,合辙押韵,已然是唐代律绝的前身,被杜甫誉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自不待言。
至于七言体,从魏晋与乐府演化至齐梁成为新变体诗形成,萧子显和萧纲、萧绎兄弟分别作有几十首,其与王均、费昶等所写同名《行路难》,虽然每韵句数整齐也注重韵转,但在声律方面却参差杂乱,尚未步入韵律轨道。直到陈代的徐陵、江总、傅縡所作同名《杂曲》,七言长体才算是比较讲究韵律,开启了唐人七古体式,在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如果说,五言五绝与七言新变体诗是由于诗、乐、舞三位一体,注重吟咏传统而讲求声律音乐之美的,那么虽然同为语言艺术的赋体,由于其语言构成的长短句形式和注重语辞艳丽的特点,在齐梁时期更为突出的是语言工整的偶对形式美,声律则是从属和寓于偶对中的。以沈约《丽人赋》为例,他在赋中这样描写美人来时的情态景象:
响罗衣而不进,隐明灯而未前。中步檐而一息,顺长廊而回归。池翻荷而纳影,风动竹而吹衣。薄暮延伫,宵分乃至。出暗入光,含羞隐媚。
无论是上下两句句对中的事对、声对、反对,还是单句中的字对如罗衣、明灯,步檐、长廊,翻荷、动竹,薄暮、宵分,暗与光,羞与媚等,都有娱耳、悦目的美感和动人之效。其他的如江淹的《恨赋》《别赋》长篇,萧纲和萧绎齐名的《采莲赋》、萧纲的《筝赋》、萧绎的《荡妇秋思赋》等短章,虽然运用的偶对不尽相同也不尽如意,但是《荡妇秋思赋》中有“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秋风起兮秋叶飞,春花落兮春日晖”等这样活泼可爱的联绵对,多少显示其语言修辞的创新特点与功夫。所以,这些被《文选》收入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作品,的确如萧统所说,能够有着娱耳、悦目的审美效果。如果对它们进行有声的吟咏,《荡妇秋思赋》中的秋月相思之情、《丽人赋》里飘荡的情思,都是可以感受和体味到的!
这里必须还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诗赋文艺究竟是什么性质?它是像《诗大序》说的“发乎情、止乎礼义”,还是如陆机在其《文赋》中所讲的“诗缘情而绮靡”?亦或如萧家兄弟所说吟咏情性在娱耳、悦目、怡情?综合以上的观点和看法,其实是在反复讨论诗赋文艺到底是审美艺术还是道德之骥尾?这个已经争论了上千年的问题,到今天我们才弄清答案:即它是前者而非后者。但是令我们不得不赞叹的是,六朝时期的齐梁诗文家其实早在公元五六世纪就已经帮我们找到了答案并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所以我们也不必在此多费唇舌去评述言志、缘情或情志兼备等论说的孰是孰非了。在这里,需要强调的只有一点,作为语言艺术的诗赋,它主要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吟诵或歌唱的。既然是要吟诵或者唱出来,那么势必就要讲求语言的音韵美、文辞的对偶美了,唯有如此,才会让人易记、易诵,同时又有美的享受。
三、唯美、尚情、娱玩三位一体文艺美学观的深层阐述
通过上文所作的极为简略的互动式对比,已经基本可以看出齐梁诗文家们共同的审美爱好与倾向了,即唯美、娱玩、尚情三位一体诗赋艺术观。但我们还有疑问的是,齐梁诗赋文艺已经和慷慨多气的建安文学,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诗文,还有崇尚自然、任性而作的陶、谢田园山水诗赋等分道扬镳了,那么魏晋的旷达风度、人性与文学的自觉、《世说新语》中所推崇的“宁作我”“正是我辈”“要作金石声”等都消失殆尽了吗?它们(暂且不论北朝文学)还属于统一的魏晋六朝文学组成部分吗?而那些生活在齐梁时期的学者,除了裴子野之外,刘勰、钟嵘对新变体诗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和“词不贵奇,竞须新事……浸以成俗”(《诗品序》)的批评,以及唐人陈子昂指责其“兴寄都绝”(《修竹篇序》),韩愈斥责它们是“蝉噪”(《荐士》诗)等等,这些观点又怎么去看待呢?仔细推究,其实不难发现,以上所提出的问题虽多,但总体而言,齐梁诗赋家自己已经作出了回答,具体来说,还需要进一步辨明以下三点。
第一,关于新变体诗赋艺术整体统属性问题。众所周知,魏晋六朝诗赋作为一个整体时代的文艺,它既相对于两汉文艺,也区别于后来的隋唐文艺,是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刘勰所说的“通变”史观,继承、革新是关键,整个魏晋六朝诗赋对两汉诗赋是有因有革的。它自身从建安文学开始就已经在承继中拓新出一种风格之变;至晋宋山水、田园诗赋创作又是一次从题材到审美趣味的新变;再就是齐梁时期的永明声律与句式、语词对偶的形式之变。萧统之“踵事、增华说”、萧子显的“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说等,是在自觉求新、求变。沈约在《答陆厥书》一文中,对于自己发明和提出的“四声”问题,谈及清宫商、清浊虽然古已有之,然“灵均以来,未经用之于怀抱”①[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0页。 [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六·历书第四》,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9页。,乃至才有扬雄“雕虫篆刻,壮夫不为”②[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0页。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之论,其实“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③[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0页。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这才说它为“此秘未睹者也”④[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98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十年》,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20页。。这也进一步说明,他们于诗赋声律是自觉认识并有意运用的。魏晋六朝人对文学的自觉,在齐梁诗赋文艺中侧重的则是通变与声律的有意运用,而“宁作我”“要作金石声”的个性人格仍是突出的,只是着眼点各有不同而已。
第二,关于刘勰、钟嵘及隋唐人对齐梁文学的批评,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公平之处。陈子昂评价齐梁诗“采丽竞繁”“魏晋风骨,晋宋莫传”“兴寄都绝”⑤[唐]陈子昂:《陈子昂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页。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十一·告子章句上》,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1页。,而韩愈在其《荐士》一诗中则认为“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⑥[唐]韩愈:《韩愈集》,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297页。。这些观点秉公持正地看,多少都有点对诗文艺术的传统儒家文道观的偏见在里面。诗赋是审美艺术,这是它的本质特点,它可以寓道存寄托,但并不是说这就是诗赋的必然与唯一要求。更何况孔子也曾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⑦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五年》,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06页。,因此诗赋讲究审美、声律与文采才是其本质要求;而载道和有兴寄只是部分文学的表现方式和途径,并不能囊括全部。至于韩愈认为文一流、诗二流,其宣扬的“文以载道”说到了晚年则发生转向,大谈“不平则鸣”⑧[唐]韩愈:《韩愈集》,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02页。,倡导怪奇主义,嘲笑齐梁诗赋如蝉噪是在前期。相较于“诗圣”杜甫所谈到的“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⑨[唐]杜甫:《杜甫集》,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和“作者皆殊列”“历代各清规”(《偶题》)⑩[唐]杜甫:《杜甫集》,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25页。等观点,实事求是地讲,韩愈无论是在气度上,还是在观念认知的水平上,实在都是无法与杜甫相提并论的。
第三,值得真正关注与追问的是,齐梁诗赋家的唯美、尚情、娱玩三位一体文艺美学观的性质,以及是否有哲理来源,或者说是否隐含了什么哲学意味。众所周知,古代的五行学说中已经派生出五声、五色、五味的概念。《史记·历书第四》载“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①[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0页。 [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六·历书第四》,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9页。。《尚书·洪范篇》将水、火、木、金、土确立为五行,并进一步论述其有咸、苦、酸、辛、甘五味。②[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0页。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益稷篇》中记载了帝舜告诉大禹说“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③[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0页。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则说先王“济五味、和五声”④[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98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十年》,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20页。。后来关于五味、五色、五声的阐述更是多不胜数,它们与耳、目、口、鼻、肤五官对应,成为中国古代的重要审美范畴。而《孟子·告子章句上》中则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⑤[唐]陈子昂:《陈子昂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页。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十一·告子章句上》,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1页。,这是从人性论角度对欲望的功能、特点所作出的最具概括性和明确性的审美感觉论,对各种形式的感性艺术的创作和发展都具有引导价值和启示作用。
至于偶对与声律的来源问题,无论是《老子》中的“有无相生”“音声相和”“美恶相依”“大巧若拙”,《庄子》中的“得意忘言”、天地并生,生死相依,或者《易传》中的阴阳刚柔之道、变通之术、言不尽意之辨,还是五声说等,都含有偶对、宫商元素。正如沈约所说,自古的辞赋作家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区别在于宫羽相变、低昂互节、前有浮声、后须切响②[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六十七·列传二十七·谢灵运》,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79页。这种音律偶对,前人“所昧实多”,直至近代才由颜(指的是颜延之)、谢(指的是谢灵运)等人自由运用③[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六十七·列传二十七·谢灵运》,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78页。,而由自己将此秘揭示出来。④[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陆厥》,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98页。
关于诗歌的吟情咏性问题,情况也相似。诗、骚及《毛诗》《乐记》等早有先声与申述,西晋时期的陆机将其突出为“诗缘情而绮靡”而与铭、箴、颂等文体区别开来。齐梁人对此并无新说法,只是强调诗赋艺术就是吟咏情性的艺术,应在写作中实施它们而已。此外,我们还要提及的是,在《文选序》中萧统虽然引用《毛诗序》中的“六义说”和“诗者志之所之”与情动形言说⑤[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序》,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页。,但谢眺、沈约等发轫的新变体诗赋之作,可以说山水风情、闺情秋思、丽人艳情、筝笙乐情无不吟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本来就有七情六欲,那么物动心摇,何情不可抒发?毛诗强调要情动止乎礼义,而这种强加的儒家纲常紧箍,扼杀了多少真情的自由流露!情不可滥,亦不能恶,闺情、艳情都属于人的情愫,为何就违背礼义而不可咏诵?今天的我们对于情感随时随地都可表达,为何古人就无资格去自由咏情?
四、结语
综合上述可见,萧统兄弟及其同好诗赋家虽然并没有明标所本为何,也无明确的标帜性理论命题,然而这种多元取义而生发出的唯美、尚情、娱玩三位一体文艺观,其实便是承续先哲、前贤们关于人性审美功能欲望观念而提升出来的人性化审美欲望论表现。这种理论观念贯穿于那个时代的诗赋艺术创作中,有别于慷慨多气的建安文学,顺乎自然、任性而发的竹林七贤之作和质性自然、钟情山水的晋宋田园、山水诗赋、画作,独树一帜,成为新的风尚,其实就是齐梁文艺的美学个性之所在。
I01
A
1003-4145[2017]12-0074-05
2017-09-10
纪 燕(1982—),女,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艺术学。
(责任编辑:陆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