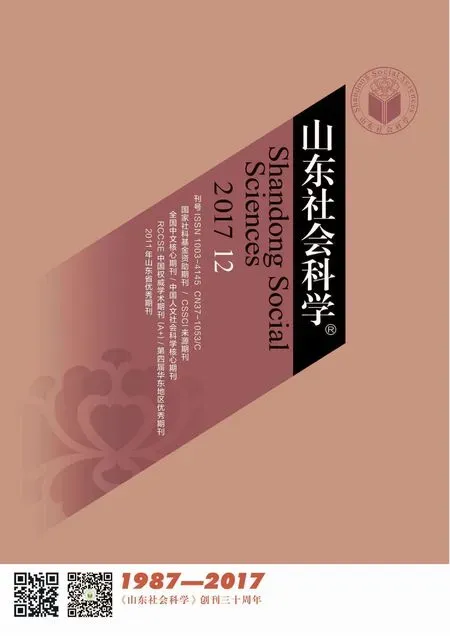医患沟通与话语竞合:新媒体环境下医患关系的话语沟通
吴洪斌
医患沟通与话语竞合:新媒体环境下医患关系的话语沟通
吴洪斌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转型期的中国医患冲突事件频发,如何缓解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已成为当前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命题。借助话语理论分析医患沟通中竞争合作的微妙关系,既能申明传统媒体时代医患沟通的“话语失衡”问题,又能阐释新媒体语境下患者如何从“沉默的大多数”自我话语赋权变成“有声的权利维护者”,进而打破了既有的医患沟通的话语权力格局,使得医患双方的“话语博弈”面相日渐凸显。化解不断激化的医患矛盾,需要医方改善话语态度、患方保持话语理性,更需要医患双方从话语竞争关系复归话语合作关系,构建齐心协力攻克病患的“利益共同体”。
医患沟通;医疗改革;话语赋权;话语竞合
倘若关注近年来的社会舆情,就会发现涉及医患矛盾的热点事件频频发生,呈现一种愈演愈烈的态势:诸如“缝肛门”“八毛门”“肾失踪事件”等层出不穷,而“医院CPU病房内烧纸”“医生被逼下跪事件”“医生被捅事件”也不断出现,医患沟通俨然已经成为网络舆论场中一个无法回避的显要话题。回顾历史,前网络时代的医患关系似乎并没有当下这种水火不容的态势。从前网络时代到网络新媒体时代,医患沟通方式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文拟将医患沟通放到媒体演进的大的历史语境中,以话语理论深度解读日益激化的医患矛盾。话语“不仅是交际的工具,而且是控制的工具”,构建、维持或瓦解社会中的权力关系,“话语分析关心的不仅是某个言说的复合语句,而且更常考虑的是两个或更多言说者的交替互动,以及用来操持和控制特定语境中之话语的语言规则与社会权力”①[美]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本文从前网络时代的医患“话语失衡”到新媒体时代的医患“话语博弈”入手,分析医生与患者双方在媒体演进中的话语权力格局的变迁,提出改善医患矛盾的对策和建议,即以医患“话语竞合”搭建良性互动的医患沟通机制。
一、话语失衡:前网络时代医方主导下的医患沟通
探讨新媒体影响下医患矛盾的沟通问题,需要首先了解在互联网普及之前的医患沟通方式。其实,检视前网络时代的医患沟通我们会发现,医患矛盾其实是一直存在的,不但存在着知识的不对称,而且存在着话语的不均衡。只是因为前网络时代公众缺少接近使用媒体的权利,患方还无力与医方话语进行博弈。
(一)医患双方的知识不对称
在疾病诊疗过程中,需要医患双方的沟通。所谓医患沟通,简而言之便是医方与患方之间关于疾病诊疗问题的话语沟通。正如西方一位医学者所指出的:“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②王克春:《卫生事业本体之道》,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页。。但必须清楚的是,医生(医师)和患者(病员)这两类医学行动的当事人群体在医学知识方面有着重大的差距。所谓“医生”是掌握医药卫生知识,从事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的专业人员,需要有着非常高的专业技术条件,从业者需要经过较高的专业训练水平(一般是医学专业本科五年,医学专业硕士三年,医学专业博士三年)之后才能入门,其后又要经过漫长的临床实践积累过程,才能成为技术精湛的专业医生。所谓“患者”是指患有疾病、忍受疾病痛苦的人,是指等候接受内外科医师的治疗与照料的病人。与医生相对,患病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情况,每个人随时都可能需要使用医疗服务,但普通患者一般对医疗健康知识知之甚少。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就像是“一只迷路的羔羊”,到底患的是什么病,需要怎样的治疗,患者并没有充分的医学专业知识供自己诊断。客观来说,医患之间的知识差距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患者寻医问病的题中之义。而在医疗诊断中,医生体现在其拥有专业的医学知识和医学技能,能帮助患者去除身体的病痛,而患者之所以寻求医生帮助,就是因为自身不具备这种诊断治疗的专业技能。这可以说是医患关系的一个固有特征,但这也决定了医患之间的话语沟通必然是一个充满潜在冲突的问题。
(二)医患沟通中的话语不均衡
医方与患方在诊断病情或治疗疾病时需要进行话语的交流与沟通,但不可回避的是医患沟通一直以来便存在着话语权失衡的问题。在医患沟通中,一般可分为医生话语和患者话语。历史地看,医生自古以来便占据着医患沟通的话语主导权。“话语权”一般指享有的发表意见的权利,而“话语主导权”则意味着某些人在某些方面具有发言的权威性。即如本文所讨论的医患沟通,医生便在医疗卫生知识方面具有发言的权威性。而普通医患者在医患沟通中因缺乏相关知识,不能做出病情判断和反思性认知,从而在医患对话中缺少主导权,在面对医生时,也只能听从医生的分析甚或摆布。在就诊之时,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对话,一般围绕着“病情陈述”“病史询问”“身体检查”“病情诊断”“治疗建议”等步骤进行,但这种医患之间的对话看似是对话,但始终是以医生为主导的。例如医生需要向患者询问病情,而患者面对医生问询需要陈述自己的病情、病史,进而医生根据患者陈述做出病情诊断,并且根据医疗知识做出治疗方案。医生对患者往往采用一种命令式的语气,诸如“张开嘴巴”“伸出舌头”“好了,外面等”等指令性话语。在医患对话中,询问病人是医生诊断病情的依据,而诸如“不要讲了,听我说”之类的打断对话则是医生行使话语权力的工具。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言:“语言具有直接的断定性:否定、怀疑、可能性、终止判断等需要一些特殊的机制,这些机制本身将参与各种语言伪装的作用。”由此可见,医生在医患对话中其话语权势地位明显,而且权势便隐藏于医患双方的对话结构之中,“话一旦说出来了,即使它只在主体内心深处发出,语言也要为权势服务。”①[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页。根据话语理论,话语发出者旨在对他人施加影响、产生效果,由此医疗话语的基本目的决定了医患对话的权力结构。由此可见,在医患互动中,医生与患者之间因为专业知识有着巨大的差别,医生掌握医学知识和技能,患者一般缺乏医学知识,两者间医学知识的不对称,造成了患者求医问药的弱势地位和医生权力强势、话语主导地位局面的形成。话语权力的失衡不单单表现在日常的医患沟通中,也在出现医疗事故的沟通处理中。在一些因为医生犯错导致的医疗事故中,医生因为知识的专业性,很容易对一些问题进行遮蔽,而患者一方很多时候也只能选取自认倒霉的心态来面对。
(三)媒体接近使用权的医患差异
在医方与患方之间,不但有知识的不对称、话语的不均衡,而且面临着媒体传播权的巨大的不平等。媒体关于新闻事实的报道,跟社会上的政治、社会、经济权力是紧密相连的,一般都会向有话语权一方倾斜。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有言:“新闻界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己的法则,但同时又为它在整个世界所处的位置所限制,受到其他小世界的牵制与推动。说新闻界是独立的,具有自身的法则,那是指人们不可能直接从外部因素去了解新闻界内部发生的一切。”②[法]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在前网络时代,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在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模式下一直秉持“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舆论喉舌和宣传工具担负着维持社会安定秩序的责任,一直存在“报喜不报忧”的问题。因此,媒体在处理医患矛盾等敏感社会问题时始终以服从政府的报道指令为旨归,在新闻的报道时间、报道内容、报道选题和报道方式等各个方面上遵从于政府的媒体政策和维稳大局,而不得对医患矛盾等敏感问题随便发出自己的声音,媒体一般只能按照政府的要求发出政府需要的声音,坚守“报喜不报忧”“帮忙不添乱”的正面报道模式。
在如此这般的媒介体制下,即使出现过度医疗、医疗致死等事件,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也很少对这种医患冲突事件给予报道。不管是因为利益关联还是出于社会稳定考虑,媒体与医院之间有着一种不成文的微妙约定,不报道或少报道医患冲突事件。即使医患矛盾无法压制最终爆发,即使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也参与报道,因媒体接近使用权的医患差异也不致起大的波澜。“媒体接近使用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法学界新提出的一项公民权利,指的是“一种法律上可强制执行的权利,一般私人可根据该权利,无条件地或在一定条件之下,要求媒体提供版面或时段,允许私人免费或付费使用,以表达个人意见”①林子仪:《论接近使用媒介权》,《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台北元照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在医患事件的相关报道中,社会上有权力或有资源的人员和机构,如医生、医院等都相对容易接近使用媒体,成为新闻信息的主要来源者和新闻事件的主要定义者。而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患者群体,因为没有资源和话语权力往往没有在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上发声的机会。因此,在普通公众接近使用媒体权利缺失的年代,即便出现一些医患矛盾等社会敏感问题,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也难以形成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从而使医患问题的敏感度相对降低了很多。
二、话语博弈:新媒体环境下医患事件的话语沟通
在前网络时代,医患之间的沟通处于一种话语失衡的状态。医生因为掌握医学专业知识进而掌握医患沟通的话语主导权,患者即使有不满情绪因为缺乏媒体接近使用权利也无处发泄,只能沦落为“沉默的大多数”。而新媒体的到来逐渐改变了医患之间“话语失衡”的格局,不但给患者带来了知识获取的便利,而且使得患者自我话语赋权,在医患沟通中能够与医生进行话语博弈了。
人类医学模式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人们对于生命、健康与疾病的认识程度发展而不断地趋向完善。它的每一次递嬗,都潜涵着丰富的伦理意蕴。
(一)新媒体影响下的“知识民主”
前文有述,医生与患者之间有着医学专业知识的不对称问题,但在新媒体影响下这种情况有所转变。“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笼统的概念,它是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媒体形态,包括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的传播形态。此中,医患知识的转移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前网络时代,医患知识转移是在医疗诊断中从医生转移到患者的过程;但在互联网时代,各种新媒体手段使得医疗知识得以民主开放,患者不但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寻找与所患病种相关的诊断治疗信息,而且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医疗平台寻医问诊,可以借助互联网掌握的特定疾病知识、治疗相关的知识,并通过医患双方间的不断互动促进患方吸收、消化接收到的知识。由此,此前医患之间医生对知识的专断转变为知识的民主。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患者对于医生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对医生权威不加质疑地接受,变成了对医生持更多的质疑和批评的看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知识转移,很多患者都会在网上查到很多病情诊断治疗的相关资料,然后打印成纸质文本来到门诊就诊。于是对于医生的一系列诊断、治疗、用药、处理,患者都会与其在网上查找的相关资料比对,并提出诸种不一致的疑问,进而质疑医生诊断的权威性,甚至怀疑医生错误医疗或过度医疗,造成医患冲突事件。例如2016年11月22日,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中,感染性疾病科的一名年轻女医师于会诊途中遭到暴力袭击,连中九刀不治身亡。其原因便是患者要求医师按照百度知道的回答来做手足口病的相应治疗,而医师根据专业知识表示不可行,争执之后,酿成惨剧。②央广网http://news.cnr.cn/native/city/20161122/t20161122_523284286.shtml
(二)新媒体环境下的“话语赋权”
前文所述,医生在医患沟通中一直掌握着话语主导权,而患者始终处于话语的弱势地位。因此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患者都被动地沦落为“沉默的大多数”。即使面对医院的过度检查、过度医疗等不正常行为,患者也只能采取一种忍气吞声、不了了之的处置方式。但这种医强患弱的话语格局在新媒体勃兴以后发生了一些变化。新媒体催生了公众可以直接参与生产传播内容的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形式。这种自媒体形式的出现是对普通民众话语权限的解放,满足甚至激发了普通民众想说敢说的欲望。针对以医患矛盾为中心的医疗卫生类话语实践,诸如“天价医药费”“最黑医生”等种种网络流行语悄然兴起,且大多表现了患方对医方的调侃、无奈、嘲讽、批评等复杂情绪。在如此庞大的网络空间里,传播内容更趋个性化和自由化,患者可以绕开传统媒介的一个个“把关人”,接近使用媒体,在网络空间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同时让自我话语权在与医生话语权的博弈对抗中得到充分维护、强调和提升。这也就是标题中所言的“话语赋权”①师曾志、金锦萍:《新媒介赋权: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演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源于新媒体技术支撑下患者一方的话语赋权,使得处于话语弱势地位的患方获得充分的言论空间。以前面对医疗事故,患者一方只能暗自忍受,或者走上访之路。但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人们看到了“上访不如上网”的道理。以前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进入大众媒体视野的医患冲突事件,可以首先发布在网络上,以寻求话语共鸣与舆论救助。尤其是面对医患冲突事件,患方一改“沉默的大多数”形象,而变成主动发声者,他们借助各种新媒体形式对医生、医院发起声讨,引起网络舆论的关注,从而对医院形成舆论压力。网络空间俨然已经成为患者释放对整个医疗体制不满的发泄地,成为舆论讨伐医院和医生的前沿阵地。
(三)新媒体影响下的舆论格局
在前网络时代,媒体面对医患矛盾总是沉默不语,即便报道医患矛盾也多是以医院或医生作为信源。但新媒体的出现,使传统媒体不再具有主导舆论、议程设定的权力,很多适合网络议题主宰着报纸、广播、电视的议程,表现出一种分裂的微权、非正式运作的民间话语力量。在这种民间话语力量的支配下,冲突性的议题能够冲破地域限制,成为公共议题。由此,新媒体倒逼着传统媒体报道扩大报道领域,将医患事件纳入报道视野。而且,互联网的兴起使得医方话语、患方话语与媒体话语在对立中经历了此消彼长过程。当网络空间从精英阶层向大众化转变之时,就是网络空间逐渐代言于弱势群体之时,过去一直处于传播“弱势”地位的“草根阶层”在网络传播中成为活跃因素,使得被社会习俗视为“弱势群体”的患方观点被响应程度占有巨大数量优势,再加之近些年来传统媒介对医者形象的负面描述和一些个案医疗传媒事件的影响扩大化,使得网民对医者的“既定印象”与“媒介印象”不胫吻合。而占有人数为劣势、话语表达占劣势的医方,在寻求共鸣中就显得非常势单力薄。
在医患冲突事件中,不但患者可以借助网络进行维权发言,媒体话语也对患方话语予以支持,受到网络舆情的影响,当下的新闻报道中往往存在着“批评医生、同情患者”的报道框架,出现了媒体话语联合患者话语对医方话语施压的情况。一些媒体过度集中地渲染医疗纠纷,将部分医护人员收红包扩大到整个医疗行业的普遍行为等不专业的医疗报道,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局面。在近些年发生的恶性袭医事件中,本来是医生群体被伤害,医护人员遭遇暴力袭击,他们是同情的对象,但在医患对立关系的普遍层面,患方依旧处于弱势的一方,因此媒体报道时也时常站在弱者的立场上为患方说话。这种报道框架的选取也与新媒体兴起有关,是网络文化与意识形态作祟。学者许子东曾经在一次讲座中提出“网络的阶级性”的三个规律:“第一,穷人和富人争执,大家帮穷人。第二,老百姓跟官员有冲突,大家帮老百姓。第三,我们通常会站在多数人一边,多比少好。”②许子东:《网络文化与意识形态》,http://cul.qq.com/a/20130603/019483.htm.这种规律不但在网络舆论场中广泛适行,而且因为媒体舆论协同效应,导致传统媒体报道也逐渐顺应网络意识形态,在新闻框架选择问题上做出自己的选择和调整。因此,媒体在面对医患矛盾类敏感问题时,盲目跟风进行炒作,非常容易引起舆论动荡,造成社会恐慌乃至社会秩序动荡。
三、话语竞合:搭建良性互动的医患沟通机制
客观地说,医方话语与患方话语既有合作关系也有竞争关系,这也就是本节标题所提到的“话语竞合”。在这种竞争与合作同在的医患对话机制中,医患关系也伴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发生着微妙变化。在前网络时代的医患沟通中,虽有话语失衡问题,但话语合作为主流,但在新媒体时代的医患沟通中,医患双方呈现明显的话语博弈状态。但也必须认识到,新媒体环境下患者话语赋权,与医方话语进行竞争,其最终目的指向医患话语的合作。医患双方应该是一组齐心协力攻克病患的“利益共同体”,尽管存在着话语竞争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话语合作关系。因此,如何搭建良性的医患沟通机制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医患沟通本不应该是一种话语的怀疑与竞争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话语的信任与合作的关系,解决医患矛盾不能从医患各方如何能更加自我保护角度着手,必须从话语的对立博弈扭转为话语的信任合作关系进行思考。
(一)改善医方的话语态度
建构良性的医患沟通机制,首先需要医方在医患话语沟通中保持谦和温善的态度。医生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在整个医患沟通中具有绝对的控制力,也正因如此,医生也承担着治病救人、安定社会的重要作用。《人民日报》评论中曾经针对医患沟通指出:“医生的一句话,一张处方,一次手术,都关系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其背后连着无数家庭的幸福,以及社会的祥和。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医生要为患者点亮温暖的灯。生命要多一份虔诚,有时候,丹心比仁术更宝贵。”①张志峰:《丹心比仁术更重要》,《人民日报》2009年11月25日,第12版。因此,医方要为构建良性的医患沟通机制付出更多的努力。医生需要从语言层面上主动做出调整。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经说:“医生有三宝:语言、药物、手术刀。”②于德华、王彤主编:《医学人文服务读本》,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可见,自古以来语言便是医生重要的治病之宝,也是建构良性的医患沟通机制之钥。据北京大学医学部对三家综合医院医疗投诉分析表明:“80%的医疗纠纷与医患沟通不到位有关,只有不到20%的案例与医疗技术有关。”③种衍军主编:《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技巧与典型案例分析》,金盾出版社2015年版,第320页。虽然医生占据着医学专业知识的优势地位,但如果在病情诊断治疗过程中感情淡漠、话语冰冷,即使患者病情好转,医患沟通仍是失败的。由此可见,医生在医患沟通中的语言态度在整个医疗服务当中的重要性。医生应该端正态度,从尊重患者的知情权、提高患者对医患沟通满意度的角度出发,尽可能为病人提供其所需要的医学信息和医学知识。然而,在现实的病患诊疗过程中,医生往往为了提高门诊效率,仅在必要时提供相关诊疗信息。
为了保证患者能有一种在充分知情情况下进行自主选择的权利,就必须寻找一种“侧重于患医关系为核心的维持,侧重于在现行管理和政治体制下,病人和医生为达成治疗方案共识而合作的模式。”④[ 美]J.Glaude Bennett&Fred Plum:《医学是一门需要渊博知识的高尚职业》,载[美]Bennett&Plum:《西塞尔内科学》第20版,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1999年版。为了建立新型的良性的医患沟通机制,病人和医生为达成治疗方案共识而合作的模式,医生转变话语沟通态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委婉、亲善、真诚、为患者着想的话语方式与患者进行病情沟通,这不但有利于缓和医患双方知识不对称的问题,而且能够赢得患者更好地话语沟通和诊疗配合。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医务人员的语言不仅是直通病人心理活动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工具、载体和路径,也是重要的医疗手段、医疗方法。诸如药物、检查等各种科技方法,要成为有价值的医疗干预技术,需要医生将其转化为病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导入病人的心理并为其所接受。如果病人心理上拒绝,再好的科技医疗也无用武之地。”⑤杨国利:《医学人文走进临床首先要为自己正名——人文医疗以语言为载体》,《医学与哲学》2005年第5A期。只有医生以一颗平等的心与患者交流,才能真正进入患者的世界,才能产生医患之间的信任和爱,培养一种医患双方的“共同参与”的形式。这种形式以医患平等为基础,医患双方各自发挥各自的积极性,相互支持,相互协同配合,共同和疾病作斗争。
(二)保持患方的话语理性
建构良性的医患沟通机制,需要患方在医患沟通中保持话语理性。在以医患关系为代表的诸多医患冲突事件中,患方话语的表达呈现出一种极端和非理性的特点,甚或在沟通不畅时采取情绪化的“医闹”“暴力伤医”等极端手段。需要清楚的是,不管任何领域,人类的对话从来就没有绝对的话语平等,更何况医生与患者双方本身有着知识的不对称性。面对医患沟通的话语权不平衡,患者应该自觉地采用比较直接的语言策略,来主动拓展自身话语权力空间,追求话语平等的权势地位。但同时呼吁患方话语的理性表达,尤其是是面对医患冲突事件时,要能够理性言说,依靠法律武器来为自己维权。医生群体虽然在现实中的医患诊疗沟通中依据知识占据话语权,但一旦放置在网络空间中,瞬间变成弱势群体,因为全国公众大都有着医患沟通中的痛苦经历,于是面对医患冲突的个案,公众自觉站在医生的对立面,以患者抱团的立场对阵医患矛盾中的医方。例如面对“陈仲伟被刺”事件,医疗界同行一片哗然与痛斥,但也仅仅限于医学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互联网上出现了许多对受害医生的谩骂之语。如辽宁丹东的@邱适777说“死了最好,国家少养条狗”“主任没少收钱吧这些年”,更有偏激的网友直斥陈医生遇袭是“罪有应得”,如湖南株洲的网友@爱新觉罗就毫不客气地大骂:“斩的好,该杀!”⑥凯迪社区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1611946&boardid=101.“陈仲伟被刺”引发的舆论纷争远远超过事件本身所承载的话语讨论范围。
同时需要注意到,相对患者医方对网络空间话语表达的高涨热情,医生一方却显得比较被动、消极、漠然。或许是神圣光辉的医生职业意识使然,或者忙碌紧张的医生职业习惯使然,医生群体并不热衷通过媒介话语来展示自我,也不想在网络这个众声喧哗的话语集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这又正应了经济学中的“马太效应”:强的更强,弱的更弱。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当医生一方的话语缺乏表达的情况下就会呈现明显的舆论患者话语一边倒境况。由此,医患舆论场中偏向于患者的话语此起彼伏,却选择性地遗忘了医生群体的生存压力与舆论压力。而这也提醒医生群体应该主动走上网络,平衡已经倾斜的医患舆论场,引导公众话语走向理性表达。例如广州医科大学的廖新波便热衷于在自己的博客、微博上回应“过度医疗”“医药托管”等医患争议性话题,以“医生哥波子”闻名于网络。他的网络表达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众对医生的看法,疏导了网络媒体上患者医方的戾气丛生的问题。
(三)构建良好的舆论环境
建构良性的医患沟通机制,还需要构建一个良好的媒体舆论环境。在医患冲突事件的报道中,媒体需要进行认真的自我反思。在前网络时代,报纸、广播、电视对医患事件保持沉默是有违公众知情权的,而做出偏向性新闻报道是有违平衡报道原理的;新媒体影响下传统媒体开始积极介入医患冲突报道之中,又因为缺乏理性、盲目跟风陷入新闻导向性错误,要警惕媒体由于迎合受众而选择倾向于患者的报道框架,从而导致报道话语的失衡和医患风险的放大。同时,建议传统媒体在医患纠纷报道中从消息源、报道标题、词汇选择等进一步做到均衡客观的报道,要清醒地认识到,大众媒体不单单是报道新闻的载体,也是积极参与社会风险治理的主体。面对医患矛盾等社会敏感问题,在网络舆论吵得不可开交之时,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应当坚持信息公开化的原则予以报道,以适应网络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特殊的媒体环境。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当面对医患矛盾之类社会敏感问题时,主流媒体必须掌握好新闻报道的力度,把握好新闻报道的时机,并对新闻报道可能引起的社会影响作出事前评估。
在新媒体翻云掀浪的现代舆论环境中,报纸、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要敢于正视医患矛盾等社会敏感问题,进行客观报道。同时要认识到批评、曝光绝对不是媒体社会责任的最终体现,倘若不考虑医患事件的社会稳定大局,不能针对医患问题提出一种切实解决的方法,媒体的揭露和批评只能在一定时间内吸引公众眼球,却无法体现出主流媒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社会责任。面对此起彼伏的医患冲突问题,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既要秉持一种公平、公开、公正的新闻报道原则,以及时、客观地呈现事实真相,也要防止因过度报道和舆论关注而造成医患问题的风险放大,从而导致媒体报道压过客观事实的问题,进而社会公众的心理恐慌。当然媒体也应该保障医方、患方表达渠道的畅通,实现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同时鼓励和引导民间医疗健康公益组织建立处置医疗纠纷的“第三方机制”①《21世纪经济报道》编著:《改革意见书——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对具有争议性的医患纠纷能够给予公正的评判,并提供相对合理的解决方案。这种方式不但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医患双方话语的理性表达,也有利于培植医患沟通的良性舆论环境和文化土壤。
C913.4
A
1003-4145[2017]12-0116-06
2017-07-02
吴洪斌,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大众报业集团期刊中心副总经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年课题“争议性新闻事件中的专家参与研究”(项目编号:15CXW00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陆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