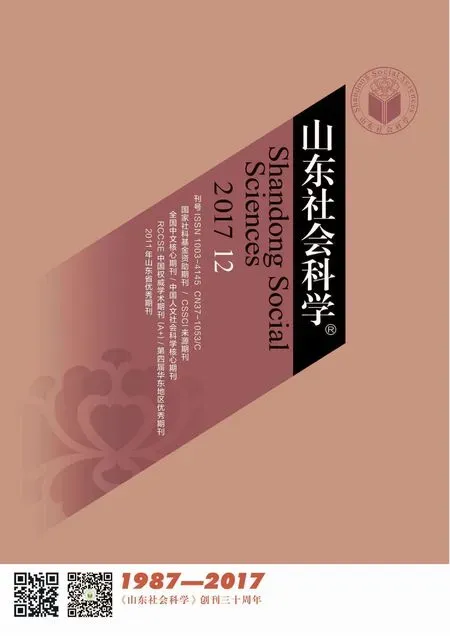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吗?
——奥斯丁法哲学理论批判
田太荣 马治国
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吗?
——奥斯丁法哲学理论批判
田太荣 马治国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陕西西安 710049)
“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是始终贯穿于英美法理学的核心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影响诸如法效力、法律规范性等问题的答案。英国法理学家奥斯丁认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其法律理论可以分为命令理论和主权者理论两部分。其在方法论上犯了还原论和实然推导出应然之错误;内容上,命令理论将法律定性为单一的命令,扭曲了法律的本质,主权者理论不能维持法体系的连续性和法律的持续性,无法解释现代社会法体系及其复杂实践。哈特的规则理论(法律是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的组合)更加合理应对了这一难题,因此是法律性质之问题的更优方案。
奥斯丁;主权者;命令;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哈特
如哈特所指出的,关于人类社会的问题,极少像“法律是什么”这个问题一样,持续不断地被追问着,同时也由严肃的思想家以多元的、奇怪的甚至是似是而非的方式作出解答。①[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法律是什么”又被称为法律的概念问题或性质问题,它始终是贯穿于英美法理学界的核心论题,②Marmor, Andrei and Sarch, Alexander, The Nature of Law,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Fall 2015 Edition), Edward N.Zalta(ed.), URL =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5/entries/lawphil-nature/>.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将会影响其他重大问题的答案,如法律的效力条件、法律的规范性来源、如何依法裁判等。
根据生活中的法律印象,我们经常听闻这样的法律规定:禁止杀人,禁止强奸,不许偷盗,禁止抢劫,勿损害他人财物……法律似乎都是以一种强制性的命令方式规范着我们的生活。那么,法律本质属性真的是一种命令吗?或者说它跟命令又有何联系呢?
19世纪的法理学家、分析法学的奠基者奥斯丁③关于奥斯丁生平事迹的完整介绍,可参见[美]布赖恩·比克斯:《奥斯丁:生平、观点与批判》,于庆生译,《北航法律评论》2010年第1辑。在其代表作《法理学的范围》一书中对这一疑问给出了肯定性的回答: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或者说是政治优势者对政治劣势者设定的规则。④奥斯丁开篇即区分了法的几种用法:分别是上帝法(the divine law)、实在法(positive laws)、实在道德(positive morality)和比喻意义上的法(laws metaphorical)。他很不满意这种“法”的混乱使用,《法理学的范围》一书的首要目的或努力便是厘清“法”的范围。奥斯丁旗帜鲜明地提出实在法乃法理学的真正研究对象,即政治优势者对政治劣势者制定的法律。见[英]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奥斯丁这一答案一般被称作法律命令理论,对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分命令理论和主权者理论两部分对奥斯丁的法理论进行剖析,并主要引用哈特的理论对其进行批驳,最后给出初步结论:法律不是主权者的命令,而哈特提出的初级和次级规则的组合或许是对“法律是什么”更加合理的解答。
一、作为主权者命令的法律⑤——命令命题的建立
奥斯丁的法律命令理论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命令理论和主权者理论。法律的性质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命令,而是主权者或者政治优势者发出的命令。本文暂且将之称为命令命题。
(一)命令理论
1.什么是命令?
在奥斯丁看来,命令的含义为:第一,一个理性存在提出的要求或意愿,是另外一个理性存在必须付诸行动和遵守的;第二,在后者没有服从前者的要求的情况下,前者设定的不利后果会施加于后者;第三,前者提出的要求的表述和宣布,是以文字或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①[英]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奥斯丁认为当你表达或宣布一个愿望,即将让对方做或容忍一些行为,如果不服从将施加惩罚,那么这一愿望就是命令。一个命令区别于其他意义的愿望在于其背后的强制力。当我宣布一项命令后,你便受制或迫于这项命令,那么这时即有了一项服从的义务。所以,命令与义务有相关性。当违背这一命令,即违反了义务,这时便会施加一项不幸,这就是制裁或强制性的服从。在此,奥斯丁区分了奖赏与惩罚,如果对于一个意愿的服从带来的是奖赏,则相当于是授予了一项权利,而非设定了义务,所以,奖赏同惩罚虽然都是服从动因,但只有惩罚才是制裁。
所以,从前面的分析结果来看,“命令”“义务”和“制裁”是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术语。每个术语就像另外两个术语一样,具有同样的意思,尽管每个术语是以自己独特的叙述顺序方式,来展示这些意思的。②[英]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命令一词侧重于命令要求的发出,义务则强调不利后果的可能性,制裁在于表示不利后果本身。③凯 尔森认为奥斯丁这一命令概念混淆了“效力”和“实效”两个概念,当受迫于命令而实际上进行了服从,不能说明这个命令是有“效力”的或者说约束力的,即是应当服从的,至多是说它具有了“实效”,即实际上为人所服从。也可以认为是“是”与“应当”之间的混淆。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7页。
2.法律是一种普遍的命令
奥斯丁认为,法律是一种普遍的命令,区别于具体的或个别的命令。最典型的莫如司法命令和立法命令,司法命令是具体的,个别的,而立法命令则是一般的,普遍的,被称为法或规则。
一般来说,大多数的法律在双重意义上是普遍的:第一,普遍性地要求或禁止一类行为;第二,对全体社会成员是有约束力的,或者,至少对其中某些种类的社会成员是有约束力的。④[英]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当今法律体系所讲的法律效力的属人效力、属地效力、属事管辖就是属于这个意义上的用法。
(二)主权者理论
1.主权者的定义
主权者,即政治优势者,社会的统治者。“优势”一词,表明了强制力的意思,即用不利后果或者痛苦影响、强迫他人的力量,通过这种不利后果恐吓,使他人行为符合一个人的要求。主权者即是具有这种政治上的优势者。
主权者具有如下的特点或显著标志:其一,特定社会中的群体,处于一种习惯服从或隶属于一个特定或一般的优势者的状态。而这样一种一般的优势者,是某个特定的个别个人,或者,是由若干个人组成的某个群体或集合体;其二,被习惯服从或隶属的某个个人,或者由个人组成的群体,并没有处于一种习惯服从其他特定社会优势者的状态。⑤[英]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所以,主权者是由两个显著标志相结合而成,第一个是肯定性的,第二个是否定性的,二者缺一不可。
另外,主权者是与独立政治社会相关联的。所谓的独立政治社会,与自然性质社会相对,即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或者所有人,都习惯性地服从一个特定或一般性的优势者,而这个优势者没有习惯服从于其他人。⑥关于独立政治社会的定义,奥斯丁批驳了其他几位学者的定义,如边沁、霍布斯、格老修斯和马腾斯。参见[英]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240页。同时,奥斯丁承认,因为“独立政治社会”这一术语之抽象无法用精确的语言表述,自己的定义同样是难免疏漏的,并努力给出了解释。参见[英]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237页。而在自然性质社会中,没有一个人是生活处于隶属状态的,或者所有人是生活于独立状态的。
2.主权者的权力不受限制
奥斯丁认为,既然主权者是不会习惯性服从任何其他的个人或集体,所以,其权力是不受限制的,否则便会同主权者这一定义本身自相矛盾。君主和主权者群体,可以试图约束自己,或约束主权权力的其他继承者。然而,即使主权者可以制定约束自己的法律,制定约束自己继承者的法律,主权权力不可能受到法律限制这样一种判断,依然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依然会是绝无例外的。①[英]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
依照上述主张,我们可以分析得知:(1)主权者虽然可以自己制定法律约束自己,但是同样也可以废除,所以与其说是限制,不如说是一种自己行为的指导原则;(2)这里的不受约束指的是不受法律约束,而不是指不受道德的、宗教的和舆论的约束,主权者可能会受道德、舆论的压力而改变命令;(3)如果当主权者是由一个人组成,则他是不受法律限制的,但是如果是由一个群体构成的,则当他们作为组成成员时是受到限制的,但作为主权者这一整体时是不受法律约束的。
二、法律命令理论的批判——命令命题的失败
以上命令理论和主权者理论共同构成了奥斯丁法哲学理论,形成了一个逻辑自洽的法律性质之说明。但是这一理论虽然影响很大,但同样是极不完善的,其已经不能解释现代社会复杂的法律现象和许多法体系的问题,也影响到了许多法律的规范性问题的解释。
(一)方法论批判
1.还原论的失败
从上述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奥斯丁的法哲学理论中,法律无非是一种制裁性的主权者统治的工具,是主权者的一种命令。法律的性质最后被化约或还原为普遍性的命令,这其实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还原主义。所谓的还原主义,一般是一种哲学解释方法,即当我们去解释一种事物的本质的时候,借用另一种事物来进行替代性陈述。②A ndrei Marmor, Philosophy of Law,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p.12.亦可参见中译本[美]安德雷·马默:《法哲学》,孙海波、王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3页。奥斯丁即将法律还原为命令理论,用命令性质替代法律的本质。这一方法受到了凯尔森的极力抵制,后者最终发展出了一套纯粹法理论。当然,凯尔森实际上也并未完全摆脱还原论。③A ndrei Marmor, Philosophy of Law,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5.亦可参见中译本[美]安德雷·马默:《法哲学》,孙海波、王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但是,这种还原论的方法是错误的,法律的本质是一项规则,而不能通过命令来进行解释,将法律强行定性为命令,只会扭曲法律的本质(至于命令如何不能解释法律,下文内容批判部分进行详述)。
2.“休谟定理”的违背
所谓休谟定理,即休谟难题,指在事物的实然与应然之间不能互相推导,我们既不可能从实然就能得出应然陈述,同样也不能从应然陈述得出实然的表达。这一难题常常成为理论上的鸿沟。从奥斯丁的主权者理论我们知道,臣民们是习惯服从于主权者的,也正是因为臣民们习惯服从于的是主权者,所以其颁布的命令才能称为法律。所以,臣民们是习惯服从于法律的,这是一项事实上的描述,即实然。而我们知道,我们服从于法律,不是一种实然意义的陈述,而是一种应然意义上的陈述,也即我们应当服从于法律,而不是实际上服从于法律,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实际上服从于法律的。然而,在奥斯丁看来,我们绝大多数人实际上的一种守法状态成为一种我们应当守法的原因,这样的一种实然状态推导出了应然意义状态。但是,任何方式的在应然与实然间的互推都将违背休谟定理,从而在方法上归于失败。
(二)内容论批判
在本部分,我们将对奥斯丁的法理论展开内容上的批判,而批判的形式则以简单的命题形式展开。
命题一:法律命令不能区别于抢匪命令。④奥斯丁误将抢匪的命令(imperative)称为号令(command),因为号令一般与权威相连,我们显然不能说抢匪的命令具有权威性。但由于号令与权威相连,反而过于近似法律,不利于分析两者区别,所以,此处仍采用命令作为模型。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简单的抢匪情境,即一个抢匪命令一个人交出钱来,不然就要射杀他。在这个简单情境中,我们依次添加三个因素,就可以接近奥斯丁的理论模型。第一个是普遍性,即将命令的受众扩大为一个群体;第二个是持续性,就是抢匪的胁迫时间是足够长的,而不是短暂的;第三个是普遍的习惯性服从,也就是说抢匪足够凶悍,他的命令得到了大多数受众的遵守。另外,对发出命令的抢匪赋予两个重要特征,其本身是独立的和不服从于其他任何个人或者群体。这样,一个抢匪情境已经建立起来,基本等同于奥斯丁法理论的社会情境,那么,抢匪的命令也就等同于主权者的命令,即法律了。而且,屈于抢匪的淫威而实际上服从,并不等于我们有义务服从,而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义务服从于法律的,所以这里奥斯丁显然混淆了“被迫的(was obliged)”和“有义务的(had an obligation)”两个重要语词在表达内涵上的差异。①详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5-80页。
命题二:法律的内容不全是制裁的。
奥斯丁认为法律是作为一种命令式的制裁,但实际上法律的内容不全是制裁,还有其他内容。一般来说,只有刑法的规定最接近于奥斯丁的理论,都是禁止性规定,科予义务;婚姻、契约、遗嘱等民事性法律规定则多数是授予权利的。但可能奥斯丁的支持者会这样反驳,违反民事性规定将导致行为的无效,所以无效也是一种制裁。这显然是对“无效”这一概念的扩张,造成混乱,因为无效可能并不必然是一种恶。例如,一个六七岁小孩私自做主将家中贵重物品赠与朋友,这样一个行为的无效对于小孩本人及其监护人并不是一种制裁,而是一种保护。
凯尔森在法律的内容上,基本与奥斯丁共享这样的命题,即法律必然是制裁性的。他认为授权规则只不过是法律的片段,不具有真正的“法”地位。②根 据凯尔森理论,法律规范分两种:主要规范,也就是对违反次要规范的制裁性;次要规范,指的是一种义务性行为。所以,次要规范的效力依赖于主要规范,主要规范才是真正的法律规范。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07-108页。但是,法律的功能主要是指导规划生活(主要功能),其次才是补救(次要功能),所以奥斯丁和凯尔森两人将法律的功能主次颠倒,扭曲了法律的本质。诚如哈特所言:“这个理论的两个版本,都企图将法律规则显然相异的多样性,化约为一个单一的形式,并宣称此单一形式可以表现法律的真正本质。这两个版本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但都将制裁作为核心的重要因素,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说明没有制裁的法律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话,这两个版本都将失败。”③[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
命题三:法律命令也适用于主权者。④也即主权者是受到法律限制的,在下文将对这一命题进行详述。
奥斯丁认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而主权者本身是在法律之外的,这种命令完全是涉他形式的。但是根据现代社会立法理论,立法不过是引进或修正社会应普遍遵守的一般行为标准,立法者并不必然就是对他人下达命令的人;他好比一个约定的提出者,运用了规则授予的权力,但是一旦约定生效,双方都是处于约束中的,而不能超脱于法律之外。所以,主权者虽然自身是制定法律的主体,同时也是受到法律约束的主体。
命题四:法律的起源并不都是命令的发出。
根据命令理论,法律全是主权者发出的命令,也就是有意创设的,一般是通过明示的直接表达,也可以通过间接的表达(如授权或默许)。所以,习惯法只有当法院刻意适用时才是法律。对此,笔者提出两点异议。第一,这应该只是适用于特定的法律体系,不具有一般性。因为我们同样可以设想某个法律体系认为法院适用前习惯即具有法律地位,如成文法一般,被适用前就是法律了。而奥斯丁显然是追求一般法理论的。第二,即使我们承认直到法院适用习惯前,习惯并不是法律,同样我们也可以主张,将主权者的未加干涉当成是这些习惯规则应该被服从的默示表达。显然命令说是无法排除这一可能性的,即其理论主张不具有必然性。
命题五:主权者理论不能维持立法权威的连续性。
在奥斯丁的法理论社会情境中,臣民们是习惯服从于主权者的。但是,“习惯服从”一词含义较为复杂,既可以指对强盗命令的服从,也可以指对权威的服从。我们还可以举一个简单的模型,如在君主雷克斯(Rex)统治下,臣民们迫于惩罚的压力会服从于雷克斯。但这种服从能否有习惯性之不加反思、轻易的以及根深蒂固的特性则很难说,将其与我们早餐时习惯性看报纸相比,二者还是有区别的。
我们可以继续推进,当雷克斯一世去世,继位的雷克斯二世(RexⅡ)如何取得臣民的习惯性服从呢?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使他一开始就成为主权者。在这之间通常来说有一个过渡期或间隙。所以,“这一情况无法说明我们在每一个正常的法体系中所观察到的连续性。首先,对一位立法者所下达之命令的单纯服从习惯,并不能够授予新立法者任何继承的权利,以及以自己名义下达命令的权利。其次,服从习惯本身并不能够提供“新立法者的命令将会获得服从”这件事的可能性,或者说有这样的预设。”①[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但是可能是奥斯丁的疏忽,我们将替他补上这样的权力预设,则此时必将面临着比习惯服从更加复杂的社会实践,即一定要有对新立法者继承资格的规则的接受。在处理这个问题前,我们先讨论习惯和规则之间的差异,即一个群体有着某种习惯,如周六晚上看电影;和一个群体有着这样的规则,进教堂时男士必须脱帽,那么这两者到底有何差异呢?在哈特看来,认为有以下三点②[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1-53页。:
1.偏离习惯并不必然受到任何形式的批评,而规则的违反则肯定会遭受要求遵守的压力。
2.在规则存在的地方,不但实际上会有这样的批评,且对于违反规则这一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受到批评的好理由。也就是说,这一批评是可以得到辩护的。
3.第三个差异可以称之为规则的内在面向。对于习惯的遵守,人们不需要去刻意地维持,只要存在他人同样行为的这一事实即可,这是一种“外在”面向。但规则除共享了习惯的这一外在面向,还要求规则内的人将其视为整个群体必须遵守的普遍标准。每当规则被违反时,都会被批评、要求遵守,这即所谓的规则“内在面向”。
此时,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法律问题上来。在雷克斯统治的社会里,我们引入这样一个标准可能更加符合现代法律世界,即任何雷克斯所规定的行动都必须去做。这使得我们最初对雷克斯的单纯服从习惯所描绘的情况发生了转变。因为在此种规则被接受的情形下,实际上雷克斯不仅规定必须做的事,并且他也有权利做规定;并且,人们不仅对其命令普遍服从,同时也普遍接受,服从雷克斯是对的。那么,现在雷克斯的言辞成为行为的标准,因此对其所指示行为的偏离将会遭到批评,人们现在普遍根据他的言辞来证立批判或遵从的要求,并且这样的证立方式也为人们普遍接受。而到这里我们发现,法律已经呈现出了规则的内在面向,而不仅仅是奥斯丁理论中的被迫服从。
所以,为了维护法律的连续性,则必须有这样一个规则,即授予每个立法者如同雷克斯一世一样的情形。但是,建立在这种表达出人们对规则的接受的社会实践,已经不同于单纯的习惯服从那么简单的事实了。
命题六:主权者理论不能维持法律的连续性。
奥斯丁法哲学将法律的遵守视为臣民对主权者命令的习惯性服从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不能解释法律本身的连续性,即先前死了很久的立法者制定的法律现在为何仍旧是后来社会的法律?因为我们的法律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比其制定者和习惯服从者那些人的生命力更长。对此,霍布斯有个天才的尝试,甚为边沁和奥斯丁所赞同,即“立法者并不是那个以其权威将法律最初制定出来的人,而是以其权威使得它们现在继续作为法律的人”③[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8页。。即一个可能对法律持续性作出解决的论证是前一个或一些主权者制定的法律经过现在主权者的确认便具备了法律的地位,而这个方法是可以通过默示的方式来实现的。但是这个辩解同前面对习惯法之法律地位辩护路径如出一辙,只不过在此是无能为力了。倘若说习惯只有经过主权者的确认或法院的适用才具备法律地位还可以牵强附会,那么认为在主权者默认前或法院适用前,过去的主权者指定的法律便不是法律则是非常荒谬的。一如哈特的举例,说维多利亚时代制定法和今天的女王议会所通过的制定法对于今日的英国来说具有完全的同等法律地位,即便在议院确认或法院适用前就是法律了。这样做的唯一优点便是提出了一个模糊的唯实论式的提醒。④法唯实论指的是法律现实主义,哈特在《法律的概念》第七章中对其作了批判。
命题七:主权者是受到法律限制的。
奥斯丁的法理论中,主权者是不服从于任何其他个人或群体的,即权力是不受到法律限制的,否则便同主权者这一定义本身相矛盾。这一理论相当的诱人,因为其一并解决了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可以从主权者的命令中鉴别出法律,以将其区别于道德、习惯或其他社会规则;二是可以确定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还是某个更大的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但是这一主张的缺陷是很大的,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五点非常严密的批判:⑤[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4-65页。
1.对立法权威的法律限制,并不是要求立法者去服从某一个更高的立法者,而是授予他立法资格的一些规则,以对其立法方式进行限制;
2.为了证实某个法案是否为法律,我们不需要追溯到立法者的意志,只要我们证实这项法律是由某个规则授予立法资格的立法者制定的,而其中不包含任何对这一立法的限制即可;
3.为了证明一个独立的法体系,也不必要去证明这个法体系的最高立法者是不受法律限制的,我们必须证明的是授予立法者资格的规则并未授予在同样的领域内具有更高的权威的人;
4.我们应当区分在法律上不受限制和最高之间的关系,虽然立法者受到限制,但只要是法领域内最高的立法者就可以了;
5.尽管是否存在限制立法者权能之规则是关键性的,但是相对而言,立法者的习惯服从至多也只是作为一种间接证据罢了。
命题八:奥斯丁的主权者是不存在的。
根据现代世界的法律体系,通常会认为即使最高立法机构的立法权力也是受到法律限制的,但是我们可以暂时假设抛开这些认识,看看能否找到奥斯丁理论中不受限制的主权者,或在现代的民主立法中是否存在这样的主权者。
依据奥斯丁的陈述,在民主立法体制中,构成或形成拥有主权者之主体的人并不是被选出来的代表,而是选民。因此,在英国,真正的主权者乃是国王、贵族以及下议院的选举人。同理,在美国,每个州的主权者便是任命立法机构的公民团体。这样,英国和美国其余的公民便服从于选举人这一团体。但是此说法显然是无法接受的,除非这里的“服从”一词有着不同于寻常的含义。
我们试着做退一步的论证。认为全社会拥有选举权的人组成的团体为主权者,那么便会造成“大多数人”习惯服从于他们自己。为应付这个批判,我们可以将社会成员的人格区分为作为个人的私人人格和作为选举人的公务资格。这样似乎就不是我们服从于我们自己了,而是服从于另外一个人格了。但是这样的区分仍旧拯救不了主权者理论,因为此处显然必须有着特定的授权规则,授予这种资格,并且他们也遵从这样的规则有效选举和立法。唯有指涉这样的规则,我们才能将这个团体的所做的事鉴别为立法或选举。但是,这些规则本身显然不具有主权者命令的地位,因为除非规则已经存在并被遵守,否则便没有任何东西可被当作是主权者的命令。申言之,主权者不能独立于规则之外被确认出来了。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将其视为仅仅是社会服从于主权者的条件了,相反,这些规则构成了主权者的一部分了。所以,选举人在选举他们的代表的时候遵从了规则。这样,就把这个理论至多带回到这样一个形式:主权者是立法机构,而不是选举人。但难题依然还在:因为立法机构仍旧可能受到法律对其权力的限制,这个与立法者理论是矛盾的。
综上所述,在方法论上,奥斯丁犯了还原论和违背休谟难题的错误;在内容论上,命题一到命题四宣告了命令理论的破产,而命题五到命题八宣告了主权者理论的破产。因此,整个规则命题被瓦解,我们需要重新寻找“法律是什么”这个难题的答案。
三、法律是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的结合——规则命题之重构
鉴于以上论述,哈特认为必须用“规则”重构法律体系。而鉴于“惯习式的社会结构”①[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3页。只有单一规则,即命令式的义务规则,哈特称之为科予义务之初级规则,其存在三个缺陷:
1.不确定性:即群体生活所依赖的规则并不会形成一个体系,而只会是一批个别独立的标准,没有任何可供鉴别的或共同的标识。一旦人们对于某个规则发生争议,将没有任何解决争议的程序。
2.静态性:这种社会结构中,规则的形成和消灭都是一种缓慢的生长过程,不存在任何为适应变动的环境而可以改变规则的方法,近似一种静态状态。
3.分散性:规则运行是需要维持的,而维持社会规则的压力在这个“惯习社会结构”中是无组织的、分散的,因而也是无效率的。
所以,必须引进三个次级规则作为相应的补救方法,由前法律世界迈向法律世界的关键一步就在于此,三个补救方法结合在一起就足以使得初级规则的体制不容置疑地转变为法律体系。法律就是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的结合。本文将之称为规则命题。
初级规则所涉及的是个人必须去做或不可以做的行为,相对地,次级规则都是关于初级规则本身的。他们规定了初级规则被确定、引进、废止、变动的方式,以及违规事实被决定、确定的方式。①[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5-86页
具体而言,次级规则又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承认规则。引进承认规则的目的在于补救初级规则体制的不确定性,消除规则之存在的争议。凡有此种承认存在之处,就存在一个相当简单的次级规则,一个鉴别科予义务体制初级规则的决定性规则。②[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但需要注意的是,承认规则可能很复杂而不止一种,所以还有位阶之分。二是变更规则。引进变更规则,使得规则的产生和消灭不再是自然的缓慢历程,而是可以自由创设。最简单的莫如授权给某人为群体生活引进新的初级行为规则以及废止旧的规则。三是裁判规则。引进裁判规则使得社会压力有序组织起来,不仅规定了谁是裁判者,而且也界定了裁判者必须遵循的程序。这些次级规则提供了体系中集中化的官方“制裁”。③[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用凯尔森之言,法律作为一种强制秩序,是对武力使用的垄断。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9-53页。
至此,我们不但拥有了法体系的核心,而且在法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们之间的许多困惑现象的分析上,也有了最强而有力的工具。但是,我们必须以这样的警告来结束本节内容:“虽然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的结合,说明了法律的许多面向,而值得被我们赋予中心的地位,但是这个结合本身不能阐明每一个问题,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的结合处于法体系的中心,但它不是全部,而且当我们从中心向外移动时,我们将必须以在后面几章将指出的方式,来容纳不同性质的要素。”④[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
四、结语
虽然奥斯丁努力通过命令和主权者两项理论紧密结合、互动,试图对“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自以为找到了“法律科学之关键”,但很遗憾,他的努力是失败的,不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实质内容上。诚如哈特所言:这个理论不仅在细部上是错误的,并且命令、习惯,以及服从等简单的观念,对于法律的分析而言都是不适当的。相反地,我们需要的是授权规则的观念(其授权可能是有限的或无限的),这种规则以特定的方式授予某个人或某些人以遵从特定程序之方式来立法的资格。⑤[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或者说,这个理论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其所建构的要素,即命令、服从、习惯和威胁等观念,并不包括,或者说不能通过把这些要素组合起来产生“规则”的观念,而如果没有这个观念,我们就连最基本形态的法律也无法说明。⑥[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3-74页。
但并不是说他的理论毫无合理性,有三点不可谓不是洞见:第一,他准确认识到了法律是一种对人行动的规范和指示,这已经成为当代法哲学讨论的共识和出发点;第二,他准确认识到了法律的强制性,法律指引人行动的方式是义务的而非任意的;⑦Andrei Marmor,Philosophy of Law,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36-42.第三,虽然命令概念这个工具无法提供法律一般性质的说明,但是命令背后所揭示的那种法律直觉——社会事实命题与独立于内容,依然是当今法理论的核心要点。⑧陈景辉:《命令与法的基本性质》,《北方法学》2013年第4期。当然,他的这种预测理论虽然观察到了规则的外在面向,如果从实践哲学来看,即基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给出了动机性的理由,但还不是规范性理由,而人类的行动理由是需要规范性支持的,特别是法律、道德等实践门类。所以“习惯性服从”等概念无助于解决法律的规范性问题。⑨当然,亦有学者对奥斯丁的理论提出了新的见解。参见周祖成、张印:《对奥斯丁法律概念的再认识》,《现代法学》2015年第1期。而哈特的规则理论或许是更好的答案,至于他对现代世界复杂的法律实践中的缺陷和不足的解释,则需要另外一篇文章来专门论述了。
D903
A
1003-4145[2017]12-0161-07
⑤奥斯丁将法律的性质定性为命令,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霍布斯的命令理论,且将法律作为国家统治的工具。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017-10-09
田太荣(1979—),男,陕西韩城人,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律治理学、行政法治理论与法律文化。
马治国(1959—),男,陕西绥德人,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