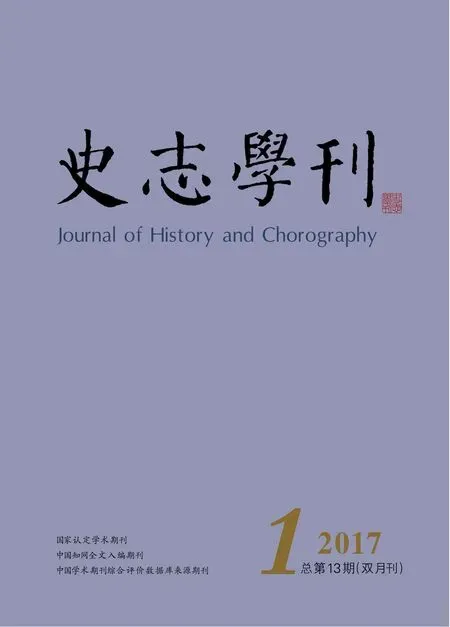唐代学官的选任标准及变化
董坤玉
唐代学官的选任标准及变化
董坤玉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100009)
唐代对于学官的选用有着不同于普通官员的两个标准,学官任用在品德和学识两个方面的要求很高。除了对儒家经典必须有高深的造诣,还要有德高望重的地位。但这两个标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举制度的盛行,在唐代中期以后发生了改变,不但对于品德和学识的要求有所降低,而且学官的选任也由唐初的重经义逐渐转变为唐中期以后的重文辞。学官选任标准的变化进一步促使了唐代官学走向衰落的过程。
学官 标准 选任
选官标准“系指国家在选拔不同种类的官吏时所要求的特殊标准及用这种标准来教育或培训拟入仕者。唐代对于官员选用的统一标准是“身”“言”“书”“判”四事,“(吏部)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词论辩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四事可取,则先乎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1]通典(卷十五)·选举.中华书局,1998.(P360)身、言、书、判四个标准符合就等于敲开了进入仕途的大门,但官职的分配与升降则与德行、才能、工作量相挂钩。品德方面毋庸赘言,但是就“才”而论,根据不同部门的工作性质则既有政事处理之才,又有审断狱讼之才,还有论辩谏诤之才等等,不同的政务部门对于才的要求是不同的。唐代学官是指唐代官办学校内教授儒家经学的教师。学官的选任除了遵循一般官员选任的标准外,还有特殊的要求。
一、唐代学官的选用标准
1.必须对儒家经典有很深造诣。《新唐书·职官志》对于学官的最高行政长官国子祭酒和其副贰国子司业的职责是这样定义的:“祭酒一人,从三品;司业二人,从四品下。掌儒学训导之政,总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凡七学。天子视学,皇太子齿胄,则讲义。释奠,执经论议,奏京文武七品以上观礼。凡授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兼习《孝经》《论语》《老子》,岁终,考学官训导多少为殿最。”[2]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P1265)“掌儒学训导之政”“考学官训导多少为殿最”是国子祭酒与国子司业的行政职责,这项职责可概括为执行政令、考核下属,是对政府各部门长官的常规性要求,并无特别之处。而“授经”“讲义”“执经论议”则是对学官学识的要求,即学官必须深入掌握儒家经典,不仅能够教授经文、释解经义,还要达到能够与众人论议的程度。为学生讲授经典是学官的主要职责,此外,皇太子行齿胄礼时学官要“讲义”、国子监举行释奠礼时学官要“执经论议”,这是国子监所承担的两项重要礼仪活动,都要求学官开讲儒经,敷陈义理,因此通晓儒家经典是从事学官职业的首要条件,而这也正是学官“才”的具体体现。
学官对儒家经典不仅仅是熟读、背诵就够了,还要研究深入,对经文义理的理解必须能够成一家之言,这样才能够胜任学官执经论议的职责。原因如下:唐代社会风气开放,学官在齿胄礼、释奠礼等重大场合讲义、论议之时常常要面对社会各学派、教派的交相论难,如果对儒家经典没有深入研究,面对如此复杂的论难场面则很容易颜面尽失,甚至难以保全儒家与学官整体的体面。执经论议是释奠礼的一个重要内容,论议之时“道士沙门与博士杂相驳难”[1]唐会要(卷三十五)·释奠.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55.(P640),不但有博学的学官儒士主讲,而且还有佛教、道教人士杂相论难,如果儒学功底不深是很容易被揭穿的。隋代国子监举行释奠礼,大儒刘焯与刘炫二人论义,“深挫诸儒,(诸儒)咸怀妒恨,遂为飞章所谤,除名为民。”[2]隋书(卷七十五)·刘焯传.中华书局,1973.(P1718)释奠礼论议之时诸儒因论义不精,被二刘挫败,颜面大失,因妒生恨恶意诽谤,迫使皇帝将二人除名。唐高祖时举行释奠礼,高祖亲临,“时(博士)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太学博士陆)德明难此三人,各因宗指,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3]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儒学传.中华书局,1975.(P4945)因为学官陆德明学术造诣技高一筹,才在这次论难中战胜了道、释二教,学官与儒家的地位得到了维护。由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在释奠礼中,学官之间,以及学官、道士与沙门之间,三派是互相论难以显示各自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讲,释奠礼成为三教争锋的战场,同时也是学官学术水平高低的展示台。另外,国子监内部的学官之间也常常会有辩驳学问之事,即使国子监的最高长官国子祭酒也免不了要碰到这种场面,如果自身艺不压人,难以服众事小,难免还会遭到其他学官的奚落。隋代国子祭酒元善通博儒经的程度本在国子博士何妥之下,但他善于讲学,听者忘倦,为后进所归,何妥心怀不平,“因(元)善讲《春秋》,初发题,诸儒毕集。善私谓妥曰:‘名望已定,幸无相苦。’妥然之。及就讲肆,妥遂引古今滞义以难,善多不能对。善深衔之,二人由是有隙。”[4]隋书(卷七十五)·元善传.中华书局,1973.(P1708)何妥不理会元善的恳求,借元善于讲肆讲《春秋》的机会,突然提出古今以来的滞留问题以使元善难堪,从此二人产生嫌隙。这个例子虽为隋代的事情,但却展现了学官们在讲论中争高下的场景,客观反映了国学讲论风气的活跃。退一步讲,即使没有学术争锋,学官的学术水平如果说不过去,在教学过程中也难以避免来自学生的挑战。以上论证都说明唐代官员只有对儒家经典有很高的造诣才能胜任学官。
2.必须德高望重。贞观六年(632)唐太宗下令“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5]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传序.中华书局,1975.(P5636);贞观十一年(637),令诸州采访“儒术该通,可为师范”者为学官[6]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采访孝悌儒术等诏.商务印书馆,1959.(P518)。唐高宗《补授儒官诏》提出“业科高第景行淳良者”[7]全唐文(卷十一)·补授儒官诏.中华书局,1983.(P141)才堪充学官。唐代宗下令“学官委中书门下,选行业堪为师范者充”[8]旧唐书(卷十一)·代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P282)。唐宪宗元和元年(806)敕书规定:“国子监祭酒司业及学官,并先取朝廷有德望学识者充。”[9]全唐文(卷六十三)·改元元和赦文.中华书局,1983.(P673)唐穆宗时下令“天下诸色人中,有能精通一经,堪为师法者,委国子祭酒访择,具以名闻,将加试用”[10]全唐文(卷六十六)·南郊改元德音.中华书局,1983.(P703)。
所谓“淳儒”“儒术该通”“学识”“精通一经”均是从对儒家经典的掌握角度提出的要求,即“才”的方面。所谓“老德”“景行淳良”“德望”均是从学官的德行方面提出的要求,“行业堪为师范”“堪为师法”则是对学行标准的概指,要求才学、道德修养达到堪为人师的程度,那么什么水平才算得上“可为师范”“堪为师法”呢?实际上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德、才水平的具体规定又是不同的。但是任何一个时代对于学官的才德两项都未曾制定过一个固定的标准,因为所谓的博学与道德高尚只是一个相对的东西,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标杆来衡量,尤其道德更不是一个可以硬性规定的东西。因此唐代大多数选拔学官的诏令常常都是含混其词、笼而统之,但这种标准在人们的观念中又似乎达到了一种社会共识的程度。
如上所述,除了一般官员选任所的身、言、书、判标准之外,唐代学官还有“德望”“才高”两个标准,即在知识方面要学识精博,品行方面要具备较高的道德修养。唐代学官为什么会有特殊的选任标准?关键在于学官的身份特殊。在封建时代,学校是为国家培养后备官员的基地,学官不仅担任教师的角色,本身还是朝廷的官员,而且在这双重角色之中,官员的身份又是第一位的。因为无论学校存在与否,教师的职能履行与否,学官作为朝廷官员的职位都始终存在,都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家事务。对于学生来说,学官不仅代表着儒者的形象与个人的修养,更代表着官员的形象,是学生最早、最多接触的官员,他们的品行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这一层面来讲,学官又是国家后备官员培养的活样板。因此,学官不仅背负着知识传承的责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国家后备官员的品行素质,因此统治者对学官的任用相当重视。《册府元龟》总结道:“自汉承秦弊,宗尚经术,求稽古之士,重学官之选。历代而下,虽废置或异,而授受之际未尝轻焉。观其延登鸿硕,优隆体貌,崇其位著,厚其禄廪,岂徒冗大官之食重高门之地而已。亦将以发挥典籍,申明治具,顾有益于风教耳。非夫大雅宏达,博闻强识,究先王之法言,蕴专门之素业,式可莫二籍甚有闻,即何以称法师之望,恢教授之业,敷畅先儒之微旨,诱掖方来之俊士,以丹青帝载而化民成俗者哉。”[1]册府元龟(卷五百九十七).学校部·选任.中华书局,1960.(P7159)自汉代以来各朝代都对学官的授受给予了高度重视。唐代规定:“凡祭酒、司业,皆儒重之官,非其人不居”[2]通典(卷二十七)·职官.中华书局,1998.(P765);唐宪宗时进一步提出“国子监祭酒司业及学官,并先取朝廷有德望举职者,充东都国子监诸馆”[3]唐大诏令集(卷五)·改元元和赦.商务印书馆,1959.(P29),学官宁缺而毋滥,重在得人。
二、唐代学官选任标准的浸变
1.唐代后期学官德才标准的要求都有所降低。
纵观有唐一代,学官选用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往往与要求不符。大体看来,唐玄宗以前,除了武则天称制与中宗韦后掌权的这一段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对于学官的选用有着以统治者喜好为转移的情况外,其他大多数时期学官的选用仍然是比较严格低遵守着“先乎德行,德均以才”的标准。安史之乱以后虽然学官的选任标准未改,但是对德才的要求却有降低的趋势。安史之乱以后,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动,官学教育的衰落,学官的选任甚至出现某些时候不依照标准进行的情况[4]这一点参见拙文.浅析唐代国子祭酒的选任变化.贵州文史丛刊,2005,(3).此处不予赘述.,学官的选任标准也出现比唐初降低的趋势。虽然统治者一再强调学行并重,可是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由于某些原因,而偏废某一方面,甚至出现了两个标准都不符合的学官。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刘蕡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唐文宗亲自策问举人,帝引诸儒百余人于廷,出策曰:“太学,明教之源也,期於变风,而生徒惰业。”刘蕡对曰:“生徒惰业,繇学校之官废”,“盖国家贵其禄,贱其能,先其事,后其行,故庶官乏通经之学,诸生无脩业之心矣。”[1]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八)·刘蕡传.中华书局,1975.(P5293,5304)当然这是考试中皇帝假设的命题,不免夸大其词,但刘蕡的应对却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即国家任用学官不重视德行,且官员缺乏通经之才。虽然,唐代后期的统治者一直努力重振官学声望,无奈限于客观历史条件,学官的选用标准仍然无可挽回地降低了,起码从诏书反映的内容看是如此。目前所见有关唐中后期学官选任标准的史料如下:穆宗长庆元年(821)《南郊改元德音》与《长庆元年册尊号诏》均授权国子祭酒从各色人等中访求能“精通一经,堪为师法者”擢为学官[2]全唐文(卷六十六)·穆宗皇帝·南郊改元德音.中华书局,1983.703“两汉用人,盖先经术。天下诸色人中,有能精通一经堪为师法者,委国子祭酒访择,具以名闻,将加试用。”唐大诏令集(卷十)·长庆元年册尊号诏.61.“天下诸色人中,有能精通一经、堪为师法者,委国子祭酒访择”。。其后敬宗宝历元年(825)《南郊赦文》也规定:“天下诸色人中,有能精通一经,堪为师法者,委国子祭酒选择,具以名奏。”[3]全唐文(卷六十八)·敬宗皇帝·南郊赦文.中华书局,1983.(P720)这几则诏令无一例外,均表达了中央政府对于学官任用的关注,但同时也都明确了学官任用的标准,即凡精通一经,堪为师法者即符合条件。这项要求与唐前期“尽招天下淳儒老德以为教官”“业科高第景行淳良者”以充学官的标准相比,对儒经掌握程度的要求有着明显的降低,从淳儒、业科高第放宽为通一经,并未对通的程度有过高的要求;从政令本身看来德行方面的要求似乎也有弱化的趋势。可见,唐后期对学官德才的要求有着明显的降低,且德一才二的顺序似乎发生了逆转,出现了偏重知识考核,弱化德行考察的倾向。当然唐中后期也出现了一些以韩愈为代表的优秀学官,但这些人在安史之乱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长河中不过是众多学官中的凤毛麟角。
2.唐代后期学官任用标准发生变化。
唐前期学官选用重德行轻文辞,对德行要求高于普通官员。《唐书·选举志》“太宗时,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谨有名於当时,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不署以第。太宗问其故,对曰:‘二人者,皆文采浮华,擢之将诱后生而弊风俗。’其后,二人者卒不能有立。”[4]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中华书局,1975.(P1166)由于文辞浮华会导致风俗之弊,才子张昌龄被挡在功名场外。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学官选任对于才能的要求出现从重经义向重文辞转化的趋势。在唐代中后期世俗重文辞潮流的带动下,因文辞而得选任国子祭酒竟然成为常事,如唐文宗时,王涯在告享祖庙时向祖先夸耀次子王洁“以奇文仕至国子祭酒”[5]文苑英华(卷八百八十一)·代郡开国公王涯家庙碑.中华书局,1966.(P4647),强调奇文而非经术或道德,恰好反映了当时对于学官选用以文为重的社会认同性。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刘峣在上疏中批评了社会上重进士轻明经的风气,他讲道:“国家以礼部为考秀之门,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响应,驱驰於才艺,不务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艺者可以约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张之!至如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张学干禄,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夫人之爱名,如水之务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必敦德励行,以伫甲科,丰舒俊才,没而不齿,陈寔长者,拔而用之,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风动於下,圣理於上,岂有不变者欤!”[6]通典(卷十七)·选举.中华书局,1998.(P407)儒家历来奉行经明行修,把经学看作儒家伦理道德的载体,但是唐代重进士的风气,使人才选用普遍偏重文辞而轻德行,导致许多士人有才艺而乏德行。刘峣认为重文辞轻德行是舍本逐末的行为,只有皇帝倡导敦德励行才能彻底改变重才艺轻德行的社会风气。但刘峣一厢情愿的倡议,不但未达到力挽狂澜的功效,反而有螳臂当车之嫌。此后历代对科举选任不重德行的批评虽多,但除了重复建议恢复古代的乡举里选的意见之外,别无建树。如唐代宗宝应二年(763),以礼部侍郎杨绾为首,包括李栖筠、贾至、严武等大臣甚至提出废除科举制,恢复两汉时代察举制的意见。但历史已经证明察举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1]杨照明.抱朴子外篇校笺(卷之十五)·审举.中华书局,2007.(P393),这种选官方式只能引起士人对于德行的矫饰和虚伪,早在汉代察举制的这种弊病就已显现,杨绾等人的建议无异于痴人说梦。由于积重难返,而皇帝和百官又没有纠正科举制弊端的有效方法,致使唐代官场逐渐形成“大臣以无文为耻”[2]全唐文(卷二百二十五)·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中华书局,1983.“自则天久视之后,中宗景龙之际,十数年间,六合清谧,内峻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搜英猎俊,野无遗才,右职以精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每豫游宫观,行幸河山,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岂惟圣后之好文,亦云奥主之协赞者也。”(P2275)的共识。
这股重文辞轻德行的风潮一直延续到唐末五代,学官的任用也受到影响,有些学官出身进士,却只懂得吟诗作赋,对于儒家经典并无高深的造诣。基于此矛盾,早在唐宪宗时期就已经规定对于新上任学官严加考试的办法,元和年间韩愈上《国子监论新注学官牒》,奏请:“非专通经传,博涉坟史,及进士五经诸色登科人,不以比拟(学官)。其新受官,上日必加研试,然后放上,以副圣朝崇儒尚学之意。”[3](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八)·国子监论新注学官牒.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P637)但考试的程序、内容以及是否切实执行,我们都不得而知。唐代未能解决科举重文辞与学官重明经之间的矛盾,有“文辞”成为“才”的代名词,这与学官选任以通经义为才相左,结果社会风气动摇了学官的选任标准,使学官“才”的标准出现由经义向文辞转变的现象。
(责编:樊誉)
The Selection Standard and Variation of Educational Officersin Tang Dynasty Official
Dong Kunyu
There are two 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officers In Tang Dynasty i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e officials.Namely,these positionsrequired higher on moral and knowledge.People must have deep attainmentson the Confucian classics.In addition people must be of noble character and high prestige.But these two standard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prevalenc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changed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not only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tandard decrease,but also the focus changed from the Confucian classics gradually into the language since mid Tang dynasty.The changes of the standard of selection on educational officers exacerbate the decline of?the offici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Officers Standard Selection
董坤玉(1979—),河北沧州人,博士,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汉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