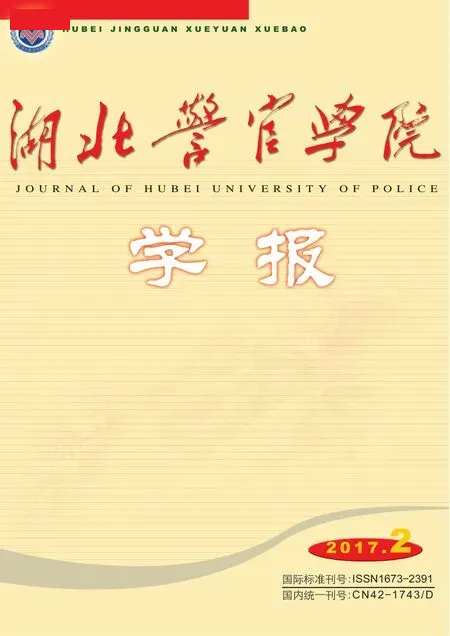死刑冤假错案证据问题之实证研究
吕泽华,贾宜臻
(1.青岛大学 法学院,山东 青岛266071;2.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250000)
死刑冤假错案证据问题之实证研究
吕泽华1,贾宜臻2
(1.青岛大学 法学院,山东 青岛266071;2.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250000)
从实证角度出发,以“生效判决曾被判死刑(含死缓)而再审后改判无罪”为标准筛选出19起死刑冤假错案,运用案例统计分析的方式,对样本案例中暴露出的被告人供述虚假、鉴定活动非法、证人证言真实性存疑、关键物证缺失、辨认出现误认、审讯录像存在造假等证据问题进行类型化分析可知,死刑冤假错案证据问题之成因在于严重的刑讯逼供导致被告人供述的虚假性、盲目轻信及制度缺陷导致鉴定乱象丛生、暴力取证及立法瑕疵影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证据搜集不充分导致关键物证缺失、程序违法及瑕疵导致辨认出现误认、电子证据规则的缺失导致审讯录像未规范化使用。应规范口供取证程序,完善鉴定体制设计,健全证人出庭相关立法规定,增强辨认过程的程序性,修正侦检部门协作机制瑕疵,完善电子证据规则,严格死刑案件证据制度,提高死刑案件质量,构建死刑冤假错案的预防和纠正机制。
死刑;冤假错案;非法证据;刑讯逼供;电子证据
诸如DNA之类的科技证据的司法应用,“疑罪从无”理念的逐步确立,“控制死刑适用”的诉讼程序改造以及网络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冤假错案问题成为近年来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和司法难题。其中,死刑案件更以其错误的不可挽回性令人侧目。死刑冤假错案实质上就是事实认知上的错误,归因于司法证明的证据问题,虽然学界对其进行过广泛的研究,但大多集中于个案的特殊性研究,死刑证明标准的单一性研究以及对刑讯逼供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个别化研究。这些研究趋于概括性、抽象性、指导性,缺乏具体的可操作规范的制度构建,更缺乏对相关案例的系统性、总结性分析,没有赖以依托的实证数据。从实证角度研究死刑冤假错案,结合死刑冤假错案中的多样证据问题进行特殊性、多角度分析,有利于细化相关法律规范,更有效地指导司法实践,进一步完善死刑冤假错案的预防和纠正机制。
鉴于网络媒体的便捷性和广博性,本文案件素材基本上来自网络媒体,主要以“中国冤假错案网”为主。从2016年12月10日至2017年1月12日,笔者从该网站所列出的146起冤假错案中,以“生效判决曾被判死刑(含死缓)而再审后改判无罪”为标准,筛选出19起死刑冤假错案。①以下案件及案情若无特别说明,均来自“中国冤假错案网”http://www.zgyjca.com,2016年1月15日访问。通过对样本案例中凸显的证据问题进行总结性分析,把相应的证据问题归纳为被告人供述虚假、鉴定活动非法、证人证言真实性存疑、关键物证缺失、辨认出现误认、审讯录像存在造假等六个方面,在类型化分析的基础之上重点研究证据问题的相关解决方法,以期有更多潜在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司法公正得以实现。
一、死刑冤假错案的证据问题现状分析
通过对19起冤假错案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有六类证据问题,各自占比为:被告人虚假供述(100%)、鉴定活动非法(68.4%)、证人证言真实性存疑(36.8%)、关键物证缺失(26.3%)、辨认出现误认(15.8%)、审讯录像存在造假(10.5%)。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19起死刑冤假错案证据问题分析
(一)被告人供述虚假
此类现象的发生比例是100%。学界也就此达成共识,被告人虚假供述已经成为死刑冤假错案的第一大证据问题。有学者根据产生的原因将口供分为“自愿型虚假口供”和“外因诱发型虚假口供”两种类型。[1]而从虚假供述的表现形式来看,笔者从统计概率角度分析,认为存在三种形式:编造不存在的犯罪事实(100%);口供反复、多次翻供(31.6%);指认现场出现伪造现象(0.05%)。
口供编造行为是指被告人出于躲避严重的刑讯逼供、减轻“罪责”等不同动机,进行与案件事实不符的虚假表述。这是被告人虚假供述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如在陈琴琴案中,其曾遭到同监女犯的哄骗,为了“早日出狱“而进行虚假供述。口供反复、多次翻供行为作为虚假供述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表明确实存在虚假供述的可能性,但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却仅将这种矛盾现象视为犯罪嫌疑人的狡辩。犯罪嫌疑人指认犯罪现场也属于对其犯罪事实的描述,但此类情况并不典型,只在张辉叔侄案中出现过,主要表现为警方控制指认现场,被告人完全按照警方所述情况进行虚假指认。
(二)鉴定活动非法
鉴定问题作为样本案例中的第二大证据问题,所占比例为68.4%,存在四种表现形式:鉴定水平低下(53.8%);鉴定程序未正常启动(30.8%);鉴定检材不合规(30.8%);鉴定主体不合法(15.4%)。
鉴定水平低下是指在鉴定过程中采用的技术水平较低,以至于得出的鉴定意见并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这类情况主要存在于DNA鉴定之中。由于DNA鉴定的技术依赖性较强,且其应用于诉讼需经历多个阶段(如检材的取得、保管、分析等阶段),只要在一个阶段出现瑕疵,就会降低DNA鉴定的准确性。所以,DNA鉴定的准确性需要高科技水平予以保障。[2]但是,在7起案件中,由于技术水平有限,DNA鉴定出现重大失误,影响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认定。如在魏清安案中,本应采用9个位点进行DNA鉴定,最终却只采用了4个位点。这种低水平鉴定根本不能确定魏清安为犯罪行为人,只能认定他存在作案嫌疑。
以鉴定检材为分类标准,鉴定主要分为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及声像资料类鉴定。[3]鉴定程序未正常启动是一种消极的鉴定活动非法现象,主要出现在物证类鉴定方面,即虽提取了与案件相关的关键物证,如指纹、毛发、血液或精液,但却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的鉴定和检验。这种做法有隐匿证据之嫌,且违背法定程序。
鉴定检材不合规是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的鉴定材料,如受到污染、涉嫌伪造或来源不明。科学的鉴定意见应建立在合规的检材之上。检材不达标,鉴定意见就丧失了真实性和同一性。即使运用高超的鉴定技术,也不能得出正确的鉴定意见。如在念斌案中,铝壶无毒但盛放于其中的水却有毒,且提取铝壶的时间比正常情况延迟达13天。这种不合逻辑的情况即属于鉴定检材来源不明。[4]
鉴定主体不合法是指相关的鉴定人员不具有法律规定的鉴定人资质。我国鉴定人员必须具有与鉴定业务相关的专业技术职称、专业执业资格或本科以上学历,同时还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且没有受过刑事处罚或被开除公职处分。但是,在相关案件中却出现了无鉴定资格人员进行鉴定的情况,如要求农机厂工人进行鉴定,导致鉴定意见缺乏专业性和准确性。
(三)证人证言真实性存疑
在19起案件中,共有8起案件的证人证言在证据真实性方面出现问题,所占比例达到42.1%。这8起案件主要有以下四种表现形式:编造证言(37.5%);证人证言反复矛盾(12.5%);证人未出庭质证(12.5%);猜测性证人证言作为证据使用(12.5%)。由于前两种表现形式与被告人虚假供述的相关表现基本一致,此处不再赘述,但这种编造、反复矛盾现象也反映出言词证据的不稳定性。下文主要对后两种表现形式进行分析。
证人未出庭质证现象在样本案例中表现得并不典型,仅出现在萧山5人抢劫案中。此案中,证人都没有出庭质证。这种质证流于形式的现象不符合我国已经确立的程序法定规则和质证规则。
此外,意见证据规则确立了猜测性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在萧山5人抢劫案中,猜测性证言却被作为定案依据使用。此案中,证人声称见过三个男子,但只对这三个男子进行了“一般性”描述,并说“大概”是陈建阳(5人抢劫案中的1人)等人。“一般性”“大概”等词语明显带有猜测性语气。根据意见证据规则,此类证据不应予以采信。
(四)关键物证缺失
关键物证缺失是指侦查人员没有遵循程序法定原则,未按法定程序全面搜集相关物证。共有5起案件出现了这种情况,所占比例为26.3%。关键物证缺失存在两种表现形式,分别是缺少作案工具(40%)以及无任何物证仅以口供定案(60%)。
作案工具通常是一种关键性物证,因为犯罪嫌疑人的指纹、血液、手印等易依附在上面,通过DNA鉴定即可鉴别犯罪嫌疑人身份。另外,还可以通过物质交换原理确定受害人身体的伤痕形状和作案工具的形状是否吻合。所以,作案工具具有重要价值,理应成为办案人员重点收集的证据。可是,在徐辉案和萧山5人抢劫案中却存在无作案工具就定案的现象。
无任何物证现象则属于更为极端的做法,张辉叔侄案、覃俊虎案及陈满案中都曾出现。在张辉叔侄案中,警方未找到任何关键性物证。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单凭口供不能定案。但该案就是在无任何物证的情况下仅依口供定案,完全不符合法定要求。
(五)辨认出现误认
根据辨认对象的不同,辨认可以分为人身辨认、照片辨认、物品辨认、场所辨认以及尸体辨认,[5]而辨认误认问题主要出现在人身辨认(33.3%)和尸体辨认(60%)中。
在人身辨认方面,主要问题是间隔时间过长,准确性差。在3起案件中,有1起案件(魏清安案)即缘于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辨认错误,所占比例达到33.3%。在魏清安案中,案发40多天之后被害人才进行辨认,此安排相当草率。相关研究显示,已有的记忆痕迹通过反复练习才会保持,否则就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衰退。当被害人回忆案发情形时,其心灵将再次经受折磨。为避免这种痛苦的记忆反复出现,被害人会刻意压抑这种信息在意识中再现,因而更容易形成遗忘。[6]所以,辨认活动距离案发时间越长,辨认的准确性、真实性就越容易下降。
在尸体辨认方面,主要问题在于程序性不足,辨认草率,60%的辨认错误案件(滕兴善案、赵作海案)都出现了此类问题。样本案例中的尸体辨认针对被害人尸体,且辨认主体基本为被害人亲属。除魏清安案和宋庆芳案之外,17起案件本质上都属于杀人案件,被害人都已经死亡。尽管被害人亲属与被害人共同生活时间较长,对被害人体貌特征比较了解,但在尸体高度腐烂的情况下,其很难用肉眼辨别被害人的身份。在赵作海案中,在对被害人尸体四次DNA鉴定无果的情况下,仅凭被害人亲属的一面之词就确定了被害人身份。这种草率的辨认程序没有考虑到尸体本身的情况以及被害人亲属的情绪状态,容易造成误认现象。
(六)审讯录像存在造假
审讯录像可以用于证明讯问过程的合法性,遏制非法取证行为。也正是由于这种特质,其易成为非法取证行为的造假对象。在19起案件中,只有2起案件的相关资料明确指出了审讯录像的问题,分别是陈琴琴案和张辉叔侄案,所占比例为10.5%,且均存在“图像模糊,音质不清,不完整”等表述。审讯录像可以归为电子证据,审讯录像造假现象也反映出电子证据鉴定规则的空白。
二、死刑冤假错案的证据问题成因分析
(一)严重的刑讯逼供导致被告人供述的虚假性
“尽管刑讯逼供并非百分之百地导致错判,但几乎百分之百的错案都是由于刑讯逼供所致。”[7]封建时期“无供不录案”及“罪从供定”思想促使“口供中心主义”的形成,加上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刑讯制度的影响[8]滋生了刑讯逼供,后者给被告人带来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最终导致虚假供述的产生。虽然我国对于“口供中心主义”进行了立法规制,①《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且在刑法上设立刑讯逼供罪以形成威慑,但遏制刑讯逼供的可操作性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
(二)盲目轻信及制度缺陷导致鉴定乱象丛生
总体来看,主客观两方面原因促使非法鉴定现象产生。从主观方面看,由于鉴定意见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司法人员易产生盲目轻信的心理,导致对鉴定意见的合法性审查和质证过程容易流于形式,鉴定主体、检材等合法性问题难以被及时发现。
从客观方面看,关于鉴定意见的体制设计还不够完善。虽然《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首次明确了非法鉴定意见的具体排除规则,对鉴定意见的证据资格审查作出了具体规定,极大地推动了相关证据立法的发展,[9]但从前文所述非法鉴定现象来看,《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仍不够详细:
一方面,缺乏完善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资质的实质性审查机制。我国立法已对鉴定机构以及鉴定人的资格进行了原则性规定,为鉴定行业树立了统一标准。但是,我国的资质审查仍停留于形式审查层面,且对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审查标准没有进行细致规定,导致实质审查机制无法落到实处,易引发低水平鉴定,违背立法初衷。
另一方面,鉴定人及鉴定机构的中立性无法得到保障。公检机关内设鉴定机构易导致侦查机关垄断性鉴定,无法保证鉴定人的中立性,其出具的意见也易沦为“侦查附庸”。另外,由于侦查机关掌握了鉴定启动权,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被赋予独立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利,在该鉴定却未鉴定时,辩方也无能为力。
(三)暴力取证及立法瑕疵影响证人证言真实性
暴力取证行为的“暴力”取广义概念,包括“威胁,恐吓等与该暴力程度相当的任何非法方式”。在19起死刑冤假错案中,有3起案件出现了暴力取证行为,直接导致证人证言的编造及反复矛盾现象。我国立法禁止采用任何非法形式获取证人证言,但只停留于原则性规定层面,而没有更为具体的规范。
此外,在立法层面,《刑事诉讼法》虽然已经建立了证人质证制度,但相关规定仍存在一定瑕疵。实践中证人出庭率较低,质证过程趋于形式化:
其一,证人出庭作证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①《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无形中提高了出庭作证的门槛。其中,法律没有对“重大影响”中的“重大”作出明确解释,增加了适用的模糊性。最后一个条件中的“有必要”表明条件是否满足由法官衡量,扩大了法官的裁量权。
其二,免除被告人亲属的出庭义务也许是出于中国式人情的考虑,但实际上,被告人亲属一般是最了解犯罪嫌疑人或最先知道案件情况的人,他们的证言有很高的价值。一概取消其出庭作证的义务可能会丧失了解真相的机会。
其三,证人出庭保障的相关规定存在漏洞。一方面,在人身保护机制方面存在缺陷。在19起死刑冤假错案中,除了魏清安强奸案和宋庆芳运输毒品案,其余17起冤假错案都是恶性故意杀人案件(强奸、抢劫),占全部案件的89.5%。我国虽然存在对证人的人身保护机制,但适用的案件范围较窄,只集中于四类案件。②即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恐怖主义案件、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及毒品案件。普通的杀人案件证人出于恐惧报复心理,只能采取不出庭作证的方式保护自己。且我国只对事后打击报复行为予以惩罚,没有建立事前防御性保护机制。另一方面,出庭作证经济补偿制度有待细化。《刑事诉讼法》已基本明确证人出庭的经济补偿制度,即证人出庭的相关费用(如交通费、住宿费、就餐费等)应当纳入司法机关的业务经费,且必须由政府财政保障。但是,依照何种标准进行费用补助,立法上还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对证人的经济补偿很难落到实处。
(四)证据搜集不充分导致关键物证缺失
物证缺失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侦查阶段证据搜集不充分,侦查人员缺乏全面搜集证据的能力,其次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不善于发现被遗漏的、需要提取鉴定的实物证据,未能督促侦查机关进行补充提取及鉴定,从而导致在侦查阶段缺失的物证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和搜集,最终造成实物证据不足、达不到证明标准就定案的现象。
一方面,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轻视实物证据,搜集证据能力欠缺。在实证调查的刑事冤假错案中,言词证据出现的问题是最多的:被告人供述、鉴定意见和证人证言的问题数量排在前三位。正是由于侦查人员重视获取言词证据,才催生了针对言词证据的各种非法取证行为,这一现象从侧面反映出侦查阶段对实物证据的忽视。由于主观上轻视实物证据,侦查人员在搜集实物证据时存在消极懈怠心理,不利于全面搜集物证。另外,技术能力的欠缺对于全面保存固定证据非常不利,也会导致关键物证的缺失。由于接触案件的大多是基层公安机关,技术力量比较薄弱,对一些需要运用特殊技术进行提取保存的证据,如指纹、脚印等,难以维持其原来的状态,从而使已经搜集到的证据灭失或者丧失完整性。
另一方面,在审查起诉阶段,公检法之间的“相互配合”,检察院过分依赖侦查人员搜集的证据,没有尽到补充搜集证据的责任,导致未达到证明标准就审查起诉,给法院审判带来很大麻烦。所以,公检机关之间要加强在取证方面的沟通,并充分发挥补充侦查的作用,尽量确保搜集证据的充分性。
(五)程序违法及瑕疵导致辨认出现误认
辨认多在侦查阶段进行。法官不能见证辨认过程,只能依靠对笔录的书面审查鉴别辨认程序的规范性。这种书面审查方式使法官无法及时发现辨认过程中的程序违法及程序瑕疵现象,加上我国辨认程序不是特别完善,导致辨认笔录的真实性易受到不良影响。另外,我国法律虽然确立了辨认笔录的基础性规范,但对辨认程序的公正性和真实性关注较少,导致辨认程序的相关制度设置并不完善,影响了辨认结论的准确性。
我国辨认程序的设置主要有以下几点缺陷:一是没有全程录像制度,整个辨认过程无法直观反映在法官面前。二是没有健全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制度。我国对于辨认过程中见证人在场没有进行强制规定,而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规定也不统一,辨认过程缺乏有效监督。三是没有及时组织辨认的规定。辨认环节距离案发时间太长,容易使辨认不准确。辨认包括感觉、记忆、辨识三个阶段,人的大脑时刻都在对记忆进行修缮,所以,在辨认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错误。距离产生真实记忆的时间越久,这种修缮就越多,导致最后的辨认结果可能出现错误。[10]
(六)电子证据规则的缺失导致审讯录像未规范化使用
我国有关电子证据的规定过于原则化,缺少相关的鉴真原则。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电子证据和视听资料并行列举于法定证据种类,确立了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但这种规定方式易混同电子证据和视听资料,从而产生所谓的“电子视听证据”,[11]导致电子证据无法构建自身的证据规则体系。除了定性问题,关于电子证据的规定较原则化、零散化,缺乏统一性。实证研究中出现的审讯录像造假问题就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电子证据鉴真规则的不足以及电子证据技术鉴定不到位。
三、死刑冤假错案预防与纠正机制的构建
(一)规范口供取证程序,遏制刑讯逼供行为
一方面,可从以下两处着手,从立法层面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第一,废除“如实回答”义务。此规定易为非法取证行为提供“合理化依据”,助长这种非法行为的发生。第二,顺应国际趋势,建立沉默权。沉默权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承认,但我国没有赋予被告人这项权利,不利于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沉默权源于人的尊严,犯罪嫌疑人拥有不被拷问、强迫供述的权利和自我决定是否供述的权利,也有放弃或恢复沉默权的自由。在确立沉默权的同时,应该明确沉默权的内容:且此项内容应当是综合性的,不应该过多加以限制。当犯罪嫌疑人行使沉默权时,不能对其做不利推定,同时也不能将这种行为作为对被告人量刑时不利的要素。”[12]
另一方面,完善相关制度设置,在讯问前、讯问中、讯问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全方位保护,保障其合法权利,规范口供取证程序:
第一,建立侦押分离制度,作为讯问前的预防性保护机制。在司法实践中,侦查和羁押基本上都由公安机关掌控,大大增加了超期羁押和刑讯逼供的可能性。针对此类问题,可以尝试将看守所交由司法局管理,区分侦查和羁押的管理机关,尽量排除超期羁押的可能性。
第二,建立律师在场制度和强制性录音录像制度,作为讯问过程中的合法性保障机制。律师在场制度使律师参与整个讯问过程,对侦查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及时发现取证程序的违法之处,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保证该制度的实施,可在讯问笔录上增设“辩护律师”一栏,并由在场律师签名并亲笔书写“我已参加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过程”。辩方发现笔迹有伪造嫌疑的,可以申请笔迹鉴定;如果确有伪造,之前的讯问笔录由于也不得作为定案依据,且相关人员应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另外,应建立强制式同步录音录像制度。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只把审讯录像作为控方应提供的选择性证据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一般不会出示审讯录像或者根本不会进行录像,法官也无法得知审讯时的真实情况。在立法上应该明确规定审讯录像为证明讯问合法性的必备证据,从而有效适用羁押讯问时录音录像制度,同时限制非法取证行为。
第三,建立完善的人身检查制度,作为非法讯问的事后救济性机制。立法上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自主申请身体检查的权利,且不受侦查机关的非法阻挠。为防止身体检查证明造假,身体检查工作应该由独立于侦查机关的医疗机构进行,且在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期间也要定期进行复查,防止刑诉逼供之后伤口痊愈无法检查。
(二)完善鉴定体制设计,保障鉴定意见合法性
第一,完善司法鉴定标准体系,引进“实质证明标准”规则,使鉴定意见的审查有据可依,逐步消除司法人员的主观轻信心理,建立依法办事的法律意识。为了统一相关事项的鉴定标准,应该由主管鉴定机构的司法行政机关出台统一细化的鉴定标准。之后,司法行政机关应加强监督。鉴定机构需将鉴定意见报司法行政机关备案,由专门的鉴定监督人员进行审查;如不符合相应的鉴定标准,则处以罚款等处罚措施,从而强化鉴定的程序性。另外,对于缺乏鉴定标准的相关鉴定事项,应当引进实质证明标准,运用经过实质性验证的规则、学理、常识对相关鉴定事项提出质疑,[13]从而有效强化对鉴定意见的质证,保障鉴定意见的真实性。
第二,建立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实质性资质审查机制。为科学评定鉴定人及鉴定机构的资格,严格准入机制,我国有必要以立法的形式建立实质性资质审查机制,明确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审查标准等,尽量消除非法鉴定现象。
第三,建立侦鉴分离体制和必要鉴定制度,保障鉴定机构中立性。为保障内部鉴定机构的客观性,有必要对内部鉴定机构和有侦查权的部门进行明确的职权划分,使侦查机关内部的鉴定人员不再参与相应的侦查工作,而仅作为一个中立方作出客观真实的鉴定意见,从而逐步消除鉴定人既承担侦查工作又进行鉴定的现象,实现侦鉴分离。另外,为改变鉴定机构的“侦查附庸”地位,遏制侦查人员对鉴定启动权的滥用,还需要逐步建立必要鉴定制度,即法律明文规定必须进行鉴定的某类案件或情形,相关办案人员无裁量权。[14]这类案件应是涉及面广、社会危害性大或情节极其恶劣的案件,且鉴定材料对于侦破案件具有重大意义,如强奸案中的精液、杀人案中的血迹或指纹等。
(三)健全相关立法规定,保障证人证言真实性
对于暴力取证问题,可以借鉴前文遏制刑讯逼供的制度设计,在立法层面尝试建立律师在场制度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对侦查人员询问证人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
另外,针对相应的立法瑕疵,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在立法方面,减少相关限制性规定,进而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质证是所有证据的必经阶段。只有通过质证,才能对该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资格进行准确判断。证人证言属于言词证据,只有在证人出庭的前提下,才能够对证人证言进行有效认定。如果缺少这一环节,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就很难予以保障。所以,立法不应对证人出庭质证附加过多的限制性规定。只要控辩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对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存有异议,证人都必须出庭作证,而无需考虑该证言对整个案件的影响程度。另外,立法上应该废除“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的规定,限制法官裁量权,从而减弱法官对于质证环节的控制。
第二,对于被告人亲属“免于出庭作证”的特权,可以尝试把被告人的亲属和普通证人置于平等地位,逐步收回被告人亲属“免于出庭作证”的特权,从而真正对案件事实有全面的了解。
第三,建立事前防御性保护机制,完善事后保障机制,弥补相关法律漏洞。一方面,建立事前防御性保护机制,即将人身保护的时间提前,只要该证人有出庭作证的可能性(不要求在后续程序中真正出庭作证),且有合理理由认为自身安全可能面临危险并提出保护请求,公检法就必须实施有关保护措施。另外,人身保护措施适用的案件范围需要扩张。在司法实践中,证人惧怕报复通常出现于严重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情节恶劣的案件以及涉及犯罪集团的案件之中。立法者可选出具有以上特点的案件列入人身保护的案件范围,而不仅限于前文所述的四类案件。另一方面,我国已经确立了出庭补偿机制,但缺乏可操作性的准则,应建立详细的出庭补偿标准。为了健全相关的证人出庭补偿制度,可以借鉴民事诉讼相关司法解释的标准,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证人因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按照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差旅费用和补贴标准计算,误工损失按照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结合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具体情况,细化证人补偿标准,完善出庭补偿制度。
(四)修正侦检部门协作机制瑕疵,全面搜集相关物证
关键物证的缺失一方面反映出我国侦查人员搜集证据能力较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侦检部门在取证方面的协作机制不够完善,故应从这两方面着手,逐步消除此类现象。
一方面,提高侦查人员的综合业务水平。因“管理不善”造成证据被破坏或丢失,反映出我国侦查人员搜集和保管证据能力低下。针对这类问题,应定期举办专业知识培训活动,提高侦查人员的综合业务水平,特别是提高基层公安机关的录取门槛,尽量解决侦查人员能力不足的问题。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补充侦查程序的作用,加强取证方面的交流沟通。除了审查职能,检察院本身还负有补充遗漏证据的义务。在对证据的审查过程中,应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公检机关之间的交流沟通,尽量保障证据搜集的充分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司法解释曾指出,可以采用联席会议制度等形式加强与侦查机关的沟通,还有一种沟通形式就是充分运用补充侦查。“当检察院认为需要补充侦查完善证据时,不仅要向侦查机关具体列出补充侦查完善证据事项,还应在补充侦查提纲上详细说明完善证据的理由并提供补充相应的完善方向、线索和对象,以解决死刑案件补充侦查难的问题。”[15]通过加强与侦查人员的交流,可以进一步完善证据,逐步解决遗漏证据的问题。
(五)完善配套制度,增强辨认过程的程序性
辨认过程的相应立法规定趋向零散化、原则化且存有一定的瑕疵,没有形成完善的程序保障体系,导致最终取得的辨认笔录缺乏真实性。有必要通过制度设置保障辨认和鉴定过程的规范性:第一,建立辨认过程全程录像制度。美国学者通过研究指出,在录像缺失的情况下,辨认过程中出现的提示或暗示在一段时间之后都无法得到重构。[16]录像资料能够真实反映当时辨认的客观情况。当双方对辨认程序的合法性意见不一时,法官可以通过录像资料进行直观判断,从而有助于对辨认笔录的真实性进行认定。第二,完善见证人在场见证制度。辨认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侦查人员不当暗示的现象。为了避免这种行为,见证人的监督十分必要。我国应该建立强制见证制度,发挥见证人的监督作用,保障辨认程序的合法性。第三,建立及时辨认制度。前文已述,鉴于记忆的修缮以及正常衰退轨迹,被害人的记忆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时间的影响,所以必须在案发之后的较短时间内及时组织辨认。立法应根据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合理规定辨认期限;如果未在法定期间内组织辨认,辨认笔录即为瑕疵证据,由法官裁量决定是否予以排除。
(六)完善电子证据规则,加强审讯录像鉴真
证据规则的完善能够对相关证据的证据资格及证明力的认定起到很大作用,并且可以为证据的审查提供相应标准。针对实证研究反映出的电子证据使用问题,我国有必要完善相关证据规则。
电子证据因其形式和介质的特殊性而极易被伪造,且这种伪造的可能性与技术发展水平成正比,其真实性很难进行认定。为了加强对电子证据的鉴真,有必要建立技术鉴定原则。技术鉴定原则是指对于电子证据是否涉嫌伪造进行专业技术鉴定,进而及时发现电子证据中存在的问题。[17]该原则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利用人的感官无法识别该证据的真伪时,必须请求对其进行专业技术鉴定,进而排除涉嫌伪造的证据,避免伪造的电子证据误导侦查视线,从而保障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另外,在司法实践中,基层办案机关请求进行电子证据鉴定的程序过于繁琐,花费时间较长,不利于第一时间调取证据。为了简化相关程序,可以利用大数据优势,建立云计算架构,完善电子证据的远程鉴定,也可逐步扩大电子证据鉴定机构的数量。通过以上措施,可以及时辨别电子数据的真伪,更好地保障电子证据的真实性。
[1]刘品新.刑事错案的原因与对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239.
[2]王志刚.论DNA证据的鉴真[J].证据科学,2015(3).
[3]陈瑞华.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问题[J].中国司法鉴定,2011(5).
[4]法治周末.念斌投毒案,有多少悬疑等待破解?[EB/OL].http:// www.legalweekly.cn/index.php/Index/article/id/721.html,2016 -01-10.
[5]韩旭.辨认笔录证据能力问题研究——以刑事诉讼法为视角[J].证据科学,2012(2).
[6]兰跃军.被害人辨认错误及其防范[J].证据科学,2014(5).
[7]查洪.浅谈我国刑事错案的预防——基于证据视角[J].科学导报, 2015(18).
[8]张定乾.对赵作海案的深层思考——拷问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的原则之“严禁刑讯逼供”[J].网络财富,2010(16).
[9]沈臻懿.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3条的诠释与解读[J].犯罪研究, 2011(2).
[10]王晨光.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与“错案追究制”的误区[J].法学论坛,1997(3).
[11]墨九.录音录像等电子视听证据的法律效力[EB/OL].http:// law.shangdu.com/b/a/falvanjian/2012/0315/33383,html.2016-03 -15.
[12][日]田中守一.刑事诉讼法[M].刘迪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88-89.
[13]郑谊英.我国司法鉴定证据规则的缺失及完善建议——基于呼格吉勒图案的反思[J].湘潭大学学报,2015(5).
[14]李玉华,杨军生.司法鉴定的诉讼化[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206-207.
[15]蒋光泽.死刑案件检查环节证据审查判断和运用调查分析[J].人民检察,2013(12).
[16]张丽云.刑事错案与七种证据[J].北京:法制出版社,2009:109.
[17]樊崇义,李思远.论我国刑事诉讼电子证据[J].证据科学,2015(5).
【责任编校:王 欢】
Empirical Research on Evidence Problems of Unjust and Erroneous Death Penalty Cases
Lyu Zehua1,Jia Yizhen2
(1.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 266071,China;2.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Starting from the empirical point of view, 19 unjust and erroneous death penalty cases have been selected with the standard of "the effective judgment was sentenced to death (including reprieve) but retrial innocence", we used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of cases, and analyzed evidence problems of sample cases, such as accused false statement, illegal identification activities, witnesses and testimony authenticity doubts, key evidence lacking, identified appeared errors, trial video fraud and so on, we revealed the causes of evidence problems, such as illegal forensics behavior, identification system and legislation defects, relevant legislative defects on attendance of witness, Insufficient evidence collection, illegal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s, defects on rules of electronic evidence and so on, we looking forward to specifying the procedures of confession evidence, improving the identification system design, perfecting the legislation of witness attendance, enhancing the procedures of identification process, correcting the defects on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consummating the rules of electronic evidence and then to solve problems of relevant evidences, strictly a death penalty cases evidence system,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death penalty cases, establishing the preventive and corrective mechanism of unjust and erroneous death penalty cases.
Death Penalty;Unjust and Erroneous Cases;Illegal Evidence;Legislative Defect
D925.2
A
1673―2391(2017)02―0055―08
2016-11-06
吕泽华(1974—),男,辽宁铁岭人,青岛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证据法学;贾宜臻(1993—),女,山东聊城人,山东大学法学院2016级法律硕士(法学),研究方向为诉讼法学。
2013年度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我国补正证明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建构”(13SFB5022);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死刑控制的证据维度”(15FFX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