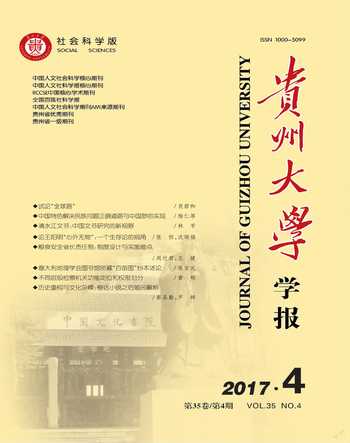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
牛磊
摘 要:
在明儒王畿的文集中,收录有许多王畿与朋友、弟子讲学论道的书信、序跋、讲会记录。在这些文章中,养生问题是王畿极为关注并经常会与友人往复讨论的一大议题。王畿对养生问题的阐释虽然经常借用道教术语,但是儒家的精神贯彻于王畿的养生实践中。性命合一而不是以命统性,实致良知而不是长生久视,才是王畿从事于养生实践的目的所在。王畿如何处理养生与阳明良知学的关系,如何处理身体保养与成德实践的关系,以及他如何在儒家与道家的养生思想之间做出区别?对这些问题的梳理有助于我们了解阳明学士人群体如何在深度汲取佛教、道教思想的过程中恪守儒家养德复性的基本精神。
关键词:
阳明心学;王畿;养生;成德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7)04-0061-07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7.04.10
“养生”一词最早出于《庄子·养生主》,庄子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保身”“全生”“尽年”若干思想。而在先秦儒家,孔子、颜回、孟子也有许多被后世学者视为养生学的言论,比如箪食瓢饮、夜气、养浩然之气等。“养生”概念的外延非常广阔,凡是根据人的生命规律而进行的物质与精神的治疗与保养都可以被视为养生。王畿养生思想异常丰富,本文拟以静坐、调息、不起意、窒欲四个子目为重点进行论述。
一、静坐
静坐是宋明理学家常用的一套为学方法,程子见人静坐便叹为好学是为我们所熟知的一例。在这一方法上,明儒与宋儒不存在太大差异,湛若水的老师陈献章便是静坐入道的典型。王阳明本人在青年时期因为体质孱弱长期坚持静坐。在龙场悟道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静坐是他教导弟子的一种重要方法。但对于静坐的态度,王阳明前后略有不同。尤其在提出致良知的观点后,他把之前的所有教法融汇在致良知这一大题目之下,对于静坐这种方法便不再像早年那样热衷地提倡了。我们可以参看阳明的一段话:“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故迩来只说良知。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炼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1]119王阳明在督滁州马政时教导学生的方法,静坐是很重要的一种。但是长期静坐而不务发明本心,便会出现喜静厌动与玄解妙觉种种弊端,所以王阳明晚年更多致力于对致良知之学的发挥。以良知为统摄,静处体悟也可,事上磨砺也可,功夫实无动静之分,所谓动亦定、静亦定。这可以看作是王阳明对于静坐的“晚年定论”。
在王阳明弟子(包括私淑弟子)中,聂豹和罗洪先似乎更以静坐而闻名。尤其罗洪先中年后服膺于濂溪主静之学,长期在石莲洞闭关静坐,为此还数次受到王畿的劝谕。对于静坐以及其背后主
静的哲学,王畿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我们先对王畿的主静观点做一说明,然后再转回静坐的内容上来。王畿对主静的解说在其文集中出现多处,随举一例:
夫主静之说,本于濂溪无极所生真脉路,本注云:“无欲故静。圣学一为要,一者,无欲也。”一为太极,无欲则无极矣。夫学有本体,有功夫,静为天性,良知者,性之灵根,所谓本体也。知而曰致,翕聚缉熙以完无欲之一,所谓功夫也。良知在人,不学不虑,爽然由于固有,神感神应,盎然出于天成,本来真头面,固不待修证而后全。若徒任作用为率性,倚情识为通微,不能随时翕聚以为之主,倏忽变化,将至于荡无所归,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疏也。[2]121
王畿本人对于主静之学持认可态度。他认为儒家主静之说,实倡自濂溪。不过他对“无欲故静”中“静”字的解法与周敦颐略有不同。依周敦颐,静即是一,一即是无欲。王畿则认为儒学有本体,有功夫。本体即是良知,而静是良知的自然狀态。“致良知”的“致”字集中体现了工夫所在,其目的在于保任良知的纯粹完美。良知本体不学不虑,出于天则,并非得之于外。“盎然出于天成,本来真头面,固不待修证而后全”一句集中体现出王畿见在良知“见在良知”是王畿学术的主要观点之一。对此问题的论述,我们可以参看他与同门刘邦采的一段对话:“先师提出良知二字,正指见在而言,见在良知与圣人未尝不同,所不同者,能致与不能致耳。且如昭昭之天与广大之天,原无差别,但限于所见,故有小大之殊。若谓见在良知与圣人不同,便有污染,便须修证,方能入圣。良知即是主宰,即是流行,良知原是性命合一之宗。故致知功夫,只有一处用。”(见《王畿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81页。)王畿同门学侣对见在良知的观念有褒有贬。比如,早年服膺于王畿之学的罗洪先,中年则在聂豹的影响之下更倾向于收摄保聚之学,从而对见在良知提出质疑。王畿则去信罗洪先说道:“盖不信得当下具足,到底不免有未莹处。欲惩学者不用功夫之病,并其本体而疑之,或亦矫枉之过也。”(同上,第236页。)本体与功夫,源头与见在,构成了王门弟子辩论极激烈的一大议题。的观点。
即天赋之良知虽不离于闻见之知,但不等同于闻见之知,它的存在不依赖于后天的修养。“任作用为率性,倚情识为通微”与阳明所批评的、久于静坐而带来“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的弊病是一致的。在静坐过程中,思虑旋起旋灭间会产生一种“窥见光景”的神秘体验。这种体验幻实相生,倏忽变化,其中大多是情识作用下的恍惚之见。如果将这种经验层面上的体悟当做学术真谛,便会陷入“荡无所归”的境地。因为此时所致得的或许并不是心之本体,而是一时兴起、过后即移的幻念。
在讨论了主静的哲学观点之后,再看静坐这种宋明时期被众多学者长期实践的身心修养方法。王畿对静坐的观点,可以以他答王遵岩的一段话作为典型例证:
遵岩子问曰:“荆川谓‘吾人终日扰扰,嗜欲相混,精神不得归根,须闭关静坐一二年,养成无欲之体,方为圣学。此意何如?”先生曰:“吾人未尝废静坐,若必借此为了手,未免等待,非究竟法。圣人之学,主于经世,原与世界不相离。古者教人,只言藏修游息,未尝专说闭关静坐。若日日应感,时时收摄,精神和畅充周,不动于欲,便与静坐一般。况欲根潜藏,非对境则不易发,如金体被铜铅混杂,非遇烈火则不易销。若以见在感应不得力,必待闭关静坐,养成无欲之体,始为了手,不惟蹉却见在功夫,未免喜静厌动,与世间已无交涉,如何复经得世?独修独行,如方外人则可。大修行人,于尘劳烦恼中作道场。”[2]10
王遵岩提问中的“荆川”是指另一位著名学者唐顺之。对于唐顺之“须闭关静坐一二年,养成无欲之体,方为圣学”的教法,王畿不以为然。他虽然不认为必须废除静坐,但是执着于此终究不是最好的办法。尤其是在静坐实践中容易滋养喜静厌动的倾向,这显然与承担社会责任和致力于济世救民的儒家实践精神有所违背。“圣人之学,主要经世”是王畿郑重提出的一个对儒家精神的基本看法。因为要主于经世,便不能作自了汉。因为要主于经世,便不能离开人伦物理来求至善。在上古三代,学者有藏修游息之学而无闭关静坐之教。如果我们在日常待人接物的生活中也能保持未发之中,正感正应,不着私意杂念,精神和心情保持饱满顺畅的状态,这与专门去闭关静坐追求的效果是没有二致的。更何况欲根私意潜藏心底,如果不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是不会暴露出来的。就像金银和铜铅混在一起,不经过一番烈火煅铸,铜铅这样的杂质是不会自己销去的。如果觉得待人接物时常因夹杂私欲而犯错,必须去闭关静坐养成“无欲之体”,这种修养方法不仅仅浪费了许多光阴与精力,而且容易养成喜静厌动之病。枯坐越久,越滞于静,越经不得世。除非不以经世为目的的宗门人物,独修独行,不与物接也无妨。真正的儒家学者则应在切实的践履中修身成德。
从王畿关于静坐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王畿培养学生的目标,并不是让学生作自我安慰的冥想家,而是让他们成为刚健有为的实践家。在“动亦定,静亦定”的大方向下,王畿更强调动的、行的一方面。从他抑静坐而倡实行的论述中,可看出致良知是王畿讲学的根本宗旨。较之闭关静坐、澄心静虑的为学方法,他更为认可念念致良知。无论是动处发扬还是静处燕居,皆可着实下手。在这一过程中既可涵养道德,又可延年养生,这才是王畿心目中的性命合一之学。
二、调息
养生术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调息。通过控制呼吸来调节身心的方法在战国时期便已流行,《庄子·刻意》便记载了“吹呴呼吸”而寿至八百的彭祖。马王堆帛书里的《却谷食气篇》也有对此方法的记录。这种功夫在深受佛道二氏影响的宋明儒者群体中尤为流行。关于调息的修养方法在王畿的文集里有多处记载,比如他答耿定理之问时说道:“调息之术,亦是古人立教权法。教化衰,吾人自幼失其所养,精神外驰,所谓欲反其性情而无从入。故以调息之法,渐次导之,从静中收摄精神,心息相依,以渐而入,亦以补小学一段功夫也。”[2]101王畿认为调息这种教学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三代远去,教化衰微,导致人们自幼便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全幅精神都扑在追逐外物上,为名利而奔波劳扰。即便偶有求之本心的想法也无从实现。所以,用调息之法使人于静中收摄精神,精神与呼吸相依而行,逐渐进入学问正途,这不失为弥补一段小学功夫。王畿对调息的看法和他对静坐的看法极为相似:以之涵养精神使之向内则可,但是过度依赖此法甚至认为不静坐、不调息便全然不能为学则不可。不过我们不可因此而认定王畿对调息法知之甚少。事实上,出于个人修养所需,王畿对调息下过一番细密的研究功夫。对此,我们可以借助他所撰写的《调息法》一文来做一了解:
息有四种,一风,二喘,三气,四息。前三为不调相,后一为调相。坐时鼻息出入觉有声,是风相也。息虽无声,而出入结滞不通,是喘相也。息虽无声,亦无结滞,而出入不细,是气相也。坐时无声,不结不粗,出入绵绵,若存若亡,神资冲融,情抱悦豫,是息相也。守风则散,守喘则戾,守气则劳,守息则密。前为假息,后为真息。欲习静坐,以调息为入门,使心有所寄,神气相守,亦权法也。调息与数息不同,数为有意,调为无意。委心虚无,不沉不乱,息调则心定,心定则息愈调。真息往来,而呼吸之机自能夺天地之造化,含蓄停育,心息相依,是谓息息归根,命之蒂也。一念微明,常惺常寂,范围三教之宗。吾儒谓之“燕息”,佛氏谓之“反息”,老氏谓之“踵息”。造化阖闢之玄枢也。以此征学,亦以此卫生,了此便是彻上彻下之道。[2]424
王畿对息做出了四种区分,风、喘和气这三种为不协调的品相,只有息为最协调的品相在佛教传统中对调息的关注与研究起源甚早,在汉代安世高所撰《安般守意经》中就有对这一功夫的详尽阐发。风、喘、气、息四相的划分,据吴震教授的研究,其思想资源可追溯至隋代智者大师所撰的《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卷上《调息第四》(吴震:《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19-321页)。在智者大师《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一书中,调息与调睡眠、调食、调身、调心共同构成了“调和第四”的主要内容,它们又与“举缘”“方便”“正修”等其余九意共同组成了天台止观法门特有的修行体系。但王畿对“调息四相”的援引并非为了宣传止观法门,而是为了实现基于良知之学立场上的、对佛教资源的吸收与融汇。在王畿《调息法》一文中,我们既可看到源自佛教传统的调息四相说,也可以看到源自道教传统的“神气相守”“息息归根”等学说。在坚持良知之学的基本精神下,王畿对佛、道二教涉及到调息方法的思想资源进行了颠倒纵横、为我所用的大胆改造。。王畿对风、喘、气、息分别作出一番解说,层层深入、渐次入微。静坐呼吸时能觉察到呼吸的声音,这属于四种调息法中的“風相”。如果觉察不到声音,但呼吸之间凝结不畅,这是“喘相”。呼吸虽然无声音、无凝滞,但是不谨细,这是“气相”。呼吸无声音、无凝滞、无粗戾,处于一种若存若亡、可觉不可觉的绵长状态,精神保合,情感愉悦,这是四种调息法中的“息相”。“风”“喘”和“气”这三种工夫都不属于最佳状态,分别会有散漫、暴戾、劳攘的弊端,因而都属于“假息”。只有最为绵长细密的“息”的功夫才属于“真息”。吾人在静坐时同时进行调息,以此入门,使得精神有所寄托,神与气得以守持,也是为学的方便法门。王畿进一步区分调息与数息,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数息是有意识、有目的地控制呼吸,人力的介入也使得杂念得以掺入这一过程中。而调息则是在无意的状态下自然进行的。调息的特点是以“中土”含育呼吸“呼吸含育”为内丹术语。“含育”指一呼一吸,气聚息停。《周易参同契》云“呼吸相含育”,清朱元育注此句为“水火既济,其中一阖一辟,便有呼吸往来,呼至于根,吸至于蒂,总赖中土含藏停育之”。(见中国道教协会:《道教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4年,第635页。),寂静虚无,不急不慢,既不停滞,也不急躁。它可以促使人们的心灵趋于平稳内敛、安静愉悦的状态,而心灵的宁静自适反过来也能促进调息。在这种心息相依“心息相依”为内丹术语。指以心顾息,行住坐卧,相依不离,使得一气归根,即中气凝聚于气穴之中。的状态下,整个身心都处于一种安静祥和的境界,无须刻意营求就能与天地化育合而为一。一呼一吸都连接着质朴含蓄而又充满生命活力的本然状态,这才是最为真实的性命之机。这种“息”的状态在儒、释、道分别被称作“燕息”“反息”和“踵息”。“燕息”一词出自儒家典籍《诗·小雅·北山》《诗经·北山》:“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见阮元:《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63页。)另外,《周易》随卦的《象传》也有“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又作燕息)”的说法,见《十三经注疏》第34页。,“反息”出自《楞严经》“反”,又作“返”,大正藏作“返”,元、明藏经作“反”。《楞严经》卷五:“我厥颂持,无多闻性。最初值佛,闻法出家,忆持如来一句伽陀,于一百日得前遗后、得后遗前。佛泯我愚,教我安居,调出入息。我时观息,微息穷尽,生住异灭,诸行刹那,其心豁然得大无碍,乃至漏尽成阿罗汉,住佛座下印成无学。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返息循空,斯为第一。”(见陈撄宁:《楞严经释要》,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143页。),而“踵息”则典出《庄子·大宗师》《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见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第74页。)。王畿认为三教所用的术语虽有不同,但都是对本心“一念灵明,常惺常寂”的状态的描述。这种调息方法对于为学和养生皆有极大的助益,所以被王畿赞为“彻上彻下之道”。我们看到,王畿在劝告友人不能执着于调息法的同时,又对这种方法持以充分的肯定态度。他所要强调的是一种顺应无滞的精神境界。一方面要借助调息来实现内心的宁静平和,一方面又要避免刻意地营求这种境界。在无滞的状态下,心境平静安详,呼吸匀称绵长,两者互为其用。这种不勉而中的功夫也许才是王畿所认可的调息的究竟义。
调息作为一种为学和养生的方法,在与王畿同时代的许多学者那里都有过实践经历和深入讨论,但王畿匠心独运地将调息与致良知之学相联系,使得他对调息法的论述展现出浓厚的心学特色:
人之有息,刚柔相摩,乾坤阖闢之象也。子欲静坐,且从调息起手。调息与数息不同:数息有意,调息无意。绵绵密密,若存若亡,息之出入,心亦随之。息调则神自返,神返则息自定。心息相依,水火自交,谓之息息归根,入道之初机也。然非致知之外另有此一段功夫,只于静中指出机窍,令可行持。此机窍非脏腑身心见成所有之物,亦非外此别有他求。栖心无寄,自然玄会,慌惚之中,可以默识。要之,“无中生有”一言尽之。[2]118
王畿劝谕欲习静坐的学生先从调息入手,用这种无意之间进行的调息工夫可以收到神返心定的效果。心定与息调相互促进,如水火相济此处的“水火”概念应是源自道教内丹学。在内丹学之中,“水火”广义上是指阴阳。但是在炼养活动之中则有多种具体的称谓,“水火”在狭义上一般是指肾所寓之真水与心所寓之真火。其中肾水又有壬水与癸水之分,前者源自先天,至清至灵,而后者源自后天,浊而不清。“水火相济”喻指“成丹”或者“结胎”。,这就是所谓的“息息归根”,是入道最初也是最基本的一步。但这并不意味在致良知之外另有一段特异的功夫,调息应该是在修养的功夫之中体悟良知,成为良知的自然发用。而不是私意安排,以调息去替代致良知吴震教授将王畿对“息”字的用法区分为呼吸(包括仁的呼吸与天地的呼吸,其中后者指谓阴阳两气的氤氲变化)与万物根源的“气”两种类型,并指出在龙溪学术体系内“调真息”与“致良知”两个命题具有紧密的关联性。(见吴震:《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42、第359页。)。良知是吾人本来所具,但调息所识得的“机窍”却有所不同。它既不是身心本来便有,却也非得之于外。这句话表述得颇为奇特,似乎存在着矛盾。但王畿所要表达的不外乎这个意思:调息的工夫与无善无恶、无定向、无方所的心之本体(即良知)在修养的最高阶段上应该是合而为一的。调息不仅仅是针对身体修养的一门练气方法,更是致良知精神性自我转化的一种进德工夫。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实现对体内之气的调节搬运,也是为了获得身心与宇宙合为一体的精神体验。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动亦定,静亦定”,既不离于调息,亦不执于调息。
三、不起意
宋明理学家在为学过程中经常面对的一个困境便是对憧憧往来的念头难以克制。一念未息,一念旋起,使人的精神茫茫荡荡宣泄而出。往往在意念排山倒海地纠缠一番过后,人们的精神和身体都会感到特别疲惫。这种经历困扰着许多学者,以至于如何处理意念构成了他们经常要讨论的一个话题。王阳明就回答过许多弟子关于这方面的提问。比如《年谱·正德八年》所记,孟源询问道:“静坐中思虑纷杂,不能强禁绝。”阳明回答说:“纷杂思虑,亦强禁绝不得;只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后,有个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专,无纷杂之念;《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也。”[1]1363思虑纷起、徘徊不去是孟源治学时经历的实际问题。王阳明认为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人毕竟不是槁木死灰,毕竟活着的每一刻都会有思虑意念产生。王阳明并不认可把普通的思虑意念一切斩断的观点,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只要能掌握本体之知,在思虑萌动之初加以省察克治之功,便不会妨事。待功夫精熟后,便能收到“自然精专,无纷杂之念”、一了百当的功效。这便是《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一句的含义。
心思外驰、念虑纷杂往往导致思虑枯竭、烦心焦躁,不但不利于求道,反而会劳损元气,对身体造成伤害,对于养德与养生都构成了巨大障碍。这对王畿的朋友和弟子们来说也是一道很难解决的难题。王畿的好友罗洪先便颇受困于这一问题,以至于不得不数次闭关石莲洞,以主静为方法涵养良知心体。如何断欲根、实现何思何虑廓然大公的境界,王畿对此投入了许多精力进行探索。我们首先来看他对“不起意”的观点:
知慈湖“不起意”之义,则知良知矣。意者本心自然之用,如水鉴之应物,变化云为,万物毕照,未尝有所动也。惟离心而起意则为妄,千过万恶,皆从意生。不起意是塞其过恶之原,所谓防未萌之欲也。不起意则本心自清自明,不假思为,虚灵变化之妙用,固自若也。空洞无体,广大无际,天地万物有像有形,皆在吾无体无际之中,范围发育之妙用,固自若也。其觉为仁,其裁制为义,其节文为礼,其是非为知,即视听言动,即事亲从兄,即喜怒哀乐之未发,随感而应,未始不妙,固自若也。而实不离于本心自然之用,未尝有所起也。[2]113
对“意”的理解构成了解读本段的关键。意指的是意识、意念、意向。据陈来先生的研究,王阳明所说的“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与朱熹所说的“意是心之所发”这两种表述,对心、意的定义并无根本区别。[3]57在王阳明的哲学视域中“意”具有多种含义,如感觉意念、实践意向等等。[3]55但笼统地说,“意”是心之所发,是一个经验意识的范畴。它并不是至善无恶的本体之心,而是不断与实现交流着的、善恶相杂的存在。这点大体被王畿所继承。王畿认为意为本心的发用,如镜照物,显其本相,而自己实未曾参与其中。只有离开心体而产生的意才是妄意,才是过恶之渊。宋儒杨简“不起意”所要堵塞的,其实是指离心而起的妄意,这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办法。至于本心自然之用的意并不在堵塞范围内,因为无此必要。妄意不起则本心清明,随意流转,悠然自得。甚至可以借此沟通人与天地,使天地间有形有象的万物都能摄入虚灵广大的良知本体之中。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知”都可以于意之所在的事父从兄之“物”上体验感知。“三个固自若也”都是对“不起意”所具有的效验的赞美和肯定。王畿特别指出意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不是己身独具的,而是在与心之本体的发用相联系时被赋予的。这种起而“未尝有所起”的意识状态才是真正的不起意。
从对“意”的讨论自然而然会延伸到对“念”的关注,因为这两个概念具有极强的关联性。不同于在“意”和“念”之间做出严格区别的晚明儒者刘宗周,在王阳明和王畿这里,“意”和“念”两个概念具有相当程度上的相通性,尤其是当“意”指向一种积极主动的实践意向时更是如此。对于念之有无的问题,王畿认为:“念不可以有无言。念者心之用,所谓见在心也。缘起境集,此念常寂,未尝有也,有则滞矣。缘息境空,此念常惺,未尝无也,无则槁矣。克念谓之圣,妄念谓之狂,圣狂之分,克与妄之间而已。千古圣学,惟在察诸一念之微。故曰一念万年。此精一之传也。”[2]464念是心之本体的发用,心不能以有无言,所以念也不能以有无言。随境起念,境过则寂,这样心体便处于一种未发之中的状态。若是境过而念存,徘徊不能去,未免会有障蔽心体之累。所以可以说此念“未尝有也”。外缘不至时此念也不是昏昏睡去,它仍然处于一种常惺惺的状态,随感随应。所以说此念“未尝无也”,否则便成槁木死灰。有事无事,此念都惺惺灵明,有却非有,无却非无,所以“有”“无”这种描述物体存在与否的词语并不适用于对意念的讨论。“克念”“妄念”中的“念”与之前的“念”的用法有所不同,这里的“念”兼“欲”而言。夹杂有好色、好利、好名之欲的邪思妄念,克之则为圣,顺之则为妄。儒学的要旨便在于“察诸一念之微”而加以惟精惟一之功。何者应该充当这种审查念虑正确与否的角色?联系王畿一贯的立场,应是本心之良知。因此,克念工夫应看做是实致良知的一个子课题。我们联系另外一段可以看此意思更清楚。在回答谢虬峰“寻常闲思杂虑,往来憧憧,还须禁绝否”的问题时,王畿答道:“‘心之官则思,思原是心之职。良知是心之本体,潜天而天,潜地而地,根柢造化,贯串人物,周流变动,出入无时,如何禁绝得他?只是提醒良知真宰,澄瑩中立,譬之主人在堂,豪奴悍婢自不敢肆,闲思杂虑从何处得来?”[2]152思虑是心之天职,心自然要思虑。这种思虑活动“贯穿人物,周流变动,出入无时”,是无法强行禁绝的。心的本体即是良知,良知便如一家的主人。主人在堂,豪奴悍婢便不敢放肆。不过,不敢放肆不代表不愿放肆,豪奴悍婢依旧是存在的。就像闲思杂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是真实存在、不能祛除的。对于如豪奴悍婢一般的闲杂思虑,王畿开出的诊方类似于阳明“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1]106。良知之与邪思枉念的关系,便如烘炉之与雪“烘炉点雪”之喻出自王阳明致黄宗贤的书信,原文为:“杀人须就咽喉上著刀,吾人为学,当从心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虽私欲之萌,真是烘炉点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1页。)。一点雪片入炉,自然消散不见。对于王畿来说,较之忧心于思虑之有无,实致良知、使炉火旺盛才是学问的关键。张学智先生评价王畿的先天功夫时说道:“王龙溪以人人本有、不学不虑的良知为出发点,他的功夫,是保任此先天良知性體流行。这样的保任虽也用去恶功夫,但比之先天,作用要小得多。王龙溪是占据先天要津,以此为主体而排遣、消释后天意念。先天本正之心流行,则后天所起之意如烘炉点雪,触之即化。”(见张学智:《明代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从不起意到克念到何思何虑,王畿对于意念、意识、思虑的看法其实只有一条,便是认得良知真做主宰。他认为,只要这样便可“直心以动,自见天则,迹虽混于世尘,心若超于太虚”[2]462。心体和乐自在,如优游于太虚之中。虽然处身于滚滚尘世之中,也不会构成心灵的系累。心灵既然不乏不累,身体自然会舒适康健,这便是养生之术的一个诀窍。
四、窒欲
欲望的泛滥虽是社会问题,但它首先是一个个人问题。对于普通人来说,对食色之性的纵容无度不仅容易导致精神疲惫萎靡,也会对身体造成重大伤害。这种现象在先秦便引起人们的关注。老子曾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五色虽美,无节制地追逐之却会让人目盲。同样地,人们只沉迷于五音、五味、驰骋畋猎、难得之货满足感官欲望时所带来的快乐,对于耳聋、口爽、发狂、行妨的负面结果却选择视而不见。所以,老子所指出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老子·第三章》)的圣人之治不仅仅是个社会的或者政治的问题,也是一个修身、养生的问题。宋明理学兴起后,如何对待欲望成为一个众多学者热衷于讨论的话题。
王畿在评价殷迈所撰的《惩忿窒欲编》时说道:
惩忿窒欲原是洗心退藏公案,损之道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即是圣功。尝闻忿不止于愤怒,凡嫉妒偏浅,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些子放不过,皆忿也。欲不止于淫邪,凡染溺蔽累,念中转转贪恋,不肯舍却,皆欲也。惩忿之功有难易,有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事上是遏于已然,念上是制于将然,心上是防于未然。惩心忿、窒心欲,方是本原易简功夫。在意与事上遏制,虽极力扫除,终无廓清之期。养生家惩忿,则火自降,是为火中取水,窒欲则水自升,是为水中取火。真水真火,一升一降,谓之既济。中有真土为之主宰,真土即念头动处。土镇水,水灭火,生杀之机,执之以调胜负者也。[2]97王畿在论述惩忿窒欲时引入“真水”、“真火”“真土”等概念,或许是受到净明道影响。在刘玉真撰、黄希文编集《西山隐士玉真刘先生语类内集》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较为相似的论述:“所谓忿者,不只是愤怒嗔恨,但涉嫉妒小狭偏浅不能容物,以察察为明,一些个放不过之类,总属忿也。若能深惩痛戒,开广襟量,则嗔火自然不上炎。所谓欲者,不但淫邪色欲,但涉溺爱眷恋,滞着事物之间,如心贪一物,绸缪意根,不肯放舍,总属欲也。若能窒塞其源,惺惺做人,则欲水自然不下流。虽如是,其中却要明理,明理只是不昧心。……惩忿则心火下降,窒欲则肾水上升。明理不昧心天,则元神日壮,福德日增。水上火下,精神既济。中有真土为之主宰(真土即黄中之理),只此便是正心修身之学。”见黄元吉、徐慧、邵以正校定:《净明忠孝全书》明景泰三年刊本(不分页),现藏日本内阁文库。依净明道内丹学,真水在肾,真火在心,三丹田皆有真土。养生修炼要水火相济,由内丹中的真土统摄,便可修成内丹。此条蒙友人李璐指出,特此致谢。
王畿认为惩忿窒欲是损己以就道。“损之又损,以至于无”出自《老子》第四十八章“为学日进,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一句。王畿认为在日损之道上,儒、道两家并无不同。“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虽典出《老子》,但它同样也是儒家所追求的境地。对于“忿”与“欲”,王畿的界定比通常理解中的范围要来得广。“忿”不仅仅指愤怒,但凡嫉妒偏激、没有涵养、不能容人、念头缠绕心中不能释怀,都属于“忿”的范畴。“欲”不仅仅指淫欲邪念,但凡习染所蔽、对一事一物贪图爱恋不能放下,都属于“欲”的范畴。王畿认为无论是“忿”还是“贪”都是对身心理想境界的违背。勿意勿必、不滞不留才是“损之又损”的修养工夫所应达到的。至于具体的修养工夫,王畿指出时人一般采用在事上用功、在念上用功和有在心上用功这三条路径,分别具有“事上是遏于已然,念上是制于将然,心上是防于未然”等特点。前两者的工夫虽然也很艰苦,但是本体一蔽,发用自偏,就算用人一己百的功夫扫除障蔽,难免遇境又为所倒,不能收到廓清之功。“火中取水”“水中取火”的说法来自道教内丹学,对此需稍作解释。根据何振中先生的研究,“道教内丹炼养活动中的水升火降与中医学的脏腑气机升降,都与宇宙自然界的升降活动具有一致。”[4]水火的升降是人体正常活动所必须的,升降过程的通畅意味着生命的健康和活力。在人体内水火升降的运动中,心肾水火相交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在心肾水火的升降往复过程中,必须听凭“真土”的主宰。而王畿所谓的“真土”,指的应是念头动处察其是非的良知本心。以之作为主宰,加以惩忿窒欲之功,便可如《既济》卦一样收到功德圆满之效。
窒欲的目的在于寡欲,寡欲的究竟在于无欲:“圣学之要,以无欲为主,寡欲为功,寡之又寡,以至于无,无为而无不为。寂而非静,感而非动,无寂无感,无动无静,明通公溥,而圣可几矣。”[2]122关于无欲,王畿借鉴了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观点。寂与感都是本心所处的状态,不能以动静论之。这点笔者在上一节讨论“念不可以有无言”时做过说明。“无寂无感,无动无静”,一切介于有无之间。心体上无喜怒烦恼,作用上喜怒哀乐爱恶欲虽然往来胸中,但过而即化,广大通畅,不滞不留。这既是对心灵健康的熏育,也是对身体健康的保养。
五、结语
出于对阳明良知之学的信仰,王畿很自然地将养生实践收摄于他的良知学体系中。较典型的表述,比如王畿在《与魏水洲》中所说的:“大抵我师良知两字,万劫不坏之元神,范围三教大总持。良知是性之灵体,一切命宗作用只是收摄此件,令其坚固,弗使漏洩消散了,便是长生久视之道。”[2]201简而言之,一切“收摄此件”的功夫都可以算作养生。针对于维持身体健康的行住坐卧、呼吸吐纳如此,针对于维持心理健康的惩忿窒欲、致虚守静也如此。虽然王畿在具体问题的论证上使用了很多道教养生的概念、方法,但对他而言养生术的终极意义在于收摄此件良知本体、求得良知自然无碍的发用流行,而不是长生久视或是炼神还虚。以养生为主则析性离命,以良知为主则养生自致,所谓“致知之学,当下还虚,超过三炼,直造先天,不屑屑于养生而养生在其中矣。”[2]478在这种思路之下,一方面王畿把养生的功夫归并到养德之中,使其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他也把养生的范围扩充到广大无边。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无论是人皆可视的举止还是一念之微的思虑,都被纳入到养生的范畴。王阳明有诗云:“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1]745这既是王阳明悟道后语,也为王畿所继承而成为他对养生问题最基本的看法。养生不仅仅要医身以长寿,还必须医心以成德,这便是王畿养生思想的心学本色所在。
参考文献:
[1]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明〕王畿.王畿集[M].吴震,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3]陳来.有无之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4]何振中.内丹医学思想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14:347.
(责任编辑:方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