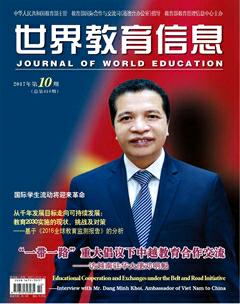留学教育及其消费行为
战湛

摘 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和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需求的持续高涨,教育开始作为一种商品在国家和地区间流动。这种流动带来的是消费者对留学教育的进一步认知和理解,以及对留学教育和本地教育的比较和选择。文章从消费者行为学的视角探讨留学教育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包括留学教育的产品属性、消费者、消费动机、消费成本与风险,以及消费行为的选择机制。其中,留学教育与消费者是消费行为发生的两个要素,而消费动机与消费风险又从不同角度影响着消费选择机制。
关键词:高等教育需求;留学教育;消费者;消费动机;消费风险
一、留学教育的产品属性
时至今日,对于中国人来说,留学已经不再是一件神秘的事。可究竟什么是留学,学界对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在中国的历史上,尤其是清末第一次留学热潮兴起前后,对于这种远赴异国他乡的求学活动,有“留学”与“游学”两种说法,前者强调“留居”,后者强调“远游”[1]。近年来,随着中国加入WTO,签署教育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后,留学形式日渐多样化,留学生年龄层次不断扩大。笔者认为,现阶段一般意义上的留学应具有以下属性:留学是一种为了达到学习的目的,满足个人教育需求的行为;留学的学习过程主要发生在国外,但不排除中间往返国内外;留学时间长短随学制和学习计划而不同,但最终追求的目标一定是高等教育学历。相比较之下,游学更多的是为了追求生活和学习体验,时间一般也相对较短。因此,留学应该是一种为了满足个人学历教育需求而远赴海外求学的过程,时间长短不一,主要由学制决定。
尽管学界对高等教育能否成为一种私人产品争论不休,但现实情况是,随着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签署,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贸易产品”[2]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市场,我国也不例外。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加快,学生、学者、教育项目的跨国流动将教育资源从发达国家输送到发展中国家。这种流动实则是发达国家的优质教育挤占发展中国家教育市场份额的过程。作为一种新产品,留学教育正逐渐改变人们的观念,为人们“创造”了新的教育需求,从而一步步地取代国内同类型的教育产品。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留学教育在国际市场的出现说明了其最终的盈利目的。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些比较年轻的、急需发展壮大的私立大学或学院,留学教育提供者中不乏一些营利性教育组织,如卡普兰(Kaplan)、纳维教育(Navitas)等。这些大学或教育组织将其掌握的教育资源优化组合,主要通过与别国教育机构或中介合作的方式,向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兜售他们的教育产品。这之中也包括一些传统的非营利性质的大学,为了扩大国际影响、提高自身在世界范围内的辨识度、发展科研与教学而参与到教育市场化的浪潮中来[3]。不管通过哪种形式,这些产品主要来自于那些高等教育公共财政遭到不同程度缩减的发达国家。事实上,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在大力支持和鼓励本国的大学向海外拓展,寻求较高的经济回报,用于弥补自身教育经费的不足[4]。不仅如此,留学生给接收国带来的经济利益远超出教育经费本身,随之而来的消费和工作机会对接收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刺激几乎是难以估计的。根据美国《门户开放报告2015》的数据,2015年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总共为美国经济增长贡献了305亿美元,并提供了超过37万个工作岗位[5]。由此不难理解,在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在向外推广其教育产品方面有着充分的动机。[6]
留学教育满足了消费者的需要。在本国教育无法满足个人或家庭教育需求的时候,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寻求替代品或更优质的教育来满足自身需要。留学教育满足了大批不同类型留学生的教育需求,其中不仅包括对国内教育质量或理念不满意的“客户”,也包括通过国内高考难以获得理想高等教育服务的人群[7];不仅包括为了找到更好工作选择镀金的职场人士,也包括为了丰富人生阅历而走出国门的年轻人[8];不仅包括寻求“短平快”、高收益的“回国派”,也包括选择移民的“移民派”[9]。总之,留学教育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出现与兴盛,侧面说明了在教育消费需求旺盛的环境下,消费者对本国教育信心不足,以及对海外教育的大力推崇。
留学教育是一种差异化的、有明确市场定位的服务产品。虽然留学有着看似“大众化”[10]的趋势,但是较之国内教育产品,其依然有着受众群小、费用相对高昂的特征。留学教育不仅对支付能力有要求,对消费能力也有一定要求,其中包括个人的语言与学术能力、自理能力,甚至自信心等心理特质。而且,提到留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先进的知识与技能、差异化的教育方式和理念、优越的学术环境、新鲜的社会文化和生活环境,这些与国内教育相比较而产生的认识暗示了消费者对留学教育的态度,从而引导了他们的消费选择。
留学教育的深层含义超出了其本身的价值。所罗门指出,“人们购买商品往往并非因为它们能做什么,而是因为它们意味着什么。这一前提并不是说产品的基本功能不重要,而是说明产品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已远远超出了他们所能实现的的功能。”[11]对于留学教育而言,其背后的深层含义代表了消费者的特征。留学背景不仅仅意味着有更好的职业发展、更高的收入,也明確塑造了“留学生”“海归”等形象。选择留学,不仅仅是选择了一种教育产品,而且说明了消费者的生活态度、消费方式,说明了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二、全球化背景下留学教育的消费者
正如阿特巴赫[12][13]所指出的,全球范围的资本世界总体而言对高等教育和知识产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且有史以来首次在世界范围内对不同程度的教育和培训进行了大量投资。受到自由贸易的影响,高等教育被视为一种私人产品,而不是公共责任。这种认识借助商业力量将留学教育推送至全球范围内的消费者面前,供他们选择。在这股力量的驱动下,世界范围内的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从2000年至2011年,这一数目翻了一番,达到了至少430万。 其中,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成为吸收国际学生最多的地区,而中国超越印度与韩国,成为输出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根据经合组织(OECD) 2013年的统计数据,在美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人数约占该国国际学生总数的三成左右,远超其他国家。[14]
在中国,留学教育之所以得到接受和认可是和全球化背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如上所述,WTO为教育产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平台和保障,使得国际教育市场日渐规范和繁荣;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经济的全球化最终带来的是文化的全球化,是理念、价值观的交流与融合。中国的消费者对于留学教育的认识也在随着对西方教育理念不断受到推崇而逐步加深。自1984年《国务院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出台至今己30多年了,中国的消费者从盲从到渐渐理智,再到重新认识留学,认识一步步深化,不再仅仅将目光放在留学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之上,而是更多地聚焦在个人素质、视野、观念与创造力的提升上。
越是年轻和富有的消费者越倾向于成为这种全球化营销的对象[15]。其主要原因是现如今交流平台和信息来源的多样化与丰富,这类消费者更易于通过这些渠道接受新兴的教育消费观念。根据腾讯、麦可思2014年的数据,受访的高中和本科毕业生分别有43%和44%是通过国内外网站了解留学信息的,而传统的信息渠道,如留学中介机构则只占到约三成[16]。但留学教育的营销对象绝不仅局限于富有家庭的年轻人,事实上,对留学教育的消费属于家庭消费的范畴,因此,其消费选择与决策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而做出的。这就必须考虑到家庭生命周期(Family Life Cycle)和家庭内部权责的分配关系对营销对象的影响。家庭生命周期决定了某阶段家庭消费的主要重心,父母的年龄、子女的个数、子女的年龄等都会决定家庭是否会关注留学教育以及消费。家庭内部权责的分配则决定了由谁最终作出决策和在哪种事项上作出决策。实际情况往往是家庭成员在经过或多或少的讨论后达成一致或相互妥协的购买决策(Purchase Decision),尤其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必然同时在留学事项上达成某种共识。所以,针对中国的传统家庭,很难明确究竟谁才是留学教育的核心消费者,毕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付费的是父母而不是子女。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在重视教育的中国社会,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要求往往予取予求,尽力满足,尤其是在经济情况基本允许的前提下。
由于留学教育有着较高的消费门槛,在留学生群体中,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占大多数。这些家庭又往往具有父母学历较高、职业分布偏向管理层和专业人员等特点[17]。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越来越多的高收入人群开始考虑将子女送往国外读书,这一比例在高净值人士中甚至达到了八成[18]。但是,符合留学教育消费者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家庭或个人就一定会选择留学教育吗?虽然学者们经常用经济收入作为比较消费模式的重要依据——经济收入决定了家庭或个人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总额,对消费行为是否发生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把经济收入作为唯一指标未免过于武断和简单。要理解消费者的行为,也需要结合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个性等心理统计学特征,以此解释其消费模式。处于市场中的每一个消费者都拥有着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对事物也有着既分散又坚定的解释。这些特定的对教育、高等教育乃至海外教育的认识,促使人们做出比较与选择。生活方式决定了家庭或个人的消费观念,比如,是否将房产变卖来支持子女留学,或者推迟留学计划而将资金投入股市?个性特征则影响了自信心、自主性、承担风险的意愿,这些对自我的认知也影响了最终的消费行为。
三、留学教育的消费动机
动机是引导人们做出消费行为的过程,并同时具有功利性和享乐性[19]。一方面,选择留学的动机包括追求海外学历,以及未来更好的就业机会和高收入等功利性目标。这时,留学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期望的结果所驱动的,而和个人内在因素关系不大。换言之,选择某种留学教育是与其国内教育相比较而言,该选择可以为消费者带来更为积极的,尤其是经济上的效益。这种动机从留学生的专业选择中就可知一二。2010-2015年,赴美留学生中选择STEM专业的比例一直保持在70%左右[20]。相比之下,这些专业的特点是就业环境较好,收入水平较高。另一方面,消费者也会被主观的、经验性的动机所驱使,如对国外生活环境的向往[21]、对文化氛围的偏好、对教育体验的追求[22]等。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能只是在寻求一种不一样的体验或感受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甚至不排除只是为了逃避现实生活环境。
在实际情况中,很难将消费者的动机区分为功利性或者享乐性,两者往往是掺杂在一起的。复杂的动机反映了消费者对产品的认识与态度。当提到为什么选择留学教育时,消费者很容易将自己的行为和留学教育的特殊属性——通常是正面的——联系在一起。这些得到消费者承认及肯定的属性来自于消费者的经验和记忆,比如经常在各种媒体上出现的成功的留学案例,可能就會使消费者产生对产品的偏好。而且不仅关于留学的正面信息会刺激到消费者的选择偏好,国内教育的负面信息也会使消费者趋向于规避这种负面作用所带来的后果而选择出国留学。对于他们来说,选择一种教育产品正面作用的同时意味着规避了另一种产品的负面作用,但也同时放弃了后者的正面作用。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作用,都几乎无法被有效比较,比如留学可能意味着更宽广的视野,而留在国内则更容易建立起有效的人脉关系。因此,一旦做出选择后,消费者倾向于寻找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决定,从而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这时相应教育产品的正面属性将被更多地挖掘出来用以掩盖其负面属性,而其竞争产品的负面属性也会被进一步放大。可以说,消费动机从始至终贯穿着消费过程,不仅触发消费行为,也是对消费行为的最终合理化解释。笔者接触到的一名访谈对象,出国留学后,其对留学的看法发生了逆转,认可了留学的积极作用。“当时,我个人是比较反感出国的,因为周围有很多朋友很早就出去了,然而过得并不像国内这么舒坦。最后,还是因为父母的坚持才出去的。现在反过头来看,总体来讲,留学是一件很积极的事,对我的性格或者说习惯的改变,产生非常大的作用。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各方面都不独立,尤其是经济上,没钱就会跟父母要。出国以后,我觉得获得的最大的锻炼就是把你一个人扔在陌生的环境,你做任何事情,都要凭你自己。”
四、留学教育的消费成本与风险
留学教育的消费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其中,直接成本是指留学期间在留学目的地发生的开销,主要包括学费和生活费,如住宿费、饮食、交通等。根据QS世界大学排名的数据,表1列出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大学所在国家和地区对国际学生的收费情况①。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除日本、韩国与新加坡以外,同样是高水平的高等院校,美国等四个主要留学国家的学费都要远高于国内学费。虽然并不是所有中国留学生都能够进入榜单中的高等院校学习,但是留学学费高昂是不争的事实。除此之外,日常生活开销也一样居高不下。一般而言,其实际花费与学费大致相当。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2013年门户开放报告》的数据,2012-2013学年国际学生对美国经济的净贡献值中,学费和其他教育支出共计177.02亿美元,而学生及亲属生活费用合计为151.08亿美元。[23]
留学的间接成本包括留学准备阶段付出的中介费用、语言培训或其他学习费用,以及留学期间回国探亲往返国内外的交通费用。留学中介费根据中介所在地市场行情的不同会有较大的差别,以北京市为例,中介机构的收费标准是人均3万元[24]。语言或预科学费是留学生在出国准备阶段几乎都要付出的培训费用,根据学生个人能力的不同,具体花费很难一概而论。但是以新东方(www.xdf.cn)提供的雅思课程为例,其为期三周的全日制寄宿课程收费约为3万至4万元。其他学习费用是指国内预科、国际班、出国班的学费,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培训费用。上述各种准备阶段的费用根据所在地域的市场行情、经济发展情况、同行竞争激烈程度以及学生自身语言或学术能力等因素会有很大浮动,但可以肯定的是准备阶段的费用支出往往不是一个小数目。回国探亲的机票费用相对于其他间接成本而言较低。在同样的往返目的地之间,机票价格根据时间、航空公司以及是否购买了往返机票等因素会略有浮动。一般而言,去北美、澳大利亚或欧洲的主要留学国家的往返机票价格约为5000~10000元。
留学的机会成本是指留学生在留学期间可能损失的工作收入。留学生学历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个人的留学机会成本的多寡。对于高中留学生而言,其机会成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而对于高学历或已就业再选择求学的留学生而言,所放弃的经济收入就比较多了。有研究表明,2013年广东省某大学毕业生起薪为3505元[25],同年湖北省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的平均月薪分别为4406元、2939元和2308元[26]。而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数据,2013年和2014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为51483元和56339元[27]。由此保守估计,目前本科生、研究生毕业后出国所放弃的经济收入大致为每年3万~5万元。
可以说高昂的消费成本是增加留学教育消费风险的主要原因。尽管有研究表明与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居民相比,海外学历达到硕士及以上可以使月工资提高48%,海外学历未达到硕士可以使月工资提高8.1%。但是该研究同时指出,只有获取较高的海外学历及丰富的海外工作经验,其回报率才会有较显著的提高[28]。否则,与8.1%的工资水平提高与动则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的投入相比较而言,并不见得就是一种最经济的选择。如果考虑到所有直接、间接以及机会成本,留学直接的经济回报率甚至可能低于一般投资利率。一名访谈对象也谈到:“(选择留学时)会想是不是借助国外的文凭回国会好找工作一些,但也会考虑国外投资这么大,回国之后能找什么样的工作,会不会有点收支不平衡。”经济上的低回报率可能会和消费者的预期有较大差距,导致消费风险的上升。这种结果的不确定性存在于留学的任一阶段,如海外升学的困难或留学目的国对非本国公民就业机会的政策限制都可能增加消费风险。此外,高额的沉没成本也容易使消费者难以舍弃先前投入,从而造成不理性的过度消费。
消费风险同时受消费者本身的信息渠道、认知及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决策能力的影响。留学教育信息纷杂,普通消费者经常难以对其进行有效辨识,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同时,消费者在接收各种信息的过程中,常根据自己的经验与偏好来分析和处理这些信息。这些经验与偏好早已随着日益饱和的各类渠道渗透至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关于留学、高考、中外教育比较等热点话题都将消费者带入一个高频率的暴露(exposure)过程。消费者甚至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已经对留学教育有了一定的认知,在面临消费选择的时候,也就不自觉地会利用这些经验。虽然互联网的发展推动留学教育信息趋于透明化,但是由于衡量标准不一、信息真实性往往难以核准,缺乏专业知识的消费者无法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有效分析和判断,容易受到“守门人”的影响甚至误导。例如,一名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的访谈对象就表示,当时在选择专业时主要听从了留学中介的建议。后来她发现同届中国学生人数相对较多,从而了解到因为当年该留学中介在大力推介此院校,所以该专业中国区招生人数从往年的两三个人一下增加到十几人,只比当地学生略少。突然涌入过多的中国留学生不仅对校方的教学管理带来了冲击,也导致该专业的实习机会受到了的影响——处于语言劣势的中国学生大多数没能找到最理想的实习机会,这也相对制约了他们后来在国外的就业情况。
如果说消费动机促使了消费行为的发生,消费风险则起到了阻碍的作用。这种不确定性降低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及做出正确判断的可能性。规避消费风险,将可以促进消费行为的产生。换言之,如果留学成本继续降低,信息渠道及市场环境更加规范,消费者自身辨识能力提高,中国的留学市场将更加繁荣。
五、留学教育的选择机制
留学教育的选择机制是建立在消费者需要的基础上的收集、整合、处理信息的过程,其中包括问题识别、信息搜索、備选方案评估、产品选择、消费行为五个阶段。消费动机与风险自始至终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影响着这个过程。其中,动机决定了留学生及其家庭对不同类型留学产品的价值判断乃至偏好,驱动着消费行为的产生。由于留学费用相对高昂,经济因素造成的消费风险往往是学生考虑的首要问题[29]。当然,除此之外,很多其他因素也左右着选择过程。
首先,即便能够识别问题,也不能决定消费者一定产生留学需求。留学只是消费者面对自身教育问题而提出的多个解决方案之一。即便消费者可能面临着升学的困难,但根据个人情况不同,这种教育需求也会转向就业需求或其他类型的教育需求。这主要是由于追求留学教育产品的成本较高,对消费者个人素质与能力,如学术和英语能力、独立性、自信心,也有一定要求,以及消费风险的存在。那些没有留学意向的访谈对象常常会用“费用较高,担心家庭/父母经济负担过重”“英语成绩不好,没信心出国学习”来作为不出国的理由。
其次,卷入度水平(involvement)影响着留学教育信息的收集与处理过程。卷入度是个体根据自己的内在需要、价值观和兴趣对客体所做出的关联度判断[30]。随着卷入度的提高,消费者会更为主动地寻求相关信息,甚至付出更多努力以期达到对留学的更深层次理解。除了关注频率提高,消费者所搜集的信息范围也会相应扩大,不再局限于留学学校排名、学费高低、专业发展及未来就业等基本情况,而是拓展至留学目的地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环境以及留学所能带来的的教育外溢性收益等多个方面。在对武汉某高校大一与大二学生的访谈中,大二学生对留学的理解明显比大一学生更为积极与深刻。这是由于相比刚刚入学的大一新生,大二学生在入学后的一年多时间内,通过与外教、同学间的交流以及自身阅历的增长,文化和价值观上的认同感增强,逐渐使他们认可了留学的价值。即便在大二学生之间,对留学的接受程度也不尽相同。事实上,对于高卷入度的消费者,留学教育往往具有更多意义,这在一些对留学推崇甚至狂热的人群中并不少见。他们能够对留学的好处如数家珍,并且坚信留学能够使自己变得更有魅力与竞争力,并且一定程度上忽视留学的风险。而对于卷入度低的消费者,尽管也许留学可以很好地满足其教育需求,但是由于对信息的不敏感,他们缺乏考虑留学教育的动机。
再次,尽管消费者在选择时倾向于收集尽量多的信息以帮助自己做出更为“理性”的选择,但是在相当一部分案例中,消费者的问题在于选择过多。大量的选项使消费者不得不花费可观的精力比较衡量,从而降低了他们做出明智判断的可能性。这种过度选择(Consumer Hyperchoice)[31]在留学教育信息的收集过程中往往又和有限的决策时间同时出现,进一步加大了消费者作出正确判断的困难。消费者可能由于某次考试失利或其他个人原因,临时决定留学,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消费者在短时间内作出决策,否则则有可能错过申请、确认接受学校通知书或开学时间。由于不愿意做出艰难选择,能力有限的消费者也倾向于寻求有经验的人士和中介提供决定性的建议和对策。
最后,做出产品选择以后,留学教育的消费行为可能延后、改变甚至取消。对于消费者个人而言,留学教育具有时效性,只有在合适的时间才对消费者具有一定的价值。因此,在留学计划由于场外因素被中断时,如学校申请失败、签证拒签、学历认证等问题,消费者则有可能做出延后、改变或取消留学的决定。尤其是对于一些高中阶段就选择“国际班”就读的学生而言,因为已经实质上放弃了高考,所以如果最终未能成行,之前高昂的学费也无法收回。对于留学失利的学生而言,继续准备或降低要求是比较常见的选择,这主要是留学沉没成本高所造成的。当然也不排除彻底放弃留学计划的情况,但是此时的转换成本一般较高,难度也较大。
六、小结
综上所述,从消费者行为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消费行为的发生包含着消费者与产品两个要素,兩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消费者选择留学教育的过程不仅受到其消费动机的影响,也受到消费风险阻碍的影响。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力量贯穿着整个从问题识别到消费行为发生的过程,左右着消费者的最终选择。而且不可忽视的是,在看待留学教育消费行为时,消费者个人的能力与经济条件、文化环境又从内外两个方面同时决定着消费者的动机与消费风险。留学教育的卷入度水平则暗示着消费者对自身及外部环境的理解,影响着消费者对留学教育的价值判断。然而,卷入的过程不仅发生在选择留学教育前,也在留学过程中,甚至结束后继续存在。因此,消费者对留学教育的认知、理解与价值评判也会随着卷入程度的加深而进一步变化。
注释:
①根据QS世界大学排名官方网站(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公布的数据计算平均数,得到各国家或地区国际学生学费均数,但并没有区分不同专业学费的差距。因为部分国家高校相关学费数据缺失或施行减免学费政策,且不是主要留学目的地/国,所以并未将德国、法国及北欧各国学费列入表内。新西兰由于仅有1所院校进入前100名,其学费不具代表性也未列入表内。中国大陆地区学费为进入榜单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4所院校本地学生学费平均数。
参考文献:
[1]章开沅.余子侠.中国人留学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1-12.
[2][13]ALTBACH. Knowledge and Education as International Commodities: The Collapse of the Common Good[J].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ummer, 2002(28):2-5.
[3]ALTBACH.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xchange in a Globalized University [J].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01(1):5-25.
[4]BARR. Financing Higher Education: Lessons From Economic Theory and Reform in England [J].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2009(2):201-209.
[5]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Economics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The 2015 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EB/OL]. http://www.iie.org/Research-and-Publications/Open-Doors/Data/Economic-Impact-of-International-Students,2015-12-16.
[6]詹德赫亚拉.提拉克著.刘丽芳,邓定译.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经济分析[J].教育与经济,2013(1):9-15.
[7]吴克明,卢同庆,王远伟.城乡高考弃考现象比较研究: 成本-收益分析的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2013(23):39-45.
[8]李鸿泽.从教育消费性收益看当代留学动机[J].教育研究,2007(8):53-55.
[9]刘扬,孔繁盛,钟宇平.中国大陆高中生海外留学高等教育的专业选择及其影响因素[J].高等教育研究,2009(4):42-54.
[10]王辉耀.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7.
[11] [19] [23] [33]所罗门.消费者行为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0,78,82,188.
[12]阿特巴赫.世界级大学领导力[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00.
[1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3:OECD指标[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310-337.
[15] [32]所罗门.消费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46,82.
[16] [17] [24] [25]王辉耀.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4)[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0, 23-25,103,275.
[18]中国民生银行,胡润百富公司.中国超高净值人群需求调研报告(2014-2015)[R].北京:中国民生银行,胡润百富,2015:26.
[20]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pen Doors Data[EB/OL]. http://www.iie.org/Research-and-Publications/Open-Doors/Data/International-Students/Fields-of-Study-Place-of-Origin,2016-01-12.
[21]LEE MIN KYUNG. Why Chinese Students Choose Korea as Their Study Destination in The Global Hierarchy of Higher Education?[J].KEDI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olicy,2013(10-2):315-338.
[22]NERLICH. Australians as International Students-Where They Go, What They Do and Why They Do It[J].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2013(4):386–395.
[26]王庚,蔡穎,桂肖敏.人力资本和专业选择对大学生起薪的影响研究——基于大学生就业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J].理论前沿.2015(15):34-39.
[27]中国教育在线.研究生薪酬连续两年下跌文科类岗位[EB/OL].http://learning.sohu.com/20140328/n397362214.shtml,2014-03-28.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指标-就业人员和工资-城镇单位人员平均工资和指标[EB/OL].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15-12-28.
[29]许家云.海外留学经历是否提高了个人收入[J].经济科学,2014(1):91-101.
[30]周金燕,钟宇平,孔繁盛.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不平等:中国高中生留学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12):28-35.
[31]ZAICHKOWSKY. Measuring the Involvement Construct in Marketing [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985(12):341-352.
编辑 李广平 校对 吕伊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