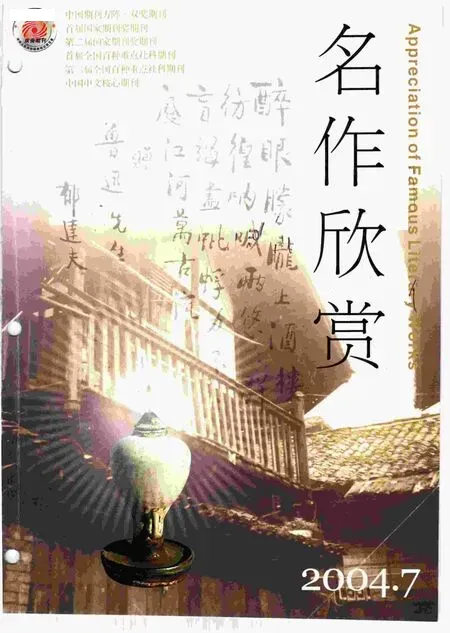反讽:欲望与权力的虚幻图景
北京 李建军
“汤显祖镜像”专栏之五
反讽:欲望与权力的虚幻图景
北京 李建军
反讽是文学的最为重要的伦理精神,也是汤显祖稳定的写作姿态。他从欲望和权力两个角度展开叙事,表现出一种自觉的淑世意识。
反讽 欲望 权力
反讽是一个优秀作家最基本的精神姿态,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精神品质。一个没有反讽激情和勇气的作家,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家;一部毫无反讽力量的作品,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汤显祖是一个内倾型的抒情型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外倾型的反讽型作家。他具有悲剧意识,也具有喜剧天赋;有时是感伤的,有时则是激愤的。感伤的时候,他抒情;激愤的时候,他讽刺。如果说,他的《紫钗记》是爱情正剧,《牡丹亭》是略带感伤的爱情悲喜剧,那么,后来的“二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则大体上可归入反讽型的喜剧范畴。他很善于通过巧妙的隐蔽手段,来表现对现实生活中种种庸俗现象的讽刺和批判。
人不能没有欲望,但人的欲望不可没有理性的节制。过度的欲望,是烦恼和不幸的根源。如果一个社会过度功利主义,只是培养人们对权力、金钱、荣誉的贪婪,那么,这个社会中人们的幸福指数,就不会很高,这个社会的文明指数也不会很高。个人会因为过度贪婪而闷闷不乐、郁郁不得志,政府也会因贪欲无艺而沦为一个牟取利益的机器,甚至为了与民争利,无所不用其极。
生命是一个有限的过程。世间没有不死的人,就此而言,所谓“寿比南山”“万寿无疆”的祝语,简直就是对生命充满讽刺意味的嘲弄。对于生命长度的过分追求,既是贪婪的,也是卑怯的,反映着生命意识上的蒙昧状态。这种对长寿的非理性欲望,本质上不是对生命的热爱和尊敬,而是对它的傲慢和无知。
然而,中国自古以来,偏偏就有为数甚夥的人,对于长生不老,孜孜以求。而且,越是有权势的人,越是对黄白之术感兴趣。为了寻得驻颜的妙方,很多人陷入狂悖状态,有人甚至丢了性命。在《邯郸记》中,卢生后来被召回朝,甚得恩宠,终于实现了“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的梦想,就像他对夫人所说的那样:“吾今可谓得意极矣。”他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皇帝送来的二十位女乐,开始做起了“黄粱美梦”。他特别渴望自己能永生不死,永远享有这些荣华富贵。于是,他开始迷恋“采战”,结果弄得自己一病缠绵,折了阳寿,一命呜呼。
有必要指出的是,汤显祖的这一反讽,绝非虚说一通,而是确有所指。他所批评的,就是在明代上层社会颇为流行的愚昧的养生方式。如果说,有明一代的统治者在政治上是法家的门徒,选择以猛治国,惯弄苛酷法术,那么,在生活上,他们就是道家的信徒,认为人若能得奇术奇方,就可以得道成仙,长生不老。如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就相信“采战”之说,服丹纵欲,结果呜呼哀哉,丢了性命。首辅张居正也迷信这一套,因为沉湎“房中术”而丧生。近代著名学者吴梅在《邯郸记跋》中说:“记中备述人世险诈之情,是明季官场习气,足以考镜万历年间仕途之况,勿粗鲁读过。”确乎如此。汤显祖笔下的反讽总是充满了时代性和现实感。嘉靖皇帝“斋醮”事,具见《明史》之《郑岳列传》和《海瑞列传》。海瑞批评他的语气,很是尖锐:“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过于苛断,是陛下之情褊……陛下受术于陶仲文,以师称之。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至于仙桃天药,妄怪尤甚。”蔡东藩《明史演义》对此亦述之甚详。
如果说,权力之恶是社会之恶的主要形态,那么,对一部深刻的文学作品来讲,政治性是反讽必不可少的一个向度。关于这一点,汤显祖即便没有现代性的理性认知,也不妨碍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而形象地揭示这一点。他在最早的《紫钗记》中写了卢太尉这样一个人物。从矛盾冲突的角度看,他是霍小玉和李益爱情痛苦的直接制造者;从揭示整个权力关系的角度看,他则是起着折射作用和代表作用的人物,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只手擎天势独尊,锦袍玉带照青春。洛阳贵将多陪席,鲁国诸生半在门。自家卢太尉,长随玉辇,协理朝纲。圣驾洛阳开试,咱已号令中式士子,都来咱府相见。”在汤显祖的叙述中,权力显得傲慢而任性,自私而又自负,完全不在乎别人的尊严和感受。他对权力的这种看法和叙述,与自己被张居正、申时行等权臣折辱的遭遇,有着深隐而密切的因果关系。
极权主义社会的权力之恶,首先就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的德性之恶。“临川四梦”中的皇帝,大都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其中好点的,可称为“影子皇帝”,到了矛盾冲突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会像影子一样飘忽而过,发一道圣旨,便将所有问题都轻松解决了——这也不过是做戏的需要而已,当不得真的。更多的时候,所谓英明伟大的皇帝,不过是低能的庸人和凶暴的恶人——他们昏聩自负,雄猜多疑,冷酷无情,连人格健全和能力正常的普通人都比不上。《南柯记》中的国王,几乎就是右相段功手中的玩偶。他听信段功的谗言,将自己的驸马外放,连累公主差点被檀萝国的强敌掳走,导致她最终丢了性命;最后,甚至将淳于棼罢官,幽禁于私室,使他受尽了屈辱和痛苦,以至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和悲诉:
〔生素服愁容上〕太行之路能摧车,若比君心是坦途。黄河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君不见大槐淳于尚主时,连柯并蒂作门楣。珊瑚叶上鸳鸯鸟,凤凰窠裏鹓雏儿。叶碎柯残坐消歇,宝镜无光履声绝。千岁红颜何足论,一朝负谴辞丹阙。自家淳于棼,久为国王贵婿,近因公主销亡,辞郡而归,同朝甚喜。不知半月之内,忽动天威,禁俺私室之中,绝其朝请。天呵!公主生天几日,俺淳于入地无门。若止如此,已自忧能伤人;再有其它,咳,真个生为寄客。天呵!淳于棼有何罪过也。
淳于棼的日子过得提心吊胆,惊魂难定。尽管于私,他曾为“半子”,于公,他“守郡多年,曾无败政”,但最后还是被国王赶出了大槐安国。王后心疼女婿,在国王面前为他缓颊,哭着反问他:“老天呵,不看女儿一面?”但是,多疑的国王心如坚冰,还是将“诸甥留此”,将他赶走了,使他家庭破散。用汤显祖的“至情”标准来衡量,这种无情无义的最高统治者,作为严重缺乏正常人性的人,本质上是一种非人的怪物,而在这种怪物的统治下,人民很难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日子。
事实上,有明一代的皇帝,自朱元璋开始,就开始诛杀功臣,迫害知识分子,虽然时时将“百姓”的福祉挂在嘴上,但却常常以恶法虐民,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最为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对全社会的精英分子,都充满难以消释的敌意,必欲除灭而后快:朱元璋将农村的社会秩序弄得非常混乱,将那里的社会气氛搞得非常紧张,“……又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缙绅、地方等高级人士,从朝廷内的高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据有的历史学家估计,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可以说,明代后来的皇帝,大都遗传了朱元璋的政治基因,大都是这种狭隘、多疑、残忍、低能的人。
统治者的价值观往往起着主宰性的作用。一个社会的道德意识和生活方式,必然会受到统治者的道德主张和行为方式的极大影响。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者,下必甚焉矣。高层的道德堕落和权力腐败,必然会像病毒一样,传染到全社会。在《南柯记》中,汤显祖尖锐地批判了大槐安国的腐败而黑暗的现实。在第二十一出《录摄》中,府幕官与小吏的一段对话,堪称经典:
〔丑跪扶吏起介〕我从来衙里,没有本《大明律》,可要他不要?〔吏〕可有可无。〔丑〕问词讼可要银子不要?〔吏〕可有可无。〔丑恼介〕不要银子,做官么?〔吏〕爷既要银子,怎不买本《大明律》看?书底有黄金。
汤显祖的这一段对话描写,非常大胆和尖锐,竟然忽略语境限制,直接提及《大明律》,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自己时代的讽刺态度。这样不加掩饰的“直刺”,简直有点使人惊骇。汤显祖的反讽话语,彰明较著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体现统治者政治意志的《大明律》的“书底”,埋藏着某种能让人获取利益、但也导致腐败的秘密。
在中国漫长的极权主义时代,科举考试制度是遴选人才的主要方式。为了保障考试的合法和安全,统治者制定了严酷的法律。但是,即便如此,几乎在任何一个朝代,各种花样的考试腐败,都层出不穷。在《邯郸记》第六出《赠试》中,汤显祖就指桑骂槐地尖锐讽刺了明代考试制度的脆弱:
〔旦〕说豪门贵党,也怪不得他。则你交游不多,才名未广,以致淹迟。奴家四门亲戚,多在要津,你去长安,都须拜在门下。〔生〕领教了。〔旦〕还一件来,公门要路,能勾容易近他?奴家再着一家兄相帮引进,取状元如反掌耳。〔生〕令兄有这样行止?〔旦〕从来如此了。
【前腔】〔旦〕有家兄打圆就方,非奴家数白论黄。少了他呵,紫阁金门路渺茫,上天梯有了他气长。
〔合前生〕这等,小生到不曾拜得令兄。〔旦〕你道家兄是谁?家兄者,钱也。奴家所有金钱,尽你前途贿赂。〔生笑介〕原来如此,感谢娘子厚意。听的黃榜招贤,尽把所赠金资,引动朝贵,则小生之文字珠玉矣。〔旦〕正当如此。梅香,取酒送行。
在这部戏里,满朝权贵,包括皇帝和太监,都被“家兄”收买了,于是,上上下下,皆为卢生夺魁,大开方便之门。就反讽的现实性来看,这些情节倒也不是向壁虚构出来的,也不是借了唐代的故事,来对明代社会进行捕风捉影的怨毒污蔑。事实上,仅在万历一朝,这样的恶劣事件,就频有发生。张居正的三个儿子,以及张四维、吕调阳、申时行等几位辅臣的儿子,都是利用他们的权力资源,才得以折桂夺魁,金榜题名。皇帝朱翊钧虽然接到了揭露张居正等首辅儿子科举作弊的上疏,但却压了下来,最终使其得逞——这与崔氏和卢生利用“家兄”打通关节,本质上并无两样,甚至更为严重和恶劣。
人的精神世界是由善恶两种元素构成的。如果一个社会压抑人向善的天性,而鼓励人从恶的冲动,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反人性的畸形的社会,而人性之恶就会导致普遍而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明代社会的人性之恶,如嫉妒、贪婪、势利、残忍、欺诈等,汤显祖的戏剧作品也有严肃而深刻的反讽和批评。
《南柯记》中的右相段功,心胸狭窄,妒贤嫉能,虚伪狡诈,人品极坏。为了加害于淳于棼,他机关算尽,给被害人带来极大的痛苦。《邯郸记》中的唐朝左仆射兼检括天下租庸使宇文融,就因为卢生不曾“钻刺”他,“不肯拜他门下”,便心生怨恨,用各种手段来报复他,先是将他“外补”,后来派遣他这样一个素不知兵的人率军解救边患,到最后,又以“通敌”来构陷他——若非崔氏到高力士那里哭诉,得了他的同情,并向皇帝求情,卢生的头颅早就被砍掉了。在流放崖州的过程中,卢生吃尽了苦头——“朝承恩,暮赐死。行路难,有如此。我卢生身居将相,立大功劳。免死投荒,无人敢近。一路乞食而来,直到潭州”;在流放地,他受尽了侮辱,差点被崖州司户打死。
我们从这样的事象中,分明可以看见汤显祖自己时代的影子,甚至可以看见汤显祖自己的遭遇。他不就是因为不肯拜在张居正和申时行等人的门下,所以才大倒其霉的吗?他不就是因为上疏批评首辅和皇帝,才被贬到大陆最南端的徐闻县的吗?
一个恶时代的道德堕落和人性败坏,几乎是普遍的,无孔不入的。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性都在败坏。普通百姓失掉了内心本来就很稀薄的纯朴天性,知识分子失去了求知的热情和人格上的特操,公正的执法者成为肆无忌惮的犯法者,保卫人们安全的人成了危害人们安全的群体,掌握权力资源的官吏阶层,更是如虎而冠,将虐民害物当作一种习惯。《邯郸记》的崖州司户这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却极具典型性。这是一个毫无人性的冷血动物。他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就是可怕的冷酷,就是极端的势利,就是庸俗的市侩人格。卢生落难,成了他刀俎上的鱼肉。他完全拿卢生不当人,百般威胁、凌辱和折磨:
【红衲袄】打你个老头皮不向我门下参,打你个硬骹儿不向我庭下跕。打你个蠢流民尽着,打你个暗通番该万斩。〔生〕宇文融可恨,可恨。〔丑〕宇文相公甚么样好人,你也骂他?打你个骂当朝一古子的谈。〔生〕不要哩,朝廷有用我之时。〔丑〕打你个仗当今一块子的胆。〔生笑介丑〕打的你皮皮开肉绽还气岩岩也。打了呵,还待火烙你个皮铁寸嵌。
然而,等到朝廷“召还”卢生的圣谕一到,他立即就换了一副嘴脸:自己将自己绑缚阶前,跪在地上,低三下四地求卢生恕罪。卢生倒也通达,笑着说:“起来,此亦世情之常耳。”崖州司户这一形象,显示了汤显祖在讽刺艺术方面的巨大才能——寥寥几笔,就将一个“合法的施暴者”塑造得入木三分,形神毕肖,使人过目难忘,四百年后读来,仿佛冷水浇背,犹觉寒气扑面。这是一个灵魂已经卖给魔鬼的人。他生来就是权力的奴才,只看上司的眼色行事,只相信刀和剑的力量——这样的爪牙,分明就是一个虐杀无辜者的恶徒。
①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6页。
②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三,卷二百二十六,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566页,第3955—3957页。
③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二十六,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956页。
④蔡东藩:《明史演义》,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76—478页。
⑤汤显祖:《汤显祖集全编》(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481页。
⑥⑧⑨⑩汤显祖:《汤显祖集全编》(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498页,第2884页,第2997页,第3055页。
⑦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6页。
⑪汤显祖:《汤显祖集全编》(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070页;引文标点,有所改动,与原文略异。
作 者:
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编 辑:
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文坛纪事
名作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