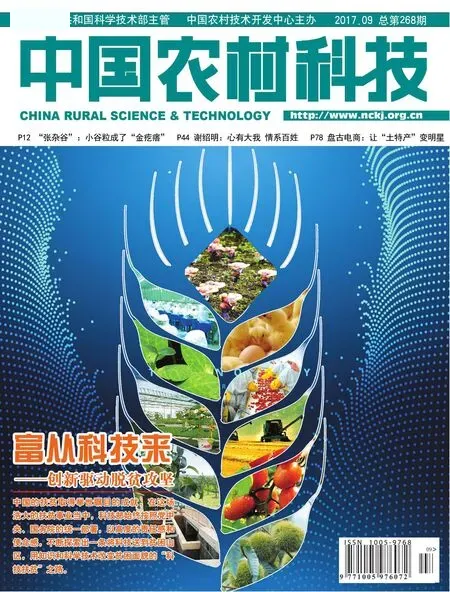谢绍明:心有大我 情系百姓
本刊记者|王雯慧
谢绍明:心有大我 情系百姓
本刊记者|王雯慧

2006年4月,原国家科委顾问谢绍明以82岁高龄重返大别山,关心农民的产业发展和脱贫增收情况。
他出生于革命家庭,全家有九口人为了革命流血牺牲,深植于血液的信仰让他时刻挂念着贫苦农民。他曾到苏联留学,为我国的航空工业做出贡献。他是科技扶贫的率先探索与实践者,从南到北、由东至西,他走遍了中国这片土地上最贫穷的地方。他说,唯有科技才能真正解决贫困,让老百姓富起来。
于漫漫历史,人生何其短暂,于浩渺星空,人是如此渺小。但有一些人,他们心有大我,对贫苦百姓爱得深沉,他们将情怀付诸实践并为此奋斗一生,这样的生命注定不平凡。
1925年,谢绍明出生于陕西延安。他是谢子长将军的儿子,十四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去苏联留学,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贡献。他是科技扶贫的率先实践和推动者,从战争到和平,他的命运跌宕起伏……
2017年7月,记者第一次见到了谢绍明。如今已经92岁的他,眼角和脸部的肌肉有明显下垂的痕迹,背有些曲驼,两鬓皆霜,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久经岁月沉淀的柔和与淡然。
“现在扶贫工作做得怎么样?老百姓生活过得怎么样?”还不等记者做完自我介绍,谢绍明便急切地问询起身边的工作人员扶贫情况。
他听得很仔细,随行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到“挂职”一词时,谢绍明连忙打断:“扶贫有没有挂职的,都在哪里挂职?有没有好好干?”说起与扶贫有关的事,他的眼睛亮了起来,那颗心系贫苦百姓的赤子之心从言语间流露……
赓续信仰 心系贫苦农民
大雪了无痕,英雄有迹可循。一个人的信仰与情怀总是与其独特的成长环境和心路历程有关。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陕北延安,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面对敌人时像雷电一样凛冽,对待贫苦百姓像亲人一样温暖。这便是谢绍明的父亲——谢子长。
谢子长出生于1897年,他和刘志丹一起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是陕北红军和苏区主要创建人和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他组织创办农民讲习所,组织农民协会,领导人民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谢青天”。1934年谢子长在河口之役时负伤,1935年2月因伤与世长辞,年仅三十七岁。为了纪念谢子长创建陕北根据地的功绩,中共西北工委把他的家乡陕北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

谢绍明
谢绍明说,“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我们老家就被国民党占领了。因为我父亲的缘故,敌人围剿时只要是跟谢家有关系的人,抓住就杀。我家直系亲属中,参加革命17人,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就有9个。在我父亲养伤期间,我一直和他在一起,他告诉我,要为人民做事。”
往事娓娓道来,仿佛看到了黎明前的延河故土,那些怀揣民族大义的有识之士与敌人殊死搏斗的身影。
谢子长去世时,谢绍明刚刚10岁。“我父亲在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对不起众乡亲,我为他们做的事情太少了!’”父亲临终前的牵挂,根植于谢绍明的记忆之中,也成了他日后的精神指引和人生所向。
攻坚克难 为航空工业添砖加瓦
谢绍明在革命家庭中锻炼与成长,从八九岁开始,儿童团、鸡毛信、放哨、捎路条……这些电影里的情节是他真实的童年记忆。
1939年,十四岁的谢绍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日本投降,年仅20岁的谢绍明成为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干部之一。1948年,为了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培养一批高层次的建设人才,中共中央选派谢绍明、李鹏、邹家华等人赴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1954年谢绍明第二次留苏,回国后,先后担任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厂副厂长、沈阳一一九厂厂长等职。那时候,厂里随处可见苏联专家的身影。

谢绍明(左二)深入大别山区走访贫困户
到了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可是很多技术都到了紧要关头。不服输的谢绍明心怀党和国家对他的期望,他深知航天工业对祖国意味着什么。他组织攻关小组攻坚克难,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咸菜就着窝窝头,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在厂里一住就是几个月,就连妻子分娩也错过了。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1963年,地对空战术导弹的心脏——自动驾驶仪终于在一一九厂研制成功。1975年,谢绍明调入北京,参与国防工办主持的《战术导弹十年规划》。1981年谢绍明调入国家科委,直至离休时任国家科委顾问。
筚路蓝缕 从大别山开始科技扶贫之路
春秋荏苒,谢绍明为国家的航空工业耕耘几十年,但他始终记得父亲遗愿。他说:“开头几十年我一直在军工部门,从航空工厂到导弹工厂,这是国家的需要。为贫苦老百姓做事,才更是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我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农民。”
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给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出了个题目:“能不能用科学技术帮助革命老区百姓解决温饱问题?”这一年,谢绍明61岁,他主动参与到国家科委的科技扶贫领导工作中。
老百姓到底过得怎样?怎样用科技的力量帮助老百姓脱贫致富?谢绍明带着调查组来到大别山区。
“我们先去了大别山地区转了一圈,首先是到了湖北黄冈的英山县、罗田县,安徽省的金寨县、潜山县和太湖这几个地方,还到了河南的信阳。”
谢绍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解放快40年了,大别山的老百姓还是那么穷。“吃饭没有米,穿衣没有布,房子还是土胚房。我去到一户人家,吃的还是政府的救济粮,一块猪皮就是一家人半年的食油,还有些人家连个灶台都没有,几块石头支起一口锅……”直到现在,谢绍明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到大别山的情景。
从大别山回来后,谢绍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大别山培育过多少优秀的战士啊!他们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流血牺牲,可是如今,解放快40年了,大别山的老百姓还是这么穷!
怀揣着对贫苦百姓的悲悯和爱,谨记父亲的遗愿,谢绍明全身心投入到科技扶贫工作中来,他要让革命老区的贫苦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不能忘了贫苦农民,不能对不起他们。”
经过实地走访调研,谢绍明了解了大别山地区的基本情况。“大别山以南属于长江流域,以北属于黄河流域。老百姓世代以种桑养蚕为生。在英山县,一些农户种茶卖茶叶,我们到卖茶叶的市场上看,都是一些比较粗糙的老茶,卖几分钱一斤都没人要……在罗田,板栗树倒是很多,但是产量不高,一棵树上就结几斤板栗。”
知道了问题所在,才能对症下药。谢绍明带着这些问题反复和国家科委领导及地方领导、科技人员研讨。没过多久,他再次带队来到了大别山,这次一同进山的还有来自农业大学、地方农科院的一批科技人员。
“我们调了一批科技人员,分别到大别山区的六个县。那时候一个县里面只能派一名科技人员,最多两名,人多了连路费都出不起,条件很艰苦。就这样我们国家科委派的人和鄂豫皖三个省派的人,慢慢形成科技扶贫团……”谢绍明回忆道。
不辞辛劳 踏遍山河万里
从大别山开始,科技扶贫的序幕由此拉开。从此,一年四季,不论严寒酷暑,不惧山高路远,谢绍明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的心里始终惦记着贫困百姓。
“有一次我到安徽金寨访问的时候,一个老太太问我,外面是不是又打仗了,你们没处跑了又跑到我们这里来了?”
“还有一次我去湖北郧西县考察,我们就走路到村子里。山坡上有那么几户人家,我去院子里一看,站着一个30多岁的男的,旁边站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还有一个瞎子老头,地上有一小堆地瓜,还有一小堆苞米。我就问老太太,你怎么睡觉?她指着一堆稻草说,那就是我睡觉的地方。”
谢绍明一次次被眼前这些贫穷所震撼。“他们过得实在是太苦了。”因此,他的脚步不断向前。
1992年,谢绍明来到青海牧区调研。“宋健让我去青海牧区看看,说是牧民的皮毛都让小商贩把钱赚了。”这一次到了牧区以后,谢绍明走访当地的牧民了解情况,去市场上了解行情。然后向牧民提出组织牧民合作社的建议。“这样牧民就可以自己组织起来,把皮毛拿到市场上去卖,钱就不被小商贩赚了,牧民手里才能有钱。”青海牧民合作社便由此成立。
年复一年,谢绍明几乎走遍了祖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最穷的地方。他的脚步从大别山、井冈山、到陕北延安;从贵州黔西南苗族地区,到北方边疆的赫哲族地区,和南边的海南黎族地区。很多地方连路都没有,步行两三个小时是平常事。一遍遍的走访调研,了解情况,根据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对症下药,引进新品种和新技术,示范推广,发展产业,让科技发挥最大的作用。湖北罗田的板栗,陕北的红枣,英山的茶叶,这一个又一个的产业无不凝聚着科技人员的心血。
身体力行 凝聚社会力量
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中国的科技扶贫从革命老区拉开战线,逐渐扩散到全国,也感染了一大批心系祖国贫困地区发展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
1992年,香港浸会大学理学院院长吴清辉教授组织“香港学者协会大别山考察团”,对大别山地区的科技扶贫工作进行了实地考察。通过这次考察,学者们一致认为科技扶贫是偏远贫困地区发展的可行路子。
为了号召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到科技扶贫工作中来,1993年6月,谢绍明率团赴香港,向香港各界介绍科技扶贫的情况与成果,与香港实业界座谈。同年12月,香港学者协会发起和筹集正式设立了“振华科技扶贫奖励基金”,用于奖励在扶贫第一线的科技人员。
只有科技人员得到相应的待遇,才有劲头才能更好地为农民办事。谢绍明惦记着贫苦农民,也惦记着那些为农民做事情的人。1995年,在谢绍明的积极奔走下,“王义锡科技扶贫奖励基金”成立。
“王义锡是一位老党员,也是大型民营企业—青岛面粉机械厂原厂长,是一位优秀的民办科技企业家。王义锡捐的钱用来鼓励和支持在老(革命老区)、少(少数民族地区)、边(边疆地区)、穷地区科技扶贫工作的科技人员。”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科技扶贫事业,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到扶贫中来。谢绍明的心里是欣慰的,因为在他的心里,没有比让贫苦农民过上好日子更重要的事情。
赤子之心 识人与谏言
如果一个人对信仰保持执着,对世界保持单纯与热情,这种感情我们常常称之为“赤子之心”。谢绍明便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心里,谁对老百姓好,对农民好,谁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他说,自己记性不好了,不如从前了。但说起扶贫的事,讲起扶贫的人,他的记忆无比清晰。
董水根就是谢绍明口中那个不错的人。

谢绍明与本刊记者(拍摄于2017年7月)
“董水根这个人很不错,他原来是安徽农科院派去潜山县搞扶贫的,挂职副县长。他去以后,大力发展茶叶,搞了一种叫做剑毫的茶叶,这种茶叶泡在水里能竖起来,跟剑一样。他把这种茶叶用天柱山命名,叫天柱山剑毫。后来这个地方的茶一下子从几块钱一斤卖到了八九百块一斤。他本来是挂职副县长,后来老百姓舍不得他走,他就把老婆孩子都带到那儿去了。再后来他得了癌症去世了……天柱山剑毫茶叶到现在还很有名。”
“张力田也是个很不错的人,张力田是湖北省农科院的一位科技人员、板栗专家。他刚到罗田县那一年,跑到山上去一看,一棵树上就挂几颗板栗。原来是树的雄花多,雌花少,问题就出在这儿。他研制了一种药水,滴在板栗树的根上,第二年雌花就多了,雌花多了挂果就多了。后来他长期驻扎在罗田县,教老百姓技术,发展板栗产业,现在罗田已经成了主要的板栗供应基地……”
对于关心老百姓的人,谢绍明总是不吝赞美,这是因为他对贫苦百姓爱得深沉,也源自于从小根植于内心的信念。
“我受的教育就是共产党都是农民的孩子,都是穷人的孩子,所以我们不能忘了农民!”谢绍明说,“那一年我给胡锦涛写过一封信,我的建议就是要减轻贫困地区农民的负担。”
事实上,这并不是谢绍明第一次给领导人写信。早在1994年,谢绍明在给国务院领导的报告中建议,组织向贫困地区捐赠衣物的活动。这份报告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批复,由此,中央各机关、军委各单位、北京及省委等单位掀起了一场向贫困地区捐赠爱心衣物的活动,这场爱心义举活动为贫困地区的儿童送去了温暖。
“你们要替我到大别山去看一看”
听谢绍明讲过去的往事,仿佛看到了十来岁的他在延安当“小兵张嘎”时的意气风发,又仿佛看到了他在青年时期为了建设新中国的闯劲儿,亦或是61岁的他踏上大别山时的情景。那些真实发生过的场景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但走过的路不会不留痕迹。
谢绍明说:“我最后一次到大别山是2006年,那是在我做完心脏搭桥手术以后,我就想去看看大别山怎么样,有没有变化。我看到老百姓把土坯房子都变成了砖瓦房,茶园也管理得很好,板栗也长得好……我们还是做了一点事情的,还是有一点收获的。”
他的脸上露出些欣慰的神情,语速加快,声音变得昂扬。
“‘房子可以冲掉,田地可以冲掉,但是我脑子里的科技冲不掉!’这是一位因科技扶贫而富强起来的农民在遭受洪灾而一无所有时说的话。”谢绍明一直清楚地记得那位农民说这句话时的自信和坚强。
“依靠科技脱贫致富,我到现在还惦记着这个事情。现在国家富裕一点了,钱多一点了,政策也很好了。我觉得科技扶贫的力度可以再加大一点。”谢绍明说。
同行的人说,“谢老一说起科技扶贫就激动,他现在身体不适合长途跋涉……”采访结束时,谢绍明站起身来送记者。他的背有些曲驼,行动也有些缓慢。他说,“我还想到大别山去……我走不动了。你们要多到贫困地区去走一走,替我去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