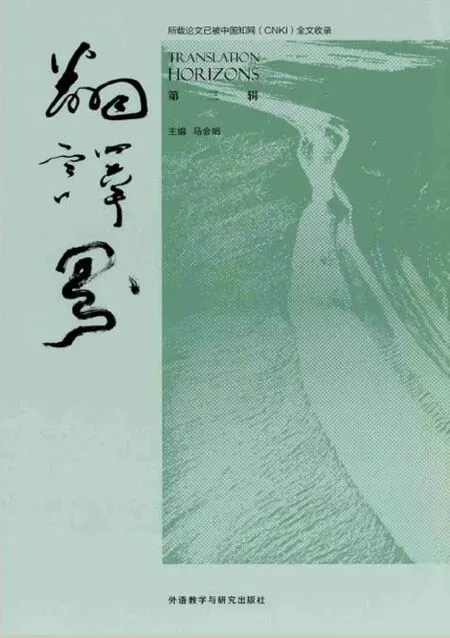口译记忆研究综述*
李 晶
南开大学
口译记忆研究综述*
李 晶
南开大学
在跨学科的口译过程研究上,记忆是重要的研究议题。据此,本文将以中西方口译记忆跨学科研究的历史、问题、发现、方法和未来方向为逻辑理据,分析二者的异同。重点探讨认知心理学等学科对口译记忆研究的介入,厘清跨学科口译记忆研究的发展脉络,以帮助研究者和从业者把握口译研究发展的多学科融合发展态势。
跨学科;口译记忆;中西对比
1.引言
记忆在口译活动中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口译研究中的重要研究对象。作为口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参数,记忆跨学科的意义在于本身所具有的认知特征及其他学科对其运作机理的合理解释和数据支撑,以及口译其他专项技能如注意力、笔记与记忆之间的密切关系等。
莫瑟·梅塞(Moser-Mercer, 2002)多年来一直是以跨学科的科学方法研究口译的领军人物,对长时记忆的作用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很久以前,良好的(工作)记忆就被视为口译员完成同传任务的核心技能(Herbert,1952; Seleskovitch, 1968)。从此以后,就有研究者通过实验来比较专业译员和非译员的记忆容量的差别,然而并未得出确定的答案,有些结果还自相矛盾(Mickkelson & Jourdenais, 2015; Köpke & Signorelli, 2012)。贝德利和希奇(Baddeley & Hitch, 1974)最初在动物身上做工作记忆的实验,结果表明每一次实验中的信息储存量都不同。贝德利和希奇(Baddeley &Hitch, 1974)针对短时记忆提出“应该用工作记忆取代短时记忆概念”,由此提出了工作记忆模型,认为在短时记忆中可以进行大量的加工和决策,从此工作记忆这一术语被广泛用于口译研究。达罗和法布罗(Daro& Fabbro, 1994)依据贝德利(Baddeley, 1990)的工作记忆理论及塔尔文(Tulving, 1987)的程序性、语义性和场景性记忆理论,提出了同声传译的记忆通用模型(Moser-Mercer, 2002)。兰伯特(Lambert, 1983)的深度处理模型建立在克雷克和洛克哈特(Craik & Lockhart, 1972)的多层次处理模式基础之上,提出对内容的记忆依赖于对下段信息处理的深度。由此可见,口译记忆的研究大多依托其他学科的科学机制为其寻找描述和解决问题的路径。
鉴于国内外现存文献中缺乏对跨学科口译记忆研究的系统梳理,本文将立足于国内外有关口译记忆跨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比分析,找寻口译记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总结现存研究方法的得失,探寻未来口译研究的发展方向,以在口译研究多学科的借鉴上有新的收获。
2.口译记忆研究的学科间性
口译研究自20世纪50到60年代以来经历了肇始与奠基、思考与探索、存疑与调适等几个明显的发展阶段,目前已经进入迅速发展的阶段(Pöchhacker, 2010)。口译研究的学科发展进程主要表现为: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的以口译实践经验总结为主的早期研究;60年代兴起的实验心理学研究;70年代起,以“释意理论”为标志的“巴黎学派”曾长期占据西方口译研究的主导地位,在口译研究中一度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1986年意大利特里雅斯特口译大会为标志,口译实证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兴起,进入“新兴期”。进入21世纪后,口译研究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均呈现活跃的多样化态势,是谓“多样化”时期(王斌华,2013:8-15)。有关口译记忆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学科的特质。作为口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忆本身就是一个认知过程。因此认知心理学在口译认知加工机理的阐释上为其提供了依据。以往的口译记忆研究多集中在长时记忆、短时记忆和工作记忆上,更多侧重研究的科学性。记忆的物质基础是人的大脑。由于神经语言学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在大脑的不同区域里找出各种记忆。例如,各种记忆都要通过和听觉、视觉、触觉区域相连的STM(短时记忆)缓冲区临时储存,然后传递到在前额皮层的工作记忆,最后到达永久性记忆。大脑在处理语言中居于主宰地位,而记忆则是其处理语言所依附的重要手段(桂诗春,2011:41-42)。据此可以判断口译记忆与神经科学密切相关,且能从中寻找记忆运作的原理。就未来口译记忆研究而言,可以考虑从译员个体特征入手,如通过译员临场的情绪稳定性、焦虑度和注意力分配、发言人的讲话风格(如年龄、口音、语速、语调、音高)以及两种语言不同方向的转换(如汉译英和英译汉由于结构差异造成的不同传译效果等变量对记忆所产生的影响)。以上维度凸显了记忆研究的人文性特征。从以上口译记忆研究的发展趋势上看,跨学科将成为未来口译研究的风向标,同时为口译研究和实践进行了合理的定位。
2.1 认知心理学对口译记忆的研究
在跨学科口译研究中,认知心理学与口译理论结合最为紧密,成果也最为丰硕。认知处理是口译研究过程的最主要研究范式。认知心理学的核心内容就是研究信息是如何获得、储存、加工与提取的。杰弗(Gerver,1976)提出了同声传译信息处理模型(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利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对同声传译中译员的时滞、记忆使用和输出监控进行了长期观察,重点研究影响口译输出的三个重要变量:噪音影响、输入速度和口译记忆,创建了同声传译第一个信息处理模型。由此看来,信息加工系统是对口译记忆的认知描述,重在描述性和实证性。20世纪80年代,以格尔瓦(Gerver)、彼得·莫瑟(Peter Moser)和马萨罗(Massaro)等人为代表的口译研究者以资讯处理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的初期研究。克雷克和洛克哈特(Craik & Lockhart, 1972)两位心理学家认为,认知心理学所说的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应该是大脑认知机制对信息进行不同深度的编码处理的功能体现。也就是说,记忆时间越长,此信息输入所需要的语义、认知分析就越多。信息提取的难易程度取决于被处理的深度,程度越深,日后该信息越易被提取,可利用的提取线索越多,记忆就越好。据此,兰伯特(Lambert, 1988)将信息处理深度定义为“输入信息所经过的一系列等级式的处理阶段”。其对口译信息处理深度的研究运用了实验法,比较了同声传译、交替传译、“影子练习”和“听”四种任务过后译员对信息的记忆能力。其实验结果显示,“听”之后的信息记忆效果最好,交替传译次之,同声传译再次之,“影子练习”排在最后。除兰伯特(Lambert)的研究外,吉尔(Gile, 1995)通过观察法和实验法分析了交替传译过程中记笔记与注意力的关系。因为笔记是短时记忆的得力助手,可以借此提高记忆的准确性。然而,通过实验证实,“记笔记”会转移译员用来“听”的注意力,并导致译员听力质量的明显下降。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的不同研究表明,承载人类知识的记忆不是一个单一性的功能体系,而是由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两大体系构成的(仲伟合,2012:83-84)。吉尔(Gile, 1995)在跨学科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卓著,曾经提出了认知负荷模型(Effort Model)SI=L+P+M+C,其中SI指同传,L是听解,P是语言输出,M是短时记忆,C是协调,其对译员有限的精力分配问题进行了科学的描述,合理地解释了译员的错译/漏译现象(Gile,2011: 156)。
国内在跨学科研究上主要侧重认知心理学层面的口译研究,多集中于探究源语理解的心理过程、口译短时记忆规律、口译笔记认知基础等(冯之林,1997;鲍晓英,2005;江晓梅,2011),如国内学者孔菊芳的《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谈口译中的短时记忆》、韩小明的《从记忆机制看口译教学中记忆能力培养》以及刘莹的《口译记忆机制和记忆策略研究》等。上述成果基本上是从口译记忆机制进行口译策略研究的。刘敏华(Liu,2001)通过实验法对同声传译中的工作记忆问题进行了研究,考察了专业译员在发展过程中的工作记忆对其口译产出的影响。刘敏华(Liu, 2004)在其同传工作记忆和专业技能的研究中指出,和非专业人士相比,译员的专业能力并非依靠更大的工作记忆容量,而是凭借口译职业领域的专门技巧,即在工作记忆的信息处理上更加高效。在口译过程中,译者不仅需要进行双语的转换,更需要对输入的信息不断进行取舍。张威(2007)运用认知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的理论和实验方法对同传中的工作记忆进行了实验分析。吴文梅(2015)利用认知心理学,尤其是记忆心理学与记忆方法等相关理论或者论述,尝试构建了口译训练模型APEC Model,深入、具体描述口译训练的理念、过程与方法,对口译记忆训练起到了一定的指引作用。所谓的APEC Model为M=A+P+E+C, 即口译的语篇分析、信息加工、意义编码、任务协调这一系列操作过程。本模型吸收了记忆心理学的有关理论,深入、详细地描述了口译记忆训练的理念、过程与方法,并把握了“任务协调”与“信息加工”两个关键核心概念,能一定程度上运用于口译训练与实践或者用于解释与预测其中的现象与规律。
从以上口译记忆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对比上来看,西方更侧重理论和过程的描述,对口译加工过程进行了一种纯理论的阐释,缺乏客观而充分的实证数据;国内则更侧重口译研究的应用性,重心在技能的训练上。
2.2 心理语言学对口译记忆的研究
莫瑟–梅塞(Moser-Mercer, 1978)的同声传译过程模式以心理语言学的话语理解模式为基础,既关注了短语和句子层面的源语输入加工,同时也反映了源语输入驱动的连续理解过程与长时记忆的知识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Pöchhacker, 2009)。近些年来,立足于心理语言学基础上的口译记忆策略研究成果并不鲜见,如斯科威尔(Scovel, 2000)指出,听是一个包括注意、理解、记忆和评价的过程,解析了听对口译的重要性,为口译记忆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国内研究方面,董燕萍(2005)通过描述口译的心理过程,即言语听辨和理解、言语计划、形式合成和发音,提出了工作记忆作为同传的核心问题,训练注意力的分配,合理断句以及避免逐词翻译以提高工作记忆效率,对口译训练策略进行了描述和论证。
上述代表性研究成果皆为口译记忆研究上的心理语言学解读,并科学地提出了口译记忆提升的策略。西方更侧重口译运行机制和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国内则更倾向于对口译教学实践的指导。
以上口译方面的跨学科研究,基本上与口译中的记忆密切相关,因为在口译过程研究中,记忆是基石。从跨学科研究成果上看,主要侧重口译的认知过程描述及口译现象的揭示。从上述中西方的口译记忆研究上来看,西方从20世纪50年代业已开始,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且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上有所突破(Gile, 2000; Gile et al.,2001; Pöchhacker, 2004),而国内的口译研究起步较晚,80年代有关刊物上只登载极少数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单纯理论说明的层次,有关口译记忆研究主要是根据经验总结具体的口译记忆技巧以及在教学和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情况。虽然也开始认识到并强调实证研究不可替代的作用(王欣红,2004;刘和平,2005),但实证性研究规模还很小,数量也很有限,远未成为研究的主流(张威,2006:66)。国内口译记忆大范围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21世纪之后发展迅猛,但相对西方的研究来说仍处在探索阶段。
综上,口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转换行为、一种复杂的认知行为、一种人际的交际活动、一种跨文化的社会活动,要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视角必然是多样的(王斌华,2013:13)。国内外有关口译记忆的研究借用了认知心理学、信息论、心理语言学、记忆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等。其实,任何学科对口译的研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如认知心理学对口译的研究中也不乏信息论的渗透,记忆心理学对其的研究也有神经科学的痕迹,这充分表明了口译记忆研究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研究特点,因此口译研究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都要走跨学科之路。这昭示了未来口译发展的大势,即多元视角、多学科融合。
3. 口译记忆研究问题与发现
3.1 自身理论的建构
中西方早期口译记忆研究都呈现出理论阐述充分而实证考察不足的特点。中西方口译记忆研究多从口译基本技能和口译员基本素质出发,强调记忆能力对口译活动的重要意义(Gile, 1995; Moser-Mercer et al., 1997; 鲍刚,1998;胡庚申,1993;李越然,1999),但是“研究仅停留在概念介绍和理论论证阶段,主要说明口译记忆的性质、特点、结构、作用等问题,研究中缺少严密的实验设计,也没有详细的实证数据,整体研究程序缺乏充分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因此研究结论的可验证性及实用性就受到很大影响”(转引自张威,2006:66)。国内的口译记忆研究主要参考国外的研究成果,没有自己独立的、自成体系的理论,建构意识较淡薄。研究方法虽然借用了大量跨学科的研究思路,但依旧存在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实证研究偏少的现象。这一方面源于研究条件的限制,如实验室设备;另一方面,费时费力、缺乏足够的样本等,导致研究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和局限。口译记忆研究的特点决定了研究的复杂性,如现场口译资料的保密性增加了真实样本研究的难度,实验对象不可控因素对研究效果的干扰,研究手段的单一性造成了研究效度的可信性以及研究人员的单一性,缺乏口译从业人员的参与等。因此,必须要全面、多向度考虑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综合性,同时也要考虑研究的实用性,不能只是停留在研究层面上,而是要在译员培训上走职业化道路,并在口译策略研究上加大力度。
3.2 专题性研究
在一贯以笔记作为辅助工具的交替传译中,长时记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却屈指可数。研究者多把目光聚焦在口译中的记忆,即工作记忆的研究上。贝德利(Baddeley, 1992)提出了记忆中的短时存储和中央执行控制功能。后来,施奥辛格(Shlesinger, 2000)针对贝德利模型中与记忆存储相关的预设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同传中译员并行的输入与输出会阻碍短时记忆的存储量,可能在两三秒之内,工作记忆中的发声记忆就会消失殆尽,因此针对输入较慢的译员来说,就很难应付高存储负荷的语料。工作记忆中最具争议的就是存储量的问题,因为它需要用多种广度任务进行测量(Mickkelson & Jourdenais, 2015: 69)。严格意义上来说,存储量的大小取决于长时记忆的效度,即科学地把短时记忆变成长时记忆可以通过激活知识点来寻找记忆组块中的信息,并通过不断强化使其常驻在长时记忆中。同时,译员的经验和知识宽度也能扩充长时记忆库的容量。帕迪里亚(Padilla et al, 1995)通过研究发现,在数字广度任务中,经过专业训练的译员要优于没经过专业训练的学生(如在九位数以上的系列数字听觉记忆测试中),由此表明,受训的译员在注意力分配上更加高效。西格诺里(Signorelli et al, 2011)研究了有关同传工作记忆中任务和年龄的影响,认为译者的工作记忆研究应该把年龄因素考虑进去。迪玛洛瓦(Timarová, 2012)证实了注意力控制(如工作记忆中的中央执行系统而非存储功能)的主要作用,样本包括28位专业译员,分配了五个工作记忆执行任务和一个同传任务,在相关性分析上得出结论,在同传多对多复杂模型下,不同的工作记忆包含了不同的子过程。总之,口译(同传)研究已经从储存功能和记忆量转向了控制不同加工任务的注意力中央管理控制系统的工作记忆上(Mickkelson & Jourdenais, 2015: 69)。
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口译记忆专题性研究有刘敏华(Liu et al, 2004)的同传工作记忆和专业技能之间的关系、董燕萍(2005)的心理语言学与外语教学、吴文梅(2015)的口译过程认知心理模型构建等。虽然贝德利和希奇(Baddley & Hitch, Baddeley, 2012: 5)对长时和短时记忆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研究,但只是广义的记忆研究,并未具体涉及口译活动中二者之间的关联。鉴于国内外研究缺乏对口译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的专题性研究,应加大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探究,使译员的工作效率得以提升。总之,相较于西方对口译记忆的描述性研究成果,国内更侧重其在实践中的应用性。
3.3 口译记忆的实用性
国内外口译记忆研究主要侧重口译的认知过程描述及口译现象的揭示,并没有过多涉及相应的口译记忆策略。翻译(尤其是口译员)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有限的记忆容量。因此如何科学地提升记忆容量就变得尤为重要。勒代雷(Lederer , 1981: 129)认为,口译是在词汇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的,因为口译要在发言人停顿之后才能操作。只有在停顿时,译员才能判断如何断句并进行意译。伊斯兰姆和莱恩(Islam & Lane, 1993)通过实证表明记忆单位是分句。作为口译,尤其是同传译员,对于“时间延迟”,即输入与输出的时间差的影响非常敏感。同传这一时间差一般在两三秒间,偶尔也有10秒的情况。时间差越短,越容易出错(如省略、添加、变化),时间差越长,内容省略越多,因为工作记忆信息负荷过重(Baker, 2001:188; Islam & Lane, 1993: 243)。由此可见,中西方口译记忆研究应更多瞄准口译记忆策略对口译实践的指导作用。
3.4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口译研究作为翻译学项下的子学科,一直处在“边缘化”的地位。这一方面源于口译研究的复杂性和难度,另一方面源于研究人员的局限性。要想深入和全面研究口译中的记忆问题,不仅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精髓,还要从实验室走出来,让更多口译从业者参与进来,这一方面可以通过采集真实语料提升研究效度,另一方面可以还原口译的真实场景,以培养口译实践的后备力量。从口译记忆深度研究来看,可以把焦点放在口译其他专项技能与记忆的互动关系上,如工作记忆与注意力的研究(Cowan,2000)、长时记忆与短时记忆之间的关联(Baddeley, 2012)、记忆与笔记的研究(Stern, 2011)、记忆与眼动的研究(刘艳梅等,2013)、交替传译过程中的错误记忆(王非、梅德明,2013)、手语与短时记忆的关系(贺荟中、方俊明,2003),由此说明国内外已经把目光转向口译记忆的深度研究上。
蔡小红(2001)认为,对口译程序模式进行深层次的分析需要借助于跨学科的研究。从口译研究的广度来看,应侧重跨学科融合的总体走势。刘和平(2005)指出,除继续跨学科和实证研究外,横向的联合应该是今后研究要走的路,也是深入研究的一种有效保证。横向既包括国内同语种、同课型、同专题的多视角和多方位研究,也包括国际范围的、围绕重大主题进行的多语种跨领域研究(刘和平,2005:71)。帅林(2007)认为,中国口译理论已开始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来研究口译过程、口译现象和口译实践,对翻译学科的建设发展和翻译理论研究话语的转型大有裨益。然而,国内理论研究相较于国外基础还很薄弱,专题研究人才还很稀缺,广度、深度尚待进一步扩展,普适性理论话语的推广与西方还存在着差距。
如上这些问题都是口译记忆研究的瓶颈,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略,笔者认为首先应该从其他学科中借鉴相应的理论或成果,因为口译记忆研究本身就具备跨学科的特质。口译记忆研究应该接受时代的挑战,不仅要尊重本学科的发展走向,还要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使交叉学科发挥应有的长处,为口译记忆研究的未来寻找合理定位和创新点。
4.口译过程的研究方法
口译研究的实证方法主要包括描写研究和实验性研究。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翻译行为,口译记忆具有其经验性和跨学科的特征,这就决定了口译记忆研究方法的选择。在口译研究中,记忆属于口译过程的中间阶段。有关口译过程的传统研究方法包括实验法、调查法、观察法、语篇分析法、经验总结法、理论思辨法和文献研究法。近些年来,随着口译研究的多向度发展,单一向度的研究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其效度需求,因此跨界合作成为研究的新动向,如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展开的同传质量评估(ECIS)项目、意大利里亚斯特大学的欧洲议会口译语料库(EPIC)项目和维也纳大学有关同传质量(QuaSi)项目。因此,借鉴更多兄弟学科的研究成果,吸纳其研究方法应该成为口译记忆研究未来发展的选择。
4.1 以描写为主的口译过程研究法
在口译加工中,语言转换与信息传递背后蕴藏着复杂的认知心理加工机制,往往涉及源语信息听辨、信息意义的表征与理解、信息暂时贮存、译语组织与计划、译语信息表达与监控等一系列彼此影响、相互制约的加工任务,语言听辨、信息转换、记忆资源应用等许多因素都会对口译加工及最终效果产生重大影响(王建华,2010:134-139)。在描写研究中,研究者在对自然环境下真实口译现场数据进行观察的基础上,就研究目标和研究问题进行尽可能客观的描写,进而形成某个方面的研究假设或得出研究结论。观察法在“生态效度”方面优于实验法,而且方便对研究结论进行重复验证(王斌华,2013:29)。
4.2 以实验性为主的口译过程研究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心理学研究范式引入口译研究并一度成为主流范式,实验法似乎在口译研究中占有很大的优势。在实验研究中,研究者一般使用设计模拟性口译实验的手段,在实验中尽量控制研究目标之外的变量,通过分析实验结果得出研究结论,或者验证描写研究中形成的研究假设。
4.3 其他跨学科研究方法
21世纪早期,口译研究者不仅继续采用语言学方面的工具,还采用了实证法和交际法来检验口译质量。目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盛行开来,针对口译产品的动态特征采用多种方法予以评估(Mickkelson & Jourdenais,2015: 376)。口译研究另一个趋势就是逐渐向应用上发展,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关系变得越发紧密。1991年厦门大学主持召开的全国首届口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奠定了我国口译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有声思维法通过口译过程的回溯对大脑中的思维活动进行捕捉,以使其显性化,这样可以方便研究者的取样和分析。黑尔和内皮尔(Hale & Napier, 2013)曾经归纳了口译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问卷调查法、人种学(包括采访、焦点小组、案例分析等)、语篇分析(对话口译)、实验法、口译教育与评估等。张威(2012)认为,口译跨学科研究打开了研究视角,丰富了主题内容和方法,并由此提升了口译质量和影响力。
国内具有标志性的成果是胡开宝等(2015)的《基于语料库的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研究》,其中在口译过程论述中谈到口译语料库的建设能够使研究者将口译过程与口译产品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从而更好地分析口译过程的某些方面。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不仅在定量研究中吸收语料库语言学的优势,还在定性中吸收来自心理学、神经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优势,因而实现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有机结合(胡开宝等,2015:17)。文秋芳和王金铨(2008)建立了“中国大学生英汉汉英口笔译语料库(PACCEL)”。虽然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还非常稀少,但这标志着口译研究在技术手段上的重大突破。
通过以上国内外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阐述,可以明显地看出国内外口译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多种方法融合的研究基调,而且国内的研究者在新视角、新技术的采用上基本上能够与国外研究前沿接轨,由此也确立了口译研究方法的未来走向,如口译不同交际环境对口译记忆效果的影响、口译员经验是否丰富体现在认知机制上的差别、口译认知理论在教学过程中的充分利用等。以上研究方法都会对口译的效果造成影响。布鲁尔和亨特(Brewer & Hunter, 2006)认为,多维方法研究对口译未来意义重大,如理论和理论验证、问题构成和数据收集、采集样本和概括总结、验证假说和因果分析、社会问题和政策分析等。这为未来的口译记忆研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和思路,为研究者打开了视野。
5.口译记忆研究未来发展走向
张威(2006)认为,口译记忆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跨学科研究的理论意识,改善研究策略与方法,设计更科学的实验程序与测量手段,对相关问题进行更细致的观察与分析。下图便体现长期以来对口译进行思考的进展情况,也反映了关键概念维度相对的主导地位:

图1 口译研究的“模因图”(Pöchhacker, 2016)
图1展示了口译历史研究所关注焦点的图景,然而这些现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作为研究者,不仅要以历史研究为基础,还要在实践中不断突破原有的研究框架,并且勇于尝试新的方法,拓宽新的思路。下面笔者将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口译未来发展的方向及可能性进行概述,以拓宽未来口译记忆研究之路。
5.1 微观口译记忆研究
口译中的记忆过程,无论是编码还是储存,保持还是提取,都是人脑的神经元根据经验而改变的能力,这种神经可塑性是记忆的基础,因此它是认知心理学的组成部分。记忆能力可以通过大量的实践活动获得,译者的这种认知能力完全可以习得,只要科学运用、合理组织大脑信息、掌握规律,就能使自身具备口译员的资格。从口译记忆的跨学科研究特征来看,主要是借助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来揭示口译过程的运行情况,因此口译记忆研究的未来依旧要相信科学、依赖科学来进行更具深度的研究。
笔者通过教学实践观察发现,语言学科的学生大多缺乏通识能力。学者里京曾倡导“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教育理念,在当今信息化、全球化、学科边界融合的大背景下,学科分化的劣势逐渐彰显,故而有必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心理、生理、时间、信息、知识结构等多元因素,优化构建基础通识教育学科,为学生的未来学习、成长和发展播撒通识的种子。通识内容会储存在大脑的长时记忆中,而长时记忆的稳定性和宽度决定了口译员是否能够应变突发情况,它的调动会丰富译员的思维,并且它随时调取以备不时之需。因此可以采取如下具体策略:通过不断重复来启动长时记忆、强化新的知识点、把握信息的语义特征等。短时记忆能力的提升可以凭借增强逻辑能力、影子训练、信息条块化、形象记忆、连接记忆、框架记忆等方法,从而增加记忆容量。分子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利根川进认为,记忆并不是肉体的现象,而是心灵的现象。任何语言都要反映人的思想,因此排斥人的参与或规避语义的作用、忽视人的意识或意愿是不符合语言研究规律的。既然口译研究的本体就是语言的研究,且与当时的语境密切关联,因此要关照所涉及的任何一方,如研究者、译者、讲话人、听众、委托方、培训师、政策制定者、服务接受方等,从人本语义的视角来研究口译将会拓宽研究者的视野及范畴,也会逐渐使口译研究不光聚焦“硬科学”,也要瞄准涉及各方的“软科学”,即人为因素对口译效果的影响,如译员风格、口译语言的语义韵、对话中的话轮转换及发言人的口音特点等。
5.2 宏观口译记忆研究
除了以上探讨的口译记忆研究所借鉴的诸多学科(如认知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以外,口译记忆研究的未来还可以从思维科学、信息论以及其他人文学科中找寻跨学科的创新点。如托尼·巴赞所创建的思维导图,其中融汇了心理学、大脑神经生理学、语义学、神经语言学、信息理论、记忆和助记法、感知理论、创造性思维和普通科学。如今思维导图逐渐被学习者认知,因为它能够在学习者建构完整的知识体系、链接畅通的知识通道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张思维导图可以帮助学习者按其所需寻找到相应的信息点,将纷繁的内容清晰化,因此对于记忆的提升会更加科学高效。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研究发现,大脑对新事物的遗忘进程并非呈均衡发展态势,而是“先快后慢”的发展原则,即在记忆的最初阶段遗忘的内容最多,速度也最快,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的内容和速度开始逐渐减少、减慢。当某种记忆在大脑中保持了相当时间之后,遗忘就有可能不会发生了。这样的结论非常有助于教学过程中课堂内容的设计,如为了避免遗忘,不断通过温故知新来强化记忆,同时也可以为译员的培训方案带来启发。上述不同角度对口译记忆研究的介入为其开辟了广阔的思路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正像哲学家威拉德·冯·奥曼·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对“语言是社交艺术”的界定以及对翻译所下的定义,即“翻译的不确定性”,口译作为翻译研究的分支同样具有动态特征和社交属性,因此许多学科可能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此时不仅要依托科研人员、教师的案头研究,还要充分利用译员的真实语料资源来脱离“场外”研究的怪圈。通过口译记忆的影响要素分析来找寻增效的路径和方法,如译者的个性特征和临场发挥、发言人的讲话风格、口译现场情境的设定、口译材料的难易程度等皆会或多或少地对口译记忆质量产生影响。因此,只有把口译记忆研究放在社会情境之中,才能拓宽思路,积极寻找跨学科的交汇点和社会发展核心问题的契合点(Mason, 2009: 123)。
6.结论
1962年,美国哲学家库恩提出了范式理论1,他认为当代科学领域中实际上存在许多“科学共同体”或“学科矩阵”。这些学科之所以形成“共同体”,一是因为它们的探索目标大体一致,二是因为它们的探索领域互有交叠(库恩,2012)。口译记忆跨学科研究的未来走向就是要形成与其他学科的“共同体”,因为在口译记忆研究的“学科矩阵”中,其他学科可以为其研究打开思路、提供方法、带来灵感。
口译记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一方面可以帮助口译记忆研究者拓展视野,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另一方面又可以从其他学科中找寻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使口译记忆研究更加科学和全面。张威(2012)曾推出了具有标志性的跨学科研究成果,通过哲学思辨对口译的发展史和未来前景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全面且深入,引发了业界对口译未来的发展走向深深的思考。鉴于记忆的特性,人类的思维研究仍处于“黑箱”状态,对口译记忆的了解和策略的探索还非常有限。因此,口译活动中有关记忆的研究无形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任务,并面临巨大的挑战。口译记忆的前期研究借鉴了大量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支撑和实证数据,因此口译记忆的未来依旧要循着跨学科的研究路径来寻找突破点。
毋庸置疑,未来的口译记忆研究,无论是微观抑或宏观,都要借力其他学科的精华,因为口译是一个复杂的信息处理过程,在信息的编码处理过程中,有多种因素影响或制约着口译记忆的效度,这诸多因素都会辐射到不同的研究领域,因此学科融合将是未来口译记忆研究的必由之路。本文通过阅读国内外大量文献,以口译记忆的跨学科为研究重心,结合认知心理学等口译记忆常见的研究领域为分析对象,通过中外研究的对比分析,对未来的研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及建议,希望在口译记忆研究上能够给研究者和从业者带来一些新的视角和思考。
注释
1. 自从库恩首次从范式及范式转变的角度来分析自然科学学科之后,“范式”这一术语就成为研究自然科学历史及其理论发展的基础。如巴黎学派倡导的口译释意理论研究范式。
Baddeley, A. D. (1990). Human Memory: Theory and practice. Welshpool, Wales: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Baddeley, A. D. (1992). Working memory. Science, 255(5044), 556-559.
Baddeley, A. D. (2012). Working memory: theories, models, and controversies. Th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 1-29, 63.
Baddeley, A. D. & Hitch, G. J. (1974). Working memory. In Bower, G. (Ed.),Recent advances in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Vol. VIII (pp. 47-90). New York:Academic Press.
Baker, M. (2001).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Brewer, J. & Hunter, A. (2006). Foundations of multimethod research: Synthesizing styles. Thousandoaks, CA: SAGE.
Cowan, N. (2000). Processing limits of selective attention and working memory:Potential implications for interpreting. Interpreting, 5(2), 117-146.
Craik, F. I. M. & Lockhart, R. S. (1972). Levels of processing: A framework for memory research.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1, 671-684.
Daro, V. & Fabbro, F. (1994). Verbal memory during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Effects of phonological interference. Applied Linguistics, 15, 365-381.
Gerver, D. (1976). Empirical studies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 review and a model. In Brislin, R. (Ed.), Translation: 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 (pp. 165-207). New York: Gardner Press.
Gile, D. (1995).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Gile, D. (2000). Language processing &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Issues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to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Gile, D., Dam, H. V., Dubslaff, F., Martinsen, B. & Scholdager, A. (Eds.) (2001).Getting started in interpreting research: Methodological re fl ections, personal accounts and advice for beginner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Gile, D. (2011).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Hale, S. & Napier, J. (2013). Research methods in interpreting: A practical resource.New York: Bloomsbury.
Herbert, J. (1952). Le manue de l’interprète. Geneve: Georg.
Islam, W. P. & Lane, H. (1993).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nd the recall of sourcelanguage sentences. 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8(3), 241-264.
Köpke, B. & Signorelli, T. M. (2012). Methodological aspects of working memory assessment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16(2), 183-197.
Lambert, S. (1983). English recognition and recall in conference interpreters.(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tirling).
Lambert, S. (1988). A 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training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s. In Hammond, D. L. (Ed.), Languages at crossroads: Proceedings of the 29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pp. 379-387). Medford: Learned Information.
Lederer, M. (1981). La traduction simultanee – experience et theorie. Paris: Lettres Modernes.
Liu, M. (2001). Expertise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 working memory analysis.(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axas at Austin).
Liu, M., Schallert, D. L. & Carroll, P. J. (2004). Working memory and expertise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Interpreting, 6(1), 19-42.
Mason, I. (2009). Research training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3(1), 1-12.
Mickkelson, H. & Jourdenais, R. (2015).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preting.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Moser-Mercer, B. (1978).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Gerver, D. & Sinaiko, W. H.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p. 353-368). New York: Plenum Press.
Moser-Mercer, B. (2002).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New York:Plenum Press.
Moser-Mercer, B., Williams, S., Daro, V & Lambert, S. (1997). Skill component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In Gambier, Y., Gile, D. & Taylor, C. Conference interpreting—Current trends in research (pp. 133-14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adilla, P., Bajo, M. T., Canas, J. J. & Padilla, F. (1995). Cognitive processes of memory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In Tommola, J. (Ed.), Topics in interpreting research (pp. 61-71). Turku: University of Turku, Centre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Pöchhacker, F. (2004).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London & NewYork: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Pöchhacker, F. (2009). Inside the ‘black box’: Can interpreting studies help the profession if access to real-life settings is denied? The Linguist, 48, 2.
Pöchhacker, F. (2010). Why interpreting studies matters. In Gile, D., Hanson, G. &Poken, N. K. (Eds.), Why translation studies matters (pp. 3-14).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öchhacker, F. (2016).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2nd 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Scovel, T. (2000). Psycholinguistic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Seleskovitch, D. (1968). Interpreting f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oblems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Washington: Pen and Booth.
Shlesinger, M. (2000). Strategic allocation of working memory and other attentional resourc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Bar-Ilan University).
Signorelli, T., Haarmann, H. & Obler, L. (2011). Working memory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s: Effects of task and 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16(2).
Stern, L. (2011). Training interpreters. In Malmkjær, K. & Windle, K.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pp. 490-50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imarová, S. (2012). Working memory in conference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Doctoral dissertation, 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 and University of Leuven).Tulving, E. (1987). Multiple memoey systems & consciousness. Human Neurobio,(6): 67-80.
鲍刚. (1998). 口译理论概述.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鲍晓英. (2005). 帮助学生实现口译“信”的标准——记忆心理学在口译教学中的应用. 外语界,(3),37-42.
蔡小红. (2001). 以跨学科的视野拓展口译研究. 中国翻译,(2),26-29.
董燕萍. (2005). 心理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冯之林. (1997). 始发语何时变成目的语?现代外语,(3),52-62.
桂诗春. (2011). 什么是心理语言学.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41-42.
韩小明. (2004). 从记忆机制看口译教学中记忆能力的培养. 重庆工学院学报(6)156-158.
贺荟中、方俊明. (2003). 聋人短时记忆研究回顾与思考. 中国特殊教育,(5)28-31.
胡庚申. (1993). 怎样学习当好译员.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胡开宝、潘峰、李鑫. (2015). 基于语料库的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研究.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江晓梅. (2011). 同声传译概述策略及其干预研究. 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66-68.
孔菊芳. (2006).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谈口译中的短时记忆.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4),122-124.
库恩. (2012). 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越然. (1999). 论口译的社会功能:口译理论基础初探. 中国翻译,(3).
刘和平. (2005). 口译理论与教学.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71.
刘艳梅、冉诗洋、李德凤. (2013). 眼动法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与展望.外国语,(5),59-66.
刘莹. (2008). 口译记忆机制和记忆策略研究. 沿海企业与科技,(10),185-186.
帅林. (2007). 跨学科口译理论研究在中国. 中国科技翻译,(3),50-52, 14.
王斌华. (2013). 口译规范的描写研究——基于现场口译较大规模语料的分析.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8-15,29.
王非、梅德明. (2013). 交替传译过程中的错误记忆现象实证研究. 外国语,(2),66-75.
王建华. (2010). 基于记忆训练的交互式口译教学模式实证探索. 外语学刊,(3),134-139.
王欣红. (2004). 同声传译过程中的非语言因素. 中国翻译,(6),61-63.
文秋芳、王金铨. (2008). 中国大学生英汉汉英口笔译语料库.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吴文梅. (2015). 口译过程认知心理模型构建.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张威. (2006). 口译与记忆:历史、现状、未来. 外语研究,(6),66-70.
张威.(2007). 同声传译与工作记忆的关系研究——中国英语口译人员认知加工的实证分析. 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
张威. (2012). 口译研究的跨学科探索:困惑与出路. 中国翻译,(3),13-19,128.
仲伟合. (2012). 口译研究方法论.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83-84.
(责任编辑 蒋剑峰)
* 本论文为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下新型翻译教学模式构建”(15YJA740019)、2015年南开大学教改项目“《翻译与全球化》课程中的通识观”和2016《翻译与全球化》全英语教学课程经费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李晶,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与全球化、二语教学、教育心理学。
作者电子邮箱:121592628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