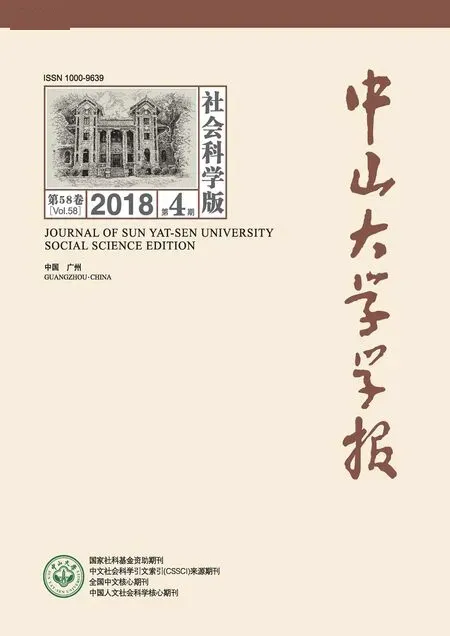跨语际文学接受的典型样本*
——早期来华传教士《三国演义》评介研究
陈 淑 梅
19世纪,经由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之手,《三国演义》开始了西传之旅。王丽娜、郑锦怀*王丽娜:《〈三国演义〉在国外》,《文献》1982年第12辑;王丽娜、杜维沫:《〈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文》,《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4期;郑锦怀:《〈三国演义〉早期英译百年》,《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3期。等学者曾论及《三国演义》的早期译本及其在西方的传播,本文关注的则是来华传教士对《三国演义》的评论和介绍。王燕对马礼逊词典中的《三国演义》介绍与郭实腊的《三国演义》评介有过详细研究*王燕:《马礼逊与〈三国演义〉的早期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冬之卷;王燕:《十九世纪西方人视野中的〈三国演义〉》,《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冬之卷。,刘丽霞等也研究了郭实腊、美魏茶介绍《三国演义》的文章*刘丽霞、刘同赛:《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三国演义〉的译介》,《济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她们引用的资料较为翔实,但有些结论和判断有失准确,分析也有待进一步深入。
本文论及的评介包括郭实腊《〈三国志*即今《三国演义》。明清时期有《三国志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三国志传》、《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等各种名称,传教士们通常将其称为“San Kwo Che”或“San Kwoh Chi”。在名称上未能与陈寿《三国志》很好地区分,也是传教士们混淆两者的原因之一。〉简介》、美魏茶《〈三国志〉中一位英雄孔明的介绍》、马礼逊《华英字典》中“孔明”词条以及卫三畏《中国总论》中谈论《三国志》的内容。如研究者们所指出的,在传教士评介《三国演义》的文章中,错漏、误读问题普遍存在。笔者认为,对于这些现象,简单的否定或者凭主观意愿勉强为之辩护都有失片面,从译介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是跨文化文学阅读与接受的典型症候,本身即是研究对象。鉴于此,本文将近距离勾勒《三国演义》给传教士们留下的初始印象,研究他们作为来自异域文化的非母语阅读者对《三国演义》的认识和理解,从中发现来华传教士对《三国演义》的“见”与“不见”、误读以及错位理解,挖掘其作为跨语际文学接受的样本的意义。
一、“见”与“不见”
马礼逊1807年来到中国,是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他1815—1823年出版的《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部汉英—英汉对照字典。这部字典除了解释字词意义,还有一些与中国历史文化有关的词条,包括古代名人。专门立为词条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名人并不多,不超过30人,而与“三国”有关的人物则有6位,分别是孔明、 曹操、刘备、孙权、孙夫人、夏侯惇,随文提到的还有董卓。另外,在“七星宝剑”的释义中提到《三国志》,在讲“太守”一词的历代沿革时提到了“三国”时期,在“妖”的释义中,马礼逊讲述了《三国演义》中(刘)玄德用猪羊狗血破除敌人(即张宝)妖术的故事。《华英字典》以《康熙字典》为底本,不少解释都是直接译自《康熙字典》。但以上这些与三国有关的内容,《康熙字典》除了“诸”的注释中有“又复姓。《汉书》有诸葛丰。《三国志》有诸葛亮”*陈廷敬、张玉书等:《康熙字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411页。这一句外,其余都未出现,更遑论列为专门的辞条。马礼逊对“三国”的熟悉及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华英字典》涉及的三国人物中,对刘备的介绍最为简短,只有一句:“三世纪中国内战期间的一位和蔼可亲而又杰出的将军。”*③④ 马礼逊:《马礼逊文集·华英字典》第4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542,779,714—716页。“孙权”词条下也只有一句:“生活于三世纪中国内战期间的一位国君,他跟蜀国国君刘备一起对抗力量日益增强的魏国。”③孙夫人、孔明、曹操占据了较多篇幅。对孙夫人的介绍主要是引自《三国志·蜀志·法正传》,如“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女们“皆执刀环立”等。“曹操”这一词条的主要内容大致是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对曹操所作评价的英文翻译,如“知人善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用法峻急,有犯必戮”、“雅性节俭,不好华丽”等。
篇幅最长的是“Kung-ming”④词条。在这一词条中,马礼逊介绍了孔明,并以孔明为主介绍了“关于那个时代的历史小说”《三国志》。在这一词条的开始,马礼逊引述历史资料,花了很多篇幅叙述汉末的乱象、董卓的残暴和黄巾起义。随后,马礼逊将历史材料与小说内容揉合在一起,叙述了刘关张三结义,魏蜀吴三国各自的国君,提到孔明的占星术、八阵图及木牛流马,最后还专门提及阿斗及“阿斗原是睡不醒”这一俗语,并说明“‘阿斗’被用来逗趣或激怒一个男孩子时,等于说‘愚蠢的木头脑子’”。这段译成汉语约为1 900字的文字中,对汉末历史的叙述很多,关于孔明的内容不到一半,对于孔明其人的直接介绍评价较简略,如“在三国内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身长八尺,自视甚高,常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对刘备忠心耿耿”、“擅长战术”等。另一方面,孔明为激司马懿战斗送他女士的服装、八阵图,去世前禳星延命等内容则被凸显出来,得到了详细叙述。显然,这些细节被认为是特别的,给马礼逊留下了深刻印象。前者很可能使马礼逊联想到了注重勇敢与荣誉的骑士精神,八阵图和禳星延命在马礼逊眼里则体现了异域文化的特异性。
郭实腊在《中国丛报》1838年第7卷第5期上发表了《〈三国志〉介绍》。郭实腊在文中说这部小说出版于14个世纪以前,把小说《三国志》的出版时间误为西晋陈寿的史著《三国志》的出版时间,这种混淆现象在当时传教士中并不少见。在这篇文章中,天示异象、黄巾起义、朝廷内乱、剪除董卓等内容占了一半的篇幅,而在原书中,这些内容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该文其余的内容集中在曹操与诸葛亮这两个人物身上,介绍了诸葛亮用火烧曹操的船(应该是火烧赤壁)、草船借箭、如何应对五路来犯之兵以及曹操在逃亡路上杀了热情招待他的一家、割发代首自我惩罚等故事,充分展现了诸葛亮的智慧和曹操的勇敢、纪律严明及不择手段。而全书的重点——三国之间的合作与斗争只是零星涉及,并无清晰脉络。只是在讲到吴(实际上文中此处并没有明确说明是“吴”)的时候写道:“另外一个在扑灭黄巾的战争中有功的将军占据了南方的省份,他凭着自己的机智圆滑在其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他要么与这一个要么与另一个结成同盟,以此保证自己的安全。”
郭实腊笔下,除了诸葛亮与曹操外,董承密谋除曹操的经过叙述得也很详细清楚,略去了中间煮酒论英雄、刘备与袁绍作战等内容,使密谋及失败的过程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此外,孙策斩于吉、左慈以法术戏弄曹操都占了较多篇幅。在《三国演义》中,董承密谋除曹操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内容,那些法术也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郭实腊专门将其挑选出来详述,体现出他的关注点所在:一方面对情节曲折紧张的阴谋感兴趣,另一方面,郭实腊评论孙策斩于吉说“这些细节显示出当时道教的流行”,可看出他对中国本土宗教较为留意。显然,这与其传教士的身份有关。
美魏茶1843年在《中国丛报》发表了《〈三国志〉中一位英雄孔明的介绍》。在这篇文章中,美魏茶叙述了刘备得到诸葛亮,“然后玄德发动了针对敌人的战争,在所有重要的事情上他都征求孔明的建议,有孔明作他的臂膀,他所有的事业都取得了成功”。随后就是刘备去世,指定诸葛亮摄政,中间的火烧新野、舌战群儒、草船借箭、赤壁之战中的神机妙算、三气周瑜等等大量内容都被略去了,而这些内容堪称《三国演义》的精彩片段,大多数中国读者都耳熟能详。
美魏茶的整篇文章侧重于介绍刘备死后诸葛亮的作为,总体而言,写出了他的责任感、智慧和意志,突出了诸葛亮不忘刘备临死的重托,为恢复汉室不辞劳苦、鞠躬尽瘁的精神。但诸葛亮六次伐魏的内容过少,病倒以至去世这部分的篇幅明显过多,超过前者的一半。对于具体的战争过程,美魏茶多数时候是以概述方式进行处理。如在叙述孔明最后一次出征伐魏与司马懿作战时,美魏茶只是说:“因为我们的英雄掌握着神奇的魔法,经常搞出令人好奇的把戏,使他的对手束手无策,有时甚至有丢失性命之虞。”略去了郑文的诈降以及诸葛亮诱司马懿劫寨、施法术歼敌等作战过程。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些内容非常有趣,能够充分体现诸葛亮的智谋。但美魏茶似乎更注重表现诸葛亮的道德光辉,对于其“智”的一面,则有意无意地作了淡化处理。
卫三畏1847年出版的《中国总论》“中国的雅文学”一章说:“中国文学中没有几部著作比陈寿在公元350年左右写的历史小说《三国志》更受人欢迎。”*[美]卫三畏著,陈俱译,陈绛校:《中国总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71,471,473页。显然将陈寿的史著《三国志》和小说《三国演义》混为一谈。在两页半的篇幅中,卫三畏介绍了汉末的混乱、黄巾起义、董卓专权,随后便是长达一页半的王允对吕布实行的“连环计”原文。除此之外,涉及作品整体内容的部分非常简略:“汉代被推翻之后,他们之间互相战斗,直到晋代重新统一全国为止。”*[美]卫三畏著,陈俱译,陈绛校:《中国总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71,471,473页。“有三个首领,曹操、刘备和孙权,很快从权力斗争中显示出本领,其后帝国分裂为魏、蜀、吴三国,这就是本书得名的由来。”*[美]卫三畏著,陈俱译,陈绛校:《中国总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71,471,473页。并专门提及了“战神”关羽和神医华佗。
总的来说,马礼逊、郭实腊、美魏茶、卫三畏介绍《三国演义》时,常将陈寿《三国志》与小说《三国志》混而为一。虽然他们将《三国志》定义为“历史小说”,但对他们来说,“小说”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他们对其中所述历史的浓厚兴趣,在介绍小说《三国志》时,他们往往花很多篇幅叙述汉末历史。除了对历史的兴趣以外,他们对神秘的宗教因素(禳星延命、法术)和妖术、阴谋的叙述也较多,而对三国之间的合作与斗争尤其是战争呈现不够。在人物方面,诸葛亮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其次是曹操,再次是关羽,而张飞、周瑜甚至刘备都未吸引传教士们的注意力。对于诸葛亮,马礼逊侧重于他的八阵图和禳星延命,郭实腊主要展现诸葛亮的智慧,而美魏茶则突出了诸葛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错漏与误读
任何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阅读都会存在错漏或误读,传教士们在介绍《三国演义》时也不例外。
郭实腊讲到曹操铲除董承一党,即将获胜时说“三结义的第三个成员,关羽,在服务于大元帅(根据上下文,此处应指曹操——引者注)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无比的英勇,现在投到了一个对立的阵营里去”*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5, September, 1838, pp.241.,接下来讲的应该是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但这之前完全没讲关羽如何降曹以及与曹的约法三章,所谓的“对立的阵营”在《三国演义》中只是回到了刘备身边。虽然此前郭实腊叙述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但此处不但搞错了关羽在三人中的排行,而且,袁绍似乎取代了刘备。过五关斩六将之后,刘备没有出现,关羽“进入了袁绍的军营”*郭实腊文中为“Shaou Yuen”,王燕认为应是“赵云”。因为郭实腊《开放的中国》中将袁绍译为“Yuen Shaou”,但由董卓被写为“Tung Cho”,可推测“赵云”的“赵”应以“Ch”开头,且由后文可见,郭实腊对中国人姓名了解不够,颠倒名和姓的情况并不奇怪,因此,此处应为“袁绍”。。在紧接着的下一段中,郭实腊说袁绍是“志在复兴汉室荣光的那一派的首领。这一集团拥有的领土包括中国西部,即现在的四川省”*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5, September, 1838, pp.241, 245, 246.,则误把袁绍当作了蜀国首领。可见,他对于各集团阵营的关系并不清楚。
此外,关羽之死也介绍得非常含糊,只是说“吴的国王被曾经征服黄巾的一个结义兄弟惹怒,把他囚禁,并把他的头献给曹操”*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5, September, 1838, pp.241, 245, 246.。小说中,孙权杀了关公,将其头献与曹操。但郭实腊的介绍中既没有出现孙权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关羽的名字。在郭实腊笔下,关羽这一人物以及他的个性、所作所为都介绍得较为模糊。
在叙述刘备称王时,郭实腊说“一旦获取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个柔顺听话的君主就变得顽固专横起来”*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5, September, 1838, pp.241, 245, 246.,虽然遭到强烈反对,仍坚持攻打吴,结果遭到失败。在郭实腊看来,刘备伐吴是因为当了皇帝以后变得专横自负,实际上刘备是为了给关羽报仇。可以认为,郭实腊对于刘、关、张之间的“义”这一条线索缺乏准确的把握和了解。
刘丽霞认为此篇译介以曹操和诸葛亮的生平为中心,“辐射对魏、 蜀、 吴三国的介绍……几乎涵盖了三国兴起至衰落中的关键事件。译介称得上是对《三国演义》 的完整介绍”*刘丽霞、刘同赛:《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三国演义〉的译介》,《济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王燕也认为“郭实腊以曹操、孔明为焦点,通过介绍二人生平经历的重大事件,不仅塑造了两人各自的形象,而且还串联起了魏、蜀、吴三国的兴衰存亡”*王燕:《十九世纪西方人视野中的〈三国演义〉》,《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冬之卷。。但我们发现,郭实腊甚至对于三个国家的首领、各集团阵营之间的关系都并无明确的概念,很难说他把握了“三国的兴衰存亡”,其介绍也实在难称“完整”。
在介绍战争时,郭实腊的文章中不够准确的地方也较多。如关于小说中最著名的赤壁之战,郭实腊的叙述中没有出现“赤壁”的名字,只提到了火攻。他讲了草船借箭的故事,但没讲周瑜,也没讲孙刘联盟,也没讲是从曹操那里借来的箭。这再次说明,他对于三国之间合作与斗争的关系并不清楚。事实上,马礼逊、美魏茶、卫三畏也都未提到“赤壁”之战,他们对小说作者用八回来叙述的赤壁之战缺乏总体把握,未意识到其在扭转三国力量对比过程中的重要性。
美魏茶介绍孔明时有一些对于战争较为具体的叙述,但亦有较多错误。如关于木牛流马部分:“探子报告了孔明,这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他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安排了伏兵,大败敌军。”*Willam Charles Miline Notices of Kungming, one of the heroes of the San Kwoh Chi, Chinese repository, vol.XII, No.3, March, 1843, pp.131, 132.这里是指王平假扮魏兵劫取他们运粮草的木牛流马,其实他们是为了得到魏军的粮草,而不是击溃他们的军队。在讲到吴配合蜀进攻魏时,魏主曹睿抓到了一个给吴国首领孙权送急件的人,吴的行动计划泄露,美魏茶说曹睿“立即采取了破坏他们的方法,进攻他们,交战了一两次击败了他们”*Willam Charles Miline Notices of Kungming, one of the heroes of the San Kwoh Chi, Chinese repository, vol.XII, No.3, March, 1843, pp.131, 132.。《三国演义》原书中双方并未交战,吴军只是做出要进攻的样子迷惑敌人,实际上数日之内全部退兵走了。
可以看出,对于战争,传教士们在介绍时要么回避,要么就是介绍得比较敷衍,对于战争的目的、战争的过程甚至是否曾经交战都有很多不甚了然的地方。
传教士们对阴谋感兴趣,但有时却并不完全清楚其前因后果。如郭实腊讲了“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故事,但说是“为了使友谊的盟约更牢固,玄德被引诱娶了吴国国王的亲戚”*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5, September, 1838, pp.243.,实际上是孙权想取回荆州,周瑜献计“假招亲扣人质”,并无友谊的成分。同样,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中谈到《三国志》时,长篇引用原书中“连环计”的前半部分(即王允将貂蝉许给吕布为妾),然后总结说:“这个计谋成功了,董卓在去废黜皇帝的路上被他的儿子杀死。”*[美]卫三畏著,陈俱译,陈绛校:《中国总论》,第473,471页。小说中王允随后将貂蝉送入董卓府中,以此离间董卓和吕布的内容完全略去未提。应该说卫三畏对这个计谋的叙述是缺乏完整性的,进一步推论,他是否把握了这个计谋的全部内容也是存疑的。
因时间跨度长,传教士们在一些事情的前后关系上也会出错。在郭实腊的介绍中,诸葛亮出山被放到了三国鼎立局势形成之后。无独有偶,美魏茶介绍孔明时,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不但把刘备的第一次拜访和第二次拜访搞混,而且在叙述刘备第三次拜访诸葛亮时说:“那时他为了征服魏和吴做了大量安排(那时帝国已经分成了魏、吴、汉或蜀三个部分,每一个都想控制另外两个)。”*Willam Charles Miline, Notices of Kungming, one of the heroes of the San Kwoh Chi, Chinese repository, vol.XII, No.3, March, 1843, pp.127, 133, 134, 126, 127, 127, 134.实际上当时三国鼎立并未形成,是诸葛亮为刘备描绘了三国鼎立的蓝图。很可能是原书作者的感叹——“只这一席话,乃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导致两位介绍者误解为“三国”在此时已经形成。
此外还有一些细节的错误。美魏茶讲到魏延冲进帐内向孔明报告魏兵来袭,正在为续命而祈禳的“孔明急转身听他的报告,没留心地上散布的东西,他踩到了那盏致命的灯上,灯立即熄灭了”*Willam Charles Miline, Notices of Kungming, one of the heroes of the San Kwoh Chi, Chinese repository, vol.XII, No.3, March, 1843, pp.127, 133, 134, 126, 127, 127, 134.。原文是“延脚步急,竟将主灯扑灭”,美魏茶忽略了“延”这个主语,误以为是诸葛亮自己把灯扑灭。而马礼逊介绍孔明之死时则是说他祈祷完毕,俯伏到天明,吐血不止而死*马礼逊:《马礼逊文集·华英字典》第1卷,第716,715,715页。;《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说诸葛亮留下的文字有“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马礼逊则误为“140 112字”*马礼逊:《马礼逊文集·华英字典》第1卷,第716,715,715页。。马礼逊还说孔明经常“一手执扇一手执巾进入战斗”*马礼逊:《马礼逊文集·华英字典》第1卷,第716,715,715页。,误解了“纶巾羽扇”的意思。
除此之外,还有与文化或有特定文化含义的语言有关的错误,如介绍诸葛亮时,郭实腊说他的名字叫孔明,又叫“葛亮”,说明他对中国的姓氏文化不太了解。刘禅得知孔明将死时,“急切地想知道关于国家未来的一些事,他立即派了一个老大臣去问孔明今后百年内事情是什么样子”*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5, September, 1838, pp.243, 249, 233, 246, 247.,原文是“问丞相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百年”在这里是“死”的隐语,美魏茶误为时间概念。
三、对《三国演义》的评价
在介绍《三国演义》内容的同时,传教士们也表达了对这部作品的肯定和推崇。郭实腊说:“任何一个对中国文章有品味的人都不会否认被普遍接受的看法,即《三国志》是中国最好的作品之一。”*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5, September, 1838, pp.243, 249, 233, 246, 247.“所有阶层的人都认为它是已有作品中最有趣的,它的风格、语言、记录事件的方式,怎样称赞都不过分。这是一部杰作,在文学史上无可匹敌。”*Willam Charles Miline, Notices of Kungming, one of the heroes of the San Kwoh Chi, Chinese repository, vol.XII, No.3, March, 1843, pp.127, 133, 134, 126, 127, 127, 134.美魏茶说《三国志》“是已有创作中最好的中国神话之一”*Willam Charles Miline, Notices of Kungming, one of the heroes of the San Kwoh Chi, Chinese repository, vol.XII, No.3, March, 1843, pp.127, 133, 134, 126, 127, 127, 134.,“跟英国十三世纪或更晚的小说相比,如果不是更好,至少也是一样好”*Willam Charles Miline, Notices of Kungming, one of the heroes of the San Kwoh Chi, Chinese repository, vol.XII, No.3, March, 1843, pp.127, 133, 134, 126, 127, 127, 134.。他认为“中国人通过经常阅读它表达对它的尊重,他们确实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因为它的一些段落的确令人赞叹”*Willam Charles Miline, Notices of Kungming, one of the heroes of the San Kwoh Chi, Chinese repository, vol.XII, No.3, March, 1843, pp.127, 133, 134, 126, 127, 127, 134.。卫三畏说:“对于中国人,它的魅力在于栩栩如生地描写阴谋与反阴谋,战斗中的相互关系,围攻、退却。书中描绘的人物有着令人钦佩的风度,他们的行为夹杂着有趣的插曲。”*[美]卫三畏著,陈俱译,陈绛校:《中国总论》,第473,471页。
传教士们对《三国演义》中人物的评价集中在诸葛亮和曹操身上。对诸葛亮毫无例外是赞美,如郭实腊认为孔明“闪耀着不逊于任何其他掌管国家的政治家的光彩”*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5, September, 1838, pp.243, 249, 233, 246, 247.,讲述了孔明应对五路来犯之兵后评价说:“这场复杂的调兵遣将被巧妙地描述出来,孔明表现出来的超凡的英勇功绩和智慧被叙述得如此完美,我们在其他任何中国历史小说中都未曾见到过。”*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5, September, 1838, pp.243, 249, 233, 246, 247.美魏茶评价诸葛亮说:“他一直在政务上表现出他的热情,并总是能表达他的正确的意见,他承担起保卫国家的责任,并且发誓不将它从痛苦中解救出来就不休息,他忠实地遵守了他的诺言。”*Willam Charles Miline, Notices of Kungming, one of the heroes of the San Kwoh Chi, Chinese repository, vol.XII, No.3, March, 1843, pp.127, 133, 134, 126, 127, 127, 134.在一般中国读者心目中,诸葛亮已经固化为“智”的象征,是三国中“智绝”的代表,中国读者津津乐道的是他在各种计谋中表现出来的超凡的智慧和预见性。但从来华传教士的介绍和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智慧(郭实腊着重介绍的),他们也强调了他的忠诚和责任感(美魏茶),并突出了他身上神异性的一面(马礼逊)。传教士们自身的“传教”身份与使命感以及来自异域的文化背景,使他们关注到诸葛亮不同的侧面。
对曹操的评价则以否定性为主。马礼逊在“Tsaou-tsauo”词条中翻译的司马光的评价是对作为历史人物曹操的评价,但在这一词条的开始,他说曹操是“在中国内战(220年)期间魏国的一位著名的但不太道德的将军”*马礼逊:《马礼逊文集·华英字典》第4卷,第871页。。这是他基于小说《三国演义》对曹操作出的评价。郭实腊认为曹操“大胆”、“坚定而又无情”,“为达到目的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最卑劣的手段”*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5, September, 1838, pp.244, 239, 238, 244, 249, 246, 249, 243-244, 249.。但他也称赞曹操军纪严明,并叙述了曹操马踏麦田割发代首自我惩罚的故事。关于这部分内容,在《三国演义》的汇评本中毛宗岗、李贽等多用“权诈”、“奸雄”等评语,但郭实腊则总结说:“通过这一举动,他在军队中获得了比最辉煌的胜利所能获得的更大的影响力。”*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5, September, 1838, pp.244, 239, 238, 244, 249, 246, 249, 243-244, 249.这一评论是中性的甚至可以说是肯定性的。中国的点评者目光如炬地看出了曹操的“做秀”(这多少受到曹操为“奸雄”这一定论的影响),而郭实腊则更侧重于评价这一举动的实际效果(显然他的判断有想当然的成分),没有或者说未能看出其虚伪。总的来说,郭实腊对曹操的看法较为复杂,他把曹操跟丹东相比,说他“受到了像在法国恐怖统治期间的丹东一样的拥戴,但他更多地依靠他的剑而不是依靠人民的欢迎”*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5, September, 1838, pp.244, 239, 238, 244, 249, 246, 249, 243-244, 249.。
除了诸葛亮和曹操,关羽被马礼逊和卫三畏类比为西方神话中的“战神”。至于刘备,马礼逊的概括是“三世纪时中国内战期间的一位和蔼可亲而又杰出的将军”,其余人则未对他作出评价。
郭实腊注意到了小说中的战争模式并对其进行了总结:“战争的胜利通常是由几个勇敢分子决定的,他们通常骑马跑出阵外,把对方痛骂一顿,然后让最勇敢的出来单挑,然后军队里的其他人就站在那儿踮起脚尖看谁能获胜。一旦决出胜负,获胜者就冲入颤抖的人群中,一阵砍杀,像羊一样驱赶他们。然后这些勇敢的胜利者就不见了,直到某个有名的首领再把他们召唤到他的旗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5, September, 1838, pp.244, 239, 238, 244, 249, 246, 249, 243-244, 249.非常形象地概括了一般战斗中常出现的情景,而中国读者已经习以为常,通常不会注意这一点。
对于具体细节,郭实腊评论说:“描写占领首都、征服者获胜、行军前的普遍的恐慌、计谋、统治者的懦弱的段落,值得留意并熟读,是中国天才的完美的样本。愈是接近大的灾难,作者的语言就越有力,惆怅悲伤之情就越强烈。”*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5, September, 1838, pp.244, 239, 238, 244, 249, 246, 249, 243-244, 249.他认为刘备“临终的场景被描述得感伤动人,值得留意熟读”*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5, September, 1838, pp.244, 239, 238, 244, 249, 246, 249, 243-244, 249.。无独有偶,美魏茶讲到刘备去世的时候也说玄德“临终的床前,是写得最感人最优美的一段”*Willam Charles Miline, Notices of Kungming, one of the heroes of the San Kwoh Chi, Chinese repository, vol.XII, No.3, March, 1843, pp.128.。很难判断他是否受到郭实腊的影响,但考虑到临终关怀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教士对人的临终时刻的特别关注就并不奇怪了。
除了肯定性的意见外,传教士们对《三国演义》也提出了批评。卫三畏说:“这一作品有其双重性质,时间跨度很长,必然缺少一部小说所应有的整体性。”*[美]卫三畏著,陈俱译,陈绛校:《中国总论》,第471页。应该说《三国演义》本身并不缺乏整体性,但从郭实腊对小说内容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对传教士们而言,完整地把握《三国演义》的内容及篇幅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郭实腊抱怨:“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对自然的详细描写,它只是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拥有热情和缺点的人的记录。”*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5, September, 1838, pp.244, 239, 238, 244, 249, 246, 249, 243-244, 249.作为德国传教士,郭实腊想必习惯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随处可见的自然描写,而中国一些古典小说受到“说话”传统的影响,以叙述事件为主,静态的风景描写确实较少,这在《三国演义》中表现得尤其突出。郭实腊从自身文学传统出发,敏锐地感觉到了异域文学在这方面的“缺失”。他还认为一些“战争细节非常无聊,充满了重复”*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5, September, 1838, pp.244, 239, 238, 244, 249, 246, 249, 243-244, 249.,“众多的人和地方的名字令人生畏,令人的头脑变得困惑。好几章缺乏趣味,充满重复,另外一些只有编号,行军,军队的后退”*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5, September, 1838, pp.244, 239, 238, 244, 249, 246, 249, 243-244, 249.。他的这一看法有一定代表性,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传教士们介绍战争时往往较简略,并有很多错漏。
四、跨语际的阅读与接受
在早期来华传教士群体中,《三国演义》受到的关注是其他中国文学作品所无法比拟的。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三国演义》的普及性。郭实腊说:“在所有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没有哪一部像《三国》那样受欢迎。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都读它,无论有学问的人还是无知的人都赞美它。”*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5, September, 1838, pp.233, 234, 234.“尽管它不少于24卷,但很少人没有读过一遍以上。即使文盲阶层,不熟悉三国的事情也是丢脸的。”*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5, September, 1838, pp.233, 234, 234.他发现:“他们的诗歌,甚至严肃的写作,都因为与三国有关的典故而变得生动活泼,庙宇和私宅都用表现主要将领的有名的行动或决定帝国命运的战争的图画来装饰。”*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5, September, 1838, pp.233, 234, 234.显然,传教士们注意到了《三国演义》在普通人中广泛阅读及被普遍接受的情况。
与此有关,在缺乏汉语教材的情况下,流行于中国各阶层的《三国演义》自然地被当作传教士们的汉语学习教材或读物。米怜在《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中说:“学习中文的人,无论是在交谈中,还是在书写时,如果希望他的表达被轻松广泛地接受,都应该仔细研读和模仿《三国》。”*米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90,89—90页。马礼逊在考虑《圣经》中译的语体时,亦决定以介于经典文言与白话之间的“折中体”——《三国》的语体为参照对象*米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90,89—90页。。1838年在一篇介绍学习汉语的便利工具的文章中,《三国演义》节译和所谓轻松的文学读物(light literature)《好逑传》、《玉娇梨》以及戏剧《赵氏孤儿》、《老生儿》、《汉宫秋》等的翻译本一起,被推荐给水平较高的汉语学习者*Review of the facilities existing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repository, vol.VII, No.3, July, 1838, pp.117-118.。
然而,从普遍存在混淆陈寿《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的情况来看,传教士对于文类的区分并不清楚。可以作为例证的是,美魏茶的《〈三国志〉中一位英雄孔明的介绍》在《中国丛报》的分类中被列入“人物”类,而美魏茶另一篇直接译自《三国演义》的文章《黄巾起义》则被列入“历史”类。也就是说,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知道它是“小说”,但仍在很大程度上把阅读《三国演义》当作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途径。这可以解释为何在介绍《三国演义》时他们的重点往往落在汉末历史上,对其文学价值的评价倒在其次,或者说他们对其文学属性缺乏关注。
从传教士们对《三国演义》的介绍可以看到,他们的确通过阅读三国了解了汉末的历史与部分历史人物,但跨语际阅读同时导致了理解方面的诸多问题。首先是词语、文化方面的错误,即将A误为A’,如将“羽扇纶巾”误为“一手拿扇一手拿巾”,认为诸葛亮叫“葛亮”等。其二为简化,如把刘备伐吴的原因解释为当了皇帝后变得顽固专横,认为刘备娶孙权妹妹是为了友谊以及抢粮误为作战等内容,都是传教士们基于先入为主的想像所作出的推测。以公式来表达,如果小说中包含的因素或过程为A—B—(C)的话,那么,传教士的理解常常只到B这一步,而且往往以他们头脑中想当然的B’代替B。其三为混淆,如搞错各阵营关系,把袁绍当作蜀国首领,把诸葛亮出山置于三国形成之后等,即如果有A、B两个因素,他们会把A误为B。其四为忽略,如略去真假难辨的与“诈”有关的内容以及各阵营之间的复杂关系。
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既与语言、文化差异有关,也与作品本身有很大关系。由于小说本身时间跨度长,线索复杂,人物众多,除了主要人物外,大多数人面目不清,不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在阅读过程中,在人物的辨认、情节的接续上易产生困难,导致混淆人物及所属集团、各集团之间的关系。正如郭实腊自己承认的:“众多的人和地方的名字令人生畏,令人的头脑变得困惑。”真实地表达了非母语读者阅读《三国演义》的感受。同时由于战争的内容远离日常生活,战争中涉及的战术或计谋较为复杂,因此不奇怪,在叙述战争时,他们往往选择略去那些与“诈”有关的使他们难辨真假的复杂内容。即便叙述了战争,他们也容易在战争的结果、战争中涉及的人物乃至战争是否发生等细节上发生错误,对阴谋的前因后果的叙述也会有误。但正是在这些误解和错漏之处,我们看到了传教士们在汉语文本的重重障碍和迷雾中艰难跋涉,在纷繁的意义元素中努力连接、聚焦、靠近以及偏离的情状。
跨语言的阅读同时也是跨文化的阅读。瓦尔特·F·法伊特谈到跨文化关系中的理解时指出:“理解有两个基本方面,理解他者和疏者(the foreign),并将其移植且整合于习者(the familiar)之中的渴望;同时,还有保持疏者之为生疏的需要。”传教士们对《三国演义》的介绍和评价也体现了这两个方面:以他们所熟悉的西方文化中的“战神”来指称关羽,将曹操比作“丹东”,对诸葛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强调,作为传教士对刘备、诸葛亮临终场景的关注等。这些都体现出他们试图将“他者”整合于“习者”的努力。另一方面,对于道术、妖术、模式化的战斗场景的聚焦、对缺少自然描写的批评则突出了与自我文化、文学传统相异的一面,体现了“保持疏者之为生疏的需要”。
在中西文化交流处于起步阶段的情况下,传教士们对《三国演义》的介绍和评论起到了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学的中介作用。站在中西之间,他们不无对受众的考虑。曲折、紧张的情节对任何读者都是有吸引力的,从这一角度说,对阴谋、计谋的详述既反映了他们本身的兴趣所在,也暗含了他们想吸引其他西方读者的愿望。另外,传教士们对诸葛亮的“禳星延命”、道士的法术、灵帝时自然界的异象、妖术等内容的详细叙述既体现了他们作为传教士对中国本土宗教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也未尝不是为了满足读者及他们自己对东方的猎奇心态。
结 语
综上,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最初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接触《三国演义》的。从他们的介绍和评论,我们看到他们眼中的《三国演义》呈现出如下样貌:是用于了解汉末历史的书,充满了阴谋和计谋,有玄幻、神异色彩。其中有大量的战争,但战争的具体情况较为模糊。与战争相比,阴谋、计谋、玄幻的因素更吸引他们。至于人物,清晰地映现在他们脑中的是诸葛亮和曹操,其次是“战神”关羽,而张飞、刘备、孙权几乎只是作为名字存在,周瑜甚至连名字都未出现。
相较于稍后出现的来华西人中更为专业的中国文学批评者,传教士们的中国文学阅读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已有学者指出,传教士们因信仰而专注于母语宗教文学的阅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们对晚清中西之间跨文学对话交流在世俗文学这一领域的足够兴趣”*段怀清:《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语境中的literature概念》,《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作为具有宗教信仰、身负使命的传教士,他们之所以阅读三国,一是为了学习汉语,二是为了了解中国,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顺利传教。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他们的评介呈现出《三国演义》与西方最初相遇的景观。曹顺庆指出,任何跨文化的文学交流活动都存在着“文化过滤”,即“接受者根据其自身与对象的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对交流信息作出选择、改造、移植与渗透等行为”*曹顺庆:《南橘北枳》,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56页。。需要指出的是,传教士们对三国的阅读不仅是“跨文化”的阅读,也是“跨语际”兼“跨文化”的文学交流活动。他们对《三国演义》的阅读与接受既存在着“文化过滤”,也存在着“文学过滤”。他们有所见,也有所不见;他们有误读,也有自己的发现和创造性理解。伊瑟尔说“作品就是文本在读者意识中的被建构”*[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著,贺骥译:《阅读过程:一种现象学视角》,周启超主编:《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第3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第176页。,传教士们对《三国演义》的评介是他们在意识中建构的《三国演义》的典型样本。这些评介不但对于《三国演义》的西传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反映着异域文学接触的典型症候,对于研究“跨语际的文学接受”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