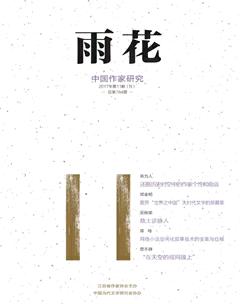乡土的内在性悖论与民间精神的复魅
金春平
新文学乡土小说经验的丰厚,为当代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可供汲取的高质量文学范式,但以既定的经验方式去应对日益更迭的乡土生活变迁,它可能又成为隐秘制约文学行进的禁锢之牢,造成文学审美的同质化泛滥。于是,寻求乡土世界的“新”的讲述方式,发现乡土生活被遮蔽的真实面目,展示乡土在人世沧桑与人心激荡中的永恒力量,就成为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情境中新乡土小说所着力构建的方向,而历史语境的转型也不断重新赋予乡土之叙事以新的思想和美学活力。王秀琴的小说集《婚驮》回避了将乡土视为文化观念演练或先锋艺术实验的窠臼,而将乡土作为一个“各类生命体的景观域”,小说中活跃着的一个个活色生香的生命,演绎着北方乡土民间的基本要义,有大爱、善性、宽容、仁厚,有狂野、嫉妒、复仇、乖戾,也有辛酸、悲苦、超脱和禅悟,他们将“生活”这一抽象概念化为具象的日常细节,也将乡土民间的空洞想象雕刻为普遍的生存姿态。当然作者并未停留于只对日常生活进行客观描摹的自然主义,而是以其内敛的“温情现实主义”的叙述透视法,去洞悉世道人心的诡谲,察明人性肌理的深邃,触摸命运之神的法门。王秀琴的乡土小说始终将“记忆乡村”与“现实乡村”进行叠加,在“虚构”和“再现”兼备的小说空间中,形塑出乡村的“自足”和“撕裂”,“循环”和“孑行”,“恒定”和“变异”的叙事机杼,作者僭越了日常生活对生命体验的制掣,以回望与想象的姿态记录着一种乡土生命的存在方式,乡土在作者的文学镜像中呈现出鲜明的乌托邦色彩;但是,作者又清醒地意识到乡土民间的良莠芜杂,乡土在政治权力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既有的乡土秩序和民间机制随时面临冲击和瓦解,这让她的乡土体验乌托邦层层褪去浪漫瑰丽的光芒,裸露出人性、生活和世道的原始生涩。王秀琴以个人化的乡土记忆去一次次碰撞和直视隐秘变动的日常生活,以静态的民间抗衡动态变迁的乡土,衍生出其小说的一种“日常生活化的悲剧美学”,而这种悲剧性往往又生成于人所面对的“卑微”与“尊严”,“民本”与“政治”,“欲望”和“自守”,“人性”与“生命”,“原始”与“神性”,“进步”与“蜕变”等之间的生存错位或压制,完结出作者对农耕文化和乡土文明遭遇现代化裹挟的艺术性民族寓言。
《福根》是一幅典型的北方乡土“清明上河图”,每个人都在既有的生活轨道努力生活,也被生活所规约和钳制,但却又处处遭遇无可控制和无法预知的诱惑或激励,“努力而认真的挣扎”成为他们的生活常态,当然这种挣扎也饱含着希望、凄厉乃至绝望。高福“把每一棵梨树都当成自己孩子,当作亲人”,“指望这些梨树使自己活到别人前头去”,“活得挺起腰板,活出人的尊严,活出男人的气概和风度”,高福的这种发家致富、活出尊严是水峪村乡民长期物质压抑下的集体生活向往和人格诉求,但与此同时,经济话语进入民间社会的价值认同结构,又不断催化着乡村的生活形态和精神结构的变化,获得经济资本主导权的乡民,重新成为乡村日常话语的“主导者”,如种梨大户高福、乡村会计福全等,经济话语权的获得还可以重新支配性别等级的操控权,如高福和苏苏由半遮半掩到公开偷情,本应是宿敌的彩兰和文兴却是一对真挚的恋人;而在以经济话语为主导的乡土世界,资本权力一旦丧失也就意味着在民间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彻底衰落,如倒闭酒厂老板张秋根甚至愿意与高福以男人和家庭的尊严换取物质匮乏的弥补,遭遇妻子患病落难的前村主任金明在经济窘境面前也不得不颔首妥协。与经济话语相伴而生的政治话语的强势入侵,也改变着基层乡村以道德话语为核心维系的秩序方式,高福因其经济成功的典范而获得集体性推崇而出任村主任一职,金明落选之后所遭遇的种种世态炎凉的生活碰壁即是显例。乡土民间不再是文学意象和现代市民的世外桃源或至纯圣境,当现代经济话语和政治话语取代了传统乡土民间依托血缘和道德所维系的运转动力时,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乡土文明内在精魂的终结。但是王秀琴却并未将这一终结处理为彻底绝望式的灰暗,而是捕捉到了乡土文化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内在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甚至是永恒,这种永恒性来自于乡土文化的惯性,更来自人性的高贵:高福在勤劳中致富,在致富中获得权力话语,甚至在与苏苏的偷情中曾一度放弃作为丈夫和男人的责任感,但是高福对金明经济困境中的慷慨相助,在上级部门极力推动梨田出让时对这一决策的坚决抵制,对结发妻子子丑的愧疚、怜惜和回归家庭,彰显出传统乡绅文化人格的现代复魅,尽管这种复魅是有限度的;金明在村主任任职期间以及再次竞选时虽然也曾表现出强烈的对权力崇拜的异化人格,但是他对妻子患病时的不离不弃,他在妻子祭年时所严格恪守的民间习俗,同样传达出他对民间道义话语的内在信仰;在子丑身上,作者同样赋予其勤劳持家、忍辱负重和宅厚仁心等多重高贵的人性品质,熨帖出一位坚守德性认同的乡土女性角色。如果说高福、金明和子丑等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对经济、权力话语的有限度抵制生成于普遍的人性,那么九叔则是小说当中农耕乡土神秘文化的人物性载体,“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纸扎花圈,缝缝补补,蒸炖炒煮,吹拉弹唱,招魂赎魄,看阴阳,说八卦,样样在行,还挺灵验”,在小说中,九叔是典型的民间乡土神秘文化存在的一种历史性的思维记忆和认知哲学的化身,这种记忆、认知和认同演化为一种遗传密码,转化为身份认同的一种文化核心,它让乡土文化得以凝聚,也让乡土文明得以获得自主性,它构成与一切标榜断裂和现代的存在模式相异的另类生活场景和心灵情境,也完成了一场能够解释生活百态和人世无常的文化仪式。
民间乡土文化在现代经济话语的冲击下所日益濒临破碎的危机,诱导出静谧人性的躁动和心灵异化的裸露,当道义话语被消费主义和欲望放纵所取代之后,既有的道德秩序对人的制约渐趋失去其集体性和内在性的制约,而个体的物欲在经济时代取得政治合法性之后,人性欲望及其泛滥不仅带来人的精神无序,还带来现实秩序和集体狂欢的混沌,在人性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双重夹击之下,传统民间乡土文化当中的道德话语就在后现代语境中被转化为一种重新进行价值整合的话语机制,无论这种整合和救赎的文化效果如何,但唯有将乡土精神与现代性话语进行对话和碰撞,才能检视其参与人文精神重建的实绩。在《脉门》当中,宋玉珍充满对权力的崇拜,張家辉处处流露出对物质的强烈渴望,玉凹村的村民几乎都在以最朴素也是最务实的生活观当中进行着日常的人际交往,“世俗”维系着人的生活热情,也让人沉溺其中获得乡村平庸生活困境的企盼,而村主任张冬生以“公开”作假的方式应对上级检查以获取资金扶持,甚至不得不和儿子家辉进行分工协议,但张冬生所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修缮校舍和修路铺桥,体制的局限和政策的纰漏让张冬生在法律层面上违规,但他的公而忘私、一心为民、信守承诺等乡绅风范却获得了民间道义的胜利,他被免职之后的无奈和落寞,反衬出的是被物质和权力所异化的乡村文化生态的蔓延,但在生活的边缘处他却寻觅到了早已遗失的本真自我,失败的英雄际遇、无常的宦海浮沉、势利的乡土人间,一切如同戏里戏外的人生梦幻,他自始至终都秉持着最为传统的民间为官之道,甚至其中不乏机智和狡黠的为政策略,但最终还是遭遇到了坚守的背叛和理想的反噬,王秀琴发现着乡土文明的最后守灯者,却也只能以道家的禅悟抵抗变动不居的世道困境。endprint
时代合法性的经济欲望所引发的乡土动荡往往是道德秩序和生命尊严的亵渎者,它在带来乡土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步的同时,却往往是以生命悲剧、人性变异和心灵颓败为进步的代价。《血口》以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方法,以牛的世界映照人的世界,或者说牛的原始野性和两性的媾和,彰显的是自然生命受制于人类欲望而不得不走向陨落的生命预知和绝望反抗,而二清在自以为是的生存角逐的胜局中,早已丧失了对生命他者和神灵高贵的敬畏,妻子的背叛、三牛的报复,一切在人的毫无畏惧和极度自信中早已陷入无法自拔的罪恶深渊,“血口”是人类打开杀戮和残忍心灵之魔的隐喻,更是人类对自我生命高贵和人性伟大的自戕的反讽,“二清口张着,却不能说话,‘哇——,他的口又成了一道血口子,而且血口子越来越大……”资本欲望和乡土自守的人性内在性交锋,撕裂的是人的精神稳定性,坠入的是永无天日的心灵沉沦的渊薮。《无处可逃》当中,卢小堰与杨爽结伴去采矿公司,恪守乡土道德法则的杨爽遭遇横祸,而欲望蠢动的卢小堰却安然无恙,采矿公司给卢小堰的“辛苦費”,他将之视为对杨爽的赎罪之物,埋在圣母庙踏跺之下接受神灵的监督和见证,尽管杨爽之死与他并无关联,但是“接受”采矿公司的“赠予”这一行为在他看来已经是对生命尊严的亵渎,他代替朋友接受并不公平的赔偿,在被威胁的情境中自己并未战胜懦弱和恐惧,终让自己所信奉的公正、道德和侠义在生活实践中远离,也让思想和心灵陷入自责的深渊,“忏悔”成为卢小堰最为沉重的灵魂枷锁,在金钱和道义的抉择中,卢小堰重拾遗落的道德担当和人性本善,随时闪现的杨爽死亡时的悲惨画面已经成为他因接受金钱赠予而生的心魔的嘲讽。因此,在《无处可逃》当中,王秀琴将人性的放纵开始收拢,重新肯定了人性对欲望的战胜,卢小堰“赎罪”“忏悔”“恐惧”的人性质地,尽管让他的心灵无处安放、无处可逃,但也隐喻着这种不安定的乡土人性本色和人道主义话语的复活,宣示出乡土民间道德精灵的再次飞扬。
如果乡土没有欲望,用封闭自足式的生活去斩断乡土时间的演进,乡土世界也未必能回归澄明的原始,或者说,物欲造成了乡土民间的人性异化,但假若乡土没有遭遇物欲的介入,或者人的物欲能够得到兑现,身体、精神和情感的残缺同样可能将人牵入平庸而无望的世界,王秀琴在《婚驮》中确认了这一疑惑。米家庄最为尊贵的婚姻仪式就是能邀请楚贵贵担任婚驮人,他驮婚时的舞姿和步伐不仅是每位新娘的身体享受,更是新娘和女性身份尊贵的一次显赫凸显而转化为一种精神享受,作为驮婚者的高贵不仅在于他的较高经济回报,并让刘贝贝一家羡慕不已倾心追随,它的身份尊严更在于以道德理性对人性欲望的战胜——“每驮一次婚,就是对男人的一次大考验”,“这碗饭不好吃就不好吃在这里”,驮婚这一过程是两性之间的孤独游戏和精神仪式,却无法逾越现实理性的道德羁绊,驮婚成为楚贵贵对人性和理性的较量,而每次精彩而成功的驮婚又是对人性压抑的加剧,王秀琴洞悉到了乡土民间的道德话语对人性压抑的深刻伤害,楚贵贵以自我满足的方式来弥补现实情爱的匮缺,乡土人际当中令人艳羡的社会地位,实则是以巨大的人性阉割和情感失落为交换,“以前,我记不住她,她可是跑了,现在,我记住她了,她却不再回来了。柳翠花,柳翠花,柳翠花却再也不回来了。”在《婚驮》当中,王秀琴对乡土欲望的书写深入到更为隐秘而强大的人的命运无望的苍凉感知,揭去了经济话语与人性物欲相互激发的帷幕,凝望着乡土民间所无法承受却又不得不承受的生命之重,也将日常生活的悲剧性上升到人的存在悖论的高度。
至此,王秀琴的新乡土叙事完成了其立体型的多棱镜观照,她将日常民间置于经济话语和权力话语的关系网络当中,去审视人的本能、欲望与道德、人性之间的激烈冲突,更蠡测到了乡土文化在时代诡谲当中坚守抑或放弃所诱导的人生悲欢和人性悲剧,她的新乡土文学小说系列,肯定着乡土对现代资本和权力话语接受的生活诉求合理性,但又否定着这种被现代物质话语所绑架的人的生存姿态,更揭露出乡土文化自身难以进行自我调和多重文化冲突的内在性状态。当然,文学更需要聚焦于外在性制约之下的人性、人心、精神和存在的肌理,王秀琴在小说集《婚驮》当中充分展示出她对乡土人性的普遍性的熟稔,并在乡土日常生活叙事的细节中看到了人控制生活以及生活反制人的或胜利或困境的丰富性,这让她的小说叙事具有鲜明“在地性”的同时亦不失对现象之下所涌动的无物力量的触摸,正如詹姆斯·伍德所说:“文学与生活的不同在于,生活混沌地充满细节而极少引导我们去注意,但文学教会我们如何留心。”因此,《婚驮》系列小说对叙事细节的密集调动,能够越过宏大的历史表象,并把意象和观念诉诸于触手可及、历历在目的心灵感觉,告密出最切近人的生命本真和生活体验,而这些细节所蕴含着的巨大叙事能量,海纳着丰富的艺术暗语,也努力化解着一切生命当中的尖锐痛楚。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