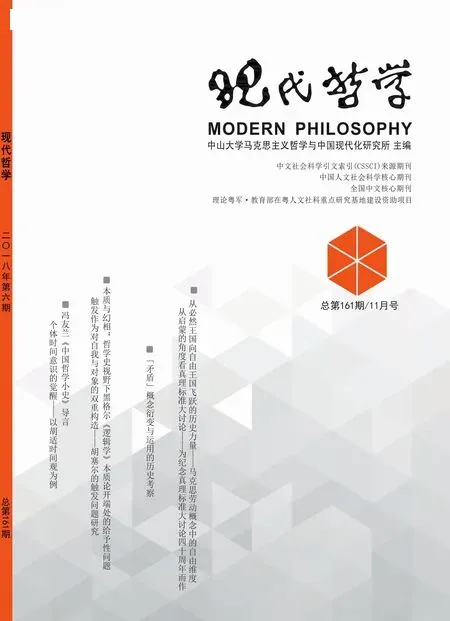触发作为对自我与对象的双重构造
——胡塞尔的触发问题研究
刘逸峰 王 恒
自我、对象与感觉素材间的相互关联是贯穿胡塞尔现象学的重要问题,不仅涉及自我的主动性与意识的被动综合,更集中表现在自我与对象关系的“触发”概念上。触发往往被视为对象客体对自我的作用。但是在对这个概念的逐步探索中,我们会发现触发现象不能简单理解为“某物作用于自我”。实际上,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一切对象都是在时间意识中被构造的,于此,便牵涉到胡塞尔现象学一系列基本概念,它们相互交织、相互规定,并随着胡塞尔本人思想的发展,形成一种系统性的动态演进,而其中的主线便是自我与对象的相互构造。
一、自我注意作为构造条件所导致的触发困境
胡塞尔在《被动综合分析》中将“触发”定义为“意识上的刺激……一个被意识到的对象对自我施加的特有拉力”[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李云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80页。,因此自我是接受刺激、受到对象作用的被动一方。在胡塞尔看来,触发可以被视为“现实的触发”与“触发的趋向”两种情况:与前者相符的是“触发着自我的对象”;而后者则对应于“感觉素材(sinnliche Daten)(素材一般〈Daten überhaupt〉)”[注]同上,第180页。,这些素材保有“触发的潜能性”[注]同上,第180页。,它们“仿佛向自我极发射触发力的射束,但在其乏力的情况下没有使触发力的射束达到自我极,对自我极来说没有现实地成为一个唤起性的刺激”[注]同上,第181页。。只要素材的触发力足以实现“唤起性的刺激”,即“一旦素材唤起了自我的注意,开始了构造进程,那么对象就会在这一构造过程中被注意到”[注]Stefano Micali, “Affektion und Immanenz bei Husserl”,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2006),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2006,S.85-98.,此构造进程完成了“触发的趋向”向“现实的触发”的转换。但素材的刺激有赖于素材间的相互关联:“单一素材的触发力量依赖于其他的素材,就像那些素材也依赖于它”[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李云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81页。,此关联被视为素材间的“对照”:“触发现在以某种方式是对照的功能……触发的等级性与对照的等级性相关联,而触发的趋向的等级性也已经与对照的等级性相关联”[注]同上,第182页。,因此对照贯穿了“现实的触发”与“触发的趋向”。首先,既然“对照”关系是素材的刺激性得以生效的条件,它当然也就成为了自我将单一素材构造为对象的前提,因为没有“对照”根本就不可能谈及任何“单一素材”的触发性,也不能讨论这些素材是否通过触发“达到自我极”,于是由于素材间对照的统一既先于“单一素材”的触发性,也先于“唤起性的刺激”,那么“单一素材”的构造进程就不出于“自我的注意”;其次,由于对照贯穿了整个触发状态,那么被构造为对象的(处于“现实的触发”中的)素材与没有足够触发力量的(作为“触发的趋向”的)素材都统一在对照中。因此,无论是否获得自我的注意,与自我相关的始终是素材统一而非“单一素材”。
在对照中的的素材统一,被胡塞尔称为“被动综合”。由于被动综合中既存在“现实的触发”,又存在“触发的趋向”,而实际上前者总是作为对象被注意到的,那么被动综合就有可能表现出一种非常奇怪的样态:如果“触发的趋向”仅仅是非对象的统一,被动综合就应该是非对象的素材统一与对象统一的混合。但这显然有背实际情况,因为对象总是处于某种环境中并具有某些背景的东西,被注意到的对象是与作为背景中的对象一同呈现的,所以“现实的触发”与“触发的趋向”之间的综合就不可能是对象与非对象的统一,而是作为被注意到的对象与不被注意到的对象的统一,而不是对象与非对象的统一。素材在被动综合中就已经被构造为对象,这也意味着“触发的趋向”并不关涉素材,而是关于对象的触发状况之表述。于是,触发状态就是对自我与对象之间注意关系的描述:“任何被构造者只要实施一个触发性的刺激,其都是前给予的,一旦自我转向、顺从、关注并且立义这种刺激,它就是被给予的。”[注]同上,第194页。以自我的关注为标志,对象被区分为“前给予”以及“被给予”两种情况,而且既然“触发已然在一切对象性构造中扮演着本质性的角色,说到底没有触发就不存在任何对象以及任何对象性的被构造的当下”[注]同上,第196页。,那么,哈特曼(John R. Hartmann)的看法就是正确的:“前给予以及被给予并不是在种类上有所区别,而是在触发的程度或相对性上有所区别,对象或对象性构造运用相关联的力量吸引着自我”[注]John R. Hartmann,“The Aporia of Affection in Husserl’s Analyses Concerning Passive and Active Synthesis”, in: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20 (2) , 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1970 , pp.135-159.。“前给予”并不意味着“被给予之前”,而是指“自我关注之前”的“被给予”。
现在,我们可以将胡塞尔提出的“自我关注作为对象构造的条件”变更为“对象构造作为自我关注的条件”。但仍然需要面对以下困难:如果被动综合构造着的是具有触发力量的对象,并且这种构造也是自我进行关注的条件,那么是否具有一种非对象性构造,而且这种构造不具备触发力量。当胡塞尔认为“没有触发就不存在任何对象以及任何对象性的被构造的当下”[注]John R. Hartmann,“The Aporia of Affection in Husserl’s Analyses Concerning Passive and Active Synthesis”, in: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20 (2) , 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1970 , pp.135-159.时,对这一困难的研究就指向了时间意识“一切理论动机都出自于第一个层次的明见性,出自于对我们来说的首要之物:这些建立在已经被结构化了的活的当下的现象上的明见性。”[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李云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97页。
二、时间意识与联想作为触发之保证
胡塞尔在“贝尔瑙手稿”中写道:“感性的本欲是对自我的触发,并且是自我被动的被拉状态”[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肖德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37页。,我们可以发现,在时间意识中触发被视为感性与自我的关联。问题在于,感性是否以对象的方式触发自我?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触发现象就超出了对象与自我的关系限定,从而扩展到非对象的构造状况当中。
胡塞尔通过内知觉研究感性体验,而“一个内在知觉(所谓‘内部’知觉),知觉和被知觉者本质上构成了一种直接的统一体……它只能抽象地、只能作为一种本质上非独立的东西与其客体分开。”[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0页。于是,体验与对体验的内知觉是直接的统一体,那么除非我们展开一个体验,否则我们就无法具有对这个体验的知觉;另外,内知觉也绝不能够使此体验发生变样,否则此知觉就不再是将这个体验的内知觉了。 因此,作为内知觉对象的体验与这个体验本身没有区别、完全一致,于是,体验必然在内知觉介入前就已经以对象的方式呈现自身,这样它才能在成为内知觉对象时保持自身的同一。
体验作为对象“是可以察觉到的,但它们未被察觉到,〈它们不是〉被把握的对象;其自身是一个可以察觉到的进程……每一个把握都得出被把握的对象,这个被把握的对象带有一个此前的视域,并且人们在这里也不断遇到未被把握之物。”[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肖德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46页。因此体验对自我的触发也表现为自我注意力的变化过程;同时,“未被把握”之物作为“此前的视域”,通过被把握的体验与自我相关。而“此前的视域”指的正是滞留[注]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三联书店, 2007 年,第110页。,它“保留着原创立的知识,它保持着处于完全的确定性和存在样式中的意义”[注][德]胡塞尔著:《被动综合分析》,李云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75页。,那么滞留也就保留着曾经的对象性意义。于是,一方面,诸对象在被动综合领域以对照的方式不同程度地触发着自我;另一方面,曾经的体验以滞留的方式、通过触发着的当下体验与自我相关。必须注意的是,滞留与自我关联的形式,并不表现为对照统一的、诸对象间的被动综合,因为滞留只是时间意识的三个维度或特征(滞留、原印象与前摄)之一,三者中任何一个都只不过是对时间意识进行抽象分析的结果,单纯的滞留与单独的现时当下“素材”不可能完成有效的意向结构[注]关于时间意识的三个维度间的关系,笔者将另外详细处理。,这些“素材”在时间意识中“不可能是逐点的,这就是说,它们必须组成延续的时间对象。”[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肖德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46页。于是滞留与自我相关联的方式,恰恰表现为时间对象对自我的触发。
感性体验触发着自我,这说明感性本身也处于对照统一之中了。这些感性体验构成了感性场境,并且“任何一个这样的感性场境都是一个自身相统一的场境,一种同质性的统一体。它对任何其他的感性场境来说都处于异质性的关系之中”[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93页。,在同质场境中的诸对象处于融合对照之中,例如“红色斑点与白色的表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他们却无冲突地互相融合在一起,当然,它们并不是以相互渗透的方式,而是以一种间接融合的方式而融合在一起。”[注]同上,第93页。间接融合是指,进行对照的对象必须具有“同质亲缘性”,而“这种亲缘性或相似性与最完全的亲缘性以及无差别的相同性这一极限状态相比,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程度”[注]同上,第93页。,同质对象间的相似程度越高,这些对象之间的对照程度就越低,它们各自的触发力量也就越低,相反,同质领域中对象间差异越大,它们对自我的触发力量就越大:对象的触发力量与对象间差异相关。同质感性场境是由“联想”构造的,“哪怕是一切原始的对比,也都是以联想为基础的:不同的东西是从共同的基础中凸显出来”[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95页。,并且由于“突现出来的感性的被给予性所作的最普遍的内容上的综合,都是根据亲缘性(同质性)和陌生性(异质性)而进行的综合”[注]同上,第93页。,因而联想不仅构造了同质统一,还构造了异质场境间的对照关系,但这可能吗?
联想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虽然原初地形成的滞留也相互关联并且与原印象关联,但这种时间意识的综合不是联想的综合……联想只在原初的时间结构的前摄的线路上起支配作用。”[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李云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00页。因此联想具有着“唤起”功能,这是一种从当下对象对新对象的指向,这种指向符合时间意识对象的构造规则,表现为对同质对象的持续构造;2、同时呈现的同质对象之间的统一性“在从亲缘者到亲缘者的过渡中被揭示出来。在这种过渡中,新的相同之物作为对同一个东西的‘重复’而出现。”[注]同上,第159页。如果亲缘对象仅仅表现为相似,那么新的东西就作为相似之物出现,于是联想提供了同质对象间的亲缘融合以及对照;3、由于联想可以被描述为“从一个a指向了b……b被a唤起。这个a在‘当下’……恰恰有一种特殊性”[注]同上,第495页。,a的特殊性是“引起一个特殊兴趣”[注]同上,第496页。,那么联想就是带有特殊倾向的指向,相似性是特殊兴趣的成就。
胡塞尔不得不承认,联想无法完成异质对照的任务。他再次将这一个麻烦抛进了时间意识之中。胡塞尔一方面认为各个感性领域在时间意识中“互相混沌地联结在一起……但诸感性领域对此无须相互照应”[注]同上,第418页。;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异质领域的不同触发会相互干扰,例如“剧烈的疼痛会压制绝大多数其他类型的触发状况。”[注]同上,第480页。胡塞尔的处理方式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如果时间对象最初是混沌地联结在一起的,那么它们如何相互分离并且各自组成同质领域?并且,如果诸感性领域在时间的共同性中无须相互照应,异质触发之间又如何相互干扰?更加深刻的困难或许在于,“时间的连续性不应被认为是任何充实以内容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将颜色素材和声音素材混合成一个内时间性的素材”[注]同上,第172页。。异质对象之间的时间构造并不相关,那么我们如何确定这些对象是“同时”或“共时”的呢?必须有某种意识能力能够解决上述疑难。
三、触发作为“我做”与被动综合的共同成就
能够解决上文所提出之困难的能力,就是动感。胡塞尔认为,在一切对象构造中“必然涉及两种感觉……第一种是以侧显化的方式构成着事物本身的相应特征”[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构成研究》,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8页。,以及作为第二种感觉的动感:“在对第一种感觉的一切这样的把握中第二种感觉必然参与……后者相应地属于每一种构成的把握”[注]同上,第48页。,因此动感就贯穿于诸异质领域之中。
动感与诸感性领域以“动机化”的方式保持关联,这是一种“如果—那么”的关系,例如:随着某种动作,身体产生拉扯、挤压感,或者产生粗糙、光滑感等,同样“在视觉中,从眼睛运动中的有序感觉系统中……都有某种系列按此方式展开。”[注]同上,第48页。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动机化”的关系并不是时间先后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是同时性关系——如果这么运动,那么同时就如此显现,于是在感性行为中总是同时有两种运作:“一方面是动感,动机化者一侧;另一方面是特征感觉,作为被动机化者一侧”[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构成研究》,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8页。。
感性体验与动感“并不是彼此并列的过程”[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9页。,相互分立的诸异质感性领域都是对动感运作要求的满足、是动感的效果。这也意味着动感必须服从特定感性领域的呈现规则:我们在一个动作中,可以同时引起视觉显现的变化以及触觉的变化,甚至包括听觉的变化,这些感性序列由同一个动感引起,但构造着完全不同的感觉对象。动感之所以能够与诸异质领域结合,在于动感本身并没有感觉素材,它“并不成为把握的对象”[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构成研究》,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8页。,因此进行对象构造的感性领域的相互分离原则对动感而言完全无效。胡塞尔也将动感视为“我做”:“一切运动感觉,每一个‘我活动’、‘我做’,都相互结合成一个普遍的统一”[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5页。,它是主动实行的“自由的过程”[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构成研究》,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8页。。于是,一方面,动感不以对象性的方式构造自身;另一方面,动感是主动实行的,那么它也不符合“被动综合”、不处于联想对照之中。那么,动感如何“相互结合”呢?在泰帕尔(Taipale)看来,“我做”中往往具有各种似乎不是主动施行的动作,比如走路时双手的摆动或跨步的方式,于是他认为:“动感不经常以主动性地方式实行……而是以没有明确目标的习惯的方式被实行。正如胡塞尔所说,自我不仅‘使自身实行’,而且‘使自身习惯’。”[注]Joona Taipale, Phenomenology and Embodiment,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56.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就可以区分出主动的动感和作为习惯的、“被动的”动感了。但是,泰帕尔误解了胡塞尔。在胡塞尔看来:“自我运作着自身,使自身形成习惯,它在后来的行为中被现前的行为所决定,于是某些动机的力量产生了。”[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9页。也就是说,习惯最初是一个主动实施的动感,它具有特定的目标,并且在不断的对目标的达成中积累成能力,一旦我们要进行一个与这个习惯相关的动感时,这些习惯就被发动起来——无论习惯的形成还是发生,都依赖于主动的“我做”。我们在走动中,具有着跨步及摆臂的习惯,我们完全能够主动地改变这些习惯,让步子迈大些、手臂不摆动,但相对的,我们整个对走动的动感也完全变化了,我对动作的刻意改变恰恰是进行着另一个“我做”。因此严格来说,习惯并不是伴随着主动行动的、未被注意到的动感,毋宁说,习惯是符合特定目标展开的动感方式。
我们在这里实际上是对动感与身体动作进行了区分,既然动感与感性领域相结合,那么动感当然可以在身体动作中得以体现,但动感绝不是动作。一切“我做”都包含着一些可以被分属于身体不同位置的动作,当我抬起双手时,身体呈现着抬起左手和右手的动作,但这种抬起双手的动感,绝不包含“只抬起左手”的动感,即便两者都包含着“抬起左手”的动作,换句话说,虽然抬起双手的动感所造成的动作整体,可以被视为分别抬起双手的动作组合,但却不能被视为抬起左手的动感与抬起右手的动感的组合。[注]我们发现身体动作总是伴随着动感,但这绝不意味着动感只“属于”身体领域,在现象学中身体实际上是触觉系统的统一,它必然是在动感中构造起来的,并且由于触觉的特殊性,身体总是呈现为动作的起点以及空间的定位中心。身体、触觉以及动感三者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细致的研究,笔者将另文处理。动感与身体动作之间不可化约的关系,在其他感性领域内也同样有效,例如,双眼观视与单眼观视,它们之间的差异不仅仅在于睁开双眼与闭上一只眼睛的身体动作区别,也表现在实际的视觉显现效果的区别:虽然在其他条件不变化的情况下,双眼看到的范围涵盖了单眼看到的范围,但双眼的动感并不包括单眼的动感,更显著之处在于,双眼系统呈像与单眼系统呈像间的聚焦以及透视关系完全不同。但是,即便动感之间并不相互包涵或相互对照,但它们仍然保持着时间上的关联,任何新动感的发生都以现时当下的动感为起点,是对现时当下的动感的改变,因此,“一切运动感觉,每一个‘我活动’、‘我做’,都相互结合成一个普遍的统一。”[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5页。鉴于上面的分析能够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动感的当下唯一性保证了异质领域的同时性,异质感性领域围绕着动感展开;第二,随着动感的变化,各个感性领域以自身特有的方式改变着显现样式,进而各种对象的呈现方式、以及对象间的对照统一情况也依照动感而变更,于是,动感参与了诸感性领域的触发发生,当感性领域的触发情况发生变化、吸引自我时,动感也同样发生变更;最终,由于动感的当下唯一性,当某一个感性领域导致了动感变更时,其他感性领域的构造及触发状况也发生相应变更,也就是说,异质领域通过动感相互牵制,它们以动感为“中介”相互干扰,在异质触发间,“获胜的触发没有消灭另一个触发,而是压制它。”[注]同上,第480页。异质领域的触发关联是由动感保证的。
动感是自我实行的自由过程,因此,触发现象就不再单纯是被动综合中属于对象的构造性成就,自我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被动综合对象的触发,而是主动地参与对触发环境以及触发对象的构造,自我也不只是以注意的方式与对象相关,而且也参与了背景对象的构造:“纯粹自我在一特殊意义上完完全全地生存于每一实显的我思中,但是一切背景体验也属于它,它同样也属于这些背景体验。”[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51页。同时,在现时当下的“我做”唯一性与感性对象的多样性之间,也体现出了自我与对象的区别,因此扎哈维认为:“自我被不同于自我的异己之物触发,但这异己之物并非独立于自我。”[注]Dan Zahavi , “Self-Awareness and Affection”in: Depraz and D. Zahavi (eds.): Alterity and Facticity,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8, pp.205-228.自我与背景对象“处于原始显现中的单纯的觉识(Bewussthaben)”[注][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99页。关系中,而“觉醒就是把视线指向某物”[注]同上,第99页。,因此,对象从背景中凸显出来、被自我注意的过程,也是自我从“觉识”向“觉醒”的发展过程。自我与对象并不是“现成的”、“静态的”东西,对象并不只以注意的方式与自我相关,自我也并不只是“静待”对象的触动,它们在相互作用中持续地变化发展,“触发”所展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复杂的过程。
四、结 语
触发恐怕是胡塞尔现象学中最复杂的课题之一。静态现象学可以视为建立在特殊意向性、亦即注意力意向性基础上的现象学,其中自我与特定对象的关系是现成的,可是一旦进入发生现象学分析,对象如何被给予自我就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胡塞尔试图清理出一个无自我的对象性领域,然后此领域中的对象再作用于自我,也就是说,被动综合实际上表明着“双重被动”:对象的非主动构造以及自我的“被触发”。但即便在被动综合的联想功能中我们也发现了某种主动性(特殊兴趣)的特征。当我们面对异质对象的触发关系时,主动性与被动综合的关系得到了完全地揭示:主动的“我做”必须参与对象性的触发构造。因此,哪怕在最深层的被动性领域,也已经存在自我的影响了:自我并非被动地等待着对象以某种效果对自身产生影响,而是积极地介入到触发的发生之中。
——专栏导语
——兼论现象学对经济学的影响》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