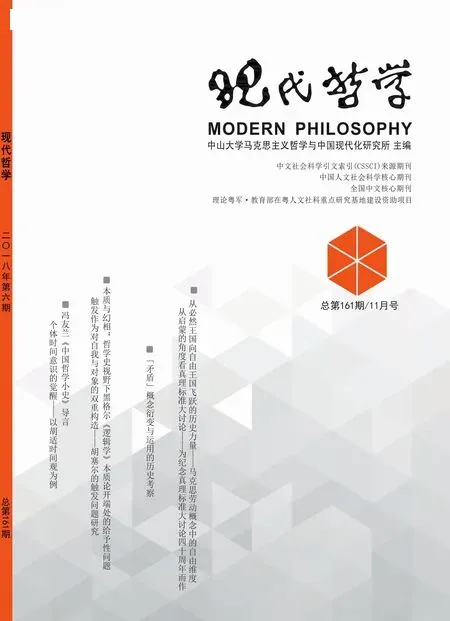个体时间意识的觉醒
——以胡适时间观为例
方 用
一百年前,自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归国杂感》中说:“我回中国所见的怪现状,最普通的是‘时间不值钱’。”[注]胡适:《归国杂感》,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28页。他认为“不值钱”的时间意识导致国人陷溺于不思进取、虚掷光阴的生活状态,不仅践踏了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也将把风雨飘摇的国家带入更危险的境地。个体和国家衰敝的现状和期待“再生”的热望,引起他对时间和生命的多重思考。在他看来,时间造就生命,一种新的时间观将赋予个体生命以新的内涵和尊严,并引发文化的变革和社会的改造。
一、“进化的观念”
晚清以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警醒了部分国人,亡国灭种的危机逼迫这些“先知先觉”者告别相对稳定的时间意识和生活状态。风行一时的《天演论》正在重塑他们的世界观,逐渐形成一种奠基于进化论的时间观。龚自珍《己亥杂诗》之四四曰:“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但在胡适看来,中国传统的“古时丹”已根本无法应对“今”之病:“今日吾国之急需……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注]胡适:《留学日记》卷3,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7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1页。
胡适是进化论思潮的虔诚拥笃者:“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注]胡适:《实验主义》,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5页。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过去、现在、未来构成时间的三维,三维的更迭即是历史的进程。胡适以“进化”为原则来理解和评判过去、思考现在、探寻未来。“进化的观念”是胡适时间观的基础,是其“历史的眼光”的核心,是其救亡图存最重的要药方。
以“进化”为基础的时间观首先强调“时代性”,主张一切因时而变,古今异质。由此,“过去”之维被限定,“现在”之维得以凸显。胡适早年以“文学进化之理”为据倡扬“文学改良”:“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页。文学改良之“八事”重在点醒古今之别,如“不摹仿古人”“不用典”等,都主张今人应直面生活的“现在”之维,以创新的形式、现代的语言,书写这个时代真实的见闻思为,即“现在的中国人”应该创造“现在的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只有主动适应时代的更迭、积极书写时代的精神,文学才能走出“古”的陈窠,获得“今”的新生。他提出韵文有“六大革命”,其“革命”二字重在凸显不同时代文学形式的差异性:“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注]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3页。
文学改良只是当时风起云涌的“新思潮”运动的一个窗口。作为“今”的代表,“新思潮”被赋予复杂的内容和重要的时代意义。胡适指出,对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注]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03页。,并明确将“评判的态度”视作“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和共同精神。“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的吗?’(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应该这样做吗?……’”[注]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99页。
整理国故,虽然首先是回到产生、盛行那个思想的具体时代,但更重要的是要评判是非、重估价值。众所周知,进化论的风靡同时带来一种“进步”的信念,表现在时间观上,即主张古今有别,进而强调自古及今是一个推陈出新、日益增进和提升的过程,古不及今。这种不可逆的线性时间观不仅嘲笑“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不变论,也有别于传统的循环、轮回思想,更冲击了各种以古为尊世风日下的历史倒退论。
显然,“评判的态度”的前两个要求都主张站在“今”的立场,重新估定“古”的价值,以“现在”“今天”为标尺来审视历史、文化的合理性并判定其命运。“时代性”意味着古代文化只在已逝的某个特殊时期有价值,但其价值不会伴随历史的洪流进入现在。“进步性”则阐明不管古代文化过去如何辉煌,终究远远落后或低于现在及未来的文化。
由于进化的观念所强调的时代性和进步性,“国故”终究只是过去式,无法真正从“古”来到“今”。胡适说文言文是“死文字”,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现代文学。他主张“历史的真理论”,认为真理的价值只是“摆过渡,做过媒”,可以随时换掉、赶走。这样的“国故”即使被“整理”出来龙去脉,其价值最终也极易被“评判”为陈设在博物馆的、没有生命的展品。时间之流终究被“评判”之利刀斩断为古今的坚硬对峙,已“死”的过去走不进现在和将来的生命。所以,“评判的态度”不仅要求人们认清古今变易的大势所趋,更要做“反对调和”的“革新家”,将目光聚焦于现在与未来。在胡适看来,生乎今之世而反古之道,是有违进化之迹的背时逆流。
五四运动唤醒了“我”,胡适坚信“唯有个人可以改良社会,社会的进化全靠个人”[注]胡适:《学生与社会》,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91页。。“评判的态度”第三条把“社会”和“我”对立起来,“社会公认”不仅指人数多,也指通过权力、习俗等被固化的“过去”。胡适期待的“我”是“先知先觉”的少数人,“我”要有独立精神,敢于质疑、敏于思考。“我”是能走出过去的枷锁,寻找和创造未来的人。
进化论者一般认为,青少年是未来和希望的代表。例如,梁启超歌颂“少年中国”,李大钊呼唤“青春”,陈独秀情系“新青年”,都是这种时代精神的体现。胡适对年轻人也充满热情与期盼。他同情学生,自称是“爱护青年的人”;呼吁“中国的少年”起来建造“少年的中国”,满心欢喜地表彰“后生可畏”[注]“后生可畏”本是胡适对《大公报》的寄语。他把不满二十八年的《大公报》称作“小孩子”,把快六十年的《申报》和快五十岁的《新闻报》称作“老朽前辈”,赞赏《大公报》为“后生可畏”。这也是胡适对年轻人的期待。(胡适:《后生可畏》,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8—179页。)。
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青少年和老年往往构成不同时间维度的代表。但在胡适看来,“年龄”不是判定“老”的唯一尺度。暮气沉沉的少年无法肩负将来[注]胡适对年轻人的“暮气”非常忧心:“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9页。),年岁渐增也可以老当益壮。他鼓励年轻人要保有朝气,勇立潮头。他送给毕业生的临别赠言是“不要抛弃学问”“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去做一种专门学问”[注]胡适:《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77页。。基于进化论以及“进步”的观念,他相信一代总能胜过一代,提醒他们若没有足够的危机意识,必将被后进的少年无情地淘汰。在他看来,想在社会挣得一席之地,防止在不如意的现实中堕落,个体必须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
同时,胡适为不可阻挡的岁月中人开出一剂“精神不老丹”:“这个‘精神不老丹’是什么呢?我说是永远可求得新知识新思想的门径。这种门径不外两条,(一)养成一种欢迎新思想的习惯,使新知识新思潮可以源源地来;(二)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布下新思潮的种子,预备我们到了七八十岁时,也还有许多簇新的知识思想可以收获来做我们的精神培养品。”[注]胡适:《不老》,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85页。如果一个人能够不为“旧”所锢,坚持求“新”,不拒新知的滋养,不失创造的精神,即使“白头”,也是时代的“新人物”,不会在进化大潮中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可见,一个人“年轻”的时间长度,并不等同于外在的物理时间。容颜易逝,而精神可以日新。
与同时代的鲁迅相比较,胡适更为乐观。本着坚定的进化观念,胡适对年轻人,以及中国社会未来一直充满信心。此外,基于进化的时间观强调古今异质,一切皆变而无物常住。在进化洪流中,任何存在及其价值都是有限的,象征终结的“死”必将随“时”而至。“死”也意味着随时间不息地奔涌向前,历史的人或事必定滞留于既往,而被进化之流无情抛弃。所以,胡适主张“死了的文言”当“废”,作为工具的真理用过可“换”。所谓“过去”不仅是时间的流逝,而且意味着与那“时”有关的生命的消失。因时而变、与时俱进,似乎标志着一切过去都将被斩断、被忘却。往日不可追,故人旧事随之沉寂。那么,还有什么可以传承?还有什么值得留恋?
二、“不朽”
胡适论“不死”。“不死”即“不朽”,指某些不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磨灭的持久因素或永恒存在。“进化”强调因时而变,“不朽”则揭示古今更迭的相对稳定性、连续性。胡适将“不朽”奉为“我的宗教”“我的信仰”,指出他所谓“不朽”既非“灵魂不灭”,也有别于以立德、立言、立功三事为“虽久不废”的传统不朽论。他要阐释的是一种新的不朽论即“社会的不朽论”:“这种不朽论,总而言之,只是说个人的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大小好坏,一一都留下一些影响在那个‘大我’之中,一一都与这永远不朽的‘大我’一同永远不朽。”[注]胡适:《不朽》,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80页。它最鲜明的特点是强调“所有人”的“一切言行”都是“不朽”的,在历史长河中,每个作为个体存在的“小我”都有其“时”。他认为这种观点正能对治传统“三不朽”的三大缺点:
第一,“不朽”的内容涵括了所有人的一切言行,这明确和推广了过去含糊有限的仅以“功、德、言”为范围的观点。胡适认为“功、德、言”只是人类活动中非常有限的内容,而基于进化论,“功、德、言”的具体内涵在不同的国家或历史时期也不尽相同。
第二,胡适认为传统“三不朽”中,真能立功立德立言终究只是少数人,所以只是“寡头之不朽”;而他主张“所有人”,包括“无量平常人”都能不朽。胡适提出“社会的不朽论”的直接契机是母亲的离世。他的母亲是一个极普通的女人,也是对其影响至深的人。平常人,尤其是女人,在过去的历史观中是被忽略或遗忘的。但现代是呼唤平等、呼唤“无量平常人”走上历史舞台的时代。每个作为个体存在的“小我”在其一生有限的时间中,都会留下自己独特的历史印记。胡适的“不朽”摈弃了贵贱有别的生命价值和帝王将相的英雄史观,把普通人纳入历史主体的范畴,这无疑展现了平等的时代精神。对他个人而言,母亲是他一生最难忘最温暖的怀念。
第三,胡适认为传统“三不朽”仅就功、德、言而立论,“没有消极的裁制”。他强调一切言行,无论大小、成败、善恶,都将在历史中产生影响、留下印痕,虽然可能程度不同、性质有别。无数“小我”相互联结、彼此承继,构成历史的“大我”,但这个为“小我”之“纪功碑”或“恶谥法”的“大我”很像唯识学中具有“藏”功能的阿赖耶识[注]“初阿赖耶识……是无覆无记……恒转如瀑流……”([印]世亲菩萨造、[唐]玄奘译:《唯识三十颂》)。作为轮回主体的“阿赖耶识”连接了“我”一期一期的生命,“无覆无记”即阿赖耶识作为种子将不辨善恶地记取“我”造作的所有业,“恒转”即这些种子作为“因”将永恒存在,并在来世产生“等流”即同等性质的“果”。因果相牵,自作自受,世世流转。当然,胡适不论轮回转世的问题,其“大我”也并非作为某一个具体生命个体即“小我”的延续。。胡适强调“小我”的一切言行都将不朽。“善”将积极地推进历史前行,是不朽的善因,将造福于后世的“小我”;而“恶”同样有力量消极地阻碍历史脚步,结下不朽的恶果。名垂千古或遗臭万年都是“不朽”,因为“这一个现在里面便有无穷时间空间的影子”[注]胡适:《不朽》,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78页。这是胡适经常引用的来勃尼慈(Leibnitz,现多译作莱布尼兹)的话。。由此,胡适强调每个个体的历史责任感:“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注]胡适:《不朽》,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81页。
胡适强调身处“现在”、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小我”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者:在空间上,其与社会或世界的全体互为影响;在时间上,其和社会世界的过去和未来都有因果关系。现在的“小我”是过去无数“小我”的各种“前因”而共同产生的“后果”,其间保留了过去“小我”的种种印记。现在的“小我”又是造就将来“小我”的“前因”,会把现在“小我”的种种印记传递到将来。无数的“小我”构成一脉相承永远接续的“大我”。作为个体的“小我”生命有限,必死无疑,但由无穷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小我”代代相传所形成的“大我”却是连绵不绝,永远不死的。
所谓“大我”之不朽,即通过因果关系的普遍性、必然性,以及前因后果的时间上的延续性,揭示“小我”在时间流逝中对个体和他人的种种广泛持久的影响、作用。“进化”强调古今异质,侧重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的推陈出新、替代更迭。“不朽”凸显了那些贯串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中并逐渐沉淀和持久留存的因子。任何的“小我”都只能在时间洪流的某一个特殊而有限的阶段活着,但这个“小我”裹挟着某些不随时间的前移而消逝的因素或力量,与已逝的过去、将至的未来因果相连。这些留存在历史进程中的“纪念品”或“遗形物”[注]“文学进化的第三层意义是:一种文学的进化,每经过一个时代,往往带着前一个时代留下的许多无用的纪念品;这种纪念品在早先的幼稚时代本来是很有用的,后来渐渐的可以用不着他们了,但是因为人类守旧的惰性,故仍旧保存这些过去时代的纪念品。在社会学上,这种纪念品叫做‘遗形物’(Vestiges or Rudiments)。”(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9页),既是“小我”的“不朽”,又通过因果相续把无数已“死”或将“死”的“小我”串联为“不朽”的“大我”。
为什么胡适特别强调“恶”也会不朽?这首先缘于直面和反省落后挨打的苦难现实。一方面,“我”现在遭受的一切苦难,正是过去懒惰不负责的“我”造成的,因而是现在的“我”无法逃避的“消极的裁制”,每个现实中具体的个体都只能背负着历史前行。另一方面,现在的“我”必须很努力很谨慎,不能荒废过去累积的善果,更不要种下未来必报的恶因。更重要的是,在进化论者看来,一切价值也因时而变,过去曾经的“善”在新的时代可能无用甚至成为阻碍时代递嬗的“恶”的力量。现在的“我”如果不能从因循守旧的惰性中挣脱出来,努力创造新的“善”,未来的“我”将更积重难返寸步难行。可见胡适所谓“消极的裁制”,既指历史进程中,现在的“我”无法推卸的、过去所遗留和累积的“恶果”,也指由现在的“我”的不思进取或为非作歹所引导的、必将成为未来的“我”不能逃脱的厄运或宿命。他确信“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注]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32页。,强调“恶”亦不朽,意在唤醒每一个现在的“我”的历史主体性和责任感。
诚然,胡适“社会的不朽论”笼统而粗疏,甚至带有浓厚的佛教因果观的色彩。但他纳一切有限的“小我”于无穷的“大我”,由“大我”的“长生不死”,将“所有人”及其行为都平等地纳入历史进程;并通过对“消极的裁制”的凸显,旨在呼唤当下每个个体即“小我”的历史责任感,主动承担过去的背负,也于现在积极努力地造善因集善缘,以避免未来更严酷的消极裁制。我们可以认为“功德盖世”与“吐一口痰”都是“不朽”只是虚说,重要的是,每个个体都应该从“我”开始,从现在的点滴开始,勇于担责,善于创造,即纳须臾于永恒。这样的个体才是真正推动历史、积极对历史负责的“小我”,由这样的“小我”所构建的历史才是有希望有前途的“大我”。
值得注意的是,标志时间和生命永恒的“不朽”,其背后挺立的仍是坚定的“进化”意识,被强化的仍是“现在”之维:不仅要勇于承受由无量“过去”之“因”积累而成的“现在”之“果”,更要努力从“现在”开始,改造旧社会,创造新气象,能否推陈出新、推动社会进步仍是判断“现在”之“小我”一切言行善与恶的唯一标志。“不朽”之“消极的裁制”强化了进化过程中历史主体的参与意识。
胡适在晚年的一篇演讲中指出:“我今天提议,不要把中国传统当作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看,要把这个传统当成一长串重大的历史变动进化的最高结果看。”[注]胡适:《中国传统与将来》,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1页。“传统”是“变”中之“常”,“把前代的创获给我们保存下来,并传给我们”[注][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页。。“传统”凝结了历史演进中相对稳定、世代传承的文化或精神,即那些“不朽”的因素。如同强调“不朽”有“消极的裁制”,“传统”在他看来也未必都是“神圣”的,中国传统也有“种种长处和短处”。与“进化”结盟的“传统”,不仅要指出某一具体传统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也要关注历史的进化是如何造成传统的进化。文化史就是从旧传统中引出新传统,新传统又取代旧传统的过程。
所以,“不朽”并不意味着单纯的纪念或怀旧,而是意味着以“进化”为原则,主动地打破、革除旧文化的枷锁,自觉地推进、创造新文化的进程。“传统”之“常”并非凝固不变的,坚守传统也并非固执旧制。所谓进化的“传统”,是在积累和淘汰、吐故与纳新、复兴和创造中不断生成的。
在胡适看来,当下的中国文化新传统正在形成。但此传统不可能拒绝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特别指出:“这个再生的结晶品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是带着西方的色彩。但是试把表面剥掉,你就可以看出做成这个结晶品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我深信那个‘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的传统没有毁灭,而且无论如何没有人能毁灭。”[注]胡适:《中国传统与将来》,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1—183页。在胡适心中,“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是中国文化之根,是中国文化真正的“不朽”,是延续千载、虽隐不绝的真“传统”。
三、“经济”
动荡的时局,救亡的迫切,容易使时人产生岁不我与的焦虑,基于“进化”的时间观更强化了时不我待的紧张。归国的胡适对“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无奈而痛心。与现代西方大机器生产的高效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他所目睹的中国工人依旧非常落后低效的生产方式和工作状态:“上海那些拣茶叶的女工,一天拣到黑,至多不过得二百个钱,少的不过得五六十钱。茶叶店的伙计,一天做十六七点钟的工,一个月平均只拿得两三块钱!还有那些工厂的工人,更不用说了。还有那些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说了。”[注]胡适:《归国杂感》,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28页。工作时间长、强度大,付出的时间成本很高,结果不仅劳动者个人的收入极为卑微,所创造的社会价值也非常有限。这样的生产又如何能使民众走出贫困,使国家走向富强?进而,胡适指出,低报酬的时间意识背后是对生命本身的漠视:“美国有一位大贤名弗兰克令(Benjamin Franklin)的,曾说道:‘时间乃是造成生命的东西。’时间不值钱,生命自然也不值钱了。”[注]胡适:《归国杂感》,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28页。生命的“不值钱”不仅指付出与收入的巨大差距,更指维持和护养生命的存在,以及尊重生命价值之观念的严重缺失。大多数人没有花时间保健康的意识,甚至连死亡也无关轻重。但没有对死亡的自觉和敏感,人对时间尤其是个体时间的感受也是空洞淡漠和无所敬畏的,不惧死,亦不知生[注]“通过时间之流经验,有死的人类实现了对自身有终性的自觉。对死的自觉,同时就是对生的自觉。弗雷泽说:人……是有死亡意识从而有时间意识的生物。”(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胡适还目睹那些不明白时间应该“值钱”的人们随意地虚掷自己的光阴,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却从未意识到在无所事事的呆坐、漫无边际的闲聊中,不仅自己的生命正在变得空虚荒芜,同时也“谋财害命”[注]美国总统富兰克林(胡适写作“弗兰克令”)的这句话在当时影响深远。鲁迅亦云:“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9页),剥夺了他人生命的存在和价值。胡适慨叹国人依旧沉浸于这种迟缓凝固的生活状态。有感于此,他从文学入手求变,力图倡导一种“经济”的时间意识。他认为短诗、独幕戏和短篇小说是“世界文学的趋势”,首要原因就是力求“文学的经济”:“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天,时间越宝贵了,文学也不能不讲究‘经济’;若不经济,只配给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老爷太太们看,不配给那些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看了。”[注]胡适:《论短篇小说》,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3—104页。随着“无量平常人”登上历史舞台,文学已不再是有闲阶层的专利。走向忙碌的普通大众的文学必须在“最简短的时间”之内,讲述或演出完整的故事,给观众带来疾风暴雨似的心灵震撼。这就是“时间的经济”。
力求“经济”的时间意识是进化思想的必然要求。“过去慢”,相对稳定的时代容易产生近乎停滞的甚至循环的时间体验。但进化揭示的是古今嬗变新旧更迭,个体已被绑上急速变化不断前行的历史大轮,只有紧跟时代的步伐才能应付。胡适区分历史进化的两种状态:“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演进是无意识的,很迟缓的,很不经济的,难保不退化的。有时候,自然的演进到了一个时期,有少数人出来,认清了这个自然的趋势,再加上一种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进,使这个自然进化的趋势赶快实现;时间可以缩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因为时间忽然缩短了,因为成效忽然增加了,故表面上看去很像一个革命。其实革命不过是人力在那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上了一鞭。”[注]胡适:《白话文学史》,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9页。
虽然进化是大势所趋,但若一味听其自然无疑只能“缓步徐行”,而“革命”是以“人力的促进”撤除进化的障碍,加速进化的过程,所以是很“经济”的手段。“经济”的时间观意味着时间并非外在于人而均质流动的,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人力”可能极大地影响时间的方向和效用:既可能人为地使自己的时间减缓停滞甚至从现在拉回过去,也可能奋起直追,奔向未来,在较短的时间赶上甚至超越经过较长时间发展的他者。
可见,所谓“时间差”并不具有绝对意义。欲实现时间的“经济”,“人力”的自由选择和主动参与非常重要。胡适有一种不怕“晚”的信心和乐观,呼吁“先知先觉”的少数人行动起来,引领大众学会甄别和顺应进化的方向,学会以“经济”的方式加快前行步伐。他坚信只要持之以恒,“我们在十年二十年里,也可以迎头赶上世界各先进国家”[注]胡适:《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98页。这是胡适在抗战胜利后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集会上的演讲。。
当然,片面强调效率、以“经济”作为时间的唯一价值,必将导致人心的躁动虚浮和功利主义的倾向。单纯强调文学是“经济的”,必然会疏忽心灵同样需要浅吟低唱的舒缓与旷日经久的熏染“文学革命”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但以之为文学发展的唯一方向,不免失之偏颇。尽管胡适强调“革命”及“经济”的时间在进化中功不可没,但也痛感人心急不可耐的危险。他曾多次提到“勤谨和缓”四字秘诀。“勤”和“懒”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时间的方式,“勤”在一定意义上是指充分、合理地利用时间,一点一滴,坚持不辍。他强调要坚持利用和积累零碎时间:“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可读十一万页书。”[注]胡适:《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77页。个体要确立自己的生活目标,努力化零为整,积少成多,终至不断丰富和提升自我。在他看来,个体生命的价值并非等同于生命的客观长度,通过“勤”,有效时间增加了,生命的价值也提升了[注]胡适曾引用两首诗:“中国的懒人,有两首打油诗,一首是懒人恭维自己的:无事只静坐,一日当两日。人活六十年,我活百二十。还有一首是嘲笑懒人的:无事昏昏睡,睡起日过午。人活七十年,我活三十五。”与此相对的是他尊称为“科学圣人”的爱迪生:“睡四点钟觉,做二十点钟科学实验,活了八十四岁,抵的别人一百七十岁。”(胡适:《终生做科学实验的爱迪生》,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31页)。“缓”并非松散、懈怠,而是能不为外在的时间所逼迫,确保自己内心沉稳的节奏,不忙不乱,不急功近利,不心浮气躁,放慢速度,耐住寂寞,平心静气、从容处事。他特别指出:“缓,这个字很重要,缓的意思不要忙,不轻易下一个结论。如果没有缓的习惯,前面三个字都不容易做到。”[注]胡适:《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74页。“忙”者易“盲”,“缓”才能无征不信,杜绝武断,慢工出细活。在胡适看来,“勤谨和缓”不仅是治学之方,也是为人行事之道。
可见,“经济”的时间观所指向的并非绝对客观时间的长短,更多的是强调个体能合理而有效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以期获得最大的收益。“经济”的时间观给予他迎头赶上的信心和乐观,“勤”“缓”的处事态度又使其避免盲动及失败带来的徘徊和绝望。胡适再三强调“历史的眼光”的重要性,主张既要通过客观的比较,评判国家和个人在有限的时间中所取得的进步;也要了解事之艰辛、路之坎坷,破除“奇迹”降临的妄想[注]胡适多次著文讨论信心与乐观的问题。例如,“今日最悲观的人,实在都是当初太乐观了的人……悲观的人的病根在于缺乏历史的眼光。因为缺乏历史的眼光,所以第一不明白我们的问题是多么艰难,第二不了解我们应付艰难的凭借是多么薄弱,第三不懂得我们开始工作的时间是多么迟晚,第四不想想二十三年是多么短的一个时期,第五不认得我们在这样短的时期里居然也做到了一点很可观的成绩。如果大家能有一点历史的眼光,大家就可以明白这二十多年来,‘奇迹’虽然没有光临,至少也有了一点很可以引起我们的自信心的进步。”(胡适:《悲观声浪里的乐观》,《胡适文集》第5册,第365—366页)。
相较而言,胡适更愿意用“改良”替代“革命”,重视“建设”胜过“破坏”。他相信进化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主张“一点一滴的改造”。坚持“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注]胡适曾在1916年1月25日的日记中表明心迹:“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明知树人乃最迂远之因,然近来洞见国事与天下事均非捷径所能为功。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为迂远而不为,则终亦必亡而已矣。”(胡适:《留学日记》卷12,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6页。),以“勤”“缓”为美德。他一直比较警惕“革命”的破坏功能,反对走捷径,反对“早熟之革命”。他主张“以学术救国”,认为“要科学帮助革命,革命才能成功”[注]胡适:《学术救国》,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3页。。这既有其实验主义的哲学背景,更与他以科学理性为基来理解时间、生命的密切相关。
四、“闲暇”
如前所述,“我”的觉醒也包括“我的时间”的觉醒,即“我”应该有自由支配“我的时间”的权利和能力。时间造就生命,而“我的时间”造就了与众不同的“我”。
胡适重视每个作为个体存在的“小我”,反对在历史进程或社会活动中无视“小我”的作用,或以任何名义淡漠甚至牺牲“小我”的论点。在他看来,每个“小我”时间都是无穷时间中“大我”必不可缺的一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每个“小我”的生命历程在进化之流中都会留下各种“不朽”,参与影响或构建创造历史的活动。“小我”的一生并非只是来世间空耗了一段与己无关的“时间”。
因为确信现在的“小我”与无穷时间的“大我”的紧密联系,胡适反对各种将“小我”游离于他人或现实之外的观点[注]胡适认为个人主义有三种:一是“假的个人主义”,这是一种“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利益,不顾群众利益的为我主义(Egoism)”;二是“独善的个人主义”,其性质是“不满于现社会,却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三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认为只有最后一种才是“真的个人主义”。(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文集》第2册,第509-510页)。他推崇以易卜生主义为代表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认为现代个体应该“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注]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40页。。换言之,每个“我”都应该是因材造就且特立独行的,甚至这就是基本人权之一[注]胡适曾说人权是“中国今日人人应该讨论的一个问题”。“平社”时期,胡适、罗隆基等人合著《人权论集》,列出做人必要的条件即人权的三个要点,其中就包括“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罗隆基:《论人权》,《胡适文集》第5册,第492页)。
另一方面,胡适反复强调“小我”若要真正有益于“大我”,必须先塑造自己,“你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注]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41页。。个体若不能坚定而充分地发展自我,就不可能积聚足够的力量与社会或其他阻碍自我发展的势力抗争,既无法“救出自己”,也不能“霸占住这个社会来改造这个社会的新生活”,甚至会如《雁》中的少年,不仅无力走向将来,反而被归化驯服,回到了过去。
显而易见,一个为生计所困、每天必须长时间艰辛劳作的个体,几乎不可能有自由支配的时间,更遑论发展有个性的自我。所以,时间的“经济”是非常必要的。胡适重视科学的力量,赞叹机器生产解放人力,期待通过改善生产方式提高效率,以便个体能在谋生的“工作时间”之外,腾出“闲暇”来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胡适把“非职业的玩艺儿”称为“业余活动”,把应付职业之外的时间称为“闲暇”。他劝诫年轻人必须以“职业”谋生,但可不以“吃饭”为唯一目标,特别强调毕业后要“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即以自己的才性和兴趣为研究学问的尺度,利用“闲暇”来发展“非职业的兴趣”。他甚至认为一个人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注]胡适:《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6页。在有限的社会条件下,个体所从事的工作或环境很可能与个体的性情相违,因而工作时间的感受可能是不适的、厌倦的。但由“非职业的兴趣”所充盈的“闲暇”却是身处烦劳工作的个体的精神慰藉和生命期待。在“闲暇”中,个体从谋生的困苦中解放出来,充满趣味和热情地从事自己向往的活动,从中感受个性舒张的愉悦,享受称心如意的快乐。在一种无压迫无功利的自由状态中,成功也常常不期而至。
当然,一个认为时间“不值钱”的个体也不会有珍惜时间的意识,不懂得如何创造和利用闲暇时间从事“正当”的活动。中国人从来不缺“闲”,关键在于如何“消闲”。这可能是鲁迅所谓的“谈闲天”,可能是王国维笔端的各种医治“空虚之消极的苦痛”之方,也可能是胡适耿耿于怀的打麻将[注]胡适曾很悲愤地给打麻将算时间帐:“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间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麻将,还是日兴月盛,没有一点衰歇的样子,没有人说它是可以亡国的大害。”(胡适:《漫游的感想》,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6—37页)。面对“闲暇”,个体的自我选择和坚持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注]胡适:《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6页。打麻将也是一种“消闲”方式,但沉湎于此,荒时废业,甚或误国。然若能潜心学问,或致力革新,假以时日,与己总有长进,与国亦有推动。
诚然,“职业”与“业余”、“经济”与“闲暇”未必总是非此即彼地对立着。但“闲暇”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闲暇”与个体的自由相关。胡适强调个体的时间和生命不应为职业所限,个体应该争取和创造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同时“闲暇”的利用取决于个体的自我选择,个体应该充分利用闲暇以丰富自己的生活、发展自己的个性、提升自己的能力。“闲暇”时光正当的“业余”活动无疑是实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重要时间保证。胡适甚至视其为个体“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防止在不如意的现实中堕落的“最好的救济方法”。他特别喜欢“功不唐捐”一词,在闲暇时间的付出终将在未来得以回报。种豆得豆,因果等流,个体如何支配闲暇,往往成就了个体独特的生命内涵。无数“小我”汇合成“大我”,因而如何面对“闲暇”也成为国家文明的标志之一[注]“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胡适:《慈幼的问题》,《胡适文集》第4册,第587页)。
五、结 语
胡适的时间观以“进化”“不朽”“经济”“闲暇”等为关键词,显然时间的客观结构、特征不是其思考重点。“进化”强调古今异质以及革故鼎新的进步趋势,这种不可逆转的、线性的时间观赋予个体追赶潮流、力求“经济”的时间意识。“不朽”揭示古今相续,强调“小我”在无穷时空的延展中不可磨灭的影响,这既有对过往的尊重,或对守旧的抗争,也有对未来的警示和担当。“经济”的时间强调高效,也使“闲暇”有了可能。
胡适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自己怎样生活”,若能坚定地“用此生作点有意义的事”,“活一日便有一日的意义,作一事便添一事的意义,生命无穷,生命的意义也无穷了”[注]胡适:《人生有何意义》,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71页。。时间造就生命。他呼吁“无量平常人”要积极参与历史进程,倡导“健全的个人主义”,即作为生命个体存在的“我”不仅要做“进化”洪流中图存的“适者”,更要负责任地创造无穷时空中的“不朽”;不仅要有时间急迫感,追求“经济”的时间,更要自主地驾驭“闲暇”时间,充分发展自我,实现个性。胡适对“个人”的大力弘扬,也标志着个体时间意识的觉醒。
与大多数进化论的信奉者一样,胡适对年轻人和未来总是保有乐观的。在古今中西的冲刷激荡中,他反对过于迷恋过去、沉浸在中国古代所谓的“祖宗的光荣”,终其一生都在期待和致力于“中国再生”。“再生”是对时间和生命的一种特殊理解。少壮、衰老、死亡是生命规律,但“人类集团的生活和国家民族的文化之演进,虽也是由少壮而衰老而死亡;但是在衰老时期如果注射了‘返老还童’针,使获得了新的血脉,那么一朝焕发新的精神,从老态龙钟转变而振作有为,于是,国族的各方面都表现了新的活动,这个时期,历史家称为‘再生时期’”[注]胡适:《中国再生时期》,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9页。。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已充满“老性”,暮气攻心。虽然疲敝不堪、奄奄一息,但终究还有一条生路,那就是尽快输入新鲜的“少年血性”。中国“再生”必须从“现在”开始,而现在的“少年”是睁眼看世界的一代,他们为中国创造新文化,是中国“再生”的新血脉。
20世纪中国思想界,既有以意欲为根基的时间观(梁漱溟),也有以情感为时间奠基的唯情主义时间观(朱谦之),更有以“道”为根基的绝对时间观(金岳霖)和以心-本体为根基的时间观(熊十力、牟宗三)。凡此种种,充满意趣,给人以无穷的遐想与安慰,但终究可爱而不可信。围绕现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文化的重建,胡适以科学理性为根基理解时间,不仅可信,而且赋予过去、现在、未来以情感态度与价值,使冷冰冰的物理时间有了温度、多了可爱。这是胡适时间观的最大特点,也是他留给现代中国哲学的重要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