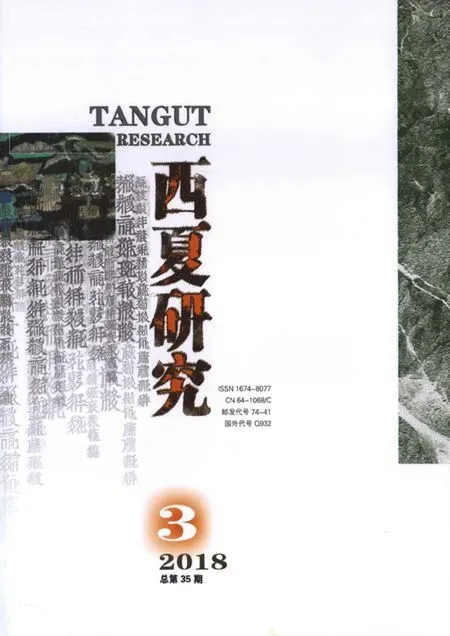吴丰培与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
□路其首
对历史学家的研究是史学史研究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20世纪以来对中国史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团体和个人。随着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历史学也进行着变革与转型,对当时涌现的学者进行研究,会让一个学科在转型发展时期表现得更加生动与立体。正如马大正所言:“对研究个体、研究群体的评述尤应重视,因为从个体到群体的过渡和群体的形成是学科发展的标志和保证。”[1]147
吴丰培(1909—1996)是我国著名的边疆史地专家、藏学家、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目前关于吴丰培的研究较少,多为纪念性文章①。吴丰培早年加入禹贡学会,与顾颉刚等人有着密切的交往。吴丰培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本文试对吴丰培与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关系作一探讨。
一、吴丰培边疆史地研究缘起
吴丰培的边疆史地研究深受家庭的影响。其祖父吴恢杰,同治十三年(1874)耳闻西北战事后投笔从戎,到新疆提督张暇幕府内做事,整理收集西北边疆史料,先后撰写了《西行日记》、《东归日记》、《西征记程》等著作。其父吴燕绍(1868—1944),光绪十四年(1888)应试秋闱,因“三场策论,有西北地理,竟瞠目不知所对,落第而归”。此事对吴燕绍打击颇深,“愤而读辽、金、元史,西域诸书,西藏史志,于西北史地,粗知梗概,边域情况,悉心研究”。光绪二十年(1894),吴燕绍中进士,任内阁中书,随民政部大臣善耆赴内蒙古考察。后任吏部候补主事、理藩院主事。因当政者对于边疆地区“一切历史源流,地理沿革,毫无所知”,吴燕绍即“奋力从事于蒙古研究”。民国成立后,吴燕绍任蒙藏院民治科、宗教科科长,对西藏、蒙古历史地理、民俗风情颇有研究,曾主编《藏文白话报》。20世纪30年代,吴燕绍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教授“边疆史料学”、“西藏历史”等课程,收集、采录了大量蒙藏等民族的史料,撰写了《西藏史大纲》,获得了极大声誉。“当时清史馆成立已久,记、传、表、志均有人承担,独西藏一篇,尚缺撰人。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亲临敝舍多次,敦请先父承担,情不可却,始允撰写。”[2]261吴燕绍又辑录编纂了史料长编《清代蒙藏回部典汇》,涉及1583年至1911年清王朝有关边疆地区的圣训、起居注、上谕、奏章、军机密档、图书等各类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价值[3]401。
吴丰培幼时多病,跟随父亲家塾学习。1930年,吴丰培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朱希祖、孟森等人研习明清史。受家中藏书影响,吴丰培早年兴趣点在明代古籍上,“我在这三个大藏书处(注:指北京大学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浸馈于中者五年,遍读罕见的明代史籍”[4]2,“对于史部目录学,渐有所知,将明代实录及李朝实录有关系倭事,均加摘录,旁及禁毁书籍,广事阅读。五年于兹,数易研究题目,最后以《明驭倭录补校》十六卷,交送审查,取得毕业证书”。吴丰培在课余时间仍然进行写作,“时于北京《晨报》艺圃撰文,如近代史中个别人物传记轶闻与专注介绍等”,又在《大公报》上与傅斯年进行了关于《明实录》的争鸣 。[5]359-360
可见,在整个研究生学习阶段,吴丰培的研究重点在明清典籍,极少涉及边疆史地。虽然家中两代人都从事边事研究,但吴丰培从童蒙时期接受经典之学,到后来研究生学习,基本属于传统史学研究的经典内容,并没有深刻领会到边疆研究的内容和意义,后来随着一系列环境的变化,吴丰培才“重操祖业”,转向边疆史地研究。
二、吴丰培与禹贡学会
吴丰培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早期加入禹贡学会及其与顾颉刚的交往,二是学术生涯中整理的西北边疆史地资料。
1934年,燕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顾颉刚与辅仁大学任教的谭其骧,联合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选课学生,于同年2月组织禹贡学会,3月1日起发行《禹贡》半月刊。吴丰培在校期间即被“邀为会员,开始习作,均载于《禹贡》中”,后来他在学会中担任了编辑的角色,“承担一些购书任务及编辑地理消息。对于发表文章,从不付酬,工作均为义务性;而稿件涌至……一跃成为蜚声中外的主要史地刊物之一;会员初仅数十人,后增为数百人,业务工作人员也倍增,成为庞大的学术团体”[6]16。
吴丰培发表在《禹贡》半月刊的第一篇文章为《明代倭寇史籍志目》[7]29-36,这属他最初研究的领域,发表年份为1934年。第二年吴丰培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变化:“(顾颉刚)嘱余将研究明代历史暂停,而将先父燕绍先生所积存蒙藏旧档,加以整理,打开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专研究北平史料之局面,另辟西藏史地研究。”②因此,该年发表的文章题为《西藏图籍录》,由于刚接触边疆研究,吴丰培声称“余于地理沿革夙属门外汉”[8]53-63。这篇文章拉开了吴丰培边疆史地研究的序幕。
吴丰培研究方向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环境的急剧恶化。1934年,顾颉刚赴内蒙古考察,边疆的政治情形使原本研究古史的顾颉刚备受震动,“查、绥两省旦夕有继东北四省沦亡的危险,心中着急,想唤起国人共同密切注视边疆问题”[9]223。作为禹贡学会一员,吴丰培也深感时局之险。一是国内形势的危急,“华北风云日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由东北转向了热河、察哈尔,既成立了伪蒙疆机构,又成立了伪冀东机构,包围华北。而谭其骧于南方授课,由冯家升继之,与顾先生通力合作,扩大了刊物范围,由古地理研究,部分转向边疆研究,向国内当局及人民大众大声疾呼,共研边隅,以固边疆”[6]16。二是深感近代以来国内政治的腐败,“读近代史,对于清代官吏之丧权,使人痛心,此所以尽毕生精力,从事于边事研究之原因。冀唤起国人之重视,以挽回危局”[10]67。
顾颉刚“将《禹贡》半月刊内容转到了以研究边疆历史和记录边疆现状为主”[9]223。1936年1月,顾颉刚作了《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后改为《禹贡学会研究边疆学之旨趣》),较为全面地规划了禹贡学会的工作思路,将重点转为边疆研究,“爱国志士中历史学者,奋起研究边陲史地,共谋对敌之策”[5]360。正如当时学会会员童书业所言:“自东北四省失陷以来……大家都暂时放弃了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至于留在学术界的人物, 也渐渐转换了研究的方向,即如本刊的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就是这种潮流的明显的表现。”[11]1禹贡学人将他们的边疆史地研究视为继清代学者边疆研究之后的“研究边疆之第二回发动”[12]68。
吴丰培的边疆研究,将重点放在了边疆史料的发掘上,不仅是由于家学渊源,更是基于民族危机下对本国历史文献的发掘与保护。“我目睹时艰,愤而从事边疆研究工作,希望用确凿的历史材料,以供恢复之用。又感各国御用学者及探险家,对于此项研究,较为详备,而国人著作反叹不如,岂国人才力不如,抑写作技巧逊色?肯定来说,均可云否。乃对于我国丰富史料,发掘不深耳。”[13]117个人心理的变化受社会环境影响和制约,尤其对具有家国情怀的学者而言,学术研究的转向必定要为当前国家社会服务。这也成为了吴丰培毕生所从事的研究,而且对其后来的学术心境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因“研究边疆问题之人日伙,而边疆之书流传较少”,1936年5月,吴丰培致信顾颉刚,建议“取稿本钞本或刊本而不易得者重为刊印,成一《边疆丛书》,以备研究者之取材”[14]76。由于经费紧缺,吴丰培提出了“集股之法”,后得中英庚款委员会资助3万元,才得以出版。“《边疆丛书》,由顾廷龙先生和我主编, 选书写跋是共同负责, 排版定式都是顾独任,拟每月出书一种,10种为一集,计划为10集。专选边疆罕见之本。”[6]17原计划有《西域遗闻》、《哈密志》、《科布多政务总册》、《西藏日记》、《经营蒙古条议》、《塔尔巴哈台事宜》、《敦煌随笔》、《敦煌杂钞》、《西行日记》、《准噶尔考》等十种,后中英庚款委员会停止资助,仅出版了《西域遗闻》,“在编者的努力下, 另筹资金,以捐款赠书的办法, 终于出版了《哈密志》、《西藏日记》、《科布多政务总册》、《敦煌随笔》及《敦煌杂钞》6种”[6]17。
在1936—1937年间,《禹贡》半月刊又创立了各种关于边疆的专号,共有十个,其中“第六卷第十二期为《康藏专号》,由吴丰培主编”[6]16。这些专号的出现,标志着《禹贡》半月刊对边疆问题的研究达到高潮[15]63。不仅如此,在1935—1937年间,吴丰培编成《清代西藏史料丛刊第一集》及《清季筹藏奏牍》三册, 分别于1937年、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计五十余万字[16]159,其中有许多罕见的珍贵史料,于西藏近代史研究极为重要。
由于北京沦陷,1937年7月16日《禹贡》停刊,会员纷纷离京。禹贡学会会址和藏书在1941年由赵贞信交吴丰培保管, 吴丰培“靠取房租维持看守人的工资和修缮之费”。不仅如此,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藏书也处于无人看管的境地,吴丰培组织同事将“有关边疆及北平方面之图书资料”,“分装二三十箱移存中法大学保存”[5]362-363。1946年北平研究院迁回,保存在中法大学的图书完好无损。1946年3月顾颉刚至京后,吴丰培将房屋和图书移交,禹贡学会重新迁入。在日寇蹂躏京城之时,吴丰培坚持看守禹贡学会的资产,为禹贡学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在敌人侦骑密布,偶语遭祸的压迫下,经过艰难隐蔽,数年于兹,终将会地房屋和图书设备安保无失”[6]17。且在此期间,其生活异常拮据,“上有七旬严亲,下有六个幼龄子女,九口之家,一人肩负”[5]363。复刊后,《禹贡》半月刊改为季刊,由翁独健负责,计划出《禹贡通讯》、《禹贡周刊》、《边疆丛书》。《禹贡通讯》出了一期便因通货膨胀而告罢。《禹贡周刊》在《国民新报》开辟专栏,共出了十期。《边疆丛书》由吴丰培负责,也面临着与前两者同样的问题。后吴丰培自筹资金,印了《北征日记》、《西行日记》、《巴勒布纪略》、《乌鲁木齐事宜》、《塔尔巴哈台事宜》、《新疆回部志》等6种书。限于经费,《回疆志》、《乌鲁木齐事宜》、《塔尔巴哈台事宜》、《巴勒布纪略》改为油印,合为《边疆丛书续编》。
可以说,禹贡学会对于吴丰培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没有当时的环境刺激和禹贡学会浓厚的学术氛围,吴丰培可能会继续研究明史。“在他(顾颉刚)的鼓励教导下,我放弃了明史研究,继承先父学业,专搞边疆史料,五十年来,一直走这条道路。”[17]187学会的氛围加之社会的环境造就了他学术研究的方向和态度。顾颉刚的指导和栽培,使吴丰培的学术研究得到了很大提升,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与顾颉刚的情谊。吴丰培在回忆当年在禹贡学会工作时道:“通过这种兼容并蓄,培养后学的办法,许多有为青年都团结在禹贡学会周围。”[18]435-436
顾颉刚提携后辈的做法使吴丰培感动至深:“他平生待人极为和气,可是对工作十分认真。记得我编《康藏专号》有几处明显错字,没有校改,即当面指出,并对于如何校稿教导了许多经验,至今言犹在耳。他在北大、燕大的历史系学生,往往指定题目,让学生习作,文成之后,亲加修改,甚至将不够水平的文章,也润饰成篇,仍用作者名义为之发表。”顾颉刚积极提携后学,“他发现有一技之长,即加鼓励,指出治学方向,希望写出文章,遇见贫苦青年,或加接济,或安排抄写工作,住处有问题,则留家中或在学会中暂住,若有写作,有水平而不合《禹贡》范围,则代向其他刊物推荐,若为专著,则代为推荐出版”[18]434-435。“这种敢于用他的声誉和地位来提携后辈的魄力,是难能可贵的。”[17]188吴丰培的描述,使一位谦和热情的学术领袖跃然纸上。赵俪生曾言:“顾先生一个重要功德,就是在生活上资助了很多后辈学者。”[19]462这也是历史地理学界乃至中国史学界的一段佳话。
三、吴丰培的边疆史地研究及其心境
(一)边疆史地研究成果述略
1936年以后,吴丰培就开始了他的边疆史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明清近代的边疆史料搜集、汇编、整理和出版上,研究区域主要为西藏、新疆二地。他在整理文献过程中写有题跋,这些题跋是了解他学术经历和思想的重要材料。目前在吴丰培学术生平的相关研究中,题跋的利用极少。
除前述两篇文章外,吴丰培发表在《禹贡》半月刊上的文章还有《西藏图籍录拾遗》、《记清光绪三十一年巴塘之乱》、《〈抚远大将军奏议〉跋》(以上三篇发表在第6卷第12期)、《〈西域见闻录〉跋》。后应《中德学志》之约,写成《达赖出亡事迹考》、《西藏志版本同异考》等文。并在北平研究院出版的《史学集刊》中发表两篇文章(《卫藏通志著者考》与《〈西行日记〉跋》,分别发表在第1期与第2期上)。吴丰培涉入边疆史地以西藏始,因家中所藏多为西藏资料,便于整理研究,后又负责《绥远通志》中“地理沿革”和“艺文”两部分的撰写,又在《大公报》和《北平晨报》发表一些文章。
1949年以后,吴丰培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继续从事边疆史地研究。因治史者“详于内政,忽略边务……使许多重要史料埋没无闻”[20]59,1984年他将早年出版的《清代筹藏奏疏》再加以整理,出版了《清代藏事奏疏》,收录了英善、福宁、琦善等驻藏大臣及清廷重臣共计47人关于西藏的奏疏。此书经历了近六十年的收集、十余年的整理,可以说,吴丰培的大部分心血花费在了此书上。除此之外,仍有《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景纹驻藏奏稿》、《西藏奏疏》等。
在整理西藏文献上,按编年体出版了《清实录藏族史料》、《清代藏事辑要》、《清代藏事辑要续编》,按纪传体出版了《清代驻藏大臣传略》、《有泰驻藏日记》。整理的方志有《藏记概》、《西召图略》、《卫藏通志》、《卫藏图识》、《西藏志》、《拉萨厅志》等,大部分收入《中国民族史地资料丛刊》。1995年,吴丰培又主编了《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共116册,21函,约千万字,收录了《金川草》、《边藏风土记》、《藏征录》、《清光绪朝布鲁克巴密档》等“前人从未发现的稿本”,价值极高。
吴丰培注重对进藏游记的整理和出版,“昔人每病藏地著作难得而又分散,今汇辑成书,庶免獭祭之繁,而可收逢源之妙”[21]112。对于西藏及其周边地区而言,游记中关于民族的记载有一定价值,也可以反映出道路交通的变化,对研究历史地理有着极大作用。因此,他编印了《川藏游踪汇编》,收录28种书,字数达30余万。并在整理同时进行研究:“考昔年入藏之途,厥分为五:一曰四川,一曰西宁,一曰云南,一曰新疆,一曰国外印度。清代官吏,习以为川康大道为进藏要途,故记自川者为多,因以名篇,陵谷有所变迁,交通亦有改道,今汇编此类书籍,使五路进藏之途,均可遍得,不仅秘籍得传,亦可供民族史地研究者之参考。”吴丰培注重地理之研究,对进藏的日记有着自己的看法,这些资料的出版可谓嘉惠学林。
与《川藏游踪汇编》相似,吴丰培继续汇编了西北地区的游记,名为《甘新游踪汇编》,共33种文献。他将这些文献分为五类:一是清廷用兵于新疆,随军而往者,此类“多记其山川,详其程站”;二是前往新疆任职者,此类偏好“访古志异”;三是边疆勘界者,此类多有勘界记录;四是获罪遣戍者,此类详载“行程之往返,舆地之要塞”;五是陶保廉等非官非罪之人,记载了“山川关隘之险事,道路之分歧,地理之沿革,风土之特殊”。吴丰培认为新疆舆地之作,首推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和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二者“稽考精湛”,为“不可多得之佳作”[22]184。他编此类材料是为了“供史地学者所需”,《甘新游踪汇编》第一篇即为《甘肃至新疆路程》,并附录了《库车琐记》中哈密至库车的路程。可见,在吴丰培的认识中,研究地理首要研究交通,尤其是边疆地区,交通是重中之重,不仅为历史地理研究之用,于当今进疆道路开拓也有很大裨益。
在新疆方面,主要搜集、整理了清代大臣关于新疆的奏疏,包括武隆、扎隆、中福等二十余人,编入《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除此之外,还整理了《西征录》、《西域图志》、《哈密志》、《新疆图志》等二十余种文献,对研究新疆地区的历史地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吴丰培还进行着内蒙古、云南、四川等地文献的搜集整理,如《清季蒙古史料汇粹》收集罕见地志三种(《定边纪略》、《库伦志》、《乌里雅苏台志略》),奏稿一种(《三多库伦奏稿》),游记三种《奉使喀尔喀纪程》、《朔漠纪程》、《游蒙日记》)。《科布多史料辑存》收集四种重要罕见史料。云南方面,整理了《鄂尔泰奏疏》、《金川草》等,《金川草》为其父吴燕绍中年所得孤本,极具研究价值。又整理了1940年边政设计委员会所编《川康边政资料辑要》,包含29个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为一手资料,价值颇大。
20世纪80年代,吴丰培即注意到丝绸之路的研究,所编《丝绸之路资料汇钞》与《丝绸之路资料汇钞增补》收录了从汉代《出关记》到明代《西域诸国》等28种文献,分别于1984年、1993年由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影印出版。后又整理了《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收集了清代“赴新记程之作”,含38种文献,1995年出版。吴丰培认为清代的部分价值较高,主要包含三类:“一为赴新履任官员所记,乃极少数。二为查勘边界,记山川险要,是国防要著,极可珍视。三为文人墨客,因被罪而遣戍新疆……由于此类人氏,知识渊博,考古论今,并记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考古等方面的情况,其作品应列为上品。”[23]182-183这也是清代新疆问题凸显的背景下所涌现的珍贵资料。在当前“一带一路”学术热点形成的背景下,这些资料是研究该时期军事地理、政治地理、民族地理的极好材料。
在目录学方面,吴丰培整理了《明代倭寇史籍志目》、《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年谱目录》、《古籍版本题记索引》等。
除以上工作外,吴丰培还担任《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审稿人,并参与编绘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其中历代西北图幅由冯家昇主持,吴丰培受邀“担任宋代及明代西北图二幅,撰写《明代西北区图幅说明书》一册”[5]364-365,“虽非最后之定稿,亦不无有一得之见”[24]277。如在明代有关卫所的讨论中,他持与岑仲勉《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东四卫考》所考方位不同的看法,为地图编绘做了不少工作。
吴丰培认为,编丛编类、汇编类的书具有博采、罕见、辑佚、校勘、存真五大作用。纵观他的成果,不禁让我们感到文献对研究所起的重大作用。吴丰培称此类工作是“为他人做嫁妆”,但“倘若你也不做, 他也不重视, 那么边疆史地研究何以发展呢? ”[25]227纵览他“述其内容、考其版本,论其著者”[26]484的题跋可知,学术研究不能急功近利,要如扫雷一般向前推进,不能遗漏任何一点可以出现错误的地方。
(二)边疆史地研究的心境
吴丰培在对边疆史地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上,处处包含着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并且在此过程中,只要有利于学术发展,就极力促进相关资料的出版,供学界享用,没有任何私心。他说:“有清二百年来,驻藏者均属满人,且大都庸碌之辈……藏地民情,素不关心。……只见其挟英以要藏,未闻挟藏以拒英。……当时在藏统治者之无能,汉藏之失睦,竟开门而揖盗。藏政不修,而深责藏员顽固不化,岂成定论。……余辑藏牍,而深慨于清廷无能矣。”[27]73吴丰培对有损国家利益的行为给予有力回击:“近观外人黎吉生所写《西藏简史》,竟无视历史之真实情况,将两地关系,写成各自独立之区,将唐代与吐蕃友好往来,避而不谈,其用意不外以冲淡两地历史之关系,其居心险恶,显而易见。今得此篇,因而恢复历史本来之面目,更足以击破其妄图。”[28]98吴丰培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
正因如此,吴丰培是一个坚定地反对“藏独”的学者。早在1942年的《中德学志》上吴丰培就发表了《达赖喇嘛出亡事迹考》。20世纪50年代末,吴丰培发表了《关于达赖喇嘛的封号、地位、职权等的考证》,从达赖喇嘛封号的由来,清代历任皇帝对达赖班禅的支持、对其职权的规定,达赖喇嘛的转世、坐床及册封等方面,客观公正地论述了清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管辖关系;以大量明清宫廷实录等资料,论证了由于清初中央政府在政治上的支持、在经济上的资助,达赖喇嘛才有了当时的地位。吴丰培的研究向世人再次证明:西藏自13世纪以来受历代中央政府的管辖、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史实,有力地驳斥了分裂主义分子的谬论, 充分展现了他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25]225
在整理内蒙古文献时,吴丰培对中俄之间的不平等交易更是感慨万千:“考外蒙古原属我国领土之一部分,非独史籍详其原委,而同时也为世界所公认。痛乎民国伊始,军阀割据,兵戎相见,内乱不已,中央官吏无不争权夺利,置国家于不顾,遑论边疆,任凭帝国主义瓜分。……何致仅留此旧史为我辈叹息。”[29]243此类惋惜与痛恨常出现在他的题跋中,不愧为一位有血有肉的知识分子。
吴丰培在整理文献和研究过程中,“并非将己藏之珍籍视为私产,藏诸深阁秘不示人,而是乐于提供学人利用,更尽心尽力印刷出版,广为流传,以此为乐”[26]484。如当其听闻重庆图书馆藏刘赞廷所编数百万字的《川边西藏资料》为罕见古籍时,便建议该馆复印成80余册,使其广为流传,造福学术。他藏有楚明善《兴龙山》一书,“今榆中县发展旅游事业,闻知余藏此书,已至急欲复制,何意此册竟可为今日开发大西北服务,焉敢秘藏”[30]226。针对档案馆将档案秘不示人的现象,他建议“执政者采取宽严相济之法,使旧档发挥作用”,并称“余所辑之各种奏稿,亦求其不为断烂朝报,能供史地研究原始资料,数十年来,孜孜于此”[31]239。学术为天下之公器,许多珍稀资料应当为研究者所分享此亦为今人所鉴。从民国时期自费出版《边疆丛书》之后,不断出版相关稀见资料汇编,多达千万字,只要“于边疆研究有一得之功,则感到无上幸慰”[32]241,无不体现着吴丰培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和大公无私。
四、结 语
吴丰培与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早年参加禹贡学会,做了大量工作。在抗战时期,保存了禹贡学会的火种,使其得到延续,为禹贡学会作了重要贡献。从1936年发表第一篇关于边疆史地的文章《西藏图籍录》后,直到1996年逝世,吴丰培始终进行着边疆史地③研究,且“一生以保存秘籍并供学人使用为己一大快事”[26]484。
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吴丰培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广泛搜集古今中外图书资料、从事专门研究及实地调查、扩大研究范围、扩大史地资料的刊行、培养接班人。每一点建议对现在都是有很大用处。比如让图书馆对其珍藏古籍微缩影印出版,重点影印宋元以来一些史料价值较高的稀有版本、稿本或抄本、各省省志和部分重要的工具书[33]310-313。研究史地要重视实地调查,还要“绘制精细地图”;要重视对国外的研究,而且“要使每个青年必须掌握二门外语,同时对古汉语亦应督促自习”,多进行学术交流,“对此专业有研究者,请作学术报告,每年一二次,并在本组织内展开各门研究的报告会,每季一二次,其成绩可作为考评的依据之一”[34]9-10。吴丰培对学术研究的计划细化到如此地步,真是用心颇深,亦应为当代学者所思考和学习。
吴丰培整理的边疆史地文献达数千万字,这洋洋大观的成果还仅只限于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西部地区,毋言其他地区。吴丰培搜集、整理、出版的文献对历史地理学研究作用极大,尤其是边疆历史地理,“这些史料对边疆研究颇有参考价值”,甚至可以“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统一”[35]384。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当学习吴丰培的精神;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当铭记吴丰培的贡献。
注释:
①知之:《兀兀穷年,壮志不已——记边疆研究者吴丰培教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年第3期。边师:《硕果累累的边疆研究者吴丰培先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2期。曾国庆:《论吴丰培先生对藏学的贡献》,《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
②关于吴丰培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开始工作的时间,吴丰培在《吴丰培边事题跋集·自序》中说是1935年,在《吴丰培自述中》一文中说是1936年。根据他在《禹贡》半月刊发表的第二篇关于西藏文献的文章看,工作的时间应在1935年。
③边疆史地是否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这是一个学科定义及其属性鉴别的问题。在20世纪末,一些学者开始主张建立边疆学,尤以马大正为代表,依其之见,“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马大正:《略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周伟洲认为:“正式将传统的‘边疆史地’更名为‘边疆学’的时机已基本成熟。即是研究单位及刊物名称(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和其主办的刊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应将‘史地’两字去掉。”(周伟洲:《世纪之交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看来边疆学并不等同于边疆史地,“史地”也不完全属于边疆学研究的内容。周伟洲在《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第2页)一文中论述20世纪30—40年代出现的有关边疆的学术团体及其所办刊物中,并未提及禹贡学会,很可能是他并不认为禹贡学会属于研究边疆的学术团体。马大正《二十世纪的边疆史地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一文认为,禹贡学会是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代表。在创刊之初,《禹贡》以“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为目”,后来扩大至边疆史地研究。但以“边政学—边疆学”的学术发展脉络来看,虽然《禹贡》“第1至6卷所刊发的学术论文与边疆史地有关的几近半数”(马大正:《略论禹贡学会的学术组织工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但“边疆学”与“边疆史地”是有差异的,不能将其视为边疆学杂志,且当时已经涌现了很多专门研究边疆的杂志。对此,李绍明对此有过很好的回答,他认为最早的边疆研究,即晚清边疆研究,如果从学科门类来看,“属于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这样一个范畴”,以《禹贡》为代表的“民国早期的边疆研究和地理学的关系很密切,这里不仅有中国传统的历史地理学,还有西方的人文地理学”。因此,张原总结道:“民国早期的边疆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种是国内的史学家出于解决边疆危机的目的来进行的带有历史地理色彩的研究,另一种是国外传教士出于在边疆地区传教的目的进行的具有社会学色彩的研究。”(王利平,等:《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边疆和边政研究——李绍明先生访谈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2期)以当时发表的边疆史地的文章来看,在内容上多为自然地理概况、地理沿革、考察报告、游记等,应属历史地理学研究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