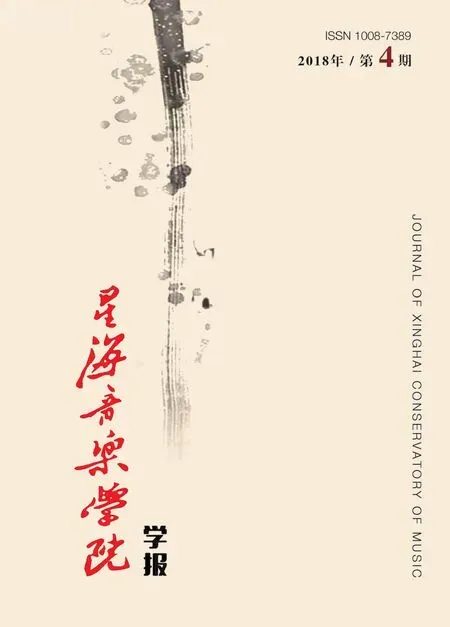赋格:理性结构与感性表达
孙志鸿
引 言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目前的西方文明是第三代文明,继承了早先的文明,古典遗产包括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文和基督教”*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4页。。由此可以看出,理性思维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石。理性思维源于古希腊,并在文艺复兴以后成为推动西方科学、艺术、宗教发展的主要动力。正是在理性思维的驱使下,西方音乐才从单音到复音,从简单到复杂,产生了许多伟大的音乐作品,成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理性音乐结构(理性结构英文为rational structure或Meaniningful form)是指理性思维为主导构建的音乐作品,它体现了符合组织逻辑的音乐结构生成过程中理性思维的主导性,与偶然音乐或者即兴音乐不同,后者是以感性思维为主导的音乐结构生成过程。当然,任何已被类型化的音乐结构多少都具有理性思维特征,如再现三部曲式、回旋奏鸣曲式等,但是在这些类型化音乐结构的生成过程中,其微观组织逻辑则表现出更多的感性思维特征,如动人的旋律,以及新奇的和声进行等个性化的技术细节,是独特个人风格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本文中的理性音乐结构,当然并不排斥感性思维在音乐结构生成过程中的作用,但它不是主导性的,它只在音乐结构中起着装饰或从属的作用。
由对位技术构筑而成的赋格,在总体结构和音乐结构具体生成过程中的组织逻辑方面,表现出理性思维占主导的特性。正如20世纪初对位法大师杜布瓦所指出的:“赋格绝不是一种着重于灵感性的创作,它主要是一种写作艺术及逻辑发展达到最高阶段的音乐作品。”[注][法]杜布瓦:《对位与赋格教程》,廖宝生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年,第1页。“灵感性的创作”指的就是感性思维为基础的创作,而“写作艺术及逻辑发展达到最高阶段”指的则是理性思维为基础的创作。由此可见,杜布瓦也没有排斥赋格中的感性思维,而是将理性思维作为赋格创作的主导因素。
除此之外,中央音乐学院杨儒怀教授也曾对赋格的艺术特征做过一段精辟的概括,他说:
这里(指在赋格这种形式中——笔者注),富有幻想的即兴创作以及出自灵感的任意发挥并不重要,也不能起太大作用,相反的,创作的技巧则更多地表现在逻辑性艺术的设计、灵活丰富的复调思维及乐曲整体的艺术构思上面。因此,与其说赋格是灵感式的自然流露,不如说它是高度艺术思维理智化的结晶。仅此而言,她是任何一种音乐创作,尤其是大型奏鸣曲、交响乐等体裁的创作不可缺少的在理性思维方面进行锻炼的绝好形式。[注]杨儒怀:《音乐的分析与创作》,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第604页。
杨儒怀先生同样在不否定感性思维(富有幻想的即兴创作与灵感式的自然流露)的前提下,强调了理性思维(高度艺术思维理智化)在赋格中的主导作用。杜布瓦和杨儒怀的共同之处在肯定赋格中理性思维特征的同时,并不排斥赋格中感性思维的作用。
一、赋格发展历史鸟瞰
作为作曲技巧之一和赋格的基本构建技术,模仿技术的大量运用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狩猎歌中。模仿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作曲技术,它使得作品中的音乐材料趋向精简和统一,是作曲技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音乐的表现需求进一步丰富的结果。不同音程的模仿,除了能保持不同声部的材料一致性外,还产生了由于音级或调式调性变化而带来的新的色彩和音响效果。而四度、五度音程的模仿,由于色彩性和功能性兼具,因而逐渐被作曲家固定下来,作为材料或主题的主要陈述和发展手法,并逐渐被这一时期的作曲家所喜用,甚至在创作中运用模仿手法构成整部作品,即through imitative style[注]陈铭志:《赋格学新论》,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1页。。这些基于模仿的创作实践汇集成赋格的源头,代表作曲家有约斯坎、帕勒斯特里那、迪费等。
巴洛克早期阶段的赋格或与赋格相近的其他复调音乐形式,在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创作实践中常用的四度、五度模仿技术基础上,逐渐定型为以模仿技术为主的音乐结构。但是,这一阶段的赋格,在主题的个性化方面还不突出,间插段还未成型,主题的发展手法也较为单调,调性的发展也仅限于近关系调范围之内。到了巴洛克中晚期,巴赫以其惊人的创造力,吸收当时诸位大师的赋格写作技术,创新性地将赋格发展到了完美的艺术境地。他创立了依据调性构建赋格的基本原则,通过高度个性化的主题,表现出丰富的情感世界。而同时期的另一位巴洛克巨擘亨德尔也在创作中大量运用赋格,他的赋格虽不及巴赫的赋格严谨精致,但是却赋予赋格以丰富的戏剧表现功能。
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是赋格发展的平稳时期。赋格经由巴赫和亨德尔等人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最成熟的理性音乐形式,这种源自理性精神,并经由理性思维所构建的复调结构在新的时代中与古典主义最重要的精神——启蒙主义思想相结合,产生了许多在艺术上极其美妙且在思想上非常伟大的赋格作品。可以说,赋格不再仅仅作为独立结构和体裁形式出现,更重要的是它融入到交响套曲结构中,甚至融入到表现时代精神的奏鸣曲式中,作为套曲中的独立乐章或者独立乐章的一部分,在表现的广度和深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具体的创作技术上,如赋格主题的不稳定性、主题内的和声内涵更加丰富、调性的迅速转换、通过调性获得乐曲发展的动力和不稳定性、向远关系调性的拓展、建立在扩展调性基础上的半音化和声、主调织体结构的渗入等等,无一不体现着时代性对赋格结构的影响。在具体的表现上,赋格不再局限于论证性的表现特性,融合其他结构原则的赋格,在表现矛盾冲突、戏剧性、群众场面、画面性、哲理性思索等方面更为突出。
浪漫主义的作曲家们在赋格的创作中却没有能够将前辈的成就进行发展,推向新的阶段。他们谨慎地在前辈大师巨大的阴影中前行,表现个性解放的自我意识。在赋格的功用方面,除了继续将赋格与其他音乐形式相融合,以拓展其表现力,如将赋格运用在戏剧性作品和交响乐中等。在赋格的语言和结构方面,结合和声技术的发展,在声部进行上多强调半音化的线性装饰以及主调织体的渗透,使得赋格在音响上产生了新的色彩和紧张度,以表现新的情感世界或描绘戏剧场景。总而言之,浪漫主义思潮对赋格最主要的影响,就是不再把赋格当成一种纯粹的复调形式,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具有表现力的通用化作曲技巧来运用。
赋格在20世纪的发展是全方位的,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大大超越前期。独立的复调套曲形式自不必说,赋格被理解为可以用更多样化的形态来呈现高度组织化的超越传统调性的音响结构,这得益于新的调性思维的发展以及主题概念的扩展。除此之外,赋格还广泛应用于以交响乐为主导的大型套曲中,或者作为独立乐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许作曲家意识到了赋格比其他的音乐形式更适合用在交响套曲终曲中。
在具体技术层面,除了主题概念的扩展所造成的主题形态以及陈述方式的多样化之外,作曲家基本遵循了赋格的基本结构原则:分声部陈述主题;非主题段落与主题段落的交替;主题展开变化如紧接、倒影、逆行等传统手法以及调式变奏、装饰加花、结构截段等新的手法;有明显的再现段落等等。这比19世纪音乐理论家戈达尔格[注]戈达尔格(Andre Gedalge,1856—1926),法国作曲家和音乐教师。他提出了赋格的基本结构成份:主题和答题;一个或更多的对题;呈示部和副呈示部;间插段和紧接段;持续音等。详见:Walker,Paul Marks,Fugue In German Theory From Dressler To Mattheson,Stats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Ph.D。的赋格概念宽泛了不少。
二、作为理性结构的赋格
赋格是理性思维主导下生成的理性音乐结构,理性思维伴随着赋格的历史演变,体现在赋格写作中的如下几个方面中。
(一)预设性与规程化
从写作程序上看,预设性与规程化是赋格最重要的创作特征,是赋格理性精神的最直接的体现。在一般的音乐创作中,曲式结构的生成过程就是创作的原始过程,音乐结构与创作的程序是基本吻合的。而赋格则不然,学院派的赋格不是按照赋格的结构进程来进行创作的,它具有复杂的规程化特征以及鲜明的预设性特征。所谓规程化,就是音乐写作中被规定的固定化程式;所谓预设性,就是在音乐创作过程中,先写好某一些片段,然后组装到整体音乐结构中。如在赋格写作中,固定对题、不同条件的紧接段甚至是间插段等结构片段都是预先写出的:先通过纵横可动对位技术完成各种不同条件的紧接段,之后将主题进行八度或者十二度纵向对位,写作其他对位声部用作固定对题。间插段则是综合性的,不同结构部位的间插段往往以一个间插段为基础进行复调变奏而形成。预设性使得赋格成为一种堆积木的游戏或者音响的建筑物,从而大大降低了感性思维在赋格中的作用。
(二)对位技术的理性化
作为赋格的基本写作技术——对位法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制定了严格的音乐规则,并按照经院学派的精神,将音乐创作视作一种理性的成果,更甚于想象和感性的产物”[注][法]保·朗多尔米:《西方音乐史》,朱少坤、周薇等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年,第8页。。对位法按照既定的规则处理音和音的关系,使多声部协调地结合在一起时,作曲家首先要遵循这些既定的规则,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化的修饰,使其从普通的对位结构跃迁为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作品。当然,在富有经验的作曲家的赋格创作中,对位规则的遵守与艺术美的追求是合二为一的,有时甚至已经内化为作曲家中的潜意识。
除此之外,中央音乐学院姚亚平教授也曾指出:“在以单个音为思维的最小单位的对位写作中,作曲者是小心谨慎地调遣每一个音,深思熟虑地玩味每一个音,他不能忽视任何一个细节,他必须顾及到上下左右的乐音的相邻关系”[注]姚亚平:《西方音乐历史发展中的二元冲突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1995年,第33页。。姚亚平教授的以上论断将对位技术的理性化思维特征作了生动的阐释。在赋格所依赖的各种对位技术中,纵向可动对位技术是包含了数理思维的以声部转换为基础的变奏和发展技术,而横向可动对位则改变了声部结合的横向时间关系,其写作往往在严苛的规则约束下才能完成;倒影对位则更具数理思维特性的变奏发展技术,不同倒影音轴的运用使得倒影后的旋律具有不同的效果;逆行对位虽然原型与变型之间变化较大,但是同倒影对位一样是基于数理思维基础的对称性变奏手法,只不过前者是横向对称,后者是纵向对称。
(三)主题因素与非主题因素的对立与统一
在赋格中,主题陈述段落和非主题陈述段落彼此之间既互相肯定又互相否定,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完成赋格的结构生成过程,是主题因素与非主题因素辩证统一的发展过程。早期的赋格是没有间插段的,间插段在赋格演进中的成熟运用标志着以对立统一为曲式构筑原则的赋格的真正成熟。主题陈述段落与非主题陈述段落的有机交替,共同完成了赋格主题的论证过程和赋格结构的生成。主题陈述段落虽然也通过主题形态、调性以及和声的变化形成发展的推动力,但是,间插段则更加强调不稳定状态的呈现。在间插段中,我们会看到更宽的调域和更频繁的调性变化、模进等展开性写法,这些写法的运用与主题陈述段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着赋格的发展阶段和不稳定状态。主题陈述段落与间插段之间除了对立的方面之外,还有统一的方面:两者的统一多是通过材料上的同一性获得密切联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涵状态。
(四)理性化的主题设计与主题的理性化发展
赋格主题是理性化设计的结果。较之其他音乐形式的主题,赋格主题更加凝练和格言化,更加注重自身的逻辑化构成。一是主题的调性结构必须得到明确而充分的揭示,作曲家必须在开始处即通过特定的旋律进行来明确主题调性结构,即使是转调的主题,新调和原调一样必须同样清晰明确。二是主题的音高材料也呈现出高度逻辑化特征,由动机材料发展的主题自不必说,即便是由对比材料构成的主题,其内部结构的逻辑性必须清晰可辨。那些诸如格列高利圣咏式的感性化旋律,是较难在赋格中作为主题而存在的,原因是缺乏结构生成的逻辑性。
赋格是主题高度理性化的变化过程,主题的发展和变化手法也具有多样性和高度逻辑化特征。在单一主题的赋格中,主题依靠强大的变化发展能力,无所不在地充斥在赋格的每一个角落,完成了论证式的结构过程。如在呈示部中,主题一般只进行调性的初步发展和音色音区的变化。在展开部中,主题则以强调调式色彩的对比为主,结合调性的深度发展、主题形态的变化(如倒影、装饰性加花、紧接进入、主题截段等等)以及间插段的运用,体现出音乐性格的不稳定状态。在再现部中,主要是主题形态、调性、音色等因素的回归或再现。此时,调性的稳定上升为美学意义的通过反复论证而将问题获得完满的解决,这与诸如奏鸣曲式中通过矛盾冲突获得解决虽然途径不同,但最终的归宿是相同的,这些进入到稳定状态的解决获得了宗教意义的升华。由此可以看出,赋格的主题发展呈现出高度逻辑化的单极结构的自足过程。需要指出的是,多主题赋格中也有鲜明的对比,但这些多主题赋格的对比方式是受奏鸣曲式影响的,不是赋格本身所固有的基本特征。
三、理性结构的感性表达
如前所述,作为理性结构的赋格,并不排斥感性思维在音响结构中的作用,相反,感性思维在赋格中起着重要的表情性作用。如果说理性思维构筑了赋格的背景和中景结构,形成了完满自足的论证化的曲式过程,那么说,感性思维则成为赋格独特风格和个性化的源泉:赋格的一些最动人、最美丽的细节,往往是通过丰富的感性思维的表达才能获得的。
(一)感性思维是赋格个性化表达和多风格呈现的内在动力
在赋格结构定型并逐渐趋向成熟之后,一些富有创造性的作曲家,为了避免赋格落入千人一面的窠臼中,在赋格写作的前景结构中,融入了独特的个性化语言,使赋格成为其个性化表达的重要手段。如同为德奥古典乐派作曲家,海顿在《f小调弦乐四重奏》末乐章中,将赋格运用于奏鸣套曲中,主题的精巧设计与严谨的对位结合,使得赋格结构宏大气派,如同被装饰了的宏伟建筑物一样,而装饰物则是多次不完整的主题进入以及形态各异的间插段等等;莫扎特《c小调柔板与赋格》中的赋格主题具有深沉的悲剧性格,多个不同条件的紧接段的运用强化了主题的悲剧性表达,从而使赋格成为表现作曲家内心悲剧气质的媒介。这两部几乎处于同一时代,在相同文化背景中生成的赋格作品差异性是感性思维在赋格创作中运用的结果——感性思维促使作曲家在遵守赋格前景结构和中景结构的同时,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形成了具有相同的艺术价值但却有不同的纹理和肌肤的艺术作品。
感性思维甚至将不同的民族风格和气质融入到赋格创作中。如20世纪美国作曲家哈里斯(Roy Harris,1898—1979)《第三交响曲》(1937)中的赋格段落,简洁的主题、对铜管音色的偏爱以及丰富多变的节奏语言,是美国音乐风格甚至是美国精神的自然流露。而肖斯塔科维奇《24首前奏曲与赋格》(1950—1951)中许多长线条的气息悠长的主题,其实就是源于俄罗斯民歌,可以说,这位作曲家的赋格在巴赫赋格的外形中跳动着俄罗斯的心脏。而20世纪南美作曲家罗梅罗(Romero)的弦乐队《赋格与帕哈里罗》(fugaconPajarillo,1951)则将感性表达发展到试图改变赋格理性结构的地步,作曲家在这部赋格中,多层次地融入了拉丁美洲的音乐风格。
(二)感性思维在赋格中的体现
一是主题。作为理性化、格言式的赋格主题自巴赫以后,常被富有创新思维的作曲家作为感性表达的突破口,在音高材料、发展技术、外部旋律和节奏形态、陈述方式以及音色特征等,注入个性化的表达。如与贝多芬同年出生的波西米亚作曲家雷哈(Reicha, Antoine,1770—1836)《36首赋格曲》(1801)第28首赋格的主题即以混合节拍构成,体现了在节拍思维方面的扩展。在20世纪赋格的主题中,个性化的感性表达表现地更加鲜明,如美国作曲家霍夫哈尼兹(Alan Hovhaness,1911—2000)《哈利路亚与赋格》(AlleluiaandFugue,Op.40b)则是刻意以圣咏作为赋格主题;而卢托斯拉夫斯基《前奏曲与赋格》(1973)中的六个主题都是有控制的偶然手法形成的无节奏与支声式织体的结合;等等。
二是赋格中间部分的写作程序。在感性思维的驱动下,赋格中部的调域(相对于呈示部)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调性关系趋于复杂化,主题的变化方式也更多样化,不稳定的间插段甚至插部在赋格中部占据了重要位置,强烈地改变了赋格的气质和内涵。如李斯特《bB调前奏曲与赋格》的赋格乐章中部,甚至引入了对比性较强的插部;在英国20世纪作曲家布里顿《第三大提琴组曲》第六乐章赋格中部,将小调性的赋格主题变化为全音阶形式,从而使主题获得了新的音响色彩;等等。
三是感性表达形成了赋格的不稳定特性或个性化特征,而基于程序化写作和背景结构理性思维,形成了赋格的稳定特性。若赋格中感性表达多于理性思维,那么赋格本身所具有的传统意义的稳定结构特征会降低直至丧失。在卢托斯拉夫斯基的《前奏曲与赋格》中,由于作曲观念和技术的变异,使得这部弦乐队复调套曲在外部形态上显示出较大的变异:在织体方面多是微复调音响层的结合,在纵向方面则是有控制的偶然结合,在音高材料方面是以自由无调性为基础并向音高细分方面扩展,等等。然而,这些外部特征的变化虽然动摇了传统赋格结构的稳定性,但是并没有改变赋格的基本结构特征:在外在无序自由的外衣下,仍然包裹着严谨的秩序化内核,体现着赋格所固有的理性结构思维特性。而在俄罗斯20世纪作曲家施尼特凯(Alfred Schnittke,1934—1998)《即兴曲与赋格》(ImprovisationandFugue,1965)中,通过另一种秩序法则——十二音序列的运用,削弱了赋格理性结构的稳定性:主题的变异性更强,主题形态更不稳定,声部关系更加模糊,大量的间插段削弱了主题的连贯性发展等等,由此使得感性表达所构成的不稳定的陈述结构远远强于理性思维所形成的稳定性结构,作为一种结构意义的赋格被推向了瓦解的边缘。
四、对赋格精神的思考
以理性思维为主导构建的赋格结构,折射着西方文明中的理性光芒,具有如下精神内涵和特性:
第一,赋格是通过理性思维构建的秩序性音响结构。通过严格的规程化和预设性写作,赋格的理性结构得以生成并获得了自体结构的完善和满足,这种自体结构的完善和满足有时仅通过观赏谱面就能获得,赋格经由演奏家的二度创作,产生了高度组织化的音响结构,使欣赏者引发了音乐与建筑结构的通感联系。如20世纪荷兰艺术大师埃舍尔(Escher)的许多版画作品,就体现了理性结构的音乐与绘画之间的一种同构关系。[注]莫里茨·科内利斯·埃舍尔(M·C·Escher,1898—1972),生于荷兰吕伐登,逝于荷兰拉伦。埃舍尔绘画与音乐同构的作品有《逆行卡农》《变型II》《蝴蝶》《天鹅》等,详见[美]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GEB:一条永恒的金带》,乐秀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而意大利作曲家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1866—1924)在看到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扉页上的哥特式大教堂后也写下了如下文字:“这座大教堂是赋格这座音乐的雄伟殿堂在建筑上的体现,赋格的确像一座复调音乐的教堂建筑,尽管里面有许多装饰成奇形怪状的滴水口,但总体轮廓绝不会因此而黯然失色。”[注][美]尼古拉斯·斯洛尼姆斯基:《韦氏新世界音乐词典》,吴江松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7年,第330页。
第二,赋格通过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与对比完成丰富的审美情感体验。感性思维在赋格中的运用,为赋格带来了不稳定和对比性段落,形成了赋格的个性化风格特征和结构的变异,而理性思维则恪守着赋格的写作规程和预设性,并通过对位技术的运用完成了既有秩序性又有表情性的音响结构的造型。
第三,赋格通过平等化的声部处理和优美结构的生成来表现理性精神世界。赋格主题虽然具有一定的表情和语义,但是当它被规程化地编织在赋格结构中的时候,它便成为了无意义的部分,而部分必须通过整体才能获得全部的存在意义。这正如瑞士著名的美学家和艺术史家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1864—1945)所说:“有美丽的细部调和为整体,而在整体中各部分细部继续自在呼吸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部分’已经服从了统治性的整体动机,而只有整体一起产生的效果才有意义和美”。[注]约普森:《对位法》,艺友出版社编辑组译,台北:艺友出版社,1986年,第12页。在赋格中,主题几乎在所有声部中遁走,并结合调性的逻辑发展以及对位法的运用完成了主题的反复论证,这个过程当然不同于史诗性的矛盾冲突与解决的大型音乐结构,在赋格中即使有对比和冲突因素的存在,这些因素也不起决定作用,它们和稳定性结构互相交替,像潮汐推动着海水形成规律性的浪潮那样完成赋格的反复论证,产生有意味的音响组织结构的纹理,表达着人类精神世界深处对理性光芒的无限渴望。
结 语
作为理性结构的赋格,在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的共同作用下,通过主题的反复论证,完成了自我充足的秩序化音响结构的构建过程,并使得审美者从有组织的音响结构中获得了精神的满足和愉悦,领悟到了秩序和法则在赋格中以美的形式的存在,并进入到形而上的精神世界中,这就是赋格这种有意味的理性结构形式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映射。
——论传统对位教学两种体系的冲突
——以利盖蒂的部分音乐作品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