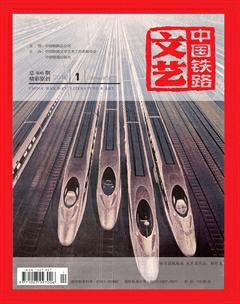乡村电影场
刘恩波
电影是生命中的盛宴。如果不提这盛宴,我们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注定会大打折扣、黯然失色,起码我是这么想的。这个世界有不喜欢看电影的人吗?如果有,肯定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们注定分属于不同的星球。
偶尔,琢磨古人的遗憾之处,觉得其中一项就是他们没看过电影。如果李白看过了,那气吞山河风卷残云的大全景推拉镜头会让他感到灵魂的洗礼和冲动吗?如果苏小小看过了,那欲语还休泪花闪烁的回眸特写,在她妩媚的视线里,该腾起怎样的生命烟云?……所以,我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光影多姿多彩的年代。
尤其小时候看电影,发生了许许多多有趣的事,值得分享追忆。
那时候,农村场院里不定期放映露天电影,两根竹竿撑起一块银幕,大人小孩忘情投入其中,随着放映机的嗤嗤转动,一段段贮存着人生故事内核和命运线条细节的胶片,演绎出迷人的心灵的底色与韵味,剪接出岁月的风华、精彩和苍凉。这咫尺之间的方寸之地,像一块大海绵,吸收着我们情感里的露珠般的感动。如今想来,早已逝去的露天电影盛宴,还在回忆的某个角落沉甸甸地闪光。
最早看的电影是《地雷战》还是《地道战》,记不太清了。我能回想起的情形是那天下雨。场地精湿,人们打着雨伞,或是披着雨布,妈妈抱着我,一个大号的雨衣遮挡着我们的身体,雨水顺着边缘流下,砸在地上,如密集纷乱的针脚。银幕上的鬼子进村扫荡,闹得鸡飞鹅跳,八路军士兵埋伏在掩体里,等待射击……
那时拷贝有限,邻村之间要交换着看。等拷贝,最长的等半宿,最短的也得半个多钟头。记得放映《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放到中间,拷贝还没到,全村的人都等着,后半夜才来,弟弟趴在妈妈怀里睡着了。那片子多吸引人啊,就像我们小时候揣在兜里的糖球,都舍不得吃。我看花果山,我看孙大圣,看妖怪的变身,每个瞬间,都舍不得放过,在脑海里印下记忆的模子。弟弟醒来,电影已接近尾声,师傅和徒弟又要上路了,那会儿,正值夏夜,不远处的天上有一颗流星滚过,晶莹的喜悦的泪花,在我眼角深处荡漾。弟弟却不干了,嚷着,说怎么不叫醒我!
儿时,盼电影就跟盼过年一样。有时候赶上农耕季节,或是片儿荒,大人们还熬得住,我们小孩子就迫不及待了,许多天盼星星盼月亮也盼不来电影。怎么办呢?于是有的大一点的孩子就开始学会撒谎。我二姑家的表哥就曾经煞有介事地跑着到我家,兴冲冲告诉我,你快准备一下,今天晚上演《战斗里成长》!我一下子乐颠儿了,赶紧拿起小板凳,就想往外冲。谁想表哥挡住了路,说,你还当真了,我逗你玩呢!
一来二去,不演电影的时候,我也开始拿更小的小孩开涮。譬如,我会哄着我弟弟,告诉他哪天晚上演电影。他眼睛闪着光彩,会兴奋地问我,啥名?我说,白跑战斗磨鞋底。以后,我弟弟也跟着学会撒谎了。就对隔壁的小女孩说,要演电影了,名字叫战(站)地看蓝天。没等说完,自己先嘻嘻笑了。
那会儿,农村常常停电。赶上放电影,如果停电,多扫兴的事!别说,我就遇到过多次这样的事,电影演到半截,忽然银幕上焦糊一片,接着断电了。黑压压的人群开始闹哄哄起来。大人们这时有说有笑的,扯起了家长里短,其乐也融融。小孩一开始不适应,直起哄,慢慢变乖了,有的拿手电筒往銀幕上照,有的在人群里钻来钻去,玩藏猫猫。其实,趁着黑下来的瞬间,搞恋爱的哥哥姐姐们有节目了。我就看见过一对儿偷偷亲嘴呢。我一叫,他们就不亲了,还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那会儿,我有点腼腆,还有点小淘气。偶尔,也帮助哥哥姐姐们递个字条啥的。乡里乡亲的,尽管不沾亲带故,可从小在一块厮混熟了,人家求你跑个腿儿,不想答应都不行。那样的活儿,停电时没少干。有时候,我还故意把字条送错人,让他们闹个脸红脖子粗,自己私下里偷着乐。而为了传个口信儿,打火机、火柴、手电筒都派上了用场,一时间在乡村场院的角落里,它们就像萤火虫一样,不断闪烁着那梦境般的光泽。直到今天,想起来,我还觉得停电的片刻,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剧情转换,对于寂寞的乡村来说,简直称得上光影之外的一种神奇的补偿。
偌大的乡村场院,本身就像一座迷人的梦工厂,当时那里停摆着马车、四轮拖拉机、拖车的车斗,还有各式各样的农具,赶上收获时节,谷穗、玉米穗、高粱秸、大豆等品类齐全的作物整整齐齐堆放着,散发出秋天饱满成熟的气息。而那两根直挺挺矗立在场院正中央的竹竿,被固定的绳索拉着,牵动着随时挂起来的幕布,成为上演生活之外另一种梦境的物质载体和符号。
一般开演之前,三三两两的观众拿着板凳、折叠椅、报纸、坐垫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带,大大方方选择好自己喜欢的角落,坐下来等候。也有的站到远一点的地方抽根烟,提提神。不久放映员开始把光线投射到银幕上尝试着对比光感、光圈和焦距,这时候孩子们难耐住心里面的幸福、期待和热情,大呼小叫地把手里的物件往光线上抛,一瞬间帽子、手绢、手套、鞋子满场飞动……银幕上涌现着欢乐的造型线条,此起彼伏。也有些情不自禁的大人们赶着凑热闹,他们用丰富的手的表情做出兔子、狗、牛、小老鼠的样子,极大提高了整个乡村电影节日的活跃指数和幸福指数。再接着,某些农具出场了,譬如锄头、镰刀、镐头等物件透过光线定格在闪亮一片的银幕上,显露着农人们沉浸于生命细节享受的喜悦与快活。当年有一阵学习小靳庄,每个生产大队都组织了宣传队,宣传队底下设有业余合唱团。至今我还依稀记得有些日子演电影前,合唱团会唱歌练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学习雷锋好榜样》等革命歌曲,那饱满的激昂的曲调,透过夜空,在偌大的乡村场院里回荡着共鸣着。
对比现在,城市里电影院的规整典雅甚至豪华,我们乡村电影场的原始粗糙落后好像无法与之比较。但是,我心里会说,我更热爱当年看电影的滋味和感觉。那种质朴的,沉迷的,无忧无虑的,天真而烂漫的味道,已经久违了。无法复制,也无法再造。不仅仅是露天的问题。后来城市里不也在某些公园或者社区兴起了露天电影的放映方式吗?我去过,却无法找回从前的记忆和梦。真的找不回。失去的是什么呢?
也许是年代感吧,也许是童年的情怀,还有最初的,永远逝去的渴望。endprint
没有贫瘠和匮乏,就没有对物质的无比憧憬、追求以及对精神世界的盼念和神往。
当年的乡村电影,是匮乏年月最美丽的心灵交汇和聚餐,久而久之,像一种民俗的洗礼,像一种生命仪式的接替和安放。
只要我们走进那个场,乡村的电影场,那么我们的爱恨情仇悲欢喜怒苦辣酸甜就有了释放承载的空间。
现今坐在城市电影院的包间或者雅座里,你很难领略大地、天空、星星的含义,你很难走进五谷杂粮的气息深处,感触那风的自由,雨水的清凉滋润,雪花的漫天飞舞,甚至一堵老墙、一扇老窗经过岁月磨砺、改造与装扮的颜色。而电影,乡村的露天场,就有着这种得天独厚的赐予和馈赠,触碰和激发。
就说看吧,看的样态和姿态,其实是不一样的。那里面大概应对、契合、印证着某些可以穿透个性群体之间深层次纽带关系的文化遗留与基因。
说小时候看电影,是农家乐,是乡野的狂欢节,一点都不过分。你想,就以大人小孩投入其中的那个看的身形表情姿势而言,我会想起一句古话,叫粗头乱服不掩国色。在这里,礼数相对弱化了,体面也变得超乎日常,而嬉戏神游消遣的野性成分占了上风。欣赏艺术,非得那么规规矩矩峨冠博带道貌岸然吗?咱乡野里的习惯约定俗成的是,男人们热天是可以光着膀子看,小孩背心裤衩足矣,女人们穿个趿拉板儿就上阵了,甚或有年轻的妈妈在电影场上奶孩子也不着意回避,因为大自然环境下的公众娱乐,解放了人的天性。要知道,那会儿月牙初现,要么就是星光满天,长庚北斗牵牛织女,如同环绕的花环众星捧月,而稻谷的飘香迎着晚风朝这边吹送,美着呢!怡人心怀啊!
在乡村电影场里,我看见过许许多多大人小孩骑着墙头看电影,趴在玉米秸上看,仰八叉倒在车斗里看,甚至是爬到树上看,或是坐到银幕背面看,那呈现的效果注定是一个角度一个样。人们用新奇刺激过瘾的方式来占据观影的制高点抑或幸福感。渴望着电影,不可思议的爱,贪,同时也成全了我们童年的口味和向往,有时候天真无邪的孩子甚至模仿那电影里的动作和情节,来给自己贫瘠的生活填充点颜色。
我记得我曾经带着邻家的小孩拿着红缨枪、烧火棍、柳树枝等一干物件,模仿斗地主或者玩儿鬼子进村的游戏。对了,还有学《上甘岭》里志愿军在防空洞中听女文工团员唱“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情景。
《闪闪的红星》看过不久,我们就温习着里面斗胡汉三的镜头,潘冬子和春伢子押解着胳膊被五花大绑的坏蛋上场的样儿,在那时的小伙伴们看来简直太酷了!怎么办?我们也想过过斗地主的瘾。不知谁从哪儿弄来个高帽筒(后来听说是用报纸和浆糊粘贴成的),戴在扮胡汉三的小朋友的头上,他还得弯着腰,低头认罪。被我们这些红孩子斗来斗去,大家喊着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究竟是不是这句,我的记忆有点打盹——也许那年头我们在现场看多了对四类分子的批斗会,那高音喇叭里传来的声嘶力竭的叫喊,就定格在心里录了音。反正我们玩儿得高兴,顾不得是否跟电影中的剧情完全一致。弓背弯腰的小哥们做动作时间久了,就闹情绪。我们大伙为了安慰他,说完事给你补偿。怎么个补偿法呢,还是我表哥有主意,我们大家弯腰两个两个对接然后连成一座人体桥,让他大大方方从上面走过去。那小子胆子特小,有点像我,他颤颤巍巍的身子宛如经过下面是万丈深渊的一座浮桥。
鬼子进村的游戏,要分成两伙人,一伙拿红缨枪什么的,装作儿童团员站岗放哨。另一伙扮成日军小分队,喊着口令,齐刷刷滚动着烟尘,压着节奏横晃着过来。地点我们选在村子东大坑附近的一棵老槐树下。三伏时节,鸭子们于宽阔的河面来往嬉戏着,巡游着,像一支小乐队齐齐整整地荡漾着生命的乐章。莲花开得很秀气,亭亭玉立的梗,袅袅娜娜的花和叶子,随风起伏,送来幽香阵阵。青蛙欢快地唱着歌,此起彼伏,错落有致。如今,记不起来往下我们演什么了。反正,鬼子兵和儿童团好像没有交火。大家在毒日头的照射下,发蔫了,就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纷纷躲到槐树底下乘阴凉。更有喜欢玩儿水的,就一猛子扎到河里,游来游去,快活至极。
乡村电影有气场,有号召力和影响力,也有渗透性和黏合性。那年月,人们离不开电影。仿佛没有电影的人生是缺滋少味的。看电影的情感,如同过节,如同每个人精神的蜜月或者神往中的旅行。
现在想来,我们当年正是在电影这片绿洲的引领下,才可能走出心灵的沙漠化的。是的,看了《刘三姐》,你会走进遥远的故事,去民族风情画卷里找寻人性的肌理,那歌声响彻着青山绿水,荡漾着生命对自由的憧憬和渴望;看了《小兵张嘎》,战火纷飞年月里的另一种童年,玩耍,搞笑,机智,活泼,生动的写真,无时不在回应着家国情怀的底色;《洪湖赤卫队》,红色的经典,英雄的神奇魔方,伴随着几多风雨中的渔歌唱晚,而那句“人老了,弦拉不准了”的台词,成为一代人的口头语,隔着光影岁月,依旧亲切熨帖,充满了无穷的遐想和回味;看《追鱼》,越剧舞台艺术片,江南吴侬软语之媚,草长莺飞之美,奇异别致的人鱼之恋,都让人赏心悦目,觉得如同人间仙境,恍入眼帘;《白蛇传》也同样好得让我们顾盼多姿,眉飞色舞,沉醉在田汉的戏文,李炳淑的扮相和唱腔,小青的豪爽,许仙的多情而脆弱,法海的法度无边之际,人的心意竟也跟着艺术的美感参差错落交相辉映,宛若浮萍遇雨,洗礼着山光水色里跌宕起落的悲喜人生;《城南旧事》,有着野草般的清香,淡雅,像是一曲隽永的民歌童谣,伸展出通向我们荒芜心灵角落的鸽哨的悠扬、铃铛的脆响和月牙儿般的沉迷舒朗;《小花》像是流年的慢板,李谷一的歌声,点亮了我们干涸沉闷的心弦,而陈冲和刘晓庆的各自纯真的出演,则构成了难以复现的青春、历史和记忆的精彩剪影与确证……
早已散场,我的乡村电影,无法重现,我的儿时光阴。
也许,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段难以割舍难以忘怀说到底是再也找不回来的日子。
那个场院时隔多年后,我去造访,发现它如同久已丢失邮寄地址的信件,没有了准确的空间着落和定位,那里已经盖起了一大片崭新的屋舍,而当年环绕四周的那堵围墙也早就不知去向,是的,更別说那些玉米秸、车的拖斗、放映机、银幕和两根竹竿……还有久违的欢声笑语,还有久违的乡音、乡曲……
我僵直地伫立了许久。
当日正值隆冬季节,村子里显得很静。空中飘着细雪,洋洋洒洒,让我略带感伤的“凭吊”多了一层苍凉。
正巧有个小男孩从家中走出来,用手捧着掉落的雪花,看它在手心里融化。我忽然情动于衷地问了句,小朋友,你们这里还放露天电影吗?
他愣了一下,什么露天电影?没听说过……
我有点尴尬地笑了笑。看着那孩子走远。
风吹拂着飘卷的雪花,在我的视线深处,又仿佛看见了星空,看见了萤火虫,看见了小板凳,看见了那隐隐约约的露天电影……endprint
——露天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