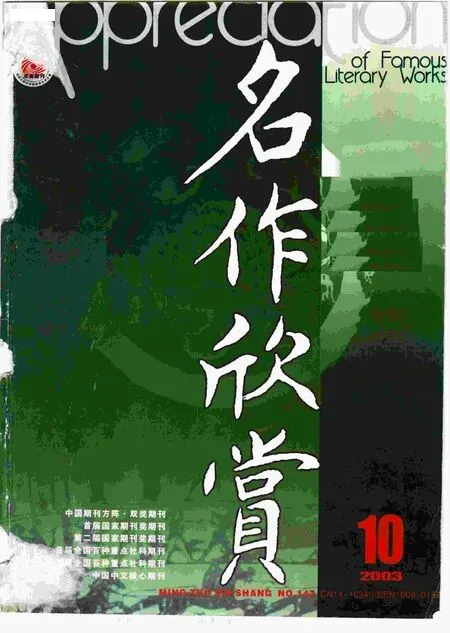镜像与隐喻:东方叙事的魅力
——评盛琼长篇小说《我的东方》
广东 安裴智
作 者: 安裴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多年前,当广东省第十四届新人新作奖揭晓时,我曾采访过在深圳文坛崭露头角的两位年轻女作家——“二盛”,即盛可以与盛琼,后来逐渐读了二人的一些小说,感觉二人都有较好的文学悟性与灵性,但二人的写作路子与文学个性却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呈现出一种相反的形态。简言之,盛可以走的是一条比较“野”的文学之路,而盛琼走的是一条比较“正”的文学之路;盛可以的小说有一种肆无忌惮、旁逸斜出的野性之美,有一种野趣,而盛琼的小说则是规正典雅的庄重之美、绮丽之美;如果说,盛可以的小说像一块冰,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袭人的寒气,凌厉尖辣,那么,盛琼的小说则是一团火,在字里行间燃烧着熊熊的理想之火,让人感到一种诗意的温暖和振奋;如果说,盛可以的小说中较多“性”的描写,从而偏向“俗”的畅销之路,那么,盛琼的小说中,“性”描写的比例相对合理,更好地衬托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如果说,盛可以的小说更多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残酷与辛酸,从而呈现出一种“裸露的真实”(贺绍俊语)的特点,那么,盛琼的小说则更着眼于对诗性人生的心灵空间的拓展与挖掘,呈现出一种理想化的文学境界。
当然,这样的类比我们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实际上,文学之路,往往是一个人人生之路的或直接或间接的艺术折射。就单纯的人生之路来看,盛可以没有读过正规的大学,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固定工作,为生计四处漂泊,生存家园、情感家园乃至精神家园都处于一个不断寻觅、求索的过程,这样一个疲于奔命的城市流浪人,她寻找家园的过程,就是其文学生命不断茁壮成长的历程,多少带有“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色彩;而盛琼自1985年以安徽省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大学毕业后一直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也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白领家庭,她的著书更多的是“为理想谋”。总体上看,盛可以活得比较累、比较野(包括生活方式、生活形态与生活观念),表现于文学中,也呈现出十足的“野味”与大胆;而盛琼则拥有一个相对稳定、优越的生活环境,她走了一条相对幸运、顺畅的成长之路。盛琼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身上的良知与正义感,从小就感染、影响着她,使她培养了一种真善美的健全人格。读她的小说,笔者强烈地感觉到她的文章中闪烁着一种人性美的光芒。因而,她对文学的理解也更规正一些,更书卷气一些。可以说,盛琼是深圳青年作家群里对文学理想的坚守表现得最为彻底的一位。这使她的文学创作从题材选择到主题承载,再到表现风格,都呈现出与别的作家不同的独特个性。
盛琼现为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是一位创作十分勤奋的青年女作家。她早年由作家出版社推出长篇小说处女作《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并获得了第十四届广东省新人新作奖。这是一部与时下众多“时尚小说”“新潮小说”完全不同的个性之作,是一部在商业狂欢的浮躁文坛仍能坚守精神家园的优秀之作,也是一部文采飞扬、富有人生哲理的好小说。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在文本风格、叙述语言及创作理念上都与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有相似之处。它们同是哲理小说,极富思辨色彩。所以,在讲述生命成长故事的同时,直逼灵魂,考问心灵,追问精神价值,思考一切生活表象后面的哲学意义,探究人的精神生存状态,这是盛琼创作这部小说的出发点。后来,盛琼又相继在国内知名文学刊物《十月》《中国作家》《天涯》等发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多篇,文学创作进入一个喷涌期,引起了全国文坛的关注。盛琼的长篇小说《我的东方》,再一次给我们以惊喜,这是盛琼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生长点。《我的东方》以东方文化背景下中国内陆一古城的普通人家三代人近百年的生存与情感衍变为内容,写出了对东方人伦理观念、历史文化的思考。可以说,盛琼的文学视野和胸怀一直都是比较开阔大气的。盛琼的文学创作有一种真诚的理想精神,她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精神追求。只不过,《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是写一个人的心灵成长史,而《我的东方》写的是一户底层百姓人家的生活史,内容相差很远。但人文关怀、历史向度、思想深度是她文学创作中一直关注的东西。
一个东方家族的当代史
长篇小说《我的东方》以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长江边上的一个在近代史上出过“高风”这样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的古城为人文背景,讲述了一户普通人家陈兴旺三代人近百年的再平凡不过的琐细生活,写出了中国人特有的情感方式和伦理精神。这部作品通过“状元街”“牌坊”“天井”等具有东方特色的儿时记忆的镜像回望,写出了东方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的美好;又通过对家园主人生命历史的隐喻叙写,表达了对东方这片古老土地的深情依恋。
繁衍百年的陈氏家族的领头人物陈兴旺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物”,他是一个饮食店的伙计,有着东方人特有的性格特征:老实、本分、木讷、腼腆,却也纯朴、善良、勤劳,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像石头一样地沉默一天”,“三锤子都打不出一声闷响”的东方式青年,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与来自乡村的东方女子陈苏氏结合了。从嫁娶方式到婚后的生活,都体现出浓郁的东方色彩。在这二人所开创的陈氏家业中,三代十数人,都是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有中学教师,有工商局长,有大学教授,有车间工人,也有博士研究生和诗人文学家等新派人物,还有不成气候的地痞流氓。于是,在看似平淡、各自独立的情节单元与故事镜像中,保守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灿烂与龌龊、平淡与传奇、辉煌与肮脏,东方文化内在一对对相互对立的观念与因素之间发生了冲突,又和谐地、合理地彼此依存着,在一种地域性文化性格的逻辑中得到了矛盾的统一。也许,对一个处于东方文化背景下的读者来说,像陈兴旺、陈苏氏和他们的四男四女及几个孙子的故事太司空见惯了,太熟悉了,但我们还是被打动了。我们被打动的理由,正在这种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细节与故事镜像所构成的历史之河中所隐喻传达的东方文化信息。作者就这样以一种十分雅致的笔墨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中国普通家族三代人的故事,描述了一部家族创业的当代史。
东方文明的礼赞与诘问
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看,家族生存与家族故事就是一种符号,是一种有深刻隐喻含义的文本镜像。那么,隐藏在这样一个东方式镜像与符号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是文化。这样,《我的东方》以东方文化背景下中国普通人家的生存历史与情感衍变为内容,写出了对东方人伦理观念、历史文化的思考。可以说,这部作品通过故事的符号和表象,揭示和隐喻的是东方华夏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的根本文化精神,是对东方文明的载体——中国人生存方式、情感习性、文化特征、伦理思想的形象诠释和独特考问。盛琼通过具有隐喻含义的记忆的碎片和故事的符号,敷衍了一条具有东方特色的历史镜像之河,借此表达中国新一代年轻女作家对东方人文精神和文化灵魂的思考。
《我的东方》对东方文化的形象诠释和考问,包括了对东方民俗文化、婚姻文化、伦理文化、建筑文化、节日文化、观念文化的反思。在小说里,状元街的诗书礼教之气与儒雅的遗风,官宦小姐殉情的凄美传说背后潜藏的儒家意识,被岁月的风刀雕蚀得有些残破而孤寒的牌坊所代表的贞节观,贮藏着所有东方人童年记忆的“天井”文化以及具有东方特色的清明扫墓文化、中秋节文化、端阳节文化等,都是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体现出来的。无数的生活细节构成生动而鲜活的历史镜像,在历史镜像的生动描摹与透视中传达了对东方伦理精神与文化精髓的独到感悟和理解。
就这样,《我的东方》通过古城一户普通百姓人家几代人长达百年的爱恨情仇,折射出“东方”所特有的精神、伦理、道德、历史以及博大精深的文化精神。作者以现代人的视角,选取历史和现实的各个片段,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展现东方真实而又梦幻的特质,感受人间美丽而又动人的温情。故事与传奇、现实与记忆、形象与情意、闪回与凝望、自叙与描述,交相辉映,组成了一幅既丰富又自由、既写实又写意、既激情又伤感、既凝重又动人的历史镜像与斑斓画卷,谱写了一首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史诗。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于为东方文化唱赞歌,而是通过生活的细节对东方文化中的糟粕与丑陋予以一定程度的曝光和批评。可以说,作者对东方文明的思考,既包含了对东方人积极向上的奋斗哲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乐善好施的救世主义人生态度和“入世”思想的歌颂,也包含了对东方文化中一些落后、封建的渣滓的批判。如陈苏氏老年分房时的重男轻女思想、大哥陈荣英的家长意识、守身如玉的美貌女子因避垢世自尽的贞节意识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作者的讥讽。
展现绵延不绝的东方灵性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中国”,这是歌曲里唱的。东方,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那里有着璀璨的文明和苦难深重的历史,那里生活着勤劳智慧却也多灾多难的普通平民。在盛琼的笔下,东方是一个永远也做不完的美丽而深远的梦。她在书中说:“东方的故事像季节一样绵绵不绝,东方的精神像民歌一样代代飘香,东方的文明像传说一样愈久弥珍。”可以说,盛琼是在为东方作传,她写了一首东方的史诗。“东方”对她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她的“东方”情结像久酿的醇酒一样浓厚。
故土和家园是一个人的精神归宿,生于斯,长于斯,这使盛琼和东方血脉相连,而东方本身的魅力和神秘也是说不尽、道不明的,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亘古常新。盛琼对东方的人伦、人情以及背负着苦难却依然顽强的底层百姓充满了敬意和感情,《我的东方》在历史传承、文化传承方面有着厚重的表达和承载。有人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到了今天,这个民族性,应该是承接了历史和未来、传统和现代的新的民族性,是一种像大河一样不停奔流、不断融合的力量。它的广度、纵深感、与时俱进的生命力是最吸引作家的地方。所以,传承东方文化的厚重伦理与人文精神,成为盛琼不自觉的艺术追求。
盛琼曾说,她一直对“东方”这个词有着丰富、饱满却无法说清的感情。在西方文化取得了辉煌成就的今天,我们实际上更需要发现东方的魅力,我们更需要重新认识东方的智慧、伦理、道德和文化,那是一个无穷的宝藏,那是一种“和而不同”“自然和谐”的博大精神。盛琼是用自己的心灵和全部的情感在写作。对东方这块土地和人民的热爱与深情、对东方文化和智慧的痴迷都促使她创作这部小说。在她的笔下,“东方”永远都是一种神秘而经久的诱惑,是一个永远也做不完的美丽而深远的梦境。在“东方”这块土地上,总有那么一些元素能让我们的泪水流尽,其内核就是一种东方人独有的文化精神。盛琼的小说就是要表达那样一种哲理:作为宇宙中孤独而智慧的生命,在灵魂和肉体之间,在传奇和现实之间,在历史和未来之间,在回忆和憧憬之间,在坚守和更新之间,在流逝和永恒之间,展现出绵延不绝的东方灵性,演绎出凄绝动人的生命绝唱。对东方文化精神与东方人情伦理的迷醉与倾情,这是盛琼创作《我的东方》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在情感与缘由。
诗性表达的断裂与“复调”式结构
在盛琼的视野里,文学像童话一般美好,令人神往,因而,她的小说中总是弥漫着浓郁的诗情和浪漫主义的氛围。在《我的东方》中,我们同样读到了这样久违的诗性表达的文字。使人印象较深的,是上部第一章“家园”的第一节“状元街”、第二节“牌坊”和第三节“天井”前一部分对古城人文历史背景和生存家园的诗性描述。那是一种典雅、隽永、令人回味无穷的诗性叙写。可惜的是,自从东北保姆小凤进入小说的叙事文本,这种诗性描述就忽然断裂了。诗情戛然而止后,涌入读者眼球的,是大量司空见惯、琐细平凡的日常生活,有些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地鸡毛”。这样,从长篇小说的全局要求来看,作者的叙述就缺乏一种完整的诗意铺垫,她的诗性表达显得仓促、零碎,有一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紧迫感。而全书五分之四的内容选取的故事又太琐碎化、太生活化了,可谓“结实”有余,“空灵”不足,“诗意的留白”不足。同时,人物关系和故事也显得有些凌乱、突兀、无序。这个家族故事也就讲得有些支离破碎,如只有大哥陈荣英的两个儿子在小说里出现,别的七人则没有交代子嗣后代的情况;下部第二章“流光”第三节“节日”对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四个东方最重要节日的描写也不错,但集中到一年来写,则突显“节日文化”的意图太明显,似乎将这四个不同节令的描写穿插于陈家三代人近百年的不同历史时期,会更小说化一些,更有说服力。而下部第一章“传奇”,则有“蛇足”之嫌,似乎经过诗化处理后放在上部第一章较为合适。另外,全书以中学教师小三退休后写一本《我的东方》的书来收尾,这个模仿曹禺《日出》的写法也不足取,意思不大,落入俗套。
从小说结构上看,《我的东方》打破了传统长篇小说故事情节的因果链,采取了《史记》的纪传体写法,是按人物来划分单元,结构全篇,这就使全书的叙述很新颖,是一种“史记式”和“复调式”相辅相成的结构方式。从表达作品的主题内涵的角度看,作者采取这样一种富有创意的结构方式,自有她的道理。也就是说,盛琼并不是要凭借故事的曲折动人来打动读者,她关注的重点仍是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及其未来的走向。另外,这部小说的许多细节描写很感人,如陈苏氏离家远嫁城里的描写,颇有《红楼梦》里探春远嫁海外的况味,令人读后唏嘘不已,感叹之至。
盛琼很注重小说创作的创新意识,希望每一部作品都有所不同,不管是语言风格,还是结构谋篇。盛琼认为,结构对于一部长篇小说的意义非常重大,所以她写作的时候,对结构的创新有一种非常严格和自觉的要求。《我的东方》在内容上涵盖面比较大,人物和故事也比较丰厚,因此采用了一种大开大合、磅礴大气的构思方法。现在看,这种“史记式”和“复调式”相辅相成的结构方式还是这部小说的特色和优势,但个别地方还可更严谨一些。
文化理解的褊狭与深度开掘的可能
单从语言上看,《我的东方》是一部很有些才气的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要求,那么,这部小说也有一些可探讨之处。最主要的,是作者对“东方文化”的理解似乎还流于表面,缺乏一种美学的深度,也缺乏一种全球化眼光,在对文化思考的深度和纵向开掘上有待深入。选材的当否,思考的俗雅,都与作者对文学与文化的理解的深浅有极大关系。
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东方文学艺术美轮美奂,从文艺文本的唯美角度看,中国文化给予我们的审美享受确实是无与伦比的,是令人陶醉的;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这种美丽光环掩盖下的东方文化对现实人生的限制与束缚,对人性的压抑与捆绑。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内陆型农业国家,几千年的农耕文化使我们的思维模式比较保守,中国文化也就具有了一种内向性的特点;而西方国家多是海岛型商业宗教社会,西方文化具有一种外向性特点。可以说,“真”与“善”在中西方文化中的表现是根本不同甚至呈相反形态的。西方文化追求“真”,西方人富于探险精神,故自然科学发达;中国文化追求“善”,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追求伦理意义上的完美,如屈原之“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更注重人的德行的修养,也更注重人伦关系,限制人的个性发展,这种伦理先天要求人们的言行符合某一种道德要求,是“存天理,灭人欲”,不管是中国古代的儒家,还是道家,都把“圣人”“至人”作为做人的标准而对华夏子民提出苛刻的要求,是所谓“圣人的伦理学”。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而不是宗教。李泽厚等学者也曾分析过,华夏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是“以儒为主,以道为辅,儒道互补,极自尊又极自卑”,为官时,志向实现,要大干一番事业,所谓“达则兼济天下”;而失意时,就身在江湖,追求逍遥,所谓“穷则独善其身”,仍不忘人格修养的完善。刘小枫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写过一本很有影响的书——《拯救与逍遥》,就是探讨中西方文化特点的。他认为,西方文化有两条线索,即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是“两希文化的互补”,希腊文化给西方人以追求真理的精神,希伯来文化则给西方人以神的安慰,故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是一种基督教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西方文化的核心是“拯救”,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逍遥”;西方文化更有爱心,中国文化更恬淡;西方文化注重对“真”的追求而不看重对“善”的苛求,中国文化则更注重对“善”的追求而忽略了对“真”的探索;所谓“中国人求伦理而不求真理,西方人求真理而不求伦理”,即是此意。刘小枫认为,华夏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导致中国的文学作品永远限制与停留在伦理的层次,深入不到哲学层次,无论艺术成就多高,都没有哲理深度。这是中国文化的软肋。
鲁迅先生一生都在思考并批判的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国民性”问题,实际上仍是渊源于那种“求善不求真”的民族心理结构。可以说,《阿Q正传》《狂人日记》《药》等作品对“国民性”“民族劣根性”的批判任务,实际上一直没有完成。那种“看客心理”“窝里斗”、权力崇拜、对人性的蔑视、对知识分子的仇恨与践踏、媚俗、媚官、媚钱、无所事事、背后整人、以人际关系的好坏作为臧否人物才能的用人标准,都是“民族劣根性”这棵历史大树繁衍至今结下的毒瘤,我们的文学家应拿起手中的笔斩除这些恶瘤。然而,1949年以来,批判中国人“民族劣根性”,挖潜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度小说似乎还没见过,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真正空白。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一种伦理本位文化和官本位文化,即以人际关系、人伦关系和权力大小作为评判人的才能和价值的最高准则,特别注重人情伦理,注重权力存在对个体生命意识的扼杀,强调集体意识对个体意识的束缚,伦理关系至上,权力至上,而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文化的价值、知识的价值,则被踩在脚下,在东方文化价值体系中不能占应有的一席之地。屈原就曾面对朋党遍地的浊世束手无策,发出了“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的感喟。所谓“明哲保身”,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都是强调“世事”“人情”“世理”的重要,只要对世事洞察入微,对世理谙熟于心,在人情世故方面练就一身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刀枪不入的好功夫,在人海的俗世里处理起各种事情来既得体适度,又游刃有余,保证做什么事都畅达无阻,就可成为“学问”与“文章”,可见中国文化对人情伦理的重视。这就导致许多国人不在真正的学问和文章上下功夫,反而苦心孤诣地钻研人际关系,以致“关系网”成为中国文化中自古就有的一道特殊的“风景”,“关系学”取代了学问,成为无数华夏子民为求飞黄腾达所必须迈过的门槛儿。从与欧美文化的比较来看,中国文化的功利性太强了。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比较注重情感,就是小说里所说的“人间美丽而又动人的温情”,而忽视了创造性思维的开掘。这与西方文化中尊重个人的独立意识,强调个人奋斗、自我意识、个体精神的内核是相去甚远的。所以,中国文化在当代重要而迫切的任务,仍是接过鲁迅先生的旗帜,接过“五四”的旗帜,对具有汉民族特点的伦理本位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对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进行批判,对“国民性”进行彻底改造,导引国民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树立健全的人格,重新高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文化的价值和知识分子的价值。
所以,从批判民族劣根性的角度看,从对复杂多维、圆形立体的“东方文化”的深度理解和深度表达上看,《我的东方》这部小说确实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遗憾,在选材及思想深度的开掘上仍可以更深入一些。虽然她在这部30万字的小说里融进了一些儒、释、道的精神内涵,这也是东方精神的基石,但她对东方文化的思考,主要停笔于对其积极向上的奋斗哲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乐善好施的救世主义人生态度和“出世”思想的歌颂,缺乏对东方文化中一些落后、封建的渣滓的批判。小说是通过人物和故事来表达这些思想内涵的,而人性的复杂是比较难于表现的,易流于简单、片面。如果从民族劣根性上来说,小说揭示得还不够。因为盛琼想展示的东方还是一种带着理想色彩的审美意义上的东方,她的东方是梦幻的,也是情感的,亦真亦幻。小说的创作手法融进了很多浪漫主义因素,语言也有一些抒情和诗意的风格,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
坚守对文学理想的追求
在一大批时尚写作如“美女写作”“下半身写作”“快餐文学”泛滥文坛的今天,盛琼没有选择时髦的新潮写作,而是坚守对文学理想和文学品位的追求。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关注与诘问,对生命存在的文学诠释和独到思考。从盛琼的文学创作道路来看,可以说,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以散文的文笔和诗人的激情,通过“等待”“妥协”“欲望”“孤独”“梦幻”这五个词来承载和表达了她对个体生命的独到思考;而《我的东方》则主要着意于对地域性群体生命,即处于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生存历史和精神取向的总体剖析,是对种群文化和群体生命现象的激情关注。从个体生命到群体生命,作为文学家的盛琼的关注焦点、思考重点和创作视点就这样发生了转变。这个转变是可喜的,因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种群文化和群体生命的现象,表明盛琼对地域文化、对生命成长的影响的理解更深了一步,也表明盛琼对文化与生命的关系的思考又向前进了一步。
现在是一个商业主义引领风尚的时代,浮躁的文坛上各种时尚的主义和新潮的写法林林总总,但越是在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新潮环境中,越要做一个“逆流”的灵魂作家,越要保持心中的理想和热情,坚持个性,固守我们的精神家园,盛琼正是这样的。她的写作向来都不是“时尚”的,她对潮流一直保持着冷静的态度与距离,只忠实于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可以说,盛琼是一个“气质美若兰,才华复比仙”的江南女子,清秀、文雅,灵气十足。她有着很高的智商,文思敏捷,也有极好的才华,散文随笔写得很漂亮。她今后仍要坚守文学这一方净土。我衷心想与她说的一句话是:创作长篇小说,一定不要急于表露才华,更不要浪费才华,力量要用在刀刃上,写最有深度的东西;对散文、随笔来说,也许文笔是第一位的,美感确实重要,但对包容着巨大的社会、历史和思想容量的长篇小说来说,却仅有语言是不够的,那仅仅是一个写作的基础,对文化思考的深度就显得特别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