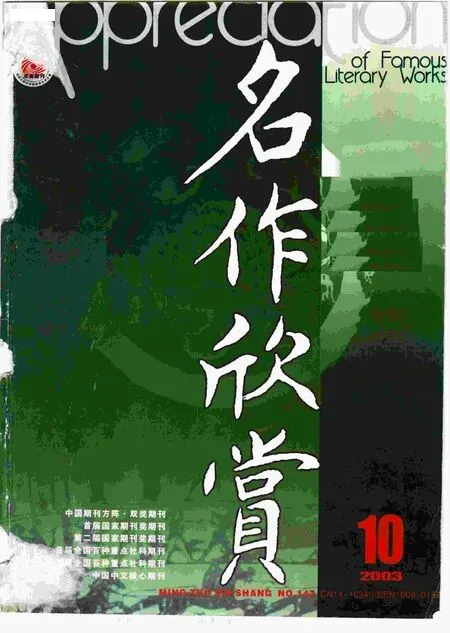门外谈中国画的创新
——周韶华先生作品观摩有感
湖北 邓晓芒
作 者: 邓晓芒,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批评家,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代表性著作有《思辨的张力》《文学与文化三论》《新批判主义》《实践唯物论新解》等。
我对国画完全是外行,但平时很喜欢观赏。近日来,因为受邀参加这届“鼎韵艺术沙龙讲谈”,对韶华先生的诸多作品有些接触,也获得了不小的震撼。同时,读了国内美术评论界的一些名家对韶华先生的精彩评论,受益匪浅,也有一点个人的感悟,不揣冒昧,想趁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
说起来,韶华先生属于我父母一辈,我的父母当年也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9年随部队南下,到湖南后从事新闻工作,与韶华先生有十分相似的经历。所以我非常能够理解韶华先生在他的大量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艰苦卓绝、气吞万里的雄健画风。那个时代的南下干部,是伴着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而投入到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洪流中去的,他们那高昂的革命意志和历史使命感,是不可能拘束于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狭小框架内而得到尽情表达和宣泄的。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作为一个带有诗人气质的文化人,恐怕只有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等一系列大气磅礴的诗词(甚至包括恣肆汪洋的“毛体”书法)才能淋漓尽致地激发起他内心的共鸣。我见各位方家对韶华先生作品的创作技法、传统师承和艺术理念方面的评论精彩纷呈,都已经说得很透彻了,没有我这个外行置喙的余地,但似乎还很少有人对韶华先生艺术风格中与自身经历及其时代密切相关的这一方面做一番知人论世的分析(杨小彦的《文化寻源与宏大抒情》一文略有涉及)。实际上,韶华先生的“大河寻源”与当年红军的长征北上有相似的情怀,他甚至还直接把自己画风变革的历程概括为“三大战役”,这绝不是一种随意的命名,而是泄露了韶华先生一直坚持不懈地在内心奏响着的当年凯歌行进的心声。艺术和哲学一样,是每个时代精神的反映,不结合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我们很难真正读懂一种艺术精神的内在精华。
的确,我们在韶华先生的作品中,读到一种前所未见的雄浑苍茫的大气魄。所谓“天人合一”和“隔代遗传”,就是跨越唐宋以来中国文人画的主流风范和一系列传承的程式,回到汉魏以前,甚至上溯到陶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从那种太古时的鸿蒙混沌中去发现最初的文明之光,去体验生命的洪荒之力。这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寻根热”若合符节。当然,90年代的寻根通常秉持的是道家精神,韶华先生却是以儒家的心态去追溯中国文化最原始的根。贾平凹在小说《废都》中这样形容自仰韶时代遗留下来的“埙乐”:“你闭上眼慢慢体会这意境,就会觉得犹如置身于洪荒之中,有一群怨鬼呜咽,有一点磷火在闪”,“你感到了一种恐惧,一种神秘,又抑不住地涌动出要探个究竟的热情。”韶华先生的画却没有这样消极和诡异,而是如此大开大合,乾坤朗朗,所追求的是“国风归来”的宏大气势。试看他的《天地一沙鸥》,尽管这画名令人联想到的是那种虚空漂渺、萧条淡远的意境,需要大面积的留白来表现;但这幅画却恰好相反,整幅画面竟不做丝毫留白(他的画一般说来很少留白),在翻腾着的海浪与滚滚云霓之上,一只孤独的海鸥轻松自如地自天外飘然而来,帝王一般地君临万象,把杜甫这一感叹年老病休而独自飘零的名句用出了新意。这种新意与毛泽东的诗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王者气派倒是可以相通。另一幅名作《黄河魂》同样将这样一种雄霸天下的霸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天地一沙鸥
不过,韶华先生的画与20世纪90年代寻根潮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立足于草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草根与帝王情结并不矛盾,孟子告诫君王“民贵君轻”,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说“人民就是上帝”,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呼喊万岁的人海高喊“人民万岁”。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草根革命,因此自从延安时代以来,革命文艺推崇的就是通俗化、大众化,强调工农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标准。但这并不妨碍少数有文人气质的革命领袖在古体诗词上创出新意,其中最出色的代表就是毛泽东诗词。然而,由于绘画的特殊性,革命文艺在美术方面长期都局限在油画和西方美术理论的框架中,在国画领域则除了技法上的创新之外,在美学理念上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仍然是传统文人画的变体。韶华先生大器晚成,后来居上,除技法上广泛吸收各派前辈及中西大师,进行“横向移植”外,在艺术精神方面对中国画进行了大规模的尝试和探索,其中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对民族文化的草根中蕴含的巨大潜力做了深入的挖掘和提炼。他的画风一方面超越了已经成为教条的“通俗化”和“大众化”以及空洞无力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而表达了真正从底层爆发出来的灵感和诗意;另一方面,也没有文人和贵族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清高孤傲,却彰显着大时代英雄的胸襟和霸气。当他从现代中国革命的激情返回到“隔代遗传”的原点时,他发现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相结合”①,或者不如说是一个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尚未分化出来的最原始的起点,于是他的创作热情便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和底气。正如胡风在革命成功的年代喊出:“时间开始了!”韶华先生在仰韶时期的彩陶纹饰中发现的是:“文明开始了!”②韶华先生的画所揭示的是中国文化最深刻的底蕴,他在这一点上抵达了一个时代的高峰。
然而,高处不胜寒。韶华先生在晚年深感困惑的是,如何在已有的成就上,跟随时代的脚步继续创新?革命战争的年代毕竟已经过去,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国风”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年轻一代艺术家还能够全身心投入当年激动着韶华先生这一代人的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吗?当代的草根精神体现在“网络爱国主义”和民粹愤青的戾气中,那绝对是非艺术的、不值得歌颂的。在一个普遍认为世风日下和道德沦丧的时代,所谓“国学热”的复古潮流虽然可以给忧心忡忡的无知民众带来一丝暂时的安慰,却遭到有良知的知识界和文化界人士的冷眼面对。实际上,据我有限的认知,当代最先锋的艺术家们正在尝试另外一种“隔代遗传”,也就是返回到鲁迅的时代,酝酿新一轮的“国民性批判”,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眼光对我们的草根文化再次展开深层次的反思,以真正的艺术家的个性来取代以往建立在大众意识和群体意识之上的伪个性。③与韶华先生念兹在兹的“东方”“民族”“国家”不同,这些青年画家心中的关键词是“人性”“个人”,以及面对社会大众的独立的批判意识。他们批判的正是大众的愚昧昏庸和自轻自贱的草根意识,是日夜盼望有一个“明君”来统治自己的受虐心理。当年鲁迅对草根民众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现今已内化为他们内心的一种自嘲和自省。当然,这只是我从几个新派美术家那里所感悟到的一点苗头,一点隐约的倾向,甚至不一定被这些画家自己所明确地意识到;但我预感到,这可能是中国当代美术不但在技法上创新,而且要在艺术精神上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开拓的一个方向。
因此我认为,当代中国画所应该有的更大的突破,主要并不在于传统艺术手段和外来艺术的材料及手法如何能够巧妙地结合,而在于艺术家的心态要真正地放开,获得全球化的视野,并对艺术本身有一种普世性(而不限于民族性)的追求和感悟。当然,在今天中国的艺术家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它要求一个人在当一个艺术家之前,先做一个世界人,要对东西方艺术精神和一般人文精神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领会,要读大量的书,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等,从中获取对一般人性和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的营养。在这种自我养成过程中,我们必然会以这种普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当代的活生生的现实,去掉那些先入为主地植入我们脑子里的遮蔽物,并触发新的艺术灵感。我们当然不会因此而不再是中国人,相反,我们作为中国人被置于世界人中的一分子来看待,由此才具有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才知道如何去发挥我们作为中国人的特长,为人类艺术精神贡献出自己独特的艺术珍品。在这方面,鲁迅先生是一个榜样,我常常想,我们的画家有谁愿意去画出鲁迅的灵魂?举例来说,鲁迅的《野草》里面就有大量值得描写的心灵画面,有些本身就是国画题材,像这样的句子:“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人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这里面的情愫完全是个人主义的,却不是文人画式的,既不是老庄式地逃避现实,也不是为某种庙堂理想而慷慨悲歌。我想象这将是一幅突破“天人合一”的混沌之气而闪耀着灵魂之光的泼墨,有如尼采一般的桀骜不驯,同时又是中国式的、东方式的。但在做这种尝试之前,首先必须读懂鲁迅,这对于青年画家来说是一个艰巨的工作。年轻人的优势是处在一个对外开放的时代,如果能够在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力的同时,也像前辈艺术家那样勤奋读书,理解前辈的苦心和历史的脉络,我相信是能够在艺术上做出超越前人的突破的。
①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与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
②见《走出仰韶系列—文明的前夜》。
③近年来,我应黄立平先生之邀观摩了在武汉合美术馆所举办的几次美术作品展,其中张大力的《龙之吻》和倒悬的人体,方立钧的光头系列和红太阳系列,庞荗琨手绘中反复出现的自拍和镜子的主题,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