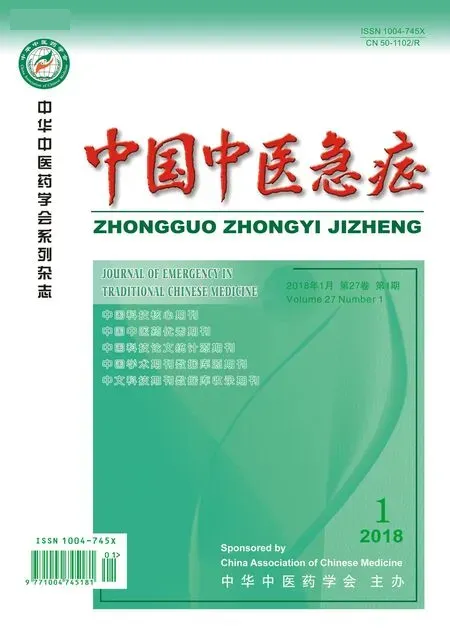中药血清药理学及血清药物化学研究进展*
卢 磊 刘晓丹 张培影
(1.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徐州市中医院,江苏 徐州 221000;2.江苏省徐州市中心医院,江苏徐州 221000)
中药及中药复方所含成分复杂,干扰因素多,药效物质基础不明,药理作用机制、代谢过程等问题难以完全解释清楚,缺乏可靠的药理学、毒理学数据,使得中药单方及中药复方制剂的药效学物质基础无法客观的表达,也直接造成了中医药制剂无法与国际质量标准相接轨,导致中医药产业发展现状窘迫[1]。目前国内外主流的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模式是将复杂体系中所含化学成分采用诸如色谱法、重结晶法等分离后进行活性导向下的追踪分离或逐个进行药效学活性测试[2],上述方法分离所得的单体成分或成分群是否为真正的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目前争议较大[3]。其一,中药及其复方所含化学成分在生物体内环境(如pH、肠道菌群、肝药酶)下多发生复杂的代谢或生物转化,分离所得化合物可能只是活性成分的前体,例如番泻苷属于蒽酮苷类药化合物,本身无泻下作用,口服后小肠吸收率低,但在大肠肠道微生物的作用下生成苷元而发挥泻下作用[4],国外苦杏仁苷注射曾用于肿瘤治疗,而改用口服后出现较大的毒性反应,其根源为肠道菌群中的β-葡萄糖苷酶将苦杏仁苷水解产生毒性的氢氰酸,因此肠道菌群的代谢是苦杏仁苷口服致中毒反应的关键环节[5];其二,中药及其复方所体现的治疗效果往往是多组分、多靶点、多环节的综合结果,采取成分分离的方法追踪活性物质基础,整合作用消失,割裂了中药的整体性[6]。因此,探索符合中医辨证思维和整体观的研究思路以及适合中药复杂体系的研究方法,阐明中药及其复方药效物质基础、配伍机理及作用机制,是贯穿中药研究始终的关键科学问题和主要内容。
1 血清药理学及血清药物化学研究方法的提出
上世纪80年代初,著名的日本药理学家田代真一首次提出了血清药理学这一创新思路。他认为中药制剂口服吸收后,在体内经过胃肠道菌群代谢和排泄过程而发挥治疗作用,因而中药及其复方中具有生物活性的成分——药效物质基础是中药经过人体生物转化之后的产物,这些产物吸收入血后与血浆蛋白结合并通过血液的流动到达靶标器官及组织。因此传统的体外药效学实验方法如直接将中药水提液或水提液经细菌代谢后的成分直接加入离体的组织及细胞反应体系中不如整体动物口服或静脉给药后检测其含药血清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更合理。自上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王喜军提出“中药血清药理学”以来,这一方法在中医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中被广泛重视及应用。
2 中药血清药理学概念、方法及应用
中药血清药理学是指将中药及复方制剂经口灌胃给予动物后收集其血清,血清中含有中药经过动物机体生物转化的代谢产物及一些内源性物质,将此含药血清取代中药复方煎煮剂、丸散剂等加入离体的组织器官或细胞体系中,并对其进行药效学及机制研究的体外研究方法。该方法对于诸如中药及复方这种复杂化学体系的生物活性成分的发现与研究较为合适,它克服了中药粗制剂直接加入反应体系中进行体外实验的缺点,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中药方剂复杂体系与生物机体的复杂生命系统的相互作用的规律。相比于直接以中药复方制剂干预的体外实验,予含药血清进行的体外研究,其结果更具科学和可信度。近年来,血清药理学在中医药研究中的应用被广泛接受,并展现出其特有的优势[7]:首先它从实验方法学上克服了体外实验不能直接观察到的中药复方经体内吸收、代谢等整体药理效应,反映了成分与成分、成分与机体的协同作用;其次对含药血清中化学成分进行药效学和药代学等进行研究,客观合理地反映出中药复方的药效学基础;第三可以用来验证一些中医学基础理论,为探讨中药复方作用规律提供新思路。
血清药理学实验方法避免了中药复方煎煮及丸散等粗制剂型直接进行体外药物研究结果所产生的影响;而且经过动物的吸收代谢等过程,其血清成分可更直接地反映中药复方制剂的药理作用,其对中药复方疗效和机制的阐述也更具科学性。因此,随着这一实验方法的不断完善和改进,其在中医药基础研究的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为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与国际接轨提供了循证依据手段。
然而血清药理学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如实验动物的选择、给药剂量、时间、血清添加量等方面也对实验结果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但随着对其理论及实验的改进和研究,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一系列实验手段解决或改善。
2.1 实验动物选择 目前对于制备含药血清,我们常采用大鼠、家兔等动物。然而实验研究中,由于动物种属的不同,其血清的内源性成分也不尽相同,为了尽可能减少不同种属动物血清在生理生化等方面的不同,减少因此而引起的免疫反应[8],要尽量选择与人类生物学特征相近的物种[9],否则其研究会出现较大的差距,影响实验结果的客观性。此外,为避免种属差异,在一些离体器官、组织、细胞等进行体外实验中,还应尽量选择与实验动物统一种属的动物来制备含药血清,这样亦可以减小因上述差异而造成的免疫反应,提高研究的可靠性。
2.2 给药剂量 实验动物确定以后,需要对动物给药剂量进行研究。给药剂量可直接影响到含药血清中的药物的浓度及含量。但是,对于给药剂量的大小也应严格控制,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在以含药血清为载体的研究中,除了将含药血清加入体外研究体系,还因需要额外加入一定体积的提供离体器官、组织或细胞营养和能量的培养基而使整个研究体系的药物浓度降低。在体外实验中,药物的浓度会直接影响实验的结果,当培养体系中的药物浓度低于体内实验要求的有效药物浓度时,有可能导致“假阴性”结果的出现。同时,考虑到中药复方制剂浓缩后药液的黏稠度、动物的胃肠道对浓缩药液的最大接受量以及过大药物剂量而导致的毒副作用,所以灌胃给药的最大剂量也应严格控制。因此有学者提出可以按照一定的公式计算给药量,给药剂量=临床用药量×动物等效剂量系数×培养体系内血清的稀释比例[10]。然而不同药物的吸收代谢、半衰期等因素差异,因此给药剂量的选择也有差异。因此对于不同药物,必须通过合理的预实验,寻找最佳的给药剂量,才能有效降低实验误差,保证结果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2.3 给药方案 因为药物本身代谢吸收、半衰期等的差异性,因此在对合适的给药剂量进行确认后,还需对适宜的给药方案进行研究。需要考虑两方面因素:是否需要禁食;给药间隔及持续时间。众所周知,口服的中药复方制剂和食物的体内过程共用同一条通道——消化道,两者合用时势必会发生相互作用。一是食物的性质会影响某些中药成分的吸收,例如根据相似相溶原理,高脂饮食能显著提高脂溶性成分的吸收,提高其生物利用度;食物中的某些含多价金属离子的矿物质可能与药物成分发生螯合作用,从而影响成分的吸收。二是食物可能短时间改变胃肠道理化性质,影响机体的生理功能,如胃液pH值变化导致弱酸性及弱碱性中药成分吸收的改变;食物促进胆汁的分泌,导致某些具有肝肠循环特征的成分吸收增加等。因此,食物和药物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中药有效成分血药浓度达到血清药理学实验要求的时间难以确定。为避免食物对中药化学成分的干扰,通常应保持空腹状态下灌胃给药。常规的做法是在实验前禁食8~12 h(不禁水),给药后2 h恢复自由采食。另外给药间隔及持续时间的选择既要贴合临床给药实际又要确保含药血清的药效。传统中药复方服用通法为“一剂药煎煮两次后合并药液,分两次服用”,制定每日1次的给药方案势必直接影响到该药的疗效,因而中药血清药理学实验多采用1 d内多次给药为主[11]。关于给药的持续时间目前文献报道的连续给药天数有3 d者[12],也有 7 d 者[13]。还有学者提出每隔 1 个半衰期给药1次,连续给药7~10 d。无论设计什么样的给药方案,其目的都是为确保有效成分在血清中达到稳态的血药浓度。由于中药及其复方成分极其复杂,成分不同,半衰期亦不同,因而中药复方整体的半衰期很难测定。目前化学成分在体内消除半衰期多为1~10 h,且按消除半衰期为给药间隔给药,经5~6个半衰期后可达药物的稳态血药浓度。因此为了确保中药及其复方绝大多数成分在含药血清中浓度维持在一个基本稳定的水平,7~10 d给药方案是比较保险的给药方法。
2.4 采血时间 药物血药浓度会对实验的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由于中药及复方经给药后,通过吸收、代谢等一系列生理过程,其血药浓度的达峰时间会因各种因素而不同,为了避免因血药浓度低而导致的“假阴性”结果,因此应尽量选择在血药浓度达峰时间段内采血。但是由于药物特别是中药复方的药代学各不同,其有效成分吸收后血药达峰浓度的时间也存在差异[14]。因此许多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将采血时间设定为给药后2 h较为合理,因为大多数药物的血药成分在给药后1~2 h即可达峰。也有学者研究含药血清抗血小板作用,以5-HT的释放和内皮细胞钙通道阻滞作用作为检测指标,通过对药物时效关系的观察,探讨含药物血清制备的最佳采血时间。结果提示对于该药物,在给药后30 min时采血,其血清药理作用最佳[15]。 陈一江等[11]通过对大鼠中药复方灌胃给药,每日2次,给药1 d,分别于末次给药后0.5 h、1 h、1.5 h、2 h后经腹主动脉采血并分离含药血清,结果表明温心汤药物血清能明显提高离体蛙心的心率和肌张力,且其药物作用与所取含药血清的时间相关,其中以末次给药后1 h的含药血清药效最佳。单味中药乃至复方,因药物组成复杂,含有多种活性成分,且药物配伍具有一定的协同或消减作用,其药物疗效并非简单的相加,而是多种药物成分药理学特性的“综合效应”,因此很难对其具体作用机制予以阐述。因此,对于单味中药、药对、乃至复方的研究,都应进行必要的血清药理学预实验,最终确定最合理的采血时间和方案。
2.5 含药血清的处理和保存 由于血清中存在许多活性成分,如各种溶酶、补体等,而这些成分都会对体外培养的细胞、病毒以及组织器官等产生影响等,因此为避免上述因素的干扰,常采用血清灭活等方法进行处理。常用处理方法[16]有丙酮法、乙醇法、加温法等。也有学者认为血清中的补体等活性成分可能参与中药复方各组分的协同作用等过程,尤其是一些特殊中药,如抗病毒类、助消化类的中药,一旦灭活活性成分,其药理作用可能发生改变,甚至出现“假阴性”结果。且从正常药物吸收、代谢过程角度,对血清进行高温等灭活处理也与药物入血、起效等过程不符,因此有学者认为不可简单地一概采用灭活的方法。韩俭等[17]通过实验研究灭活处理对含药血清的影响,结果发现经过灭活处理后的含药血清,对研究的几种细菌均无抑制作用,而未灭活处理的含药血清可显著抑制或灭杀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而低温冷冻真空抽干也因过程中补体作用的活性成分的丢失或失活而出现阴性结果。所以对于血清的处理和保存,应尽可能使用新鲜或保存时间短的灭活血清。
2.6 血清添加量 为了验证药物的药效学及机制等研究,含药血清的浓度和添加量等至关重要。有研究发现,随着对体外细胞、器官等体系中逐渐增加含药物血清的添加量,其药效-含药血清添加比例曲线呈一定的正态分布趋势,这说明反应体系中含药血清的添加量对药物的药效学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作用并非越大越好。高浓度可能因其强细胞毒性作用而影响结果。有学者报道较高浓度的含药血清在体系中可不同程度抑制细胞增殖,而10%的添加比例应用于实验中最佳[18]。 王霖等[19]通过实验研究含药血清的添加量与药理毒理作用时发现,当含药血清被10倍稀释时,含药血清对细胞毒性的几乎无影响。然而因各类实验条件的不同,最好的方法是通过预实验验证的最佳血清添加比例。
综上所述,随着血清药理学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各种方法对某些研究条件进行完善和改进,以期更好的服务于科学研究。有学者指出血浆和血清两个概念本身即存在明显的差别,含药血浆中的药效成分含量高于含药血清[20],建议体外药理实验用含药血浆代替含药血清[21]。对中药特别是中药复方的研究,血清药理学将是一把利器,可更好的阐述中医药的疗效与机制,使之为现代医学领域所认可,实现中医药的国际化。
3 中药血清药物化学概念、方法及应用
中药血清药物化学是对中药药效物质基础进行研究的新领域,在中药现代化研究中起到重要作用。血清药物化学是以给药后的血清为研究对象,从血清中分离并鉴定出移行成分,对血清中移行成分与药物疗效进行相关性分析[22]。通过该实验方法,可直观反映中药给药后吸收入血的成分数和量随采血时间的变化规律;另外,采用血清色谱指纹图谱为指导,可选择性去除血清固有的内源性杂质,富集吸收入血的有效成分。因此血清药物化学可以很好地弥补血清药理学无法确定最佳给药方案、最佳采血时间、血清固有成分干扰试验结果等缺陷,可推动中药药理及药代动力学的发展,实现中药研究与国际标准的精准接轨。
中药血清药物化学是以中药及复方药物成分基础为研究目的的。这也决定其研究范畴应囊括以下几方面[1]:1)对给药样品建立指纹图谱,明确给药样品所含原型成分、含量,并对样品质量稳定性精确控制;2)通过在线检测,确定采血时间及方式;3)采用科学方法对含药血清的样品进行制备;4)联合高效液相色谱法、液-质联用法等现代分析手段对血清样品进行分析和鉴定;5)采用色谱技术、膜分离技术对血中可变成分进行单一化处理;6)对血中相关成分与中药固有的药效进行相关性分析,明确药效的成分;7)对中药复方进行研究,阐明复方的药动学特征,指导最佳给药方案。
血清药物化学在中药及其复方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单味药中,从远志水提物的血清中的移行成分分离获得了3,4,5-三甲基肉桂酸及其代谢产物甲基3,4,5-三甲基氧基肉桂酸,药效研究示两者具有显著镇静催眠作用;越桔茎叶提取物口服给药后血清中含熊果苷及秦皮苷,药效研究显示两者活性与越桔疗效具有相关性;白术提取物入血清检测未发现无苍术酮及苍术内酯,而仅有TEDYA水解产物TEDY吸收入血,提示其直接作用物质为TEDY,TEDYA为前药;东北红豆杉醇提物入血成分含紫杉醇、紫杉宁、银杏双黄酮等成分,且药效实验证实其为药效部位群;口服刺五加提取物后,异秦皮啶的药时曲线呈现双峰吸收,但异秦皮啶单体给药则显示单峰吸收,该现象可能为提取物所含游离异秦皮啶及其多种前体化合物在体内生物转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刺五加提取物相当于异秦皮啶的缓释系统[23]。在复方研究中,茵陈蒿汤全方口服后吸收入血的21种移行成分中,8种成分为各单味药或任意组合给药后入血移行成分所不含,经追踪发现该8种成分具有显著的保肝利胆活性[24-25];六味地黄丸血清药物化学研究发现鉴定的11种血清移行成分中,5-羟甲基-2-糠酸含量较高,但体外含量甚微,其出现是药物与人体以及药物之间相互协同作用的结果[26-27]。
综上所述,血清药物化学在中药质量标准的建立、复方药效物质基础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4 血清药理学与血清药物化学的有机结合
以往中药成分的研究多停留在系统分离的层面上,未能对药物体内吸收、代谢过程中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中药多以口服给药并经胃肠道、肝肠循环过程中多种酶、微生物的代谢作用而进入血液,从而发挥一定的治疗作用,即中药原药成分并非仅仅通过直接作用而发挥疗效,而可能通过中药原药成分、原药成分代谢产物以及机体随之产生的内源性生理活性物质多靶点、多途径的整合作用而产生综合效应(见图1)。近年来,指纹图谱控制中药及其制剂的质量逐渐为国内外提倡和接受,但是中药指纹图谱只能反应中药及制剂质量的稳定性,却不能直观反应其疗效。采用数据处理技术将指纹图谱中色谱峰峰面积积分数据和药理学数据进行关联,探讨化学成分和药效学的相关性,即从谱-效关系结合角度研究其生物效应机理,应能更客观地反映中药复方的药效物质基础及配伍规律。窦志华等在国内较早地采用了“血清药理学”与“血清药物化学”相结合的模式,通过含药血清谱-效关系分析这一方法初步阐明了复方制剂五仁醇胶囊保肝作用的药效物质基础[28],此后又利用谱效关系研究思路对茵陈蒿汤不同配伍方法下的含药血清分别进行血清指纹图谱研究以及保肝作用评价,并分别采用双变量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指认血清指纹图谱中与药效相关的色谱峰[29];经过筛选得到柴胡-黄芩保肝作用有效部位后,将该有效部位给药后取不同采血时间的含药血清进行体外保肝活性研究,同时建立血清指纹图谱,通过双变量分析得到谱效相关性结果,最终显示两个峰与保肝作用密切相关[30]。因此,随着对血清指纹图谱及其血清药理活性的谱效关系的深入研究,对于中药或复方疗效物质基础研究也将进一步得到阐明。

图1 血清药理学及血清药物化学示意图[31-32]
传统的中药谱效关系研究是指将指纹图谱与药理药效相结合,建立两者的数学模型,从相关性结果中发现能够反映药材及制剂质量的指标。而含药血清中的化学成分(中药原药成分、原药成分代谢产物、生理活性物质)与药理活性直接相关,因此将血清药物化学、血清药理学两者结合能更直接反应物质基础与功效、作用之间的关系,能克服中药及复方粗制剂本身对实验结果的干扰,并提高药理实验重复性、真实性和可靠性。尽管血清药物化学和血清药理学仍有许多盲区,但却有着重要的应用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科的交叉互补,相信血清药物化学与血清药理学协同研究及其谱效关系研究的会不断深入和完善,以期更多地应用于中药及复方的药理和机制研究中,为中药谱效关系研究提供更为准确地评价方法。
[1] 王喜军.中药血清药物化学的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J].中国中药杂志,2006,31(10):789-792.
[2] 齐炼文,周建良,郝海平,等.基于中医药特点的中药体内外药效物质组生物/化学集成表征新方法[J].中国药科大学学报,2010,41(3):195-202.
[3] 王喜军.中药及中药复方的血清药物化学研究[J].世界科学技术,2002,4(2):1-4.
[4] Dreessen M,Eyssen H,Lemli J.The metabolism of sennosides A and B by the intestinal microflora:in vitro and in vivo studies on the rat and the mouse[J].J Pharm Pharmacol,1981,33(10):679-681.
[5] 左风,严梅桢,周钟鸣.肠道菌群对中药有效成分代谢作用的研究进展[J].中国中药杂志,2002,27(8):11-15.
[6] 安莉萍,窦志华,候金燕.中药血清药理学、血清药物化学研究进展[J].中南药学,2013,11(7):521-524.
[7] 王国佐,葛金文.血清药理学方法在中药研究中的进展[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7(3):78-80.
[8] 张开镐.依赖性药物药理效应的种属差异[J].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10,19(5): 413-415.
[9] 孙敬方.动物实验方法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110-126.
[10]王力倩,李仪奎,符胜光,等.血清药理学方法研究探索[J].中药药理与临床,1997,13(3):30-32.
[11]杨奎,周明眉,姜远平,等.中药血清药理学的方法学研究——给药方案的研究[J].中药药理与临床,1999,15(3):44-45.
[12]康敏,王仁生,刘文其,等.血清药理实验方法学在抗鼻咽癌中药筛选中的应用[J].临床医学工程,2013,20(1):16-18.
[13]陈晓白,王晓平,赵仕花.毛鸡骨草含药血清体外抗乙型肝炎病毒作用的研究[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2,18(22):218-221.
[14]董淼伟.时辰药理学与临床合理用药[J].人民军医,2008,51(4):241-243.
[15]柯玮,朱建华.中药血清药理方法学的研究概况[J].中国医药指南,2011,9(6):24-25.
[16]陈赐慧,花宝金.关于中药血清药理学实验的几个问题和探讨[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3,31(1):46-48.
[17]韩俭,于红娟,吴勇杰,等.中药血清药理学方法学研究——抗菌试验含药血清处理方案的研究[J].中药药理与临床,2002,18(1):47-48.
[18]詹红生,赵咏芳,冯伟,等.含药血清方法在中药调节骨与软骨代谢基础研究中的应用[J].中国骨伤,2000,13(11):21-22.
[19]王霖,张云,汪受传.中药血清药理学研究中含药血清添加量问题的商榷[J].山西中医,2006,22(1):51-52.
[20]罗琳,窦志华,丁安伟,等.大鼠灌胃复方五仁醇胶囊后血清和血浆中五味子醇甲和五味子乙素的比较[J].中草药,2006,37(10):1486-1489.
[21]葛金文,朱惠斌,王宇红,等.关于中药血清药理学方法的再思考[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8,10(6):16-22.
[22]魏元锋,张宁,冯怡,等.中药血清药物化学在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中的应用[J].中草药,2009,40(9):1489-1492.
[23] Sun H,Lv H,Zhang Y,et al.Pharmacokinetics of isofraxidin in rat plasma after o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extract of acanthopanax senticosus using HPLC with solid phase extraction method[J].2007,55(9):1291-1295.
[24] Wang X,Sun W,Sun H,et al.Analysis of the constituents in the rat plasma after oral administration of Yin Chen Hao Tang by UPLC/Q-TOF-MS/MS[J].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d Biomedical Analysis,2008,46(3):477-490.
[25] Wang X,Lv H,Sun H,et al.Quality evaluation of Yin Chen Hao Tang extract based on fingerprint chromatogram and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five bioactive constituents[J].J Sep Sci,2008,31(1):9-15.
[26]王喜军,张宁,孙晖,等.六味地黄丸的血清药物化学研究[J].中国天然药物,2004,2(4):29-32.
[27]王喜军,孙文军,张宁,等.六味地黄丸血中移行成分的分离及结构鉴定[J].中国天然药物,2007,5(4):277-280.
[28]窦志华,罗琳,丁安伟,等.复方五仁醇胶囊含药血清指纹图谱与保肝作用的谱效关系[J].第四军医大学学报,2008,29(2):116-118.
[29]窦志华,罗琳,候金燕,等.基于方剂配伍含药血清“谱-效关系”的茵陈蒿汤保肝作用药效物质研究[J].中国医院药学杂志,2016,36(22):1968-1972.
[30]许刚.柴胡—黄芩药对保肝作用有效部位及其谱效关系的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08.
[31]王国佐,葛金文.血清药理学方法在中药研究中的进展[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7(3):7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