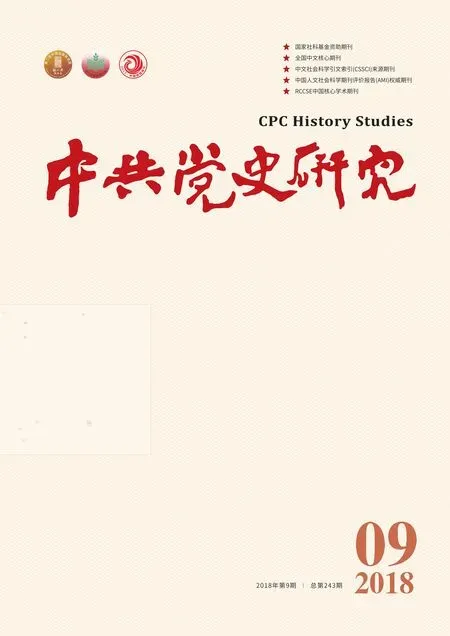“中归联”历史研究五题*
周 桂 香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被关押在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的原日本侵华战犯*1956年6月至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开庭,依法对45名罪行特别严重的日本侵华战犯进行公开审理,分别判处8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对其余1000余名战犯,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并释放。于1957年成立的日本民间组织。几十年来,“中归联”以“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为宗旨,坚持认罪和反省,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动。
1990年,笔者作为外事翻译,与“中归联”成员开始有了接触和交流。笔者祖籍山东,抗战时期,那里饱受侵华日军摧残,而“中归联”的一些成员恰是曾经在山东犯下滔天罪行的战争罪犯*抗日战争期间,部分“中归联”成员跟随侵华日军第59师团驻扎在山东境内,其中一些人甚至就在笔者家乡。。所以在刚接触这项工作时,长辈们讲述的战争伤痛,尤其是日军的罪恶行径总是在笔者脑海中挥之不去——“中归联”的“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是真诚的吗?他们不断忏悔、努力赎罪,是不是有所企图,又能坚持多久?在随后将近30年的跟踪观察中,笔者发现这种情绪并不少见。中日两国人士都或多或少地对“中归联”有所怀疑。日本方面认为他们被中共“洗脑”,或曰新中国借此打“外交牌”,视其认罪反省为“说谎”“自虐”*参见石田隆至、張宏波:《加害の語りと戦後日本社会(1) 「洗脳」言説を超えて加害認識を伝える——戦犯作家·平野零児の語りを通じて》,《戦争責任研究(季刊)》第72号,2011年夏;富永正三:《あるB·C級戦犯の戦後史——本当の戦争責任とは何か》,影書房,2010年,1—5頁;大澤武司:《人民の義憤を超えて——中華人民共和国の対日戦犯政策》,《軍事史学》2008年第44巻第3号;富永正三:《発刊の趣旨》,《中帰連(季刊)》創刊号,1997年6月。;中国方面也不乏对其动机和诚意持怀疑态度的人。当然,更多的学者、民众则对“中归联”的历史知之甚少。
中日两国学者对“中归联”原战犯的思想改造和认罪反省已有若干研究,但坦白地讲,在相关史料尚未得到有效搜集整理的情况下,想要全面还原这段历史其实是不太可能的,甚至会在理解上出现偏差。同样由于史料不足,本文只能以抚顺战犯管理所及其关押过的“中归联”成员为例*太原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战犯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北各地及华中、华南等地逮捕的从事行政、特务等工作的日军官兵。这部分比较复杂,本文暂不涉及。,片段式地介绍“中归联”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五个比较受人关注的问题;与其说是提供一种研究结论,不如说是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思考,希望能够启发、吸引更多学者投入到这一课题中来。
一、关于新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政策
关于新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教育改造,最引人关注的一个方面或许是:中国政府“以直报怨”,甚至“以德报怨”,在生活上为日本战犯提供了人道主义待遇。不少人认为,新中国政府是带着很强的自觉性来实行人道主义政策的,目的是让顽固不化的日本战犯实现认罪反省。这种观点或许会让部分同胞在民族情绪方面感到不适,除此之外,表面上看似乎并无不妥;实际上,它却为国外的“洗脑”“外交牌”等言论提供了某种依据。新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政策果真是这个样子吗?对此,尚需从头说起。
1950年7月18日,在中苏边境绥芬河车站,苏联政府将969名日本侵华战犯移交给中国政府,其中包括伪满洲国司法、行政、军队、警察系统,以及铁路警备队、关东军宪兵队、关东军下属部队等各个层级的官员、士兵。对于接收日本战犯,周恩来提出的要求是必须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注]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改造战犯》,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9页。。这显然只是一个大致的规定,既划定了“底线”,又为负责具体工作的人留下了自主发挥的空间。7月21日,这批战犯抵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时称“东北战犯管理所”)。
中苏交接之后,日本战犯从苏联的“闷罐货车”换乘中国干净整洁的客车,反差之大令其百般不解。这无疑应该是人道主义政策的发端了。实际上,负责战犯接收任务的东北公安部政治保卫处执行科长董玉峰回忆说,为完成中央交给的“不跑不死”的任务,也曾考虑用“闷罐车”运载战犯,以防发生“跳车身亡”事件,但东北公安部部长汪金祥表示,“天气太热,还是使用客车较好,但要加强戒备”,于是安排了20余人的押解工作组和看守小组[注]《回忆改造战犯》,第10页。。这表明此事并非中央刻意安排,而是具体工作人员根据天气条件、人体感受作出的决定。或许当事人并未多想,但这种做法说明:从一开始,中方工作人员就将日本战犯当作“人”来对待,这应该是中国人“与人为善”观念的一种体现。然而,因为有了苏联高温难耐的“闷罐车”作对比[注]島村三郎:《中国から帰った戦犯》,日中出版,1975年,10頁。,再联想到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种种突破人性底线的行为,战犯们心理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关于来中国后的第一顿饭,战犯们在回忆中多以“丰盛”“美味”来描述。但据董玉峰回忆,当时准备的是在哈尔滨订购的面包、香肠等易储藏、携带的食品[注]《回忆改造战犯》,第10页。。就是这样的食物令“中归联”成员金子安次终生难忘。他在回忆中提到,当年自己与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在同一个车厢,年轻战犯对久违的“美食”狼吞虎咽,而藤田茂等年长者则咀嚼不动,有人提议扔掉,随车管教吴浩然坚定地回答:“不许把面包扔掉。面包是中国农民用汗水换来的小麦制作、中国工人付出辛苦烤制的……牙口不好的提出来,下一站给你们换粥,将面包交还回来。”到下一站,果然给年纪大的战犯配发了粥。[注]金子安次:《藤田会長との出会い》,《中帰連(季刊)》第16号,2001年春。大部分战犯此前在西伯利亚经历了五年慢性饥饿下的重体力劳动,如今他们在整洁、舒适的车厢里体验到了饱腹感,脸上泛起了久违的笑容[注]参见絵鳩毅:《皇軍兵士、シベリア抑留、撫順戦犯管理所:カント学徒、再生の記》,花伝社,2017年,128—225、227頁。。
入所初期,日本战犯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有的因对苏联将自己移交给中国而不满、恐慌和绝望;有的准备“卧薪尝胆”“东山再起”;还有的像战争期间一样蔑视中国,疯狂抵抗,情绪极不稳定[注]参见鵜野晋太郎:《菊と日本刀》(下),谷沢書房,1988年,41頁。。生活方面,与管理所工作人员一样,战犯们也以高粱米为主食。他们中间,有人对此感激涕零,也有人提出各种要求,如“我们是日本人,要给吃大米,高粱米这东西是给牲口的”,“中国没有钱买大米可以借钱,将来由日本政府来还”,“日本人没有鱼怎么行”等等[注]中国帰還者連絡会編:《私たちは中国で何をしたか——元日本人戦犯の記録》,新風書房,1995年,17頁;国友俊太郎:《三つの国家と私の昭和史――洗脳の人生》,風濤社,1999年,290頁;李秉刚等整理:《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访问资料(2)(黄国城)》,未刊手稿,2008年1月。,个别战犯甚至绝食抗议,管理所只得将相关情况向上级汇报[注]《回忆改造战犯》,第5页。。1950年8月29日,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对在押的日本和伪满洲国战犯,在生活上要按照国际惯例分别管理,要尊重他们的人格[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72页。。按照这一指示精神,日本战犯在管理所能够吃到大米、白面、鸡鱼、肉蛋。这种人道主义待遇因与当时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形成了一定的反差而颇受关注。
实际上,新中国政府并非一开始就超标准地、像“招待客人”一样对待日本战犯,反而是在其入所一个月以后,才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待遇。只不过中国当时太穷了,以至于按照国际惯例提供的战犯待遇,竟远超普通百姓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显然并非有意推行人道主义政策,中国人甚至无法理解战犯们所体会到的“人道主义”,因为后者是联系自己过去在中国犯下的没有人性的罪行,来感受现实生活待遇的,两者之间的反差必然极为强烈[注]相关案例在“中归联”成员的回忆中随处可见。比如1953年夏,抚顺战犯管理所主治医师温久达在抚顺矿务局总医院背着骨折的战犯安井清上楼就医。温久达之所以这样做,其实只是出于医务工作者的责任,而安井清却联想到侵华日军种种泯灭人性的犯罪,深感“太对不起中国人民”,并因自责、感激而落下眼泪。对于安井清内心的激荡,温久达浑然不知,还以为他是由于伤处疼痛难忍而哭泣,于是一边艰难地爬楼梯,一边安慰安井清。参见《回忆改造战犯》,第117页。。
在之后的工作中,管理所工作人员把对战犯的尊重、理解和包容融入每一个不经意的生活细节里。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这种做法既源于中国人的自律,更有严格的工作纪律作为约束。其间,也有人表露出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情绪,但这样做是要受处分的[注]参见李秉刚等整理:《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访问资料(3)(姜禹成)》,未刊手稿,2007年12月。。在战犯们看来,工作人员的严格自律再次与自己的种种罪行形成强烈反差,这使得他们心中所谓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开始动摇,对中方逐渐产生信任;而战犯态度的转变则使工作人员体会到了成就感,感受到了工作的价值,也就更有积极性了,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注]日本学者石田隆至认为,新中国在教育改造日本战犯过程中实行的“宽大”政策,正是彻底的“严格”政策的结果,二者是互为表里、有机结合的。参见石田隆至:《中国の戦犯処遇方針にみる「寛大さ」と「厳格さ」——初期の戦犯教育を中心に》,《PRIME》第32号,2010年10月。。
事实上,“中归联”原战犯们对中国方面的人道主义待遇一直疑惑不解。1983年,也就是离开中国27年后,“中归联”成员来华访问,迫不及待地向战犯管理所原工作人员询问当年的情况[注]参见中国帰還者連絡会(正統)本部編:《27年目の邂逅(元撫順戦犯管理所職員の回想録)》,私家版,1983年;山岡繁:《私の感想》,私家版,1985年。。正是在随后的交流中,双方对彼此的了解逐渐加深。“中归联”成员们体会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超越人道主义的、“过度的”感情与精神上的牺牲,认识到认罪不能停留在“你给我人道主义待遇,我回报你认罪”的层面上,而是只有“倾尽一生的认罪”,才能报答中国。恰如“中归联”成员难波靖直所言,当年管理所的“认罪模范”宫崎弘回国后在“中归联”的活动中几乎“销声匿迹”,这种“交易式”的认罪无法回报中国政府和人民忍耐国仇家恨和感情痛苦、作出巨大牺牲而给予自己的人道主义待遇,这种人不能称之为“有情有义之人”[注]石田隆至:《寛大さへの応答から戦争責任へ——ある元兵士の“終わりなき認罪”をめぐって》,《PRIME》第31号,2010年3月。。
二、关于对日本战犯的不同管教方针
从结果上看,新中国政府十分成功地对日本战犯进行了教育改造,但历史研究不能满足于“结果”,而管理、教育日本战犯的“过程”实际上是十分曲折的。仅就笔者所在课题团队收集到的资料而言,对于如何管理日本战犯,开始时并没有一个“顶层设计”;接收战犯一年半后,中央有了开展“认罪教育”的指示,却依旧没有规定具体的方式方法。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围绕如何管理和教育日本战犯,工作人员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方针[注]《認罪~中国·撫順戦犯管理所の6年~》,NHKハイビジョン特集,2008年;吴浩然:《我回忆战犯管理所的工作和斗争》,未刊手稿,1987年8月。。
一种管教方针是单纯看管的“猪倌式”管理,即“做到中央的指示‘不跑、不死’四个字。只管他个‘吃、喝、拉、撒、睡’,喂得胖胖的,到时候统统拉出去宰掉,为中华民族报仇雪恨”。另一种则是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即“以政治思想方面的攻势来摧毁其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气焰,然后进行思想改造教育,使他们认罪服法”,也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摧毁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思想”。[注]吴浩然:《我回忆战犯管理所的工作和斗争》,未刊手稿,1987年8月。双方分歧相当严重[注]1952年,主张后一种方针的曲初被以其他名义收监审查两年左右。同样秉持这一方针的吴浩然则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并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二人后来均获平反或改正。参见中共抚顺七六一管理所委员会:《对吴浩然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决定》,1979年1月;纪敏:《历史不会忘记他们——记为改造日本战犯做出贡献的人们》,未刊手稿,2017年8月。。
即便采取后一种方针,触动灵魂的思想改造又该如何进行?1951年初,计划中的侦察处理日本战犯工作由于“三反”“五反”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而暂停[注]徐志民:《新中国审判与改造日本战犯研究综述》,《澳门研究》2016年第4期。。一段时间里,战犯们每天只是在规定时间内生活起居,没有审讯和劳动,过了一段“轻松快乐”的时光[注]《認罪~中国·撫順戦犯管理所の6年~》,NHKハイビジョン特集,2008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管教人员开始思考和探索具体的管教方法。
在此之前,1950年10月,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抚顺战犯管理所临时北迁至哈尔滨,分为道外、道里和呼兰三处[注]溥仪等伪满洲国战犯被关押在哈尔滨市道外监狱,由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负责。日本战犯由副所长曲初负责。其中,200余名校级及以上战犯被关押在道里监狱,管教为金源、张梦实、谢连璧等;其余近700名尉级及以下战犯被关押在市区以北32公里处的呼兰监狱,管教为王枫林、吴浩然等。参见《回忆改造战犯》,第7、29、38页;《認罪~中国·撫順戦犯管理所の6年~》,NHKハイビジョン特集,2008年。。呼兰监狱的管教吴浩然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某部教导员转业不久,在部队中,他长期负责基层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如今,虽然工作环境换成了封闭管理模式下的监狱,工作对象也变为年轻的战犯,但吴浩然认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做思想工作,于是自然而然地搬用了过去的工作方法。当然,这次针对的是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日本战犯,工作难度不可同日而语,需要更强的原则性、更多的耐心和更坚定的信念。
在呼兰监狱,吴浩然借助自己精通日语这一语言优势,从1950年11月开始,广泛与战犯沟通,启发他们“在学习中认识真理,树立新的人生观”,“解决人生怎样才能有意义、有价值地活下去的问题”,强调“思想改造,认罪服法,争取光明的前途”。他还拿出自己珍藏的日文版列宁著作《帝国主义论》,组织战犯展开学习。[注]吴浩然:《我回忆战犯管理所的工作和斗争》,未刊手稿,1987年8月。
思想改造的管教方针肯定发挥了作用,但也不是“药到病除”。这些战犯当初在日本才是真正被“洗脑”了,清除其头脑中所谓的军人精神、武士道思想,绝非一日之功。因此,尽管一些战犯在初步学习中逐渐有所觉悟,但尚未实现认罪;相比之下,道里监狱的将校级战犯更为嚣张[注]道里监狱的战犯不仅寻衅闹监,甚至还殴打管教。参见《回忆改造战犯》,第31—37页;吴浩然:《我回忆战犯管理所的工作和斗争》,未刊手稿,1987年8月。。
1952年2月,周恩来看到公安部《内部简报》介绍的日本战犯对管教方针、政策不理解,甚至拒不认罪、抗拒改造等情况[注]参见纪敏:《历史不会忘记他们——记为改造日本战犯做出贡献的人们》,未刊手稿,2017年8月。,随即批示要求对日本战犯进行“认罪教育”[注]抚顺战犯管理所编:《十四年来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工作基本总结(第二稿)》,1964年6月。。从现有材料看,中央层面似乎没有给出更具体的指导。如何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还需要管理所的管教们自主探索。
道里监狱负责将校级战犯管教工作的张梦实等讨论、分析了战犯们的言论,进而认识到,这些战犯不清楚自己“为何而战”和“为谁而战”,他们虽声称“效忠天皇”,但并不清楚日本天皇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如果说“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那么“精神的力量也必须用精神的力量来摧毁”,于是张梦实提议用学习《帝国主义论》的方式对战犯进行“认罪教育”。[注]纪敏:《历史不会忘记他们——记为改造日本战犯做出贡献的人们》,未刊手稿,2017年8月。
在选择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作为学习材料这件事上,张梦实同30多公里外的吴浩然之间没有任何沟通[注]参见周桂香、石田隆至、张宏波采访张梦实的记录,2014年3月。,二人所用的版本也不一样——张梦实没有找到日文版,于是特地翻译了部分章节;但是,他们推行的学习方式几乎完全相同,都是组织战犯自主学习。呼兰监狱组织了80余名有学习愿望的战犯,分成六个小组展开学习[注]《回忆改造战犯》,第89页。;道里监狱关押的战犯思想更为顽固,“直接弄不了,要培养积极分子”[注]李秉刚等整理:《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访问资料(4)(张梦实)》,未刊手稿,2008年3月。,所以参加学习的是14名有“思想基础”的将校级军官。经过学习,呼兰监狱的战犯在1951年3月迁回抚顺时,情绪已比较稳定[注]吴浩然:《我回忆战犯管理所的工作和斗争》,未刊手稿,1987年8月。;道里监狱还开展了悔罪、认罪的教育实验,达到了预期效果,原伪满洲国总务次长古海忠之的认罪与反省极大地带动了其他战犯[注]参见李秉刚等整理:《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访问资料(4)(张梦实)》,未刊手稿,2008年3月。。
呼兰、道里两个监狱在教育战犯的方式方法上存在不少相似之处,这是不是能够反映出新中国教育改造日本战犯的某些内在规律?同时,这种“巧合”和“偶然”再次说明,新中国政府没有试图对日本战犯“洗脑”,或者通过展示“以德报怨”“以直报怨”的姿态来沽名钓誉[注]关于国内劳教分子的处理,毛泽东曾经指出:“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与方法要正确才行。”但有材料表明,对于如何改造日本战犯,他的看法或许有所不同——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在接受日本记者新井利男采访时回忆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战犯长期关着也没什么用。也不能一直这么关下去。要是猪的话还能吃,战犯是人也不能吃。教育嘛,搞一段时间就行了。我们的目的也不是把他们教育成共产主义的领导者,放回日本推翻政权。日本的军队教育搞得彻底,纪律严明,所以即便有外面的教育,他们也不会轻易理解和接受的。放他们回去算了。”倘若毛泽东真的说过这番话,所谓新中国政府教育改造日本战犯是有所企图甚至是在“洗脑”的观点便不攻自破了。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2页;新井利男資料保存会編:《中国撫順戦犯管理所職員の証言》,梨の木舎,2003年,58—59頁。。至于如何解释这种所谓的历史偶然性,笔者尚未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
1951年迁回抚顺后,呼兰监狱关押的尉级及以下日本战犯的认罪学习逐渐走上正轨。吴浩然通过摸底排查发现,“战犯之中80%是日本劳动人民的子弟”[注]吴浩然:《我回忆战犯管理所的工作和斗争》,未刊手稿,1987年8月。。结合中央“认罪教育”的指示,他想起了自己在部队组织战士开展以“诉苦”“三查”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的成功经验。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副所长的曲初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便同意选几个“最苦的”战犯试一试,人数不宜太多[注]纪敏:《历史不会忘记他们——记为改造日本战犯做出贡献的人们》,未刊手稿,2017年8月。。吴浩然尝试通过“忆苦”启发几名穷苦出身的战犯的阶级觉悟,进而达到使其自觉悔罪认罪的目的。这种理论联系实际、对日本社会阶级压迫进行分析批判的方式,唤醒了战犯们对日本底层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为提高战犯的觉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注]吴浩然:《我回忆战犯管理所的工作和斗争》,未刊手稿,1987年8月。。
在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特别指出。其一,前述两种管教方针的分歧并没有随着“认罪教育”的开展而消失。管理所的一些工作人员“骨子里憎恨日本军国主义,有复仇心理”,不过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所以尽管对中央指示保留看法,组织上行动上还是坚决服从、认真执行。后来,主张思想教育的工作人员甚至受到了“左”倾错误的冲击。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归联”邀请原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访日,当年反对思想教育的人才相信战犯们真的被改造好了,思想教育真的有用,这才向曾经意见对立的同事道歉[注]参见纪敏:《历史不会忘记他们——记为改造日本战犯做出贡献的人们》,未刊手稿,2017年8月。。历过30多年的风风雨雨,双方终于实现和解。
管理所原工作人员的和解因“中归联”原战犯而起,反过来却又影响了“中归联”原战犯。1967年前后,“中归联”因日共、日中友好协会分裂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多种原因,分裂成两个阵营[注]这一时期,“中归联”分裂成“中归联(正统)”和“中连”,前者侧重日中友好,后者的活动则以战争证言为主。参见中国帰還者連絡会埼玉支部:《埼玉支部の歩み(統一の兆しと統一大会)》,私家版,1995年,29—52頁;中国帰還者連絡会編:《帰ってきた戦犯たちの後半生——中国帰還者連絡会の四〇年——》,新風書房,1996年,127—133、313—324頁;富永正三:《あるB·C級戦犯の戦後史——本当の戦争責任とは何か》,252—254頁。。两个派别的原战犯有着同样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自己在中国做了那么多坏事,中国人为什么对自己那么好?所以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可以与战犯管理所原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后,他们各自都在寻找答案。两派成员了解到,管教们当初不仅压抑着精神上的痛苦来引导、帮助他们,还因为坚持进行思想教育受到批判。这让他们非常感动,进一步激发了感恩与谢罪之心。更重要的是,管理所原工作人员的和解极大地触动了“中归联”两派成员;而且,深受两派成员敬重的管教们明确提出,希望“中归联”结束分裂。在这种情况下,“中归联”重归统一,并于八九十年代掀起了反战和平运动的新高潮[注]参见《帰ってきた戦犯たちの後半生——中国帰還者連絡会の四〇年——》,313—324頁;帰山則之:《生きている戦犯:金井貞直の「認罪」》,芙蓉書房,2009年,284頁;富永正三:《あるB·C級戦犯の戦後史——本当の戦争責任とは何か》,255—256頁。。
其二,日本战犯之所以能够转变思想,除人道主义政策和思想教育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这一胜利颠覆了战犯们对日本和美国的认识,也改变了他们一直以来对中国人民的蔑视态度,使其开始希望了解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注]参见《認罪~中国·撫順戦犯管理所の6年~》,NHKハイビジョン特集,2008年。。在管理所良好的生活、学习和思考环境中,战犯们了解了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进而改变了对侵华战争的认识。
其三,抚顺战犯管理所在组织战犯开展学习时,会定期向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作书面汇报或请示,战犯们在学习过程中也写下了很多学习体会[注]抚顺改造战犯历史研究会编:《教育改造战犯研究》第1辑,内部资料,2012年,第102页。,这些史料亟待挖掘和梳理。有战犯回忆说,自己在管理所期间抗拒着、抗拒着,不知不觉中思想发生了变化[注]帰山則之:《生きている戦犯:金井貞直の「認罪」》,192頁。。个人回忆当然可以这样讲,但在研究“中归联”原战犯的思想转变过程时,则应该尽力搞清楚由“量变”向“质变”过渡的过程——前提是搜集、整理或公开相关档案材料。
三、关于原战犯认罪反省的契机
20世纪90年代,日本精神医学家野田正彰在对“中归联”成员反复展开访谈的基础上,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指出:感情压抑、僵化的战犯们在恢复丰富感情过程的终点实现了认罪[注]参见野田正彰:《戦争と罪責》,岩波書店,1998年,111—187頁。。的确,尽管曾经的罪恶是无可辩驳的(新中国政府对其免于处罚,实际上是宽恕了他们的罪恶),但这不能改变原战犯也是“人”这个事实。笔者在与“中归联”成员接触的过程中,听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大家都同样是‘人’”。很多战犯回忆说,日军死在战场时,绝大部分喊的是“妈妈……”,没有见过喊“天皇万岁”的。那么,是什么契机使得这些被军国主义教育剥夺了“人”的情感的原战犯“重新做人”?野田正彰所说的“终点”到底在哪里呢?
战犯们的出身、职级、经历、年龄、立场观点各不相同,认罪的时间、契机以及深度自然也有差别,尽管如此,其认罪经历仍旧存在某种共性。从“中归联”成员们的回忆中不难看出,部分战犯(如安井清、土屋芳雄等)在中国政府人道主义政策的感召下,认识到了自己的战争罪行;另有不少人的转变发生在自己、家人或家乡受到伤害的时候,那种切肤之痛使他们感受到了受害者的痛苦,由此联想到侵华战争中的中国战争受害者;当然,也有人是在回国后参与“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时体会到使命感、责任感,或者说是一种负罪感使然,最终实现了对战争责任认识的彻底转变[注]参见周桂香:《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原日本战犯的认罪看中日战后和解——以原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成员三尾丰为例》,《纪念全面抗战爆发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内部资料,第229—238页。。
相关案例比比皆是,最典型者当属原伪满洲国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长岛村三郎。起初,岛村三郎是管理所里最顽固的“抵抗者”[注]这是岛村三郎回国多年后对自己的评价。参见伊東秀子:《父の遺言:戦争は人間を「狂気」にする》,花伝社,2016年,54頁。,但在后期的侦讯阶段中,他从中国受害者的控诉书中体会到受害者家属对他的仇恨,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暴虐和侵略统治的残忍。这使他联想到,如果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遭受外敌侵略、凌辱,自己会如何面对,由此产生了一种感情认同。真正使岛村三郎理解“认罪”之含义的,则是其爱子的意外死亡。丧子之痛使他体会到中国受害者们的痛苦及其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注]参见島村三郎:《中国から帰った戦犯》,166—168頁。
又如,入所初期,中国政府一系列人道主义待遇使原侵华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第110大队机关枪中队中尉中队长金井贞直产生了误解,以为自己是背井离乡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治安的“有功之臣”,接受人道主义待遇是理所应当的[注]《認罪~中国·撫順戦犯管理所の6年~》,NHKハイビジョン特集,2008年。。有些战犯彷徨绝望时,他还微笑着给大家“鼓励”,以至于战犯们一度将他奉为“豪杰”[注]鵜野晋太郎:《菊と日本刀》(下),9—14頁。。直到1954年底,大批战犯认罪结束、开始各种文体创作活动时,金井贞直仍旧迟迟没有检讨之意。促使金井贞直认罪反省的是其未婚妻1955年3月寄来的家书[注]1954年10月,李德全率中国红十字总会代表团访日,公布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名册》,战犯开始与家人建立通信联系。,信中介绍了日本被美国占领后的“苦难生活”,例如年轻女性为逃避美军凌辱,有的将头发剪短,有的把脸上涂黑。金井贞直无法容忍自己的家乡受到如此“践踏”,进而从对美国“侵略者”本能的仇恨中醒悟:自己正是在他人国土上肆意摧残、给他国人民带来伤害的侵略者。金井贞直就这样站在了受害者的立场上,推己及人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注]参见帰山則之:《生きている戦犯:金井貞直の「認罪」》,307頁。
此外,石田隆至和张宏波多年来坚持走访“中归联”成员,对其坦白承认战争罪行、重新认识战争责任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们指出:促使战犯大规模正式认罪的重要契机之一,是原侵华日军第39师团某中队长宫崎弘在管理所战犯全体大会上的坦白发言。宫崎弘声泪俱下地承认了自己在侵华战场上犯下的一件件残暴罪行,诚恳地表示愿意“接受任何惩罚”。这对战犯们造成了极大的触动。[注]参见石田隆至:《寛大さへの応答から戦争責任へ——ある元兵士の“終わりなき認罪”をめぐって》,《PRIME》第31号,2010年3月;《認罪~中国·撫順戦犯管理所の6年~》,NHKハイビジョン特集,2008年;絵鳩毅:《皇軍兵士、シベリア抑留、撫順戦犯管理所:カント学徒、再生の記》,266—275頁。
从上述案例看,真正促使战犯认罪的因素似乎是许多个性化的、带有偶然性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战犯管理所的思想教育反倒显得不那么突出。其实,不妨把新中国政府的教育改造比作一粒深深埋下的种子,之后的“顿悟”无论发生在中国还是日本,都是这粒种子结出了果实而已。周恩来曾说,20年之后才会知道我们做的决定是正确的[注]《認罪~中国·撫順戦犯管理所の6年~》,NHKハイビジョン特集,2008年。,大概也是这个意思。至于果实成熟的时间何以不同,是不是与原战犯的出身、职级、教育背景、生活经历等因素有关,能否从中挖掘出新中国教育改造战犯“效果”背后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关于“中归联”成员是否真诚认罪
近年来,中央档案馆公开了842名日本侵华战犯的笔供[注]参见《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1辑,中华书局,2015年;《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2辑,中华书局,2017年。其中第1辑共有50册,第2辑共有70册,全套图书将近63000页。,“中归联”成员在回忆中也经常提及自己所写的笔供。笔者认为,将“中归联”原战犯获释回国后的言行与其在中国写的笔供相对比,不失为一个观察这些人认罪是否深入、真诚的独到视角。
例如,金子安次回忆说,当年根本没有加害意识,认为在战场上是“奉命行事”,写的笔供只不过是给中国政府一个交代,日后中国政府可以以此向日本政府索要大量战争赔偿,算是对中国方面人道主义待遇的回报。的确如此,金子安次回国后在战争证言中提到了80次以上的性暴力犯罪[注]星徹:《私たちが中国でしたこと——中国帰還者連絡会の人びと》,緑風出版,2015年,122頁。,而在笔供中,他只轻描淡写地交代了四次[注]参见《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2辑(35),中华书局,2017年,第119—190页。。
1956年,金子安次踏上日本国土后,真正认识到中国政府是守信用、可信赖的。随着结婚生子,对妻女的挚爱之情使他终于站在了受害者的立场上反思自己的战争罪行,越发认识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到的东西是正确的,痛感幼年接受的灌输教育对自己影响之大。联系到本文的上一个问题,这应该是金子安次找回做“人”的感情之契机。他回忆道,教科书中天皇的神话以及大和民族的“优越”使他对军队无限憧憬,希望参军报国、出人头地,军队中非人的私刑和中国战场上残酷的“活人试胆”训练则泯灭了他的人性。他所在军队的“扫荡”实行的是“四光”政策——不仅要“杀光、烧光、抢光”,而且还要“毁光”,因为只有将“劣等的清国佬”斩尽杀绝,才是对天皇“尽忠”。[注]参见星徹:《私たちが中国でしたこと——中国帰還者連絡会の人びと》,111—127頁。
晚年的金子安次与另一位“中归联”成员铃木良雄不顾年迈,不惜放弃幸福生活,以战争亲历者的身份在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上作了从军“慰安妇”加害证言。日本军队在侵华战场上犯下无数难于启齿的丑恶罪行,然而,勇于站在国际法庭上作战争证言的,只有这两位年逾八旬的老人。面对检察官的提问,金子安次回答道:“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深刻认识到了中国人民有多么的痛苦。这种事情绝不可以再次发生。而现在能够阻止此类暴行再次发生的,只有在这个世上所剩无几的我们了。”[注]金子安治:《女性国際戦犯法廷における中帰連会員の証言:「慰安婦」は強姦防止に役立たなかった》,《中帰連(季刊)》第15号,2000年12月。
原本还有其他愿意作性犯罪证言演讲的“中归联”成员,但由于遭到家人强烈反对,妻子甚至以离婚相威胁,无奈之下,只好改作其他方面的证言[注]高橋哲郎:《なぜ「加害」を語るのか(座谈会发言)》,《中帰連(季刊)》第20号,2002年春。。然而,金子安次和铃木良雄表示,他们之所以毅然选择承认“最难以启齿”的性暴力犯罪,正是因为“没有人讲”。他们这代人“必须把战争的真实情况、侵略战争的真相留下来”。[注]鈴木良雄:《なぜ「加害」を語るのか(座谈会发言)》,《中帰連(季刊)》第20号,2002年春。
又如,作为原关东军司令部特殊情报队中尉中队长,小岛隆男进入战犯管理所时“根本不认为用刺刀挑死农民、砍他们的头、拷问是犯罪”,只是觉得“干的事情不好,一旦败露会遭到报复”,所以拒不认罪。晚年的小岛自我评价说,自己进入管理所的第一年“简直就是个无赖”。后来,他得知一名日本女孩在被驻日美军强奸后遍寻犯罪美军,由此意识到“谎言是掩盖不住的”,一旦暴露必定会受到严查,与其被动败露,不如主动坦白。在吴浩然的指导下,小岛隆男形成了认罪笔供。但他仍然没能认识到,自己是以罪犯之身被宽大释放的,而是只想着“可以回国了”,至于为什么被释放,全然没有考虑。[注]野田正彰:《戦争と罪責》,105—106、129頁。
回国后,小岛隆男结婚生子,儿子五岁时,一天夜里,他看着自己可爱的孩子,猛然想到1942年4月在中国战场上惨死在他手里的一个五岁男孩。之后,两个孩子重叠的影像困扰了他很多年。在当初的笔供中,小岛隆男只是笼统地记述了残忍杀害小男孩一家五口的过程。他写道,五个人排成一列后,自己命令一名士兵“将枪口贴在父亲的后背上,一枪将五人全部射杀,尸体放于原处离去”[注]《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2辑(92),中华书局,2017年,第148—149页。。这种笔供显然只是在记录一项战争行为,并无太多悔罪之意。其实那个五岁的孩子当天并没有死,第二天确认现场时,孩子还睁着眼睛怒视小岛隆男。当然,小岛隆男是不会让这个孩子继续活下去的……小岛隆男一直将这件事深藏心中,连家人也未曾告知,直至受到爱子之情的感召,才对这一罪行作出反省。此时已是事发50多年之后了,而且还是在学者引导下,他才痛苦地认罪反省。[注]参见野田正彰:《戦争と罪責》,133—139頁。
前文提过的日本学者野田正彰指出,中国方面要求战犯坦白、认罪,从根本上讲“仅仅是谋求战犯认清加害与被害的事实”[注]野田正彰:《戦争と罪責》,120—121頁。,许多“中归联”成员的回忆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注]在对日本战犯展开侦讯和认罪教育的过程中,管理所方面并未给出任何所谓的“提示”或“引导”,而是完全由战犯自主供认犯罪事实。参见《認罪~中国·撫順戦犯管理所の6年~》,NHKハイビジョン特集,2008年。。因此,在中国写下的笔供不能说明战犯们是否真的被改造好了。不过,若能像上面两个例子那样,将当初的笔供与回国后的证言相对比,就可以清楚地勾勒出“中归联”原战犯持续认罪反省的过程。一两个例子当然是不够的,系统整理“中归联”成员的战争证言应该是“中归联”历史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当然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无论多么困难,时间不等人,随着“中归联”成员陆续离世,其遗留的材料必然加速流失,搜集整理工作已经显得越发迫切和必要了。
回到认罪是否真诚的问题上来,铃木良雄曾对记者说:认罪不能止于在中国的笔供,而是要持续一生;这不是一次谢罪就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坚持谢罪[注]鈴木良雄:《戦場で強姦は日常茶飯事だった》,《中帰連(季刊)》第16号,2001年春。。其实不只铃木良雄,大部分“中归联”成员都表示,战犯管理所里的认罪只是一个初步的阶段,他们回国后才逐渐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认罪”。认罪学习并没有在抚顺、太原完成,那只是他们倾尽一生要做的“真正的认罪”的第一步。[注]星徹:《私たちが「受け継ぐ」べきこと》,《中帰連(季刊)》第20号,2002年春。
返回日本后,“中归联”原战犯大多回到籍贯所在地。尽管散居各地,他们却要面临同一个问题,那就是遭到日本特高课的长期跟踪监视。而且,获释归国时,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也已三十过半,多年的军队、监狱生涯使其严重脱离社会,许多人没能顺利找到工作。有的虽然谋得一份差事,却终因有过一段“赤色中国”经历或参加了“中归联”的“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而遭到解雇或被迫离职。[注]参见《認罪~中国·撫順戦犯管理所の6年~》,NHKハイビジョン特集,2008年;富永正三:《あるB·C級戦犯の戦後史——本当の戦争責任とは何か》,256頁;野田正彰:《戦争と罪責》,239頁。此外,除了少数“中归联”成员能够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外,更多的人则要面对亲属们的不理解,因为他们的确为家人带来了“压力”和“麻烦”[注]参见富永正三:《あるB·C級戦犯の戦後史——本当の戦争責任とは何か》,263頁。。
尽管阻力很大,许多“中归联”成员还是选择直面自己过去的罪行。他们尤其重视具体到个人的战争责任。曾任“中归联”会长的富永正三认为,应该是“执行者承担作为执行者的责任,在此基础上再追究命令者的责任”[注]富永正三:《あるB·C級戦犯の戦後史——本当の戦争責任とは何か》,239頁。。也就是说,“中归联”原战犯希望找到与自己直接相关的受害者,并当面谢罪。这当然是一个很有难度的目标,但真的有人做到了,例如三尾丰。1943年,时任关东军宪兵队大连黑石礁警务班长的三尾丰将从事抗日活动的王耀轩等四名中国人押送至731部队做人体试验。20世纪90年代,随着731部队罪证材料的公开,三尾丰将反战和平活动的重点转到了揭发731部队罪行方面。1997年10月,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中国受害者就731部队发动细菌战向日本政府索赔案,三尾丰作为加害者出庭作证,并呼吁道:“我们犯下了战争罪行。这是国家的责任,国家应当承担责任,进行谢罪并赔偿。”[注]参见《認罪の旅――731部隊と三尾豊の記録》,私家版,2000年,10、74—83頁。不仅如此,他还多次专程来中国寻找受害者家属,最终凭借真诚的谢罪态度得到了受害者王耀轩遗属王亦兵的谅解[注]王亦兵:《三尾豊さんの思い出》,《中帰連(季刊)》第30号,2004年秋。。在这一点上,三尾丰是“幸运的”,富永正三等更多的“中归联”成员则无法找到惨死在他们屠刀下的受害者,他们连跪地谢罪的对象都没有,只能将这终其一生无法抹去的痛苦和遗憾铭刻于其所修建的“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之上,永远树立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注]熊谷伸一郎:《富永会長へのことば》,《中帰連(季刊)》第20号,2002年春;《帰ってきた戦犯たちの後半生——中国帰還者連絡会の四〇年——》,717頁。。
“中归联”成员长期坚持认罪反省,时间之久,同样令人印象深刻。2015年夏,笔者和石田隆至对“山阴中归联”[注]2002年,“中归联”总部解散后,其山阴支部更名为“山阴中归联”。参见《自由発言(要約) 山陰支部 鹿田正夫氏》,《前へ前へ》第60号,2002年6月20日。成员进行走访调查。93岁高龄的上田胜善在得知笔者是中国人后,当即深深鞠躬行礼,声泪俱下地为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忏悔。他表示,感谢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使他们有了今天幸福的生活,而那些被他们残酷杀害的受害者却再也无法挽回生命,他们要用余生为“反战和平、日中友好”而努力奋斗。耄耋老人颤抖的声音和谢罪时的痛苦表情令笔者难以忘怀。“山阴中归联”的另外两位成员鹿田正夫、难波靖直等也曾以同样的方式向来访的中国学者张宏波表达感恩与谢罪之意[注]石田隆至:《寛大さへの応答から戦争責任へ——ある元兵士の“終わりなき認罪”をめぐって》,《PRIME》第31号,2010年3月。。同样年逾九旬的今田实夫至今仍在反思那场侵略战争,认为当年自己充当新兵教官也是一种间接的犯罪,因为接受他培训的士兵参加侵略战争,也会犯下战争罪行[注]参见石田隆至、周桂香采访今田实夫的记录,2015年7月。。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曾经受到新中国教育改造的战犯都能倾尽余生去感恩、谢罪与反省。1957年“中归联”成立时,成员包含了全部获释归国人员,但后来真正参加组织活动的不到一半[注]参见《帰ってきた戦犯たちの後半生——中国帰還者連絡会の四〇年——》,76、92頁。。也许是迫于各种压力,相当一部分人从此隐姓埋名;有的则根据具体情况,力所能及地参与一些活动;还有人忙于组建家庭、经营生活,直到退休后,经济和精力上有了余力,才开始投身“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另外有一些人由于住所比较偏远,虽然参与活动,但与组织联系得不多……[注]参见石田隆至、張宏波:《加害の語りと戦後日本社会(1) 「洗脳」言説を超えて加害認識を伝える——戦犯作家·平野零児の語りを通じて》,《戦争責任研究(季刊)》第72号,2011年夏。凡此种种,实在不能一概而论。在困难重重、大浪淘沙的情况下,那些有勇气和毅力坚持活动的“中归联”成员,应该是在真诚地认罪反省。
这些“中归联”成员之所以能够一生背负着对中国的感恩并坚持为自己的战争行为谢罪,既是为了报答中国政府和人民,完成对自己的精神救赎,同时也源于对亲人和祖国的热爱。他们经历过战争,深知战争意味着什么,希望中日之间、世界各民族之间能够世世代代永远和平、幸福地生活[注]若月金治:《戦争の時代に生まれ、侵略戦争に参加し、冷戦の時代を経て、平和共存の時代を生きる回想録》,私家版,1992年,185、245頁。,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希望日本能像德国那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人单力薄,终究没有形成气候,没能撼动日本的主流社会思潮,但他们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去讲述那段历史,希望让全世界知道“中归联”的存在[注]星徹:《私たちが中国でしたこと——中国帰還者連絡会の人びと》,160頁。,因为他们认为:“21世纪日本人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对过去的历史拥有正确的认识。”[注]山冈繁:《戦争証言》,講演原稿,1998年9月。他们担心,如果不坚持认罪,美化战争的声音会愈发强大,日本社会有可能一步步倒退至战前状态[注]石田隆至:《寛大さへの応答から戦争責任へ——ある元兵士の“終わりなき認罪”をめぐって》,《PRIME》第31号,2010年3月。。因此,无论多么艰难,都要继续下去,尤其要影响年轻人——多一个理解他们心情的日本年轻人,不就意味着少一个不理解的吗?
总之,在新中国政府人性化、理性化的教育下,日本战犯认识到了自己的战争责任,能够直面自己犯下的罪行,站在加害者的立场上反思侵华战争。无论是被判刑的还是被宽大释放的战犯,无一不认罪服法,千余战犯中仅有一名回国后翻供[注]参见《帰ってきた戦犯たちの後半生——中国帰還者連絡会の四〇年——》,120頁。,不少人终其一生认罪反省,甚至有人能够作为战争加害者与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实现和解,由仇人变成朋友。这些原战犯成立的“中归联”是战后日本唯一一个彻底反省战争责任的团体。如今,随着大部分“中归联”成员的离世,他们对战争的认识与反省、对和平的珍爱与追求已经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行为才更加难能可贵,他们的思想转变才更加真实可信,关于他们为什么能坚持到最后的研究也才更加意义深远。
五、关于“中归联”历史研究的史料
以上几题或许可以从不同侧面展现出“中归联”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乃至社会价值,希望笔者的介绍可以吸引更多学者尤其是懂日语的有识之士加入到这项研究中来。对于历史学而言,“研究未动,史料先行”,恰巧笔者与石田隆至、张宏波等组成了跨国合作的研究团队[注]2014年,大连理工大学聘请石田隆至为“海天学者”,自此开启了“中归联”历史研究的国际合作模式。几年来,双方精诚合作,优势互补,在本课题研究的基础资料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中归联”的资料搜集方面作了一些努力,算是对史料略知一二,所以在此作一点介绍,也算是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可以按图索骥的线索。
国内史料方面,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保存了关押日本战犯时的部分档案和“中归联”活动的部分资料。由于相关档案大多尚未公开,所以目前能够利用的主要是战犯管理所原工作人员的回忆录[注]前文注释中数次出现的《回忆改造战犯》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本。该书于2000年首次出版,名为《改造战犯纪实》。。具体来说,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金源出版了个人回忆录,其中涉及管理所对战犯的教育改造和“中归联”的一些活动[注]参见金源著,崔泽译:《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183—241页。;前文提过的张梦实也对管理所的工作作了简单回忆[注]参见张梦实:《白山黑水画人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35—145页。;在“中归联”原战犯回忆录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管教吴浩然,除有回忆文章被《回忆改造战犯》一书收录,并接受过日本记者新井利男的采访外,还留下了一份反映当年管教方针分歧的未刊手稿[注]即前文多次引用过的《我回忆战犯管理所的工作和斗争》一文。。此外,2007年前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下,李秉刚等学者对30余位管理所原工作人员作了口述史访谈。
还有一些“新型史料”也值得研究者注意。例如,国内一些媒体对“中归联”活动有过跟踪报道,留下了若干影像史料[注]例如1956年6月、7月和9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中国》等集中报道了新中国审理日本战犯的情况,以及受审战犯忏悔过去罪行,决心拥护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等情形。又如2015年8月,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与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五集纪录片《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首播。再如2017年8月,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纪录片《正义之剑——战后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揭秘》中的第五集“铸剑为犁”,介绍了“中归联”的一些情况。。又如,抚顺战犯管理所出版了一本画册,收录该所关押过的“中归联”成员岛亚坛、桧山高雄、熊谷清创作的版画、油画作品,内容均为作者在侵华战场上亲身经历、亲眼看见的场面[注]本课题团队成员承担了相关著作的编译工作。参见抚顺战犯管理所编:《罪行与宽待:原日本战犯反省绘画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15年。。
必须指出的是,相当数量反映新中国教育改造日本战犯以及“中归联”历史的原始资料仍然散存于相关当事人、家属或其他民间人士手中,亟待有关部门、各界学者加以搜集和整理。即便是那些存放在官方、半官方机构的档案,其保存状况也是值得忧虑的。
国外史料当然主要集中在日本,据不完全统计,有关“中归联”的文献至少有100余部[注]其中既有正式发行出版的,亦有自行印制、小范围交流的;既有“中归联”组织及其成员出版的,亦有与其他人合作出版或者由他人编辑制作的。,还有大量材料保存在2006年成立的民间组织“NPO中归联和平纪念馆”里,更多的日文史料则同样散存于民间,有待搜集整理。相关史料主要分为三类:
一是“中归联”以集体形式留下的材料。“中归联”成员的活动大多记录在所在支部的支部报里,支部报原本应该被送到总部并由后者收藏,总部则定期向全国成员发行会刊[注]“中归联”总部的会刊名为《前へ前へ》。1967年至1986年“中归联”分裂期间,两派之一的“正统”创办了自己的会刊。1986年“中归联”统一后,会刊也恢复统一发行,直至2002年总部解散。,对各地成员的活动进行归纳整理。二者相加,估计共有400余期。这对“中归联”历史研究而言,无疑是极其珍贵的史料。但是,无论支部还是总部,成员都是兼职的,文件传递不可能十分规范,而且总部自身运作也存在诸多困难,所以除了山阴支部的支部报因被岛根大学图书馆收藏而保存得非常齐全之外,“中归联”会刊和其他支部的支部报均不完整。笔者所在课题团队正在尽力搜集余下的支部报,但时间、精力、经费都很有限,尚且无法全部掌握。会刊和支部报是仅供内部交流的材料,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份公开刊物——为了与日本右翼势力展开论战,1997年6月起,成员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中归联”公开发行《中归联(季刊)》,至2002年4月总部解散时共出版了20期。随后,“中归联”的继承组织[注]“中归联”的“继承组织”是民间人士因认同“中归联”的精神而自发成立的,初期成员主要是原来一直随“中归联”活动的“赞助会员”,原“中归联”成员则作为“特殊会员”参与其中。“抚顺奇迹继承会”继续编辑出版该刊,至今为止又发行了40余期。
“中归联”还以集体名义出版了一些著作,其中的代表作是《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原日本战犯改造回忆录》(《私たちは中国で何をしたか——元日本人戦犯の記録》)和《战犯们回国的后半生——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四十年》(《帰ってきた戦犯たちの後半生——中国帰還者連絡会の四〇年——》)。前者详细记述了日本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生活情况和思想转变过程,后者介绍了“中归联”成员回国后40年的活动历程。“山阴中归联”联合其继承组织“继承山阴中归联之牵牛花会”自费印制《残留的风景:我们在湖北犯下的罪行——(抚顺战犯·第三十九师团将士的认罪)》(《残してきた風景:私たちが湖北省で犯したこと——(撫順戦犯·第三十九師団将兵の認罪)》),讲述了侵华日军第39师团在湖北犯下的战争罪行。除此之外,“中归联”历次全国大会也留下了音像资料。
二是“中归联”成员个人的回忆著作。获释回国当年,即有原战犯出版回忆著作,介绍自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或太原战犯管理所的亲身经历[注]参见野上今朝雄等:《戦犯》,三一書房,1956年;平野零児:《人間改造——私は中国の戦犯であった》,三一書房,1956年。。但或许因为“中归联”成员大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整体上看,此类回忆录的数量并不算多。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活跃的那些“中归联”成员,当年基本都是年轻的基层官兵,没有多少文化[注]参见鵜野晋太郎:《菊と日本刀》(下),41頁;吴浩然:《我回忆战犯管理所的工作和斗争》,未刊手稿,1987年8月。,不擅长著书立说,写的东西比较质朴,很难形成系统。尽管如此,他们在日本各地作证言演讲,还是留下了不少音像和纸质资料。此外,90年代时,应吴浩然号召,“中归联”成员还为抚顺战犯管理所撰写了100余篇回忆录,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简单的回顾和总结。
也有若干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归联”成员留下了回忆录或口述史。其中,岛村三郎的《中国归来的战犯》(《中国から帰った戦犯》)和富永正三的《一个B、C级战犯的战后史——真正的战争责任是什么》(《あるB·C級戦犯の戦後史——本当の戦争責任とは何か》)细致地描写了自己感情和认识的变化过程,较有代表性。稻叶绩的《战斗到底——被残留在山西省的士兵们》(《終わりなき闘い:山西省に残留させられた兵士たち》)从自身经历出发,揭露了日本政府掩盖战争罪行的行为,向年轻一代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与罪恶。
还有几名“中归联”成员家属完成了类似当事人回忆录的著作。例如,岛亚坛的遗属回忆了他利用版画揭露战争真相、追求和平的经历[注]2005年6月,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道主义精神的感谢,岛亚坛将30幅反映日本侵华战争的版画赠送给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2006年,罹患癌症的岛亚坛拖着病体坚持作画,在得知赠送给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作品被顺利接收后的第二天安然去世。参见當原ツヨ編:《島亜壇――日中友好と平和を貫いた生涯》,私家版,2008年,13頁。。上坪铁一的女儿伊东秀子在《父亲的遗言:战争使人“疯狂”》(《父の遺言:戦争は人間を「狂気」にする》)一书中回忆了父亲获释回国后对战争的反思、自己阅读父亲笔供的感想,以及对父亲认罪过程的认识。
三是学者、新闻工作者等对“中归联”成员的访谈材料。石田隆至将绘鸠毅的“人生三部曲”[注]绘鸠毅的“人生三部曲”包括《撫順戦犯管理所の6年——監獄が自己改造の学校であった》(撫順の奇蹟を受け継ぐ会神奈川支部,2010年)、《シベリア抑留の5年~強制労働、慢性飢餓、極寒、人間不信の世界~》(撫順の奇蹟を受け継ぐ会神奈川支部,2010年)和《皇軍兵士の4年――カント学徒戦犯への墜つへーー》(撫順奇蹟を受け継ぐ会神奈川支部,2011年)。整理成《皇军士兵、西伯利亚扣押、抚顺战犯管理所:康德学子再生记》(《皇軍兵士、シベリア抑留、撫順戦犯管理所:カント学徒、再生の記》)一书。绘鸠毅在书中回忆了自己由一名东京帝国大学学生沦为战争罪犯的经历,以及接受教育、转变思想的过程,并将中国的战犯管理所称作“自我改造的学校”。石田隆至还与张宏波一起,在野田正彰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归联”成员进行调查访问,并据此发表系列文章,考察了“中归联”成员获释回国后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不断加深,以及展开认罪反省的情况[注]参见石田隆至、張宏波:《加害の語りと戦後日本社会(1) 「洗脳」言説を超えて加害認識を伝える——戦犯作家·平野零児の語りを通じて》,《戦争責任研究(季刊)》第72号,2011年夏;石田隆至、張宏波:《加害の語りと戦後日本社会(2) 「棄兵」たちの戦後史(上) 「認罪」経験の二つの捉え方》,《戦争責任研究(季刊)》第73号,2011年秋;石田隆至、張宏波:《加害の語りと戦後日本社会(3) 「棄兵」たちの戦後史(下) 「加害者」である「被害者」として》,《戦争責任研究(季刊)》第75号,2012年春;石田隆至、張宏波:《加害の語りと戦後日本社会(4) 戦争を推進した社会の転換へむけて(上) 山陰支部における「相互援助」を中心に》,《戦争責任研究(季刊)》第76号,2012年夏;石田隆至、張宏波:《加害の語りと戦後日本社会(5) 戦争を推進した社会の転換へむけて(下) 「相互援助」が可能にした「加害証言」》,《戦争責任研究(季刊)》第78号,2012年冬。。新井利男对参与战犯移交、管教和处理的相关中国当事人展开采访,留下了目前为止最为完整的中方当事人回忆史料集——《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的证言》(《中国撫順戦犯管理所職員の証言》)。星彻对多名“中归联”成员进行口述史采访,写出了《我们在中国干的事情——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成员》(《私たちが中国でしたこと——中国帰還者連絡会の人びと》)一书。
此外,日本各界人士编写了多部与“中归联”有关的资料集,例如日中友好协会编《证言——来自二十世纪的遗言:年轻人问询的侵略战争》(《証言——二○世紀からの遺言:若者が問う侵略戦争》),以及前文引用过的《认罪的旅程——731部队与三尾丰的记录》(《認罪の旅——731部隊と三尾豊の記録》)。日本媒体几十年来始终关注“中归联”,其对“中归联”活动及其反响的报道和评论也是一种重要的史料类型。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这对任何一个史学题目来说都是确定无疑的,“中归联”课题亦不例外。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对日方“中归联”史料的利用还很不够,因而很难将“中归联”历史研究推进到原战犯的认罪反省及其回国后的言行、思想层面,即便有所涉及,也只能似是而非地泛泛而谈[注]国内对“中归联”原战犯的研究多集中在1956年的沈阳、太原审判和对大批战犯的宽大处理上;至于对日本战犯教育改造的研究,则主要关注过程和意义,较少涉及战犯们从抗拒到认罪,再到积极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的心理变化。参见徐志民:《新中国审判与改造日本战犯研究综述》,《澳门研究》2016年第4期。。日本学者方面,由于立场观点各异,更是难免良莠不齐。这样一来,两国学界在“中归联”问题上竟然只能各行其是,几乎找不到共同点。“中归联”的历史蕴含着宽容、忏悔、和解等许多关乎中日两国共同命运的意涵,原本不应如此默默无闻。
语言当然是一个障碍,可是日语也不能算是极其小众的语种,或许还是因为了解“中归联”的学者不够多吧。希望本文能够吸引更多同仁加入研究“中归联”历史的行列中来,与笔者所在团队一起,把这个课题做起来、做出色、做下去,向中国、向日本、向全世界讲述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我们愿意同所有真正有志于此的学者分享多年来搜集到的珍贵史料。此外,“中归联”的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其实是超越学术层面的,学者不能画地为牢,仅仅局限于学术研究,而是应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有关部门则更应该有所作为。
结 语
“中归联”原战犯在“皇国史观”的教育下成长,满怀着“八纮一宇”“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狂妄理想,为完成“圣战”的“使命”而来到中国。他们曾视中国人民如草芥,在侵华战争中“烧光、杀光、抢光”,犯下无数滔天罪行。然而,信念坚定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和耐心细致的教育,竟然使这些嗜血成性的杀人恶魔认识了真理,恢复了理性。在此基础上,为了中日两国的持久和平与两国人民的长久幸福,中国政府最终宽大处理了这批日本战犯。
获释回国后,这些原来的战犯成立了“中归联”。他们中的许多人由衷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恩情,对战争罪行发自内心地谢罪,实现了彻底的转变。面对生活、工作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这些“中归联”成员没有放弃信念,而是基于对生命、对和平的挚爱,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质朴的方式为中日和平友好而努力,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2002年4月,由于成员年事已高,“中归联”东京总部宣布解散,但其山阴支部拒绝解散,并更名为“山阴中归联”,誓言“坚持到最后一个人”[注]石田隆至:《寛大さへの応答から戦争責任へ——ある元兵士の“終わりなき認罪”をめぐって》,《PRIME》第31号,2010年3月;今井雅巳:《「中帰連平和記念館」開館一〇周年に寄せて~会館までの歩み~》,《中帰連(季刊)》第61号,2016年12月。。如今,“山阴中归联”成员的平均年龄已超过96岁,但他们仍旧坚持不懈,并努力培养接班人。“中归联”总部解散时,日本民间人士还成立了继承组织。原“中归联”成员遗属和一些有识之士也以多种方式传承着“中归联”的精神,致力于“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
曾经满怀国仇家恨的管教人员尊重并引导战犯们重新做人,曾经罪行累累的原战犯倾尽余生反对战争,曾经在战场上刺刀见红的敌人最终携起手来为和平而共同奋斗——这就是“中归联”独特甚至不乏悲壮的历史。中日双方当事人都希望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告诉全世界,希望人类不再有战争,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子孙后代永远幸福。不夸张地说,“中归联”的历史为各对立乃至敌对民族、国家间的和解与共存提供了典范。而同这段历史的价值相比,现有的史料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工作无疑亟须加紧和改进。
抗日战争的硝烟早已在70余载岁月中随风消逝,日本战犯获释距今也有60多年之久,在沧海桑田般的巨变面前,这1000余名原战犯的人生轨迹似乎只是历史淡淡的划痕,不值一提。可是,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似乎永远无法抚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原本掌握着这些战犯“生杀大权”的新中国政府,却最终作出了宽大处理的决定?这些人配得上我们的宽容吗?本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远远谈不上充分,但愿有更多学者给出自己理性、平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