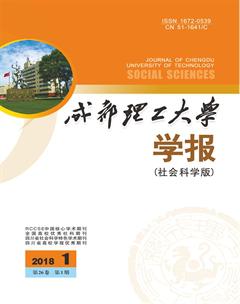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我国《刑法》第二十八条重构论おお
刘昊
摘要:
立法实效以立法实用为前提,实用之标准核心在于“规范的可适用性”。以裁判文书网为检索样本可以发现,我国《刑法》第二十八条关于胁从犯规定的适用率很低,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传统刑法理论将胁从犯理解为“独立共犯种类”,由此导致认定胁从犯过程中胁从犯所起到的作用认定和胁迫认定缺乏明确标准,进而模糊了胁从犯与紧急避险等阻却事由的界限。因此,有必要对以往“胁从犯废除论者”的观点予以辩证式的考察与借鉴,以期提高胁迫事实之于刑法的司法实用性。
关键词:胁从犯;实用性;废除论;情节
中图分类号: D924.13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8)01002307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11月10日,刘某伙同岳某、陈某、冯某等人,对宜宾富豪章某进行绑架勒索,并以喷辣椒水、捆绑手脚、捂嘴蒙眼等方式将其困在一出租房内,并用自制手枪威胁章某在2016年3月前缴纳赎金,章某迫于威胁被迫同意。为确保章某能按时缴纳赎金,四绑匪威逼章某对吉某某以绳索勒颈的方式将其杀害,后才将章某放回。2015年11月11日凌晨4时许,章某向警方报案,中午1时许,四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2016年9月29日,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绑架罪分别判處被告人刘某、岳某死刑,判处陈某、冯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中,检察院自始没有将章某列为犯罪嫌疑人,法院也未对章某的行为进行评价。
无独有偶,与“宜宾富豪杀人案”相似的还有“检察官被胁迫强奸杀害女大学生案”(1)“昆明男子胁迫坐台小姐杀人案”(2),前者以检察官自始未被处理为结局,后者则是检察院对两女子作出了相对不起诉的决定。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由此说明“坐台小姐杀人案”中的被胁迫杀人行为应当被定性为情节轻微。但是,《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的刑罚轻重的顺序采降序排列的方式,足以说明故意杀人罪社会危害性之大,以胁迫之事实能否抵消故意杀人罪的社会危害性,最终被评价为犯罪情节轻微,不无疑问。笔者认为,依据《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同样可以实现对该类案件的量刑均衡,并能够以法院判决的方式对行为进行妥当的评价。法院之所以对该类案件均未以胁从犯规定论处,可能与胁从犯条款的适用情况存在着联系。
二、实用标准之确立
德国法学之历史发展经过了“理想的概念法学”到“经验的利益法学”再到“暂时性终点的价值法学”。从概念法学到利益法学是范式之转化,从利益法学到价值法学则是知识之传承,前两者虽存在着方法论与认知论上的重大差异,但如今价值法学所否定的是概念法学唯概念马首是瞻的做法,并不否认概念之于法学回归社会的重要性,而概念融入社会因素的进程则深层次体现的是法学朝“逻辑与经验”二元认知论与方法论的方向发展,这种折衷的趋势反映了大陆法理论与英美法理论的融合,因为英美法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经验,价值目标是实用,大陆法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概念,价值目标是完善[1],以实用性标准衡量立法质量正是大陆法系合理吸收英美法系优势的完善的过程,也是立法取得实效的重要前提。
起初,概念法学企图以构建的方式达致法学体系的成立,建构之方法目的在于法律规范的关联性形成,由此阶层式的概念体系得以成立,概念的层级使体系能够通过演绎的方法产生下位概念,由此涵摄变化多端的事实。概念法学代表人物耶林曾赋予“建构方法”这种法律技术以两个任务:简化法律及确保法律实用性[2],但概念法学的实用性内涵在于司法不是人为的适用与创造过程,而是机器式的生产,只要规范能够通过概念演绎的方式进行现实地处理就不去过多地考虑结果的妥当性。不过,最终理想幻化成泡影,仅注重规范的自我生成而忽视个案的正义,导致了越来越不能接受的结论,同时,规范的自我生成也对法的安定性产生一定的冲击,利益法学随即在能满足个案的正义的优势下取代了概念法学的统领地位。
利益法学派认为,不论是立法抑或司法都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需要对尽可能想到的利益进行比较。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人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与利益的广泛性,必然对衡量过程造成阻碍。为此,利益法学派代表人物海克虽然认为立法者所要保护的利益纷繁万千,但是着重强调了生活利益、实用性利益以及描述利益对利益法学规范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实用性利益系指立法者不能只是在规范当中进行实质的判断,还需照应到它公布的规范是否能有效率的适用,为了使法律适用能够比较容易,就不要把法律效果直接系诸在一个很难确定的利益状态之上,而应当寻找一个可以检验的代替性特征。例如,有关行为能力的成年时间应当是直接规定一个年龄而不是依靠法官去依个人精神的成熟度来判断[2]244-245。可是,利益法学派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只注重规范的利益衡量,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评价标准,这就很难处理立法当中的价值观念变迁问题,是依旧还是从新,而这也自始决定了利益法学走向价值法学的宿命。值得注意的是,从利益法学发展到价值法学,并不是价值法学代替了利益法学,而是对利益法学的衣钵传承,因此利益法学规范形成的三种重要利益并不为当今学者所遗弃,反而贯彻于现有的理论当中。
的确,按照德国刑法学者罗克辛的观点:体系性思考可以减轻审查案件的难度,可以给法律适用提供前提条件,可以使得法律更为简明和更好的操作性[3],罗克辛所强调的即是体系的建构成功应以实用性为重要标准,即使是简化法律,也是为法律实用性做铺垫,若费尽心血地立法却不能得以适用于社会,这可谓之极大的资源浪费。回归至法教义学体系,胁从犯概念的提出虽具有我国独特的历史与政策依据,但长期以来,一方面,胁从犯的研究从未在法教义学之内大展拳脚,反倒是以遭受学者的批判为主要特征;另一方面,实务上对于胁从犯条款的适用也极为有限,严重影响了立法的实效性。可以说,以实用性标准来判断胁从犯的存废之路更具有现实意义。
三、胁从犯适用受限的实体法原因
我国传统观点认为,胁从犯成立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受到他人胁迫而参加犯罪;二是在共同犯罪中起的作用比较小。据此,胁从犯之成立与量刑均有赖于“胁迫程度”与“作用大小”的认定。而事实上,两个要素的认定,司法并无具体规范文件的出台,也就是说,《刑法》第二十八条的适用完全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从笔者在裁判文书网与北大法宝案例检索库检索胁从犯的适用情况来看,初步结论是《刑法》第二十八条的适用处在被搁浅的状态,即使是适用,能被认定的也只在少数(3)。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虽不乏司法体制的不合理设定因素,但笔者认为,将胁从犯理解为一种独立共犯种类也是值得关注的因素。
(一)胁从犯作为独立的共犯种类
一般认为,我国《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于共犯章节之下,胁从犯应被视为独立共犯种类。所以,有关胁从犯刑罚的减免规定必须以构成共同犯罪为前提,对于存在胁迫事实但并非共同犯罪的情况,不能以胁从犯条款直接适用,而关于胁迫能否作为量刑情节,也存在认识的差异。其次,胁从犯的成立需要参照主犯与从犯的作用来认定,这就要求胁从犯存在的场合以三人共同犯罪为常态,一旦发生两人共同犯罪的情况,由于较小作用的认定缺乏与次要作用的比较,将会出现胁从犯与从犯难以分清的情况,而胁从犯与从犯的量刑基准是不一样的。最后,我国传统不区分“违法与责任的共犯体系”势必导致共犯成立范围的限缩,如以未成年人起主要作用的共同犯罪,会以“主犯”不符合犯罪的主体要件而否认共同犯罪的成立,由此限缩了胁从犯的成立。
(二)作用认定与胁迫认定缺乏明确标准
诚如前述所言,胁从犯是“在他人威胁下不完全自愿地参加共同犯罪,并在共同犯罪中起较小作用的人”,这是对刑法进行体系性解释的合理结论。一方面,“较小作用”作何理解尚存疑问,引发了关于胁从犯能否转化为主犯与从犯的长期争论(4)[4];更有不少学者认为,作用大小是人为补充的客观特征[5]。另一方面,确认胁迫事实的存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首先,需要确定的是胁迫认定的主体标准,是采用主观认定方式还是客观认定方式,进而追问造成的身体强制与精神强制在何种程度上才能够被认定为胁迫;其次,若需要考虑个人主观因素,那必然将胁迫解构为诸多要素而逐一分析,如胁迫的内容、程度、对象、胁迫的现实性(被害人过错)、胁迫的紧迫性、胁迫的限度(小于或等于)、案件适用范围等[6]。相较于从犯的次要作用认定,胁从犯的成立能够容纳诸多评价性因素,在个罪特征不一的情况下,胁迫事实的认定缺乏统一的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当事人普遍存在取证困难,所搜集的样本之中多以当事人的口供为唯一证据。综合来看,在查询的案例中,鲜有案例中的行为人被认定为胁从犯。
(三)与紧急避险等阻却事由缺乏明确的界限
由于紧急避险、不可抗力以及意外事件的构成要件之中也存在被胁迫事实,同时胁从犯之中常存在行为人为保护A利益而牺牲B利益的情况,当对胁从犯的胁迫程度与利益的相当性认识出现分歧时,就容易混淆胁从犯与各类阻却事由的界限,造成罪与非罪的判断失误。例如,行为人被迫去毁坏他人贵重财物以保全自己不受伤害,其中对于财物与健康价值的比较(胁迫的限度)就决定了是否构成紧急避险,而个人的承受能力(胁迫对象)与作用大小则决定是否构成压迫性的强制,进而能否成立不可抗力。
事实上,这种判断的失误,与我国长期采取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不无关系。因为在我国传统耦合式的犯罪构成理论之下,一体化的判断方式导致只能做出罪与非罪的结论,而无法就胁从犯、紧急避险与不可抗力做出细致的区分。因此,学者们倾向于以德日阶层式犯罪构成理论为分析框架,以被迫行为的法律效果为标准将其分为无责性被迫行为、免责性被迫行为和减责性被迫行为[7],并有学者认为被迫行为与期待可能性理论存在天然的契合,应当据此减免责任[8]。也可以看出,期待可能性为“宜宾富豪杀人案”的减免责任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至少就《德国刑法典》第三十五条而言),但在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环境之下,期待可能性能否成为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而被适用,则尚存疑问。综上,我们不禁要质疑,胁从犯是否真的被需要?
四、对胁从犯的批判观点及评析
对于上述质问,通说认为应当将胁从犯解释为独立的共犯种类,而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支持应当废除胁从犯的条款。实际上,废除论者多以“改造论”面貌出现,因为胁迫之于犯罪,具有定罪与量刑的意义,没有学者会全盘否认胁迫进入刑法的视线。归纳已有的文献观点,废除论者多以“共犯分类不符合逻辑”“胁从犯可能起主要或次要作用”“胁从犯的主观恶性较小”“政策依据的检讨、刑法条文依据缺乏”等否定胁从犯作为独立的共犯类型。
(一)逻辑之于体系的重要程度
有的学者认为:“理论上的胁从犯不可能是依据共同犯罪的作用标准进行分类的产物,否则便违背了逻辑关系的‘子项不相容理论”[6]。为此,我们必须追问,共犯分类的逻辑是否影响体系的完备与运用?笔者认为,首先,胁从犯存在的不符合逻辑原理问题在于作用分类法中“主要与次要”之外仍存在着“较次要”。若以主从是一对完整矛盾体而不能存在第三种可能,势必会没有胁从犯的空间,但事实上若认可胁从犯起次要作用,即胁从犯只是从犯具有胁迫情节而已,仍可能会依据刑法当中普遍存在的类原理——如类法益与具体法益、特殊法条与一般法条——认可胁从犯存在,但也面临着如此划分是否合理的质疑;其次,法教义学的本质在于完整概念体系的建立,实现体系内在演绎以包罗万象,其对层次与要素的划分必然寻求逻辑的契合,但法教义学的始祖——概念法学——亦成为法学的枷锁,往往使法律与社会正义脱節[2]17。为此作为例证的是,耶林从概念法学到利益法学的重大历史转变,深刻影响整个德国法学走向,而更为贴切的例证是耶林时期的德国刑法学者李斯特为跨越“李斯特鸿沟”做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法教义学固然要坚持内部体系的自主完善,但也应当以问题为导向实现个案的正义。相比于胁从犯是否在主要和次要作用之外另设较小作用,我国共犯体系缺乏的反倒是关于量刑情节更为细致的规定,应当认为较小作用的存在是有利于实现罪刑均衡的。最后,即使承认在主要与次要作用之外存在较小作用有违基本逻辑的妥当性,但很明显,这种分类上造成的逻辑矛盾应当区分于“因采用此分类而造成结论上的矛盾”。申言之,我们并不会因为共犯当中有了胁从犯而造成共犯体系的适用产生逻辑上难以自洽的结论。事实上,造成较小作用为学者们攻讦的主要原因是较小作用的认定困难,极易混淆了次要作用与较小作用,并非逻辑上的分类错误。
(二)政策依据的检讨
胁从犯之规定来源于“首恶必惩,胁从不问”的具体刑事政策,在毛泽东同志所论述的历史文献中有固定的根源,藉此,学者从两方面对胁从犯的刑事政策依据进行反思:(1)胁从犯设立时的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而如今社会情势与犯罪状况发生变化,现行的基本刑事政策是“宽严相济”,刑法典应当对此做出反映,在共同犯罪的刑事立法问题上也应当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1]113。(2)由于最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人员的失误,将毛泽东同志手迹中“十”和“力”字组合的简化“协”字写成了“胁”字,导致了今天我们对刑法第二十八条理解的错误,并以此产生了关于胁从犯的“较小作用”“小于从犯的作用”“处罚轻于从犯”等理论观点[9]。不可否认,胁从犯的来源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既然政策具有灵活性,奠基于之上的刑法规定自然也应当随社会形势的改变而完善。但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不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否定,而是对其的继承与发展,着重体现区别对待的核心思想与刑法宽宥处罚的一面。而胁从犯的规定恰是基于区别对待与宽宥处罚的刑事政策而产生,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但不否定、甚至为胁从犯提供了政策依据。至于是否有必要深究胁从犯的历史依据,诚如前述所言,笔者更倾向于当关注胁从犯存在的政策基础——区别对待与宽宥——是否被妥善地继承,以及是否能在实践取得良好的立法效果。
(三)胁从犯有客观定罪之嫌
有观点认为,“在‘胁从犯的情形中,犯罪动机( 或者说大部分犯罪动机) 是由诱因所引起的,因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十分微小,或者几乎没有,将这种状态下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未免有客观归罪之嫌,与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相冲突”[10]。然而笔者认为,首先该论者说法并不准确,司法实务界常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中国概念——“主观恶性”( 凶狠恶毒的性格) ,它不等于刑法中的“罪过”概念,而是犯罪学元素,它与三阶层犯罪论中的“责任”概念相似,但两者并不相同[11]。主观恶性亦不是针对具体行为时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态度,而是由该种心理态度所驱使,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所表现出来的犯罪人的思想品质,它是一种既存的实然心理事实,也就是说,是一种客观实在事实,应当属于已然的犯罪范畴[12],而据此将胁从犯的主观罪过弱化至无,乃至得出胁从犯的刑罚处置会产生交叉感染的风险,干脆用非刑罚措施(包括民事以及行政处罚)来预防,以体现刑法的谦抑性,未免矫枉过正。
更重要的是,论者并未区分个人“没有去做选择的能力”还是“很难去做选择”的情形,欠缺前者则无罪过,欠缺后者则是当事人缺失机会去选择[13]。动机的善恶与否,并不能直接否认罪过的存在,个人的意志自由对应于“去做选择的能力”,而胁迫的存在造成的是“行为人很难去做选择”。在后者的情形下,实则是责任的核心内容,即在行为人很难选择去遵循合法的方式之时,即使行为人是故意而为之,也不应当对其加以责难,这一点与英美法学者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如英美法学者认为,即使将“被迫”视为犯罪的可宽恕事由(5),承认行为人对其所为负有责任,我们也不能对其称赞抑或责备,而应更倾向于道德中立[14]。这种评价结果在“正当化事由与可宽恕事由”之外开辟了第三种情形,即“行为是坏的,且行为人是有责任的,但在特定情形下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以至于不被处罚”[15]。这种观点渐渐为英美学者所接受,不仅在故意杀人罪的情形下如此[15],在其他犯罪的情况下,也应在量刑环节考虑被迫犯罪的困境,而不应执着于对责任的探讨[16]。由此看出,以相关罪名对被迫杀人行为进行认定,进而在量刑阶段考虑胁迫的情节,从而判处免除刑罚的做法在英美已有倡导。
因此,关于处理类似于“宜宾富豪杀人案”的极端情形,虽然我国传统犯罪构成要件明显存在着局限[17],但必须承认,被迫实施的事实影响的并不是个人基于意志自由的选择能力(可做选择的能力),而是影响其选择的机会(环境限制了选择)(6),出于自保而杀人与出于泄愤而杀人主要是选择机会的差异,即犯罪动机的差异,进而影响行为人的可谴责性程度。在我国现有的理论背景与框架之下,出于对行为人行为的评价动因,考虑到行为人不具有特殊预防的可能与法律不强人所难的法律原理,采取英美法系学者在量刑阶段考虑胁迫事实的做法是较好的路径,利用胁从犯“免除处罚”的规定,由此程序法上酌定不起诉也成为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必须以责任刑和预防刑对应于刑罚目的,将目的与动机置于预防刑情节的考虑当中,因为“如果将目的与动机确定为责任刑的情节,那么,在目的非法、动机卑鄙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责任刑的上限提高,因而导致刑罚较重;反之,如果将目的与动机确定为预防刑的情节,那么,即使是目的非法、动机卑鄙,也不会导致责任刑的上限提高,因而导致刑罚缓和。”[18] 藉此,虽然胁从犯在主客观统一原则之下构成犯罪并无多大阻碍,在其动机与目的并非构成要件的情况下,认定动机与目的是预防刑的情节因素,则可以在责任刑之下,进行量刑调整。
五、《刑法》第二十八条的解释论困境与胁从犯立法重构的具体路径
(一)《刑法》第二十八条的解释论困境
经过上述对胁从犯废除论观点的正本清源之后,并不能当然认定通说的合理性,只要继续将《刑法》第二十八条解释为胁从犯并置于共犯章节,就一定无法避免将胁从犯的认定限制在共犯的范围内,由此造成司法适用率低下。所以,对该条款的解释论集中走向了认可《刑法》第二十八条是作为量刑规则存在的,由此摆脱构成胁从犯所需要的成立要件。但是,必須面临的是胁迫情节的广泛适用带来的罪刑不均衡的风险。可以说,通说将胁从犯视为独立共犯种类,并将其设置为“应当减轻、免除处罚”的规定,就是考虑到胁从犯的成立必须以较小的作用和被胁迫犯罪的事实为条件,由此区别于主犯、从犯的量刑规定。而若将该条款理解为量刑情节,则势必导致该条款是以规定胁迫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条款,由此作用的限定将不复存在,主犯亦可能适用该条款,结果却有可能是主犯的刑罚轻于从犯(7),由此造成从犯与主犯的罪刑不均衡。这实际上就陷入了胁从犯解释论上的困境,将之视为共犯类型将导致司法适用率的偏低,将之视为情节类型又可能导致罪刑不均衡,目前还无它类解释。而化解前者出路在于将该条款移出共犯,化解后者出路在于将“应当”改为“可以”;而要一劳永逸,则既需要将该条款移出共犯章节,也需要对条款的表述进行改变。
(二)胁从犯立法重构的具体路径
胁迫事实对于刑法的价值,催生了诸多对胁从犯条款的改造方案,主要为两类:一是废除论[10]55;二是将该条款解释为量刑的规定。具体有如下可能:(1)将该条款予以废除,以胁迫为酌定量刑情节适用于司法(实为形式上废除);(2)需要置于共犯章节,改为法定量刑情节;(3)置于共犯章节,进一步将“应当”改为“可以”[4]61;(4)移出共犯章节,改为法定量刑情节[19]。
依笔者所见,废除论忽视了胁迫作为独立情节的价值,不可足取。而名为废除论者,实际上仍然重视被胁迫事实的存在意义,并将其并入其他条款,如柳忠卫教授:“取消《刑法》第二十八条关于胁从犯的规定,将其合并到《刑法》第十六条当中。”[1]114能否将胁迫视为酌定情节来考虑,这与通说将胁从犯视为独立共犯种类的看法并不矛盾,但这并不是最好的改革方案。因为即使将《刑法》第二十八条按通说解释,也并不否认胁迫对于量刑过程的重要意义,《刑法》当中随处可见胁迫情形的存在,总则中紧急避险之“迫不得已”,不可抗力之“难以抗拒”,分则中敲诈勒索之“陷于恐惧”,抢劫与抢夺之区分于“暴力程度”等,皆是将胁迫作为定罪与量刑的情节考虑。而真正的障碍在于酌定量刑情节需要司法经验的长期积累,且适用酌定情节可能致使裁量权过大,也不利于实现个案之间的均衡。要实现胁迫情节的酌定化,需要实务部门长期的经验总结与规范化。酌定情节的规范化,可以避免法官的不敢适用与滥用的情形,相比于法定情节的方式更具灵活性。不过,也可以预估,以个案和个罪为中心的规范性文件并不能为“胁迫”这个上位概念划分一个统一具体的适用标准,整个胁迫情节的适用规范化进程仍需要长期的司法经验予以补足。
而将《刑法》第二十八条视为法定量刑情节并无太大障碍,也可以避免缺乏形式法律依据的质疑,因为《刑法》第二十八条处在共犯章节,胁迫与较小作用的功能即旨在满足量刑的需求,将两者结合并将其视为独立共犯种类只是可供选择的解释路径之一。当把该条款移出共犯章节,起到的效果是扩大胁迫情节的适用范围,不过依旧需要面临将《刑法》第二十八条解释为法定量刑情节导致的罪刑不均衡问题。所以,仍有必要进一步将《刑法》第二十八条的量刑规则由“应当”改为“可以”;同时,基于实用性考虑,可以增加从轻规定,一劳永逸地解决罪刑均衡问题,也可以依据不同的胁迫类型而个别化的量刑。
综上,笔者认为胁从犯的立法规定重构应包含三个步骤:(1)理解为法定量刑情节;(2)“应当”改为“可以”并增加从轻处罚的规定;(3)移出共犯章节置于第四章。条文可以表述为: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可以按照它的犯罪情节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所以,成文刑法比立法者聪明,解释者比成文刑法聪明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解释的实质化与灵活化带来的裨益也为刑法频繁修正做了折中的努力,当解释面临着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寻求立法途径是迫不得已的选择,由此催生出新的解释思路与实务规范。诚如笔者提出的改造路径,并非没有顾虑,如依旧可能存在法官的滥用,也依旧面临着裁量权的过大问题,由此可能造成新的不均衡。不过应当承认的是,并不存在完美的解决方式,提出的思路需要相关的附属规范与制度进行保障执行,纵使是不对胁从犯改造,也能够通过提高法官的自身素养加以解决适用率偏低的问题,而我们自始至终不过是在寻求立法的帕累托最优而已。
注释:
(1) 案件发生在2008年10月的河南省平顶山市,由石某构成的8名犯罪团伙先后绑架了于区检察院工作的检察官夏某与女大学生王某,为达到勒索夏某1000万的目的,石某等人以蒙眼、绳索勒脖的方式,迫使夏某强奸该女大学生,并于强奸之后威逼夏某用绳索勒死女大学生,团伙对整个过程进行录像留存作为“证据”,并以此达到敲诈勒索的目的。最后,夏某并未被立案侦查。
(2) 案件发生在2007年3月,昆明市警方接到两女子报案,声称她们杀死了一名女子,并叙述了整个杀人过程的前因后果:犯罪分子袁某与周某以抽三张扑克(两张9,一張K)的形式,让三名坐台小姐抽,宣称“谁抽到老K,谁就得死。”方某不幸抽到老K,在袁某和周某威逼下,报警的两名女子将方某杀害。事后查明,袁某和周某本打算抓几个卖淫女并对她们进行控制,迫使其卖淫,为达到小姐听从自己使唤的目的,两犯罪嫌疑人策划了此“杀人案”,并对整个过程记录。
(3)笔者于2017年2月28日进行的数据取样,首先是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检索库进行,在“全文”范围内以“精确”匹配方式输入“胁从犯”进行检索,所得刑事样本数1518个,进而为了查询《刑法》第二十八条被法院的适用情况,在结果中以全文范围内输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八条”,所得结果为0,而基本上未被法院采纳的说辞是以“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为由。其次,在裁判文书网上,以“胁从犯——刑事案由——一审”的关键词顺序得到样本数798个,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八条”为附加关键词在结果中搜索,得到样本4个,经阅读只有“(2010)舟岱刑初字第73号方军、赵华等强迫交易罪案”“(2015)石大刑初字第315号颜士明、张某贩卖毒品案”“(2016)鲁0285刑初440号曲永涛、王建文等故意伤害罪案”三个案件适用了胁从犯规定。
(4) 笔者此处就未被深入讨论的问题进行说理与纠偏,限于篇幅,不过多牵涉已为现有学者对通说——“胁从犯”是否可能会转化为主犯或从犯以及胁从犯是否具有刑法依据——作出的辩护。参见阎二鹏.胁从犯体系定位之困惑与出路——一个中国问题的思索[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2,(2):57-61.
(5)英美刑法的犯罪构成分为实际意义上的犯罪要件和诉讼意义上的犯罪要件。一般认为,实际意义上的犯罪要件即犯罪本体要件,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为第一层次。犯罪定义之外的责任充足要件(或称抗辩事由)是诉讼意义上的犯罪要件,为第二层次。本文所言的正当化事由与宽恕事由采取的是道格拉斯·胡萨克《刑法哲学》一书中的称谓,为第二层次的犯罪要件。
(6)大陆法系也存有相同的看法,即将心理事实与对心理事实评价作出区分,以德国癖马案为标志,将传统以心理事实为责任内容的心理责任论推向了基于心理事实而对行为人进行谴责的规范责任论,并开创了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司法适用。其中,选择的能力即是事实意义上对认识与意志,而选择机会是对行为人作出选择的环境作出评价,当不能期待行为人作出合法选择的情况下,不谴责行为人。
(7)在同案中,法院一般会以主犯应当判处重于从犯的刑罚而限制胁迫情节的适用。在各区域/各法院之间,就相似案件,则可能会导致A案主犯轻于B案从犯的情形,造成同案不同判以及罪刑严重失衡等问题。
参考文献:
[1]柳忠卫.论被迫行为的刑法规制及其体系性地位的重构[J].中国法学,2010,(2):103-114.
[2]吴从周.概念法学、利益法学与价值法学:探索一部民法方法论的演变史[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5.
[3][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第一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27.
[4]阎二鹏.胁从犯体系定位之困惑与出路——一个中国问题的思索[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2,(2):57-61.
[5]赵微.论胁从犯不是法定的独立共犯人[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2):23-28.
[6]谷永超.论英美刑法中胁迫的理论基础——兼论对我国胁从犯规定的借鉴意义[J].政法学刊,2014,(1):11-15.
[7]魏汉涛.被迫行为的性质及其体系性地位——一个批判性分析[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80-89.
[8]陈明华,吴文志.我国刑法中的紧急避险与被迫行为关系之多维检视[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法律科学),2006,(5):85-90.
[9]郑厚勇.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共犯种类——胁从犯——胁从犯的刑法依据和政策依据质疑[J].河北法学,2005,(4):140-143.
[10]李欣.胁从犯存废论[J].北方法学,2014,(3):48-55.
[11]储槐植,闫雨.刑事一体化践行[J].中国法学,2013,(2):139-146.
[12]游伟,陆建红.人身危险性在我国刑法中的功能定位[J].法学研究,2004,(4):3-14.
[13]Michael Gorr.Duress and Culpability[J].Criminal Justice Ethics,2000,(19):3-16.
[14]Claire O.Finkelstein.Duress:A Philosophical Account Of The Defense In Law[J]. Arizona Law Review,1995,(37):251-283.
[15]Joshua T. Carback.Death Before Dishonor——Judging Duress As Affirmative Defense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ccording To Lex Naturalis[J].Indonesian Journal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2016,(3):651-702.
[16]Ray Ryan.Resolving The Duress Dilemma:Guidance From The House Of Lords[J].Northern Ireland Legal Quarterly,2005,(56):421-430.
[17]柏浪涛.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下受胁迫行为的体系性分析[J].政治与法律,2011,(2):82-90.
[18]张明楷.责任主义与量刑原理——以点的理论为中心[J].法学研究,2010,(5):128-145.
[19]任海涛.论胁从犯之应然理论定位[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4):121-124.
Abstract:The practical effect of legislation is based on the practicality of legislation, and the core of practical standard lies in “the applicability of norms”. Take the case system of Supreme Peoples Court as analytical example,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application rate of Article 28 of the Penal Code is very low.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raditional criminal theory regards coerced accomplice as an “independent accomplice species”, which led to the lack of an clear standard of the role of coerced accomplice and the degree of dures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ituting coerced accomplice.Thus blurred the boundaries among coerced accomplice and necessity etc.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idactically examine and learn from the viewpoints that advocate to abolish and improve the statue of coerced accomplice ,which can help improve the judicial applicability of the coerced facts in criminal law.
Key words: coerced accomplice;utility; abolition theory; plots
編辑:鲁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