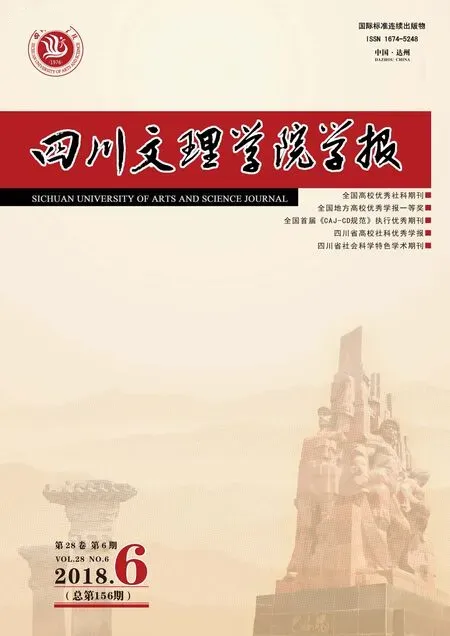从鸟神崇拜到道教审美视域下飞鸟形象的演变
孙鑫蓉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0)
鸟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在历史文化的演变过程中它最初是作为图腾来崇拜的。从审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讲,鸟神崇拜对后世的文学艺术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影响,不难发现在后世的文学艺术中时常能找到鸟这一文化原型,不过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学样式以及不同的审美视域下,鸟又有着不同的形象体现和审美内涵,本文试着探讨从最初的鸟神崇拜视域下的鸟形象到道教审美视域下鸟形象的演变,从这一演变的过程中看到中国美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发展变化。
一、鸟崇拜和鸟神话下的飞鸟形象
由于图腾崇拜的时代缺少文字的记载,我们只能从现存下来的文物遗址以及有文字以后的文献资料去印证先民的图腾崇拜。华夏民族之所以有鸟崇拜这一说法和现今出土的大量有关于鸟的文物遗址和文献资料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今较早的文献记载有《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1]这是一种典型的鸟图腾崇拜。除了文献记载以外,现如今出土保留下来的文物遗迹也可以印证先民的鸟崇拜,目前来看,最早的出土文献是距今大概7000年的“双鸟负日”骨雕和“双鸟朝阳”牙雕,“中间雕刻着五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外围上端刻出炽热的火焰状,以象征太阳的光芒,两侧各有一振翅欲飞的双鸟作圆眼、钩喙、伸脖昂首相望之态。”[2]这一文物突出刻画了双鸟形象,同样表达了对鸟的崇拜,虽然不同于玄鸟生商的意义,但却有着另外的崇拜意义,鸟长着人类没有的羽翼可以自由在天空中翱翔,因而被认为是沟通天地的使者,这种原始崇拜表达了对自由、光明、生命的向往和追求。
现今最早有关鸟神话的文献当属《山海经》,《山海经》中讲了大量有关于鸟的神话故事,以至于有学者认为:“细读《山海经》,全书讲的都是鸟的故事”。[3]除了文献的记载以外,相关的出土文献也证实了这一点。距今大约4740年左右的四川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了一株有着“一龙十鸟”(一说九鸟)的青铜神树,被学术界命名为“太阳神树”,生动再现了《山海经·海外东经》所记的“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的情形。[4]虽然遗址是鸟的形象而文献中是太阳的说法,但是在那个时代鸟和太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鸟的崇拜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太阳神的崇拜,鸟可以无限接近太阳因而具有神的性质。学者唐世贵认为:“三星堆出土的诸多青铜鸟首是鱼凫蜀王的图腾像,它迎合了《山海经》中约23种动物的1种;鱼凫、开明两代蜀王皆以《山海经》的神兽为其部落图腾的,并以此作为部落名称。”[5]由此来看,《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和原始先民的鸟神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在图腾崇拜的基础上才会有后来的神话故事。朱狄在《原始文化研究》一书对图腾崇拜在审美发生学的意义上的影响做出了具体分析,他认为:“这种影响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实践上的,图腾信仰直接引起了一系列从属于这种信仰的艺术形式的发生或对已经发生的某些艺术形式进行规范化”。[6]细读《山海经》便会发现《山海经》其实便是从属于鸟图腾崇拜的艺术形式的产物,《山海经》多处写到了飞鸟形象,例如《山海经·南山经》:“有鸟焉,其状如雞,而三首三目六足三翼”,[7]4“有鸟焉,其状如,而白首三足人面”;[7]10《山海经·西山经》:“其鸟如鴖,其状如翠(翠似燕,而绀色也),而赤喙,可以御火”,[7]16“有鸟焉,其状如鸮,青羽赤喙人舌,能言”,[7]22“有鸟焉,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见则天下大水”。[7]28
像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从这里可以发现《山海经》里的鸟形象和我们今天看到的鸟形象有着很大的差异,其中最明显的特点是带着人的想象和情感色彩后的变形鸟,虽然每一种鸟在具体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异,但是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充分受到了图腾崇拜的心里基础和事实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具有神性的鸟形象,尤其突出的是人鸟结合半人半鸟的形象,由此来看,在鸟崇拜和鸟神话的时代,鸟的形象和原始崇拜巫术信仰密不可分,单从外形来看,这些鸟都不是自然界正常的鸟类,从审美愉悦的角度来看,这些鸟形象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审美愉悦,而是从一个部落的政治统治、社会生活、图腾崇拜、巫术信仰等角度去诠释它的意义,此刻的审美状态还处于朦胧的阶段,那么这种朦胧状态是如何一步一步明朗化的呢?接下来通过探讨庄子逍遥游世界里的飞鸟形象以窥探审美状态的逐渐明朗化。
二、庄子逍遥游世界里的飞鸟形象
庄子《逍遥游》开篇便讲到了鲲化为鹏的故事,并且庄子笔下的鹏是要从北冥飞向南冥的,从这一转化思想以及向南飞的思想可以看出庄子哲学思想的传统根源。我们从图腾崇拜的审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庄子的思想,便可以理解庄子为什么一开始就讲到了鲲化为鹏的故事,并且鹏还要迁徙到南冥。
鲲化为鹏这一“大化”思想表达了庄子对自由生命的向往与追求,这和原始的鸟图腾崇拜有着非常相似的思维模式,为什么这样说呢?北冥中的鲲在深渊中也可以自由自在的遨游,但是庄子为什么要它转化为鹏呢?这和我们前面讲到的“双鸟朝阳”类似的鸟神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鸟儿有着人类没有的羽翼,能够在天空中自由翱翔,天上的太阳在先民的认识思维中也是神的存在,鸟儿在天空中飞翔就可以接近太阳神。从先民思维模式中的太阳神和鸟神的结合来看,对自由生命的追求从人类诞生以来就成了亘古不变的话题,更重要的是这种自由始终都包含着身体自由和精神自由两部分,对身体自由的追求主要表现在希望生命可以被神眷顾而长久,即便生命不在了也可以转化为另外一种形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从历史来看这种思想影响是深远的,从庄子到后来的道教都是十分注重身心自由的。在庄子的逍遥游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先民们身体自由和精神自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诚然,北冥中的鲲可以不必扶摇而上,它在北冥的深水中也可以身心自由,但是这里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吗?庄子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庄子看来首先必须实现身体的自由然后才能实现精神的自由,身体必须在自然界中无所待的自由翱翔才能达到精神上的与天地合一,因而在庄子的逍遥游世界里身体自由是基础,也是最根本的追求,实现了身体自由自然便可以与天地合一进而实现精神自由,这样来看庄子开篇就提到的“大化”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这种“化”的思想是庄子哲学的基础,因为有“化”的思想所以继之才有庄子的齐物论、庄周梦蝶等思想。王博先生在论及“化”字时,认为:“鲲化为鹏,正是对自己的一种超越,化是一种象征,一种遗忘和丧失自己的象征,化也就有了超乎形体之变的意义和象征”。[8]对于前半部分笔者是比较认同的,“化”是一种超越一种象征,但是结合前面的鸟神崇拜的实质内涵,笔者认为这里的“化”是强调和重视自我的象征,通过“化”实现了生命的新生和永恒,是对生命长久和自由的追求。
以“化”的思想为基础,庄子构建起了自己的逍遥游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鹏的形象具体是怎样的呢?《逍遥游》中有两处写到了鹏的形象。其一:“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9]1其二:“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9]4这两处同时强调了鹏的大,尤其突出了羽翼的大。在前面我们谈到了《山海经》鸟的形象,突出的特点便是人兽结合的变异鸟,庄子在描写鸟的形象时,一方面受到了《山海经》的影响,其中第二处的句式上明显带有《山海经》的描述口吻,另一方面庄子又为什么要单独强调鸟的“大”呢?这里可以理解为是从图腾崇拜向审美状态逐步明朗化的开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一个典型的审美范畴,“大”在图腾崇拜的基础上产生并且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包含了道德和善的观念,因为这时的人们已经从原始部落发展到了奴隶社会,社会的文明程度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包含了道德、善和美的结合。先看儒家讲的“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10]这里的“大”和道德伦理完美结合,突出了儒家伦理美的特点。老庄也讲“大”,但是相比儒家伦理美,老庄更崇尚自然无为的美。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9]156这里的思想和前面的大化境界如出一辙,同样在强调无为无不为的合道境界,可以看出庄子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内在统一性。所以在庄子逍遥游的世界里,先是讲到了鲲化为鹏的故事,可以看到庄子对先民鸟神崇拜思想的继承;接着又具体讲到了鹏这一飞鸟形象,突出强调了鹏的“大”,可以看出庄子思想在图腾崇拜思想基础上的创新,庄子的创新使得图腾崇拜这一蒙昧的审美状态逐渐明朗化,后世的美学思想在庄子思想基础上一步一步丰富发展起来。
三、秦汉神仙信仰里的飞鸟形象
在谈论飞鸟形象的演变过程中,秦汉时期的神仙信仰思想对飞鸟形象又做了进一步的影响,促进了飞鸟形象一步一步向飞鸟意向的审美状态过渡转变。
在谈论飞鸟形象之前我们先要明确神仙信仰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神仙信仰?首先是神仙信仰这一概念的界定,神仙以及神仙信仰的结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最开始神仙一词是分开来使用的。《说文解字》分别解释神仙为:“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从示,申声。”[11]8仙:“僊,长生僊去。”[11]167这样来看神和仙的对象是不同的,神的对象没有确定性而是包罗万象,仙的对象则具体到人。《礼记》也这样解释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12]《释名》讲到:“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13]第一次将神和仙合在一起来使用的是班固。他在《汉书·艺文志》中讲到:“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迁之文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14]这里的境界和庄子逍遥游的境界有相通的地方,主要强调保持生命的本真,使生命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下。近代学者牟钟鉴、张践在《中国宗教通史》中将神仙定义为:“其一形如常人而能长生不死,其二逍遥自在又神通广大。”[15]关于信仰的解释《辞海》中这样说到:“信仰,人们对某种理念、思想、学说极其信服,并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16]由此来看,神仙信仰可以理解为对长生不死、自由飞升的一种极度相信并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这种观念以达到长生不死、飞天成仙。
从神仙信仰的内涵来看,这一概念在先民们神的概念上有了新的发展,其中鲜明地突出了对自我的关注和追求,这也是为什么会产生神仙信仰的主要原因之一。秦汉时代是历史上大统一的时代,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促使人们开始对自我的关注和追求,尤其是拥有权力的上层统治者,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迷信长生不死的秦始皇和汉武帝。《博物志》记载道:“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乃供帐九华殿以侍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云车而至于殿西,南面东向,头上戴玉胜,青气郁郁如云。有三青鸟,如鸟大,使侍母旁。”[17]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追问神仙信仰有什么依据使得统治者为之深信不疑甚至亲自实践呢?要理解这一点必须结合神仙信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首先是神仙信仰的理论基础,从先民神的观念发展到神仙观念的过程中道家的思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庄子的思想,庄子“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人类如何才能从感性文化和智性文化造成的生命分裂与冲突中解脱出来,使人能过一种真正自由而快乐的生活。这个要求,使他在生命世界里的荒原里开辟了一条精神超越的大道”。[18]庄子所开辟的精神超越的大道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大化”境界,即从鲲化为大鹏在天空中自由翱翔无限接近神从而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庄子的这一思想是后来的神仙信仰的直接理论基础。除了“大化”的思想之外,庄子在逍遥游的世界里还真正描写了神仙:“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9]7-8神仙信仰里的神仙便是在庄子对神仙描写的基础上的更进一步扩大化和丰富化。除了神仙信仰的理论基础外,秦汉为什么如此迷信这一说法还要和当时的现实环境联系起来,秦汉结束了春秋战国纷纶战争的时代,第一次实现了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稳定社会相较繁荣从而促使了人们对自身的关注和追求,尤其是统治者希望能够长生不死永保自己的基业,也是因为人对自身的更多关注和社会的更进一步发展使得巫师的社会地位受到严重的跌落,不甘于碌碌无为的巫师们充分抓住了统治者的心理期望,趁机借助于老庄思想的理论基础炮制了一套迎合统治者心里期望的学说即神仙信仰,神仙信仰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这一思想对秦汉时期的文学艺术影响深远,飞鸟的形象也因为神仙信仰的渗入而进一步丰富化,突出了秦汉时代的审美特色。《仙赋》:“乃骖驾青龙,赤腾为历,躇玄厉之擢嶵,有似乎鸾凤之翔飞,集于胶葛之宇,泰山之台,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19]将鸾凤置于神仙世界中,作为一种仙鸟的代表在描述。除了汉赋中有大量的飞鸟形象的描写,汉乐府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如《清调曲·董逃行》:“百鸟集来如烟,山兽纷纶,麟辟邪其端,鹍鸡声鸣”。[20]将百鸟群集的场面描写成烟,一方面突出了鸟的轻盈、灵动,另一方面也象征了仙境幽远缥缈的画面。从这些飞鸟形象来看,都带上了仙鸟的特征,形象较神话故事里的鸟更可爱轻盈,突出了仙境的幽远宁静美好。在此基础上,东汉末年形成的道教一方面吸收了秦汉以来的神仙思想,另一方面又在宗教组织的形式上加以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神仙理论,飞鸟形象也在道教独特的审美视域下完成了从审美形象到审美意象的转变,至此以后飞鸟便成为文学上的一种常见意象即艺术形象。
四、道教审美视域下的飞鸟形象
道教作为一种宗教组织在东汉末年正式成立,以老庄道的哲学思想和秦汉以来的神仙信仰观念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道教此刻更强调宗教内容,庄子美学思想中的“大美”带上了浓重的宗教色彩,秦汉以来的神仙信仰思想在审美中越来越突出,从神仙信仰下的长生不死到追求个体生命精神的完善,既注重生命的长生又开始关注个体精神的完善,最终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社会意义。道教理论大家葛洪曾说过:“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物之大宗也。眇眇乎其深也,故称微焉;綿邈乎其远也,故称秒焉……故玄之所在,其乐无穷。”[21]这里的玄既有老庄哲学中“道”的基础,同时也是道教理论中的“道”。这里的“玄”包含了大、深、微、远、秒等众多审美内涵,正好体现了道家美学思想向道教审美思想转变的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道教的审美思想最终强调了它的审美落脚点——乐,这里的乐实际是道——乐,即体道、悟道、修道而达到的长生不死、精神完美的境界,但是应该注意这里的乐并不是针对当时信仰道教的下层普通百姓,能够有这种审美体验的必定是当时信仰神仙道教的社会中上层阶级和落魄的知识分子。赵沛霖先生在《从郭璞的神仙道教信仰看他的〈游仙诗〉》一文中也曾说到:“神仙道教不但满足了士族大户、王公贵族延续享乐生活的欲求,而且也迎合了中下层知识分子摆脱道德危机,寻找精神寄托的需要。”[22]
既然道教的核心思想是“神仙”,那么道教的美学思想也必然围绕着神仙思想而展开,突出表现为对神仙理想之美的描述赞美和向往。 在道教这一独特的审美理想下,和神仙理想有关的文学题材游仙诗也兴盛繁荣起来,在游仙诗中飞鸟形象成功完成了文学意象的转变。在谈论飞鸟形象的转变之前,本文有必要对游仙文学以及游仙诗作一界定,游仙诗作为游仙文学的一种,在魏晋唐以来得到繁荣发展,这和道教的兴盛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唐代的游仙诗十分盛行,据初步统计,魏晋的游仙诗保存至今的大约有一百多首,但是到了唐代游仙诗就达到三百多首,唐代将道教作为自己的国教,称自己为老子的后裔。关于游仙题材的创作有史料记载的有《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到“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23]《仙真人诗》今已佚亡,不过从秦始皇积极寻仙的历史记载可以推测该诗应该是描写寻仙 、访仙、仙人之乐等一类的,到了魏晋以后神仙道教正式成立,有关于神仙世界的描写迅速增多,文学中主要的代表就是游仙诗,这个时候的游仙诗和以前的游仙诗有什么不同呢?钟嵘《诗品》评郭璞《游仙诗》:“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凛咏怀,非列仙之趣也”,[24]李善在《文选》卷二十一郭璞《游仙诗七首》注中说:“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例景,饵玉玄都”,[25]从较早的评价来看,游仙诗主要是言志抒发胸中的失意和记录游仙途中的美景和乐趣。魏晋以前有关游仙题材的描写主要是仙人仙境,魏晋以来道教正式成立以后,道教审美思想中的世俗化、政治伦理化色彩对于审美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而情感的表达和寄托也越来越突出,这也是道教的审美思想和以前的审美思想的差异,唐代游仙诗所表现出来的审美世俗化和政治伦理化色彩更加突出。吴筠《游仙诗》二十四首中有两首写到了飞鸟:“欲超洞阳界,试鉴丹极表。赤帝跃火龙,炎官控朱鸟。导我升绛府,长驱出天杪。”[26]5671“大空含常明,八外无隐障。鸾凤有逸翮,泠然恣飘飏。寥寥唯玄虚,至乐在神王。”[27]5672朱鸟本是神话故事中南方的神,炎官是神话故事中的火神,这里将神话故事中的朱鸟变成了神仙世界里的仙鸟,是引导凡人成仙的使者。鸾凤在神话故事中也多次出现过,不过这里仍然是将其置于神仙世界中,用“逸”“泠然”“飘飏”等词来描写,突出了仙鸟的轻盈、飘逸超脱和灵动等特征,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仙境的喜爱和向往。好道的李白许多游仙诗中也有飞鸟形象,其中《古有所思》:“西来青鸟东飞去,愿寄一书谢麻姑”,[27]这首游仙诗作于天宝后李白被放还归山,从创作的背景来看,正是李白仕途失意之作,带有明显的政治内容和人生感慨。青鸟在神话故事中是西王母的使者,这里不单是西王母的使者,而是整个仙界的使者,麻姑据《神仙传》记载是一位美貌的仙姑,李白通过青鸟向麻姑表示歉意不能去往仙界,实际表达了现实的不顺人生的失意,青鸟寄托了作者的感情,同时也包含了对青鸟的喜爱向往之情,青鸟成了人可以信赖的亲密伙伴。曹唐的大小游仙诗在唐代也具有典型的道教审美特色。《汉武帝将候西王母下降》:“昆仑凝想最高峰,王母来乘五色龙。歌听紫鸾犹飘缈,语来青鸟许从容。”[26]4373-4374《张硕重寄杜兰香》:“碧落香销兰露秋,星河无梦夜悠悠。灵妃不降三清贺,仙鹤空成万古愁。”[26]4375两首诗中的飞鸟首先都是仙鸟形象,其次这里都用到了拟人的手法,把人的情感带入到鸟的身上,多了情感寄托的美。
从鸟神崇拜到道教审美视域下飞鸟形象经过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从最初的人兽结合到轻盈灵巧的仙鸟,从审美思想的朦胧阶段到逐渐明朗化再到审美特殊化,鸟形象从图腾崇拜逐渐演变成文学艺术中的鸟意象,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兼与赵沛霖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