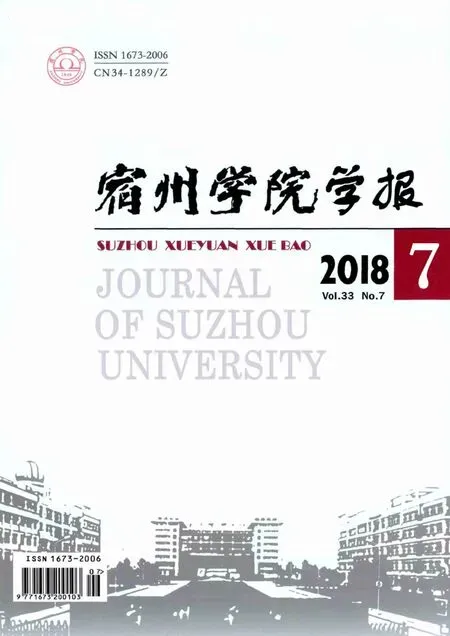社会环境变迁视域下五河民歌的形成
朱家席
蚌埠学院文学与教育学院,蚌埠,233030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民歌、渔歌或山歌的产生,且能自成系统,最终形成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艺术形态,多源于其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地缘辽阔,人烟稀少,劳动者引吭高歌以叙其事抒其情,如陕北的信天游,“这个山头高来那个山低,瞧不见哥哥在哪里”(陕北信天游《想哥哥》)正是其写照。五河地居平原,位于淮河中下游段,水陆交通便利。与前述的民歌、渔歌或山歌多产生于封闭区域截然相反,五河民歌最终定型于五河而不是淮阴或淮南,自有其道理。《宋史·地理志》:“(五河)有浍、潼、沱、漴、淮五河,故名。”五河沿淮河向东未几,邻京杭大运河、洪泽湖,因水路交通发达,明清时期人烟辐辏,商贾云集,众多驳杂的人群带来了艺术文化的碰撞。五河民歌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1458年(明天顺二年)所修县志。同时,五河也是历史上“楚歌”的发源地之一,淮河流域连年饱受水患、战乱,民间艺人乃至于寻常百姓依靠“唱小调”“排小戏”“打花鼓”等糊口谋生,促成“南腔北调”的形成。由于统治者的爱好和身体力行,移民事件也对五河地区的音乐、娱乐风俗习惯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五河民歌的传播具有明显的融会贯通特色。
目前,学界在区域文化研究中往往以区域定位作为个案进行相对孤立的挖掘、分析,其目的无疑是为了凸显该地域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的厚重。然而,文化或文艺形式相通性因素太多,在相当广阔的区域内,都有类似的艺术形态存在,大同而小异。因此,考察五河民歌的产生,不能脱离它所生存的地域历史沿革。南宋咸淳七年(1271)始置五河县,属淮北东路淮安军。明洪武四年(1371)属临濠府,洪武六年(1373)九月改属中立府,洪武七年(1374)八月改属凤阳府。清初属凤阳府。雍正二年(1724)升泗州为直隶州,五河改属泗州。“中华民国”元年(1912)直属安徽省,三年(1914)五月隶属于安徽省淮泗道,十六年(1927)直属安徽省,二十一年(1932)属安徽省第六行政督察区,抗日战争时期属淮北苏皖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泗五灵凤县。1949年改泗五灵凤县为五河县,属皖北行署江淮第二行政公署,后几经改隶,1983年7月1日改属蚌埠市。自明清以降,五河县域没有脱离“大凤阳”(凤阳府)的概念,五河民歌的前世今生注定要与凤阳歌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洪武七年(1374)八月五河改属凤阳府,府属所辖区域不断变化,最多的时候为12州28县,明弘治年间5州13县渐趋稳定。在此意义上,论及五河民歌的形成,不可不涉及上述地区。而对五河民歌的历史考察,又着重于小调的研究,区别于凤阳歌或花鼓调。
1 交通便利加快文化交流碰撞
现代五河民歌扬名于五河县小溪镇,新中国成立前隶属凤阳县(其中东部蒋庄村属盱眙县),地处五河县最南端,淮河南畔,依山傍水,交通便利,104国道纵贯全镇。穿镇而过的026县道,之前则是连接嘉山县(现为明光市)潘村等地的交通要道。淮河由大柳巷折而向南,流入洪泽湖,因此这条三角淤积平原上的古道商贸通畅,人烟辐辏,经济繁庶。附近的大柳巷、朱顶、潘村、古沛、大溪河、小溪河、沱湖、临北回族乡等地,五河民歌都广为盛行,且笼统以五河民歌称之。由于五河自古水路通畅,南北文化交流频繁,五河民歌流行的区域也在不断扩展,淮河中、下游两省十几个县、市都有流传,甚至波及山东省部分县、市。
五河以淮、浍、漴、潼、沱5条大河汇集而名,漴潼河水系包括北淝河、澥河、浍河、沱河、石梁河、漴河、潼河等,浍河、沱河在五河城北相汇,石梁河出天井湖,一路由漴河自五河入淮,五河位于淮河中下游南北运口附近, 以浮山峡扼淮河东流入海,东承运河导漕运交通南北,因地处水运枢纽而逐渐聚居成镇,“舟车鳞集,冠盖喧阗,两河市肆,栉比数十里不绝,北负大河,南邻运河,淮南扼塞以此为最。”(《乾隆淮安府志》卷五·城池)中运河之间的北淝河、澥河、包浍河、沱河、新汴河、奎濉河、徐洪河,横跨河南商丘、安徽宿州、淮北、蚌埠和江苏徐州、宿迁等3省、6地市,由西北—东南流向汇入淮河经洪泽湖入江海。
黄河夺淮以前,淮河独流入海,尾闾畅通,水利通达,物阜民丰,所以有“走千走万,不离淮河两岸”之说。隋朝为了统一天下,“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隋书·高祖纪》),藉此攻伐陈,实质上则沟通了长江和淮河的航运。隋炀帝大业元年(605)三月,“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万,开通济渠”(《资治通鉴·隋纪四》),沟通洛阳经成皋、中牟、开封、商丘、永城、宿县、灵璧至盱眙入淮河,从而形成了长江、淮河、黄河等水系的勾连畅行,促进了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一时之间,扬州成为生活富庶、繁华辐辏的代名词,南朝宋人殷芸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即为当时的写照。
北宋漕运分四路向京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集运,江、淮钱粮日用,由江南入淮水,经汴水入京,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淮南路,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两浙路)的漕粮、纲运,均由该水路运往开封,“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宋人张方平说:“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在这条路线上,五河扼其咽喉,成为必经之地。《武林旧事》中记载:“元夕舞队之村田乐即此。江、浙间,杂扮诸色人跳舞,失其意;江北犹存旧风。”宋金元争战之际,淮河一度成为界河,其地理位置愈发重要,随着大量移民的文化迁移,各种文学艺术样式相互交流加剧,在南北交融中不断吸收着各地养分,慢慢走向完善成熟。
明清以降,北京、成都,漕运成为封建王朝极其重要的生命线,江南粮米钱财悉由此道,运河作为漕运的载体,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淮河流域位于全国之中,水利资源极其丰富,五河水系发达,淮河经此独流入海,贯通东西,其位置仍不可忽视。交通的便利带来商业贸易的兴盛,文化消费产业也因之崛起,民间商业的繁荣发展,茶楼酒肆的星罗棋布,使得一些民歌小调,以卖唱艺人为载体,由南北东西辐辏于五河,由五河走向全国各地。
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五河处于几大流域文化的交汇之处,淮河流域文化、运河流域文化、黄河流域文化均对五河区域文化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反言之,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来看,区域文化之间的影响与交流并非是定向的,淮河流域文化研究虽然起步较晚,目前研究成果也并不多见,但不代表这种文化就一定落后于长江、黄河流域,甚至可以说,黄河、淮河、长江同时名列“四渎”,它们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因此,五河民歌的形成和发展是多元流域文化的产物,分析五河民歌要注意针对不同文化现象进行区域文化比较辨析。
根据周玉波的研究,有明一代,民歌势力呈从弱到强、由北到南推进痕迹,嘉靖、隆庆间,《寄生草》《罗江怨》《桐城歌》《银纽丝》逐渐兴起,且影响渐及两淮以及江南,北地民歌开始渗透南方地区。嘉靖、万历年间,南北真正合流。由上述内容可知,交通便利加快了文化交流碰撞,五河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地跨南北,通江达海,民歌的传播具备了优质的基因而逐渐孕育壮大[1]。杨栋先生曾专门就“山坡羊”一调进行考证,认为其源出北曲,本应是一首北地牧歌,始名为“山坡里羊”,在关汉卿时代由文人接手创作,于是有“山坡羊”之简名与“苏武持节”之雅名。最早采用此调入杂剧的是关氏同时人杨显之,较早用于散曲的应是陈草庵, 亦与关氏同时。南戏《张协状元》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此二人,其中所用“山坡羊”由北曲传入,是北曲南化的一个变体[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时尚小令》:“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则以《闹五更》小调的风靡一时为合流的标志。五河民歌中至今仍保存了大量以“闹五更”为题材的小调,如《五更疼郎》《五更情》《五更盼情郎》《五更盼郎归》等。再如,明代冯梦龙《山歌》中有系列《送郎》歌谣:
《送郎》送郎送到五里墩,再送五里当以程。本待送郎三十里,鞋弓袜小步难行。断肠人送断肠人。(之一)
《送郎》郎上孤舟妾依楼,东风吹水送行舟。老天若有留郎意,一夜西风水倒流。五拜拈香三扣头。(之二)
《但逢佳节》雄鸡啼罢渐星稀。梦醒巫山郎要归。留郎不住。任郎早回。送郎执手。问郎后期。(郎道、姐呀、)你有心时我有意。但逢佳节约重陪。[3]
清代民歌承其余绪,在《霓裳续谱》《白雪遗音》等集子中此类送别、惜别的曲子屡见不鲜,清代民歌《禁令》: “既有真心和我好,再不许你耍开交,再不许你人面前儿胡厮闹,再不许你嫌这山低来望那山高,再不许你见了好的又把槽来跳”,写尽女子对情人的依恋。清方浚颐(子箴)理两淮盐运,更着意于时调小曲,传为他所编的《晓风残月》辑有“滩簧”“南京调”“淮红调”“碧波(破)玉”“满江红”等南方俗曲,“俏人儿你去后,如痴又如醉”“俏人儿人人爱,爱你多丰采”等,有一些则成为扬州清曲的流传曲目,深深影响了两淮民歌的风气。现存五河朱顶镇流传的民歌《送郎》:“送(么)郎(我)送到脚踏板子面,手里拿着(那)自来火(就)与我吃香烟。转头我叹口气(呀)我的哥嘎,怨了一声天(哪)我们几时能再团圆……”[4]在南北交汇中,传统五河民歌很好地继承了前人的风貌,歌词不断融入时代背景、生活内容,在创新中得以发扬光大。五河地处要冲,域分南北,成为民歌极其重要的传承地带,各地民俗方言在此交流碰撞,以五河方言为特征的民歌样式由此诞生,兼容并蓄而独树一帜。
2 行政力量的助推作用
五河元属临淮府,明属凤阳府,清属泗州,民国初属淮泗道,行政区划相对稳定,明清以降多属凤阳府所辖。凤阳一度作为明中都而得以大兴土木扩建城池,五河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明清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融入凤阳并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分析五河民歌的特征,则绕不过凤阳歌、凤阳花鼓对其的影响。朱元璋为淮西起义军首领,恃凤阳起兵,凤阳最终成为龙兴之地,因而对家乡的感情很深。凤阳府最辉煌的时候领有12州28县的地方官府建制,同时还设有八卫一所:留守左卫、留守中卫、凤阳卫、凤阳中卫、凤阳右卫、怀远卫、长淮卫、皇陵卫、洪塘湖屯田千户所,拥有兵丁数万余人;建立统一的大明王朝之后,他对自己的家乡凤阳一带进行整治,实行了一些免租税和徭役的政策,以休养生息。“凤阳兴龙之地,今天子肇建中都,四方百货之聚,陆辇中土,水道长淮,视他郡为最。”(《荥阳外史》之《送凤阳府税课分司副使高彦芳任满序》)为了加强对凤阳的控制,朱元璋还多次采取了从外地大量移民的措施,“均浙直之民于江淮齐鲁”,洪武二十二(1389)年,“迁杭、湖、温、台、苏、松等无田之民往淮河以南滁、和等地耕种。”[5]46据《凤阳县志》载:“洪武三年(1370)六月,朱元璋令迁徙苏杭一带民众4 000余户至临濠府耕种。所种之田永为己业,官给牛、种、舟、粮等钱物以资助,且三年不征税。”“洪武六年(1373)十月,朱元璋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丰州、云内等州县受北方元兵骚扰,故将这一带居民移居中立府,共8 238户,39 349人。”[6]大量的移民,不仅增添了本地的人口,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对五河地区的音乐、娱乐风俗习惯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移民先后带来了各地的方言,与当地语言融合积淀,最终形成皖中江淮官话。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文化空间的全新构成下,五河民歌在不同文化基因中不断汲取养分茁壮生长,在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日趋成熟丰满[7]。五河、凤阳同处淮河中下游,长期饱受淮河流域灾荒之苦,尤其是明清时期,往往是“三年恶水三年旱,三年蝗虫灾不断”的灾区,由此产生了名闻天下的花鼓歌。为躲避自然灾害,每年秋后都有成群结队的妇女外出逃荒,唱着《凤阳歌》,走南闯北,卖唱乞讨,其中也不乏身背花鼓流落各地卖唱的职业艺人。凤阳花鼓天然带有很多民歌的成分,对凤阳歌、五河民歌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孔尚任《踏歌词》有云: “凤阳妇女唱秧歌,冬冬腰鼓自婆娑。”凤阳人的花鼓且歌且舞,歌唱内容无非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五河作为凤阳府属地,五河民歌与凤阳花鼓、凤阳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彼此融合不可分割,无论从艺术形式还是主题表达上,要想将二者截然分开是十分困难的。
《明史·乐志》记载,“洪武三年又定朝会宴飨之制。”“凡宴飨……大乐作。升座,乐止。进第一爵,和声郎举麾,唱奏[起临濠之曲]。”[5]1503足见统治者非常重视礼乐对治理国家、教化官民的作用。此外,太祖朱元璋还亲自参与音乐理论的探讨和实践:
秋七月乙亥,太祖御戟门阅雅乐,自击石磬。学士朱升辨五音,误宫为徵。……太祖曰:“乐以人声为主,人声和,即八音谐矣。”(熊)鼎曰:“乐不外求,在于君心。君心和,则天地之气亦和。天地之气和,则乐无不和。”太祖深然之。[8]
朱元璋提出“乐以人声为主”的主张,自击石磬,调和八音,并于洪武三年着手制宴飧乐章:
一奏《起临濠之曲》,名《飞龙引》:千载中华生圣主,王气成龙虎。提剑起淮西,将勇师雄,百战收强虏。驱驰鞍马经寒暑,将士同甘苦。次第静风尘,除暴安民,功业如汤、武。[5]1560
临濠为朱元璋起兵龙兴之地,生于斯长于斯,感情自然非同一般,起临濠之曲即是太祖皇帝从临濠崛起的颂歌。他以“提剑起淮西”的气概,转战南北,建立不世之基业,曲中流露出意气风发的昂然向上的风度。为满足皇族奢靡享受,制造歌舞升平的景象,朝廷还要举行很多大型活动,有时候需要上千乐人参加才能保证正常的需要,明谢肇淛《五杂俎》载:
太祖于金陵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曰来宾,曰重译,曰清江,……曰南市,曰北市。盖当时缙绅通得用官妓,如宋时事,不为见盛时文网之疏,亦足见升平欢乐之象。[9]
统治者的积极参与倡导,促进了音乐创作社会环境的持续变迁,一直影响到社会底层,作为有明一代文学样式的代表之一——民歌的勃兴也不难理解了。明代中晚期,政治的腐败加上思想的解放,“整个社会上兴起了一股竞相追求色欲的狂潮”,统治者穷奢极欲的享受也影响了民间百姓的生活。一旦地里庄稼收成不错,日子还能过得去,则于婚丧嫁娶、节庆之余大兴排场,《许云村贻谋》为许氏家训,其中有:
今有方值丰亨,便生骄溢,喜筵庆赏过饰,婚丧伎乐声容,沸腾倾动,仆器服食,珍丽整齐,胜绝乡邦,光暎门户,盖是谓已夫无德,富贵谓之不祥。歌舞俳优,鹰犬虫家,戏剧烟火,一切禁绝,虽乐宾怡老娱病,亦永勿用。燕会亲宾,……则令子姓考钟鼓歌古诗为乐,近世淫声悉屏不用,于凡事皆然。[10]
清代民歌承续有明代的民歌成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繁荣时代。郑振铎认为,“象明代成化刊的《驻云飞》《赛赛驻云飞》的单行小册,在清代是计之不尽的。刘复、李家瑞编的《中国俗曲总目稿》所收俗曲凡六千零四十四种,皆为单行小册,可谓洋洋大观。其实还不过存十一于千百而已。著者曾搜集各地单刊歌曲近一万二千余种,也仅仅只是一斑。”[11]由此可见,仅仅从数量上来看,清代民歌远胜前朝。由于文化交流、思想活跃,许多新的题材进入民歌视野,如资本经济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异族统治在人们生活中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痛,滋生了新的作品广为流传。轰轰烈烈的清代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受到了群众的崇敬和欢迎:“竹叶青,竹叶长,太平军路过瓜洲塘(在今扬州附近)。打翻坛子翻开碗,家中没有一拉粮。太平军,恩难忘,烧杯清茶敬遵王。”“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烧了毛子楼,灭了邓苏教。杀了东洋鬼,再和大清闹(《杀了东洋鬼,再和大清闹》)。” 可见,清代民歌在数量、题材内容的广泛拓展、艺术形式和手法的多样化诸方面有了新的发展,上述都是典型的代表。今天的五河、凤阳、怀远的所在地作为明中都京畿之地,在此风尚下首当其冲,揭开了五河民歌创作与传播的序幕,最终成型,经过明清、民国时期的发展,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五河、蚌埠为核心,播布皖苏两省十几个县市的广大地区。五河民歌源于民间生活,在劳动中手敲瓷碟木块,伴以胡琴竹笛,信手拈来,即事而发,抒发着丰收的喜悦和情感,逐步发展成为节日、春会、红白喜事和其他礼俗活动不可缺少的活动方式。
3 自然灾害致使民歌在迁移中日渐成熟
历史上黄河多次夺淮入海,最终因淮河入海口堰塞而改道,致使淮河曲流婉转,支流纵横,流域内水旱灾害不断,天灾人祸连绵不绝。“以明朝的二百七十五年而论,惨绝人寰的灾荒基本上就从未休止过,其中,水灾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旱灾、虫灾、风灾约占百分之三十弱。”[12]
灾难之际,逃荒成为淮河流域的一种民俗。如同凤阳民歌的形成一样,五河民歌的最终形成也是歌者在家园倾圻,被迫四处逃荒糊口、颠沛流离中不断成熟完善起来的。明代张瀚《松窗梦语》提及,淮河沿岸“间有耕者,又苦天泽不时,非旱即涝,盖雨多则横潦弥漫,无处归束,无雨任其焦萎,救济无资,饥馑频仍,窘迫流徙,地广人稀,坐此故也”。随着民间逃荒习俗的形成,民歌在灾民的四处流浪中也盛行开来,花鼓戏、打钱杆、莲花落、小调不断得以滋补生长,蔚然而为大观。莲花落,又称之为莲花闹、莲花乐,元明以来,被人们写入诗文戏曲。李声振《莲花落》:“乞儿曲名,以竹四片,摇之以为节,号四块玉。”如今淮河流域仍十分常见,乞者以竹板或牛角相击打,作为节奏,随景编词,脱口而出,着实有一定的技巧。
又如“十不闲”,李声振《百戏竹枝词》就有专门的记载,“凤阳妇人歌也。铙鼓钲锣备特悬,凤阳新唱几烟鬟。问渠若肯勤桑织,何事夸人十不闲?”[13]则是直接对其进行批判,指责歌者不事农桑,专以乞讨为业的特点。苦难生活的淬炼中,民歌艺术反而愈加醇厚,逐渐形成派系。
4 结 语
总体说来,现代意义上的五河民歌是以五河为中心,涵盖凤阳、固镇、盱眙、泗洪、明光、蚌埠、怀远及周边地区,乃至沿淮及淮北地区现存的优秀汉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代表。五河的特殊水路交通、地域历史沿革及其行政力量的助推作用、淮河流域频发的自然灾害的影响等因素共同构成外因,五河民歌借助这些因素,最终独立于凤阳民歌、凤阳花鼓等艺术形式,自成一体,经过逐渐发展成为今天享誉全国的民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