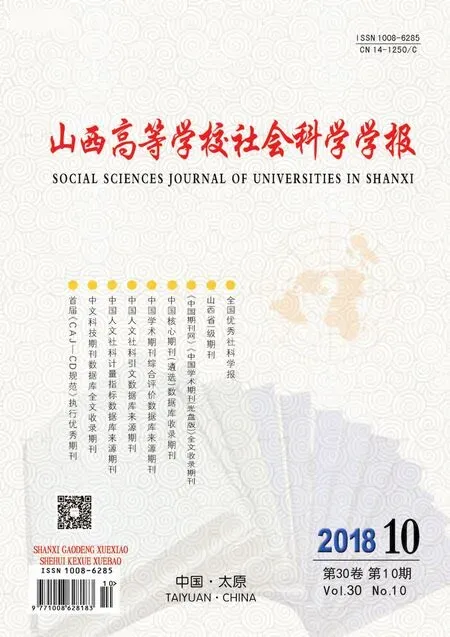“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救亡戏剧宣传的困局与新生*
——以山西为例
段 俊
(1.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2.山西财经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脚步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尽管东北的沦陷昭示了侵略战争已然爆发这一事实,军民反日情绪的高涨也掀起了团结抗战的怒潮,但国民党当局对日仍保持着一种暧昧的态度。在这一背景下,民间救亡宣传的呼号之声日益高亢,华北省区普遍出现了救亡戏剧的萌芽。然而,因经验积淀不足,其宣传方针、创作原则等仍处于自发的状态。民众的呼声虽迫切凄苦,但宣传的时效、广度、深度等方面均存在着不足。直到1937年后,“集体化”的戏剧编演方针逐步形成,“大众化”的戏剧创作原则逐步确立,戏剧宣传才完成了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变,实现了由“救亡”而“抗战”的思想提升。
一、消极抗战的官方态度导致的剧团生存危机
中国革命运动到“九·一八”事变后,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最主要和最迫切的任务。伴随新的斗争形势,以宣传与教育群众起来抗战为目的的救亡戏剧运动开始在山西兴起。1931年9月,太原举行了十万人规模的抗日救国大会,此后山西知识界与民间自发的抗战宣传活动就从未停止过。但在南京国民政府消极抗战政策的影响之下,缺乏官方支持的抗战剧团处境窘迫,纷纷陷入了存续的危机之中。
“九·一八”事变后,祁县的旅外学生为唤醒民众、宣传抗日,在1931年寒假期间成立了联合会。并为马占山部的抗日斗争进行了募捐,还与祁县化妆讲演团合作,排演了新编历史剧《卧薪尝胆》《温峤绝裾》《触目惊心》《怨日行》、话剧《不抵抗主义》《蝉翼为重》等众多饱含卫国情怀的戏剧[1]。
1931年太原“一二·一八”惨案[注]“一二·一八”惨案指1931年12月18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镇压抗日运动,枪杀太原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政。发生后,赵树理在晋城的上党简易师范组建了一个三十余人的剧团,到晋城、阳城、高平一带演出了抗战反蒋剧。同年,陵川县杨村学校亦组织剧团,到各村演出话剧《绥东之夜》,歌颂绥东民众抗击日军的事迹,并动员民众缝制“民族英雄”慰问袋,送至前线慰问抗战官兵。1936年夏,经过救亡戏剧的宣传,晋城建立了牺盟会组织,会员迅速扩展到2万多人,一大批知识青年还参加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2]。
1932年9月23日,太原进山中学的进步师生在学校所在地兰村为民众公演了六个小型戏剧,所有剧目都有着鲜明的反帝反封建主题。特别是该校学生集体创作的《归来》一剧,通过东北归乡学生的视角,批判了民众中漠视侵略、醉心于“田园生活”的麻木倾向。该剧抓住了时代的主要矛盾,对观众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3]78。同年10月,尤春维、吴乃茂、常振芳、何普琦(何文今)、刘连藻五人于太原成成中学组建了以抗日为目的的进步剧社。该社于1933年在学校的校庆会上演出了张季纯创作的《二伤兵》,揭露了“何梅协定”将华北奉送与日军的卖国行径。1933年10月,太原“民众剧社”成立,剧社成员有王毅哉、张季纯、张丽云(张艾丁)等30人。此后,该社演出了由山东省立剧院、山东民教馆创作的《北国一朵花》《咖啡店之一夜》等反日话剧[4]165。
除此以外,太原的其它一些进步戏剧社团还有:“亚波罗剧社”(1932年6月成立于今纯阳宫北口,组织人王庚瑜、何普琦等)、“壬申俱乐部话剧组”(在今海子边西,负责人傅辛培、凌信子)、“民众教育馆戏剧研究会”(1933年12月成立)、“太原剧社”(1934年2月成立)等[5]。
1935年日军入侵绥远,山西成为国防前线,在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的影响下,山西的抗日宣传达到了新的高峰。1935年5月,杜任之联合王毅哉、张丽云、张季纯组成“西北戏剧编审会”,创作了《醒来吧!》《金钱的罪恶》《谁的罪?》《出路》等剧,猛烈地抨击了社会的不平等,抒发了扶助工农、团结抗日的进步理想。同时,杜任之又与王毅哉、张季纯、惠实夫成立了“艺术通讯社”,继而于当年6月举办短期戏剧研究班,并于10月创立了旨在弘扬进步戏剧的《文艺舞台》一刊。1935年9月初,杜任之等创办的“西北剧社”公演了之前创作的《醒来吧!》《出路》等剧[6]。在构建创作演出理论的同时,以救亡宣传的实际行动全面推进了抗日进步戏剧的发展。
抗战即将全面爆发时,各阶层民众必须认清侵略者的伪善面目、放弃对投降派的幻想、抛开独善其身的消极态度。山西的救亡演剧活动应国家之危难而生,矛头直指日本的侵略与国内的妥协势力。这一时期,东北事变题材的剧本占据了最高的比例。其中团结抗战的倡议,体现了文艺界爱国进步人士自发的热情与血性。山西“许多优秀的干部大部分都参与过这个时期的工作,它直接或间接教育或培植了相当多的戏剧工作人员”,“中国戏剧博得崇高的地位,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和工农分子的爱戴,也开始在这个时候”[7]。
至1937年,日本国内的排华宣传已空前露骨。“甚至在官方无线电广播程序中的儿童节目里,常有关于‘勇敢的皇军’和‘欺诈的华人’的道德故事”[8]14。然而不幸的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积极反共,对日本侵略者却顽固地贯彻着其“以空间换时间”的消极政策。从1931年到1939年末,这些“用空间换来的时间里所装的东西差不多只是等待外国的某种援助了,自助的努力渐渐消失了”[8]147。戏剧界自发的救亡宣传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支持。诸多由社会地位低下且经济拮据的学生、失业文化人、职员、工人及社会青年组成的有着救亡渴求的剧社,也曾通过各种途径谋求官方的认可与支持,希望以此维系剧社并发挥更多的作用,但均在挣扎中被迫关闭解散。
二、急于事功的编演方针导致的“剧本荒”问题
山西戏剧人虽然在救亡宣传方面作出了许多的努力,但其编演方针急于救亡宣传的事功,创作演出往往只是不同地域戏剧人各自为战,这导致了救亡戏剧作品长期停滞于自发呼号的层面,宣传内容一直没有应抗战形势的发展而及时更新,继而引发了严重的“剧本荒”问题。
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救亡演剧已然成为最有力、最普遍的抗战宣传形式。“好一计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是全国各地在抗战宣传中经常演出的戏剧。陈鲤庭执笔创作于1931年的街头肃奸剧代表作《放下你的鞭子》曾在山西多地上演。剧中青年工人发出了“我告诉你们,叫你们挨冷受苦,无家可归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抵抗的卖国汉奸”的呼声。观众则应道:“不错!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卖国汉奸!”[9]该剧对投降不抵抗的汉奸卖国贼给予了痛斥,表达了民众抗战肃奸的诉求。街头话剧《三江好》表现东北松花江上抗日英雄“三江好”同日伪军的斗争情形。
抗战时期,尤其是剧本比较缺乏的抗战初期,以《放下你的鞭子》为代表的东北抗战剧被改编移植成多种戏剧形式,在山西根据地和八路军抗日前线都留下了大量的演出记录。1936年夏,在共产党人徐一贯老师的带领下,晋城东沟镇县立第三高小的师生组成了“曙光剧团”,在周边村庄多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战剧。同年12月,晋城获泽中学学生在教师孟新恒的组织下,到县城及周边村庄演出了《流亡曲》《放下你的鞭子》等。1937年初,刘裕民与决死三纵队的政工干部薄怀奇、倪学慧、郭钦安、席炳午等在晋城黄帝庙演出了街头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2]。1937年1月,牺盟会太原分会组织成立的太原救国剧社排演了话剧《放下你的鞭子》[10]。1937年10月,曲沃县一些进步少年在决死队三纵队的组织下组建了一个娃娃兵小剧团,排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亡国恨》等剧,由陈晓带队先后赴翼城、运城等地演出[11]。1937年10月下旬,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动员剧团赴晋西北静乐、岚县、岢岚、五寨、保德、兴县、临县等9个县,演出了戏剧《放下你的鞭子》等[12]。1938年9月下旬,太行山剧团历时三个月巡演百余个长治、晋中一带的村庄,演出戏剧《三江好》。1938年冬,国民政府军委会抗敌演剧队第三队在晋西北演出戏剧《三江好》。这些东北抗日剧虽然令广大民众深受感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剧本的高频率演出也反映出新内容抗战剧本的严重缺乏。造成这一现象主要由于创作者自身才思枯竭和创作语言贫乏,广大群众中的编演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既有传统戏剧的表现形式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借鉴。
老舍在他的第一部四幕话剧《残雾》演出后,针对当时戏剧界呈现出的“剧本荒”问题指出:“话剧总是《放下你的鞭子》与《电线杆子》几出老戏。”他疾呼道:“没有剧本,没有剧本!” “剧本荒是普遍的!”日本法西斯分子的侵华战略由蚕食到鲸吞,由掠夺到占领。戏剧如果继续限于警语式的呼告,则不免使大众归入“狼来了”一般的麻木之中。怎样向大众宣传“抵抗什么人、为何而抵抗、如何去抵抗”等道理,这是经过初期救亡宣传阶段之后,在步入抗战宣传的新时期之时,山西戏剧人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三、教化式创作原则导致的宣传实效困境
中国有着面积广阔的乡村,有着数量极为庞大的农民大众。尽管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不高,却是抗日时期最值得依靠最值得信赖的斗争力量。然而“九·一八”事变后的山西救亡戏剧,其创作原则仍然有着高姿态、重教化的特征。在此原则影响下,搬演西方经典、编演多幕大剧成为戏剧编演者不经意中的一种习惯。如此一来,在农村人口占据绝对多数的山西,戏剧宣传就难以获得实效,大大地背离了救亡戏剧人的初衷。
1932年9月23日,太原进山中学师生在兰村为民众公演了俄国作家亚穆柏的《可怜的裴迦》等剧。1934年春,太原民众剧社在大水巷承庆茶园演出了俄国文学家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一剧。经过张季纯等人改编的演出台本,将这一俄国现实主义讽刺戏剧呈现出了一定的中国风味,借此揭露和讽刺了山西官场政治的腐败和作风的堕落,引起了观众一定的反响,剧社演出三日,六场皆满座,轰动一时。1934年,又演出了俄国契诃夫的《白茶》、亚穆柏的《可怜的裴迦》及日本菊池宽的《父归》三个独幕剧。1936年1月,演出了法国法朗士的喜剧《哑妻》、英国菲利普斯的话剧《未完成的杰作》[3]78。
这一时期太原市的戏剧演出条件逐渐丰富和改善,布景、灯光、效果等均开始由萌芽状态向专业化转变。从最初的布条布景到布景板的使用,从水粉化妆逐渐使用油彩化妆,灯光上使用土法泄力,改变电压使光线产生渐明渐暗的变化效果。但上演的戏剧在倾向上不明确,进步与落后的思想并存[4]165。 这种一味求大追高的创作原则一直持续到1941年左右,伴随着“剧本荒”问题的日益严重,诸多既有剧本内容不贴合现实、形式不符合受众欣赏习惯、表演要求不符合宣传环境等弊端才逐渐一一凸显出来。这些外国名剧艺术性虽强,“但和我们民族的现实生活有距离”[13]。很多大剧观众看不懂,只能评价道:“好!屋子很新很漂亮,衣裳还很新,可是说的啥故事?”[14]甚至一些大剧出现了“一丈高的硬景”[15],这样的舞美布景要求,显然是严重偏离基层抗战宣传的实际条件的。
一部追求审美鉴赏体验的大戏,就如同一柄装帧华丽的名剑,美则美矣,却不免因之削弱了杀伤和战斗的力度。自1920年代以后有着十余年历史的中国新演剧运动,在对敌宣传斗争最需要它的关键时刻,却“几乎完全为着一种外来演戏传统所支持着,堆砌着外国演剧的风格和外国演剧的成分”[16],成了广大工农看不懂、不愿看的尴尬存在。
由于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底层农村大众对救亡与抗战的认知还停留在一个较低甚至含混的水平。一位山西老农在太原等地相继沦陷时认为,“这不是打共产党,便准是和南京政府打仗!”[8]126可见自1931年至1937年的数年之间,包括救亡戏剧在内的山西救亡宣传,其实效是有限的。
四、统一战线推动下山西抗战戏剧的新生
尽管在“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救亡戏剧中有不少抗日主题的作品,但其创作和演出却多依靠戏剧人的自发,对斗争方略的思考也还不够深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山西戏剧界才结成了广泛互助的整体,并系统梳理了编演实践中的经验教训,逐渐形成了“大众化”的戏剧创作原则和“集体化”的戏剧编演方针。肇始于自发,新生于自觉,山西抗战戏剧终于实现了从救亡呼号到抗战宣传的涅槃。
1937年9月,山西组建起了牺盟会、山西新军、战动总会等统一抗战的机构,对日伪的全面斗争随之开始。在统一战线精神的指引下,山西戏剧界爱国进步人士一致行动,确立了戏剧宣传工作的基本原则,初步制定了创作演出计划,产生了改造运用山西传统戏曲形式的思潮,将既有的救亡演剧活动进一步发展成了抗战戏剧运动。
为了广泛而有效地组织发动广大民众,牺盟会、新军、战动总会等组织迅速组建了前线剧社、工卫剧社、动员剧团、前哨剧社、燎原剧社等抗战戏剧团体,以便于群众理解和接受的形式排演了诸多抗日剧目,并进入城乡开展了宣传活动。八路军在展开武装斗争且获得平型关伏击、阳明堡夜袭等一系列战斗胜利的同时,火星剧社、战士剧社、先锋剧社、战斗剧社等军队大型专业剧团也在山西根据地进行了一系列抗日戏剧的演出活动,对山西各地的进步剧团起到了组织、领导、宣传与实践的模范作用。
1937年11月8日,日军侵占太原,战争重心由华北地区的正面防御战转向敌后游击战。晋察冀、晋冀豫、晋西北(1938年12月扩至为晋绥根据地)、晋西南根据地先后建成,在共产党及各地牺盟会的组织下,各根据地中八路军太行山剧团、晋东北大众剧社、襄垣农村剧团、襄垣县盲人宣传队、孝义县战斗剧社(后改为民革剧社)、武乡县盲人宣传队、武乡县牺盟会抗日儿童话剧团、阳城县第二区下伏编村儿童话剧团、辽县抗日先锋剧团、牺盟会洪赵中心区吕梁剧团等抗战剧团陆续成立。西北战地服务团、国民政府军委会抗敌演剧三队等一些外省区的专业文艺团体也进入山西,开展了一系列演剧宣传活动。
这些专业大剧团在承担编演任务的同时,还积极扶持成立农村剧团,同时认真向基层剧团学习传统戏剧语言与表演技巧,形成了互帮互学的抗战戏剧集体风气,为抗战戏剧向“大众化”“集体化”方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杨村彬认为,“从教化化走到大众化”乃是戏剧发展的必然趋向。戏剧界应首先致力于“教化化”的创作演出活动,以戏剧唤醒大众、指导大众,承担起这一艺术形式的社会使命。进而戏剧人更应在此后的工作中融入大众、带动大众,绝不能放任戏剧成为少数人的鉴赏品或玩物。他向戏剧文艺工作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吁:“别留恋在少爷小姐的怀抱里寻开心吧!有多少强健的、热情的农民、工人,他们有大手,愿意和你们握手做好朋友”[17]。孙强于1938年发出了职业剧团深入农村演出大众化的戏剧,“做宣传的剧团”[18]的呼吁。戈丽进一步提出戏剧必须大众化,戏剧的内容必须农村化、民族化,“避免演出西洋味重的戏剧”,“可以采用旧形式新内容”,“戏剧工作者必须深入群众,多采取民间故事编剧”[19]。1939年晋东南文化界救国总会颁布了《晋东南文化界救国总会工作纲领》,确定了“大众化、地方化、通俗化”[20]的工作原则。史群提出抗战初期戏剧运动的方向应该是:第一,“要把戏剧运动和全民族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戏剧必须服从于战争,必须跟从于建设,戏剧要表现民族生活的各方面,适合于民族的利益。第二,“要在戏剧运动中接受一切历史的文化成果,力求进步,克服困难。”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的戏剧运动的内容与形式,要善于运用旧形式和新形式。第三,“要使戏剧运动成为大众的战斗的进步的运动。”[21]
1942年1月18日,太行区举行了文艺及敌占区文化工作座谈会。赵树理向太谷、襄垣、昔东、昔西、潞城、榆次等县的参会代表特别强调了文艺大众化的迫切需要[22]。在1944年晋察冀边区文联发起的新年剧作运动中,作品“必须力求通俗化大众化”[23]已经成为了指导性的要求。1945年太行山区举行的纪念“五四”青年节大会上,中共中央北方局李大章作了《敌后根据地的文化政策》的报告,把“提倡大众化”确立为敌后的文化政策[24]。
抗战戏剧宣传,并非是要戏剧人孤芳自赏地大行教化之道,而是需要他们从启发民智入手,使戏剧逐步完成从职业化向大众化的转变。当戏剧运动有了坚实而广阔的主体基础,就会出现民众自己成立剧团、自己编演剧目的图景。戏剧事业将因此焕发生机,戏剧宣传也将因此力量倍增。“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走出的作家们就曾以集体创作的方式,对沦陷区民众在日本奴役下的生活困境、精神疾苦及抗争意识进行了有力的表现。老舍敏锐地注意到,“集体创作”正是解决“剧本荒”问题的有效途径。他身体力行,于1940年与宋之的集体创作了四幕抗战话剧《国家至上》。在此后的创作过程中,山西抗战戏剧人采取了“集体讨论、推人执笔”“群众讲述、作家整理”“群众讨论、集体编排”等多种集体创作方式,以风靡于山西本地的晋剧、秧歌剧、眉户剧等戏剧形式,写就了大批及时高效反映抗战斗争新需要的优秀剧作。《大家好》《三个女婿拜新年》《新旧光景》《王德锁减租》等剧均成为根据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时代经典。
“中国真正的力量在哪里呢?不在大城市也不在省会,而在这里。它们是在小村落和小城镇里,与那些因为受了好多年的无智识和内战的痛苦而来的大部民众团结在一起。他们是一个能感觉能进步的团体。”[8]213
为形成人民战争的局面,包括戏剧在内的所有文艺宣传形式,把自己熔铸进了大众之中,树立了深远的斗争观念,坚定了人民的斗争信心,催化了大众的斗争热情,传播了正确高效的斗争经验与手段,在准确把握大众诉求的基础上发挥了宣传教育作用。新生的华北抗战戏剧实现了与广大基层群众的有机结合,在战斗与生活的沃土中汲取了丰富的创作养分,针对迅速发展的抗战形势作出了及时准确的宣传反应。在斗争的淬炼中,终于实现了向着自觉的蜕变。在其影响和感召下,农村成为了坚实的抗战堡垒,工农大众成为了全民抗战战略的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