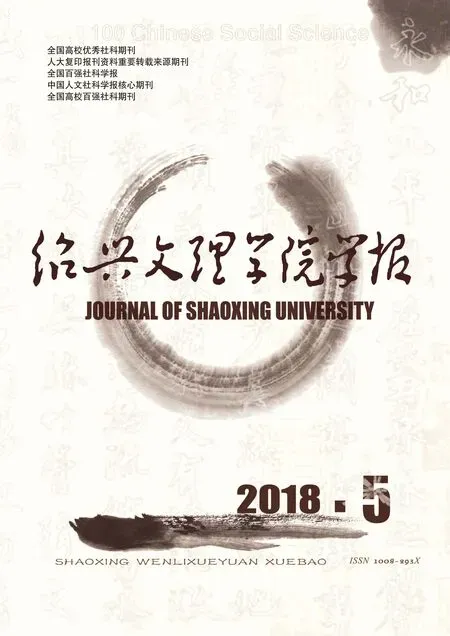龙场悟道:对人生意义的追问
王晓乐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因言获罪,被贬为龙场驿丞。此时,他对早年所学进行反思,对人生意义发起追问,顿悟“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格物致知之旨,成为阳明心学的“独立宣言”。随后,他提出知行合一,完成了阳明心学的早期建构。王阳明的这段思想转折历程,被学术界称为“龙场悟道”。
龙场悟道由追问人生意义而达致,但学界对其人生哲学的性质却鲜有分析和论述。笔者认为,确定和阐明龙场悟道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对于深刻理解阳明心学、发明其恒久价值具有基础性作用。本文首先介绍阳明为龙场悟道所作的思想准备,随后揭示和确定龙场悟道的核心课题:人生意义。围绕这一核心课题,笔者在文章的第三和第四部分将详细论述阳明心学的突破和完成。
一、准备:五溺三变,归正圣学
据《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11岁时便有“读书做圣贤”的志向。做圣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彼时的王阳明恐怕还根本不清楚“做圣贤”究竟意味着什么。考察阳明在龙场悟道前的求学经历,有助于我们发现和还原一个兴趣广泛、不断求索的青年王阳明,也让我们看到阳明龙场悟道并不是幸运或意外,而是有其充分的思想准备。
关于王阳明早年的思想经历,有“五溺三变”的说法。湛若水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中说:“(王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作为王阳明思想上的至交好友,湛若水的概括应该是可信的。据《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确实在15岁时“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26岁时“学兵法”、27岁时“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31岁时“筑室阳明洞”、“思离世远去”。可以说,湛若水的说法大体概括了王阳明思想所溺的经历;当然了,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上一个“溺”完全结束之后才开始下一个“溺”,而是不同的“溺”交叉错杂(这也符合青年人的思想特点)。
阳明早期的“五溺”已如上述,但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不是阳明早期思想的全部。除此之外,阳明在理学上所花的工夫与心思并不亚于上述诸“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阳明乃文士出身,既然参加并通过了科举考试,必然对四书五经和程朱义理有基础性的了解。另外,据《阳明年谱》记载,阳明18岁时“日则随众课业,夜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21岁时“为宋儒格物之学”“遍求考亭遗书读之”。只不过这是“圣贤之学”,并不属于“溺”,因而不在湛若水的“五溺”之中。
关于阳明早期思想经历,“五溺”之外犹有“三变”之说。钱德洪在《刻文录叙说》中说:“先生之学凡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观此“三变”的前两个阶段,与“五溺”之说大体相同,只不过略去了任侠与骑射,将神仙与佛氏合并为“二氏”。另外,王畿也对王阳明的“学之三变”作出过概括,其云:“其少禀英毅凌迈,超侠不羁,于学无所不窥,尝泛滥于词章,驰骋于孙吴,虽其志在经世,亦才有所纵也。及为晦翁格物穷理之学,几至于陨,时苦其烦且难,自叹以为若于圣学无缘。乃始究心于老佛之学,缘洞天精庐,日夕勤修,炼习伏藏,洞悉机要,其于彼家所谓见性抱一之旨,非惟通其义,盖已得其髓矣。”[3]与“五溺”和钱德洪的“三变”略有不同,王畿的“三变”将任侠、骑射、辞章等混杂以作为“经世”之学,指出了朱熹格物穷理之学在阳明早期思想经历中的重要地位。
任侠、骑射、辞章等是“经世”之学,而佛老、格物穷理便是心性之学,或者说性命之学,阳明本人对此也是认同的。1512年,阳明在《别湛甘泉序》中写道:“夫杨墨老释,学仁义,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学者以仁义为不可学,性命之为无益也。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辞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偏,吾独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246正是经过了佛老性命之学的洗礼,王阳明深切认识到记诵辞章对圣学有害,这使得他有志于、也有能力在34岁时归正于圣学,从此走上以性命之学成就圣人之志的道路。
二、课题:居夷处困,生死一念
正当王阳明矢志圣学,准备学仁义、求性命以成就圣人之志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了。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上书论救戴铣等御史言官,触怒权宦刘瑾,被贬贵州龙场驿,经历了居夷处困的艰难孤寂。然而,事实上这场灾难并没有这么简单。
王阳明的因言获罪并非个案,而是正德初年明王朝最高层权力斗争漩涡所激起的浪花。明武宗即位后的正德元年(1506),以刘健(时任内阁首辅)、谢迁、李东阳为首的阁臣上书明武宗,要求处死刘瑾,由此引发了这场阁臣与宦官集团的权力斗争。阁臣们失败了,刘健与谢迁等人去职;戴铣等御史言官为刘健、谢迁等人鸣不平,遭到逮捕并被廷杖致死;王阳明为戴铣等御史言官鸣不平,才遭受牢狱之灾并被贬龙场。这是一场涉及各级官吏的全局性的政治风波,年仅35岁性情正直的兵部主事王阳明被卷进了这场政治斗争。在突然而至的牢狱之灾中,前途未卜、生死难料的王阳明可能第一次明白了死亡的恐怖,因而在《狱中诗》里写下了“心之忧矣,匪家匪室。或其启矣,陨予匪恤”的句子。
幸运的是王阳明没有死,而是被贬为龙场驿丞,但是,往赴谪所的道路并不平坦,而是充满了九死一生的艰难险阻。《阳明年谱》对此记载道:“先生至钱塘,瑾遣人随侦。先生度不免,乃托言投江以脱之。因附商船游舟山,偶遇飓风大作,一日夜至闽界。比登岸,奔山径数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纳。趋野庙,倚香案卧,盖虎穴也。”刘瑾遣人追杀,阳明跳江才得逃脱,搭乘商船却遇大风而漂泊海上,深山之中托身野庙。这种种遭际都可以置阳明于死地,无怪乎《赴谪诗》里时有“人生各有际”“人命各有常”这样的句子。
经过千难万险抵达谪所之后,王阳明的日子仍然很不好过。“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没有居室要自己搭建,缺乏粮食要自己耕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孤寂的精神生活,让王阳明深深认识到自己只是个将死未亡之人。在《瘗旅文》中,他哀叹客死龙场的无名小吏,对身边童子说“吾与尔犹彼也”,仰天歌呼道“性命不可期,吾苟死于兹兮”!
《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心境,云:“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从这句“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可知,此时的王阳明已经彻底没有了富贵功名的希望(因为不可得),只剩下对生命之留恋、感慨(因为怕死)。“吾惟俟命而已”的自誓之语,应当与孟子所谓“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4]参照来读。王阳明不甘心夭殁于龙场,但死亡却时时逼迫着他,于是让他想起孟子的这句话,只有修身俟命才能夭寿不贰。这句誓言标志着阳明从怕死转向修身(求道、体道)。“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可以有两意:一是以前的圣人(孔孟、程朱)之道都不顶用,皆应抛弃;二是在此种境地之下,我若要做圣人应该寻求什么道呢?李贽曾云“圣人唯万分怕死,故穷究生死之因,直证无生而后已”[5]171,因怕死而修身,因修身而尽弃往说(用禅宗[6]、朱熹[7]688、李贽[5]66的说法,彼时不过是“矮子看戏,随人短长”),穷究追问自己的生死根因、人生意义。这就为阳明立志成圣的性命之学提供了核心的课题和突破的契机。
三、突破:吾性自足,心外无物
王阳明决定以性命之学成就圣人之志,接续而来的政治灾难与龙场经历让他直面死亡、思考人生,发出了“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的心灵追问。就在这时,王阳明经历了一种类似宗教顿悟般的体验,使他完成了在生死问题上的突破,也实现了对宋儒理学的大翻转。
关于此次类似宗教顿悟般的体验,《阳明年谱》记载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的心灵追问在这里终于得到了答案,那就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吾性自足”的说法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遥相呼应,由此可知阳明之悟并非别造妄念,而是有其圣学根基的。先领悟“吾性自足”而后证诸《五经》之言,也表明阳明的此番悟道更接近于陆九渊所谓的“六经注我”。但是,明白这些还不足以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可以解除对生死一念的忧虑、完成对人生意义问题的回答,要理解这一点,还得从著名的“南镇观花”说起。
“南镇观花”出自《传习录》的记载,其云:“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8]231学术界对这段记载通常理解为,阳明的“心外无物”不关心客观事物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而是关注伦理道德、精神感受,或者(更广泛地)关注意义世界对人(我)的呈现。这种理解当然是对的,但还不够深刻圆满,还是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看成了两截子(好像先有一个客观世界,只是隐而不显,只有等到我去“看”的时候,它才呈现为有意义的主观世界)。笔者认为,对阳明的“心外无物”完全可以作更为彻底的理解。对“深山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的正确回答是:之所以这会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你对“心”的理解是片面的、常识性的,也就是把“心”仅仅理解为知觉之心(看听嗅尝触),而没有将它理解为阳明所谓的心。
“心”当然是我的心,因为“心外无物”,所以我死之后世界也就不存在了,那么死亡自然也就不可怕了。这种想法虽然可以片刻缓解焦虑,但终究难逃自欺欺人的隐忧。真正能够排除这种恐惧和焦虑的,只有阳明所谓的“心”或“心之本体”。关于“心”或“心之本体”,阳明有许多说法,其中有一条道:“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而又亲切简易。”既然“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那么这里“心”就不仅仅是你我知觉意义上、包含我们情感和欲望的“一团血肉”,而是“心之本体”。它是超越了客观与主观的,在“心之本体”的观照之下,世界有且仅有一个。成圣之道全在证心,而“心之本体”与个体之心(汝心)的某种关联使得个体证心得以可能。个体的人若证得此心,便与日月同寿、与天地万物同在,死亡已不足为惧!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南镇观花”中友人的问题便不是为什么心外无物(心之本体),而是怎么样心外无物(汝心)。因而,阳明的回答是就工夫论而言的。
四、完成:心意知物,知行合一
“心外无物”既是本体又是工夫,此已如上述,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心外无物”,或者说做“心外无物”工夫的具体节目有哪些呢?明代以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而阳明又深入钻研并最终矢志于性命之学,那么《大学》八条目中的格致诚正成为他的工夫节目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只是阳明对格致诚正所针对的心意知物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大学古本傍释》虽然刻于正德十三年(1518),但是《与黄勉之》云“古本之释,不得已也。……短序亦常三易稿,石刻其最后者,今各往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见,未可据以为定也”[]206,《阳明年谱》云“先生在龙场时……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以诚意为主,而为致知格物之功……”由此可知作书时间远早于正德十三年(1518),而其主要思想则是龙场时期的。
《大学古本傍释》对心意知物和格物之物有明确解释,其云:“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发,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之格,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在这里,阳明突出了“诚意”的作用与地位,试图以“意”为枢纽统一心意知物,以“诚意”为指针引导和重释了格物致知。这种以诚意正心引导格物致知的做法,是阳明“吾性自足,心外无物”立场的自然展开,提供了心学立场下较为完整的工夫节目系统。当然,此时阳明关于心意知物的解释尚不够完善,直到后来提出了“心之所发为意,意之所在为物”乃至“四句教”等观点才算完善,但其思路倾向于龙场之时已经大致底定。
正德四年(1509),阳明主讲贵阳书院时提出“知行合一”之说。“知行合一”之说所针对的有两个:一是宋儒“知先行后”的说法,一是由“知先行后”说法导致的知而不行的弊端。关于“知行合一”,阳明在不同的地方有多种说法。《传习录》便有记载道:“此(指将知行分作两件——引者注)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不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恁的便罢。”[8]10在这里,阳明提出了“知行本体”的说法,并一再强调“知行本体”原是一个,后人误认为是两件事是因为被“私欲隔断”。是什么私欲、怎么隔断,贵阳时期的阳明对此并未详述。笔者以为,要理解“知行合一”的深刻内涵,还需要返诸生死一念的困惑和求索。龙场之时的阳明直面死亡,对人生意义发出追问,此时如果知得人生意义何在、以何致之,求道者焉有不行之理!这才是真知,才是知行本体。所谓“被私欲隔断”,也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死、不关心人生意义的问题、并无成就圣人的志向,这样的人便只会“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两事”[8]110。
重新解释心意知物和提出“知行合一”,标志着王阳明人生哲学体系(本体论和工夫论)的初步完成。“吾性自足,心外无物”,新的格致诚正与“知行合一”学说既在理论上破解了王阳明的生死困惑,又在实践上为“做圣贤”“修身以俟之”、追求和落实人生意义指明了方向。
五、结论
王阳明早年曾广泛涉猎各种学说,最终归正于圣学,决心以性命之学成就圣人之志。早年的求学经历,为其日后的龙场悟道提供了思想准备。王阳明直面死亡,追问人生意义,终于悟得了“吾性自足,心外无物”的道理,完成了对程朱理学的大翻转。与此同时或在此稍后,王阳明重新诠释了《大学》格致诚正之学,以“知行合一”之说完成了他早期的人生哲学,并为此后的政治哲学和形而上学思考开辟了道路。
揭示阳明心学的性命之学性质,发现生死困惑在居夷处困时期的核心地位,阐明龙场悟道如何追问并回答人生意义之问题,对于我们理解阳明早期思想的实质并以超然而深切的态度把握心学与理学的异同具有重要作用。忠孝节义等具体的道德价值也许已经成为历史,且从来不曾应用于欧美、非洲、拉美等非中华文化地区,但是只要作为个体的人终将一死,只要人生短暂、终将一死的人还会思索并追问人生的意义,阳明心学就能给当下与未来世界各地的人们以慰藉、启发、鼓励和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