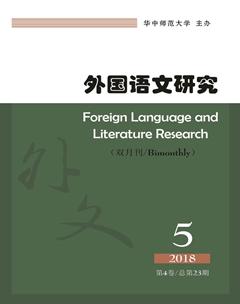无言的悲悯与诘问
内容摘要:“命运与责任”是石黑一雄文学创作的一贯主题,透过《别让我走》揭示的人体器官捐献者的命运与伦理困境,作品对克隆人“顺从”与“责任”的伦理意识书写,不免使我们联想到日本传统“效忠”文化,感受到作家对日本民族二战历史悲剧成因的无言悲悯与诘问。基于这样的认识,文章以文学伦理批评视角,透过小说特定伦理环境中克隆人的伦理选择能指,探赜形成克隆人伦理意识的文化渊源,索隐克隆人“责任”伦理表现与日本“效忠”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理解作家与作品的深层所指。
关键词:石黑一雄;《别让我走》;伦理意识; 文化渊源
基金项目:本文是作者主持的江苏省南通市“226”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项目(批准号:(2016)II-143号)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文娟,江苏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文化研究和英美文学研究。
Title: Wordless Sympathy and Questioning: on Creating thought and Origin of Ethical Consciousness in Never Let Me Go
Abstract: “Fate and responsibility” is consistent theme of Kazuo Ishiguros literary creation. His novel Never Let Me Go reveals the fate and ethical dilemma of clones who are organ donors of human body. Through writing the ethical consciousness of “obedience” and “responsibility”of human cloning, making us think that Japanese traditional loyalty culture, feeling the writers wordless sympathy and questioning for tragedy causes in Japanese national history.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clones cultural origins of ethical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roughing ethical choice signifier of clone in specific environment, this paper also interpret in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ponsibility” ethics and Japanese “loyalty” culture , to understand the deep signified of writer and works.
Keywords: Kazuo Ishiguro; Never Let Me Go; ethical consciousness; cultural origin
Author: Zhou Wenjuan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Her major areas includ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ture. E-mail: zzwwjj68@126.com
日裔英籍諾奖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出生于日本长崎,六岁跟随父母移居英国,与奈保尔、拉什迪一起被誉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对日本民族历史悲剧的潜心回望,使他的作品具有了“命运与责任”主题特征,被认为“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①他的小说《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荣获全球文学奖金最高的欧洲小说奖,被《泰晤士报》列入1923年以来百部最伟大的英语小说之列,并再度提名布克奖。尽管石黑一雄自认为“我是一位希望写作国际化小说的作家”,期望自己的“写作能跨越身份、地域、种族的障碍,寻求身份的独立性和开放性”(余静远 311)。然而,“小说的生命来自于地域” (Welty 118),在石黑一雄时刻沉浸的人性反思之中,他那些寓言式文学叙事关于人类终极问题思考的意识基础,仍发源于他对日本民族“效忠”文化悲剧的悲悯诘问之中。
《别让我走》堪称“命运与责任”意识倾向的典型之作,小说讲述了一群被作为人体器官捐献之用克隆人的异样生活经历,揭示了他们困顿痛楚的内心世界。克隆人被剥夺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创造”他们的目的是随时向“真正的人类”捐献他们的身体器官,就如牛羊猪犬之类为人类提供肉食皮毛一般。虽然也开设课程让克隆人学习各种知识,甚至“精心挑选……包括绘画、素描、陶艺,所有的散文和诗歌”(石黑一雄,《别让我走》31)等克隆人的作品收藏。但这样的教学,只是为了打发他们躯体器官活着需要度过的时光;他们被绝对禁绝吸烟等可能影响身体健康的嗜好,并每周为他们做一次体检,这样做也只是为了保证他们所捐献器官的健康性。克隆人的人生历程,早在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已被最终规划且不容改变,作为鲜活的生命主体他们仅被定格为生物意义上的“人”,他们虽然和那些监护他们的人一样,具有同质的躯体组织与思想情感,却无权选择自己的生活取向与生命历程,只能任凭创造他们的“人类”,依照一己需要随时取走他们器官乃至生命。他们为“捐献”而“被出生”,又因“捐献”而“被死亡”,他们的“人生”悲惨绝伦为何却无意反抗?基于这样的追问,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通过对小说克隆人伦理身份和伦理意识的释读,从其特定环境的伦理选择书写中,探赜《别让我走》克隆人“顺从”“责任”心理与日本民族“效忠”文化间隐性存在的伦理意识渊源,更好地理解作家与作品创作思想的深层所指。
一、权利规训与伦理身份接受
初读《别让我走》的读者几乎都会疑问:克隆人为什么不思逃跑也无意抗争? 细读情节我们才初有了解,那是因为克隆人默认捐献身体器官“是我们应该做的事”(石黑一雄,《别让我走》207)。换言之,他们已自发地接受“器官捐献者”这样一种伦理身份的认定。克隆人这样伦理身份的自我认定,又是怎样形成的?
“在文学批评中……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21),伦理身份是个体在一定伦理关系中的定位归属,是形成个体伦理意识的基础。也即是说,在一定伦理关系中,首先需要被归属者自我认同归属关系,如果自我认同错位则关系失衡,抑或产生抗拒。《别让我走》中克隆人面对身体器官捐献和死亡,之所以不思反抗也不逃跑,正是由于他们认同器官捐献为自我“责任”的伦理归属。
《别让我走》最初的篇章中,作家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克隆人对自我伦理身份的执着追问。他们一旦有机会外出,无论“在城里、在购物中心或者路边的小餐馆里,总是留心注意‘可能的原型”(石黑一雄,《别》127),这样试图“看到可能的原型的事层出不穷”(石黑一雄,《别》128)。作家之所以这样表述,其意并不仅限于表现主体对自身身份认知的渴望。石黑一雄的良苦用心还在于,通过对克隆人强烈的身份意识表现,揭示他们与正常人类一致无二的思想情感属性,以此与盲从赴死的“责任”感形成鲜明反差,再次使读者存疑克隆人不思抗拒的原因。以便作家通过小说情节告诉我们,克隆人之所以会认同捐献器官“是我们应该做的事”,继而屈从这样的噩运而不思反抗,完全是由于克隆人制造机构从最基本的伦理意识深处,对克隆人施行了“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的权力规训(福柯,《规训与惩罚》241-242)。最终使他们“根据拥有权力的特殊效力的真理话语……被迫去完成某些任务,把自己献给某种生活方式或某种死亡方式”(福柯23-24)。
“规训”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创造使用的关键性术语。“权力规训”即指实现权力的规训机构,通过一系列的规训手段实现对被规训者的控制。规训既以权力干预训化肉体,也不断制造知识影响意识,是对人进行“权力——知识”相结合驯化的技术手段。“统治阶级依靠权力生产各种知识话语、真理话语,从思想上牢牢地控制整个社会,而这也正是现代规训权力的实质”(胡颖峰114-145)。毫无疑问,所有的权力规训总是先从环境约束开始的。克隆人所在的黑尔舍姆是一所封闭的住宿“学校”,校舍“位于一个四周都是高地的平整山谷中……有时候我們好多天看不到一辆车子沿着那条狭窄的路开过来,那些开来的车子通常都是一些货车或者卡车,给我们送来供给、园丁或者工人”(石黑一雄,《别》38)。学校不仅在地形上如同岛国一样四面隔离封闭,还鲜有外人造访,除了那些“园丁或者工人”再没有其他外人来到黑尔舍姆。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导致克隆人心理封闭,构成了他们对外部未知世界莫名的恐惧心理。这些本应锋芒展露的年青克隆人,除了每日目睹的生活内容之外别无所知,他们甚至惧怕窗外的森林:“远处阴森森得忽隐忽现。最安全的地方是在主楼正面,因为从那儿任何一扇窗户你都看不到树林。即便如此,你总是不能完全摆脱它”(石黑一雄,《别》56) 。除了这样直接的环境制约之外,还不乏实施意识恐吓的奴役手段,学校一届一届的克隆人“学生”中,始终流传着被故意散布的恐怖故事:
一名男孩“从黑尔舍姆跑了出去。他的尸体两天后在林子深处被发现绑在一棵树上,手脚都被砍掉了。另一个传言说,一个女孩……某天她爬过栅栏,仅仅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当她想要回来的时候,她就被拒之门外。她一直徘徊在栅栏的外面,恳求着允许回来,可是没有人让她回来……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她就死了。可是她的鬼魂总是在林子里游荡,盯着黑尔舍姆,渴望着能够允许回来”(石黑一雄,《别》46) 。
这两则恐怖流言的性别针对性是十分明显的,不说男孩被砍掉手脚不足以吓住锋芒初露的男孩;不被允许回来、死了之后哀求都不被允许回来,又足以吓住充满好奇、但又无从知道外面世界的女孩,使她们绝对不敢逾越栅栏半步。
《别让我走》作品中,石黑一雄用大量的篇幅对克隆人的生活环境做了细致的描写,这些叙述有效地释解了正常智力的克隆人为何不敢擅越雷池的原因。克隆人制造者正是这样以环境和意识的多重阻隔,压制了克隆人了解外部世界的热切渴望,使他们无从体会生命和生活的真正价值,无法想象如果离开黑尔舍姆之后他们能去往哪里?又怎样生存?由此也无从知道除了“捐献”自己之外,还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其他出路?进而迫使他们接受克隆人制造者机构的“权利规训”,认同自己“器官捐献者”的伦理身份。由此,他们只能遵循“已经被规划好了的人生:“你们会长大成人,然后在你们衰老之前,在你们甚至人到中年以前,你们就要开始捐献自己的主要器官。这就是你们被创造出来要做的事”(石黑一雄,《别》73-74)。这里的“权利规训”以“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将“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福柯,《规训与惩罚》227),从而使克隆人乖乖地恪守自己的伦理身份。严格意义上来说,《别让我走》应属科幻小说,纯属虚构并无类似的真实生活素材。作家杜撰出这样一部纯属幻想虚构的小说情节,究竟意欲何为呢?
二、作品创作思想与伦理渊源索隐
有研究者评价《别让我走》“以平常人心写非常人的生活和情感”,认为“小说的悲伤和凄凉是这些不平常人偏偏拥有他们永远无法享受的最平常的情感”(恺蒂 40-44)。可见,《别让我走》故事讲述的是关于人类伦理与命运的思考,作家以人道主义思想鞭笞非人道的器官捐献行径。并以细腻的描述,揭露了克隆人怎样被权利规训认同器官捐献为“责任”的真实原因。然而,这些权利规训究竟源于怎样的伦理渊源呢?释解这一意识困惑,无疑是帮助我们透过小说情节能指,深入探赜作家与作品深层所指的关键所在。
石黑一雄在回答关于文学创作动机时曾经说过:“我十分关注当代现实发生的重大事件”,“但我并不想把它设在这些特定的历史事件中,让它读起来像报告文学……作为一名作家,我想写一些更具有隐喻性的故事”。②这就解释了小说为什么以科幻的虚构来揭示这样一桩近乎直接屠杀的反伦理勾当。石黑一雄出生在蘑菇云升起的长崎,作家在接受采访时,曾坦言自己创作思想与日本二战悲剧的关系:“我父母那一代人确实是经历了惨痛的战争。我想这对我是有影响的”,“日本遗忘了历史,这本身就成为一个问题”(陈婷婷, 《如何直面“被掩埋的巨人”— 石黑一雄访谈录》107)。由此,石黑一雄通过小说表明的思想也是显而易见的:“战争需要清算,否则依托‘遗忘手段而构建的虚假和平迟早会被打破”(陈婷婷 105)。透过作家的上述表述,我们不难觉察到《别让我走》文学书写与作家担忧人类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
《别让我走》克隆人的遭遇与日本二战民族悲剧之间,存在怎样的具体联系?首先,小说主题貌似伦理批判。但稍加思索我们就能发现,如果仅限于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反伦理立场,小说叙事揭露克隆人培育者认为“这没有关系”,克隆人“还不足以成为人类”就足够了。但石黑一雄并没有就此罢休,耐人寻味的是他笔下的汤米、露丝等所有器官捐献者不但不反抗,反而视捐献为至高无上的“责任”,这样的书写无疑是别具用心的。存疑本是石黑一雄匠心独到的叙事风格特点,《别让我走》据此给读者悬置了一个大的疑问:低级动物都具有逃生意识,为何克隆人甘愿赴死?为何“他笔下的主人公永远是安静的牺牲品,对于‘责任认命且默默承受,不知道‘抗争是什么”?(恺蒂 40-44)他们居然认为:“当我成为一个捐献者时,我是相当有思想准备的。感觉该那样了。毕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石黑一雄,《别》207) 。克隆人这种盲目顺从的错综伦理意识,究竟缘何而来?为探赜解索这一悬念,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作家所属日本民族的二战悲剧及造成这一历史悲剧的文化渊源。
众所周知,二战期间日本军国文化绝对“效忠”的权利规训,将整体日本国民由“虚构的关系”幻化成“真实的征服”,驱动他们忠于天皇去投入战争,最终走向幻灭。二战初期由于法西斯同盟曾一时得逞,从而使日本军国主义梦想空前膨胀,以为摧毁美国海军就能独自征服亚洲,进而建立“大日本帝国” 的“大东亚共荣圈”“皇道乐土”。一时间,“大日本皇军”所向披靡的“捷报”和军国主义者的疯狂蛊惑使得日本举国沸腾,举国上下群体沉浸于效忠天皇、为法西斯战争捐躯、重新创造“大日本帝国”历史的“责任”意识之中。但他们始料不及的是苏联红军的合剿和美军原子弹的轰炸,顷刻间据亚洲为己有的“大日本帝国”黄粱美梦彻底破灭。日本战败,尤其是长崎原子弹爆炸的伤痛,使人们“将心爱的小提琴置之高阁;怀孕了却并不高兴;怀孕六七个月的女人每周都在死去亲人的墓前哭泣;清晨梦醒时,人们觉得仿佛依稀还是灾难发生之前的美好时候;小村庄炸毁后留下的废墟,和大片坑坑洼洼的荒地依旧提醒人们留意过去的惨痛;接二连三的儿童谋杀案昭示着战败后的暴力犯罪现象的增长”(赖艳45)。那时的日本,举国上下笼罩在“道德和精神的大崩溃”之中(步平16)。战败的严酷现实,终于使人们认识到盲从“效忠”的惨重代价。
每一种伦理意识都不是孤立的,都有形成它的历史文化渊源。人们普遍认为,“石黑一雄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历史色彩”,他的“主要作品似乎意在诠释日本在二战中的历史悲剧。在回忆的断片之上架起了当代阐释的凸镜。透过这一凸镜,人们看到的是日本文化的基因”(唐岫敏30)。其实,这也是石黑一雄架构《别让我走》小说故事人物“责任”感的重要文化基因。石黑一雄的多部作品,都以人物“效忠”“顺从”行为与最终命运的巨大冲突,表现了作家对造成悲剧成因的深刻理解,向读者展示了作家揭示和深化作品主题的哲学思考。《别让我走》中,受害者和施害者在被权力规训为“驯服的身体”的同时,也自觉建构成了他们“臣服的主体”,即心甘情愿地接受宰割和宰割他人,都成为理所当然的责任和义务。这一现象与二战期间无限“效忠”天皇的臣服伦理观如出一辙,南京“这样的屠杀在城内外一连干了十天的光景,当然是按命令干的……因为这是命令,就什么都不想了”(森山康平 40)。“个体不再认为对自我行为负责,而是将自我定义为执行他人愿望的工具”(Stanley 134 )。不管作家初设与否,《别让我走》中器官捐献者的悲惨命运和无奈处境,以及他们绝对“顺从”不抗争的伦理意识,无不与“唯以主君为重,一旦发生了什么事,就以死狂的冲动奉献自己”(山本常朝,《叶隐闻书》88)的日本传统“效忠”文化,有着毋庸置疑的内在联系。《别让我走》虽是一部伦理题材的小说,但小说既没有过多关于伦理因果的表述,也没有任何人体器官捐献场景的直接描写。而作品落笔最多的却是对器官捐献者进行权力规训的过程及器官捐献受害者和施害者心路历程的书写。可见,作家意欲表现的重点并不是对人类反伦理立场的揭露批判,而是藉此影射二战时期日本国民的盲从与无奈,着力引导人们去深切反思日本二战民族悲剧成因。至此,作家良苦用心可谓彰明昭著毋庸置疑了。
《别让我走》代译序中写道:“好作家必须是讲故事的高手,擅长闪烁其词,能够耐着性子掩藏秘密” (恺蒂 40-44 ),透过《别让我走》的“闪烁其词”,我们看到其中隐藏的“顺从”和“臣服”的日本文化基因,透露的是作家对日本民族“效忠”文化悲剧的悲悯诘问。造成日本民族二战历史悲剧的成因是历史性的,是日本反动势力长期实行权利规训,追捧武士道精神、奉行军国主义教育,狂妄鼓吹民族优越感、无视生命价值的必然结果。日本右翼势力早在十九世纪末就跃跃欲试企图扩张领土,早已形成了精心建构的战争思想体系。武士道古典《叶隐》(Hagakure)开篇就宣称;“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山本常朝,《叶隐闻书》1)。寸土岛国要想实现称霸于世的目的自感力量不足,因此竭力以武士道精神激励其国民以必死的决心去克敌制胜。为了鼓舞士兵的杀人底气,他们又蓄意向民众灌输“神创造了日本”,大和民族至高无上等妄自尊大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将其他民族蔑视为“次人类,他们活该被屠杀”(Herbert 50)。这一切系统的权利规训,日积月累逐渐构成了二战期间日本极端的民族主义国家观,形成了日本国民对民族和天皇绝对服从的强烈“责任”意识。由此,受狂妄扩张的侵略野心唆使,军国主义者通过一系列规训手段,把全体国民规训成自动真实的征服者,將他们一步步诱入了二战灾难的深渊。
《别让我走》源于作家对日本战后创伤的认识体验,以小说“责任”情节折射出二战时期日本盲从“效忠”文化的危害性,以此警示世人不可遗忘而重蹈覆辙。正如石黑一雄所言,作为民族文化根基的“大多数人对周围的世界不具备任何广阔的洞察力。我们趋向于随大流,而无法跳出自己的小天地看事情,因此我们常受到自己无法理解的力量操控,命运往往就是这样”(李春,《石黑一雄访谈录》136),石黑一雄在这里表述的“受到自己无法理解的力量操控”的现实窘况,与《别让我走》幻境中受害者和施害者可悲的伦理意识困境是何等的相似不二。他接着表白说:“大多数人无能为力,而只能随波逐流……这似乎是回顾20世纪时所意识到的诸多痛苦之一”(李春 135),石黑一雄透彻地认识到底层人在意识困惑中挣扎:“尽管他们的动机是善意的(想为人类谋福等等),但因为他们对周围的世界看不清楚,结果发现自己做的事违背了本意,在我看来,这种事情似乎是很容易就会发生的”(李春 136)。克隆人被器官捐献机构规训,认为献出器官和生命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发动二战的罪魁祸首同样堂皇规训日本国民,使他们认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圣战,是至高无上的历史使命。这里内在的必然关联性绝非偶然,不管作家是出于深思熟虑的故意,还是有意无意的潜意识释放,《别让我走》中克隆人的悲惨命运和无奈处境,以及他们绝对“顺从”不抗争的伦理意识,无不与日本文化“效忠”、“捐躯”责任意识紧紧关联。尤其选择人体器官捐献这样似有切腹之痛的故事来寄寓这样的关联性,使读者感同身受,不乏体现了作家对日本民族二战历史悲剧的无限悲悯之情。回顾二战噩运,石黑一雄感慨:“让人难过的是人类有时认为他们生来如此,还自以为是。可事实上,他们通常并非真的献身于他们一直认可的事”(李春 136)。至此我们不难理解,《别让我走》克隆人“安静牺牲”捐献的伦理意识书写,正是对二战时期日本国民盲目“效忠”天皇、为法西斯战争捐躯行为的直接影射。
三、结语
通过以上对作家创作思想的探赜索隐,我们认识到《别让我走》是石黑一雄“创造想象”的、“以某种方式来传达萦绕纠缠着我的思想和情感的风景”(Swaim 96)篇章。作品以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从伦理学的角度展开叙事,但作家并无意针对克隆人技术的社会伦理、科技伦理和生命伦理等诸多伦理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也没有更多的道德批判。小说以缺陷重重的现实世界为故事背景,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克隆人不可违逆的既定命运和他们痛楚无比的心路历程,突出展现了他們身不由己的生存状态所折射出的、人类世界普遍的生存问题。作家讲述的是一个“隐喻性的故事”,以此影射二战时期日本国民的盲目与无奈,着力引导人们去深刻反思战争悲剧成因的痛楚渊源。对盲从伦理与“效忠”文化的深重灾难后果,提出了深刻、沉痛的诘问与批判。他的这种以“反常的逻辑表达自己的心声”的文学叙事(杨金才72),不仅表达了对“安静牺牲”者的无限悲悯之情,更饱含着作家醒世警人的良苦用心。这便是他作品的创作思想和伦理意识的深刻渊源所在了。
注释【Notes】
①澎湃新闻:中国社科院专家:石黑一雄得诺奖出乎意料。2017-10-5
②NRP, “The Persistence—and Impermanence—of Memory In ‘The Buried Giant.” Feb. 28, 2015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步平:《超越战后:日本战争责任认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Bu, Ping. Beyond the W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Japanese War.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 Press, 2011.]
陈婷婷:如何直面“被掩埋的巨人”——石黑一雄访谈录。《外国文学动态研究》1(2017):105-112。
[Chen, Tingting. “How to Face ‘Buried Giant – A Visit by Kazuo Ishiguro.” A dynamic Study of Foreign Literature 1 (2017): 105-112.]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Foucault, Michel. Society must be Defend. Trans. Qian Yu.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Trans. Liu Beicheng and Yang Yuany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Herbert G. Kelman. “Violence without Moral Restraint: Reflections on the Dehumanization of Victims and
Victimizers .”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 (1973): 25-61.
胡颖峰:规训权力及规训社会——福柯权力理论新探。《浙江社会科学》1(2013):114-145。
[Hu, Yingfeng. “A New Exploration on Foucaults Power Theories—Discipline Power and Discipline Society.” Zhejiang Social Science 1 (2013): 114-145.]
恺蒂:平常人心非常人。《书城》 6(2017):40-44。
[Kai, Di. “Preface to the Chinese Version of Never Let Me Go.” Book Town 6 (2017): 40-44.]
石黑一雄:《别让我走》。朱去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Kazuo Ishiguro. Never Let Me Go. Trans. Zhu Quji. Nanjing: Yilin Press, 2007.]
赖艳:《石黑一雄早期小说中的日本想象》。《外国文学研究》。5(2017):44-52。
[Lai, Yan. “Japanese Imagination in the Early Novels of Kazuo Ishiguro.”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2017) : 44-52].
李春:《石黑一雄访谈录》。《当代外国文学》4(2005):135-136)。
[Li, Chun. “The Interview with Kazuo Ishiguro.”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05): 135-136.]
森山康平:《南京大屠杀与三光作战》。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4。
[Moriyama, Kouhei. Nanjing Massacre and Battle of Sanguang. Chengdu: Sichuan Education Press, 1984.]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 1(2010):12-22。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Stanley,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 New York: Harper, 2009.
Swaim, D. “Interviews Kazuo Ishiguro.” In Conversations with Kazuo Ishiguro. Ed. Brian W. Shaffer and Cynthia F. Wong. Jackson, USA: UP of Mississippi, 2008: 89-109.
唐岫敏:《歷史的余音——石黑一雄小说的民族关注》。《外国文学》 3(2000): 29-34。
[Tang, Xiumin. “The Historys Remain—National Concern of Kazuo Ishiguros Novels.” Foreign Literature 3 (2000): 29-34.]
Welty E. A. Place in fiction The Eye of the 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山本常朝:叶隐闻书。李冬君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Yamamoto, Tsunetomo. Hagakure. Trans. Li Dongjun. Nanni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7.]
杨金才:《当代英国小说研究的若干命题》。《当代外国文学》 3(2008):64-73。
[Yang, Jincai. “A Number of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English Novels.”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3 (2008):64-73.]
余静远:文艺简讯:石黑一雄斩获诺贝尔文学奖。《世界文学》 6(2017):310-312。
[Yu, Jingyuan. “Literature Newslette: Kazuo Ishiguro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6 (2017): 310-312.]
责任编辑:翁逸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