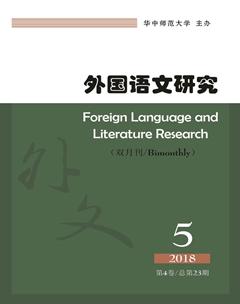论《群山回唱》中男性形象斯芬克斯因子的失衡 及其伦理启示
曲涛 徐璐洋
内容摘要:阿富汗裔美籍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第三部小说《群山回唱》以一对兄妹因贫穷和战争所铸成的六十年悲欢离合为主线,讲述了与其关联的家庭纽带中各个人物所面临的困境与选择。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通过分析小说三个阿富汗男性人物斯芬克斯因子失衡的原因,以此来诠释他们如何摆脱各自所面临的抛弃亲人的道德困境,重建亲人间相互关爱的家庭伦理意识,从而实现精神层面的自我救赎。
关键词:卡勒德·胡赛尼;《群山回唱》;文学伦理学批评;斯芬克斯因子
基金项目:本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反常的叙述行为:伊恩·麦克尤恩近期小说‘非自然叙事研究(L15BWW009)部分研究成果。大连外国语大学2017年度科研基金项目“英国维多利亚小说犹太形象及其犹太性书写研究”(2017XJYB08)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曲涛,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英语小说和叙事学研究;徐璐洋,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Title:Male Characters Imbalanced Sphinx Factor and Its Ethical Revelation in And the Mountains Echoed
Abstract: Afghan-American author Khaled Hosseinis third novel And the Mountains Echoed describes siblings 60 years separation and reunion due to poverty and war and portrays each characters dilemma and choice. By close reading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reasons of the imbalance of Sphinx factor existing in three male characters: Saboor, Nabi and Mr. Wahdati so as to interpret how they get away from their moral predication from deserting family members, how they reconstruct their family ethical consciousness and how they accomplish their spiritual self-redemption.
Key words: Khaled Hosseini; And the Mountains Echoe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uthors: Qu Tao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in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contemporary English novels and narratology. E-mail: qutao@dlufl.edu.cn. Xu Luyang is postgraduate of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contemporary English novels. E-mail: 1137909020@qq.com
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的第三部小说《群山回唱》(And the Mountains Echoed)以一对兄妹因贫穷和战争铸成的六十年悲欢离合为主线,讲述了与其关联的家庭纽带中各个人物所面临的困境与选择。由于生存的困境、内心的欲望等因素,小说中三位男性人物做出了违背伦理规范的错误选择,酿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但作为具有理性意志的人,他们也都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用责任感化解了不可调和的内心挣扎,完成了心灵上的救赎。这部给人以心灵震撼的小说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许多学者从创伤、女性主义等不同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了阐释,尤其以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研究的居多,但都侧重于不同的方面,有的重点分析家庭伦理,有的则分析伦理身份的杂交性等。本文拟从文学伦理学视角重点分析来自于不同阶级的三个阿富汗男性人物——萨布尔、纳比与瓦赫达提在面对伦理困境时,各自斯芬克斯因子不同的表现,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产生的伦理冲突及其带来的伦理启示。斯芬克斯因子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重要概念,它由两部分组成: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并通过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发挥作用。“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中人性因子为高级因子,兽性因子为低级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斯芬克斯因子是理解文学作品的核心,有助于读者理解人物的复杂性。(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6)。”在小说中,而萨布尔、纳比与瓦赫达提身上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伦理冲突,导致他们做出了不同的伦理选择,而他们伦理回归后的自我救赎又表现出文学作品的道德教诲目的。
一、挣扎的萨布尔与伦理困境
在《群山回唱》中,处于伦理困境中的萨布尔面临着艰难的伦理选择。他的人性因子来自于要保护全家人的责任感,而他的兽性因子体现在他违背道德,做出卖掉女儿的伦理选择。萨布尔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使他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处于不同的冲突变化中。萨布尔一家生活在物质资源匮乏与环境恶劣的阿富汗农村沙德巴格。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用自己的血汗换来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肩负起一个男人的责任。作为父亲,他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经常给他们讲故事,陪孩子玩荡秋千,即使下班回家非常劳累,也不会拒绝孩子的要求。显然,此时的萨布尔是受人性因子的主导,具有伦理意识,他对家庭的爱与责任是最好地体现。但上天似乎是不公平的,贫苦的下层阶级人民注定要与生存斗争。一个寒冷的冬天,刚出生两个星期的小儿子奥马尔的生命被无情地夺去,仅仅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衣物与保暖措施,这给萨布尔带来了无情的打击。很快,冬天又要到来,甚至会更为寒冷。由于害怕过去的悲剧重演,经过内心无限的挣扎,他接受了孩子们舅舅纳比的提议,将自己最疼爱的小女儿帕丽卖给喀布尔的上层阶级瓦赫达提一家,来保护其他家人免受严寒的侵蚀。萨布尔的选择不仅使他自己失去了生活的希望,更造成了一对至亲至爱的兄妹阿卜杜拉与帕丽长达60年的分别。这一错误的伦理选择充分体现出萨布尔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严重失衡。
这一伦理事件的外因是沙德巴格本身严峻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将他置于了伦理困境之中,成为了他卖掉女儿的导火线。生存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人生在世不得不与生存作斗争。胡赛尼的作品一贯致力于向世人展现阿富汗人民面临的生存困境、恶劣的自然环境、阶级压迫、种族斗争、性别歧视、政治权利斗争等等,使人民的生活处于极端的生存条件下。在《群山回唱》中,作为父亲的萨布尔就是一个充满悲情的人物形象,而恶劣的生存条件则是造成悲剧的导火线。由于政治宗教的原因导致阿富汗一直冲突战乱不断,加之气候环境恶劣,阿富汗一直处于贫穷状态,人民普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万千苦难阿富汗农民中的一员,萨布尔无法与自然抗争,只能接受其无情的考验。寒冷的冬天来临,他必须要为家人做好保暖措施,可贫穷则是更大的一道障碍。种种压迫下,他最终做出了自以为两全其美的选择,卖掉了自己的女儿帕丽。可以说恶劣的环境条件正是导致他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失衡的导火索。
萨布尔的自尊心是造成其斯芬克斯因子失衡的内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对于尊严的坚持使他被兽性因子所控制。正像纳比所说:“萨布尔像我的许多同胞一样,总是受到自尊心的折磨。这种折磨既幼稚又可笑,又难以动摇。他永远不会要我的钱。……他是男人,他要自己养家”(胡赛尼 100)。如果他能放下尊严,向纳比寻求帮助,他也就不用卖掉女儿,做出丧失人性的伦理选择。萨布尔骨子里的自尊感或许是阿富汗男性普遍存在的对自我认知的刻板印象。在阿富汗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下,男性固执地认为男人应该靠自己赚钱养家,宣告作为男性的权威。但萨布尔没想到这样本应该值得赞扬的品质会将家人及自己推向深渊,他强烈到近乎苛刻的尊严正是他兽性因子的体现。他不懂得向形势退让,结果竟选择了最让人嗤之以鼻的解决方法,他亲手卖掉女儿的行为丧失了人性,践踏了道德。这一伦理选择不仅造成了一对至亲兄妹的几十年的分别,更亲手摧毁了萨布尔的精神,使他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相对于萨布尔的无情,阿卜杜拉对于妹妹感人至深的呵护与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给读者以震撼人心的伦理冲击。萨布尔作为一个男人、一个父亲做出的选择不仅反映出人性的扎根性,即人性中顽固的部分,而且这一整个伦理事件也展现了其道德的教诲价值,无论在什么条件下,贩卖子女的行为都是丧尽天良的。作为父亲,应该保护好自己的家人,维系好家庭的纽带。
萨布尔人性因子使他能夠分辨善恶,但他的兽性因子却使他抛弃了善,选择了恶。错误无法弥补,他只能通过惩罚自己进行赎罪。失去了女儿之后,他彻底改变了。他砍倒了自家门前的橡树,帕丽和阿卜杜拉以前经常在树下玩耍,这橡树承载着与女儿有关的幸福回忆,但现在它却成为萨布尔作为一个失败的父亲的见证,不断地刺痛着他的内心。不仅如此,“有时候,他会冷不丁地瞅见父亲脸上灰云密布,陷入难以言传的感情阴影。如今,父亲看上去萎靡不振,好像失去了支柱。他不是懒洋洋歪斜在屋中,便是坐在新买的大铁炉烤火,把小伊克尔放在腿上,失神地呆望着火苗。他的声音也变得疲惫不堪,与阿卜杜拉记忆中的父亲判若两人,说出的每个字都好像秤砣一样。他往往神情幽闭,长久地沉默不语。他再也不讲故事了”(卡勒德·胡赛尼 48)。失去女儿的萨布尔开始回归了伦理意识,人性因子开始支配他的意识,使他能够分辨善恶。此时他的理性意志体现为他高度的伦理自觉,他的自我精神摧残就是最好的证明。从此他陷入了一种绝望,行尸走肉般的境地之中,他无法原谅自己,只能通过惩罚自我的方式完成心灵的救赎。萨布尔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变化,反映了其伦理意识从迷失到觉醒的过程,也正是通过这样的伦理冲突,表现了文学作品的教诲意义,呼唤正确的伦理与道德。
二、迷失的纳比与伦理选择
在小说中,纳比斯芬克斯因子中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失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他受到了兽性因子中非理性意志的主导,渴望梦想与自由,从而抛弃了责任;另一方面其人性因子受到了兽性因子的压制,出于对爱情的幻想,做出了错误的伦理选择。在兽性因子不断主导人性因子的过程中,他的非理性意志逐渐取代其理性意志,不经意间造成了几个家庭的悲剧。
聂珍钊教授指出“非理性意志是理性意志的反向意志,是一种非道德力量,渗透在人的伦理意识中。它的产生并非源于本能,而是来自错误的判断或是犯罪的欲望”(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 13)。就像萨布尔一样,纳比同样出生于沙德巴格,但他不想被村子里的生活所束缚,希望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于是他选择了逃离,留下了两个妹妹独自住在村中,其中一个还瘫痪在床。他来到喀布尔,最终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富裕的瓦赫达提先生家担任厨师与司机的工作,逃离了照顾瘫痪妹妹的责任,逃离了艰苦枯燥的贫穷生活。身为长兄的纳比虽清楚理应担当起照顾妹妹的责任,但他的人性因子终究被兽性因子主导,非理性意志支配了他的选择。“当时我感觉村子里的生活扼杀了我。我和两个妹妹一起过,有一个还是残疾”(胡赛尼 75)。不想被生活束缚的纳比就这样迷失了自我,逃离了家,逃避了作为哥哥的那份责任。
纳比的迷失不仅是由于受到了自身兽性因子的支配,还有一个外因是阿富汗男权社会的伦理环境,在这里男性被允许拥有自己的工作,实现个人理想,女性却受到严重地压迫。“虽说《古兰经》在男女两性问题上,要求男女平等,这只是伊斯兰教法妇女观的终极认识目标,但它降示在封建的阿拉伯社会,它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父权社会,在这种时代,人们的妇女观深深烙上‘男尊女卑的印记”(马东平 52)。妇女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属品,社会地位低下,只能作为妻子与母亲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社会规约的限制逐渐禁锢了她们的思想,剥夺了她们追逐梦想的勇气。这样的社会背景使纳比的逃离显得天经地义,因为即使他这样做了,也不会受到社会的指责。而她的妹妹,健康的帕尔瓦娜却没有追求理想的奢求,只是想一心嫁给阿卜杜拉。这样一个对男性有着极大包容性的文化场域大大地影响了纳比的伦理选择,成为了他坚持逃离的催化剂。他的逃离虽然使他拥有了自由,但也间接造成了两个妹妹生活的不幸。
瓦赫达提娶了妮拉为妻,却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这是由于他受到了非理性意志的支配。他仍然过着以前那种安于孤独的生活,与妮拉互相伤害。虽然妮拉嫁给他也只是靠婚姻来逃避一种更不幸福的状态,但瓦赫达提确实是在利用妮拉。他选择隐藏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是为了避免造成一种伦理混乱。“伦理混乱即伦理秩序、伦理身份的混乱或伦理秩序、伦理身份改变所导致的伦理困境。由于身份的改变是同道德规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身份的改变就容易导致伦理混乱,引起冲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257)。瓦赫达提陷入的伦理困境是自己的同性取向与娶妮拉为妻之间的两难境地。他不得不做出一种伦理选择,脱离理性意志的约束。但他人性因子中的理性意志还是使他回归了伦理自觉。在他瘫痪之后,妮拉决定带着帕丽远走他乡,他并没有挽留,而是给予了妮拉自由。在他向纳比表明真心之后,他决定放纳比离开,不想成为纳比的累赘。“所以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我想让你走。走吧,纳比,给自己找个妻子,建立自己的家庭,就像所有人一样。你还有时间”(胡赛尼 119)。虽然当时由于自己的私心,他希望纳比能够一直陪伴他,但现在他瘫痪了,他不想再牵制纳比的生活,他决定给纳比自由,希望完成自我救赎。他的这种伦理意识同样树立了道德榜样,达到了文学作品的教诲目的。
《群山回唱》中男性人物的斯芬克斯因子对展现阿富汗人民的生存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表达出胡赛尼书写小说的伦理意蕴。无论是萨布尔、纳比还是瓦赫达提,他们都面临着自身的伦理困境,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也在不同的选择中不断冲突与变化。这三个人物虽是独立的个体,是《群山回唱》众多人物中的一部分,但其不同的阶级伦理身份说明无论贫穷还是富有,人的斯芬克斯因子都会失去平衡,也从侧面向读者展示了阿富汗各层人民的生存图景。 聂珍钊教授指出“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不仅构成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且还影响人物的伦理选择并决定人物的命运。斯芬克斯因子能够从生物性和理性两个方面说明人的基本特点,即人无完人”(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38)。关键是做出错误选择后,人的伦理意识的回归,重建亲人间相互关爱的家庭伦理,从而完成精神的自我救赎,这也是胡赛尼借此小说传达的伦理启示。再者,胡赛尼通过对小说中男性人物的道德困境书写引发读者的思考,并试图通过文学作品的教诲功能呼吁世界对阿富汗人民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的关注,体现其对生活在阿富汗底层社会的边缘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这也是《群上回唱》在更大意义上的伦理意蕴。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卡勒德·胡赛尼:《群山回唱》。康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Hosseini, Khaled. And the Mountains Echoed. Trans. Kang Ka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Publishing House, 2013.]
馬东平:论伊斯兰教法之妇女观。《甘肃社会科学》5(2001) : 52-53。
[Ma, Dongping. “On View of Women in Shariah.” Gansu Social Sciences 5 (2001):52-5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6(2011):1-13。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and Sphinx Facto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2011):1-13.]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外国文学研究》6(2015):10-19。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Exposi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Definition of Huma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2015): 10-19.]
责任编辑:张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