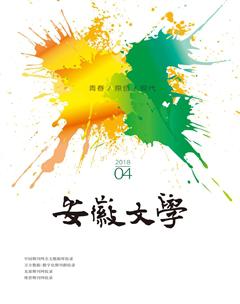论《匿名》的归乡隐喻
杨蕾
摘 要:《匿名》是王安忆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运用传统的“归乡”叙事模式,营造了丰厚的意蕴空间,并由此展现出了隐喻性质。本文通过对《匿名》叙事模式的分析来解读其归乡隐喻,探讨该小说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王安忆 《匿名》 故乡 归乡
王安忆的最新长篇小说《匿名》不同于其以往的写作题材和模式,写了一个阴错阳差的绑架案,充满了形而上的意味,很多读者的阅读体验因此变得不那么愉悦。但通过进一步的文本分析,透视其本质,就能够发现该小说还是运用了一个传统的“归乡”叙事模式,只不过在叙事过程中,添加了太多枝节、太多形而上的体验,导致这一叙事模式的意义空间被拓展,显现出了隐喻特质,因而让人难以把握。本文基于对《匿名》中 “归乡” 模式的分析,试图明确其隐喻特质。
一、叙事模式
“归乡”模式在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耳熟能详的如鲁迅的《故乡》、荷马史诗《奥德赛》、托马斯·哈代的《还乡》。王安忆也不例外,只不过她在此种故事框架下,展现了与其他作家不同的立场与野心。王安忆试图在小说中展现的是她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但借用的是传统的叙事模式,是一种旧瓶装新酒的写作实验。我们首先对这一框架展开分析,以此为基点来透析作家的写作情怀和目的。
故乡是与某个人有着明确情感和亲缘关系的地方,《匿名》中主人公的故乡就是上海,这也是作家最为熟知的城市,也是经常作为其创作背景的地方。归乡,就是游子回归故乡的过程,所以故乡和归乡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归乡这一过程可以容纳千奇百怪的事物、缤纷多彩的体验和情感等一系列内容,使得这个模式拥有巨大的内容量,使其不仅适合讲述故事,也为作家抒发情感、实现创作目的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性。且归乡模式免不了在故乡与他乡的对照中双线并行展开故事,使作品更容易形成强烈的时空对话。这种处理方式并非个例,《奥德赛》也是在故鄉与他乡双线并行同时展开,在对照中使故事产生了巨大时间和空间差异,差异往往产生意义,由此作品才能形成多重意蕴空间。《匿名》中,主人公的家人们在上海运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去寻找失踪的主人公,并产生了一系列情感煎熬。而身处他乡的主人公却在失忆的情况下经历了种种生存考验和自我进化,并一步步不自觉的踏上归乡之路。在这种环境和经历差异的强烈对比之下使作品呈现出了宽阔的时空范围并产生对话,使作品产生了辽阔的意蕴空间。此外,该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个老年失忆男子的 “归乡奇遇记”,他从繁华的大都市上海,“移动”到现代文明的边缘地带大山深处,再“移动”到一个城乡结合部,再到县城,最后于返乡前夕落水而亡。在空间的不断转移的离乡与归乡过程中,主人公接触到了奇特的、五花八门的人和事,巴赫金说:“主人公是在空间里运动的一个点......他在空间里的运动——漫游以及部分的惊险传奇,使得艺术家能够展现并描绘世界上丰富多彩的空间和静态的社会......世界就是差异和对立在空间上的毗连”①。王安忆通过主人公的不断位移,描绘了许多个不同的且差异明显的“世界”和不同人的生存状况,呈现了荒蛮与文明的差异。且于异乡不断改变、二次“进化”的主人公与曾经的安于现状、恪守规则又木讷的主人公之间也产生了对比,这样的差异和对比无疑丰富了小说的意蕴空间。
小说主人公被绑架离乡再到踏上归乡之路,实现了一个轮回。在这个轮回中,主人公可以说是隐居在他乡经历了一场修行。但《匿名》中主人公是由于记忆的链条中断了,丧失了以前的记忆,才误打误撞地在他乡“隐姓埋名”,“隐居”在大山深处的褶皱里开始了“修行”,并逐渐找回了“自己”。主人公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和过往,成为了一个“匿名”之人,这个丢失的 “我” 就成为主人公不断思考的问题,也使得小说氤氲上了形而上的气息,于是归乡模式就充满了隐喻意味。
归乡对小说主人公这样一个年老体衰又失忆的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然而他却在无意识中被命运的洪流推动着踏上了返乡之路,一点点接近故乡,故乡上海在冥冥中一直召唤着他。另外,归乡这个过程必然隐含了时间因素并展现出强大的摧毁和重塑的力量,这也是归乡模式的隐喻所在。“原乡作品的叙述过程......,都隐含时间介入的要素。”②主人公的家人在经历漫长无果的寻找之后决定注销他的户籍,这说明他已经被他的家人和社会宣判死刑,他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证据被一笔抹掉了,主人公符号性死亡了,他“匿名”了,这隐喻着他已经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死亡了,成为了一个死了的活人或活死人,时间摧毁了他也摧毁了一个原本完整的家庭。而在深山里的主人公,几乎丧失了现代文明社会所教与他的知识,在一片空白的状态下,模仿哑子习得了生存技能,在原始蒙昧中自我进化、艰难求生,重塑了一个崭新的自我,这样的变化无一不体现了时间的作用并具有隐喻特质。
二、意义生成
《匿名》中的主人公在被迫并失忆的情况下“匿名”进入深山“隐居”和“修行”,作家为什么要虚构这样一个故事呢?
我们先来讨论下文学的“真”。文学之“真”不在于认识论的真,我们只能在价值论的层面上来认识文学的“真”。文学不注重反映科学之真,而注重人的价值和意义。《匿名》的情节是虚构的,在认识论层面它是“假”的,但在终极视域下,运用本体论观点,我们知道这只是作家的一种创作手段,也是作品价值的存在方式,我们不能被故事的表象所蒙蔽,故事是否真实发生并没有多大意义,只要能看到这个故事的精神诉求和隐喻就足够。
“海德格尔晚年也常用‘回乡这样的主题来书写对于存在之真的情愫。这不过是一种隐喻或者寓言。‘异乡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思想的行动让人在回乡路上获得自己的存在之光,但人永远不能摆脱‘异乡人的身份。” ③ “异乡”状态是人的一种本真的生存状态,在远离“故乡”规范和禁锢后,“异乡人”往往能够回归本真,所以《匿名》中的归乡模式在这个意义上不过是一种人归于本真的隐喻,身在“故乡”的主人公按部就班地过日子,不会思考生活的意义,不知道抗争,更不会思考“我”是谁。实际上一切都源于现代文明的遮蔽,因为社会飞速地发展,不断地规范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当文明过分地统治了人,文明的阴暗面便显现出来,遮蔽了人的本真。主人公在大山深处或偏远小镇,远离了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暗”,便渐渐清除掉了其本真的遮蔽物,开始听从本真的声音,思索我是谁和存在的意义。主人公在异乡渐渐变得像个老小孩,甚至“退化”得像个婴儿,消解了现代文明的影响,跟随本真,率性而为,并一直不停地思考“我是谁”等关于存在的、事关人类尊严的问题,这也是作家主观认知的表现,是小说的意义价值所在。
然而作家为什么要让一个失去故乡记忆的老人走上归乡之路呢?主人公在即将到达上海前夕死亡又该做如何解释?归乡毋庸置疑存在其目的性,它意味着有所图有所寻求,对于作家来说,意义可能在于“归乡”这一过程本身,那么主人公的归乡之路或者说归于本真之路就能够得到合理化的解释了,因为意义的生成在于过程而非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详尽的叙写了主人公的所思所想,探讨了一些形而上的问题,这也是《匿名》不同于其他返乡作品之处,以及王安忆何以能在老套的题材下写出新意的原因所在。且主人公只有在异乡才能保持本真的状态,远离了故乡带来的束缚,才变得更加接近本真的自我。此外,故乡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象征,是永远无法真实抵达的,它只能作为一个理想和向往,一个永恒的向度,而非一处可以抵达的乡土。这或许也是主人公被安排死于抵达上海前夕的缘故之一。
那么《匿名》所隐喻的是什么呢?实际上,那些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才是作家着重要展现的。
(一)时间
作品中对于时间的书写俯拾即是:“时间好像在这里凝固了,完全不流动”,“他感觉出时间的走向”④等。这是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时间和对时间的感受而非现代社会的线性时间。我们只能够感受到时间而看不到时间,只能依靠变化来察觉时间的流逝。在人类社会还未存在之时,时间存在吗,又是如何存在?现代经济社会在利益的驱动下,分解了时间的整体性,将其细化成“时分秒”,这是十分功利的,为的是合理规划生活和工作,终极目的还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在没有规范化的时间之前,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时间是一种混沌的状态。而人在现代社会却似乎成为了人为划分的时间刻度的奴隶,一直被鞭打被催促,缺失了确切时间,人就丧失了安全感。时间是人类为自己编织的“牢笼”,在远古社会,人类并不被时间辖制,不过于依赖时间,“鼓腹而游”无需特别关注时间,人相对自由。当文明渐渐细致,生命、生活、生产被牢牢地拴在时间的刻度上,被时、分、秒催逼赶促,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节奏,并接受时间成为人的“类本质”,从而开始依赖它。一旦时间停滞、紊乱或失去,生活即陷入混乱和恐慌,因为一切行为失去了参照与标准。混乱和空虚使人陷入深深的悬欠感和不安,因而丧失安全感。
在小说中主人公的时间概念也脱离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念,以空间和事件来定义和划分时间,回归了原始的时间感受,时间成为了一系列事件和空间的组合,所以时间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循环和轮回。关于时间的隐喻是王安忆对现代社会病相的洞察,也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殷殷关切。
(二)轮回
从被迫离乡到在异地艰难生存再到不自觉地一步步走上返乡之路的过程中,主人公经历了很多不一样的环境,遇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人。在大山深处几乎无人知晓又毫无现代文明浸染的林窟,失忆的主人公本能的求生意识让他在这个原始地带像动物一样学习生存技能,他学着除草、采集、编织、生火煮食,顺从大自然的法则,适应环境以求生存。表面上看主人公已经完全抛弃了现代文明教化出的知识和技能,退化成了最低等的只有生存欲望的动物,但实际上,这何尝不是一种进化,习得了人类在所谓进化过程中抛弃的技能。这一过程隐喻着人类社会的轮回,时间和历史的轮回,人类就是在原始到现代再到原始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轮回,从历史中寻找到再次进化的动力,王安忆在这里试图表明人类社会并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在不断的轮回之中有所变化和进化。
(三)自我
主人公对自身身份的认知缺失使他一直觉得空洞和迷失,所以他即便在受到生存威胁的情况下仍然不停地思索这个困惑他的、让他失掉内核的问题--我是谁?所以小说中的主人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现实的遭际带来的巨大冲击,更是来自精神世界等形而上问题的考验,因而匿名之名也具有了隐喻和象征意义,它不仅仅指主人公的名字,更是我之为我的标志。当“我”抛开了一切现代社会赋予“我”的名字、头衔等等之后,我究竟是谁?这个问题意味着主人公主体自觉性的觉醒,若我可以是任何东西,那么我还如何是我,我的存在就丧失了合理性。我必然是一个确定的什么东西,才是我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是我的标志,在精神领域,如果能够明确那个区别我与其他东西的存在,能够让我找到安稳感和归属感,对自身形成统一全面的认知,才能实现心灵的满足。人类是拥有自我意识的高等动物,活命自保只是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人类绝不愿意浑浑噩噩地度过自己的生命,而是试图在思想上实现超越。所以主人公“匿名”的归乡之旅实际上隐喻着这是一场寻找自我的旅程,他在与故乡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文化中“修行”,探寻了人的本真,并通过归乡来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找到踏实的存在状态,“归乡”模式的隐喻特质也由此凸显。
综上,在《匿名》中,王安忆通过归乡这一传统叙事模式,探讨了一些具有形而上意味的问题,展现了其对于人和世界的终极关怀,具有隐喻特质,使得《匿名》这部作品呈现出了较高的文学意义与价值。
注释
① 巴赫金.长篇小说的历史类型[A]//巴赫金全集·第3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215-217.
②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M].上海:三联书店,1998:225.
③ 王乾坤.文学的承诺[M].上海:三联书店,2005:167.
④ 王安忆.匿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34-35.
参考文献
[1] 顾江冰.王安忆《匿名》:意料之中的“偶然性”[J].名作欣赏,2016(29):147-148,164.
[2] 王光东,郭名华. 现代性反思与生存方式的探寻——解读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匿名》[J].中国文学批评,2016(3):17-23.
[3] 刘杨.空间结构中文明与生命的可能——读王安忆新作《匿名》[J].中国文学批评,2016(03):23-29.
[4] 權维伟.荒芜现实中的诗意幻想和沉思——评王安忆[J].
[5] 张新颖.王安忆《匿名》的“大故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06):1-12.
[6] 钟媛.时间在空间里流淌——论王安忆小说《匿名》中的时空隐喻[J].扬子江评论,2016,(02):6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