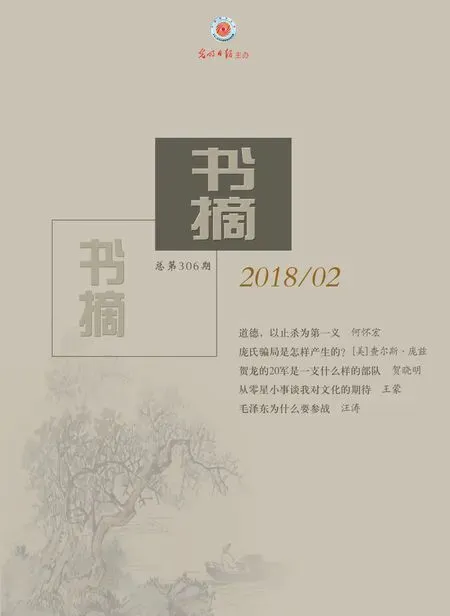好雪片片
☉朱良志
唐代的庞居士对禅有精深的理解,他是药山惟俨大师的弟子。一次他到药山那里求法,告别药山,药山命门下十多个禅客相送。庞居士和众人边说边笑,走到门口,推开大门,但见得漫天的大雪,纷纷扬扬,乾坤正在一片混莽之中。众人都很欢喜。庞居士指着空中的雪片,不由得发出感慨:“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有一个全禅客问道:“那落在什么地方?”被庞居士打了一掌。
这是禅宗中最美妙的故事之一。庞居士的意思是,好雪片片,在眼前飘落,你就尽情领纳天地间的这一片潇洒风光。好雪片片,不是对雪作评价,而是一种神秘的叹息,在叹息中融入雪中,化作大雪片片飘。不落别处,他的意思不是说,这个地方下了雪,其他地方没有下,而是不以“处”来看雪,“处”是空间,也不以时来看雪,如黄昏下雪、上午没下之类的描述。以时空看雪,就没有雪本身,那就是意念中的雪,那是在说一个下雪的事实。大雪飘飘,不落别处,就是当下即悟。它所隐含的意思是,生活处处都有美,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我们抱着一个理性的头脑、知识的观念,处处都去追逐,处处都去较真,那就无法发现这世界的美,像这位全禅客。其实现实生活中的人,常常不免要做全禅客,我们对眼前的好雪片片视而不见,纠缠在利益中、欲望中、没有意思的计较中,生活的美意从我们眼前滑落。不是世界没有美,而是我们常常没有看美的眼睛。
在说上面这个故事时,我正看到好雪片片,在中国画的苑囿中纷纷扬扬地落。
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雪溪图》,据传是摹自王维的作品,王维曾说:“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他是一个高明的诗人,但似乎他更愿意做一个画家。画史上,王维的名气很大,他被当做南宗画的始祖,他的画后人的摹作很多。这幅《雪溪图》,就是一幅摹作,从画面的笔墨和气氛看,比较接近画史上对王维作品风格的描绘。上有宋徽宗亲笔题字,所以摹本的时代当在北宋或北宋之前。这是一幅我国早期山水画的杰作。

王维《雪溪图》
读此画有一种深深的安宁感,真可谓笔墨宛丽,气韵高清,凡尘不近。画的中段为溪流,溪流中有个小渔舟,小舟的篷面上覆盖着皑皑的雪,两个打鱼人忙碌着,两边为雪岸,近手处画一弯小桥,沿着小桥向前,到溪岸,溪岸边屋舍俨然,参差的老树当风而立,树枝上也染上了白色。隔岸则有平岗绵延,若隐若现的村落,一样在白雪的覆盖之下。此图着意表现冬雪茫茫的意境,不在于表现凄寒,而在于表现雪意中的平和、澄澈和幽深。
王维生平非常喜欢画雪,他可以说是一位画雪的专家。他的雪景图,仅见于宋徽宗朝《宣和画谱》的著录就有26幅。王维可以说是中国画史上第一个将雪景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画家。今存王维雪图,除了上面所说的《雪溪图》之外,还有《江干初雪图》《长江积雪图》(皆为摹作)。雪似乎是他画中的重要道具。传说他曾画过《雪中芭蕉图》,芭蕉不可能在冬天出现,但在他的感觉世界中,冬天的物也可以出现在夏天。禅本来就是要打破这世界的秩序,我们以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理性世界,禅认为不是,我们常说,一叶落,而知劲秋,但禅说“一叶落而知春”。
五代南唐的巨然是一位画雪的高手,他的《雪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绢本,水墨,画的是深山雪霁之景,深山中,一片茫茫,如宇宙初开之状。溪桥山道之间,寺宇半露,向上以浑厚的线条画出远山,雪意茫茫,浑厚华滋。又有古松若干,卓立于冷逸世界中。这幅画是白的,又是香的,而不在于冷。在这里,不仅山净,树净,那坡陀间的一溪寒水,也分外明净。雪后时分,行旅几人,轻盈地朝着深山走去,掩映在半山中的寺院,就是他们的目的地。

黄公望《九峰雪霁图》

巨然《雪图》
他们走向明净,走向幽深,走向香界,远离尘世的纷扰。王羲之“快雪时晴”的感觉,在这幅画中可以见出。
这幅画可以以“高松飘白雪,深寺掩香灯”来评价。巨然是个僧人画家,这幅山水其实表达的是对佛的信心。对于禅师来说,雪就是空,是不加装饰的本色世界,是无尘土的净界。禅认为妙悟的过程就是抖落身上尘埃,所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神秀)。
元四家之一的黄公望,也是画雪的高手。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九峰雪霁图》,绢本,墨笔,是他的画雪杰作。黄公望善于画高耸的山峦,在中国画史上,最得浑厚之妙,人多以“浑厚华滋”评之。此画作于他80岁时,这幅画老辣中见温柔。画不似王维平远的山势,而是山峰林立,所谓“九峰”者,多峰也。山峰一一矗立,欲与天公试比高。这幅画在构图上具有独创性,山如冰棱倒悬,这就是我初读此画的感受。这幅画的境界超迈,更是令人魂惊魄悸,此山不应是人间所有,而是仙灵中的世界。黄公望画的是一个琉璃世界,一个玉乾坤。大雪初霁,山峰静穆地沐浴在雪的拥抱之中。山峦以墨线空勾,天空和水体以淡墨烘出,以稍浓之墨快速地勾画出参差的小树,而山峰下的树枝如白花一样绽放,笔势斩截,毫无拖泥带水之嫌,法度极为谨严。雪是冷的,但大痴画来,却有玉的温润、玉的透灵。这通体透灵的琉璃世界,居然是用水墨画出,真是不可思议。石涛曾说:“混沌里放出光明。”这幅画正可当之。正是山空有云影,梦暖雪生香。在这样的冷世界中,使人体味到清香四溢的境界。
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民族不喜欢雪,大雪飘飞,白雪皑皑,人在这样的氛围中,容易忘记尘世的烦躁,产生一种超越的感觉;雪是干净的,而人们的俗世生活很容易沾染上污浊的东西,在雪中,我们似乎将心灵洗涤了一番,有诗道“皑如山上雪,明若云间月”,雪是清净身;雪是冷寂的,给人凄凉的感受,使人有深深的内心体验,和这个充满戏剧般喧闹的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雪中,人们获得心灵的安宁。唐人司空曙有诗云:“闭门空有雪,看竹永无人。”琉璃世界,一片静寂,深心独往,孤意自飞。空灵中有清净,有永恒的宁静。雪给人带来性灵的怡然。
雪是一个安宁的世界,一个安顿性灵的世界。南宋梁楷的《雪图》,今藏日本,画缅邈无垠的雪境,乾坤混蒙,一片茫茫,笔致柔和,风格细腻,和梁楷的其他一些作品风格不同,将雪温柔神秘的特点表露出来,中有二人骑马,在荒天雪地中,这是一次惬意的旅行。行者没有那种匆匆赶路的神情,而是在静静地享受着这一片宁静,这一片神秘。
对于中国画家来说,雪是一个至为丰富的体验世界,一个能彰显人的生命感受和情绪意志的对象。文徵明说:“古之高人逸士,往往喜弄笔作山水以自娱,然多写雪景,盖欲假此以寄其岁寒明洁之意耳。”清恽南田说:“雪霁后写得天寒木落,石齿出轮,以赠赏音,聊志我辈浩落坚洁耳。”这都点出了雪画情感寄托的特征。白雪连绵,荡尽污垢,在雪意阑珊中,使画家不落凡俗,从而自保坚贞、自存高迥。画雪反映了中国画家的超越情怀。明王穉登赞赵大年《江干雪霁图》有“皎然高映”之趣,有“人在冰壶玉鉴中”之感,即是就超越情怀而言的。雪为白,白为无,白雪提供了一片空无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画家同于宇宙浑莽之中。王维《雪溪图》就有天浑地莽、玄冥充塞气象。霰雪纷其无垠,云霏霏兮承宇,云雪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宇宙。

李成《寒林骑驴图》
在中国画家眼中,雪更是妙的,就是说雪中有妙意。他们常常将自己的哲思寄寓于雪中。我们注意到,对雪有偏爱的画家多是僧人画家,如巨然等,或是倾向于佛教尤其是禅宗情趣的画家,如王维、关仝等。在禅宗中,雪意味着一种大智慧。有僧问:“什么是摩诃般若?”青耸禅师道:“雪落茫茫。”摩诃是大,般若是智慧。大智慧就是雪落茫茫。百丈怀海说:“雪山喻大涅槃。”大涅槃,即根本的超越。禅宗反对比喻象征,道不可比,但并非是绝对的。雪就是禅宗中一个很重要的喻象。在佛教中,有这样的说法,说是释迦牟尼在过去世曾到雪山修行,所以被称为“雪山童子”。这样的比喻当然与清净法身有关。传禅宗中的牛头法融开堂讲《法华经》,讲得素雪满阶,群花自落。茫茫的雪意是智慧的渊海,它沉稳、内敛,深邃、平和、空无。我想在上举三幅画中,似乎都体现了对这大智慧的追求,那空明、清净的智慧世界,原是画家心灵之法身。
在中国艺术中,雪具有感发人心的功能,因而,它往往具有和酒同等的作用,催发意兴,激荡生命。黄公望《山阴访戴图》,颇有意境。画的是东晋时的一个故事。东晋名士王徽之,就是那位爱竹成癖以至说出“何可一日无此君”的诗人,他在山阴时,一天夜晚,一觉醒来,知是下雪,急命打开门窗酌酒,四望皎然。他在雪地里踱着步,咏着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到了朋友雕塑家戴安道。此时戴在剡溪,离此有相当远的路,他却命家人驾小舟去访问,小舟几乎在雪溪中走了一夜,快到了戴的住所,他又命船家返回。人问其故,他说:“我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一定要见戴安道?”这是何等潇洒倜傥的人生格调。他解除的是目的,高扬的是“兴”——生命的悸动,夜、酒、诗、友情,再加上雪,这就是他的兴发感动,他有不可遏止的生命冲动。
或许人的生命本来蛰伏的东西太多,我们原以为自己平庸,乏味,原以为自己道不如人,其实,人人的生命都有灵光,雪的映照,使灵光跃现出来,原来,这里也可以灵光绰绰。
“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这是中国诗学中一个由来巳久的有趣话题。灞桥,在西安东,近年灞桥的遗址出土,那个令千年前无数人断肠的地方,浮出了历史的水面。那里曾是唐代长安人送别的地方,人称销魂桥。乱云低薄暮,流风回舞雪,孤独的游子在万般无奈中踏上路程,放眼望,苍天茫茫,乾坤中空无一物,只有一条瘦驴在彷徨。正所谓人烟一径少,山雪独行深。此情此景,怎能不勾起生存之叹,怎能不产生命运的恐慌。诗意的大门被这寂寞所撞开。
画家常以此为画题。北宋李成的《寒林骑驴图》,就是表现这种境界的作品。此作曾被张大千收藏,上有“大风堂供养天下第一李成画”的题签,今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此画大立轴,绢本,淡设色,乃李成生平杰作。占画面很大分量的是古松,从左边侧出,直插画面,有撑天拄地的气势,树干劲挺,气象萧瑟,残雪历历其上。天寒地冻,大河滞断水流,暮色苍茫,大雪飘飞,苍天混莽一片,大地失去姿容。溪岸上白雪皑皑,一人骑着瘦驴,目光惊悚,前后有二童子。真是路出寒云外,人发暮雪中。寒气凛凛,如在雾中。明吴伟的《灞桥风雪图》,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画的也是灞桥风雪中的送别场面。在寒冷的风雪中,瘦驴、窄窄的小桥、远行者伤感的神情以及这寂寞的天地令人印象深刻。

在中国艺术的语汇中,雪总是和人的精神境界联系在一起的。雪后寻梅,是中国文人很喜欢表达的境界,画中也是如此。
明代江夏派名笔吴伟(小仙)的《踏雪寻梅图》,今藏安徽省博物馆,绢本,是一高近两米的大幅立轴,乃小仙中年后作品。由此作可见出画家放逸纵肆的特点,与要表现的精神气象颇相合。明代浙派大家戴进也画过《踏雪寻梅图》,戴的画细而文,和戴进相比,小仙的笔速快了许多,风格也更豪放。这幅画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但也不是全无法度。此画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寻梅归来,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桥头有一户人家,傍山而居,山坡上却有老树数株,枝干虬曲。高耸的山峰以乱笔扫出,山头野树上积满了雪,山下丘壑纵横,林木古刹在一片雪海中隐现,很有精神。在静绝尘氛的境界中,在白雪皑皑的天地中,人寻梅抱琴而行,小仙虽无言,但精神气度跃然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