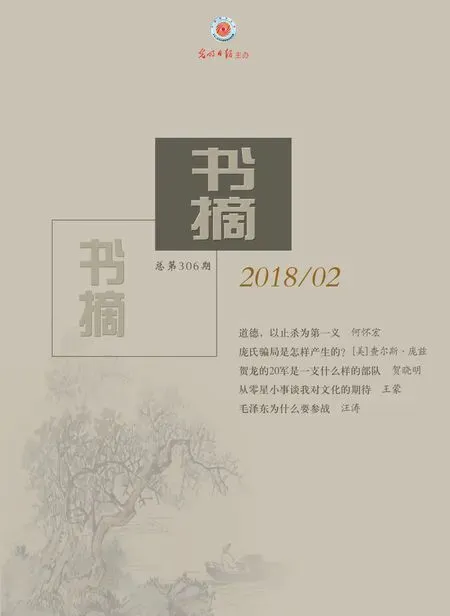我和央视结缘
——兼记民选台长落选
☉杨伟光 口述 刘世英 编著

不情愿接受的工作调动
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串数字:1985年7月16日。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再普通不过的日子里,我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机遇。只是那个时候的我怎么也没有意识到。
1985年7月16日,当时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副台长,早晨刚开始工作,电话铃声响起。
对方是时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的郝南平。他在电话里说:“是伟光同志吗?请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好,我马上来。”放下电话,我随即向他的办公室走去,却怎么也没有想到,那里等待我的竟然是一纸意外的“任命”。
“杨伟光同志,部党组决定调你到中央电视台任副台长。”郝部长满脸微笑,平静地向我宣布了这一消息。可是,我却完全无法平静,觉得脑子里“轰”一下就蒙了。离开熟悉的广播,去做陌生的电视?这太突然了!
于是,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我对郝部长说:“我对电台的业务比较熟悉,对电视比较陌生,能不走吗?”但是,郝部长只答复了我四个字:“已经定了。”
这个时候,我知道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便起身告辞。可是,这并不代表我就接受了任命。那天坐在办公室里,我的心里特别烦闷。晚上回到家后,还是没有想通,觉也没睡好。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再做一次努力。我当时认为我的理由是充分的。
从1961年毕业到1985年,我在广播领域工作了整整24个春夏秋冬,从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到新闻部副主任、工商部副主任,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这里是我事业的起点,也是我成长的学校。所以,对于广播事业,我有着深切的眷恋,从未想过要离开。这是其一。
其二,经过多年的摸索、积累和学习提高,我对广播领域已经驾轻就熟,正是可以大展拳脚的时候。而且不久前,我还在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广播会被电视冲垮吗?》的文章,论证广播不会被电视冲垮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时刻,我这个电台副台长居然要跑去主持电视工作,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儿?
当然,也有来自电视方面的担忧。我这个电视门外汉,一旦到了央视,他们能接受和认可吗?央视人才济济,其中不乏与我能力相当者,他们在央视苦干多年都没有当上副台长,对我这个外来者肯定会有抵触。此外,我对央视的业务不熟悉,也是很现实的问题,不能不做考虑。
于是,第二天早上8点,带着这些想法和顾虑,我直接去堵了时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办公室的门,希望部党组再考虑一下其他人选。
“这些组织上都考虑过了,你就按组织安排去吧。”艾部长的答复也是如此的斩钉截铁。此时我很清楚,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只能是服从组织的安排。这样想着,我的心情也平静了。
就这样,怀着无限的眷恋,我告别了熟悉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一年,我49岁。
站在今天,再度回首这段往事,我只能感叹:机遇往往降临在不经意间。在当时那个我不情愿接受的改变里,竟然隐藏着足以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机遇。
20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与广播、报纸等老牌媒体相比,几乎处在绝对的劣势地位,不仅是电视人,就连主管电视的领导也频频处于被动地位。中央电视台搞砸了1985年的春节晚会之后,一天收到几麻袋的批评信,上级领导越发感觉到加强电视领域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了。于是,他们决定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选调一个人到中央电视台去抓新闻,而我正是被他们选定的那个人选。
新官上任,我先不“放火”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我没有走这个路子,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点火,这火很可能烧不起来。所以,在来到央视的前两个月,我没有多说话,而是针对中央台节目质量不高(包括《新闻联播》)的现状,先是花时间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跟班参加《新闻联播》的审发工作和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结果发现,缺乏新闻意识是《新闻联播》存在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时效性差、信息量少,且缺乏新闻价值。
胡乔木同志曾说:“新闻的发表不光是论日子,而且要论钟点,耽搁一小时往往就耽搁了二十四小时。”而当时《新闻联播》的时效性很差,新闻部的记者下午三四点钟前拍的时政新闻通常要到第二天的《新闻联播》才播出。而且,新闻中的很多内容根本就不是新近发生的事情,最应该报道的一些“新近发生的、正在发生的”重要新闻却不能被及时捕捉到。
一方面,30分钟的《新闻联播》只播出十几条新闻;另一方面,一些没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事件播放时间长达三四分钟,好像小专题,严重影响了信息的新闻价值。
在调查的基础上,我和沈纪同志针对如何解决问题写出了《关于电视新闻改革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我们明确提出电视新闻的改革目标:要求把《新闻联播》办成要闻汇总,做到新、短、快、广。新闻应该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做到重要新闻不漏。时效迅速,重要新闻应力争比报纸快,努力发出正在发生和刚发生的消息。同时还要有自己的、具有电视特点的评论。评论要做到言之有物、旗帜鲜明、针对性强、短小精悍,语言生动;形式也应活泼、声形并茂,为群众喜闻乐见。
这份报告递呈给了时任广电部部长的艾知生同志,不仅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还得到了广电部的老部长吴冷西同志的大力肯定。他为这个报告做了一个很长的批示:“我在任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一定要把电视新闻搞好,但是一直没有实现,希望你们能够按照这个方案把电视新闻搞好。”
报告得到领导的大力肯定,我们打心底里高兴,这说明我们这数月的努力没有白费,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也是一个充满挑战和诱惑的旅程。
走上台长之路
在到央视上任后不久,台里举行了一次征求台长人选的意见调查,我竟然落选了,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事实上,在调任央视副台长之前,组织就找我做过一次谈话,主要内容是了解我对出任副台长的一些具体想法。在这次谈话之后,基本确定了这样一个思路: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和准备后,我将出任央视的台长。
对于落选的事情,我并没有耿耿于怀,而是对落选原因做了客观的分析,我认为主要有这么两点:一是央视人事关系比较复杂,这对于刚调任央视不久而且还是“半路出家”的我来说,显然极其不利。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当时我还没有做出能让大家认可的成绩。虽然央视台长是由上级部门指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个人能力”这一选项。有能力、有成绩才能服众。所以,对于这次的失利,我很快就释然了。
打破“先对内后对外”的新闻编排常规,在《新闻联播》中将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时爆炸的新闻放头条;首次播放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破产法》制定过程;直播第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实况;向全球转播党的十三大开幕式实况;克服困难,成功现场直播中国、日本、尼泊尔三国运动员登攀珠峰的壮举;打破广播时效性神话,以最快时效报道汉城(2005年1月19日,汉城的中文名称改为“首尔”)奥运会;高质量完成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的报道任务……终于,经过几年努力,央视改革有了明显成效,而我也终于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时刻。
“不管正在做什么,马上来我办公室。”1991年12月18日下午,我接到这个来自艾知生部长和王枫副部长的紧急电话。接到电话的那一刻,我敏感地意识到一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个时间正好是我审查当天《新闻联播》的时间,如果不是有要事发生,两位部长不会在这个时候打来这样的紧急电话。
我迅速赶到了艾知生部长的办公室。除了艾知生部长和王枫副部长,当时的央视台长黄惠群同志也在场。
没有寒暄,没有客套,一切能省的礼节也都省了。艾知生部长拿起办公桌上的一个文件,宣布了组织的决定: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杨伟光同志为中央电视台台长。从1985年7月16日接到调任的通知,到1991年12月18日再次收到任命,在央视副台长的位置上,我待了差不多七年的时间。说实话,这个过程比我想象的长了一些。
其实,我是真正意义上的“寒门子弟”——出生于广东梅县雁洋镇南福乡的一个贫苦农家,在我1岁的时候,父亲就去南洋闯荡谋生,后来病故在异国他乡。完全是母亲一个人,把我和姐姐、弟弟抚养长大,并省吃俭用供我读书。
那个时候的贫穷完全不是现在的年轻人能够想象的。因为贫穷,1948年小学毕业后,我不得不辍学回家种地。直到1949年冬,梅县解放了,我才重新回到学校。先考上了当地的松口中学,后又考入省立梅县高级中学。
因为贫穷,我14岁以前没穿过一双鞋,一直是打赤脚穿木屐;初中、高中都是依靠政府发放的助学金。也正因如此,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
1957年,我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后来这个专业合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第一次进京,我只带了一个小书包,里面装了几件旧衣服。到北大入学后不久,天气就转凉了。我当时还是单衣单被,床上铺的是稻草,幸好学校为我购置了棉衣棉被。学校每月还发放16.5元的助学金,其中12元用来吃饭,4.5元用来零花,所以,我非常感激国家和学校对我的照顾,一门心思认真学习。
也是因为贫穷,在京求学四年,我没有回过一次老家。一趟路费要七八十元,那时候家里根本负担不起。直到1961年,我大学毕业了,思儿心切的母亲卖了一头猪,然后把钱寄给我,我才得以回家与她团聚。
看来,贫穷让人痛苦。可是,也正是因为贫穷,让我受益匪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得感谢那些清贫的岁月,是它们成就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