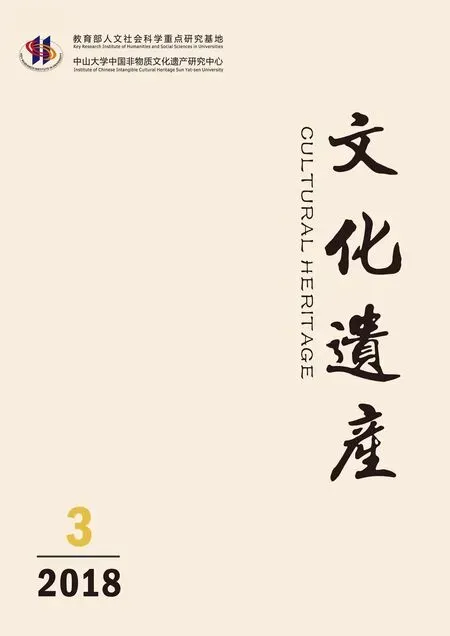“洪武赐曲”之说及其所蕴含的曲学史意义*
彭秋溪
所谓“洪武赐曲”之说,即指:洪武初年明太祖在亲王前往所在封国就藩时,以一千余册词曲赐之。这个说法,最早见载于李开先(1502-1568)《〈张小山小令〉后序》。后来中国戏曲史(尤其是明代戏曲史)的研究者,屡屡援引此说。就笔者所见,现今论著援引“洪武赐曲”的用意,主要有三种。其一,用以证明朱元璋试图以戏曲声色消弭亲王的政治野心,以达到稳固中央政权的目的。*此说较为普遍,凡述及明初杂剧发展史的著述,多持此论。其二,据以表明明初即已将戏曲纳入“礼乐”系统。*如李舜华《礼乐与明代前中期演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其三,用来展现康海(1475—1541*关于康海的卒年,参见金宁芬《明代戏曲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84页。)的曲学成就与明初戏曲文化之间的关系。*参见王瑜瑜《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413-414页。
而援引此说的著述,几乎不作任何考辨,即信而从之。然而,笔者以为,在李开先之前,并未见“洪武赐曲”之说,而如果此说不虚,乃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对于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意义不可谓不大。因此,有必要考察此说的虚实信妄,以及其所蕴含的曲学史意义。
一
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中云:“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对山高祖名汝楫者,曾为燕邸长史,全得其本,传至对山,少有存者。”*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44页。此为目前所知载录“洪武赐曲”之说的渊薮。
嘉靖十年(1531)春,李开先输饷宁夏,中途经过陕西乾州(今乾县),偶逢康海,归途中又前往鄠县(今户县)拜访王九思(1468—1551)。康海卒于嘉靖十九年冬,次年李开先被罢职还乡,而《〈张小山小令〉后序》作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原刻本该序末尾署“季冬腊日中麓再书”,则当为十二月。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中册,第644页)误作“十一月”。。从“对山高祖名汝楫者,曾为燕邸长史,全得其本,传至对山,少有存者”云云,来推想李开先的撰写语境,可知“洪武赐曲”之说,应来自康海无疑。而康海自正德五年(1510)赋闲于乡后,逐渐放浪形骸,寄情声乐与歌酒。则早在康、李初见的嘉靖十年或已谈及“洪武赐曲”,甚至早在正德五年康氏还乡后、寄情曲乐时,此说或即已在其友朋间传流。
然而,《太祖实录》、《大明集礼》(洪武三年成书)、《皇明典礼》(建文二年成书)、《大明会典》(弘治十五年成书)、《礼部志稿》(泰昌元年成书)等官修典章制度之书,只见载明初赐乐工于藩王,而无“赐曲”之说。此说若源于康汝楫,则有必要考察其大致履历。
《太宗实录》载记,永乐元年(1403)二月辛亥,升四川安岳县知县康汝楫等为北京行部左侍郎,并云“汝楫盖藩邸旧臣”*《太宗实录》第6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302页。。何景明(1483—1521)《雍大记》载云:“康汝楫,字济川,武功人。洪武初,举明经,为县学训导。太祖皇帝选天下文学知名之士教太子、诸王,乃以训导为燕王相,参录其军国事。洪武末,出为安岳知县。……有子曰海,弘治壬戌状元,官翰林院修撰。”*何景明:《雍大记》卷二十九“志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第18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250页。
另外,雷礼(1505—1581)《北京行部尚书侍郞年表》云:“康汝楫,陕西武功县人,洪武中儒士,永乐元年升行部左侍郎。二年,卒于官。”*雷礼:《国朝列卿纪》卷六十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第93册,第776页。又,《北京行部尚书侍郎行实》谓:“康汝楫,字□□,陕西西安府武功县人,洪武中以儒士荐授燕府训导,洪武三十一年,升四川安岳知县,永乐元年升行部左侍郎。二年,卒于官。”*《国朝列卿记》卷六十八,第777页。据此可知,康汝楫卒于永乐二年(1404)。
康海撰《先平阳府君夫人张氏行状》,亦云其高祖康汝楫“至昭皇帝时,始赠资善大夫、工部尚书焉”。*康海:《先平阳府君夫人张氏行状》,贾三强、余春柯点校《康对山先生集》卷四十五,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725页。又《先公墓碑》记云:“至仁宗皇帝时,侍郎始赠为资善大夫、工部尚书。”*康海:《先公墓碑》,贾三强、余春柯点校《康对山先生集》卷三十五,第611页。与雷礼等所记对比,可知康海对其高祖履历的追述,已经较为模糊,毕竟距其高祖亡故,已七十余年。而至李开先《对山康修撰传》载记康汝楫事迹时,已部分偏离事实,甚至出现讹误:“永乐初任工部侍郎,殁赠尚书。”*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中册),第917页。
揆诸上文,《〈张小山小令〉后序》作于嘉靖四十五年,彼时距康海亡故已二十多年,而康海、李开先时代前后,并没有其他文献载记“洪武赐曲”之事及其相关文字,则李开先所记“赐曲”之说,也是追忆,而非别有所据。“赐曲”之说,也当是对康海追述其高祖事迹的转述,是否有误差,本身就值得思虑。
李开先之后,周晖(1546—?)《金陵琐事剩录》所谓明武宗南幸,好听杂剧散词,徐霖等进献曲本“不止数千本焉。此章丘李中麓云”*周晖:《金陵琐事剩录》卷二“进词本”条,转引自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前言》(增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0页。,即从李开先而来(按,《闲居集》嘉靖间已有刊本流行),但却不提“洪武赐曲”之说。至万历,王骥德《曲律》中云“金元杂剧甚多,《辍耕录》《录鬼簿》及《太和正音谱》载六百余种,康太史谓于馆阁中见几千百种”*王骥德:《曲律》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7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2页。,则不知其所据。入清,梁清远(1606-1683)《雕丘杂录》(卷十五)亦提及“洪武赐曲”之说,文字与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全同,*梁清远:《雕丘杂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3册,第772页。亦当抄自《闲居集》无疑。再后来,焦循《剧说》(卷六)引述相关文字,即据《雕丘杂录》而来,同样未作辨析。*按,《雕丘杂录》此条之前,有所谓“传奇凡十二科”条,故《剧说》亦引之。
二
若“洪武赐曲”为历史事实,且“洪武初年”泛指洪武十年以前,我们不妨先对这一时期亲王就藩的情况作一番考察。
据《明史》所记,明太祖诸子封王、就藩情况如下:

朱棣(1360—1424)被封“燕王”,也在洪武三年,但就藩北平,乃在洪武十三年(1380)。很显然,康汝楫入燕府,自然在此之后。可见,“洪武初年”之“初年”,与诸亲王最早就藩的时间(洪武十一年),已不能相合。则“初年”之说本身已自相矛盾,何来“初年”“赐曲”之举?*按,今人李昌集曾对比朱权《太和正音谱》与《录鬼簿》《录鬼簿续编》所录剧目,对“洪武赐曲”之说已有所怀疑:“果如此,则朱权当得其赐,其《谱》中则应有相当数量的新资料,但《正音谱》录杂剧作家无一出《录鬼簿》,剧目亦绝大部分与之同,总不致所赐‘词曲’皆词与散曲(明中叶后人所云‘词曲’通常指散曲与戏曲)。作何解释,颇难斟酌。”显然,李氏对此说有所怀疑。惜其未再作考察,且未注意到“初年”的限定与其所举朱权之例并不合适(因为朱权就藩国,时间乃在洪武二十六年,已远非李开先所谓“洪武初年”)。参见李昌集《中国古代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1页)。
再考康汝楫入王府的时间。明太祖征聘儒士教导太子、诸王学习之事,在洪武元年十一月左右:
(洪武元年十一月)辛丑,宴东宫官及儒士,各赐冠服。先是,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图书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按,“太子、诸王”,当是追记之词。另外,依照明初王国礼制度,亲王十五岁“选婚出居京邸,至长始之国”,“之国不拘年岁”。参见《大明会典》卷五十六,《续修四库全书》第790册,第147页。,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上时时赐宴赋诗、商确古今、评论文字无虚日。*《太祖实录》第2册,第665页。另外,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四载记与此同,文字略异。按,张铨《国史纪闻》(卷二)载记同《皇明通纪》,而《礼部志稿》卷六十七记为洪武二年十一月,实误。
在此之前,洪武元年九月,太祖下诏访求贤达之士(所谓“诸儒”)共治国事。*《太祖实录》第1册,第629-630页。但综合何景明《雍大记》、康海《先平阳府君夫人张氏行状》,康汝楫在元末曾任武功县县学训导,最早或在洪武元年即入南京教导诸王。考虑到朱棣封王、就藩的时间,“为燕王相”、“辟为燕府官”应是追记之词,则康汝楫入北平为燕王府长史,最早在洪武十三年。洪武三十一年康氏被调为安岳县令(见前引雷礼《行实》),永乐元年复入燕府。若“赐曲”之说有所凭据,且“初年”所指时间段再往后延展五年——洪武十五年之前,则最早被封为藩王的秦王、晋王、燕王,分别在洪武十一、十三年就藩时,必在“赐曲”之列。
按,“定封建诸王国邑及官署之制”*《太祖实录》第2册,第818页。按,洪武三年正月甲午,“定王府官制:王相府,左右相各一人,正二品;左右傅各一人,从二品;参军府,参军一人,正五品;录事二人,正七品;纪善一人,正七品。其班位,各以其品秩列朝官之次。”参见《太祖实录》第2册,第951页。,在洪武二年四月。次年四月,太祖封建诸子,诏中即谓:“(诸王)皆授以册宝,设置相傅、官属及诸礼仪,已有定制。”*《太祖实录》第2册,第1001页。与此相应,就明初内廷文献记载而言,当时亲王就藩,所获赐物之中,并未见“曲本”在列。亲王之国,明太祖的确赐给藩王乐工二十七户。这为当时文献明确载记。但是,赐予藩府乐工的初衷,在于明太祖及其侍臣意欲扫清“胡俗”、重建汉唐礼乐系统。*参见拙文《论明太祖反“胡俗”及其与明初戏曲发展之关系》(待刊)。因此,当时京师、王府、地方政府均须配置乐工,以备祭祀、朝贺、宴会礼乐之需,而非单独赐给王府乐工,也并非仅仅为了娱情。戏曲作为“逸乐”的代表,在洪武时还没有进入“礼乐系统”的契机与渠道。而且,洪武初年被赐给藩王的乐工,无疑是元末以来的旧乐工,当时庆贺、祭祀所用的乐章尚不被赐予藩王,更何况并不被纳入礼乐系统的戏剧曲本?
笔者这一看法,还可以从后来大明皇室成员与中央政权的往来文书中得到印证:
(一)洪熙元年八月,赵王朱高燧获赐“乐工二十七户,及乐器、衣服”。*《宣宗实录》第10册,第213页。
(二)宣德二年二月,宁王朱权奏请补赐乐器、衣服:“宁王权奏,已赐乐工,而乐器、衣服之类未给。上命行在工部制给之。”*《宣宗实录》第10册,第652页。
(三)宣德十年九月,“赐梁王瞻垍乐工二十四户及乐器、衣服,从王奏请也。”*《英宗实录》第13册,第168页。
由上可知,亲王之国,被赐之礼乐系统,只有乐工、乐器、(乐工)服饰,并无曲本、乐章之类。
再退一步,即时在洪武三年四月,太祖昭告天下、分封诸亲王,当时的军事形势,亦不容太祖有“赐曲”之举,致生后患。
虽然早在洪武元年秋,朱明武装即已占领元大都,标志着元政权统治结束,但因元朝残余势力的争衡,东北、西北、西南战事并未因此消歇。这些史实,均可见于《大明太祖皇帝御制集》、《明实录》、《明史》等书。当其时,尤其是北方、西南地区尚未彻底平定,军事倥偬,国体未稳,太祖如何选择以“词曲”本子赐给亲王、消弭其政治野心?更何况,太祖一直视“优伶”为贱辈、戏曲为“淫哇”之俗曲,早在洪武初年,即便是将军饮酒、听乐,太祖即已因此而调离各军所在地的乐户,聚于京师(南京),以免妨害军务:
朕平定天下,勋业已成,而琐琐残胡,不能尽讨,致连年出师,劳民扰众,孰任其咎?朕姑为尔言之。今驻师去处,皆有房宇妻妾,身虽在外,实同家居,一也。肥马轻裘,纵意驰骋,不知下人饥寒之忧,二也。燕乐玩惕,因循苟且,不能谋事,三也。*朱元璋:《谕大将军徐达等勑》,《大明太祖皇帝御制集》(明内府钞本)卷三,中华书局编《稀见明史研究资料五种》(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09页。
这与永乐间刘辰(1335-1412)《国初事迹》载记相合*按,笔者所见诸版《国初事迹》未见此条标有年代。陈艳《明初教化思想对戏曲的影响》(《四川戏剧》2008年第6期)云此事在洪武十三年,不知何据。今不从此说。:“太祖立富乐院于乾道桥……专令礼房典吏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及舍人*舍人,太祖心腹之人。刘辰《国初事迹》:“太祖于国初立君子、舍人二卫为心腹,选文官子姪居君子卫,武官子姪居舍人卫,以宣使李谦安子[李]中领之,昼则侍从,夜则直宿更番不违。”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6册,第16页。,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太祖又为各处将官妓饮生事,尽起赴京入院居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6册,第12页。另外,此书尚有《借月山房汇抄》本、《泽古斋重抄》本、《金华丛书》本。另外,《客座赘语》卷六“立院”、“平话”条,即录自《国初事迹》。其中“立院”条末尾,顾起元曰:“彼时良贱之分如此,今澜倒尽矣。”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3册,第365页。
可见太祖对于边事之警惕,断不至于以“优伶”之辈,自埋隐患。何况太祖锐意以诸亲王镇守边地,牵掣地方军事力量,以图朱明王朝之更加稳固之余,尚且忧虑诸王性命(典型者见《谕晋燕二王勑》、《谕燕王勑》)。而且,明初亲王与中央政权政治斗争,大致在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朱标病亡前后,则把“赐曲”之说与“消弭诸王政治野心”关联起来的看法,显然混淆了史事的前后时间。
三
研究者或据《南词叙录》所载明太祖称赏《琵琶记》,用以展现明初内廷的演剧情形*持此类说法者,如李舜华《礼乐与明代前中期演剧》“第一章”、李真瑜《明代宫廷戏剧史》“第一章”等。,或是用来阐明太祖对戏曲的喜爱与“洪武赐曲”间的关系,亦有待商榷。
实际上,考察一下明太祖对戏曲的真实态度,《南词叙录》的载记,更偏向于“传闻之词”。《南词叙录》云:
我高皇帝即位,闻其名,使使征之,则诚佯狂不出,高皇不复强。亡何,卒。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既而曰:惜哉,以宫锦而制鞋也。由是日令优人进演。寻思其不可入絃索,命教坊奉銮史忠计之,色长刘杲者,遂撰腔以献。南曲北调可于筝琶被之,然终柔缓散戾,不若北之铿锵入耳也。*徐渭:《南词叙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758册,第411页。
然而,《闲中今古录》所载却与之不同:
元末,永嘉高明……因编《琵琶记》,用雪蔡伯喈之耻。其曲调拔萃前人。入国朝,遣使征辟,辞以心恙不就。使复命,上曰:朕闻其名,欲用之,原来无福。既卒,有以其《记》进,上览毕,曰: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羞百味,富贵家岂可缺耶?其见推许如此。今流传华夷,不负所学云。*按,笔者未见《闲中今古录》原书,所见只有明沈节甫所辑《纪录汇编》本、陶珽辑《说郛续》本。二书均为节本(《说郛续》题“四明黄溥言”撰)。本文所引此条,二书文字同。参见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纪录汇编》本),《丛书集成初编》第289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16页;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第9册)卷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74页。
两相对比,二者不同之处在于,一记作读剧本(所谓“有以其《记》进,上览毕”),一记为观戏。
二书孰先孰后,可以根据作者、成书年代推得。《闲中今古录》作者黄溥,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天顺元年在任四川提刑按察司*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五)“潜溪先生集”条,《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27页。,官至广东按察使。黄氏生卒年今虽不详,但据其登第之年,假如黄氏二十五岁及第,至正德十六年,已年近百岁;而徐渭生于正德十六年,其明年即是嘉靖元年(1522)。由是可知,《今古录》的成书,远在《南词叙录》前。*按,笔者所见《今古录》,为《纪录汇编》摘录本,已非该书原貌。四库馆臣批评《纪录汇编》:“诸书有全载者,有摘抄者,甚或有一书而全录其半,摘抄其半者,为例亦复不纯,卷帙虽富,不足取也。”从史源学的角度、太祖对女乐的态度(见后文)来看,《今古录》的载记,远比《南词叙录》可信。
此外,戏曲研究者,或援引周观政谏阻太祖纳女乐之事,用以说明太祖与明初演戏之关系。按,此事见《明史》“周观政”传:“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奉面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张廷玉等:《明史》(第13册)卷一三九,第3983-3984页。
但“女乐”不等同于“戏子”。“女乐”虽然是宋元以来对女性乐人的称呼,明代内廷各种节庆(元旦、圣诞等)礼仪中的承应者,也有被呼为“妇人”的女性乐人,但这类“妇人”承应的乐、舞,乃是被视为朝廷正乐、雅乐系统之一部分者。这从《明史》“礼乐志”所载可知,亦可从《元史》(卷七十一)“乐队”的记录,得到充分的理解。兹引《元史》“乐队”条下的“礼乐队”,加以明示:
礼乐队(朝会用之):引队礼官乐工大乐冠服,并同乐音王队。次二队,妇女十人,冠黑漆弁冠,服青素袍,方心曲领,白裙,束带,执圭;次妇女一人,冠九龙冠,服绣红袍,玉束带,进至御前,立定,乐止,念致语毕,乐作,奏《长春柳》之曲。……次八队,妇女二十人,冠笼巾,服紫袍,金带,执笏,歌《新水令》之曲……次九队,妇女二十人,冠车髻冠,服销金蓝衣,云肩,佩绶,执孔雀幢,舞唱与前队相和。次十队,妇女八人,冠翠花唐巾,服锦绣衣,执宝盖,舞唱前曲。……次妇女三人,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之曲终,念口号毕,舞唱相和,以次而出。*宋濂等:《元史》(第六册)卷七十一,第1775-1776页。
而朱元璋征所谓“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云云,并非巧言虚饰,确属实情。因为,“宫中音乐废缺”,乃是明初因裁革女乐之后,南京内廷用乐的实况。*徐学聚辑:《国朝典汇》卷一百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5册,第749页。
不仅如此,明太祖对优伶之辈始终保持距离之外,*按,太祖对平民艺术,并非毫无接触。如刘辰《国初事迹》载录太祖曾命人说书:“太祖命乐人张良才说平话,良才因做场,擅写省委教坊司招子,贴市门柱上。有近侍入言,太祖曰:‘贱人小辈,不宜宠用。’令小先锋张焕缚投于水,尽[发]乐人为穿甲匠,月支米五斗。”参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6册,第19页。亦多次告诫子孙毋得亲近优伶,臣子戒听逸乐。*朱元璋《谕勉群臣》:“恐群臣以天下无事,便欲逸乐,股肱既墮,元首丛脞,民何所赖?”参见何乔远辑《皇明文征》卷二十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28册,第472页。洪武六年正月,太祖对儒臣詹同云:“朕尝思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苟不知远之,则小人乘间纳其淫邪,不为迷惑者几人焉?况创业垂统之君,为子孙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谨。”*《太祖实录》第3册,第1431-1432页。因此,宋濂在《洪武圣政记》“新旧俗”中亦举此为一圣政:“上平日持身之道,无优伶近狎之失、酣歌夜饮之欢。”*宋濂:《洪武圣政记》,沈云龙选辑《明清史料汇编初集》第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41页。洪武十一年、十三年,太祖又训诸子,重申此意。*《国朝典汇》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4册,第374页。
太祖强调其“无优伶近狎之失”,虽不能据此断言太祖从未接触优伶,但至少表明太祖始终与优伶之辈保持距离。笔者的这个看法,还可以从太祖的以下史实得到佐证:
其一,太祖在《谕驸马都尉李祺还乡勑》中,斥责驸马“同诸小人日狎优伶以为至友”。*朱元璋:《谕驸马都尉李祺还乡勑》,《大明太祖皇帝御制集》卷五,第16页。按,李祺被迁往崇明之事,应与当时党争有关,日狎优伶的“罪过”,仅是其中之一。按,李祺尚临安公主在洪武九年,则太祖指责李氏狎优伶,当在此前后。
其二,《国初事迹》载洪武建元不久,“徐达围苏州,太祖特命指挥傅友德领军马三百,与同徐州陞[陆]参政出哨济宁,以警中原。赐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拨与歌妓十余人。太祖令内官觇视,得国珍令妓妇脱去皂冠、皂禙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太祖怒,令壮士拘执国珍,与妓妇连锁于马坊,劓去鼻。叶国珍称说: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锁。太祖曰:尔不遵我分别贵贱,故以此等贱人辱之。鞭讫[数]十,发瓜州做坝夫。后释之。”*刘辰:《国初事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6册,第20页。方括号内容为笔者据《丛书集成初编》本补。按,此条《丛书集成初编》本文字略有不同。
可见明初乐户的社会地位之低下,而太祖等视之为“贱人”*按,宋元以来,乐户即被社会普遍视为贱籍,明初依然如故,明太祖在《御制大诰》(初编)、榜文(如洪武二十二年榜禁军官人等习唱,斥之为“高贵复贱”)即是明证。的事实。而且,因为如此,太祖锐意以服饰制度,来区别庶人、优伶,则可以想见,太祖主观上绝无意于默许优伶随意进入王府、朝廷(藩府)礼乐系统。
四
揆诸前文所考,“洪武赐曲”已不可信,“一千七百本”之数,看似言之凿凿,而实际上应是捏合朝廷“赐乐工”、皇室藩府藏曲,以及明宪宗、武宗大力搜求词本诸事,附会而来。这其中,“赐乐工”制度的推行,是“洪武赐曲”之说产生的关键所在。
明初即已设立“教坊司”管理乐户,因长期战乱,當時“乐工”中多有“优伶”“娼妓”“娼夫”之流充任。*参见邱仲麟《明清的乐户:基于一种特殊官方体制的考察》(《明代研究》2015年6月第二十四期,第117页)引弘治三年国子监祭酒郑纪(1438—1513)《东园文集·修明祀典疏》:“教坊司本身以作乐为职,妻女以接客为生,其于交神之道,诚有不可窃记。国初人民稀少,京师寥落,故宽其法禁,以填实之。”如此一来,其中所谓的“乐工”传藏元代以来的曲本,在所难免。这些曲本,随着“乐工”进入各地藩府,亦在情理之中。需要指出的是,“乐工”进入藩府(或所管辖区),作为地方礼乐系统的重要部分,是经过礼部的干预、作为中央政府关联藩王的一项文化制度而得到执行的,是明初重要的文化举措之一。因此,“乐工”的被“赐”,本身已沾染“皇权”的色彩,而“曲本”因乐工进入“藩府”,被附会为皇帝所赐,显然是非常容易的。
而燕王府本为元代戏曲繁盛之地的大都,且家臣中不乏汤式、杨讷、贾仲明等曲学才人,曲本的创作、搜集,自然为王府的曲籍储藏,提供了基础。参酌宁王朱权、周王朱有燉的戏曲活动(包括剧本创作),可以想见其他藩府唱曲、演戏之盛,以及收藏曲本之富。所谓“一千七百本”,当与此直接相关。洪武十一年以后,康汝楫曾任职于北平,并预谋“靖难”诸事,直至洪武三十一年被调离燕王府,则其曾得曲本于燕府,也非完全没有可能,“受赐”之说,顺理成章。更何况“靖难”前后,燕府所处地位的“特殊性”*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朱标病殁后,秦、晋二王亦分别在洪武二十八年、三十一年相继亡故,诸亲王中实以燕王朱棣为长,故朱元璋在《谕燕王敕》中云:“朕之诸子,独汝才智克堪其任,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参见《大明太祖皇帝御制集》卷四,第424页。,也为“赐曲”之说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至于为何到正德五年(1510)康海削职归田、六年王九思亦解职归里、嘉靖二十年(1541)李开先被罢职还乡,“赐曲”之说才随之出现,笔者以为,应与当时戏曲的社会地位整体上升、北曲衰微有关。
如果从现存文人所作剧本来看,宣德、正统,尤其是成化、弘治以后,戏曲的发展,与明初几十年相比,明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可以从何良俊(1506-1573)《四友斋丛说》(隆庆三年初刻)所记,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证:
余应之曰:公奕叶簪缨,处通都大邑之中,所见如此,固不为异。余农家子也,世居东海上,乃僻远斥卤之处。……余家自先祖以来即有戏剧。我辈有识后,即延二师儒训以经学,又有乐工二人教童子声乐,习箫鼓絃索。余小时好嬉,每放学即往听之。见大人亦闲晏无事,喜招延文学之士,四方之贤日至,常张燕为乐,终岁无意外之虞。今百姓十九在官,十一在家,身无完衣,腹无饱食……*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第103册,第374页。
按,皇甫司勋,即皇甫汸(1497—1582)*皇甫汸,字子循,号百泉、百泉子。著有《长洲艺文志》二十四卷、《百泉子绪论》、《解颐新语》、《皇甫司勋集》等。传见《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其任苏州知府,在正德三年至七年间*参见冯桂芬等纂《(同治)苏州府志》(三)卷五十二“职官(一)”,《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区)第五种,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1435页。。可知皇甫氏谓其“小时”所见云云,即在正德初年。当时苏州(所谓“通都大邑”)地区演戏,似已相当发达,故长、吴二县专门提供戏资。而根据何良俊所述其“先祖以来即有戏剧”,则早在天顺、成化间,何家似已蓄养家班,至良俊少时(正德间),甚至聘请乐工教子弟学习声乐,而文人集会、“张燕为乐”,已成为常事。这些载记,已粗略显示出明代中叶以后的戏曲发展状况。
李开先本人藏曲丰富,却感慨当时元代旧曲本传流稀少,追慕“洪武赐曲”、宪宗武宗搜罗曲本之力度,则当时元代以来的旧曲籍,的确少见。李氏谓“今宜词曲少,而小山者更少”,“词曲”实指北曲(主要是散曲)*明前期社会重视的仍旧是成于文人之手的散曲,明后期才逐渐对剧曲的价值加以重视。元代刊行的《太平乐府》《阳春白雪》,以及明中叶以后所刊《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所收均以散曲为主,即是表征。参见小松谦、金文京撰《试论<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版本性质》,黄仕忠译,《文化遗产》2008年第2期。。也因此李开先序文中不仅以“小山”乐府来对称,而且以宪宗蒐罗杂剧、散曲,以及武宗搜集乐府、小令等故实,来作为叙述背景。这些文字,意在说明北曲本子在当时传流稀少的状况,故整理张小山乐府时,李开先特意强调“每样曲终,镂板不剔空,以待博学君子,词山曲海,不惜寄示”,以望大成。
李开先对北曲衰微的感慨,显然透露出其对俗文学发展中“喜新厌旧”(或“推陈出新”)的文艺规律的无奈,而戏曲、散曲作为俗文学的代表,恰在其中。成化、弘治以后,戏曲的发展已取得新的成就,尤其是南戏、传奇,在以江浙为代表的江南地区,正悄然蓬勃发展。*参见黄仕忠《<香囊记>作者、创作年代及其在戏曲史上的影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而家居山东的李开先,却汲汲于北曲的蒐辑整理,似有意重振弦索、维护北曲的社会地位。当然,这与康、王、李三人的交游、曲学渊源或不无关系。
细寻“洪武赐曲”之说的产生、流传,以及此说之所以能附会成言的缘由所在,似与当时朝廷“赐乐户”制度的衰落有关:
(一)宣德十年九月,英宗赐梁王“乐工”二十四户,十一月赐襄王“二十余户”(均见前引)
(二)正统八年五月,英宗从礼部尚书胡濙等奏,“梁府原设乐工十二户、厨役十人,今梁庄王已薨,宜存留乐工三户、厨役四人,其余乐工宜发有司为民,厨役起送光禄寺应役。”*《英宗实录》第15册,第2106页。
(三)继宣德十年三月,英宗“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为民”*《英宗实录》第13册,第65页。,天顺元年五月再放教坊司“乐工、乐妇四百八十六名,各还原籍从良”。*《英宗实录》第20册,第5947页。天顺八年正月,昭告将内府医生、厨役、乐工等“年老不堪应役无丁替者,悉放为民,有司另行签补。其起取乐工原係良人者,仍发原籍从良当差”。*《宪宗实录》第22册,第20页。
(四)成化二十一年七月,礼部奏言教坊司乐工所奏中和韶乐“多不谐协,而善弹瑟及箜篌、击钟罄者殊少,恐因循失传,渐致大乐不备”。*《宪宗实录》第27册,第4536页。
从这些内廷文献的记录,可以大略见出明代中叶以后“赐乐工”制度逐渐衰落的事实。*按,台湾学者邱仲麟对明中叶以后朝廷赐给藩王乐工的情形亦有所考述,见氏撰《明清的乐户:基于一种特殊官方体制的考察》。随之而来,朝廷坚守的“雅乐”,由此亦受到冲击,后人也因此对“赐乐”一事渐生隔膜。这无疑在客观上,为后人信从“洪武赐曲”之说,营造了一个“雾里看花”似的文化氛围。
虽然“赐曲”之说已不可信,然而“赐乐户”却是明初中央政府确立的关联封建王国的礼乐制度之一。这是中国古代前所未有的“创举”。戏曲怎样由此获得发展的推力,以及“赐乐户”制度的衰落对戏曲的影响,均有待探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