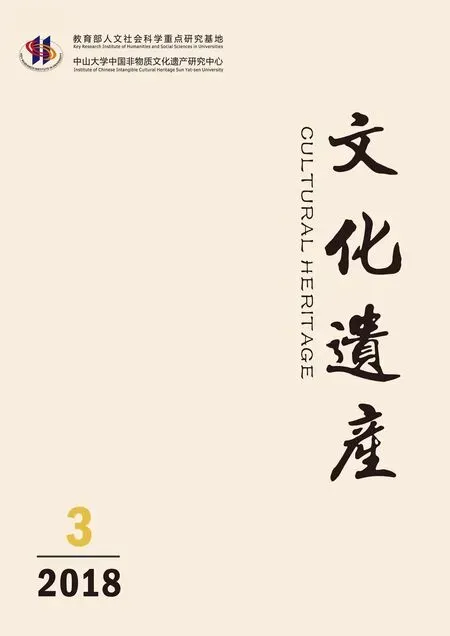“采茶”人生路
——粤北采茶戏国家级传承人吴燕城访谈录*
王静波 采访整理
吴燕城,粤北采茶戏国家级传承人、国家二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戏剧协会韶关分会理事,曾任韶关市第五、六、七届市政协常委。主演多部采茶戏作品,包括大型古装戏《白蛇传》《生死牌》《恩仇记》《皇亲国戚》,大型现代戏《红灯记》《爱情审判》《一撞钟情》《人生路》《紫色风流》《青山水东流》《母亲岭》《霜雪山梅红》等。吴燕城的艺术人生,伴随着粤北采茶戏几十年的变革和发展。她是粤北采茶戏表演艺术的杰出传承人,也是粤北采茶戏发展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2016年7月14日,笔者很荣幸地采访了吴燕城女士。她多年的老同事李学慧女士*李学慧(1955-),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人。1979年调入韶关采茶剧团工作,至2010年退休。曾在《恩仇记》《皇亲国戚》《人生路》等剧目中担任角色。与之同行。与吴燕城和李学慧共事多年的陈中秋先生*陈中秋(1946-),湖南湘乡人,剧作家、词作家。196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70年分配至韶关地区文艺办公室从事文艺创作,1981-1983年任韶关地区采茶剧团团长,1987年调省文化厅任副厅长,2000-2008年任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为访谈提供了场所——广东省京剧促进会办公室。访谈在融洽的氛围中进行。
一、与文艺结缘:连县的 成长经历和进入训练班
吴燕城出生于1949年。她的家就在连县县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各艺术团到连县的演出、年节期间民间的欢庆演出、家附近的连县歌舞团的平日训练,以及父母爱好的熏陶,在她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文艺的种子。巧合之下,她进入了韶关地区采茶剧团训练班,在那里开启了她与粤北采茶戏长达半个世纪的缘分。
王:吴老师您好。作为粤北采茶戏的研究者,我对您已经久仰,非常荣幸有这次宝贵的采访机会。我们从您的成长经历谈起吧。首先想请问,您在连县长大,您成长的环境对于您后来学习和从事文艺事业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吴:谢谢你对于粤北采茶戏的关注。
我成长的环境对我从事文艺有很大影响。我们连县原来艺术方面还可以。因为我们是大县,我们那里有个大广场,韶关很多地方的团体都到连县演出。韶关那时候有粤剧,还有杂技,韶关歌舞团也经常去演出。原来每个县都有歌舞团,连县也有。另外湖南有祁剧、花鼓戏,都会去演出。我们小时候很爱看,经常放学以后去看。他们演白天场,到下午四五点钟开演一会后,不用再买票了,我们就去看最后的一两场。
逢年过节,不只在剧场演,白天还围着墟镇、在广场上、街上演出。我最记得采茶歌,是歌舞团演的,演员拿个茶篮,拿个扇子。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我们在街上围着看。连南歌舞团有瑶胞——跳舞的瑶胞,也会经常出来演出。这个氛围对我在文艺方面有启蒙的作用。以前歌舞团来演出,我很崇拜那些演员。我有个同学的表姐就在韶关歌舞团的,他们那时候歌剧团挺出名的。他们去演出的时候,我同学偷偷带我进去,后来同学的姐姐演《洪湖赤卫队》《雷锋之歌》,我们都上后台那里去看。
我家在学校住,我妈是老师。刚好连县歌舞团住在我们学校大门里头,在文化馆里面。所以他们每天练嗓子练功,我们听得见、看得到。另外我母亲也喜欢搞文艺,我父亲喜欢美术,这些都对我热爱文艺影响很深。
王:我听到您与李老师交谈用的是粤语,您的母语不是客家话?您什么时候学会客家话的?
吴:我是来到团里才开始学客家话的。我们连县是客家地区,县城就是(使用)白话,也有部分人讲客家话;周边很多人都会讲客家话的。连县语言非常复杂,因为靠湖南,又有湖南话,还有连南的瑶胞(讲瑶语)。(客家话)我听得多,但是在家里没讲过。后来来到韶关以后,我们一句句跟着台词走,学习客家话,所以我们的客家话不是那么准。韶关的客家话有好几种,有曲江客家话、翁源客家话、南雄客家话,不同地方的客家话有所不同,我们就以曲江的为主吧。我们觉得曲江的比较白,容易听。我们团讲的话也基本以这个话为主,平时在生活中,我们很少使用。但是在舞台上念台词的时候,我就会慢慢跟着走。顺了以后,现在就会说。
王:连县本身采茶戏氛围怎么样?
吴:我小时候对采茶没什么印象,只觉得是跳舞唱歌。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农村的人也会出来唱唱春牛啊,拿个大头啊,或者花篮、扇子啊,演演那些带采茶的文艺形式。
连县有一个叫唐家村的地方,是采茶的发源地之一。唐家村的西岸这个地方,农民一唱开口就是采茶调,就等于唱山歌一样。采茶戏的发源地之一还有南雄的南亩。*根据《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广东卷)记载,粤北采茶戏的来源分三派:“南雄灯子”,源于南雄的龙凤茶花灯;“韶南大茶”,源于旧韶州府以南的纸马花灯;“连阳调子”,源于连阳舞狮唱调子的狮子堂。参见《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广东卷),中国ISBN出版中心1996 年,第1784页。我小时候读书到处去*吴燕城的母亲是老师。在小学四年级之前,吴燕城随着母亲的工作调动在连县不同的乡镇生活和念书,到四年级返回连县县城。,不知道这些。我是来到团里以后,差不多演戏演了十来二十年后,才慢慢去关心这些。以前我们除了排练演出就是下乡,很少专门去研究什么,后来慢慢有时间了,去了解它,才知道那个地方是发源地。
王:您的采茶戏基础是在哪里打下的?
吴: 我的功底是在训练班的时候打下的,才三个月。不过那时候年纪小啊,很容易。再加上是有一些天分,不用压腿就可以劈叉的。那时候也容易上手, 老师教什么都记得住。而且当时整个学习氛围是很浓的。我们下乡,等公共汽车来的时候都要压腿,车还没到,我们就拿木头箱、道具箱,就开始练。有时候有些老同志也挺热情,看出来哪里不对,就提醒一下。自己也有心,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也认真去看,慢慢积累下来。
王:1963年,您进入了韶关地区采茶剧团训练班。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去考训练班了呢?
吴:我家住在文化馆旁边。考试的时候,是采茶训练班来招生。那时候我刚好小学毕业,就陪着我们同班同学去考试,我没想考。后来老师说:“你也唱一首吧”,我就唱了《洪湖赤卫队》的一段。结果好像那个同学没有被录取,我被录取了。我爸妈不让我来,那时候我太小了,才13岁多,又考上中学了。我妈对戏的印象也没有那么好,对歌舞的印象好一点。
后来,第二次采茶训练班招生,刚好派了歌剧团的一个人代表采茶班招生,他就直接找到我们家了。我爸妈听说是歌舞团,就说:“你去试一下吧。”那时候还正在放假,我听了之后很高兴,就坚决要来了。之后他们说是采茶训练班招生。我就问歌舞团招不招生,招考人员回了韶关打听,说歌舞团叫我去复试。那时候交通不便,去韶关也不容易,我是跟着我爸学校的毕业生,刚好考上韶关技术学校的学生一起来的。复试以后就没有回去了。
到了之后,刚好歌剧团没有小学员,人家也下乡演出了,结果又把我丢回采茶训练班去学习。我也很高兴,因为采茶训练班有好几个是连县招来的。采茶训练班办了三个月,我就被分到团里了。分配的时候,采茶剧团在排《血榜恨》,导演叫王弢。在采茶训练班,学员们都很熟了。我来都来了,觉得能唱歌跳舞就行了,也没管分到哪个团。加上那时候采茶还是比较兴旺。歌剧团下乡呢,不吃香;采茶一下乡很热闹。分配的时候,我就说“好啊,去哪里都行啊”,就在采茶剧团里一直待到退休。
我父母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很大。我小学毕业就进入剧团,写信还是有错别字的。我父亲把我寄回去的信中的错别字,拿红笔圈住改掉,又把信寄回给我。这些信到现在我还留着。
王: 采茶剧团训练班的教学方式是怎样的?

具体的曲牌当时还没有教我们,以教我们发音、练声、练气为主。那时候大家的声音还像小孩一样的,不统一。到团里头以后,排练的时候才跟着老演员学唱曲牌。老演员唱,我们就听,自己有时候也琢磨一下。进了戏以后,有戏排了,我们也进到曲牌里头去了。那个时候我们的曲牌还是挺地道的,是一整套一整套的。该是什么人物,就按曲牌套进去。
王:您在师承关系里讲何瑶珠是您的老师,能谈谈她对您的影响吗?
吴:首先是艺德。因为我来到团里的时候,她就是主演,是这个团的花旦。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团里面的大戏包括《血榜恨》《牛郎织女》《刘三姐》等等,都是她担纲。一举一动,我都很认真地向她学习。他们老一辈演员在台上表演很认真。另外,我们虽然是学员,老同志很关照我们。以前下乡条件很辛苦,去到一个地方,有一间房子就不错了。他们就说,你们这些小孩住里面,我们就住外边吧。排练的时候,她对我们也挺严格的。她虽然不是(像)导演那样地指点你,但是平常演出的时候,她会给你提建议。
唱功方面,我的声音没她好。她的声音很漂亮,人家叫她“小郭兰英”。细节方面的东西,一个她,一个罗发斌*罗发斌(1936—2009),广东乐昌人,粤北采茶戏著名演员。1956年进入粤北民间艺术团,演艺生涯基本在粤北采茶剧团(后改称“韶关地区采茶剧团”“韶关市采茶剧团”)度过。应工以丑行为主,在《张三借靴》《王小二过年》《女儿上大学》《人生路》《青山水东流》等剧目中担任角色。(处理得好)。虽然我学不像,但是他们演出的时候,我会认真去听。特别刚来团里的时候,她演的都是大戏,长的唱段比较多。我的性格比较内向一点,我喜欢听了以后,慢慢地琢磨,有时偶尔问问他们。我没有正式拜她为师,但是我就默默地认为她是师傅了。
王:您对包括何瑶珠在内的老一代演员的艺术风格有怎样的印象?
吴:何瑶珠是老一代的艺术家。他们戏比较浓,唱比较下功夫。他们比较好地传承了传统,但向前发展地少一点。他们表演起来虽然有动作,但是舞蹈少一点,只是拿两个扇子动一下,但采茶的味道是很浓厚的。
王:根据您的学习和这么多年的积淀,您领会到的采茶戏的特色是什么?
吴:采茶戏主要反映的是我们这片区域客家劳动人民的生活。它本身有三大特色:走矮步、竹筒袖、扇子。它是把劳动使用的道具、生活中的动作,艺术加工成歌舞道具和动作。茶农经常在山上跑,摘茶叶要半蹲,炒茶也是蹲,所以农民在劳动过程中自己动脑筋,对很生活化的动作进行艺术加工,变成采茶戏里的“矮子步”。竹筒袖也是类似的。它原来是腰上绑的一条带子,有些堂倌用它扇扇凉、抹汗。把它变成表演服装以后,就做了半个袖子,这个特点,其他戏剧绝对没有的,是采茶独有的。另外,扇子的使用也是很普遍的,劳动人民上山时经常会使用。采茶戏就把这三个结合起来,这是动作的特点。采茶戏的服装也有特点,不像才子佳人戏的服装是有水袖的。
另外,采茶戏的唱也有特点,一段一段小调地唱。它原来是唱山歌的,就是一段一段地唱。山歌里头有很多词:看见一棵树他唱树;看见花他唱花;看见你,他就跟你对歌。就像讲话一样,只是用音律唱出来。它的小调慢慢演变,就像歌一样,也挺好听。采茶戏的曲牌有很多,就是看到什么唱什么。
脚色方面,一般都是“两旦一丑”:旦脚是小旦,不叫花旦;一个是彩旦,是泼辣一点的农村妇女;还有一个小丑。最早是三个脚色,由“三脚班”发展成采茶戏。
王:传统粤北采茶戏的表演有流派的区别吗?
吴:有,分南派和北派。我们团虽然小,我也从中看到和了解了一点。谢福生*谢福生(1936-),韶关市曲江区人,粤北采茶戏演员。应工为丑、武生, 在《王小二过年》《阿三戏公爷》《青山水东流》等剧目中担任角色。他们那一代,就没有说是具体的哪一派了,什么好就取一点。对于流派的区分,我知道一点。在唱法方面,一个是地方语言、发音不一样;另外,北派更戏曲化一点;南派就白一点,就是现代一点,粗犷一点。做功方面,北派比较美,开放一点,动作方面,矮步上取中高桩比较多;南派矮步比较多,粗犷一点。从唱腔到表演,南派没有北派那么优美。韶关没有多大,所以南派和北派其实分得不是很清,它的区分没有大剧种的派别那么讲究。
二、崭露头角:舞台上的历练
训练班的学习结束以后,吴燕城便正式登上舞台。她从出演小角色开始接受锻炼。不久,政治运动袭来,粤北采茶剧团也受到冲击。幸运的是,她在军分区宣传队、粤北文工团等文艺单位,仍进行着艺术方面的积累。粤北采茶戏移植现代京剧《红灯记》时,她出任李铁梅,开始崭露头角。
王: 您在《探山》(1963)中出演角色小青梅,您自己说过这是舞台实践的开始,能谈谈当时的感受吗?
吴:《探山》我不是A角,我是跟着A角来唱,唱的一般是小调、小曲牌。有一段表演,要甩辫子、走圆场。那时候是小孩,开始上台有点紧张,手忙脚乱。
王:您入团不久,就到了文革时期,粤北采茶剧团也受到影响。*编者注:1965年,粤北采茶剧团被抽调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1968年,全团进入“五七干校”。1969年,韶关地区革委会从“五七干校”抽调原剧团四五十人,组建“韶关地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在全区专业、业余宣传队中选拔人员,扩充成近百人的“粤北文工团”。参见范炎兴:《粤北采茶戏》,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9~51页。您参加了军分区宣传队,后来进入粤北文工团。这段时期,您都参演了一些什么样的节目呢?
吴:那时候小歌舞挺多的。我参演了联合队*据吴燕城回忆,1971年,专业和业余的几个单位合在一起代表韶关地区文艺界参加省调演,所以称“联合队”。的《一根扁担》《红色饲养员》《红灯记》片段,后来又演了《红灯记》全剧。《探山》中,我负责打锣。那个时候小,什么都学一下。
王: 粤北文工团用粤北采茶戏移植了现代京剧《红灯记》。在这部戏中,您担任李铁梅B角。可以说从这时候起,您开始承担有份量的角色。您可以聊聊这当中的心路历程吗?
吴:演《红灯记》的时候,我心里很怕。文工团的乐队比较大,有五六十人,又全部是精英,其中大部分是音专*全称为“广东音乐专科学校”,为星海音乐学院前身。的毕业生,他们比较有才华,也很严格。我就硬撑吧。那时候我在宿舍里贴了一张李铁梅的照片,一天到晚对着她,一点点学。之前我只看过几次电影,是别人到广州学习,学回来以后告诉我是怎么演的。
李:她演《红色饲养员》的时候是演一个小孩,我看了。她演小戏的时候都是演小孩。所以一开始曾有人怀疑,她这么矮小,能演成人的女主角吗。演《红灯记》的时候,还没有麦克风,她嗓子是比较细的那一种,就有人担心她节奏跟不上,担心乐队听不到,等等。我看到她在台上的演出后,觉得她胜任这个角色绰绰有余。后来大家看到她演得这么好,认可了她。
王:您曾经提到郭仙梅、周思明等前辈对于您的帮助,具体影响是怎样的?
吴:郭仙梅原来是珠影*即原“珠江电影制片厂”。演员队的队长,下放到英德,后来又被我们韶关抽去。周思明是省话剧团的,也是团长。他们在艺术界都挺有名气的。周思明对我的印象很好。他觉得我演戏有另外一种风格和味道。那时候(我)年轻吗,记忆力也还可以,模仿样板戏模仿得很细。对于能不能胜任演出那么大的戏,唱那么长的唱段,我确实有点怕。他说试一试,演吧,所以他对我的鼓励很大。郭仙梅很严格,她是演员队的队长,演员出一点点差错都不行的。她对我影响也很大。我那时候是有压力的。压力归压力,人家那么信任你,我还是硬上了。
王:样板戏剧目是怎么用采茶戏这一地方剧种来表现的呢?观众的接受程度又怎么样呢?
吴:采茶戏把样板戏移植过来,是以采茶唱段为主。音符都要是一样的,不能变,主要是唱腔发生变化。用采茶来唱样板戏的时候,音乐是搞音乐的人创作的。作为演员,唱的时候会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原来是京剧吗,移植以后,观众说我们是唱京歌。但是那时候不能改。只能按唱腔,唱自己的声音,按节奏来哼,一点都不能动,一个小音符也不敢动。表演也是按样板戏的。样板戏就是这么严格。这种形式观众也是喜欢的。我们去每个县演,观众都很热情,很多人看。
王:您个人觉得,在这段时期,您获得了哪些方面的成长?
吴:那时候开了一个头,胆子大了不少。在文工团自己也锻炼了不少,唱歌、杂技、变魔术,都有所接触。
王:在这个阶段,您对采茶戏的唱法是否因此出现了一些变化呢?
吴:其实在唱里边,我内心有过很多的斗争。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文工团(的时期)。文工团有歌剧团。歌剧唱法和戏曲的唱法不同,我就在当中纠结,自己不知道向哪个方面走。我为什么没练得很深的嗓子呢,因为那时候我斗争地很厉害:光是唱戏呢,好像觉得声音很单,觉得自己年轻,应该尝试新事物;但是说唱洋、唱歌剧吧,不适用于采茶。你能唱出一首歌来,但是唱戏不一定能唱得完,因为气息不同。所以说,那时候我的思想斗争很厉害。我的声音是细的、单的那种,应该说唱戏曲比较合适。但是我那个时候又想唱唱歌,既然在文工团,我也想学一学。后来1974年以后分采茶团、歌舞团、杂技团,我被分回采茶剧团了,那时候我才决定:你还是唱回采茶吧,不要学那么多。从那时候开始,我才向这方面琢磨。采茶的发音很蹩,但唱得是有味道。那时我参加了一次唱歌比赛,我就按土的唱法来唱。有些参赛人员声音唱得比我顺,很好听,结果我还得了第一名。其实可能搞曲子的人懂,这个就是“味道”“风格”。那时候我的想法还没真正理清楚,但是我觉得既然比赛,就按戏曲吧,人家就说“有韵味”。
三、融会贯通:担纲期的摸索与创新
1974年,韶关地区采茶剧团得以恢复。文革结束后,随着文艺氛围回暖,粤北采茶戏渐渐恢复生机,剧团也在摸索采茶戏的发展道路,传统戏、古装戏、现代戏并举。吴燕城在各种戏中都曾出任核心角色,也曾担任编舞,对于在坚持采茶戏本色的前提下,如何打通它与其他大戏剧种、话剧之间的表演技法,将自己接触和学习过的民间歌舞、现代歌舞融会贯通,她有着切身和独到的体会。在多种角色的磨炼当中,她渐渐走向成熟。

吴:改革开放之前呢,有段时间古装戏不能演。1977年左右,恢复古装戏,剧团演的是《十五贯》,在韶关演了三个月,场场爆棚。因为观众很久没机会看了吗,另外这个戏也很热闹。
恢复传统的时候,比较热闹。“百花齐放”对我们这个剧种比较有利。虽然这个剧种不是很古老的那种,但也是几百年过来的,有一些传统的东西,继承它们对我们剧种的发挥会很有帮助。不过那时我个人正在恢复排古装戏。
王:1978年,剧团排练大型古装戏《白蛇传》,您扮演小青。您是怎么进行古装戏基本功的学习和训练的?出演古装戏,您有哪些体会?
吴:这出戏我演的青蛇。道具有刀、剑什么的,戏里有踢枪,所以肯定是要练的。老师是黄文富*黄文富(1941-),广东省佛冈县人。担任韶关市采茶剧团团长多年,曾任演员、导演等。,还有一两个(老师)是杂技的。那是文工团时期过后,所以有杂技的(演员),都一起练功。我也去增城看了两场粤剧,看了之后就自己琢磨。
那时小孩才三个月,我还在产后恢复的阶段。孩子就放在排练场。白天练功辛苦,晚上小孩都没奶吃。最苦的是第一场化妆。我是第一次尝试古装戏,要戴冠,头纱不扎紧怕它掉,扎紧了头酸得不得了,还没出场就想怎么办。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再后来我们下乡演了好多场。
王:这一时期排演了不少新的剧目。既有现代戏,像《爱情审判》(1979)、《一撞钟情》(1981移植现代戏);又有古装戏,像《皇亲国戚》(1982)、《真假王岫》(1983)等。现代戏和古装戏哪个更受观众欢迎?采茶戏的古装戏演出是否存在一些困难呢?还能运用采茶戏的表演程式吗?音乐又如何设计呢?
吴:我感觉我们那时候演的戏下去,观众没有说不喜欢的,古装戏和现代戏都很爱看。就是现在下到农村,我们那一代都会很喜欢看。
古装戏好办。因为采茶戏离不开矮步。本身男生穿的服装都是竹筒袖,拿的都是扇子,所以人家有个说法,“手巾、竹筒袖、扇花”是不离手的,跟矮步结合,动起来就是绝配。另外古装戏有很多程式动作,比较花一点,可以把它用上去。现代戏就要考究了,看什么角色该用什么动作。因为服装不同了吗,同样是走矮子步,要看是什么人物,英雄人物和反派肯定是不同的,所以比较考究一点。
采茶原来是曲牌体,没有板腔,后来慢慢发展到板腔。发展到演大戏以后,就要看创作音乐的人怎么去编曲,很多相当于从头作曲。我演过那么多大戏,所以有体会,每个曲子都不同了,但是采茶的调也有所保留。采茶戏使用板腔体音乐,早在五十年代演古装戏《牛郎织女》*《牛郎织女》为粤北采茶剧团成立之后移植排演的第一部戏,参加了1959年韶关地区专业艺术会演。其唱腔音乐由饶纪洲设计。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是饶纪洲作曲。大戏如果没有板腔,人物根本不好唱的。
李:我最佩服她演的《皇亲国戚》和《人生路》,她都是演的一号,花旦。剧情里面需要她怎么表演,如果今天导演排练的时候跟她说了,她做不到,她也不会胡乱去表演。但下一次排练,她就能做到。她能把导演要求内心怎么处理,表演上比如舞蹈、身段怎么做,很正确地反映出来。她就住在我家楼下,我从来没有听她练练唱、讲讲台词啊。一回排练场,就看到她的变化。
王:那应该是您回去之后不停地在琢磨吧?
吴:会的。做饭切菜都在那里想台词的。脑子里都会想,也不是刻意的。
王:《人生路》*根据路遥小说《人生》改编。编剧陈中秋、张云青,作曲蓝曼,导演陈东明。该剧于1983年参加广东省新编剧目观摩调演,1984年参加首届广东艺术节演出。的演出将您推上了演艺事业的高峰,您在这部戏中扮演女主角“巧珍”。您对塑造这个人物角色有什么心得体会?当时在塑造巧珍的时候,是否考虑加一些采茶戏的动作特点?
吴:那个角色确实印象很深。我记忆最深的是第二场卖鸡蛋,那个唱段我下了不少功夫,身段也做了不少研究。另外还有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高加林变心以后,她去找高加林时的表演。巧珍是一个农村姑娘,单纯朴实,对于角色那时候的思想变化,我自己很有感触。另外还有“寻梦”那一段,她神情恍惚;还有最后跟高加林见面,跟马三结婚;还有一段就是她在井边跟德顺公交流。因为要演到人物里面去,要带着感情。角色是我自己创造的,一点一点想出来的,肯定有印象的。
这个戏里面有很多采茶的动作。而且角色戴有头帕,我特意把它拿下来当手巾用。剧中就有很多手巾(的动作)了。
我们那时候创作角色,不像现在有录像(能加以模仿),就是自己看剧本。看了剧本之后,需要自己思考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形象。导演只安排你从舞台哪个位置进场,哪个位置出场,安排位置调度。你把唱词、台词背熟以后,你的歌配什么样的动作要自己编,怎么出场,怎么走法,人物的形象塑造,都要靠你自己去(设计)。那时候对我的锻炼确实很大。
王:那演采茶戏的现代戏跟演传统戏有什么区别呢?
吴:现代戏就很生活吗,做功没有那么多,以唱为主。传统戏很多做功,很多动作。演现代戏也不会有很多困难。因为我们没有很多功底作为局限。不像京剧、粤剧,一招一式都有程式。我们一练就是民间歌舞动作,就像跳舞一样,当然表演起来是稍微收一点,没那么大幅度。一演起现代戏,我们就很自如。不会像那些(大戏剧种),演现代戏走路都不舒服。
王:1995年《母亲岭》您饰演“山姑”、2000年您饰演《霜雪山梅红》中的“山梅”,您对于这些人物角色的创作有怎样的体会?您个人最欣赏哪个戏?
吴:《母亲岭》跟《霜雪山梅红》的角色截然不同。《母亲岭》故事发生的时代是革命时期,《霜雪山梅红》的主题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致富,这两个角色性格不一样。排练《母亲岭》的时候,我们借了广东省粤剧院的钟汉秋做导演。他的手法传统一点,布景这些都是按原来古老一点的样式。排这个戏的时候就是按照程序、按照对人物的理解慢慢去走。这个角色,我觉得自己进步不是很大。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霜雪山梅红》。原来广东话剧院的周瀛跟他妻子梁咏两个人都是导演。他们很细心,很认真地去考究,他们甚至半夜睡不着的时候就改道白,考虑怎样讲观众能够接受。对这个人物,每一个动作、道白、眼神,他们都会亲自帮我磨出来。台词轻重,他们都会慢慢地帮我理。有些道白,偶尔也运用了话剧的道白。他们导演手法活一点,任我发挥人物。但如果有不到位的地方,又会马上提醒我。所以这个角色,我觉得自己提高比较快。除了《人生路》印象比较深,这个角色也是不错的,自己觉得比较有戏,演得投入。
王:您接受话剧影响是从这个戏开始吗?
吴:也不是。以前也经常会借鉴的,但是真正地有人指点,还是第一次。
王:《青峰山传奇》(1986)您担任编舞,这个戏也产生了较好的反响。对于粤北采茶戏中舞蹈的编排,您有怎样的理解?怎样使戏剧作品保持采茶戏和粤北民间的特色?
吴:我们排《青峰山传奇》,2/3都是采茶歌舞。那个剧本写得很巧,有要把粤北民间的东西给皇帝看的情节,我就想借这个节目把粤北民间文艺展示出来。我在里面运用了春牛、纸马等民间舞蹈,我想到了小的时候在连县看过的春牛、纸马,刚好用上了。道具师傅也很认真很配合,制作了好多道具——扇子、花篮、龙头、凤尾、鱼肚、春牛、纸马,等等。
与老一辈艺术家单纯做戏不同,我们这一代演员接触面广一些。我们吸收了其他剧种的一些特点,也要逐步地对采茶戏有所发展。在军分区宣传队和文工团的时候,我也接触吸收了一些歌舞,也把它运用到这个戏的编舞当中。
李:《青峰山传奇》舞蹈全是她编的,吴老师排第一个舞蹈的时候,就要求我们:虽然大家都不是学舞蹈表演出身的,但是可以把韵味表演出来,一定要把采茶歌舞的特色表演出来。我们这个舞蹈跳得非常好。到省里演出的时候,本来没有群众奖的,加了一个群众奖。*《青峰山传奇》导演陈东明,编剧杨澄璧、朱玉醒、郭福平。该剧于1986年参加第三届广东省艺术节,获剧本创作三等奖、表演艺术二等奖、舞台美术一等奖、音乐唱腔三等奖、艺术革新奖、导演二等奖以及演员个人奖、群众演员奖等奖项。
四、坚守:传承生态的变迁及对发展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由于粤北采茶戏佳作频出、屡屡获奖,韶关曾被称为广东省的“戏剧强市”。近三十年来,与全国其他剧种一样,粤北采茶戏也经历着政策环境变化、娱乐方式多样化等的洗礼。与粤剧等大剧种相比,粤北采茶戏的抗冲击力稍弱,得到的扶持也相对有限,其作为地方小剧种的尴尬处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于当下它的传承和发展状况,老粤北采茶人往往感到心痛。作为国家级传承人,吴燕城一方面身体力行,践行着传承的职责;另一方面,她也在对采茶戏的发展出路进行着思考。
王:粤北采茶戏一直有下乡演出的传统,你们的演出范围有多大?
吴:多数在韶关境内。那时候韶关地区很大,包括新丰、翁源、连县、连南、乐昌*1963年6月起,韶关辖1个市15个县,为韶关市,曲江、乳源、仁化、乐昌、始兴、南雄、英德、翁源、连县、连南、连山、阳山、清远、佛冈、新丰。1970年10月,改设为韶关地区(辖区不变)。后又经几次调整,2004年5月起辖3区7县(市),为浈江区、武江区、曲江区,乐昌市、南雄市、始兴县、仁化县、翁源县、新丰县、乳源瑶族自治县。……但是我们多数走新丰、翁源、曲江、始兴、南雄,我们在清远一个县都走半年呢,在那些乡镇都有人看的,一个晚上演几场。像一些很小的镇,白天根本看不到人,就只有几个合作社、供销社开门,晚上就好多人来看,而且还有人买不到票,还要订票。
王:20世纪80年代,轻音乐开始流行,它也影响到了剧团的演出。1985年,粤北采茶戏曾吸收流行文化,编排音乐歌舞节目,二位老师能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李:八十年代,我们也去歌厅唱歌。那时候叫轻音乐,有老板承包的。从我们团请五个乐队成员,请几个歌手,唱当时最流行的《酒干倘卖无》《是否》《雨中即景》这些香港老的歌星的唱段。慢慢地我们自己也组织了一个轻音乐团。采茶本来载歌载舞,我们曾经把轻音乐团叫“山茶花”轻音乐团,结果没多久就失败了。
吴:那时候经济开始紧张了,团里靠自己多了,迫不得已向社会求生存。那时还没有(开始)差额拨款*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许多院团已经开始实施“差额拨款”。这个制度的实施,是为促进剧团走市场化的道路。韶关市采茶剧团是从1992年开始实施“差额拨款”,即只发放工资的60%~70%,对于“差额”的部分,剧团需要通过商业运作,从市场挣回来。,但是办公费什么的已经比较欠缺了。我们也尝试过把《斑鸠调》之类的唱进轻音乐,也挺受欢迎的。本身调子比较活跃。那时候卖票,要经济划算,要是只演采茶戏可能一下子没人接受了。我们那段时间很少下乡,整天围绕轻音乐,都在城市里头演出。
王:出于什么原因,那时候放弃了在乡村的演出?
吴:要是下了乡,租赁场地要花钱,要自己找酒店,住宿、车费都要花钱,肯定要亏本。所以只能在附近县城演出。《青峰山传奇》时还挺正规的。那个戏以后,就说文艺界要改革,轻音乐一阵风吹进来,剧团又要搞差额单位了。那时候三四十个人下去乡镇,一个公社已经不好接待了。像韶关每个乡镇的剧场都没了,拆的拆,变的变,搞成歌厅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少下乡,多数走大城市了。
王:1989年剧团排大戏《青山水东流》,风气是不是好多了?
吴:好多了。那时候又有调演*指1989年第四届广东省艺术节。了,后来我们还是恢复原来的样子。轻音乐搞的(时间)不长,试过一两年,还是回到创排大戏。
王:1979-1980年间,采茶剧团分客家话队和普通话队巡回演出,演出的对象分别是谁?接受度如何?您个人如何看待采茶戏演出的语言问题呢?
吴:演出对象都是下边的县、镇,农民多。因为有很多工矿,讲普通话。我们(客家话队)就是去新丰、翁源这些讲客家话的老采茶区,群众特别热爱采茶。普通话队有些现代歌舞节目。因为我和李老师都会讲客家话,而且我们原来也演戏,所以被分到客家话队;有些(演员)是其他省来的,客家话讲得不准,就分在普通话队。
对于采茶戏演出使用的语言,我们现在的看法是应该保留客家话。这是它的特色之一。本身这个剧种没有很多传统留存下来的东西,地方戏就是使用地方方言的。为了广泛宣传,或者推向全国的话,也可以偶尔变一变,像粤剧讲英语一样,但不是长期的。回到这个地方,要改回来,这是你的根。
王:您现在带徒弟吗?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吴:我们很少说收什么徒弟之类的。他(她)认真好学,跟你联系,只要能的话,我就指导他们。这个一定要有心,没有心,再有条件,没有用的。现在不是以前的戏班了,不可能说我叫你来跟我学。
学生里面我指导比较多的是张波和王云芳。张波现在是韶关文化馆副馆长。去年韶关采茶剧团解散了以后,他考上文化馆。他很用功,之前他排每一个戏都会叫我去辅导。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他对业务还是很有信心的。王云芳现在是南雄文化馆副馆长。她原来是翁源县的,后来调到南雄。她一向对这方面很有爱好,也有兴趣钻研。我原来不认识她的,她找过我好几次。通过省、市局搞的个人大赛,我跟她才有来往。她很认真,很刻苦,现在南雄也是主演。现在南雄的节目也是她一手负责了,而且主要角色她都会担当。*本段所介绍的是2016年采访时的情况。
王:您认为对于粤北采茶戏的传承,困难在哪里?应该如何改善它的境况?
吴:困难之一在于缺乏人才,剧团招不到人。这些年剧团招人挺苦的。从90年代开始,外省的,包括江西的,我们招了很多。有些人来了,有的条件挺不错的,等学得差不多了,因为没有指标,人家又走了。一个真正的戏剧人才很难得。以前挑演员,声音、条件、形象都要挑。另外,演戏要有悟性,要有心。戏剧的表演需要慢慢地磨炼,能坚持下来。也要有好的环境,给他们充分的角色和机会多演戏、多锻炼。
如果想传承好,应该办个学校,最起码可以办些培训班。一方面学员来源广泛,一方面方便传习。单个传授也可以,但不是长久之计。要是有资金,就像粤剧院一样办个学校或者办个班,这样可以把老一代(演员)都动员起来,一起来传。
粤北采茶戏需要更多的重视和政策扶持。赣南有一些措施值得学习。他们有个艺校,办有采茶训练班。赣南还有一批一批的老艺人,不管退休了也好,没退也好,他们都集中起来研究,等团里演出一回来,就有新的戏出来给他们练,给他们学。赣南采茶戏是大剧种,在当地的地位相当于我们的粤剧。
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小剧种,在广东的一个角落,自身条件有限,所以受局限。现在粤北采茶很孤单的,它有四个脚色,有丑、生、花旦、彩旦。现在只有一个小旦(花旦)行当有传承人,其他脚色都没有传承人。演整个戏的话我可以帮忙,但不是整个套路都理得起来。所以我们这个剧种,肯定要多几个这方面的人。这几十年,我发觉自己积累的表演经验的来源包括几支:我们吸取了一些老艺人传下来的采茶戏的特点;赣南的东西我们很接近,大同小异,我们也吸取了一点;还吸收了别的剧种一点东西,这样自己慢慢琢磨出来。
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政府和社会的扶持。一些统筹组织的工作需要政府来牵头。作为国家级传承人,这几年我尽量去跟人打交道,但是跟学校等单位的联络,需要政府出面。目前韶关建立了一个传承中心*2015年,韶关市采茶剧团一度停止演出和解散。2016年5月,在多方努力下,“韶关市粤北采茶戏保护传承中心”成立,粤北采茶戏又有了自己的传承和演出队伍。,也是很好的消息,可以充分利用起来,开展传承工作。这几年我年年去南雄搞集训,都是他们的相关政府部门来安排。他们有热情,去组织了,我尽我的能力来传。只要人家用得上的,我都会去。
另外,采茶戏也缺少观众,要培养观众。观众的流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我们先要演起来,把传承的工作做好,来吸引观众。
王: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您认为采茶戏可以向其他剧种、其他艺术样式学习什么?又应该保持哪些要素?
吴:很多东西应该向其他剧种学习。很多套路要规范,例如说动作、表演,因为毕竟是小剧种,演大戏虽然能演出来,但还是在深度上有所欠缺。这些方面要向大剧种学习。
要保持住地方的东西,首先就是客家话了;另外就是矮子步、袖筒、扇子这三个特点;此外还有它的曲牌音乐;在表演上,它也是有独特的东西,比如小丑、彩旦各有自己的特色。
王:请您回顾几十年的采茶人生路,做一个总结吧。
吴:我在剧团几十年,是很幸运的。我能够担当大梁,一个是运气好,当然也下了一点苦功。另外也碰上了一帮舞台好姐妹,她们帮了我不少。比如下台赶妆,不用叫,马上来帮忙,有点什么事就互相关心、互相帮忙。我们团互相之间很关照。另外,我这一辈子能演上几个大戏,也碰上几个好导演,这很难得。你喜欢搞这一行,很难碰上好老师。团里面每次比赛,都从外面请导演。其他方面也有一些老师,对我也挺关照的。我13岁就到剧团了,是采茶剧团把我养大的。来的时候不知道是搞什么,也没有恒心。唱戏吧,开始感觉一般;歌舞吧,挺喜欢,后来是慢慢地搞上这一行,看到观众的热爱。有人说“采茶很土的”,就算是再土,我们觉得好像也没这个想法了,对它是热爱的。不改行,也是因为这个热心。搞的时间长了,待了几十年,对这一行业确实是有感情了。
王:您对年轻一代采茶人寄予怎样的期望?
吴:希望当然很多喽。很希望他们能够接上班,也希望他们有心传承下去。这毕竟是几百年的历史流传下来的,是我们韶关地区特色民间戏。如果丢失了,我们广东就损失了这样一个特色的东西。我希望年轻人能把它继承下来。
王:吴老师,感谢您与李老师接受今天的采访,也谢谢陈老师一直给予的帮助和支持。希望这篇采访刊出以后,能够唤起更多人关心和支持粤北采茶戏。
后记:
与笔者之前对于一位著名演员的设想有所不同,吴老师性格偏于内敛,不事张扬。继续接触之后发现,吴老师是一位格外的有心人。她在讲述自己的艺术成长历程时,经常提到自己在默默地观察、揣摩;谈起粤北采茶戏,脉络非常清楚,话不多,却都讲到了要点;而与笔者结识之后,她也在关心着笔者的成长。吴老师演戏被评价“别有一番味道”,而她的经历也说明,成为一名好演员的道路并非千篇一律。《人生路》是粤北采茶戏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吴燕城老师的代表作,而她也一直走在粤北采茶戏相伴的人生路上。这条路虽然艰辛,但她在言谈之间是幸福的,她也希望,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能够选择采茶人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