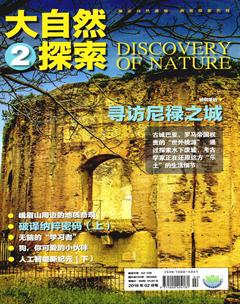无脑的“学习者”
杨宇琴
对人类和很多动物来说,记忆和学习与大脑功能和一系列复杂的神经活动有关。而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些结构较为简单的生物虽然没有大脑却也能学习。箱形水母、海兔和海星都是无脑学习的典型例子。也许这并不算什么大新闻,毕竟,这些生物也并不是没有神经细胞,只是它们的神经元在体内的分布较为分散,并不聚集成束。严格来讲,是神经元使它们拥有学习的能力。
那如果连神经元也没有呢?地球上大部分生物都没有神经元,但它们却可以随意做出复杂的行为。以前,科学家们将这一现象归结为生物历经数代进化出的先天反应,但现在看来,这些不起眼的非神经生物似乎真的可以学习。这让科学家感到不可思议。一些科学家正努力探寻它们的学习机制,而另一些科学家则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利用这种能力,来为对抗疾病和设计智能机器提供新的思路。
神奇的黏菌
黏菌是一种不寻常的生物,它既不是植物、动物,也不是细菌或真菌。它通常看上去像一滴落在地板上的柠檬酱。这种外观只是黏菌生命一个阶段的表现,在这个阶段,大量有自己独特DNA的单个细胞混合和融合在一起。由此产生的黄色斑点可以长到几平方米大,而整个斑点只是一个内含成千上万个细胞核的巨大的细胞。
沿着枯木“爬行”的黏菌。
在自然界中,当黏菌沿着森林的地面爬行时,它依靠分布于其表面的化学感受器来感知道路上的物质。如果黏菌感受到任何有吸引力的东西,如食物,它就会迅速有规律地跳动,使自己接近那个东西。如果黏菌遇到毒素等有害物质,则产生相反的反应,黏菌会减慢其规律的跳动,收缩身体,远离潜在的伤害。
黏菌行动缓慢,最高速度只能达到每小时4厘米。但黏菌的可移动性为研究人员在实验中带来许多创意。2016年,法国科学家迪叙图尔及其团队用黏菌做了一系列实验。他们准备了黏菌爱“吃”的燕麦,并将燕麦有策略地放置在黏菌无法触及的地方,仅留一座“桥梁”可容黏菌爬过。然后,他们在桥上放置了咖啡因等黏菌不喜欢的物质。尽管这些物质的浓度不至于对黏菌造成伤害,但也足以延缓黏菌通过的速度。最后,黏菌还是屈服于食物的诱惑,通过了桥梁。
随着时间流逝,黏菌通过桥梁的速度加快。几天之后,黏菌已经能完全忽略咖啡因等物质。也就是说,黏菌在逐渐适应这些物质。这是一种简单的学习方式,即对无关线索的反应会随着时间减弱。这令研究人员很惊讶,因为黏菌并没有神经,而在此之前,所有学者都认为学习的能力依赖于神经系统。
黏菌的学习机制
如果不是神经系统使得黏菌能够学习,那又是什么呢?科学家推测,黏菌的经历改变了它们的基因表达。细胞核内有些分子可以结合到DNA上,以激活或停止某种基因的表达。它们不会改写基因序列,但可以暂时改变它的读取方式。这一过程被称为表观遗传调控,它满足了对记忆和学习的最基本的要求。有科学家认为,这就是黏菌学习的方式。
类似的学习机制也存在于海兔中。海兔又称海蛞蝓,它没有大脑,只有少量神经细胞。根据神经生物学的相关理论,当动物学会某件东西时,记忆就会被储存在相邻神经元之间的突触中。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海兔进行了反复刺激,使它记住了这种刺激。然后,他们打断了海蛞蝓在训练中形成的突触,结果不出所料,这些记忆消失了。然而,当用电流刺激神经元时,神经突触会重新生长,记忆也会恢复。研究人员认为,这些记忆会以表观遗传变化的形式储存在神经元的DNA中。科学家由此推测,其他类型的细胞也可能发生类似的变化,这令没有神经系统的生物也可以学习。
海兔,一种无壳的软体动物,因具有数量少而体积大的神经元而常常被用于神经生物学研究。
通过训练适应了盐的黏菌(H)很快通过了含盐的桥,获得了食物。而不具适应性的黏菌(N)则长时间被阻挡在桥边。但经过充分融合后,所有黏菌都学会了快速通过盐桥。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黏菌不仅可以学习,它们还可以互相传授知识。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将已经对盐产生了适应性的黏菌与未经训练的黏菌融合在一起。结果,混合黏菌毫不犹豫地迅速通过了一座含盐的桥。三个小时后,他们又将混合的两部分分开。原本未经训练的那部分黏菌却在通过桥梁时能继续忽略盐的威慑,好像之前对适应盐的那部分黏菌通过某种方式,将它学习到的知识传递给了“同伴”。对于这个现象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黏菌在融合过程中,交换了表观遗传信息。
植物也会学习
含羞草在受到某些外界刺激(如觸碰)时,会迅速合上叶片。
除了像黏菌这样的单细胞生物,没有神经元的多细胞生物似乎也有学习能力。而这其中的生理机制就更难解释了。因为它们有更多的细胞,而且这些细胞还必须相互协调,共同完成某种活动。当没有神经系统来整合和协调时,它们是怎样学习的呢?
澳大利亚一个研究团队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们反复将一些含羞草从15厘米的高度扔向地板上的软垫。刚开始,含羞草在坠落时,会“惊恐”地合上叶片。但经过约5次安然无恙的落地之后,含羞草就不再合起叶片,仿佛明白了这种坠落不会给它们造成伤害。甚至在静养一个月后,再一次的坠落实验也不能引起任何反应。含羞草“记住”了之前的经验。
豌豆苗实验模型:用Y型管套住小苗,一组的光源和风扇在同一方向,另一组则在相反方向。
观察到植物的习惯化现象后,他们想更进一步。既然巴甫洛夫通过长期训练狗,可以使狗听见铃声(无关刺激)就想到食物(奖励)。那么,能否让植物也学会把一种奖励和无关刺激联系到一起呢?
科学家们对豌豆幼苗进行了训练。众所周知,植物具有向光性,幼苗的向光生长尤其明显。研究人员把豌豆苗放在黑暗中,然后从一个特定方向照入光线(奖励),并在相反的方向放置风扇吹风(无关刺激)。而另一些豌豆苗,则设置为风和光线从同一方向进入。训练结束后,他们把光源移除,仅使用风扇对所有的植物吹风。结果发现,那些适应于光和风来自同一方向的豌豆苗逐渐向风扇方向生长,而那些适应于光和风来自不同方向的豌豆苗逐渐远离放置风扇的方向。这些植物似乎在寻找它们的奖励。它们已经学会将风和光联系起来。
一些科学家对这一振奋人心的结果略表怀疑。有学者认为,这個关于植物习惯化的初步理论缺乏有力的支持证据,应该在在初步证据的基础上建立理论之前,把支撑材料再准备丰富一些。另外,在动物的联想学习实验中,大约90%的受试动物会做出反应,而植物实验中只有60%的豌豆苗做出反应。还有一个质疑的重点则在于学习的定义。根据神经生物学相关理论,学习和记忆都是头脑中进行的心理过程,而这一过程集中发生在大脑中。按照这一定义,植物是无法学习的。
无脑生物的启示
当然,不是所有科学家都赞同这种严格的定义,也有些学者对植物学习的机制颇感兴趣。动物神经细胞中有一种叫做NNDA受体的分子,这种受体可加强在同一时间被反复刺激的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动物将同时发生的事件联系到一起。有科学家推测,在植物中应该也有类似的“关联分子”。科学家认为,一定有某种系统能让这些记忆被记录下来,并正确地储存在生物体中,当植物受到相应刺激时就会触发记忆。
这种机制可能很难理解,不过只是意识到无脑的生物体也有学习能力,就已经可能带给人类一些实际的回报了。有很多单细胞生物对人类非常有害,例如导致疟疾的疟原虫,它和黏菌都是原生生物,以前从来没有人想过这类生物是可以学习的。科学家认为,了解病原体是否能够学习以及如何学习,有助于研究出防治它们的新策略。
了解表观遗传学习机制也可以帮助计算机科学家改进人工神经网络。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模仿动物神经网络行为进行信息处理的算法数学模型,人工智能的算法基本都是基于这一模型建立的。目前的神经网络模型基于赫布的学习理论——当两侧的神经元同时激活时,突触就会变得更强。换句话说,那些同时被激活的神经元会连接在一起。有科学家认为,将表观遗传记忆的概念也融入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将会使这种模型更丰富。
记忆转移
而黏菌相互学习的现象还让一些科学家想到一种关于“记忆转移”的理论。如果一个黏菌能通过与另一个黏菌融合来传授知识,那在动物身上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吗?半个多世纪前,美国科学家麦康奈尔的实验表明,动物身上也可能会有类似的现象。他对淡水扁虫进行了训练,通过反复在电刺激的同时予以光刺激,来训练扁虫对光产生恐惧。然后,他把它们磨碎,喂给没有受过训练的扁虫。之后,每当有灯光闪过,这些未受训练的扁虫就会抽搐。
麦康奈尔认为,那些受过训练的扁虫的记忆被编码成小分子,未受训练的扁虫将这些小分子吞下后拥有了同样的记忆。他的实验不具可重复性,因此这一结论并不太可信。但是,在当今的许多科学家都认同一种相似的观点:小RNA(一类表观遗传分子)可以激活记忆。一位神经生物学家说:“通过将RNA从一种动物的大脑转移到另一种动物的大脑来实现转移某些方面的记忆,原则上说,这不是不可能的。”而如果记忆转移真能实现,将造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
貌不惊人的淡水扁虫(涡虫)囊的能传递记忆吗?
也有一些科学家对记忆转移持更谨慎的态度,但不完全否定生物体间可以传递某些适应性或敏感性的可能。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当我们对自然界的了解越多,就越不会轻易否定某种可能性的存在,因为大自然中有太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了。
不需要大脑
人类全身有约860亿个神经元,其中,大脑皮层的神经元数量就达到了160亿个。而有的生物只拥有很小的脑或根本没有大脑,却具有惊人的能力。
黏菌:没有神经元
当研究者将黏菌的食物按照模拟东京周边城市布局放置时,黏菌会将自己的菌体扩散形成一个网络,这个网络与经过精心规划的日本东京铁路系统非常相似。
日本东京及其周围的铁路网络(a)和黏黼体网络(b)。
经过训练,大黄蜂能把小球搬到指定位置(黄色圆圈内)。
豌豆苗:沒有神经元
研究人员提供给豌豆苗两种生长环境,一种营养供给稳定,另一种营养非常丰富但可能之后会变得贫瘠。当豌豆苗本身养料充足时,它们会更倾向选择前者;但当豌豆苗本身养料不足时,则它们更倾向于赌一把,为更多潜在的奖励冒着风险选择后者。
箱形水母:约13万个神经元
箱形水母可以使用它们24只眼睛里的其中4只来透过水面观察树冠,以指引自己穿过红树林沼泽。
箱型水母
淡水蜗牛:约2万个神经元
一个仅由两条神经元组成的回路决定着淡水蜗牛是否进食。控制神经元感受食物的存在,动力神经元向大脑传递饥饿感。
果蝇:约2.5万个神经元
果蝇在分辨非常相似的气味时花费的时间比分辨差别很大的气味时花费的时间更长,这说明它们是在思考后而不是冲动的做出判断。
大黄蜂:约100万个神经元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用一个特殊装置训练大黄蜂,让它们学会通过拉动一条绳子吃到糖。然后一批未经训练的大黄蜂也被放入这个装置,这些大黄蜂可以通过观察被训练过的大黄蜂,学会拉动绳子。通过训练,它们还可以将一个小球搬运到指定目标上。
联系的力量
巴甫洛夫的狗学会了把铃声和即将到来的食物联系起来。这是一种简单的学习方式,但它也许可以造成某些看似复杂的动物行为。
以黑猩猩用石头做工具砸开坚果为例。这种精密的行为被认为是目前观察到野生动物界最复杂的行为之一。而黑猩猩可能是通过一种被称为“反向推理”的过程,将一系列小步骤联系在一起,从而学会用石头砸开坚果。首先,黑猩猩可能从它妈妈那里偷来带壳的坚果,并将坚果与美味奖励联系在一起:之后,当它用石头敲打坚果时,将这一行为与美味奖励联系在了一起;之后,手握石头又变成一种奖励……如此重复,直到黑猩猩可以熟练使用这一工具。做完这一系列事情几乎不太需要推理,但是一旦事件链条建立完整,黑猩猩就增加了一项高级技能。
这种方式对简单生物体影响深远,甚至一些植物也可以通过联系来学习。那么,原则上来说,即使一个神经元也没有,它们也可以通过反向推理学会更复杂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