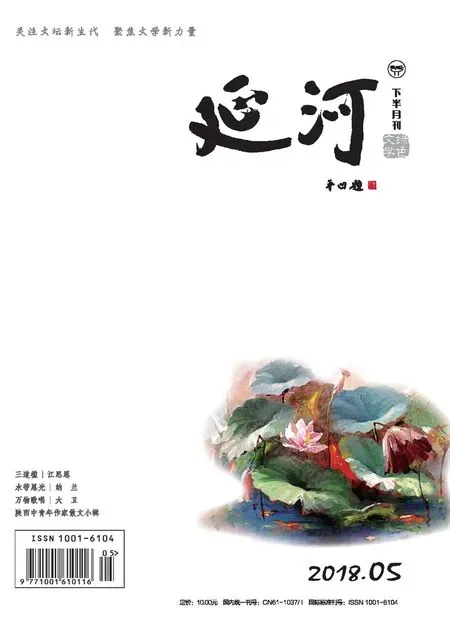艺术对照录
丁小龙
暗光与暗涌
博尔赫斯是一位对时间、迷宫、永恒与哲学充满玄思妙想的作家。这种瑰丽甚至怪异的思想来源于对祖先们事迹的追忆与思考。例如,他的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便是对此记忆的探究与发现。这本诗集首版只发行了300本,但博尔赫斯却声称此诗集是他以后所有作品的清澈源头。同时,也来源于广阔的阅读与高端的审美趣味。在少年时期,他便翻译了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的王子》,后来将这位极端的唯美主义作家视为知己,尽管他们所呈现出来的写作风格迥异万千;他学生时代已将《神曲》《浮士德》与《荷马史诗》等大部头通读了好几遍。在《七夜》这本书中,他声称《神曲》是所有文学的顶峰。
后来,他成为图书馆馆长,这是他一生中最满意的职业之一。因为每天只需要用一个小时便可以将那些事务性的工作处理完,然后将整个自己献给书籍与写作。去工作的路上,他阅读的是荷马史诗、维吉尔或者霍桑的原文书籍,听着风,将自己幻想为风的国王。
在哈佛大学的诺顿讲坛中,他谈论诗之谜、隐喻以及诗人的信条等话题。这些演讲稿汇集成书,取名为《诗艺》,成为与贺拉斯相互映照的名作。但是,这本书并不是探讨诗歌的方法论,这本书就是诗歌本身。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视力“像黄昏一样逐渐消逝”,但并不影响他的写作。他在永恒的黑暗中用口述方式探讨永恒史。也许,这更是一种写作的象征体:他返回到荷马时代的写作方式。
用这种追根求源的方式去探讨这位阿根廷大作家本身就是一种危险:那些外在的表象并不能反映出他内心的风暴,那些社会学意义上的考据无法替代他美学意义上的形而上思考。博尔赫斯一生酷爱哲学,但声称自己从来不是思想家。他喜欢的哲学家有德国的叔本华与英国的休谟,但他又不同意任何人的观念。他具有自己的审美体系,这种体系具有强烈的超验风格。
我最近重读了他的文论集。在这些论文中,博尔赫斯再次表明了自己的美学立场。这种立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反对既定的权威。现在随手摘抄几个:1.对于德国人而言,《浮士德》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对于其他民族而言,它是著名的引起厌倦的方式。2.《神曲》缺乏一个人物。他不在那里,是因为他太具有人性了。这个人就是基督。3.济慈的《夜莺颂》不可能给“原型”下一个定义,但他在很早之前便设想出来了叔本华的前提。4.霍桑最好的作品是他躲在屋子里面写的那种神鬼怪诞之作,而不是喋喋不休的《红字》。5.《尤利西斯》是一本让人无法阅读的糟糕的巨大的书,而不是伟大的著作。乔伊斯是被严重高估的作家。
其实,每个真正的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美学观和文学史。每位作家在阅读的时候都会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双重审判:对艺术客体意义上的审判以及对个人主体意义上的审判。文学史或者艺术史本身就是一本庞大的无言之书。
博尔赫斯对永恒有着惊人的热烈玄想。他说世界本身就是一首永无止境的诗歌,每个诗人的作品都是其中的注脚、分支与诠释。同理,世界本身就是一本无言之书。我们所做的就是用不同的语言符号来对其进行辨认与确定,但这种尝试在哲学意义上就如同西西弗不断推动的石头:永无止境,永远重复,永远失败,但又不停地从头开始。
我喜欢这种哲学意义上的失败,因为其赋予了写作一种悲剧之美。这本浩瀚的世界之书如同《圣经》中的巴别塔,终有一天会倒塌:倒塌意味毁灭,但毁灭又意味重生。这多么类似于我们的生命本身:在自我否定中获得重生,在艰难险阻中得到复活。
博尔赫斯将图书馆作为天堂的比喻让我们或许更加容易靠近他的美学理想。这种理想就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永远矗立在那里,永远无法达到。这种无法抵达的感觉最重要的便是体现在对他的重新阅读与重新发现。我读过博尔赫斯所有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但每重阅读他的时候,我就像重新阅读一本新书那样——充满了诡谲的想象力与晦涩的辩证的作品。我明白,这也是博尔赫斯最重要的美学选择:他的作品就像他常用的迷宫、匕首与老虎花纹那样,充满各种令人眩晕并且产生溃败感的质地。
博尔赫斯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或者是“作家中的考古学家”。他像其他伟大作家一样,为其他写作者提供了新的美学范式,或者说确定了新的文学法则。在这个世界上,能配得起如此称号的作家并没有几个人。他们推翻了以往的法则,确定了自己的文学疆域,而很多人的作品便是对其作品的变形与模仿。
博尔赫斯说,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是发现了大海,发现了爱一样。而我们也可以说:发现了博尔赫斯就像是发现了大海,发现了爱一样。
博尔赫斯反对诠释与重复,但是对于这样的诠释与重复估计也会接受吧。毕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启发了很多作家,包括他的学生与反对者。例如写下《跳房子》的科塔萨尔,写下《2666》的波拉尼奥,写下《酒吧长谈》的略萨,写下《火山情人》的桑塔格等都是他文学意义上的学生。
博尔赫斯在访谈中明确表示自己最在意的是诗歌,其次是小说,最后才是散文与文论。即便如此,当我重读他的文论时,这些所谓的最不在意的作品同样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阅读博尔赫斯时,我会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像是走入了但丁所谓的黑色森林。他像维吉尔那样在前方照耀着我的路,让我一次次穿过赫拉克利特的河流,看到时间的本质与空间的奇妙构筑。他的作品最终指向是永恒。
在一篇文章中,他明确表示自己从不看报纸,而始终关注的是永恒的作品。这种看似极端的方式让我们更清醒地看到这样一位艺术家的形象:他始终与书为伴,书籍成为他进入不朽天堂的阶梯与扶手。
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作品与神话之间,作家与哲学家之间的互换式的镜像选择与指涉。例如在写卡夫卡的时候,他指涉北欧神话与克尔凯郭尔。在写霍桑的时候,他指涉《白鲸》《聊斋志异》与《圣经》。在写时间的时候,他指涉到了古兰经、老聃与希腊神话传说等等。在另外一些作品,例如《书》《时间》与《论古典》等作品中,他将自己这种浩瀚的知识与深奥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他想要用整个艺术史与哲学史来揭示永恒的真谛。
晚年,他失明了。这几乎是一场灾难,特别是对一位作家而言(就像耳聋对于贝多芬那样)。但他很早便接受了这种家庭遗传的现实。他形容自己的失明就像是薄暮慢慢地在自己的眼前降临,我想那时候会有某种荣光所在。有时候我想,他大量的阅读正是对自己失明的提前预演。他在很早便意识到了这种命运并且积极地反抗。很显然,他是胜者,并且带着圣保罗式的光环。在《博尔赫斯与我》中,他将自己作为自己的审判者:艺术中的自己与生活中的自己分裂成两人。在这篇文章中,博尔赫斯如此写道:上帝的存在时在永恒中发展的,而永恒则是许多昨天的持续不断的、无休无止的进展。这就是博尔赫斯对永恒的诠释,也是他通过其作品通向永恒的钥匙。
在小说《阿莱夫》中,他写到了一种可以承载世间万物的事物:阿莱夫。在这篇高度凝练,充满空间客体与心灵主体的作品中,博尔赫斯将对人类与自我的观照指向了阿莱夫。阿莱夫就是永恒的象征,是作家的诗意沉思的客观物。像其他所有作品一样,无论用多少迷宫或者镜子,永恒的谜底会浮现,但不会被解开。
而我也明白,一个无法对永恒与时间充满痴迷与想象的作家也无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为时间是通向永恒的钥匙,而永恒或许只是人类遥不可及的镜中之梦。
写作与阅读或许是通向永恒的虚妄通道:前方始终黑暗弥漫,但仍有暗光与暗涌。
我又看见了新天新地
最近半年一直在听勃拉姆斯。很难想象的是,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便创作出了《德意志安魂曲》与《第一钢琴协奏曲》,想来他的内心深处肯定有某种深渊。因为只有深渊才能够吸引深渊。很多人都觉得勃拉姆斯是一个音乐上与情感上的双重保守派,音乐上没有比同时期的另一个音乐大师李斯特技巧繁多,标新立异,生活上也没有其洒脱不羁,前卫先锋。当然我欣赏李斯特,时常聆听他的《巡礼之年》与《但丁交响曲》。就我个人的偏好而言,我更趋向是勃拉姆斯的音乐信徒,可能我在艺术的品好上也属于古典而保守的派别。
但是,他们仿佛古典音乐在浪漫时期的两种互为镜像的异色面孔:前者追根溯源,与德奥音乐古典时期的智性严密遥相呼应,而后者则开天辟地,发出了欧洲现代音乐的先声号角。前者推崇上帝,并由此探寻通往天堂的路;而后者则在质疑中抛弃上帝,在通往地狱的路上越走越远。前者的哲学同路人是康德,而后者则是克尔凯郭尔。然而,他们音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消解了这种二元对峙,因为地狱就是天堂的另一个名字。
如果你想要听出两位不同美学趋向的大师的分歧之处,不要去看那些晦涩的章节乐理分析(当然我也看不懂),而是直接去听,因为你的听觉上的判断会引导你的美学选择。例如,可以对比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与李斯特的《但丁交响曲》。例如,我们可以在听完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之后再去听李斯特完整版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不能分开的原因是李斯特的这部作品没有章节,中间还破天荒地加入了三角铁的声音)。我们不需要对那些抽象的乐理或者乐思焦灼,对音乐而言,耳朵才是最重要的审美器官。当然,有的视觉敏感的人说他可以在勃拉姆斯的《钢琴三重奏》中看到一篇象征森林,在《命运之歌》中看到沉溺河水中的黑天鹅,在《第二交响曲》中看到区别与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层峦叠嶂的迷雾,在《匈牙利舞曲》中,你则可以看到民间舞蹈与传说。
不要凝视勃拉姆斯那副留着厚厚胡须的年老时候的面容,我们可以找出他年轻时候的照片,那绝对是美貌、智慧与才华三位一体的高度融合。据说,他留着胡须是为了遮挡自己俊朗的面孔,为了不让自己看起来浅薄与无知。
很多传记对他的情感指向态度暧昧。有人把他与女钢琴家克拉拉的感情经历猜疑到了艺术史上的某种悬案的程度。当然,还是法国的作家们比较直白,他们说勃拉姆斯与克拉拉之间是精神之爱。勃拉姆斯同时爱的是克拉拉的丈夫,另外一个伟大的发疯的作曲家:舒曼。为此,他专门以舒曼为主题写了一组稍显沉重的变奏曲。伟大艺术家的灵魂从来都是雌雄共体,而勃拉姆斯便是其中鲜明的例证。我想弗吉尼亚·伍尔夫也喜欢勃拉姆斯音乐吧,否则她的这个论断也过于言之灼灼。
勃拉姆斯给予的另外一个意象就是:永远的黄金单身汉。艺术是有趣的,艺术也是要有所牺牲的。当然,在艺术史名单上,这样的人如同长河中倒影,变幻莫测,如果有人有福柯那种上纲上线的哲学能力,那么有一本关于单身汉的哲学著作可能产生,名字可能是这样子的:《美与真:论单身主义视阈下的艺术史流变》。
勃拉姆斯不是总摆着那种受难般沉思者的神态的,他也有轻盈灵活的时候,那些流传广泛的反而是他的短小之作:《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摇篮曲》与《爱之歌舞曲》。不过回想起来,我们所谈的那些大师们的最多的或许也是短小之作:贝多芬《献给爱丽丝》,莫扎特《土耳其进行曲》,舒伯特《摇篮曲》,拉赫玛尼诺夫《伴唱练习》,柴可夫斯基《天鹅湖》,最亏的应该是瓦格纳,那么多宏伟壮丽的超大型歌剧,我们谈的最多却是他的《女武士》,并且还是通过库布里克《奇爱博士》那个经典电影镜头才记住这个片段。大师们如果预感到这样的情景,应该会眩晕与恐慌并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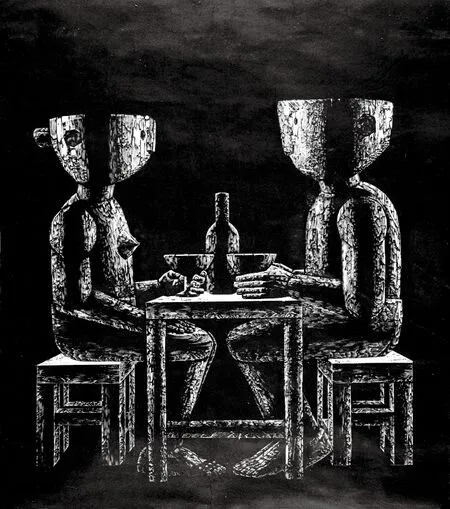
昨天晚上回到房间,不想看电影,也不想读书,于是我想到了勃拉姆斯。打开音响,选择了他的四首交响曲。我坐在床上,随着音乐冥想。总的来说,我最喜欢的还是古典乐,因为其创建的空间更易于自己冥想,在空中漂浮,而音符便是翅膀。从晚上的八点十分到晚上的十点十五分,我重新听完了其所有的交响作品。我非常喜欢这些作品,每一部都是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审美体验。但是最爱的是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OP.98)的第三乐章。在那里,我感受到一个困在迷雾中人慢慢向前缓缓走路的神态。他似乎看到了光,但更享受走路这个缓慢的过程。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强烈生命意志力不同,与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最后的乐章完全遁入黑暗不同,与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第二乐章中完全寻找某种精神上宗教性救赎不同,与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中的某种明朗不同,勃拉姆斯在最后一个乐章达到了音乐上的升华,这种升华是缓慢的过程,像是背负着十字架的人缓慢向前行走的脚步声。中间的大提琴与中提琴的声音在彼此呼应的时候,有某种叹息声在里面,这是一个疲惫的人,他不需要休息,因为他被神的荣耀所照亮。
我所听的是富特文格勒的版本。以前也听过其他的版本,仔细辨别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很多细微差别。例如,在伯恩斯坦的版本中,我们总能想到指挥家个人鲜明的艺术形象,如同号令千军万马的将领,而与此相反,在伯姆的版本,指挥家的形象却完全消融在了弦乐器的声响之中。例如,在卡拉扬的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贝多芬的变奏在响起,卡拉扬闭着眼睛沉溺在自己的世界中,而弦乐器一如既往地充满了歌唱性,而在朱里尼的诠释中更多的是中观照万物万事之后的苍凉之感,与此相反,瓦尔特提供的则是一种温厚之情。而昨晚所听的这个版本有凝思,有洒脱,有挣扎也有踟蹰,而那些精细的情感与微妙的乐思转换的部分则令我动容。
当然,语言是有界限的。语言无法更准确表述这种超验性质的差异。就像之前所说的,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耳朵,是自己审美上的直觉与判断。不过,所有的这些指挥大师的不同诠释,也让勃拉姆斯的形象变得立体甚至抽象,如同乔治·波拉克风格多变的立体派绘画。又有这样的一个结论:最伟大的艺术史经得起各种诠释解读甚至是误读的。不论是卡尔维诺还是博尔赫斯,他们都信奉这个艺术信条。勃拉姆斯的音乐提供了某种例证。勃拉姆斯总是为艺术史提供各种例证。无论是作为音乐创造者,还是作为音乐史中的具体的人。
你喜欢勃拉姆斯吗?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女作家萨冈通过一本小说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没有读过这本书,但对这个问题饶有兴趣。因为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回答的问题。
大学毕业后,聆听形色缤纷的各种音乐,与阅读不同种类的书籍,对我来说同等重要。这两件事情是我每日的必修课。每个夜晚,我都会聆听一个小时以上的音乐,是为了消遣,更是为了在抽象的乐思之中忘掉自我与时间。在去除我执的状态中,我看到了自我的微弱与茫渺,而不断地靠近实相的彼岸。
夜晚睡觉时,我翻看了《圣经·启示录》,中间有这样一句话:
“我又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晚上,我做了一个怪诞的梦。
清晨,我又将其忘记了。
异乡人的国度
对于一部电影喜爱总是以海报为开始。一个黑衣女子,有风,有赤诚的沙漠。一个背影,我们看不到她的面孔,但这个人独自走向沙漠。她的所感所受也许只能当事人自己可以体验。作为官能癖好者,我喜欢浓烈的色彩作为参照。也许是一个故事,也许不是。也许和自己有关,也许与自己没多大的联系。但是,自己总愿意从一个人的文字描摹另一个人,从一个人的面孔端倪到她的灵魂。我想到她在走路时哭泣,或无奈,或坦诚。面对浩荡色彩与背景,观者同样被其吞噬。
在《末代皇帝》之后,意大利导演贝纳多·贝托鲁奇便推出了此部电影。导演一如既往热衷于叙述宏大时代的人情况味。这是发生在撒哈拉沙漠的故事。作曲家和妻子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随着时间刀刃的撕裂,越来越不能弥合。他们想到了旅游,于是便去了非洲。随行的还有一个年轻英俊有情调的朋友。于是类似于萨特,波伏娃与其情人们的故事在沙漠这种背景下上演。
沙漠:心灵欲望镜像的外在场域。
作曲家和妻子都有各自的爱情,而婚姻的承诺在此成为欲望空洞的回音。他们讨论旅行者和游客的区别。她的朋友说:游客是观光后回家的人,旅行者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而这句话却为电影的结局埋下暗笔。电影里出现这样的细节:当作曲家讲述一个梦境之时,凯特却不断地打乱他的叙述。因为在她看来一切事物都充满了隐喻,而隐喻则是通向命运的秘符(这种梦境隐喻不是弗洛伊德或者荣格式样的,而是属于纳博科夫与达利这样的艺术家系列)。任何事物都是隐喻?我也赞同这种态度。一个黑色水杯,一粒尘土抑或是一个陌生人的表情都是传达某种巴尔特式的文学暗语。而我们的悲剧却来自于熟视无睹,这或许也是整个人类悲剧的核心之一。只有生活在一个隐喻的世界里,我们才会看到其中的意义与无意义。
凯特和朋友的那段在火车上的表演可谓活色生香。一杯香槟可以缓解一个人的恐惧。而与真正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尽管时间短暂,那也是值得用余下的半生去铭记。我喜爱一切细碎的美丽。包括一辈子也不会去见的人,一本不会重新打开的书。
她的丈夫死了,死于一场疾病。他的遗言只有一句:我的一生就是学习如何爱你。他们的彼此情感的戕害因为他的死而被抹平。她成了飘零者,非洲的飘零者。她做了非洲某个族长的妻妾,后来却沦为乞丐。最后被美国的大使馆找到,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实际上,这部电影是关于异乡人的隐喻:从故乡到异乡,从异乡再到故事,身份的丧失与身份的认同在寻找的过程同时演绎。
我们都是异乡人,对于心灵漂泊的人而言,任何疆域都是异乡人的国度。我们用各种艺术形式来完成奥德赛的心灵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