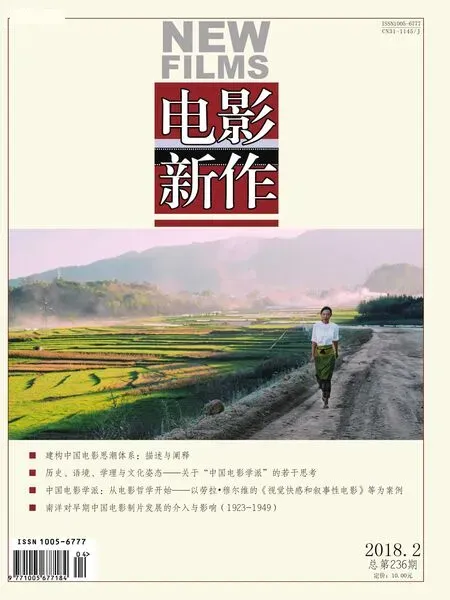眷念与反哺:黄宗霑与早期中国电影
王玉良
1945年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为了恢复国力,以及配合战时签订的“中美文化交流战略”计划,便从各个行业派出大批专家、学者出国考察学习。第二年春,著名作家老舍便在政府的安排下出访美国。当时,他的小说《骆驼祥子》的英译本《洋车夫》(Rickshaw Boy)在美国已经引起了很大反响,并由“纽约雷诺和希治板(Reynal﹠Hitchcock)书局出版,被‘每月新书会’推选而成为畅销书”。该书当时在美国已发行五百万册,销路极好。这一现象引起了好莱坞著名华裔摄影师黄宗霑的注意,一直以来,他都希望有机会制作一部反映中国本土文化的影片。《洋车夫》的风行,让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小说的摄制权,并出钱请了两位作家改写剧本。
黄宗霑(James Wong Howe),20世纪上半叶好莱坞重要的电影摄影师之一,1899年生于中国广东省台山县,五岁时随父迁往美国。他18岁涉足影坛,先后在拉斯基影片公司(派拉蒙前身)、联美公司、米高梅公司、FBO影片公司、福克斯公司、华纳兄弟公司拍摄过许多优秀的作品,并与好莱坞重量级导演西席·B·地密尔、霍华德·霍克斯,著名演员玛丽·迈尔斯·明特、葛洛丽亚·斯旺森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黄宗霑是黑色电影“低调摄影”(Lowkey)技法和动态摄影的首创者,沉稳厚重的摄影风格使他被誉为“带摄影机的诗人”,奠定了他好莱坞摄影大师的地位。他一生拍摄了130多部影片,其中10次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2次获得最佳摄影奖,是世界电影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华裔影人。黄宗霑在1976年逝世前曾两次回访祖国,在当时国内的电影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对中国和中国电影的那种眷念,体现了早期华裔离散影人的怀乡之情,同时也折射出了“文化混杂”的个体身份带给他的认同焦虑。

图1.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黄宗霑
一、折戟1948:黄宗霑与电影《骆驼祥子》的创作始末
20世纪40年代的好莱坞,是机遇与挑战、繁荣与危机并存的重要时期:《海斯法典》的社会影响、制片厂体制的由盛转衰、类型电影的繁荣昌盛、世界大战的政治影响、冷战思维的国际效应,使这一时段的美国电影呈现一种斑驳陆离、错综复杂的社会景观。尤其是战后好莱坞电影以绝对优势垄断了中国市场,美国电影商“不仅在中国发行放映,而且也在中国摄制电影,由于复杂的历史和文化原因,有关中国或以中国为主题的电影一直很受好莱坞制片人的青睐”。当时就有报道称,好莱坞环球公司拟拍摄“孙中山传记”,“片中之两项主题,为治外法权与民主……计划费二百万元于该片之摄制”。并称赛珍珠女士和胡适博士将参与制作,由保罗·茂尼主演。这一时期,还有好莱坞著名导演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和编剧菲利普·邓(Philip Dunne)由香港来沪,“拟计划摄制有完全以中国题材中国背景而在中国摄制的影片”。这无疑都激发了战后好莱坞制片商来华拍摄电影的热望。
黄宗霑自1917年初涉影坛之后,几经挫折,最终确立了自己在好莱坞的声望和地位。他辗转福克斯、米高梅、华纳等公司,在事业上达到了顶峰,创作了一大批质量上乘的优秀作品,并获《瞭望》杂志颁发的1947年度“摄影成绩优异奖章”。但由于国籍和身份问题,二战期间他被拒绝参与美国战争纪录片的拍摄,这给他心理上带去了难以抹掉的阴影,也加重了他对自己国族身份的思考。战后,“随着海外市场重要性的上升,好莱坞电影中的‘国际因素’与战前相比,也更为突出和具有吸引力,但好莱坞不在延续先前的策略,即把欧洲人才吸引到好莱坞,而是直接把制片业务移植海外。”在此潮流下,1948年,黄宗霑“联络挚友彼得夫妇,成立泛太平洋电影公司,第一部影片就准备拍《骆驼祥子》”。公司初步预算成本五十万美元,为了做好影片拍摄前的准备,使影片更加真实,他们决定启用一部分中国演员在中国本土拍摄。
据中央社纽约1948年1月27日电,老舍将小说《骆驼祥子》的摄制权以两万五千美元卖与黄宗霑,黄氏不日返国,“物色若干最优秀之男女电影演员,于国内拍摄,然后携美制片,由中美演员以英语合演”。按原初计划,黄宗霑“这次来到北平,带来彩色胶片甚多,将以两星期的时间大量拍摄外景,和搜集有关资料。四个月后,带到好莱坞开始拍制”。对于这次创作,他显得格外谨慎,希望能拍出最为淳朴的中国味道。因此,在演员选取方面,他曾说:“约翰·迦裴尔说要演《骆驼祥子》,但究竟没有中国演员演来合适。好莱坞拍的有关于中国的片子,中国人都是斜眼睛,所以(这次)一定要用中国人来演。”

图2.1948年,黄宗霑在《骆驼祥子》的拍摄现场
在创作风格上,黄宗霑力求制作出一部带有明显中国风味的作品,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化内涵中撷取精华。他在采访中称,“该片之叙述、摄制、光线、结构,渠决本廿余年来摄片经验,以纯中国之手法处理,摈弃好莱坞一般惯用之所谓‘噱头’,期该片摄成后能成为一幅幽静之中国古画,使我固有之艺术精神,得以充分发挥且将来在国际间亦能得广泛之宣扬。”于是,在1948年2月,他由香港返回内地,一方面准备影片《骆驼祥子》的取景和演员挑选,同时借机对中国电影业进行考察交流。
之所以拍摄《骆驼祥子》,黄宗霑在北京参观“中电”三场时曾说过,“中国电影在美国,谈话里知道苏联、意大利、法国、英国影片在美国都上演过,只有中国电影在历史上还没有踏到美国的影院,这真是一个可耻的事。”虽然此前根据中国故事改编的好莱坞电影不在少数,但这些影片呈现的几乎都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在中国人看来,难免有种“熟悉的陌生感”。即使1930年的《上海快车》,其中有黄宗霑在中国拍摄的部分片段,但这部影片也是被斯登堡“异化”了的中国故事,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和在地经验相去甚远。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这次拍摄《骆驼祥子》有两个目的,其一是“给予中国电影界一个启示,即此后制片力求争取国外市场,以换得外汇,向国外订购今日国内电影界所急需之各种器械物资”;其二是希望通过本片,“把中国的电影片在美国市场打下一个天下……最低限度叫美国人知道中国也有‘电影’和中国的伟大”。
正当中国电影界对黄宗霑的《骆驼祥子》抱着极大热情和希望的时候,《申报》在1948年11月13日突然刊出了一则这样的消息,“(本报北平十二日电)《骆驼祥子》搬上银幕,已成泡影,顷黄宗霑自美函平李炳荪女士(约定饰虎子演员)称:泛美公司以《骆驼祥子》一书业已过时,多数反对摄制。黄本人因工本浩大,亦不拟自费拍摄。”这预示着黄宗霑当时设想的美好计划即将化为泡影。
这个结局虽然有点出乎意外,却也在意料之中。1948年国内的政治形势十分严峻,国共内战已进入关键时期,电影业器材低劣但动荡的时局却令之无法改进,物资缺乏而无法解决。因此在他回国拍片之前,国内已有人预言,“即使黄宗霑回到上海,有意在祖国一显身手,但在这只‘开麦拉’前,保证他也定有无用武之地”。加之一直以来西方影片对中国现实的描写,刺激了国民政府敏感的神经。国民政府对“辱华片”的敏感,使它担心影片会把一些负面形象传播到国外,尤其是在国共内战的非常时期。
政治时局的影响,直接加大了影片的制作难度。据说黄宗霑从北平机场到六国饭店的途中,看到满街跑的都是三轮,稀稀落落的只有几辆洋车,“这部片中,多少个以洋车点缀古城街头景色的主要镜头,将因洋车的减少,同样也使他的兴趣减少了”。另外在男主角的选取上,也很难找到合乎要求的人物。在黄宗霑看来,“主角祥子必须是一个身高五尺十一寸,体重一百六十磅的二十多岁的壮男,相貌无需俊美,但要有精明强干的外表。”当时中国的电影明星中,符合这个标准的几乎没有。他多方寻觅,“男主角则‘踏破铁鞋无觅处’,有些年龄不合适,有些不懂英语,有些样子年轻、思想不年轻,有些缺少一个明星应有的条件”。而且报上传言童芷苓和白光都有可能出演《骆驼祥子》中的角色,与黄宗霑交情颇深的黎莉莉也可能出演女主角,甚至黄宗江的夫人朱嘉琛也曾传言饰演虎妞一角。这一切都给影片创作蒙上了一层暗纱,影影绰绰、扑朔迷离,使黄宗霑本人对影片的拍摄也渐渐地丧失了兴趣。而随着解放军逐渐向北平开进,这部电影在政权移交的前几个月最终宣布停拍。
黄宗霑一回到美国,就把在北平拍摄的所有素材带回好莱坞冲洗,据说,胶片所呈现出的北平街景的画面色彩令人惊叹。这些用柯达彩色胶片摄取的画面,色彩质朴真实,洗尽铅华,和创作者的艺术旨趣不谋而合。“故都”非凡的建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被呈现出来了。

图3.1981年,凌子风(左一)在《骆驼祥子》的拍摄现场
虽然黄宗霑拍摄《骆驼祥子》的尝试折戟而终了,但1948年上海出现的另一部喜剧电影《街头巷尾》,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观众的遗憾。该片导演潘孑农在回忆录中说到,“我在上海编导的影片《街头巷尾》,在塑造人物方面,多少得到了《骆驼祥子》的启示。”黄宗霑和潘孑农在战后都对《骆驼祥子》产生了极大的创作冲动,却因各方面的原因,最终都没有得以完成,但他们的这些尝试,却对后来的电影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黄宗霑,他的这次努力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直到40年后,凌子风导演的《骆驼祥子》也还受到黄宗沾(霑)的启发,他在挑选祥子的演员时,就是以黄宗沾当年在北平街头记录的一个洋车夫的形象做模特儿的。”虽然《骆驼祥子》的创作失败了,但中国电影人不会忘记黄宗霑对祖国的眷念和他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尤其是他曾经在中国电影最为关键的变革时期,为促进中国电影的发展,所起到的助推作用。
二、黄宗霑与变革时期的中国电影
“1929年是大家公认为电影技术史上最重要的时代”,世界电影出现了巨大的时代转型,有声时代的到来,宽银幕影片的出现,全彩长片(allcolor feature)的兴盛,电影业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与好莱坞相比,1929年的中国电影业也处于一个特殊的变革时期。首先是商业竞争导致了电影粗制滥造的现象,电影业为了追求利润,普遍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这种流于粗陋的创作状况,亟待变革;其次是这一年中国上映了第一部有声电影,随着有声时代的到来,中国电影在技术上也急需革新,才能与世界接轨。就在这一年,黄宗霑首次踏上了祖国的热土,开始了对中国电影的全面考察,用一种赤诚的“反哺”情怀,为变革时期的国产电影业指点迷津。
黄宗霑的这次中国之行,对当时的电影界来讲,无疑是一次巨大的震动。他结合美国电影的发展趋势,分析了当时中国电影的成就与不足,并对中国电影创作中的各种问题,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尤其是他热情地向中国电影演员介绍化妆与摄影的关系,使中国电影界对化妆的作用开始重视起来。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技术变革对电影创作的影响,分析了“目前美国电影事业之发达,犹且注意各种发明与新发现之电影艺术及其科学”。这些意见和建议,对处于变革时代的中国电影业来讲,可谓切中肯綮。
当时上海有一本十分畅销的电影杂志《新银星》,该杂志从1929年3月第8期开始,连续刊载了六篇文章对黄宗霑的首次中国之行进行报道,全面介绍了他的这次访问行程和对中国电影的希望。1929年4月11日,黄宗霑参观了大中华百合公司。该公司的经理朱瘦菊和导演王元龙亲自陪同,前往摄影场、洗片室和剪辑室等各个部门,逐一参观。由于正赶上公司新片《劫后孤鸿》和《奇侠救国记》的拍摄,黄宗霑对摄制组在布景、摄影打灯等方面的运用手法,给予了肯定和赞赏,同时他还亲自为这两部影片分别拍摄了数百尺内容。
随后,黄宗霑参观了明星公司,当看到该公司资本雄厚、人才济济时,就表示出对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极大信心,还把自己从美国带来的几部新式摄影器材赠予它们,其中包括四个电影变焦镜头,这是当时“东方所未有的”。他还提议为明星公司拍摄“公司男女基本演员”的纪念影片,其中有赵静霞、汤杰表演的香艳滑稽剧,胡蝶、朱飞表演的爱情剧,王献斋、郑小秋、夏佩珍表演的提倡婚姻自由的家庭剧等。在拍摄时,“黄君或以远摄、或以近摄、或以特写等优美之角度摄之”,毫无保留地对明星公司的两位摄影师董克毅和颜鹤眠(即颜鹤鸣)进行示范指导,这些小品影片后被黄宗霑带回美国放映,成了美国电影界了解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资料。

图4.1929年,明星公司欢迎黄宗霑的大会留影
20世纪20年代末,正是中国商业娱乐电影大肆泛滥的时期,而黄宗霑对电影艺术精益求精、严肃认真的态度,与当时中国电影界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的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参观明星摄影场时,正赶上《火烧红莲寺》拍摄“红姑夜探红莲寺”那场戏,张石川便让黄宗霑现场指导“夏佩珍在红莲寺墙外跃上高墙”的那个镜头。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黄宗霑要求二十架灯光全部打开,但他还是感觉光线不足。站立一旁的张石川不禁摇头叹息,事后还对人说,“一堂搭满整个摄影场的大布景,也无需二十双司泡脱(注:spot,“灯光”的意思)开足,现在拍这样短短几十尺片子的一个镜头,还嫌光线不足,吓坏老夫也!”这充分说明了在摄影用光方面,当时好莱坞与中国电影界的巨大差异,尤其是黄宗霑一直以来对摄影中的光线要求极为严苛,这也正是他当初能在美国电影界脱颖而出的最主要原因。
在电影摄影中,光线的运用极其重要,这一点黄宗霑了然于心。在好莱坞,许多女明星喜欢在他的镜头前表演,因为“黄氏对女明星的拍摄手法,很有独到之处,他能够用特殊的方法,增加她们的美丽,掩盖她们的缺点。”他十分强调光线在摄影中的艺术表现力,曾设想写一本名为《光线应用之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Lighting)的参考书,来总结一下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心得。他对摄影时的“用光”非常重视,“黄氏并不看重技巧的摄影,他所感兴趣的只是如何在正统摄影范围之内研求逐步的艺术化,极力研究气氛的加强,纯粹在光与影上设计,研求色调(TONE)与调子(KEY)的最高境界。”他不赞成那种“全部清晰(SHARP OVE ALL)的摄影法”,他认为“‘简单’是摄影的首要条件,只有简单才能彻底表现主题,才能让人感到真实。”黄宗霑是第一个发明用低调(Low Key)或者特殊效果的光线来摄制影片的人,他对光线在摄影造型中强调,对当时中国电影界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1929年5月24日上午9时,黄宗霑搭乘“麦金莱总统”号返美。当日明星公司总经理张石川、副经理郑正秋、导演程步高、演员郑小秋和王吉亭、宣传部张韦焘、摄影师董克毅和颜鹤眠、《新银星》杂志主编陈炳洪一行九人,前往码头送行,送别时董克毅和颜鹤眠分别用手提摄影机和照相机记录了这难忘的一幕。三个月的参观交流,黄宗霑对中国的电影事业有了全面的了解。即使返美后,他还曾数次写信给陈炳洪,反馈美国电影界的最新动向,尤其技术方面的新进步,建议中国尽快发展有声影片,赶上世界电影发展潮流。其中一封信中,黄宗霑谈道:“返美后耳目所见闻与余离美时情景大不相同矣。随处皆为有声影片。余知不久所谓默片者将成为古物。荷莉坞与纽约之摄影场,家家日夜赶制有声影片。所不能推测者为中国或其他国家将如何处置默片。余以为唯一方法即从速鼓吹电影事业于中国。”
在写给陈炳洪的另一封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发展有声电影的热切期盼。他不但给陈炳洪邮寄了几本美国新近出版的关于有声电影摄制法的新书,而且还在信中探讨了有声电影、宽银幕及彩色片的前景等内容,足见他对电影技术发展的热情态度:“我夹着寄上一张福斯公司所出的新影片做葛兰大影片的,你留心看察声音是在影片的旁的,那细小黑点是声浪,就是发出声音之处。片中景物几与立体无异,放映时候是在广阔的白幔,比现在影戏院银幕要大两倍有半。此种片子能普及与否,还不能断定,但我相信将来电影之改进是在于放映的面积与效力。若这种片子要普及起来,那么所有现时电影的一切都要改变了,如摄影机、放映机、冲洗器具等等。目下最应时的就是有色的有声片,这是已经很得观众所欢迎,有声片带着色给了片中景物一个生的表现。从前我们只可看到黑白影子唱着说着,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彩色更加逼真玲珑了。试想有一出中国有色的声片,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柔软与辉煌色彩的中国衣服怎样美丽悦目了,那岂不是要抬高我们的事业千倍吗!”
黄宗霑在华期间,热情地支持和推动中国电影业对有声电影制作的尝试。在明星公司参观时,他与摄影师颜鹤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的启发和鼓励下,颜鹤鸣发明了“颜苏通”(后改名“鹤鸣通”)录音设备,并尝试拍摄了中国第一部使用自己国产电影录音设备的有声影片《春潮》(郑应时导演,1933),他为中国电影技术的变革起到了重大的助推作用。当战后中国尝试彩色片创作时,黄宗霑再一次伸出了友谊之手,为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的拍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的上海电影界,迎来了许多好莱坞影人的光顾,除了黄宗霑之外,还有道格拉斯·范朋克、摄影师施密斯等。黄宗霑的中国之行,为变革与迷茫时期的中国电影带来了一束光亮。他不仅给混乱无序的电影市场打了一针镇静剂,还用好莱坞的制片标准引导中国电影的创作,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在有声时代的变革中指明了方向,鼓励技术改进,不断与国际接轨。这种“反哺”情怀,体现了黄宗霑这位华裔离散影人身在海外,心系祖国的怀乡之情。作为一位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黄宗霑的两次回访也体现了一种“旅居者”的身份转喻。
三、离散与怀乡:跨国影人的身份转喻
20世纪上半叶,活跃在好莱坞的华裔影人中,除了黄柳霜(Anna May Wong,1905-1961)之外,影响最大的当属黄宗霑了。这两位在早期好莱坞打拼的华裔影人,似乎有着共同的“旅居者”身份和“跨洋”经验。他们穿梭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游走于美、欧、亚大陆,以“电影使者”的身份在世界各地出现,从事文化交流和宣传工作。但在这种光鲜靓丽的文化身份背后,透出的却是早期华裔影人在好莱坞尴尬的人生际遇和社会挣扎。从1882年美国颁布《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之后,旅居美国的华人就开始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歧视。尤其是20世纪初期,种族主义风潮更是有增无减,美国文学中开始出现了像马克·吐温《苦行记》中的异教“中国佬”(Chinaman)形象,电影银幕上也开始呈现萨克斯·罗莫脑海中的傅满洲(Dr. Fu Manchu)角色。

图5.好莱坞著名华裔演员黄柳霜
在种族歧视和反华情绪的裹挟下,旅美华人的处境举步维艰。黄宗霑摄影方面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尤其“特写镜头的美妙、紧张情节的处理和节奏的剪接明快”方面,甚至与《乱世佳人》和《蝴蝶梦》的摄影风格相比,毫不逊色,但奥斯卡金像奖却对他视而不见,这无不说明了好莱坞对他的不公。可是这一切并没有挫败他自我奋斗的锐气,像许多华人一样,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重重阻碍,逐渐获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肯定。好莱坞对黄宗霑的排挤与歧视,与当时中国国内对他的认同与推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黄宗霑作为好莱坞赫赫有名的华裔影人,对早期中国电影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彼时的中国电影界也一直引以他为荣。中国当时的大多报道,都十分强调黄宗霑的民族身份,诸如“国人”“我外籍华人”等,认为黄宗霑在美国的荣誉为祖国增光不少。“在电影艺术上或技术上能够和外国人争一日之长短的,美国有黄宗霑,苏联有陈郁兰,这两个都是替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摄影师。”1946年《反攻缅甸》在中国上映时,《申报》上就有这样的评论:“因为这片的摄影监督是中国的黄宗霑氏,看到片中美丽的画面时,多少有一些得意的快慰。”1949年10月28在上海金门大戏院和卡尔登大戏院同时首映的好莱坞影片《绝处逢生》(Pursued,1947)的广告宣传中,就明确标注有“华裔摄影师黄宗霑摄制”的字样。两次回国,不仅体现了以他为代表的海外“离散影人”的“怀乡之情”,同时也完成了他们从“外国人”到“中国人”的身份转喻。这种身份转喻,是一种自我认同,也是一种国族认同。
1946年4月5日的美国联合通讯社(The Associated Press)报道了一则新闻,著名中国教育家晏杨初(James Y.C. Quen)与黄宗霑氏商议,本年在华发展大规模电影计划,并阐明其目的在于“普遍教育电影于中国各地,尤其注意于向来缺少影片之地区,务使教育电影在质量方面有长足之进步。”虽然这一计划后来不了了之,但充分说明了黄宗霑对祖国的眷念之情。黄宗霑一直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曾希望“能在祖国拍几套教育电影,以配合一广大的促进识字及公共卫生计划”。当时的《岭南大学校报》也有报道称,“名摄影师黄宗霑将为本校摄制影片”。很多报道听说黄宗霑即将来华发展电影事业,甚至通过漫画形式,向中国观众传达黄宗霑“预备把上海造成中国好莱坞,使之东西交辉”。尤其是黄宗霑第二次来华,不仅受到了雷电华在华经理郭纯亮、“中电”代表周克、白光、陈燕燕,及董克毅父子的热切招待,而且还得到了国民政府的特殊关照,“此次晋京乃赢蒋夫人之召,据悉蒋夫人对于十六糎电影片极感兴趣,认系发扬电影教育之一大工具,故拟于黄氏一。”这多少为他的北平之行抹上了一丝政治味道。

图6.1948年,黄宗霑指导《深闺疑云》的拍摄
无论是他对中国电影创作的指导,还是对中国电影发展的殷切期望,都植根于中华民族同根同源的国族认同。在电影创作方面,哪怕是很小的细节,只要对中国电影发展有所帮助,他都会无私地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例如他推荐使用肥皂水,解决了早期中国电影在拍摄时汽车玻璃反光,影响画面效果这种棘手的问题。1948年3月,黄宗霑在北平期间,正赶上“中电”三场拍摄徐昌霖导演的《深闺疑云》,就被邀请前去指导拍摄。他为影片“拍了三个镜头,对于灯光的角度地位,以及演员的动作,都亲自动手导演”。这都体现了他对中国电影的莫大关爱。他为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实际的帮助和有价值的思想,夏衍曾评价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

著名电影史学家李少白和邢祖文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构思过关于《中国电影艺术史》一书的内容框架,其中一节就包括对黄柳霜、黄宗霑这些华裔影人在好莱坞创作活动的介绍。与黄柳霜相比,黄宗霑似乎更能得到中国同胞的认同。对于黄宗霑的关注,当代中国电影界从未间断过,尤其在他逝世后的20世纪80年代左右,学术界连续刊发过一系列怀念文章和学术论文,这可以算得上国内第一波对黄宗霑的系统研究。1982年,为纪念他逝世六周年,北京和上海两地举办了“黄宗霑生平图片展”“电影作品回顾展”等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又不断出现了一些有关黄宗霑的研究成果。这些文章和论著,大多翻译自国外的成果,从黄宗霑的人生经历、艺术风格、摄影技法和世界影响方面对他做了全方位的介绍。虽然对于黄宗霑的这些介绍,很多都涉及他于1929年和1948年的两次中国之行,但遗憾的是,几乎所有成果在论述这方面内容时,都是浮光掠影式的一笔带过。而事实上,无论是为了《骆驼祥子》的拍摄重归故土,还是在中国电影变革时期的传经送道,黄宗霑在早期中国电影史的书写中都是不可缺席的重要人物。他的两次中国之行,不仅明确了当时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发展坐标中的位置,也为早期中美电影的交流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参考经验。
【注释】
①舒济编:老舍和朋友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167.
②谢荃、沈莹:中国早期电影产业发展研究(1905-1949)[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162.
③制片商准备摄制孙中山传记[N].申报,1946-1-5.
④好莱坞著名导演编剧联袂抵沪考察[J].电影杂志(上海),1949(36).
⑤澳理查德·麦特白:好莱坞电影: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史[M].吴菁、何建平、刘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116.
⑥张伟:沪读旧影[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187.
⑦《骆驼祥子》将上银幕[N].申报,1948-1-28.
⑧《骆驼祥子》拍片难[J].东亚声,1948(25).
⑩旅美名摄影师筹备自费拍片[N].申报,1948-3-17.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8年4月视察湖北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保护好长江中华民族母亲河”“治好‘长江病’,要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