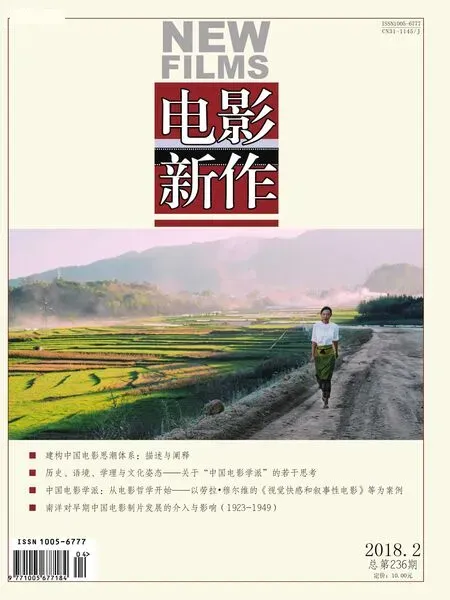经验共享、道德训诫与“真实”追求:20世纪20年代阎瑞生故事的媒介呈现
李九如
电影在中国诞生百年之后的今天,一些有趣的“返祖”和轮回现象开始陆续显现。这从以《画皮》为代表的中国式“魔幻”电影与20世纪初的神怪片的热潮对应,以及以《归来》为代表的家庭伦理影片的“归来”等,均可看出其鲜明的迹象。不但如此,2014年出品的姜文电影《一步之遥》,居然再次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的杀人故事,历史的惊人相似,在此又一次显露无遗。本文不拟全面探讨中国电影的百年轮回现象——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电影史甚至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课题——而只准备以《一步之遥》为契机,重新回到影片所讲述的故事起点上,探讨一下将近百年之前,中国早期的媒介——包括印刷刊物、电影,乃至当时正在改良之中的舞台——是如何呈现这个轰动一时的案件的。众所周知,《阎瑞生》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长片,有着对于“真实”的“拙劣”追求,并因此遭受了长久的抨击。有意思的是,《一步之遥》恰恰也聚焦于电影这种媒介的真实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虚假性),展开了其狂欢化的讽刺性叙事,并由此将阎瑞生故事的相关实践阐释为一场意识形态操控的阴谋。基于此,本文意欲从《一步之遥》的媒介真实观谈起,进而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场景中去,考察一下“真实”和电影对它的追求,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一步之遥》的媒介真实观
《一步之遥》可以说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即所谓的“元电影”。这种自我反射的性质,让它获得了一种对于电影自身的反思性。整体来看,《一步之遥》讲述的正是一个原先通过操纵大众媒介玩弄大众于股掌之间的人,被大众媒介及其背后的操纵者(连同大众一起)迫害致死的故事。在这样一个故事中,所谓的大众媒介,除了广播、报纸和舞台之外——影片也展现了它们对于大众的愚弄,比如影片开场那个借助新兴的广播技术实现“全球直播”的“花域总统”选举活动,以及王志文饰演的王天王在舞台上的表演——最重要的就是电影了。可以说,在《一步之遥》中参与对原先的大众媒介操控者马走日进行“迫害”的媒介之中,电影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影片揭露了电影所谓“真实性”的虚假,尤其是当改行为电影艺术家的前舞台艺术家王天王发表了他那一番显然是学习自“库里肖夫效应”的蒙太奇理论之后,周韵饰演的大帅之女武六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用电影拯救马走日的计划,而在此之前她是一位痴迷于电影真实性的电影爱好者。与此同时,已经被逮捕的马走日——他的原型就是阎瑞生——早就拒绝了那个用电影拯救他的计划,在那个计划之中,马走日需要按照大众对他的想象,即一个丧心病狂、处心积虑、谋财害命的杀人犯,来饰演自己,然后在那部名为《枪毙马走日》的电影中,用替身为自己在大众面前死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计划中的欺骗性,武六显然是默许了的,由此可见,武六对于电影真实性的坚持,也是有所选择的。

图1.《一步之遥》
在《一步之遥》中,马走日和武六拒绝了电影这种意识形态操控机器的拯救,最终只能选择以最原始的方式做一对亡命鸳鸯。但从影片中武六对待电影欺骗性的前后态度来看,他们真正拒绝的,显然并不是电影这种媒介的欺骗性,尤其是,在影片开头部分,马走日还在熟练操作着大众媒介的欺骗技术。在这里,颇有意味的一点就显现出来了,马走日和武六所拒绝的,其实是在背后操控电影这种意识形态机器的人,而在《一步之遥》里,这些人就是被称作“暴发户”的粗鄙的大帅、他挥霍无度的儿子、投靠了洋人的项飞田以及舞台兼电影艺术家王天王。当然,这个名单之中本来也应该包括女主人公武六,但她后来显然被表现为一位“纯粹”的电影爱好者,更重要的是,她认同了男主人公马走日,因此她也就被排除在了这个“暴发户”群体之外。需要注意到,在影片中似乎是作为噱头的开头和结尾的两段关于马走日和前清太后对话的讲述,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相反,它们标明了男主人公马走日的身份,一个前朝贵族。影片中有两处出现了马走日与他人关于敬称“您”的讨论,由此显现了“贵族”与“暴发户”之间的差异。到此可以看出,《一步之遥》实质上讲述了一个“贵族”在“资本主义”,或者说新的世界秩序中没落的故事。
影片中的那些“暴发户”们,显然是新世界中的胜利者,而在《一步之遥》这样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中,这些“暴发户”又都临时性地成了玩电影的票友。这样的设置,高度相似于电影《阎瑞生》拍摄时的情况。在此,《一步之遥》十分明显地透露了它对于20世纪20年代电影史的看法:那个时代的电影,是某些人愚弄大众借以达到其利益和目的的工具。由此,《一步之遥》形成了一种颇为“精英”化的电影观念。在这种观念里,电影这种媒介的受众,在很大程度上是愚昧的,可以灌输和操控的,而它的操控者,则抱持着各种不同的利益和目的。更进一步的,这些被灌输和操控的大众,又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压迫力量。
显然,在《一步之遥》看来,20世纪20年代的戏剧和电影人,至少在阎瑞生故事的相关文本中,利用或者说操控了电影这种媒介的“真实”性,从而达到自己龌龊的目的。故事片对历史事实是否尊重并不重要,然而此处对早期电影人和电影史的看法,仍然值得商榷。要重述20世纪20年代阎瑞生故事相关文本的艺术实践,首先要回到当时的都市语境中去。
二、都市现代性与震惊经验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正在日益成为远东最为现代化的城市之一。在这座城市之中,工业资本主义刚刚经历了一次大发展,各种现代消费娱乐场所正逐渐兴起,摩天大楼的高度也开始不断地刷新着纪录,汽车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也正在加入日渐拥挤的城市街道之中。总之,这里正在成为一个现代性大爆发的场域。也就是在这个场域里,城市空间本身,和正在兴起的大众传播媒介,诸如各种报纸、期刊等,不断地向居住其间的居民和受众,呈现和传播着各种本雅明意义上的“震惊”经验,很快,作为当时的新兴媒介的电影,也加入了其中。
关于都市现代性,本雅明有独特而有趣的观点。在他看来,都市所呈现给人们的现代性经验,集中表现为一种“震惊”体验。借助于对波德莱尔这位“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论述,本雅明描绘了像巴黎这样的近代都市所带给人们的现代性经验,他将这种经验集中表述为“震惊”。当谈到波德莱尔的诗歌《致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时,本雅明表示该诗表达了一种只有在都市空间之中才会产生的震惊感;在另外的地方,本雅明又论述了大众的出现所带给人们的震惊体验,他写道:“害怕、厌恶和恐怖是大城市的大众在那些最早观察它的人心中引起的感觉”。尤其重要的是,本雅明不仅描述了“现实世界”中各种类型的都市现代性所带来的震惊经验,他还进一步将目光投向了伴随都市现代性的兴起而来的大众媒介,把媒介呈现与“现实世界”等而视之,同样当做现代性震惊的源泉:照相机赋予瞬间一种追忆的震惊。这类触觉经验同视觉经验联合在一起,就像报纸的广告版或大城市的交通给人的感觉一样。在这种来往的车辆行人中穿行把个体卷进了一系列惊恐与碰撞中。在危险的穿越中,神经紧张的刺激急速地接二连三地通过体内,就像电池里的能量。
可以看到,在本雅明那里,“照相机(的照片)”“报纸的广告版”与“大城市的交通”是一回事,它们共同给都市中的人们带来了震惊感,因而它们同样都是都市现代性的一种表征。本雅明的这种“通感”式的论述,被米莲姆·汉森和张真等人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继承了下来并有所发展。在《银幕艳史》一书中,张真表述了她的早期电影史观,她提出“电影的感官历史……平行、交叉于世界语境中,都市现代性在工业资本主义滥觞扩展时代所走过的历程,并将之具体化呈现”。由此,早期电影既被当做都市现代性的一部分,又被视为是对都市现代性的“具体呈现”。这样的思考路径,显然得益于本雅明的都市现代性论述。缘自本雅明的这种都市现代性表述,将电影放置在了工业革命时代以来涌现的众多现代性事物当中,作为它们的一员。事实上,本雅明通过波德莱尔的研究,提炼出了一套观察现代性的认识论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建立在通感基础上的隐喻,比如,前文提到的“照相机(的照片)”“报纸的广告版”与“大城市的交通”之间的同构关系。基于这种认识论,“白话现代主义”所指涉的,不仅仅是早期电影,也包括文学、戏剧乃至当时重要的大众媒介印刷期刊。而沿着这样的思路可以发现,阎瑞生案件本身,以及围绕它所出现的报纸、书籍、期刊、戏剧、电影等各类大众媒介对案件的呈现——它们构成了早期媒介史上一种不自觉的“跨媒介”实践——其实均可视为是都市现代性的一次集中的“平行、交叉”显现。

图2.《一步之遥》
三、震惊经验的“跨媒介”呈现
如果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是中国卷入近代化进程以来较早的一起引起巨大影响且有大众媒介参与的案件的话,那么阎瑞生案件大概是最早的一批真正具备“现代性”的案件之一。在当时就广为人知、后世又不断被搬上银幕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虽然当时的《申报》有所报道,并且据称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的审理,但从根本上说此案还是一起“传统”案件。与此不同,阎瑞生案则已经是一起不折不扣的“现代性”案件,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审理机关已经是现代化的司法机关,更因为该案的当事人、作案方式、案件发展过程等等各方面,都是“现代性”的。案件的凶犯阎瑞生,是民国初年的大学毕业生,洋行里的买办,属于当时中国人中少有的“都市”人群;被害者是一名高级舞女。需要注意的是,她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舞女”,而是一名参照现代选举制度推选出来的“花国总理”,这意味着她是经由公共领域产生并存在于公共生活之中的“准明星”人物;在作案过程中,当时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性象征物的汽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案发之后凶犯阎瑞生的逃跑借助的是轮船、火车这样的“现代化”交通工具;而他的被捕,又与正在变得无处不在的大众媒介——报纸有很大关系。从根本上说,阎瑞生案件的发生,跟作为现代化进程之一部分的女性的公共化,有密切联系。作为一个女性的特殊群体,舞女是中国最早进入社会的公众视野的人群之一,尤其是那些“高级舞女”,不菲的收入和炫耀性的在公共场合招摇过市——一种公共性的获得,为她们带来荣耀的同时也招致了巨大的危险。法国汉学家安克强描述了这种危险性,他写道:“虽然她们的出行路线是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之内,但一旦夜幕降临,她们仍有遭到袭击的危险。”阎瑞生案件的发生,就是这些新近获得公共性的女性们遭遇危险的一个极端且典型的例子。可以说,阎瑞生案件,作为一个残忍的血案,正是本雅明所说的那种都市中的人们所经历的“大城市的交通”一类的现代性震惊经验。
这种震惊的经验,不仅属于凶案的被害者,它也属于处在都市中的所有人。经验的广泛性和公共性,来自于正日益蓬勃发展的大众媒介。凶案发生之后,各类媒介很快进行了跟踪报道。就在案发之后,《申报》迅速登载了“捉拿谋财害命凶手阎瑞生赏格”的启事⑭,此后在凶手阎瑞生等人被捕及审理过程中,《申报》还有很多跟进的后续报道。综观这些报道,可以说它们构建了一个跌宕起伏、情节环环相扣的长篇故事,而它们的读者——都市中的公众们,则通过这些报道,严密跟踪并实时观察着故事的进展。不仅如此,凶案刚刚发生不久,商业嗅觉极其灵敏而且行动迅速的上海出版商们,就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出版了《莲英被害记》《莲英惨史》《阎瑞生秘史》等书,阎瑞生被枪毙之后,又很快出现了《枪毙阎瑞生》等书。这些书籍,向都市大众们细致讲述了凶案的两位主角阎瑞生、王莲英的种种生活细节,以及案件本身的详细过程,堪称巨细靡遗,纤毫毕现。而这种叙事方式与风格,实际上也延续到了差不多同时期出现的阎瑞生戏剧以及随后出现的电影之中。
作为对阎瑞生案件这样的都市现代性震惊经验的呈现,印刷媒介在那个时代显示了它“自然主义”式的“纪实性”和极其迅速的即时性,将一种个人化的震惊经验,迅速传播到了更广大的都市空间之中。有意思的是,当下已经被公认为“艺术”的戏剧和电影,面对阎瑞生案件,也在不同程度上向印刷媒介看齐,同样着意于追求即时性和“纪实”效果,这种追求甚至到了模糊它们各自的“艺术规定性”与“现实世界”之间边界的地步。在这个意义上,有关阎瑞生案件的戏剧和电影,典型地表征了与都市现代性之间的“平行、交叉”关系。

图3.《一步之遥》
阎瑞生案审结之后,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当时上海的戏剧界。据称,“就在阎瑞生伏法的次日,即11月24日,《申报》就已刊登了大世界乾坤大剧场25、26日上演《莲英劫》的广告”。这表明,早在案件审结之前,戏剧艺人们就已经紧盯着案件的进展,并据以进行戏剧的编排和演练。在大世界之后,当时上海的各个著名戏剧舞台,诸如大舞台、共舞台、新舞台等,也都紧随其后纷纷上演了有关阎瑞生案件的时事京剧。时事京剧本身就是正在经历现代性冲击的上海所产生的一种改良式的京剧,与传统京剧的抽象化程式相比,时事京剧有着越来越强烈的“写实”趋向。这种趋向在有关阎瑞生的戏剧实践中,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综观各个舞台上演的阎瑞生时事京剧,不仅剧情发展基本按照案件本身进行编排,更重要的是,在舞台置景方面,也越来越凸显机关布景的“真实性”,力求在舞台上真实复现阎瑞生案件的整个流程。仅在阎瑞生被枪毙之后的第四天就上演《头本阎瑞生》的大舞台,在广告中宣称其布景“材料异常丰富如洋房书寓旅馆汽车火车站跑马厅一品香群仙戏园新世界自由厅等彩景式式俱全”。与大舞台相比,紧随而来的共舞台在布景之外,又在演员上朝“纪实”性迈出了一大步:因为法租界的“政策优势”,共舞台得以让女演员登台扮演受害者王莲英,并且该演员还由于“和上海堂子里的高级舞女颇为熟识”,因此可以“活灵活现模仿莲英”。更进一步的是,共舞台在阎瑞生戏剧中,首次真正打破了戏剧与现实的界限,将受害人莲英的“妹妹”玉英邀请来,并且扮演的正是她自己。当然,将“纪实”趋向彻底发挥到模糊艺术与现实界限的,仍然要数著名的新舞台。新舞台的《阎瑞生》,融入了大量现代话剧成分,进一步打破了京剧艺术的原有规定性。不仅如此,它的“纪实”取向,甚至远远超越了话剧,在当时,“观众最津津乐道的是新舞台几可乱真的布景及真实的道具”,这其中就包括真实的汽车,乃至人造的以真实的水做的“河流”等。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新舞台的表演,在《阎瑞生》中也完全逸出了舞台的边界,比如,在剧中登台的汽车——阎瑞生的作案工具——开出剧场舞台之后,车上的演员居然会向大街上的行人“频频致意”,而剧场之外的人们,居然也欣然加入这种互动之中;在该剧的另一段落中,演员表现阎瑞生跃入水中逃跑,“每当水花四溅至观众席上,观众无不喝彩”。这种奇特的景观,当然并非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先锋探索,而是当时各种都市现代性经验之间“平行、交叉”关系的一种体现。对于当时的观众来说,观看阎瑞生戏剧,与通过印刷媒介观察案件本身的进展,乃至在刑场亲历枪毙阎瑞生,这些经历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它们是互联互通的,处于一种混沌状态。
加入这种混沌化的经验,呈现的就是早期电影了。与处于改良之中的京剧相比,初生的中国早期电影,更加处于一种自身规定性不明确的阶段。这不仅是由于它的发展尚处于幼稚阶段,也是由于电影本身就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一种产物,是都市现代性的直接体现,因此它更加受制于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都市现代性经验。跟戏剧一样,电影《阎瑞生》也追求与现实的高度一致性,并由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混淆了与现实之间的界限。电影上映于1921年的7月份,此时距阎瑞生被枪毙已经过去了大半年,相比于戏剧来说,作为故事长片的《阎瑞生》,在时效性上稍微差了一点。但考虑到电影制作的特殊性,以及当时技术条件的落后,电影《阎瑞生》在“反映现实”方面,恐怕仍然是电影史上少见的“神速”了。而关键在于,电影天生的纪实本性,给了电影《阎瑞生》很多其戏剧版本无法具备的“真实性”优势。根据《中国无声电影剧本》所载的影片说明书可知,电影《阎瑞生》的故事,也是严格按照案情发展铺展开来的。这就从叙事上保证了影片的“纪实性”,可以说,它基本上就是一部罪案“实录”。虽然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再看到《阎瑞生》的影片,但除了留下的影片说明书之外,当时杂志登载的剧照,也能说明本片忠实于罪案“事实”的“实录”性质:《时报图画周刊》在影片拍摄期间,以一组照片,像连环画一样按照阎瑞生犯罪、逃跑到被捕的过程,呈现了电影《阎瑞生》的大致概貌。在演员方面,与专业的戏剧演员不同,电影《阎瑞生》的演员,在身份上与其所扮演的角色高度一致,甚至据宣传,在长相上也非常相似。扮演阎瑞生的是陈寿芝,他与阎瑞生一样都是洋行的买办,甚至两人还是“至友,据说面貌也非常相像”;阎瑞生的帮凶由邵鹏扮演,巧合的是两人居然也是“朋友,时相往来还有杯酒之交”;最后,影片的女主角则找了一个已经不再从事相关工作的舞女来饰演,可想而知她要比共舞台的那位熟悉舞女的女演员更为接近“真正”的舞女,不仅如此,广告还宣称女主角与受害人长得“一模一样”。在拍摄方法上,电影《阎瑞生》更显示了它相比于戏剧的优越性,本片宣称基本都是实地取景,这要比“几可乱真”的新舞台布景更为“真实”。另外,或许是因为追求忠实于罪案本身的缘故,从目前留下的剧照看,作为长片的《阎瑞生》显然比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劳工之爱情》的场景更为丰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场景镜头中,除了大量正面取景的舞台化的全景镜头之外,也出现了少量角度、景别更为多样的电影化镜头:比如王莲英梳妆的镜头,就是背后取景,并且利用了镜子以呈现更为丰富的信息;阎瑞生逃跑至教堂的段落中,出现了大远景的画面。人们有理由质疑,这些都并不是主创人员有意的艺术追求。但有意思的地方恰在此处,主创人员刻意营造的,的确不是“艺术”,而是“真实”,这部号称“实地表演情景逼真”的影片,如果说有什么镜头上的独特之处的话,那么它也只是追求“真实”地复现罪案的诉求的副产品而已。所有这些,在为电影《阎瑞生》带来真实感的同时,也模糊了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

图4.《一步之遥》
四、敞开媒介中的“道德纪实主义”
《一步之遥》通过王天王的舞台表演再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各种阎瑞生舞台剧演出的现场,对于当时阎瑞生戏剧的火爆程度、互动性等有所呈现。不过,这种再现是带着价值评判的非客观再现,王天王被表现为一个滑稽的丑角式人物,而观众则显然是狂欢的群氓。至于在当时的剧场中那种火爆的互动场面,对于置身其中、置身都市的人们是否还意味着更多的东西,《一步之遥》并不关心。这恰是问题所在。阎瑞生舞台剧(包括电影)演出的火爆,是否可以简单看作一场意识形态操控的阴谋?显然,都市现代性的视角,以及对相关历史细节的重述,似乎可以提供另一种判断。
从表面上看,各种媒介中的阎瑞生故事,均存在着对“真实”层层加码的近乎执拗的追求,而这种追求看起来则很接近于我们经常提到的“现实主义”“纪实主义”或者“自然主义”。当然,如果我们就此以这些概念来评判20世纪20年代相关的阎瑞生文本,则肯定离谬以千里只差“一步之遥”了。无论是“现实主义”“纪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作为艺术观念,严格来说它们指向的均是一个个自足的文本。而相比之下,20世纪20年代的阎瑞生文本,如前所述,则通通都是“敞开”的(即便是京剧,也是改良之后的所谓时事京剧,而并非彼时已经发展完备具有充分自足性的作为国粹的京剧),这不仅意味着这些戏剧和电影并不“成熟”,更表明它们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平行、交叉”关系。或者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阎瑞生戏剧和电影中,对“真实”的追求,首先表现为这些文本及其承载媒介的“敞开”性,也就是它们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平行、交叉”关系。在此,所谓“敞开”或“平行、交叉”,又可与托马斯·沙茨在描述类型演变的早期阶段时所使用的“透明”一词的意义相互参照。在沙茨看来,早期的电影类型有一个形式透明的古典阶段,而在此之前,类型则比透明还要“透明”,它倾向于把电影“作为一种媒介来使用”,如果允许简化,此时的类型简直可以称作社会新闻——这恰是电影《阎瑞生》所处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认为阎瑞生故事在追求“真实”,不如说它们追求的是一种现代性经验的共享,或者是沙茨所说的“社会集体地对它自身的言说”。那些对“几可乱真”“一模一样”的执拗强调,其目的在于唤醒观众的现实世界视野,进而就此展开有关现代性震惊经验的共享、交流乃至讨论。由此可以说,阎瑞生故事,作为一种现代性震惊经验,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不断讲述,对于处在都市“危险的穿越中”的居民来说,构建了一个震惊经验的交流场——米莲姆·汉森称之为“现代型公共空间”。在此公共空间中,早期观众得以“从感觉的层面参与进现代性的各种矛盾”,而由此“现代性的各种创伤性后果——或扬弃或否认,或转化或强调——都会得到反映”。显而易见,20世纪20年代阎瑞生戏剧和电影的观众,作为正在经历现代性冲击的都市居民,他们观看阎瑞生故事的过程,恰正符合汉森所描述的公共领域机制。这种机制使得他们得以逐渐适应都市现代性的剧烈冲击,进而在适应中确认自己新的都市现代性身份。
当然,无论是印刷媒介的报道,还是戏剧和电影的演绎,所有的阎瑞生故事,最终都呈现为一个善恶有报的道德惩戒结局。在这方面,一部极有可能由郑正秋编剧的阎瑞生戏剧《莲英被难记》,在广告上有如下苦口婆心的词句:编阎瑞生戏,正秋颇费心血,倘使多编他下流情形,变成宣讲拆白教科书,岂不是要带累看客,无形中受恶影像在脑筋里么?故此多演他犯罪后痛苦,使得大家看了回去作十日想,希望人类中减少残杀底悲剧呢。
可以说,这种道德化的主题,是当时所有形式的阎瑞生故事的主旨,至少是主旨之一。即便是在电影史上颇受诟病的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阎瑞生》,在震惊化的现代性影像背后,传达的仍然是一种道德惩戒。这种道德化现象,也成为此后整个20世纪20年代中国早期电影的重要特征。实际上,道德训诫是古老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市民阶层,在面对现代性的冲击之时,所依赖的最重要的一种安慰。在早期电影中,道德教化,更是知识分子所开出的第一例应对现代性焦虑的药方。
事实上,阎瑞生故事的道德训诫倾向,也清楚地说明,这些文本并不是真的在追求那种自然主义的“真实”。除去新闻报道之外,20世纪20年代所有的阎瑞生文本,如果说它们有什么艺术观念的话,那么这种观念可以称之为“道德纪实主义”。这一术语一方面意味着一个道德训诫的情节走向——比如《莲英被难记》“多演他犯罪后痛苦”的情节取舍——另一方面,则还隐含着某种有关“真实”的道德哲学理念。与徐欣夫等人同属电影《阎瑞生》的拍摄者,同时也是中国影戏研究社成员的顾肯夫,在《影戏杂志》的发刊词上,指出了“逼真”的意义:现在世界戏剧的趋势,写实派渐渐占了优胜的地位。他的可贵,全在能够“逼真”。照这趋势看起来,将来的戏剧,一定要把“逼真”来做范围。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们在看戏的时候,要是这出戏不能“逼真”,那么,演戏的自己明明晓得自己是正在演戏,看戏的也只晓得自己是正在看戏,戏剧感动能力的大部分,必因此减少。要是戏剧能够“逼真”了,那么,演戏的自己已忘掉了自己是一个“扮演着”,以为是“剧中人”,能够替“剧中人”有同一的感情。看戏的也把自己当做“剧中人”,像亲身经历戏剧中的一番情形一样,那感动力就增加了千百倍。
显而易见,顾肯夫是站在进化论的立场上来看待戏剧的“逼真”。进一步说,在他那里,“逼真”又是戏剧“感动力”的来源。而所谓感动,对于顾肯夫而言,即意味着“通俗教育”,实际上也就是道德训诫。由此,在这种艺术观念中,真实就成了道德教化的根基。事实上,顾肯夫的艺术真实观并不孤立,就在这一时期,五四新文学的旗手之一的茅盾,站在进化论立场上攻击鸳鸯蝴蝶派文学时,就宣称“中国作家必须先经过自然主义的洗礼”,并且很明显,茅盾所说的“自然主义”也并不是左拉式的自然主义,相反其中潜藏着强烈的启蒙,或者说教化的主观倾向。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进步”的即是“道德”的,而真实又被看做“现在世界戏剧的趋势”,或者被看做文学进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那么顺理成章的逻辑便是,真实的也就是道德的。照此逻辑来看,阎瑞生故事对“真实”的追求,从一开始便蕴含着道德的目的和意义,而围绕着它们所建构起来的经验的交流场,从一开始也便是一个道德化的公共领域,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感官经验层面的交流场域。
结语
作为一部故事片,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要求《一步之遥》完全忠实于历史,将《阎瑞生》的拍摄情况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呈现给观众,但这也并不妨碍我们从其所透露出来的电影观念出发,以之为契机展开历史的重述。这里并不拟就电影史的本体问题做长篇大论的探讨,但作为一名电影史的研究者,仍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电影史来说,史观固然是重要的,而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更是值得注意的。就《阎瑞生》的拍摄参与者来说,其中的人,确实有不少是“买办”,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的确属于热心于电影的知识分子,为此他们在那个中国电影还很荒芜的时代,组织了同人性质的中国影戏研究社,甚至还创办了最早的专业电影杂志《影戏杂志》。如前所述,在该杂志的发刊词上,研究社成员之一的顾肯夫站在“进步”的观念基础上,提出戏剧要有“通俗教育的旨趣”,要达到这个目的,“逼真”是很重要的美学方法,而在所有的戏剧中,影戏恰恰是最为“逼真”的。这种电影观念,在左翼电影观出现之前,其实是最为主流的“进步”电影观念之一,并且事实上与《一步之遥》中女主人公武六的电影观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当然,由该社推出的《阎瑞生》主观上是否完全执行了这种电影观念,也许是值得怀疑的,但看其对“纪实”的刻意追求,以及在结尾对于善恶有报的道德观的张扬,可以说,电影《阎瑞生》至少没有太过偏离顾肯夫的电影观念。至于影片上映之后,观众是否被灌输和操控,以及由此是否造成了对阎瑞生这样的个人——尽管那时他已经被枪毙——的某种压迫。一句话,电影的上映究竟是导致了愚昧大众的狂欢,还是某种经验交流场域的形成,由于史观的不同,以及诸如观众接受情况方面资料的匮乏,大概就只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在此,本文倾向于后者,即在20世纪20年代初,阎瑞生案件及其相关文本的产生,尤其是其中的戏剧和电影,经由其“道德纪实主义”的渲染,显然构建了一个道德化的感官经验交流的公共领域,在此空间中,观众得以强化并修复其所经受的现代性冲击,以在“危险的穿越中”适应现代性的生存。
【注释】
①这里的愚弄大众的逻辑,显然跟《让子弹飞》里张麻子以假黄四郎的死来欺骗大众是一致的。
②这样的电影史观,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电影发展史》是一致的,后者在评价电影《阎瑞生》的时候,是这样说的:“《阎瑞生》是一部极端恶劣的影片……影片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阎瑞生的犯罪行为,宣传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中国所豢养的买办,如何承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极端腐朽堕落的品质,渗透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意识……投合了一部分落后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因而也骗得了不少的观众。”参见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第45页。当然,可以看出,在对待“阎瑞生”这个人物的问题上,《一步之遥》与此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在《一步之遥》中,以阎瑞生为原型的马走日,是一个“正面人物”,而不是“腐朽堕落”的买办。这是《一步之遥》在历史观上的一个重大修正。
③本雅明并未对“震惊”作条分缕析的界定和分析,相反,这种关于都市现代性经验的概括,分散在他关于波德莱尔的各处论述中,但总的来说,这些论述又是集中而统一的。
④[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等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40.
⑤[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等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45.关于大众,在那些“最早观察它的人”中,本雅明举出了爱伦·坡和恩格斯等人作为例子。在这些人的笔下,大众被描述为机械的、面无表情的、行尸走肉的乌合之众,他们——大众们是可怕的和威胁性的。参见[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等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37-138、142.
⑥[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等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46.
⑦参见米莲姆·布拉图·汉森.大批量生产的感觉: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经典电影(刘宇清等译)[J].电影艺术,2009(5):125-134.
⑧张真.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沙丹等译)[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4.
⑨参见张旭东.本雅明的意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23.
⑩参见吴钩.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平反过程.http://www.21ccom.net/articles/fsyl/yulu_2013082890768_3.html.































——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为例